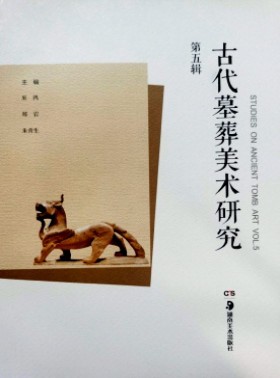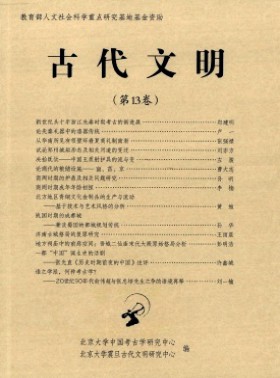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古代飲食文化2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
一、唐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的飲食特色
唐代飲食文化極其繁榮,食物品種繁多,制作過程精細,故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飲食文化專著《食譜》(韋巨源撰),這既是傳統飲食文化的發展,也吸收了各民族的飲食文化。唐代飲食文化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由于北方民族大量內遷,他們以面食為主的飲食習慣推動了麥類作物在南方地區的大面積推廣,以京兆尹為例,大歷三年時京兆府有麥田九十三萬余畝,到開成元年是麥田已經發展到四百萬畝,平均每年增長率為21.63%。在唐代后期北麥南稻作為漢民族的主要結構形成。唐代面食種類大大增加,幾乎現在所有的面食在唐代幾乎都已具備,且日常食用和祭祀都離不開,面逐漸成為北方百姓的第一主糧,這與當時胡食盛行分不開。隨著面食的普及,在主食上,燒餅、胡餅、塔納已成為唐代北方家庭最為普遍的充膳之物,并流行于各個階層,成為一種飲食風尚,白居易《寄胡餅與楊萬洲》詩云:“胡麻餅樣學京都,而脆油香新出爐。寄與饑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當時市間食店多把胡餅當作必備的主要品種。更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不穩,更將搟面杖柱門,何如買個胡餅藥殺著。”蓋譏不北食也。在副食上,唐以前以素食為主,隨著大批以狩獵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內遷改變了這種習慣,《隋書?地理志》載:“梁州……漢中之地;質樸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可見肉食習慣已很普遍,唐代羊肉是最基本的肉類食品,也有專門的產羊區。唐代官府提供給官員的肉食供應也是羊肉“親王每月供給二十頭羊,三品以上每日供給四分羊肉,四品、五品三分”。胡法烹飪的菜肴制作方法以羊肉、奶酪為主料,多用烤炙的方法加工而成。羌煮貊炙,《搜神記》中有記載“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羌煮既發源于西北諸羌的涮羊肉,貊炙即兆端于東胡群的烤全羊,都很受當地百姓歡迎。另外游牧民族常食的各種乳制品也受到唐人的廣泛歡迎,甜乳、酸乳、干酪和酥等食品和烹調術相繼傳入,甚至于在當時成為人們比喻美好事物的象征。北方人食味偏好甜食,“大底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這種南北迥異的食味偏好可能與當時的地理環境有一定關系,北方氣候晝夜溫差大,有利于植物的糖分積累,而北方人長期食用這些食物很容易形成嗜食甜食的飲食習慣。
宋代飲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大大減弱,但宋人在生活中仍大量接觸各種胡食、胡飲,如胡桃(核桃)、胡瓜(黃瓜)、胡餅、胡椒、羊肉、葡萄酒等。甚至極具游牧民族色彩的牛乳也很受歡迎。唐宋兩代北方少數民族飲食習俗基本相似,但唐代飲食文化具有明顯的貴族化色彩,下層廣大平民極少與胡食有緣,而宋代平民化色彩大大增強,較多的反應了宋代普通百姓的飲食生活,唐宋時期形成了多元交匯的飲食局面。此外,北方少數民族的飲食習慣同樣對唐代飲食文化有影響。飲食習俗上,“胡”坐圍食對唐代合食制的形成不無關系。華夏民族一直以禮儀之邦自居,對飲食禮儀有諸多繁文縟節的規定,《禮記•禮運》篇有“夫禮之初,如諸飲食”,專門制定“食禮”一章,用來約束人們的飲食行為。而唐代隨著胡食的引入,北方豪放的飲食風格也逐漸被中原人士所接受,狂飲大嚼,粗放飲食。各種胡曲、胡舞經常出現在唐人的酒宴上,胡人形象“酒胡子”則成了唐人勸酒的酒令工具等等。唐代著名的西域酒及制作技術也傳入中原,相傳唐太宗在宮中釀出八種顏色的葡萄酒,“芳香酷烈,味兼緹縈,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唐代的胡酒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漿和龍膏酒等。著名詩人李白特別愛逛“酒家胡”,“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作”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完全不顧及身份,李白在《將進酒》中也作“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表示粗放到宰牛割羊的地步。胡商進入中原開設食店、酒樓也很普遍,促進了唐代商業的發展。特別是長安,成為當時的國際大都市。食案曲幾變桌椅。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在唐代前后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從以前的席地而坐改為垂腿而坐。這一習慣的改變和十六國北朝時期大量北方游牧民族遷居中原是分不開的。先秦和漢晉時期中國人都習慣于席地而坐,吃飯時飲食器皿也都直接放在筵席上。商周時期的飲食器皿都有高高的腿或器座,戰國以后飲食器皿的高度漸漸趨于低矮,漢代以后就不在使用帶有高足的器皿,這主要是因為食案的出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紛紛內遷,把他們的坐具—胡床帶到中原,胡床是類似于折疊椅的坐具。唐代以后,生活習慣從席地而坐變為垂腿而坐,原來放在枰榻上的靠屏和曲幾演變成為凳子的靠背和圈手,有靠背和圈手的凳子叫“椅子”,沒有靠背和圈手的坐具叫“墩”或“凳子”。案的腿加高,于是改為“桌”。“桌”與“卓”音同字通,《說文解字》釋曰:“卓,高也。”可見桌子命名的原因是比案要高。
二、對唐宋飲食文化的思考
研究中國古代飲食文化史主要是為了具體地總結我國飲食生活的經驗教訓,有助于提高和改善我國人民的飲食生活質量,為當今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借鑒。唐宋時期的飲食生活中,許多優良的傳統值得今天繼承和發揚。從漢代傳承下來的以糧食為主,輔以一定量的魚類、肉類、蔬菜的健康飲食結構,在唐宋時期還在沿用。這種飲食結構,當今全球先進地區基本采用。由于這一時期唐代的兼容并包政策,在飲食上選擇更多,并能滿足更多需求。對于唐宋時期的飲食弊端我們應該吸取教訓,并加以改正。唐代后期就把有益于身體健康的分食制摒棄了,現在大家都推崇合食制,認為合食熱鬧,加深感情,但實際上這種津液交流的合食制非常不利于健康,容易交叉感染。現代人都認為合食是從古就開始的,這種陋習扎根于我國飲食生活,改起來非易事。早在漢代就已出現刻意追求珍奇異食的現象,大量獵殺奇珍異獸。北方游牧民族的飲食始終保持自己的特征,并對中原地區的飲食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瞿宣穎先生說“自漢以來,南北飲食之宜,判然殊異。蓋北人嗜肉酪麥餅,而南人嗜魚菜稻茗,如此者數百年。隋唐建都于此,饒有胡風,南食終未能奪北食之席”。宋代在飲食思想方面,比唐代更注重飲食禁忌和養生。在禁忌方面,蘇軾在《東坡志林》中作“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豬羊,然性嗜懈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銅懈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所求凱,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鹿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在養生方面,蘇軾也在《東坡志林》卷“記三養”中指出“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撰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次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更加注重飲食法。
三、結語
飲食文化,是人類有關飲食實踐的多方面社會經濟內容的各種表現形式的總稱。唐宋盛行胡食是因為善于吸收外來文化,敢于開拓進取的一個側面反映,同時也是與北方諸國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必然產物。今天,我們的飲食文化領域,更是滿園春色,這是經過歷史不斷積淀而成,也是了解歷史的重要步驟。
作者:姚新園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
(二)
一、道教飲食理論的形成與實踐
蕭梁陶弘景一方面繼承了葛洪在服餌術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養性延命錄•食戒篇第二》專門論述了有飲食養生的理論,其中很多觀點流傳至今,婦孺皆知。書中強調“飲食有節”,譬如“養性之道,不欲飽食便臥及終日久坐,皆損壽也。人欲小勞,但莫至疲及強所不能堪勝耳。人食畢,當行步躊躇,有所修為為快也。故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勞動數故也。故人不要夜食,食畢但當行中庭,如數里可佳。飽食即臥生百病,不消成積聚也。食欲少而數,不欲頓多難銷。常如飽中饑、饑中飽。故養性者,先饑乃食,先渴而飲。恐覺饑乃食,食必多;盛渴乃飲,飲必過。食畢當行,行畢使人以粉摩腹數百過,大益也”。又如“食不欲過飽,故道士先饑而食也。飲不欲過多,故道士先渴而飲也。食畢行數百步,中益也。暮食畢,行五里許乃臥,令人除病。凡食,先欲得食熱食,次食溫暖食,次冷食。食熱暖食訖,如無冷食者,即吃冷水一兩嚥,甚妙。若能恒記,即是養性之要法也。凡食,欲得先微吸取氣,嚥一兩嚥,乃食,主無病。”還有“熱食傷骨,冷食傷藏,熱物灼膚,冷物痛齒。食訖踟躇,長生。飽食勿大語。大飲則血脈閉,大醉則神散。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此皆助五藏,益血氣,辟諸病。食酸咸甜苦,即不得過分食。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季不食脾。如能不食此五藏,猶順天理。燕不可食,入水為蛟蛇所吞,亦不宜殺之。飽食訖即臥,成病,背痛。飲酒不欲多,多即吐,吐不佳。醉臥不可當風,亦不可用扇,皆損人。白蜜勿合李子同食,傷五內。”這些觀點都被后來的孫思邈所繼承。并且經過不斷的流傳發展,在唐宋世俗生活尤其是士人階層中深入人心。譬如唐代張皋在《清波雜志》中說“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盛則疾疹作”;郭印說“夜氣若要長存,晚食尤宜減些”;宋代蘇軾也認為“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而不可益寬胃以養神”。此時道門飲食養生的理念已經涵蓋了包括食物的選擇、飲食的分量、時間與禁忌等方方面面的規范,客觀上符合當時社會貧寒百姓的基本維生需要,也能滿足士大夫們修身養性的精神追求,這也是道教之所以能誕生于民間又流行于士紳階層的原由,可以想見,此時道教的飲食理論對各階層群眾日常飲食習慣都頗有影響。
二、與道教有關的飲食風氣與節令食物
道教的影響不斷擴大之時,一言一行都能引起社會風潮。《抱樸子內篇》中提到有服食松脂、菖蒲、茯苓等“仙草靈藥”者能夠童顏長生,民眾紛紛效仿的事例不勝枚舉。適逢亂世,百姓流離失所,衣食無著,或許服食并非出于精神需求而僅僅是生理需要,但由于道教服食術中提到的眾多草藥并不罕見,足以滿足下層民眾“填滿肚子”的謀生需求,因此備受推崇。就連葛洪自己也說,“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可見道門飲食對世俗生活,尤其是歷來被歷史忽視的普通百姓的人生影響之深刻。流行于江浙一帶的小吃烏飯,一名青團,其淵源出自道教齋食青精飯。陶弘景《登真隱決》載:“太極真人青精干石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煑,取汁浸米蒸之,令飯作青色,高格曝干,當三蒸曝,每蒸輒以葉汁溲令浥浥,日可服二升,勿服血食,填胃補髓,消減三蠱。”這是青精飯首次出現在文獻之中。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染青飯”條引《歲零總記》記載:“楊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葉染飯,色青而又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謂之青精干石飠凡飯。”可知青團逐步變為了寒食節的一種時令食物,但其養生滋補之功效依然被認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逐步成型的茶文化。盡管早在西漢宣帝年間王褒所立的《僮約》中已有“烹茶盡具”“、武陽買茶”的記載,但直到唐代,我國第—部有關茶的專著《茶經》才誕生,這說明魏晉南北朝正是由漢到唐飲茶風氣逐步形成的時期。而在這期間,道教與飲茶風氣的形成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晉道士王浮《神異記》中記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邱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余,不相遺也。’因立祭祀。后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陶弘景《新錄》記提到“苦荼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又有如壺居士在《食志》中稱“苦茶久食羽化”。丹丘子、黃山君是傳說中的神仙人物,飲茶可使人“輕身換骨”,可滿足道教對長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追求。另外,茶本性清淡、虛靜,又具有提神療病的功能,自然也會受到意圖修身養性的士紳的青睞,宗教的需求和現實生活的需要得到了完美的結合,進一步推動了飲茶風氣的形成。不僅如此,許多民間習俗中的節令食物也都和道教有關。蕭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中提到“元日,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卻鬼丸。各進一雞子。凡飲酒次第。從小起。梁有天下。不食葷。荊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讀作耐老。柏是仙藥。”屠蘇酒的配方沒有詳細記載,而東晉的著名道士葛洪以細辛、干姜等泡酒,認為食之可使人去除瘟氣。椒、柏,桃等也都是道教推崇的所謂有“仙氣”的食物。而五辛盤則是出于《抱樸子內篇•煉化》“用柏子仁、麻仁、細辛、干姜、附子等分為散,并華水服之。”而豚酒則與《抱樸子》所載“月晦之夜,灶神上天,白人罪狀。”的灶神崇拜相關。百姓為了不讓灶神說自家的壞話,就于“臘日以豚酒祭灶神”。反映了道教和民間食俗之間的生動關系。《歲時記》中還記載了重陽節的來歷:“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費長房,桓景,均為東漢道士。”這一事件流傳開來之后,逐漸形成了一種風俗。而早在東晉,葛洪就在續《西京雜記》中寫道“九月九日配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蕭梁吳均《續齊諧記》也有類似記載。當然,道教與民間習俗擦出火花的例子并不止于此,端午節飲用菖蒲酒、雄黃酒的習俗也與道教丹藥服食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上可見,由其宗教追求而產生的飲食觀念在世俗飲食的產生、傳承和發展中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對本草與食療學的開發
道教自古注重養生,認為合理的飲食可以達到延年益壽,羽化成仙的效果,而在養生家中,又以醫道最為相容,攝生尚玄、醫道同源,兩者相輔相通。自魏晉以來,名醫、藥師多出自道門。而通過醫藥,尤其是食療來達到養生目的,體現了道教飲食對世俗生活最為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葛洪《肘后備急方》(后又有陶弘景作《補闕肘后百一方》),欽定《四庫全書》作序說“其方簡要易得,針灸分寸易曉,必可以救人于死者。為肘后備急方,使有病者得之,雖無韓伯休、家自有藥,雖無封君達、人可以為醫,其以備急固宜。華陽陶弘景曰:‘葛之此制,利世實多’”。他特地挑選了十分常見易得的草藥,如“救中熱暍死方”有“搗菖蒲汁,飲之一、二升”,“干姜、橘皮、甘草,末,少少內熱湯中,令稍稍咽,勿頓多,亦可煮之。”改變了以前的救急藥方不易懂、藥物難找、價錢昂貴的弊病,并且療效顯著,因此深受百姓歡迎。陶弘景隱居山林,深知鄉民缺醫少藥之苦,因此撰寫《名醫別錄》,并與流傳已久的醫書《神農本草經》中原有本草合成《本草經集注》一書,糾正和補充了《本草經》的訛誤和不足。《集注》中的許多藥物都是常見食物。譬如果菜類中有枸杞、菘、葵、李、棗、梨等等。另有《名醫別錄》補證:“薏苡處處有,多生人家,交趾者,子最大實重累者為良,用之取中仁,今小兒蛔蟲病,用根煮汁,糜食之甚香,而去蛔蟲大效。”便是一則食用與藥用價值充分結合的典例。此外,《集注》和《別錄》中還記錄了很多六朝時流入中國的朝鮮藥物,陶弘景也對其藥性進行了研究記錄。唐代著名醫師、道士孫思邈作《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以前醫藥學成就的系統總結,從內容和分類方面體現了對六朝醫學的繼承與發展。首先,食療內容獨立成卷。《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一篇從果實、菜蔬、谷米、鳥獸、蟲魚五類記載了各種動植物的屬性功用,如谷米類第一條記載“薏苡仁味甘溫,性無毒。主筋拘攣不可屈伸,久風濕痹,下氣,久服輕身益力。其根生下三蟲。名醫云:薏苡仁除筋骨中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一名(艸贛),一名感米,蜀人多種食之。”“名醫”即《名醫別錄》。之后,唐代孟詵、張鼎在《備急千金要方》食治篇的基礎上增訂寫成《食療本草》這部食療專著,以類似菜譜的形式記述可供食用、又能療病的本草。其記載仍然保留了道教養生修仙之思想,譬如“黃精”一條記載黃精“能老不饑餌必升天”,“青蒿”一條記載“益氣長發,能輕身補中,不老明目”等等,不一而足。其次,繼承了本草分類法。《集注》的主要成就在于將《本草經》原本把藥品分為上中下三品改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共六品(不包括有名無實的條目),進一步開發和驗證了藥物的屬性。而《千金翼方》的本草卷,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并按玉石、草、木、人獸、蟲魚、果、菜、米谷、有名未用分類,明顯承襲《集注》。自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道教逐步將用于修煉養生的動植物引入到日常飲食范疇之中,為唐宋食療著述的成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反映出道教對醫學尤其是本草和食療方面的深遠作用。
四、總結
總體而言,道教飲食不僅僅局限于士紳貴族服食養性,也不單單只為修煉成仙。道教對自然的鉆研和對生命的熱愛,在民間習俗和飲食醫療之中有著方方面面的體現。可以說中國沒有哪個學派或宗教對個人的生命和日常的生活有如此熱切而積極的關注。它一方面超脫塵世欲念,另一方面又留戀生命,這種以出世之身行入世之事的態度和特點,使道門孕育了眾多杰出的醫者藥師,并在這個“以食為天”的國度中以親民的形式蔓延。尤其在魏晉南北朝這個分裂動蕩的時代,它的存在似乎能讓每一個人擁有生存的希望,更讓道教對中國飲食文化的影響變得深刻而久遠。
作者:蔣湘慧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