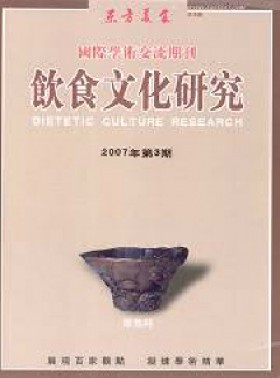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談飲食文化與社會變遷,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食物種類豐富,飲食著述增多
明朝中晚期,隨著美洲新大陸和新航路的發現,各種商品及農作物開始流入中國;繼元之后,飲食風俗有了新一輪的融合與創新,眾多因素的加入,使明末飲食種類變得極為豐富,飲食種類也更加朝精細化、多元化、情趣化發展。玉米、甘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入,以及胡椒、丁香、肉豆蔻的進口瑏?瑦,擴大了食物品種和人們烹調的多樣性。朝萬歷年間人黃正一編輯的《事物組珠》就記載了許多美味的少數民族飲食,如“回回食品”,“女真食品”,“蒙古食品”等等。這些帶有濃厚少數民族特色的食品,豐富了大眾飲食生活。在士大夫群體中,對飲食頗具研究的非張岱莫屬,他不僅各處搜尋美味,“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為口腹謀”瑏?瑧。他還自己動手制作食品,組織“蟹會”。其祖父張汝霖更是組織“飲食社”,以食會友,并寫《饕史》以傳世,張岱在此基礎上整理而成《老饕集》。明朝中晚期作為中國古代史軸上的末世王朝之一,各種總結、整理類的著述頗為豐富,飲食著作也不例外,尤其在士大夫群體中盛行。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外,還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美食家、飲食理論家,如宋詡、高濂、袁宏道等人,以及眾多飲食文化論著問世,最具代表性的有《宋氏養生部》《觴政》《飲饌服食箋》等飲食著作。中國飲食審美思想因此更趨向豐富和系統。
二、飲食趨向享樂化,更加注重養生
明朝中后期,隨著陸王心學的進一步傳播,社會風氣大開,傳統禮制開始受到挑戰。追求享樂、展現真性情成為一股潮流,其中,當屬袁宏道最有代表性,他倡導“真樂”,即要“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瑏瑨?。與其交相呼應的是李贄倡導的“童心說”,倡導人的真情性,明確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強調了人們進行物質享受的合理性,并在輿論上進行宣揚。除此之外,飲食享受更多地表現在與飲食相關的外在的形式方面。據《明宮史》所記載的宮廷內的螃蟹宴:“凡宮眷內臣吃蟹,活洗凈,用蒲包蒸熟,五六成群,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臍蓋,細細用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更令人驚嘆的是各色小吃的做法,如夏季的西瓜膏的做法:“取五月桃花汁、西瓜汁一瓤一絲,灑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瑐瑠?通過對這些食品制作過程生動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在飲食活動中體現著啟蒙思潮中所蘊含的追求真樂人生的情致,這在提高了烹飪的技藝的同時,飲食的文化品味也相應提升。同時,飲食器具也趨于多樣化、精致化;宴飲中地點選擇、歌舞技藝更加挑剔,“妓鞋行酒”在當時蔚然成風。
士人們充分意識到了飲食對于健康的重要性。《內經》云:“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孔子曰:“食能養人,亦能傷人;取樣之道,貴在有度。”管子亦說:“飲食節,則身利而壽益;飲食不節,則形累而壽命損。”明人在此基礎上認識得更為深刻。高鐮認為,“飲食—活人之本也。是以一身之中,陰陽運行,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飲食,故飲食進則毅氣充,毅氣充則血氣盛,血氣盛則筋力強。脾胃者五臟之宗,四臟之氣皆察于脾。四時以胃氣為本,由飲食以資氣,生氣以益精,生精以養氣,氣足以生神,神足以全身,相須以為用者也。”何良俊也認為,“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飲食”,并說出了自己對美食的認識和看法,認為其并非僅為佳肴美味,而是飲食觀念上要注意一些規范和禁忌,如果飲食無所顧忌,就會生病甚至傷及生命。明朝中后期道教思想也頗為盛行,人們對傳統的飲食保健理論頗有心得,在養生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參悟。
三、“虐殺”與反“傷生”
明中晚期士大夫中不乏饕餮之徒,為了滿足口舌之欲而不惜殺生、虐生。如嘉靖、隆慶年間,無錫安氏家巨富,有“安百萬”之號。他專門在家筑一莊,飼養家畜以供膳食。平常養有鴿子數千只,每天宰殺三四只。有時夜半想吃鵝,來不及宰殺,就讓廚子割鵝一肢,以供食用。吃畢,鵝還婉轉未絕。“…至于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灸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今酒席中之羊背皮所謂薦體在元謂之拿,設上賓用之或馬背皮爵,賓用前手后手,鵝則敬胸,今俗敬首,在北人則否也,若貴戚之家有名曰割牲者,以數十金駿馬奚入當堂呈過,一厄丁特利刃飛取其臀肉一商而獻之,以夸豪奢也。”等類似的描述不勝枚舉。這一“虐生”行為,也遭到了一些仁愛之士的痛斥:“以生物多時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不為,況稍具婆心者乎?”?同時他們從朦朧的環境意識方面論述了反對虐殺的必要性。“漁人之取魚蝦,與樵人之伐草木,皆取所當取,伐所不得不伐者也。”
就像劉志琴所認為的,反對“虐生”的提出,是明代的飲食文化中最具有價值的思想之一,也是明清初期啟蒙思潮在社會風俗領域中的反映。他表明人們已經意識到,要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中滿足口腹之欲。同時,飲食倫理中的人文關懷,也從人和人的關系擴展到人與動物的關系?。像大多數王朝一樣,明朝中晚期社會進入比較寬松的時代,農業的恢復與發展,商業城鎮的興起與繁榮,交通運輸新航路的開辟,佛、道、陸王心學的盛行、禮法制度的崩潰等等都為飲食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文土壤;養生、傷生、反虐生交互存在,反映出明朝中晚期復雜的社會現象;腐敗盛行,宴飲無度同樣折射出末代士人在時代潮流的裹挾下追名逐利,耽于享樂,置修齊治平的追求于不顧的末世情懷。但如果從整個中國古代史的角度來看,至明朝中晚期,中國古代飲食文化達到了一個頂峰,飲食文化的多樣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風氣的轉化。正如滕新才教授所認為的,明晚期的消費觀念、消費方式和消費結構的變化,促進了農業的進步、手工業的更加發達以及商業貿易的日益頻繁,從而打破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結構模式,使得社會各階層都與商品市場結成了緊密的聯系,也為“奢能致富”思想的盛行奠定了基礎。
作者:馬玉威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