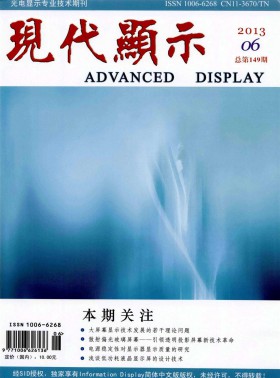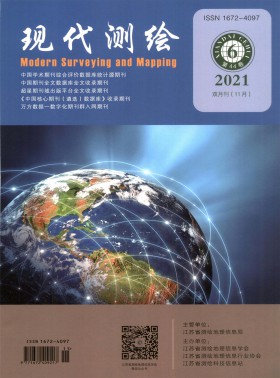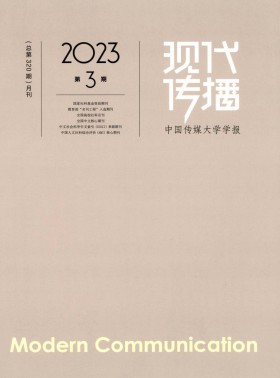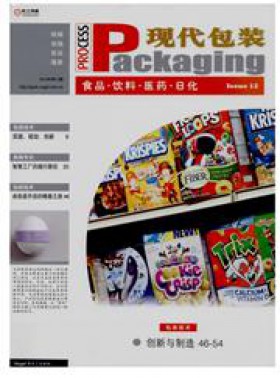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文學語言發展探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的發展史
基于現代語言運動來講,是國民的大眾語言從文言文——白話文——口語的一個轉變過程,白話文從魯迅興起,與今天的口語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是語言發展的畢竟階段,前者為文學語言,后者為形式語言。無論發展指向如何,這都代表了現代語言的發展歷史成果,這種變化取決于社會與文化的傾向與壓力,在不斷的變化運動中不斷的迎合當代歷史。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史是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變革史,最初的開端便是之中的白話文運動,這一活動的興起,主要是由于當時歷史文化以及社會的進步而引發的在這一運動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學革命同現代語言變革二者間的生發與激勵。在使其,雜感文也能夠對具體文學形式發展同文學語言的變遷之間的關系進行體現,以文學這一角度進行觀察,同一般的文學作品相比而言,雖然雜感文本身也存在著對主觀情感的表達以及對客觀形象的再現功能,然而,較之于小說與詩歌等文學體裁來說,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其在對客觀形象進行再現時,經常會體現出概括化以及單一化的特點,并且,在對客觀現象以及具體事實進行描述時,其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闡述一定的議論,從對于語言的特殊要求這一角度進行分析,同時期所進行的語言革命的主要目標之間存在著許多方面的一致性,較之于白話語言在發展過程中的要求,雜感文在語言形式上同時詩歌之間的差異并不十分明顯。與此相比,對于現代詩歌來說,其晚熟的特點也能夠通過對文學形式關系以及語言變革這一角度來進行分析與思考。在現代白話詩歌最初的發展時期,其主要的語言特征表現為暗示、含蓄、抒情以及寓意等,在詩歌的領域之中,由于語言發展的理性化與精確化,抒情詩的情況也要比哲理詩以及敘事詩更加理想,在我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古典詩詞經過不斷地發展,形成了一系列的適用于文言文體系的要求與規范,也在不斷的詩歌創作中,留下了許多富有著豐富內涵且通俗易懂的詞匯,這也使得許多人雖然并不具備著較高的詩歌創作天賦,然而,只要能夠多讀書,多涉獵閱讀一些詩歌,那么,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也將會顯得十分那容易,然而,對于白話詩來說,這一特性顯然不具備,在對詩歌創作時應用白話語言,不存在規定的格律,也不存在短小精悍的典故詞語,這也就無法對其進行應用,甚至可以說,許多詩人在應用白話文進行詩歌創作時,其本身對于白話的語言特性也并不具備十分透徹的了解,這主要是由于當時應用白話文的時間相對較短,絕大多數的人對于白話語言的預警特性以及聲音特性等很難做出準確并全面的研究,因此也可以理解,在的初期,詩歌、小說、戲劇以及散文等諸多文學形式在發展時所存在的不平衡。
二、“雅致的俗語文”
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的發展同文學語言的變遷之間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順應,而是文學自身不斷地通過文學性這一特點對現代語言的發展與豐富起到了推動的效果,從這一角度可以認為,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之中所表現出來的語言自覺情況,不僅在現代語言的“從鬼話到白話,從白話到民眾口語化的運動歷史”這種十分簡單的重復,而是在文言、白話等諸多的語言場域之中自足并自主地垂涎與選擇,在不斷地發展中將文學的語言歷史生成。在諸多的文學形式中,若是仔細地進行研究,均能夠體會出其中所蘊含著的藝術之美,這種美在詩歌這一文體之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表現,詩人在對詩歌進行創作時,不需要對白話與文言進行區分,而是應根據自身所創作的詩歌的形式來對最為合適的文體進行選擇,李金發主要是通過西化的句式以及語法,并應用常人認為十分怪異的修辭方式,并應用白話文與文言文結合的詞語來進行詩歌的創作,以此保證其所創設出的詩歌語言效果具有著陌生化的特點,在不合情理的詞語搭配之中,將一些十分深刻的情理與思考蘊藏在其中,并以此來形成一種在晦澀中蘊含著美感的獨特的抒情風格,王獨與麻穆木天在創作時應用了“純詩”這一改變,并且將印象派的音樂作為參照,對于詩歌的聽覺感受進行強調,保證詩歌在朗誦時能夠給人一種舒適的美感,并且對運動的、音樂的、立體的、理想的以及曲線的詩歌體系進行追求,并且,當白話新體詩這一體裁得到了學術界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之中,其主要的目的是對我國詩歌長期的傳統進行接通,對年深日久流傳下來的遺產進行利用。在事實上,對文言之美進行發現并肯定是現代中國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潛流,其同現代語言變革的大勢所相逆,然而,其往往能夠使得詩歌與白話文體現出許多的雅致,因此,許多的作家選擇回歸文學這一本位來甄別并選擇語言,當前所應用的白話文,是好還是壞都屬于實施對于理論所展開的十分強有力的抗議,并且,在白話文運動的中心,也已經從白話轉移到了文學領域,由以往的文學底白話化轉變成為了如何以白話作為基本的創作工具,樹立起一個豐富的且具有著身后內涵的新時代的文學。究其原因,主要原因則是由于白話過于簡陋與頻發,同文學意境的縝密與反復之間呈現為反比例,無論在哪一個國度之中,都存在著白話與文言之間的區別,因此,對言文進行截然分離所體現出來的問題促使我們應將文學的工具調整的更加現代化與淺顯化,以此來保證其活力與新鮮能夠得到恢復。與此同時,也是的我們必須要對現代語表達出一種成人的態度,或者對某一種問問進行惟妙惟肖地摹寫,想要完全地勝任文學表現的工具,則需要對變化多端的人生進行充分地應對,反而言之,若是當前的白話對于當期那我們所需要的文學工具能夠完全地勝任,或者雖然并沒有達到勝任的效果,我們仍然對這并不符合實際的要求與主張進行實踐,那么到最后,僅僅能夠得到這不幸的也是無法避免的結論:如果不是我們本身所掌握的文學內容過于淺薄與簡單,那么則是這文字內容將會不斷地趨向于淺薄與簡單。在之后不斷發展并完善的現代漢語,從實質上來說,則是經過了歐洲化的白話文,這一種語言經過了對歐洲概念與文法的吸收,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著規范化特點的語法系統,以此使得語言思維的邏輯力量以及表達嚴密與準確性得到了加強,對于我國傳統語言之中所具有的不嚴密、含混以及感性化等諸多的缺點進行了一定的淡化,經過這一改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語言在應用中對于科學的思維能夠更加適應,可以說,這不僅屬于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一個重大進步,從客觀上來說,也使得歐化文法之中精密的文學形式得到了應用與發展。
三、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的構建
索緒爾經過研究認為,對于文學語言來說,其值得不僅是在文學作品之中的語言,更是指對于整體進行服務的,經過培植的非正式的或者正式的語言,因此,從這一角度上來對現代文學語言進行研究可以認為,其同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之中的民族共同語構建存在著十分密切的聯系,現代民族國家所建立的并不僅僅是一個實體,更應該包括語言學、文學以及美學等諸多的想象性建構,以作為開端的語言革命,其對于歷史有著十分重大的貢獻與意義,對于語言革命來說,其所取得的成果必然需要將語言藝術之中的文學作為依賴,并以此進行鞏固,因此可以說,一種新的文學的誕生,能夠產生的意義并不是單單能夠對新文學自身的發展起到效果,這種意義是多方面的。以詩歌作為研究的范例,新詩經過發展,已經從十分僵硬的、沒有新意的舊詩之中得到了解放,并且對于舊詩的各種舒服與規范都完全沖破。將舊的枷鎖進行了沖擊并打破,使得詩本身的生命得到了復活,這對于我國的詩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是脫胎換骨、起死回生的。對于代表著舊的語言方式的古典詩詞同新詩之間的沖突,這對于確立新的語言方式具有著特殊且十分重要的意義,從這一角度對新文學的產生進行思考與研究就可以認為,若是分析其所具有的歷史貢獻,并不需要將其限制在文學這一領域之中,而是屬于反對文言文并對線代表花紋進行提倡的語言革命,甚至可以說,是我國文化從舊走向新的一個歷史性的時代。然而,凡是有利也有弊,雖然其具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性意義,然而,在這一革命之中,也使得中國語言陷入到了兩難的境地之中,為了對科學發展的要求進行適應,語言必須要符合界定性、精確性的要求,然而,想要達到這一目標,則需要將我國傳統語言方式之中所具有的模糊性、隱喻性等具有著文學色彩的特定進行拋棄,若是想要對這一語言風格進行保存,那么,則很難適應科學思維這一要求。在構建民族共同語這一過程之中,作為作家,必然會自覺地對于語言的同一性存在著偏離或者順應,通過語言與文學不同的發展規律進行分析,在文學書寫同民族共同語之間所存在的互構情況,并在共同語同一性實現之后并不會必然地導向文學書寫的語言一體化,對于文學書寫來說,其應該屬于在整個民族語言活動之中一種最具有探險性以及實驗性的部分,其不斷地對民族語言的疆域起到拓展的作用,對民族共同語起到推動的效果,使其在動態中不斷地對新的同一性進行生成。因此,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同文學語言的變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不僅應對已民族共同與構建作為目標的現代語言運動對于文學形勢發展能夠起到的影響進行關注與研究,更需要對中國現代文學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的實際情況投以應有的重視。這是擺在每一個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創作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此外,更需要我們指的注意的是,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都會存在不同的作家,作家的語言實踐在對文學自身起到推動與豐富作用的同時,對于現代語言也能夠起到一定的推動與豐富作用。
四、結語
總的來說,經過現代諸多作家不斷地努力,在當前的社交以及語言的應用中,文言文已經退出了舞臺,在當今許多的文學作品中,白話文已經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并且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與豐富,與此同時,在這樣的發展與豐富過程之中,文學也對自身進行了發展與豐富和深入,并不斷對我國現代文學的傳統進行了創造和革新,使得我國的文學形式不斷地向前發展和豐富。
作者:馬健 單位:渤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