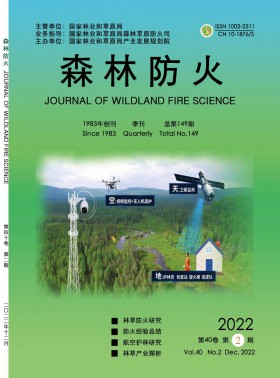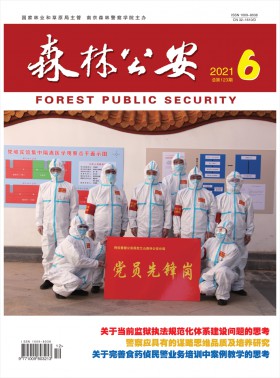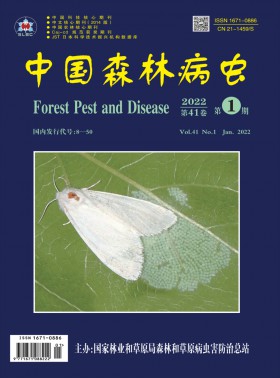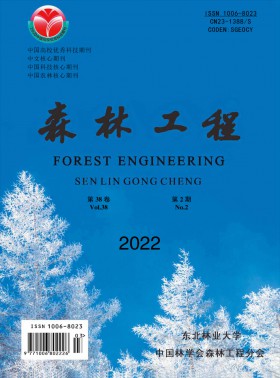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森林民族文化研究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西南地區
解魯云在年已經對云南地區少數民族生態觀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細的梳理和綜述,其成果可資借鑒。許再富等撰著的《熱帶雨林漫游與民族森林文化趣談》一書是進入世紀前我國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該書從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等諸多方面闡述了西雙版納熱帶雨林形成與演變的過程,并分析了自然環境對生活在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響,認為這里民族的種種文化皆與熱帶雨林有密切的聯系。羅蘋闡述了西雙版納地區少數民族的森林風俗和情趣。周鴻等將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稱為神山森林文化,認為這種森林文化體現一種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學,有著深刻的自然保護意義。這足以看出這種獨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發展的意義。吳兆錄等研究發現,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西雙版納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靈為萬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須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生態觀。同時認為這一傳統生態觀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護森林為中心的生產活動中,具體表現為多樣的森林管理傳統,實現了人與自然雙方的和諧相處和持續發展。
尹紹亭通過研究云南少數民族利用森林的傳統方式———刀耕火種,認為當代的刀耕火種是亞熱帶、熱帶山地民族對于其所處生態環境的適應利用方式,是一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許再富以西雙版納為案例,探討了民族森林文化與生物多樣性有效管理之間的關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維持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因素,現代的生物多樣性管理也離不開民族森林文化。周鴻等將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稱為神山森林文化,認為這種森林文化體現一種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學,有著深刻的自然保護意義。楊玉、趙德光則以西南邊疆民族為中心探討了神山森林文化對生態資源保護的作用。西南邊疆各民族在與當地環境的不斷適應過程中創造了以神山崇拜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傳統生態文化模式,它維系了山地農業的生態平衡系統,又保護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種,對西南邊疆的生態資源有重要的保護意義。這足以看出這種獨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發展的意義。蔡磊以貴州省都勻市兩個少數民族村為例,研究了少數民族地區以村規民約為基礎的社區森林資源保護問題。邱寅瑩通過梳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森林資源保護法律體系,通過個案再現守法、執法、法律監督等各個法律實施的具體環節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出現問題的原因和改進策略。劉冬梅等從鐵刀木文化、貝葉文化、龍山文化和稻作文化這四個方面綜述了西雙版納傣族森林文化對當地植物多樣性的積極影響。吳思震總結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態觀,他指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認為“萬物有靈”,把自然和樹林當作一種神秘力量而無限崇敬;對其居住地區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許多保護森林、愛護自然生態的習俗文化;形成積極植樹造林的文化習俗;在森林管理統籌方面以哈尼族“分區育林”與“種子孫樹”文化為典型代表。
關傳友從物質、精神文化兩方面,對西雙版納地區的森林文化進行了初步分析,總結了西雙版納地區的森林文化現象。作者認為物質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蓋食用、衣飾、居住、書寫載體、生產生活工具、樂器等六個方面,精神方面則表現為神林崇拜、神樹崇拜、佛教圣樹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風民俗。雷啟義、周江菊研究了黔東南植物多樣性的原生態文化表現形式,進一步證明了原生態民族文化對植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的積極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態民族文化保護植物多樣性的重要建議。李莉、梁明武以黔東南苗、侗族自治州為案例,從建筑工藝、鼓樓、風雨橋、吊腳樓以及生活、娛樂工具入手考察了這一地區少數民族的物質文化,以及以林業契約、碑刻、林諺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樹神崇拜、民俗民風等精神文化的內容。與貴州、廣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區也是森林茂密、民族眾多的地區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絢爛奪目。由于這一地區從大的地理環境上看可歸入大西南的范圍,故而將其附于西南地區進行討論。學術界對這一地區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陳瑛等探討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設問題,闡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設的有利條件,并從建設軟環境、搞好規劃引導、探索規模經營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四個角度提出了建設策略。劉俊宇、鄒巔闡述了湘西少數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態觀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并在此基礎上挖掘了其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探討了其生態倫理思想的當代價值,特別是在旅游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胡萍、吳萍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四個層次論述了湘西南地區森林民族鮮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這些民族性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應用價值。
2.東北地區
世紀年代,張碧波先生主持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重點項目———“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課題組歷經十年的艱苦奮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繼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論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書一百二十余萬字,以中國北方古代民族為綱,將文化學的內容分別歸入各個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劃分來研究文化的重要實踐,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書中涉及了肅慎、挹婁、勿吉、室韋等東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萬字的《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專題文化卷》,該書打破了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學科界限,將民族學與文化史相結合,并融合文化人類學、歷史文獻學、考古學等諸多學科知識,試圖以更加宏觀和立體的視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學科,對北方區域文化及民族文化進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學的開拓意義。該書內容豐富,涉及了中國古代北方各個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學思想、宗教、神話、習俗、文學、史學、音樂、舞蹈、美術,乃至巖畫、石窟、醫術、科技、軍事、體育等,其中也涵蓋了東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獵、漁撈、采集等與森林息息相關的文化。這部著作填補了我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綜合研究的空白,也標志著“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的最終完成。
上述著作雖然包羅萬象,其中不乏對東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統論述,但首次明確提出關乎東北地區森林民族文化這一概念的是歷史學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東亞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認為:“大興安嶺深處為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所覆蓋,自古以來就有游獵民族生活在這片原始森林深處,至今這里仍保留著一些剛剛定居不久的游獵民族,如鄂倫春、鄂溫克等。在這個森林生態環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獵民族,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及其心理素質方面積淀下來的歷史文化基因為我們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類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會化石。”他的論述可謂深刻。他隨后出版的《鮮卑史研究》更是研究東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鳳超回顧了呼倫貝爾地區森林文化的歷史,指出呼倫貝爾原始林區是北方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搖籃,從古到今,這里生活著鮮卑、女真、蒙古、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等眾多少數民族,創造了燦爛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應繼承森林文化遺產,為呼盟特色經濟服務。為此他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樹立綠色文化觀念,恢復自然生態;第二,合理開發森林資源,大力生產綠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開發森林旅游資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業產業結構。-南文淵指出:東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態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對其森林生態環境的保護和適應,形成了與森林生態系統相協調的生計方式、社會規范、信仰體系和價值觀念。提出傳承森林生態文化,促進城市化發展與建立區域廣大的森林自然保護區相結合,是東北各民族建設生態文明的制度途徑。對東北地區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龍江流域民族歷史與文化叢書》,其中包括張嘉賓的《黑龍江赫哲族》、韓有峰的《黑龍江鄂倫春族》、波•少步的《黑龍江鄂溫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叢書》,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龍江赫哲族文化》、吳天喜的《黑龍江鄂溫克族文化》、韓有峰的《黑龍江鄂倫春族文化》。
這些著作全面介紹了黑龍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歷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張慧平在廣泛搜集資料和專項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運用闡釋學方法及現代多學科知識和理論,對鄂倫春族的民族文化進行了梳理、挖掘和闡釋。作者從鄂倫春族傳統自然知識、人對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學觀念、民俗行為等幾個層面對該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態意識進行了系統研究,并運用唯物主義原理,分析了鄂倫春族生態意識對現代生態意識和生態實踐的支持作用及對林業實踐的現實意義。于佳從音樂的角度對鄂倫春族的森林文化進行了研究,她通過對鄂倫春人、鄂倫春音樂盛事、鄂倫春代表音樂的大量實地調查,解析了鄂倫春民族的森林觀與自然觀,揭示了鄂倫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樂語言特征。通過分析鄂倫春音樂的旋律、節拍、節奏、結構特征來解讀其中蘊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綜述
歷史與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形成發展的,歷史又是廣義上文化的組成部分。森林文化與森林文化史的關系也同樣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與人類的起源、發展相生相伴,對森林文化歷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學者們重要的課題之一。王韓民便較早地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進,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重新認識和發展森林文化對于繼承和挖掘我國燦爛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領域的研究十分顯著,是目前國內森林文化史研究領域成就較高的學者。他依據森林文化的構建主體———人類對森林利用的方式將森林文化的發展時期劃分為六個階段,分別是狩獵與采集文化時期、原始農耕文化時期、封建農耕文化時期、現代農業文化時期、工業與知識文化時期、生態與信息文化時期,并將不同森林文化時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與森林的關系、歷史時期、經濟特征、社會文明、森林藝術形式等八大特征進行了系統歸納,清晰簡潔,一目了然。但新球繼而又分別撰寫專文集中探討了原始社會和農耕時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據考古學研究成果,將原始社會的森林文化劃分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屬、石、木混合四個階段;分析了原始社會不同階段的森林文化藝術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樹木崇拜,樸素的森林生態觀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會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對農耕時期森林文化的闡述中,他首先對農業的起源和農業生產工具的發展做了回顧,進而按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將農耕時期森林文化的發展階段劃分為刀耕火種階段、原始木耜階段、畜牧金屬耜鋤階段和機器耕種階段;按社會形態劃分為原始農耕、奴隸氏族農耕、封建農耕、資本集團農耕和社會合作農耕;按農耕組織形式又可劃分為原始公共合作農耕,氏族公共農耕與氏族集團農耕,奴隸國家農耕,封建地主集團農耕,企業、農莊農耕,合作、股份、個體農耕和工業化農耕。在此基礎上又系統總結并全面分析了農耕時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從文化層次上全面反思了農耕時期的森林資源遭到持續破壞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闞耀平認為森林文化在人類的史前時期、農業化時期、工業化時期體現為材料文化、攝取文化、尋根文化,也對森林文化發展階段作了歸納。
蘇祖榮認為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總是同一定的生產實踐和生產方式相聯系。同農耕社會相聯系的是農耕文化,同工業社會相聯系的是工業文化。而在農耕社會之前,同原始漁獵社會(石器、木器時代)相聯系的則是森林文化,人類在史前曾經歷了一個森林文化階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農耕文化。森林文化的發生發展歷經淵源(漁獵社會)、萌芽、形成、成熟(農耕社會)和拓展(工業社會)等五個階段。蘇祖榮又提出農耕文化之前應有一個森林文化階段。農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個過渡期,而這個過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階段,中華文化是從森林文化中不斷孕育發展而來的,這是因為:中國植被的基本格局決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標志著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類進入石器時代之前,還存在著一個漫長的木器時代;利用林火確證森林文化的存在;構筑木巢也證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飛、嚴耕探討了古代術數活動中的森林利用情況,如以森林樹木的生長情況比附人事的瑞祥災異,一些術數工具為竹木材質,在驅兇避邪的活動中利用林木,重視風水林等。這一系列的對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著豐富的森林文化內涵,這既是原始森林樹木崇拜的遺留,樹種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樸素的生態和諧觀也反映了生態文明視野下傳統文化的別樣價值。李明根據考古發掘材料指出中國的森林文化基因不僅包括東北地區,對東南地區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視。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遺址中便發現了豐富的竹編器物,如竹簍、竹籃、竹席、竹簸箕等。在論證中國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時,還探討了中國森林文化對日本森林文化的影響,指出作為日本森林文化核心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國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文獻典籍中,蘊含著許多與森林文化有關的生態環境思想。
林震、仲亞東認為林業包括森林生態、林業產業、林業思想三個層面的內容,其中林業思想包括林業產業思想和林業生態思想兩部分。根據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林業生態思想可分設天人和諧、森林功效兩方面,林業產業思想又分設林業科技和林務管理兩方面。作者通過對上述四部分進行考察后認為,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了森林的重要價值,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諧、適時而作、樽節愛養的思想。李飛、嚴耕梳理了《左傳》中典型反映中國古代社會樸素的自然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變化及應對的文獻,闡釋了古代生態思想的萌芽,包括陰陽調和、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道法自然、順天則時的生態發展觀,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生態實踐觀。周景勇、李飛分別從動物、植物圖騰崇拜為對象入手,論述了各自圖騰崇拜的特點。動物崇拜許多是以森林中的動物形象為圖騰,先秦時期的人們在崇拜動物圖騰的同時,也帶有濃厚的動物保護意識。植物圖騰崇拜中以山林崇拜為較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時期的人們已模糊地認識到了森林植被與風調雨順之間的特殊關系,山林便被賦予了神靈的色彩,產生了原始的植物圖騰崇拜和植物保護意識。羅美云闡釋了《詩經》中生態和諧思想的幾個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諧、人和自然萬物的和諧、人和社會的和諧。她又提出了《周易》所體現的生態倫理思想主要是一種“和合”思想,具體說來就是天人合一的萬物一體觀、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關系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為當今時代的主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借鑒。周景勇、嚴耕的《試論漢代帝王詔書中的生態意識》首先回顧了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概況,繼而通過對史料中所載之漢代帝王詔書內容的研析,認為其反映出的生態意識包括了如下三個方面: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的生態和諧意識,勸農順時、減刑育物的生態保護意識,假民山澤、鼓勵樹藝的生態經營意識。
作者還進一步對上述生態意識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維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觀念的作用;其二,社會思潮上,受天人感應理論的影響;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農思想和生態意識的影響。馮尕才以清代至民國的甘肅為例,通過研讀地方志等文獻,首先論述了對甘肅森林生態問題的認識,包括了對甘肅惡劣生態環境狀況的認識;對甘肅生態問題形成原因的探討;將近代甘肅災荒頻繁的原因與森林生態環境的惡化聯系起來;把甘肅森林生態問題與黃河、長江中下游歷年水災聯系起來,進而有了通盤考慮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歸國有,林業應該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總結出了近代甘肅森林生態認識的現實意義:其一,提高了人們的生態意識,有助于遏制日益劇烈的濫采濫伐活動;其二,促進了植樹造林、水土保持、防風固沙等活動的展開;其三,甘肅的森林生態問題在西北地區具有普遍性。森林作為重要的資源,在中國古代很受統治者的重視,進而形成了一套對林業的管理機構和制度。夏瑜等從宏觀上系統梳理了中國自先秦至明清歷朝歷代中央生態管理機構的變遷,總結出中國古代中央生態管理機構的特點,即管理工作以利用為主,兼顧保護;生態管理機構持續發揮作用,不斷演進;六部系統生態管理機構不斷成長,最終承擔最主要的管理工作;為皇室服務與管理一般性事務的生態機構長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優勢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共同發揮作用。
余明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分別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各個歷史時期的林政狀況。-李飛、袁嬋研究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林政的管理設置及政策法令。劉錫濤考察了唐代林政和當時植樹造林的綠化活動。胡勇、丁偉對民國初年的林政狀況予以細致考察,就其興起與衰落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總結。關于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問題,也是學術界十分關注的林政問題之一。韓國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辦的變化》、李志堅的《論明代商人對皇木的采辦》《明代皇木采辦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營建采木述略》、陳季軍的《明清時期黔北皇木采運初探》、馮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時期四川官辦皇木研究》、袁嬋等的《明清皇木采辦及其影響》-等文從皇木采辦的背景、原產地采伐及運輸流程、儲藏、機構設置與官員管理、影響及弊端等諸多領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討和闡釋。長期以來,森林文化也是中國古代文人墨客吟詠贊嘆的對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筆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獨特的山林情趣。閻景娟考察了作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為地賦予了意義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著民族文化的集體記憶,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語法,幫助我們塑造和評判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李元從文化史的視角梳理了中國古代植物文化的的發展史,進而將其與中國古代士人聯系起來,認為士人階層是推動我國古代植物文化演變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變過程中完成對士人階層的反塑造。劉雪梅總結了中國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審美情趣的內容,即游具古樸而超凡脫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閑雅的情趣、游賞品味山林景象的詩意神韻情趣,并分析了這些山林情趣對當今森林文化建設及森林旅游業發展的價值。她又通過研析中國古代文獻典籍,闡述了古代隱士文人的生活形態,即學術研究,文化傳承;稼穡伐樵,樂在田園;縱情山水,逍遙閑適;清靜寡欲,修道養生。
三、關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幾點體會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縱觀近三十年來學界對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論問題,還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鄉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國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森林文化產業發展等諸多領域,已呈現出多維度、多視野的研究態勢,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無疑是舉足輕重的。學者們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無論是從宏觀上還是從微觀上都有不少建樹,特別是微觀上,學者們以我國兩大森林民族聚居區———西南和東北地區森林民族為案例,對其民族性、生態倫理觀、民風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諸多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別是對其時代價值和如何呼應時代訴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經初步實現了多學科合作、多維度分析,林學、生態學、生物學、環境學、歷史學、經濟學、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視角多樣。對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樣令人矚目,學者們將森林文化與人類的進化與發展緊密相扣,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發展史的壯觀畫面,尤其是有學者提出在石器時代前還有一個漫長的木器時代,農耕文化產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時代,這些論斷可謂振聾發聵。一些學者還通過研讀中國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國古人與森林有關的生態環境思想,這無疑大大豐富了中國思想史的內涵。也正是因為這些生態環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統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對森林十分重視,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學,學者們對這些問題也給予了必要的關注,值得肯定。
目前學界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對森林民族文化還缺乏整體性的研究,學者們的著眼點主要集中在某個地區、某一個或某幾個民族身上,缺乏從大的地域范圍乃至全國進行宏觀視域下的研究。其二,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論建設,特別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與民族學理論有機結合起來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學者們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與森林有關的內容,缺乏從民族學的角度給予更加理論化的論述。其三,缺乏對東北與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對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國主要聚居于東北和西南地區,兩個地區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氣候環境,創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學者們多是將兩個地區的森林民族文化作為兩個獨立的個體進行研究,缺乏將其進行橫向的對比。如若能夠從宏觀和微觀上分別對比兩大地區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將有新的發現,創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對于東北地區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遜色于西南地區。作為同處于森林覆蓋率較高的東北地區,古往今來也生活著諸多森林民族,他們所創造的燦爛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學者給予關注。
雖然先有張碧波主持的“中哈爾濱學院學報年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產生了一批有價值的著作,后有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龍江流域民族歷史與文化叢書》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叢書》,但對該地區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將其作為部分章節進行了論述的,尚缺乏專門系統的闡釋,關于這方面的論文數量也遠少于西南地區的研究成果。最后,對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關注不夠。學者們多是以現代民族為案例進行研究,對于古代文獻及考古發掘資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還缺乏足夠的關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學科、多視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與現實的聯系方面也還有巨大的深化空間,這是學者們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的觀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體是廣袤的原始森林,他們生于斯長于斯,對森林生態環境充滿敬畏,許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護森林生態環境的內容。隨著人類對自然界的開發,特別是進入工業時代后,時代經濟在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嚴峻的環境問題,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生態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動物瀕危甚至滅絕等,人類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態環境危機。因此,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們對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樹立保護植被、保護環境的觀念,讓綠水青山重回我們的家園,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其次,有利于豐富民族學理論,完善民族政策。通過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使我們更加細致地了解了森林民族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這些與森林相伴相生的民族內心世界,這些內容大大豐富了民族學的理論和內容,為我國繼續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等一系列民族政策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最后,有利于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促進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森林不僅孕育和催生了農耕文明,并長期與其相融共生,與工業文明也同樣相互滲透。在新的歷史時期,森林民族文化為適應時代的發展和訴求,也被賦予了時展的意義,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森林民族文化資源的利用價值也在不斷提高。通過深入挖掘森林民族文化的內涵和價值,能夠將其轉化為生產力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造福當地。同時,對森林民族文化的弘揚也順應了我國當前文化建設這一時代課題。許多森林民族文化在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已經瀕臨消失,為了保存這些民族文化的記憶,豐富新時代文化的內涵,我們應該采取措施努力保留并延續這些珍貴的森林民族文化根脈,這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王禹浪 王俊錚 陳志剛 單位:大連大學 蘿北縣林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