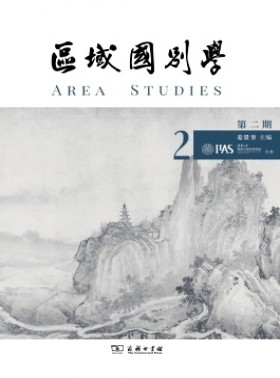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區域文化研究問題,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區域文化的學理千頭萬緒,本文選擇區域文化的概念界定、內涵要義及其與主流文化關系的三個最基本的問題進行討論,認為:區域文化的區域界定隨著區域劃分的變化而變化,其中既有行政區域亦有自然區域和文化區域;區域文化的內涵要義主要包括特性和共性、自守和開放、獨立和包容、內涵和外延四個對立統一關系;區域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系主要有源與流、根系與主干、基礎與主導的關系。
關鍵詞:傳統文化;區域文化;主流文化;中原文化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各地區自主性社會經濟建設和旅游產業開發的加強,傳統區域文化日益受到重視,也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從現有的開發、建設和研究狀況來看,區域文化百花齊放,研究成果層見疊出,不計其數,但尚有幾個最基本的重要問題值得繼續關注和深入探討。本文略談淺見,以陳一家之言。
一、關于區域文化的概念界定問題
區域文化雖已是一個非常流行的熱門詞語,但對它的概念界定,則仍是眾說紛紜,亦不十分清楚。區域文化亦稱為地域文化,顧名思義是一種與某一地理區域相關的文化,或產生形成于某一區域內,或覆蓋流行于某一區域,即區域文化是區域的產物,以區域為依托,而作為區域文化依托的區域是有歷史變遷和不同范圍之分的,與此相應亦不斷有新的區域文化出現。從歷史變遷方面來說,區域文化隨著區域劃分的變化而變化。我國早期的區域文化是淵源于以中原地區為生活范圍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時代的中原文化,這是當時皇權統治范圍內的總體文化,后來隨著皇權和國家版圖的擴大,中原成為一個區域,中原文化亦成為一種區域文化。到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興起,如“秦”、“晉”;“燕”、“趙”;“齊”、“魯”;“巴”、“蜀”;“楚”(“荊楚”);“吳”、“越”等,均有以各諸侯國為稱謂的區域文化產生,或以一國為名,或以兩國為名;這些諸侯國雖然在秦朝以后不復存在,但作為以各自的地理人文為基礎而形成的區域文化因素則延續了下來。自秦朝以降,由于國家版圖的擴大和行政區域劃分的變化,又有許多以行政區域為依托的區域文化的產生,比較典型的有嶺南文化、西域文化、湖湘文化、關東文化、閩臺文化等。到了近代以后,隨著新政權區域和新型獨立性大城市的產生,又產生了一些新的區域文化,如港澳文化、中共革命根據地文化、上海文化(或稱海派文化)等。從區域范圍方面來說,區域文化有大小區域之分。上述所提到的那些區域文化均可謂是大區域文化,都包括現在的一個省以上的地區。此外,在這些大區域文化之內還有眾多的中小區域文化,它們雖有同一大區域文化的共性,但亦因有不同的地理人文環境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小區域文化。如越文化中之東越(閩越)文化、南越文化、浙東文化、浙西文化;嶺南文化中有廣府文化、潮汕文化、香山文化;荊楚文化中的荊襄文化;吳文華中的蘇南文化等。有的論者認為,區域文化不能以行政區域進行劃分,而是以人文狀況的不同特性進行區分,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可絕對而論,應該是兩者均可。從上述所列舉的大區域文化幾乎都是以行政區域為范圍的,中原文化和戰國時期以各諸侯國為范圍的文化,在其產生之時都是以皇權及諸侯國的統治區域來劃分和定名的,只是到了這些統治區域消亡以后,其延續下來的文化在后續朝代里才不再與新的行政區域完全復合,但仍有一定的關系。上面所列舉中小區域文化中則兩種劃分狀況都有。純粹以人文狀況的不同特性進行區域文化劃分,實際上更主要的不在于區域文化的劃分,而在于文化區域的劃分。區域文化與文化區域雖有一定的內在關系,但兩者還是有區別的。區域文化的劃分主要是從它的產生源頭上進行劃分,其后來因自身行政區域的擴展或因影響力的擴散等原因而擴大或覆蓋到其他地區,則是其發展壯大的表現,但這不是普遍的情況。而文化區域的劃分,則主要是指以不同的區域文化來劃分地理區域,即以某一區域文化為主體文化的地區范圍,這種文化區域既有與本行政區域相吻合的,也有跨越本行政區域的,后者的形成是某一區域文化形成之后,因其影響力所及而覆蓋到本行政區域之外的其他地區,并成為該新覆蓋地區的主體文化,從而將該新區域納入到本區域文化之中。因此,從區域文化的產生發展過程來說,在其形成之后,特別是在近代之后,某些區域文化隨著其自身的發展和行政區域劃分的變化,它與行政區域就不完全相一致了。區域文化和文化區域這兩種概念,都是區域文化研究所需要注意和包含的。當然,也有完全以脫離行政區域而完全按地理特性來劃分的區域文化。如以江河進行劃分者,古已有之的黃河文化、江南文化、江右(江西)文化,新近提出的長江文化等;以山脈進行劃分者,古已有之的泰山文化、華山文化,新近提出的黃山文化等;以方位進行劃分的,大者如東夷文化、西域文化(西部文化),小者如浙東文化、浙西文化、蘇南文化、蘇北文化、閩南文化等。此外,亦有論者認為區域文化屬于傳統文化的范疇,這當然言之有理,但亦不可絕對化。區域文化的形成都經歷過較長的歷史過程,并在區域社會中沉積和延續下來,存在著一定的傳統性,因此也是一種傳統文化,這是區域文化的大多數狀態。這一傳統的時間應該可長可短,長者自不待論,短者如近代以后產生形成的一些區域文化,它盡管歷時不久,并在時代性上屬于現代文化的范疇,與一般意義上的傳統文化有所不同,亦有獨特性的文化存在,不能把它排除在區域文化之外。即使時形成時間更晚,傳統性更少的區域性文化,它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有特殊意義區域文化,也是有研究價值的。其實幾乎所有大小、新舊范圍的行政區域或自成一體的自然區域都蘊藏著自己特有的文化因素,只是特性、影響大小不同,或是否為人所知而已。那些已為人所知曉的區域文化,無論哪個、哪種區域文化,都是由人總結和提倡的,被認知和提倡較早,且特性較強、影響較大者則成名較早、名氣較大;被認知和提倡較晚,且特性較弱、影響較小者則成名較晚、名氣較小。其他尚未成名者,有的尚待發掘,有的意義不大。現在各地都在加強區域文化的發掘和研究、保護,涌現了無數的區域文化,基本上均是循著這些原理而提出的,但其內涵尚有待進一步探索。
二、關于區域文化的內涵和要義問題
首先是區域文化的特性和共性問題。各個區域文化由各自的地理人文、風土人情、政治經濟等因素而構成,自有各自的內容、形式和精神,因而各有差異和特色,也就是所謂區域文化的特性。揭示、總結和傳承區域文化的特性和社會作用,使之具有一定的學術和社會價值,應該說是區域文化研究和建設的最主要目的。但是有些不同的區域文化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因素和精神,特別是相鄰和相屬的區域文化之間。如吳文化和越文化,兩者所依托的地理人文環境相差很少,其文化差異也很少,古籍《越絕書》有記載說:“吳越為鄰,同俗并土”,“同氣共俗”,甚至被認為是“同源同出”,因而該兩者也被合稱為“吳越文化”。又如齊文化和魯文化,亦是產生于齊和魯兩個相鄰的諸侯國,兩國同處東夷之地。開創之時,周朝以姜子牙分封齊國,以周公旦及其子分封魯國,齊行道家和法家之術,魯行周禮和儒家之術,形成幾近對立的兩種文化。但后來,隨著管子、孟子、荀子相繼在齊國引用和宣講儒學,使儒學和儒家文化漸入齊境,融入齊文化之中,出現了兩國合成的齊魯文化。其他戰國時期產生的幾個區域文化亦有類似的情形,如秦文化與晉文化合稱“秦晉文化”;燕文化與趙文化合稱“燕趙文化”;巴文化與蜀文化合稱“巴蜀文化”。至于這些大區域文化內的小區域文化,則同源于一個大區域文化,更具有共性因素。研究區域文化的特性和共性各有其要義意所在,揭示區域文化的特性,旨在呈現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彩、多元并進;揭示區域文化的共性,旨在說明中華文化的聯結紐帶、多元共處。其次是自守性和開放性問題。區域文化既有區域的范圍界限,又有地理人文等的特定條件,那么它的存在自有一定的限定性,《穀梁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說:“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這種區域的限定性也就基本決定了區域文化的限定性。一般來說在它形成以后,其基本范圍和內涵即處于相對固定和穩定的狀態,具有一種相對封閉自守的性質,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為一種傳統。特別是相隔距離較遠、風土人情差異較大的區域文化之間,其各自封閉自守性就更大,基本處于互相隔絕的狀態,即所謂“作秦越之視”,不相往來。但是區域文化已有開放的一面,因為文化是由人創造的,人的移動就會帶來文化的移動。自古以來,各區域之間并不限制人的移動,當一個區域有外區域的人進入時,就會把外區域的文化帶入。當這種外區域移入人數達到相當規模,或有重要的文化人物移入時,就會在這一區域內出現和形成移入者所帶來的外區域文化,這種現象一般在每個區域文化中都有存在。在歷史上,這種不同區域之間的人口和文化人物的移動是相當頻繁的,各區域文化之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象亦頗為普遍,甚至有人口大遷徙而產生獨成一系的新文化圈,如嶺南、閩臺、江右(江西)、巴蜀文化區域中的客家文化。到了近代以后,在許多大城市中,伴隨著大量移民而出現的這種文化的跨區域存在更為明顯。區域文化自守性和開放研究的各自要義在于,前者有助于認識其形成傳統的緣由,后者有助于認識其發生變遷的緣由。再次是獨立性和包容性的問題。區域文化的自守性和開放性,也就決定了它具有獨立性和包容性。就獨立性而言,區域文化自守在自己的區域范圍內,以自己所在的區域為根本所在。因此,它與其他區域文化之間雖有一定的聯系,但沒有依存關系,而是獨善自處,自成體系。盡管各區域文化中都會有外部文化的進入,乃至融入,然而這些外來文化大多不能改變其固有文化的根本和主體。即便是客家文化這樣有較久歷史和較大影響的文化,也只是散落在各相關區域中,成為所在區域中的一派文化,或許可以成為其聚居地的一個很小的區域文化,但沒有成為其所在大區域的文化根本和主體而形成一個集中的區域文化;已有的相關研究也多取民系文化和聚落文化的角度,而未見有從區域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的。又如上海這樣一個近代形成的移民城市,其文化根本和主體仍是本土文化,即便是其中人口和勢力最大的寧波人和廣東人也不能以浙東文化或嶺南文化作為上海文化,而只能融入其中,成為上海文化中的一派或一個元素。就包容性而言,區域文化因其開放性而使各區域文化之間得以互相交流和互動,乃至彼此容納。上述的戰國時期形成的大區域文化的分而合一,以及客家文化的產生、上海文化的形成,都是區域文化包容性的明顯表現。區域文化獨立性和包容性研究亦各要義所在,前者以凸顯其獨特性,后者以透視其可融性。最后是內涵和外延問題。區域文化既有自己的獨特性和開放性,自然就會有其內涵和外延的存在,其獨特性由內涵得以顯示,其開放性由外延得以反映。所謂內涵,就是各區域文化中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和因素,主要是指它的本體文化,應包括它的區域范圍,以什么標準劃定;內部結構,如地域結構、文化因素結構、民系結構;基本特點,有什么有別于其他區域文化的核心文化和基本特點;主要精神,形成了何種獨特的精神氣質;歷史影響,在歷史上發揮過怎樣的社會作用。所謂外延,主要包括各區域文化所輻射的外流文化和它所保留的外來文化。外流文化是指本區域文化流入其他文化區域的文化,其中有的被同化或融合,有的則未被同化或融合而獨立存在。這種獨立存在的外流文化,雖仍保留著本區域文化的特質,但已不在本區域的范圍之內,不能再作為本區域的文化,而把它作為本區域文化的外延比較合適。外來文化,是指進入某一文化區域內而未被同化或融入的外部文化。與外流文化相應,這種外來文化雖從區域概念來說它已是本區域文化中的一種文化,亦與本區域文化建立了一定的關系,但仍保持著其原來的特質而獨立存在,因而不能把它作為本區域的文化因素,而只可作為本區域文化的外圍文化或寄生文化。這種區域文化的外延,類似于客家文化,是隨著人口的流動而散落到其他文化區域中的,亦具有民系文化或聚落文化的特性。區域文化的內涵和外延的研究的各自要義所在是,前者有助于反映區域文化的具體內容和要素,后者有助于認識區域文化的交流和互動。
三、關于區域文化與國家主流文化的關系問題
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大,區域眾多,使區域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同時中國自古便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雖有更代換朝、版圖張縮、離亂分合,但統一是基本態勢,因而亦自古存在著相應的國家層面的主流文化。因此,中華文化中既有區域文化亦有主流文化,兩者關系如何是中華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問題,也是區域文化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問題,其中至少包含下述兩個方面:一是區域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淵源關系。從國家的產生和形成過程來看,國家以區域為構成部分和基礎,并隨著國家版圖的擴大而有更多的區域并入其中,這些區域在國家產生和擴展之前已經存在,即先于國家而存在,但在國家產生和形成之后則被劃分為各個行政區域而得以強化。與此相應,附著于區域的區域文化,其最原始的成分亦在國家產生之前已經存在,在國家及其行政區域產生之后得以強化和建造。同時,國家產生之后,為著統治所屬的各個區域,也會采取某些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為主的主流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區域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有一種互相孕育關系。一般來說,在原始時期先有區域文化后有主流文化,此后則互相共育。形成和主宰夏商周三代的作為最早中華文化主流的中原文化,它是在先前已經存在的分布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各族團區域文化,并吸收融合長江流域的各區域文化的精髓而形成的。此后,隨著國家版圖的擴展和中原人口的四向擴散,中原文化被傳播到東南西北的各個區域,并與當地的土著文化相結合孕育出當地的區域文化。這些新生的區域文化,因流入的主流文化因子不同和土著文化的差異而孕育出各別的區域文化,戰國時期各不相同的各諸侯國文化,都由周文化不同因子和各地土著文化結合的結果。如作為春秋戰國時期三大文化派別的儒家、道家、法家文化,都是這樣產生的。其中的儒家文化所以在魯國產生,與周公旦及其兒子引周禮治魯有著直接的關系,使孔子在繼承周禮的基礎上始創了儒學。此外,這兩者之間也存在著源流關系。一般來說,區域文化是源,主流文化是流。這不僅是因為:區域文化先于主流文化而存在,而且還因為區域文化直接植根于基層和民間;而主流文化不僅建筑于區域文化之上,而且承載著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治國之道,它必然會隨著國家統治者及其治國之道更替和時代變遷而不斷改變。秦漢以后歷代的主流文化,或出自廟堂或出自民間,且大多出自民間,亦即出自區域文化;近代以后還增加了外國文化的來源。如作為中國古代社會2000多年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分別淵源春秋戰國時期的魯文化(魯國孔子)、齊楚文化(齊國姜子牙、楚國老子)、齊魏文化(齊國管仲、魏國李悝)等;作為宋代以后興起并成為士大夫治國治家新理念的理學則創自湖南人周敦頤;作為明末清初流行并成為洋務派思想源頭的經世致用思想出自吳越文化(浙江的黃宗羲、江蘇的顧炎武,另有湖南的王夫之);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則出自嶺南文化(孫中山)。由此可言,區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系,主流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枝干主干,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二是區域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肉靈關系。區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構成部分,猶如人的各部肢體;主流文化中華文化的引領者,猶如人的靈魂。沒有區域文化就沒有中華文化,也不會有主流文化;沒有主流文化,區域文化就只能是一盤散沙,甚或互相打架,不能得到協調和整合,不能形成整體性的中華文化,也不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如由于中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產生、擴散和延續,使各區域文化中有了共同的基因,有了形成共識的基礎。主流文化還因其具有較強的時代適應性、主宰性和先進性,對區域文化有著引領作用,使之明確發展和前進的方向。由此而言,區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礎,主流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導,各有功用,互為依存。基于上述思考,在區域文化研究中必須同時兼顧主流文化,既避免區域文化研究的孤立化和碎片化,也避免主流文化研究的無根化和片面化。
作者:虞和平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