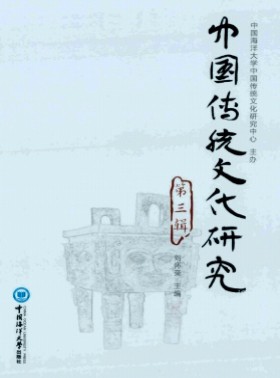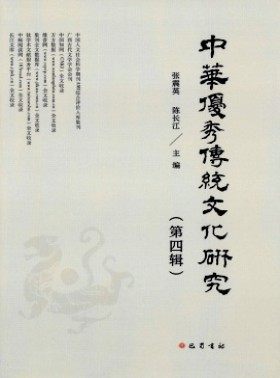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傳統(tǒng)文化生態(tài)思想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蒙古族宗教觀念中的生態(tài)意識
自然崇拜、宗教信仰作為人類原初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起源于原始初民對自然的懵懂無知和對自然力無法控制而產(chǎn)生的驚異、敬畏或困惑的心理。薩滿教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是蒙古族等阿爾泰語系諸多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其宗教基礎是萬物有靈論。在薩滿教的原始觀念中,天地、宇宙、人事都是由無法預測的神力掌控的。此外,薩滿教認為,草原、山川、江河、樹木等均由各自的神靈掌管。所以,在薩滿教的自然觀中,自然是有目的、有意志、有思想、有各種魔力的人格化體系。在這個人格化體系中,這些神靈都具有神奇的力量,掌控著宇宙時空的升沉禍福。如果人類虔誠地敬奉并愛戴它們,它們就能夠保佑人類;如果人類忤逆、違背它們的意愿,它們就會降災于人類。而且,在神靈和人類之間,還可以通過交流來傳達彼此的心愿或想法,這種相互溝通的媒介是通過祭祀來完成的,而薩滿就是完成人神之間溝通的神職人員。原始先民通過各種各樣的祭祀禮儀,表達他們對神靈的敬畏、敬重,以期獲得神靈的庇護。同時,通過祭祀,他們也把神的旨意送達人間,用以表示神靈也會關注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告誡人們要約束自己的行為,善待生靈,否則,就會遭到神靈的懲罰。因而,薩滿教的萬物有靈論能夠時時勸勉或告誡人類虔誠地善待自然、愛護自然。這樣,人類就成為虔誠的生態(tài)保護論者,如同后藤十三雄所說:“化生萬物的太陽、水和大地,對他們來說,恐怕不是所謂自然的抽象觀念,而是切身感受到了太陽、水、大地的偉大力量,因而對它們都抱有一種神秘的情感。”久而久之,這種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世界的思維和神秘的情感就轉化為先民的原始信仰。信奉薩滿教,篤信萬物皆有靈魂、深信靈魂不滅的蒙古人,把自然看作衣食父母和守護神,對其加以呵護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久而久之,就會形成良好的生態(tài)保護意識并傳承下去,生生不息。蒙古族認為,廣袤的大地是動植物繁衍生息的根基。因而,蒙古族非常敬畏和愛戴土地之神,一切玷污和破壞土地的行為都要受到譴責和懲罰,其原因就是怕惹怒神秘力量,導致災難降臨。這對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維護和修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蒙古族敬畏自然、敬重生命的生態(tài)意識,在他們祭拜天地、神山、圣水等各種習俗中也有集中體現(xiàn)。例如,蒙古族在飲酒時都要祭天,后來,這種祭天習俗逐漸發(fā)展為祭神山、祭敖包、祭神樹等。在蒙古族先民的思維里,高山丘陵等突兀之處都充滿了神秘感,它是神靈居住的地方,是部落的保護神,也是通向天堂的幸福之路。對神山的祭祀膜拜,有很多禁忌。正是這些禁忌,使得蒙古族先民們不能肆意破壞自然。羅布桑卻丹在《蒙古風俗鑒》中曾說,如果祭祀湖泊,就不允許人們吃湖泊里的魚;如果祭山,就不允許折損山上的一花一果、一草一木。土地崇拜、神山崇拜逐漸演化為祭敖包。牧民把敖包看作是神靈居住的地方,“每方土地都有各自的‘精靈’———蒙古語叫‘土地之主’在居住,被認為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敖包也是蒙古族經(jīng)常祭拜神靈、表達心愿的場所。敖包一般設在草原上地勢開闊、風景秀麗的高山丘陵之頂、突兀之處或是要道之旁,它一般用石頭堆砌成圓塔形的小山,頂端插著一根長竿,竿的頂端系著各種寫有經(jīng)文的布條。每年盛夏之際,虔誠的牧民從各處聚集,奉獻犧牲(對牧民來說,祭敖包時供奉的犧牲是返還給造物主的),舉行祭祀儀式。儀式由薩滿主持,既要感謝自然神靈恩賜各種豐饒之物,又要向天地神靈祈求風調雨順、牧草茂盛、牛羊肥壯。可以說,在蒙古族的心目中,敖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從蒙古族先民流傳下來的習慣法規(guī)定,敖包是禁地、圣地,不準在敖包腹地破壞草木、掘土開墾、圍堵狩獵。如若有人侵犯禁地,不遵守習慣法,將會受到各種重罰,甚至會付出生命。這種敬畏自然、敬重生命和神靈的祭敖包儀式,不斷影響并鑄造著蒙古族牧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方式,使蒙古族心存善念和感恩之心。愛惜生命、尊重生靈、熱愛草原、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客觀上起到了保護自然、關愛生命的作用。
二、蒙古族天葬儀式中回歸自然的生態(tài)智慧
海德格爾說:“只要此在生存著,它就實際上死著。”即人是向死而生的,有生即有死,有死即有生,生命的完整性體現(xiàn)為生與死的輪回過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在生前設計好死后的喪葬方式。因而,對于人類來說,喪葬方式和人的誕生同等重要,甚至在原始先民看來,人的死亡比出生更令他們困惑和好奇。也正是這些令人不解的問題,促使先民非常重視喪葬儀式,希望親人死后可以投胎轉世,靈魂可以升入天堂。為此,舉行各種喪葬儀式進行祭奠。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喪葬方式因受各自生產(chǎn)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宗教信仰、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而各式各樣,它透射出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國家和民族對生死存亡、靈魂轉世、生命輪回的認識與體悟。受自然天惠極少的蒙古族牧民,因受到蒙古高原干旱少雨、土地貧瘠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及其特有的游牧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影響,形成了本民族獨特的喪葬儀式。蒙古族的喪葬儀式中最具代表性和富含生態(tài)意蘊的是天葬,它折射出蒙古族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珍愛自然、回歸自然的生態(tài)智慧。這種智慧包含著天人合一、天人共存的思想,維系了人與自然唇齒相依、血脈相連的關系,對本已脆弱的蒙古高原生態(tài)環(huán)境起到了緩解和調適的作用。如今,蒙古族天葬雖然伴隨著現(xiàn)代化的推進和草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日益惡化漸漸遠離人們的生活,從而成為一種追憶,但回憶歷史、追尋美好生活所給予我們的各種啟示,卻是令人深思、意味悠遠的。就像荷爾德林所說的那樣:“萬物親密地存在,我如何表達謝意?要在深刻地考驗之際去把握。”對此,海德格爾說:“考驗必須透徹。必須使固執(zhí)之心屈服,使之消隱。”“通過反反復復的傾聽,我們將變得更有傾聽能力,但也會更加留意那種方式。”蒙古族天葬的精粹在于它的世界觀、價值觀,及其在生產(chǎn)生活中的應用。傳統(tǒng)的蒙古族天葬是將死者的尸體以白布裹身,面孔朝天,蓋上一塊寫有經(jīng)文的白布,放在荒郊野外,讓鷹、野狗、狼等食肉動物吞食。三天后,死者親屬前來查看,如果尸體被鳥獸吃得所剩無幾,就說明死者前世積德行善、樂于助人,死后靈魂借助鳥獸升天,同時也預示著子孫將獲得吉祥福壽;如果死者的尸體未被野獸吞食或吞食得很少,就被認為死者生前罪孽尚未消除,連鳥獸都不愿以其果腹,這時,死者親屬就請喇嘛誦經(jīng)超度,替死者懺悔、贖罪,同時在尸身上灑黃油或酒,直到骨肉尸身被野獸果腹,才認為對死者已盡心意。這一點與藏族的天葬是類似的,只是在具體細節(jié)上略有差別。隨著蒙古族生存方式和生活環(huán)境的變遷,其喪葬儀式逐漸失去了自身獨具的特點,和其他民族的喪葬儀式逐漸趨同,墓(土)葬、火葬逐漸成為主要方式,而天葬逐漸淡出歷史舞臺。那么,在蒙古族游牧文明所承載的傳統(tǒng)生產(chǎn)生活方式中,為什么會出現(xiàn)天葬儀式?它與蒙古族傳統(tǒng)的游牧生產(chǎn)生活方式具有哪些內在的關聯(lián)呢?其一,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其天葬儀式產(chǎn)生與傳承的文化根源。蒙古族信仰薩滿教,其至高無上的神靈長生天與蒙古族原始先民的“狼圖騰”崇拜有著須臾不可分的內在聯(lián)系。蒙古族先民認為,狼是長生天派遣到人間的使者。按照蒙古族薩滿教信仰觀,人死后,靈魂盡快歸天轉世是一件既重大又吉祥的事情。狼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是會飛的,當狼把人的尸體吃掉,天葬才算圓滿完成。蒙古族天葬的產(chǎn)生,既與其先民的原始信仰有關,也與藏傳佛教所宣揚的靈魂不滅、輪回轉世的思想有關。對于蒙古族民眾來說,不論是作為捕獵對象的禽獸,還是保證生存與發(fā)展需要的家畜,既然都是由具有神力的自然賜予的,那就要對自然無私的賜福饋贈表達謝意,以自己死亡之后的身體進行天葬來回饋自然,就是一種向神靈表示感謝的現(xiàn)實舉動。對大自然、長生天恩賜的每個動物,無論獵物還是家畜,“僅僅意味著是偶然的死,而求其生則是永恒的希望”。當人類的生存與動物的生存發(fā)生矛盾時,蒙古族人選擇人類的利益,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決不會像當今一些人那樣毫無憐憫之心,將動物的生命視如草芥,趕盡殺絕或將其看作為人類服務的工具。蒙古族牧民或狩獵民會帶著深深的歉意與動物對話、交流,以求得動物的理解、原諒,并懷著敬畏之心,舉行各種儀式,以此表達歉疚之意。其二,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和草原食物鏈的動態(tài)平衡,是蒙古族天葬儀式得以實施和傳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一個由自然地理環(huán)境、動植物和人構成的復雜系統(tǒng)。在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中,肉食動物、草食動物與草地資源之間能否實現(xiàn)食物鏈結構的良性循環(huán),直接關乎整個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及其功能的穩(wěn)定和良性發(fā)展。肉食動物通常處于草原生態(tài)食物鏈頂端,它們不僅以草食動物為食,也食腐肉。蒙古高原上大批肉食動物的存在,是蒙古族天葬得以實施、延續(xù)的重要保障,它使得天葬的亡者尸體被它們叼食腹中,避免尸體腐爛,發(fā)出濃烈腐臭味,滋生繁衍有害細菌,傳播疾病、瘟疫,危及動植物良性發(fā)展及草原生態(tài)。其三,蒙古族自古天成的游牧生產(chǎn)方式是其采用天葬儀式的社會動因。自公元8世紀以來,蒙古氏族開始西遷,進至斡難河和怯綠連河(今蒙古國鄂嫩河和克魯倫河)流域,游牧氏族形成游牧部落,游牧生產(chǎn)方式借此產(chǎn)生。蒙古族“逐水草而遷徙”的游牧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了蒙古族先民不會選擇砍伐樹木制作棺槨,以破土挖坑、修造墳墓的形式來安葬死者。其原因是,這既不符合蒙古族民俗法規(guī),也會破壞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態(tài)植被;再者,對于“逐水草而遷徙”、沒有固定居所、奔波忙碌的蒙古族先民來說,從遙遠的地方騎著馬或趕著勒勒車長途跋涉去祭拜亡者,既不合理,也不現(xiàn)實。蒙古族天葬是蒙古族傳統(tǒng)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具體體現(xiàn),它包含著人與自然渾然一體、休戚與共、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思想。這種喪葬方式,既保證了草原食物鏈的良性循環(huán),促進了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利用和發(fā)展,又消除了修造墳墓、火葬等喪葬形式給草原帶來的諸多不良后果。需要說明的是,草原游牧人除了飼養(yǎng)家畜謀生以外,還獵殺一部分動物為食,所以,蒙古族牧民認為,人死之后以自己的皮囊肉身喂以鳥獸果腹來回報自然萬物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這種喪葬方式看似不合人情常理,甚至有些殘酷無情,實則蘊含著人與自然萬物水乳交融、和諧共生、生命同根同源的生態(tài)大智慧。當然,這種生命覺解的大智慧絕不是對各種區(qū)別的消融,而是與區(qū)別于自身的異己之物的共屬一體,即“奇異化之運作、畏懼之要求”,是一種對自然無限恩賜的感恩和回饋。
三、蒙古族民規(guī)民約、習慣法規(guī)中珍愛自然的生態(tài)理念
在蒙古族民規(guī)民約、習慣法規(guī)中處處體現(xiàn)著蒙古民族珍愛自然、熱愛生命的文化理念和生態(tài)思想。對于生活在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來說,自然就是衣食父母。也正因為此,在與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做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jīng)驗,形成了自身的獨特文化,也形成了對自然的特殊感情。蒙古族牧民可以根據(jù)地形地貌來判斷牧草的疏密、青草的發(fā)芽情況、水源情況,新生的幼畜在哪個位置可以躲避風雪、抵御風寒,甚至可以根據(jù)土地所散發(fā)出來的氣味來辨明方向和地理位置。蒙古族懂得過度放牧會危害牧場,草場的好壞和水資源的狀況直接關系到人畜的生存安危。蒙古族牧民每年必須輪換牧場數(shù)次,由于冬季不備干草之故,必須調整移動路線,一般冬季就停留于家畜容易獲得野生枯草和水源的合適場所。如果不長年逐水草而遷徙,那么,草場就會被牲畜啃光而無法休養(yǎng)生息,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就會被破壞,牧民們就無法生存,這就是殘酷的生存辯證法。因而,蒙古族很早就形成了很多有關草原、山川、河流、樹木等自然保護的習慣法、成文法。人們都自覺遵守,自覺維護,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它使得蒙古族自然保護習俗傳承至今。元代以后,有關環(huán)境保護的習慣法、成文法逐漸在蒙古社會廣泛推行。如在《黑韃事略》中就曾有“遺火而炙草者,誅其家”的記載。由于北方草原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生活在這里的蒙古人非常愛惜水源,不準以任何方式玷污水源。為了表達對水神的敬仰之意,成吉思汗的“大扎撒”曾規(guī)定春夏之季,禁止人們在河流中洗涮、便溺,不得用金銀器皿汲水,以免引起電閃雷鳴。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jīng)Q定了他們和自然環(huán)境相互依賴、休戚與共的關系。1251年,當蒙哥稱汗之時,便昭告天下:不允許各種生靈和非生靈遭受苦難;不準用騎行、馱用重物、絆腳繩和打獵等方式折磨家畜,使家畜疲憊不堪;要讓天上飛的、水里游的、草原上跑的禽獸免遭獵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脅;要讓大地不為樁子和馬蹄的敲打所打擾。北元時期的《阿勒坦汗法典》也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規(guī)定。這充分體現(xiàn)了游牧文明獨特的自然觀、價值觀和生態(tài)理念。
四、結語
概而言之,蒙古族所賴以生存的草原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以游牧業(yè)為主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了其生產(chǎn)生活方式必須全面考慮草原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承載能力,否則,將會制約游牧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牧草資源、水資源和畜群資源是游牧民族的生命線,它直接關系到游牧民族的興衰,而生態(tài)保護意識的形成和傳承直接關乎牧草資源、水資源和畜群資源的優(yōu)劣好壞、興衰枯榮。蒙古族正是以適應自然規(guī)則和人類挑戰(zhàn)而產(chǎn)生的游牧生產(chǎn)生活方式,使自己生生不息。即使從現(xiàn)代科學的角度看,游牧生產(chǎn)生活方式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在環(huán)境的保護和資源的利用上具有自己的獨特優(yōu)勢。
作者:包桂芹 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