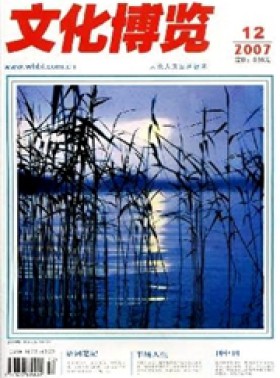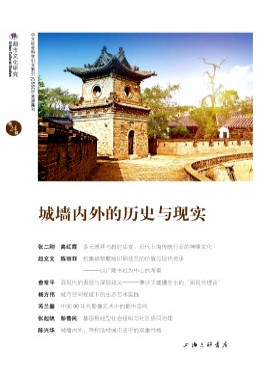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編精選了8篇文化翻譯論文范例,供您參考,期待您的閱讀。

翻譯理論下中西文化論文
1.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與翻譯
中西方所處的地域、地理環(huán)境和自然條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語(yǔ)言的產(chǎn)生與人們的勞作和生活是息息相關(guān)的。英國(guó)作為一個(gè)島國(guó),通過(guò)航海認(rèn)識(shí)了世界,因而生活中有許多習(xí)語(yǔ)源自于航海業(yè)。如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奮力圖存)中國(guó)自古就是農(nóng)業(yè)大國(guó),以耕田為主,常有“像老黃牛一樣干活”、“氣壯如牛”等詞;與中國(guó)文化不同,馬在英美國(guó)家文化中則是吃苦耐勞的象征“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as a horse”。中國(guó)屬于典型的大陸性氣候,中國(guó)人認(rèn)為“東風(fēng)”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與此相反,英國(guó)人對(duì)“西風(fēng)”有好感“東風(fēng)”在他們看來(lái)是凜冽刺骨的寒風(fēng)。
2.歷史文化差異與翻譯
歷史文化指由特定的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中沉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個(gè)重要文化就是習(xí)語(yǔ)。習(xí)語(yǔ)包括成語(yǔ)、諺語(yǔ)、格言、典故、俗語(yǔ)、和俚語(yǔ)。比如英語(yǔ)中的“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直譯為“一塊石頭打死兩只鳥(niǎo)”,而漢語(yǔ)卻說(shuō)成“一箭雙雕”或“一舉兩得”,德語(yǔ)說(shuō)成是“一個(gè)拍子打死兩只蒼蠅”。我們漢語(yǔ)中的春夏秋冬,英語(yǔ)俚語(yǔ)是根據(jù)景物,候鳥(niǎo)表示季節(jié),cuckooing(布谷催耕)意謂春、swallow(燕子)意謂夏、wildgoose(大雁)意謂秋、plum alone(梅花獨(dú)放)意謂冬。
3.風(fēng)俗文化差異與翻譯
風(fēng)俗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和交際活動(dòng)中,各民族的風(fēng)俗習(xí)慣形成的文化。比如在待人接物,打招呼時(shí),中國(guó)人習(xí)慣說(shuō)“你吃了嗎?”“上哪去?”“干嘛去?”表示一種親切感和關(guān)心,但是西方人會(huì)很尷尬,覺(jué)得是在打聽(tīng)他的隱私。在西方,打招呼通常只是說(shuō)“hello”“Morning”比較簡(jiǎn)單的打招呼。再比如說(shuō)對(duì)于顏色的認(rèn)知,西方比較注重科學(xué)理性的教育和科學(xué)態(tài)度。常用客觀事物的具體顏色來(lái)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義。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紅色(red)主要指鮮血(blood)顏色,所以red使西方人聯(lián)想到“暴力”和“危險(xiǎn)”從而產(chǎn)生了一種顏色禁忌。著名漢學(xué)家霍克斯在翻譯“紅樓夢(mèng)”時(shí),意識(shí)到red可能會(huì)使英語(yǔ)讀者聯(lián)想到“流血”,所以采用小說(shuō)原用的書(shū)名《石頭記》,譯為T(mén)he story of the stone。中國(guó)文化中的顏色內(nèi)涵和象征意義十分豐富,而且顏色詞的象征意義是多元的。中國(guó)文化中的紅色源于太陽(yáng),如烈日如火,其色赤紅。所以喜慶的日子會(huì)常用紅色。
4.宗教文化差異與翻譯
兒童文學(xué)翻譯分析
0總述 兒童文學(xué)翻譯與其它文學(xué)翻譯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不但要考慮中西文化差異,還需考慮成人與兒童在價(jià)值觀、理解、和審美等方面的差異。國(guó)內(nèi)對(duì)兒童文學(xué)翻譯的研究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一直被忽視。筆者對(duì)十年間的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進(jìn)行分析,以歸納出其中變遷。 1研究方法 筆者對(duì)1999年至2008年十年間發(fā)表的共69篇相關(guān)論文進(jìn)行分析,其中期刊論文39篇,碩士學(xué)位論文30篇。 2分析與討論 分析數(shù)據(jù)顯示出以下兩點(diǎn):(1)兒童文學(xué)研究的數(shù)量有所提高。(2)兒童文學(xué)研究覆蓋各領(lǐng)域。 2.1總體趨勢(shì) 在1999年至2008年間,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數(shù)量大幅提升,筆者以五年為一個(gè)時(shí)段進(jìn)行劃分。數(shù)據(jù)顯示,在前五年,僅有2篇期刊論文涉及該題材,而在后五年則有37篇,占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的期刊論文總數(shù)的93.78%。在研究生學(xué)位論文方面,前五年,僅有1篇學(xué)位論文涉及該題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發(fā)表,占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的學(xué)術(shù)論文總數(shù)的96.67%。據(jù)統(tǒng)計(jì),95.65%的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均在后階段完成。 2.2研究?jī)?nèi)容 筆者將所分析論文歸為五類:時(shí)段研究、譯者研究、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個(gè)案研究、總體描述,其中個(gè)案研究與其它分類偶有交集。數(shù)據(jù)顯示:大部分學(xué)者關(guān)注于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其次為個(gè)案分析。 2.2.1時(shí)段研究 著重于兒童文學(xué)翻譯時(shí)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塊: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較。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中國(guó)早期的兒童文學(xué)翻譯是以成人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并非以兒童為受眾,但這時(shí)期引入的國(guó)外兒童文學(xué)奠定了中國(guó)兒童文學(xué)的基礎(chǔ)(吳雪珍,2007;陳麗嬌,2007;趙國(guó)春,2006)。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中國(guó)真正引入國(guó)外兒童文學(xué)是在五四之后,這時(shí)的兒童文學(xué)翻譯開(kāi)始注重兒童的興趣、價(jià)值觀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榮華,2007)。還有學(xué)者對(duì)五四前的兒童文學(xué)翻譯內(nèi)容和技巧進(jìn)行了比較(張道振,2006;桂念,2006;楊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譯者研究 一些學(xué)者對(duì)知名兒童文學(xué)譯者展開(kāi)了研究,如魯迅、周作人等。這些研究從譯者角度展開(kāi),如譯者眼中兒童文學(xué)翻譯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認(rèn)為兒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認(rèn)為更應(yīng)關(guān)注兒童語(yǔ)言(張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譯理論和策略 在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中,學(xué)者們應(yīng)用了多種翻譯理論和策略對(duì)兒童文學(xué)譯作進(jìn)行了分析,如美學(xué)和接受美學(xué)、接受理論和兒童本位等。鑒于兒童文學(xué)翻譯的受眾是兒童,譯者需要更多去考慮兒童的視角,學(xué)者們多從兒童認(rèn)知、智力和價(jià)值觀角度對(duì)作品進(jìn)行了分析。在翻譯策略方面,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翻譯的異化和同化,基本上認(rèn)為同化更為適合兒童文學(xué)翻譯。秦君和應(yīng)承霏認(rèn)為異化應(yīng)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則用于語(yǔ)言(秦君,2006;應(yīng)承霏,2007)。 2.2.4個(gè)案研究 數(shù)據(jù)顯示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的個(gè)案覆蓋不同國(guó)家和時(shí)期的作品,其中《愛(ài)麗絲漫游奇境》的譯本最受青睞,其它被研究的經(jīng)典兒童文學(xué)譯作有《安徒生童話》、《快樂(lè)王子》等,也不乏現(xiàn)代兒童文學(xué)譯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盡管具體的研究譯本具有顯著差異,研究結(jié)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譯、兒童本位等(秦君,2006;楊丹屏,2006,張代蕾,2006)。 3結(jié)論 在1999-2008年間,兒童文學(xué)翻譯研究的數(shù)量顯著增長(zhǎng),在后五年尤為明顯,2004-2008年間的相關(guān)期刊論文和碩士學(xué)位論文占研究總數(shù)的95%以上。越來(lái)越多學(xué)者開(kāi)始關(guān)注兒童文學(xué)翻譯,包括時(shí)代變遷、譯者、翻譯理論和策略、個(gè)案分析等,但個(gè)案分析的對(duì)象范圍較窄,多為經(jīng)典兒童文學(xué)作品翻譯。兒童文學(xué)翻譯有著其獨(dú)特的屬性和價(jià)值,通過(guò)上述研究能夠?qū)Ξ?dāng)下中國(guó)的兒童文學(xué)翻譯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漢英翻譯人才培育方式
一、全球化與“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 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fā)展,中國(guó)同世界其他各國(guó)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遺憾的是,我們?cè)谖幕敵龇矫孀龅貌⒉焕硐搿?ldquo;如果這種文化輸入和文化輸出的局面長(zhǎng)期繼續(xù)下去,勢(shì)必會(huì)造成西方文化對(duì)我國(guó)的影響越來(lái)越大,而我國(guó)的文化在世界影響越來(lái)越小,久而久之,很可能造成我國(guó)文化的民族特色越來(lái)越模糊,甚至逐漸失去民族文化的獨(dú)立性,在東西文化趨同過(guò)程中被融合乃至消亡。”(包惠南、包昂,2004:序言)基于“文化逆差”現(xiàn)狀,中國(guó)政府在不同場(chǎng)合強(qiáng)調(diào)了要實(shí)施“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總書(shū)記在2003年12月5日召開(kāi)的“全國(guó)宣傳思想工作會(huì)議上”要求我們“大力發(fā)展涉外文化產(chǎn)業(yè),積極參與國(guó)際文化競(jìng)爭(zhēng)。”2004年6月,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在北京召開(kāi)了“中國(guó)文化企業(yè)走出去研討會(huì)”,就中國(guó)文化企業(yè)如何才能走出去并在國(guó)際市場(chǎng)站穩(wěn)腳跟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研討。 二、“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背景下我國(guó)對(duì)漢英翻譯人才的需求 為貫徹“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我國(guó)政府和相關(guān)部門(mén)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國(guó)外開(kāi)設(shè)“孔子學(xué)院”、舉行“中國(guó)文化年”、召開(kāi)世界漢語(yǔ)大會(huì)、主辦“漢語(yǔ)橋”演講比賽等等。在所有的措施中,其中重要的一項(xiàng)是漢籍英譯,中國(guó)外文局支持的“向世界說(shuō)明中國(guó)”的《大中華文庫(kù)》(漢英對(duì)照版)翻譯出版工程、全國(guó)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辦公室設(shè)立的“中華學(xué)術(shù)外譯項(xiàng)目”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漢籍英譯需要大量合格乃至優(yōu)秀的漢英翻譯人才。自明末清初至上世紀(jì)末,漢籍英譯大多由西方譯者完成。但是,近些年來(lái),越來(lái)越多的學(xué)者意識(shí)到,漢籍英譯既需西方譯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國(guó)翻譯家勇挑重?fù)?dān)。中國(guó)譯者都是土生土長(zhǎng)的中國(guó)人,長(zhǎng)期浸潤(rùn)在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語(yǔ)境當(dāng)中,翻譯時(shí)能夠從語(yǔ)言層面和文化層面正確理解原文,做到忠實(shí)傳達(dá)原文內(nèi)容、尤其是忠實(shí)傳達(dá)原文中的文化成分;西方譯者英譯中國(guó)文化典籍可能還有其他的目的,再者由于受自己所處文化立場(chǎng)和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影響,翻譯過(guò)程中會(huì)有意識(shí)地進(jìn)行跨文化操縱,結(jié)果導(dǎo)致中國(guó)文化經(jīng)典在翻譯過(guò)程中的扭曲和變形。但是,目前中國(guó)合格的漢譯英人才十分缺乏,高端的漢譯英人才更是寥若星晨。針對(duì)這種現(xiàn)狀,中國(guó)譯協(xié)副會(huì)長(zhǎng)、國(guó)際譯聯(lián)理事及副主席黃友義先生呼吁中國(guó)教育界抓緊時(shí)間、花大力氣培養(yǎng)更多合格的中譯英人才,以便承擔(dān)起漢籍英譯這項(xiàng)歷史性的任務(wù)。 三、漢英翻譯人才培養(yǎng)的幾點(diǎn)建議 筆者結(jié)合當(dāng)前中國(guó)外語(yǔ)院系英語(yǔ)專業(yè)的翻譯教學(xué)現(xiàn)狀,提出以下幾點(diǎn)建議。 3.1 英語(yǔ)專業(yè)設(shè)置“漢譯英”課程 根據(jù)穆雷教授(1999:33-38)的調(diào)查,盡管國(guó)內(nèi)幾乎所有的外語(yǔ)院系都將翻譯列為英語(yǔ)本科階段的一門(mén)必修專業(yè)課,但課時(shí)數(shù)有限。筆者調(diào)查了省內(nèi)外一些兄弟院校的外語(yǔ)院系英語(yǔ)專業(yè)的翻譯教學(xué)情況,發(fā)現(xiàn)由于受總課時(shí)數(shù)的影響,大部分外語(yǔ)院系的英語(yǔ)專業(yè)只在大三學(xué)年開(kāi)設(shè)一個(gè)學(xué)期的翻譯課,約32-36個(gè)課時(shí)。在這有限的課時(shí)內(nèi),有些教師只講授“英譯漢”;有些教師則既講授“英譯漢”,又講授“漢譯英”。很少有外語(yǔ)院系的英語(yǔ)專業(yè)獨(dú)立開(kāi)設(shè)“漢譯英”課程。要想培養(yǎng)合格的漢籍英譯人才,為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開(kāi)設(shè)“漢譯英”這門(mén)課程很有必要,通過(guò)為學(xué)生講解漢譯英基本理論和技巧,為他們的漢譯英能力打下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因此,外語(yǔ)院系的英語(yǔ)專業(yè)在進(jìn)行課程設(shè)置時(shí),應(yīng)該考慮到“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背景下我國(guó)對(duì)漢英翻譯人才的需求,獨(dú)立開(kāi)設(shè)“漢譯英”這門(mén)課程。 3.2 加強(qiáng)學(xué)生翻譯能力培養(yǎng) 現(xiàn)在,許多英語(yǔ)專業(yè)的學(xué)生畢業(yè)走向社會(huì)后,面對(duì)一個(gè)個(gè)漢譯英翻譯任務(wù)時(shí)要么顯得束手無(wú)策,要么翻譯出來(lái)的英語(yǔ)譯文錯(cuò)誤百出,令外國(guó)人看得如墜云霧。這些都是因?yàn)樗麄冊(cè)诖髮W(xué)期間翻譯能力沒(méi)有得到有效的培養(yǎng)所致。英語(yǔ)專業(yè)漢譯英教學(xué)過(guò)程中,教師除了應(yīng)該向?qū)W生講授基本的翻譯理論外,尤其應(yīng)該注重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翻譯能力,因?yàn)榉g能力是一名合格的漢英翻譯人才的必備素質(zhì)。教師在翻譯教學(xué)過(guò)程中應(yīng)該注重培養(yǎng)學(xué)生的雙語(yǔ)能力、百科知識(shí)能力、翻譯策略與技巧能力、翻譯技術(shù)能力以及交際能力。首先,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漢英雙語(yǔ)能力是根本,因?yàn)闈h英雙語(yǔ)能力是確保譯文準(zhǔn)確和通順的必要條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國(guó)內(nèi)的外語(yǔ)院系大多忽視了培養(yǎng)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的漢語(yǔ)能力,因此,教師在翻譯教學(xué)過(guò)程中應(yīng)向?qū)W生強(qiáng)調(diào)漢語(yǔ)對(duì)于翻譯的重要性,要求學(xué)生在課外多讀一些可以提高漢語(yǔ)水平的書(shū)籍。其次,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百科知識(shí)能力也不容忽視。翻譯家不但得是個(gè)“專家”,還得是個(gè)“雜家”。合格的漢英翻譯人才必須具有寬廣的知識(shí)面,對(duì)中西文學(xué)、歷史、藝術(shù)、政治、文化、經(jīng)濟(jì)等各方各面的知識(shí)都要有所涉獵。再次,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能力也至關(guān)重要。一名合格的漢英翻譯人才應(yīng)該精通并能夠靈活運(yùn)用一些常用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教師在漢譯英教學(xué)過(guò)程中,應(yīng)該向?qū)W生講解異化和歸化、全譯和變譯這些基本的翻譯策略,告訴他們什么時(shí)候采取異化翻譯策略、什么時(shí)候采取歸化翻譯策略、什么情況必須全譯、什么情況最好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譯手段。再者,應(yīng)該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翻譯技術(shù)能力。近十年來(lái),隨著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自然語(yǔ)言處理技術(shù)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各種各樣的計(jì)算機(jī)輔助翻譯工具層出不窮,如機(jī)器翻譯軟件、電子語(yǔ)料庫(kù)、在線詞典、桌面排版系統(tǒng)、本地化工具、搜索引擎、網(wǎng)上百科全書(shū)和網(wǎng)上報(bào)刊雜志等等,有效使用它們可以大大提高翻譯效率。美國(guó)學(xué)者Angelelli就曾經(jīng)指出,“能否熟練地使用翻譯工具,是翻譯新手和資深之間的一大區(qū)別”(肖維青,2011:44)。教師在漢譯英教學(xué)過(guò)程中應(yīng)該向?qū)W生介紹這些常用的計(jì)算機(jī)輔助翻譯工具。最后,也是最值得強(qiáng)調(diào)的是,應(yīng)該培養(yǎng)學(xué)生的交際能力,如如何與客戶談判、和其他譯者合作、恪受翻譯職業(yè)道德等。教師在翻譯教學(xué)過(guò)程中應(yīng)向?qū)W生強(qiáng)調(diào)翻譯職業(yè)道德的重要性,促使學(xué)生樹(shù)立嚴(yán)守翻譯職業(yè)道德的意識(shí),培養(yǎng)出德才兼?zhèn)涞膶W(xué)生。#p#分頁(yè)標(biāo)題#e# 3.3 改善翻譯教學(xué)模式 長(zhǎng)期以來(lái),國(guó)內(nèi)英語(yǔ)專業(yè)翻譯教學(xué)都是沿襲傳統(tǒng)的翻譯教學(xué)模式:首先由老師向?qū)W生講授基本翻譯理論與技巧,然后給學(xué)生布置翻譯練習(xí),最后對(duì)答案。這種傳統(tǒng)的翻譯教學(xué)模式以教師為中心、以糾錯(cuò)為主要教學(xué)手段、以教師向?qū)W生傳授翻譯知識(shí)和翻譯技巧為終極目的,存在如下幾個(gè)弊端。首先,不能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的主觀能動(dòng)性。傳統(tǒng)翻譯教學(xué)模式中,教師處于“中心”和“主導(dǎo)”地位,學(xué)生只是被動(dòng)地接受知識(shí),主觀能動(dòng)性得不到發(fā)揮。其次,教學(xué)方法缺乏現(xiàn)代翻譯技術(shù)的參與。最后,學(xué)生翻譯實(shí)踐機(jī)會(huì)不多。翻譯水平的提高是以大量的翻譯實(shí)踐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翻譯教學(xué)中,除了教師平時(shí)布置的少量課后練習(xí),學(xué)生很少有機(jī)會(huì)進(jìn)行其它的翻譯實(shí)踐活動(dòng),這就造成了學(xué)生的翻譯理論同翻譯實(shí)踐脫節(jié)這種“致命傷”。正是由于以上傳統(tǒng)翻譯教學(xué)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學(xué)生的翻譯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培養(yǎng)。近年興起的建構(gòu)主義翻譯教學(xué)理論可以解決傳統(tǒng)翻譯教學(xué)的許多弊病。建構(gòu)主義翻譯教學(xué)理論提倡用“學(xué)生中心”替代傳統(tǒng)翻譯教學(xué)的“教師中心”,其指導(dǎo)性原則是“讓學(xué)生在真實(shí)情景中,在專業(yè)人員指導(dǎo)下自主學(xué)習(xí)、合作學(xué)習(xí)與外界環(huán)境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互動(dòng),進(jìn)而獲得翻譯經(jīng)驗(yàn),發(fā)展翻譯能力。它具有以下幾個(gè)突出的特點(diǎn):(1) 基于項(xiàng)目的學(xué)習(xí):從練習(xí)轉(zhuǎn)移到實(shí)踐(Project-based learning: From practiceto praxis); (2) 提倡重視翻譯實(shí)踐的課堂;(3)教師是翻譯項(xiàng)目的管理者,是學(xué)生的示范者、鼓勵(lì)者和幫助者;(4)學(xué)生的目標(biāo)是培養(yǎng)翻譯能力、自信和專業(yè)行為。顯而易見(jiàn),建構(gòu)主義教學(xué)范式在注重學(xué)生與外部環(huán)境互動(dòng)和個(gè)體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構(gòu)建、發(fā)揮學(xué)生的能動(dòng)性上具有積極意義”(薄振杰、李和慶,2011:79)。在建構(gòu)主義翻譯教學(xué)理論的指導(dǎo)下,教師在翻譯教學(xué)的具體操作過(guò)程中可以采取“基于真實(shí)翻譯項(xiàng)目的過(guò)程教學(xué)法”,即將真實(shí)的翻譯項(xiàng)目引入到翻譯教學(xué)過(guò)程中,從而將翻譯練習(xí)轉(zhuǎn)變?yōu)榉g實(shí)踐,增強(qiáng)翻譯教學(xué)的真實(shí)性。例如,筆者將本校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承擔(dān)的學(xué)校所在地市政府的英文網(wǎng)站建設(shè)項(xiàng)目引入到漢譯英翻譯教學(xué)過(guò)程中,將整個(gè)翻譯教學(xué)過(guò)程分為“確定翻譯項(xiàng)目—分配翻譯任務(wù)—小組翻譯—班級(jí)討論—翻譯評(píng)估”五個(gè)階段,很好地培養(yǎng)了學(xué)生的各種翻譯能力,取得了比較好的教學(xué)效果。 此外,教師可以很好地利用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畢業(yè)論文撰寫(xiě)這個(gè)環(huán)節(jié)。目前國(guó)內(nèi)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畢業(yè)時(shí)都需要用英語(yǔ)撰寫(xiě)畢業(yè)論文,選題大多集中在文學(xué)、文化、語(yǔ)言學(xué)、翻譯等方面。其中翻譯又是一個(gè)熱點(diǎn)選題范圍。例如,筆者所在學(xué)校的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的畢業(yè)論文中,每年翻譯選題約占了論文總數(shù)的30%。由于學(xué)生數(shù)眾多,每年翻譯選題中都會(huì)出現(xiàn)重復(fù)現(xiàn)象,至于不同屆學(xué)生之間的重復(fù)選題現(xiàn)象則更加普遍。此外,由于太多的學(xué)生以翻譯為選題,導(dǎo)致論文內(nèi)容陳腐,很少有新意,且許多學(xué)生的論文存在抄襲現(xiàn)象。凡此種種,導(dǎo)致學(xué)生的畢業(yè)論文流于形式。因此,筆者建議:對(duì)于對(duì)翻譯感興趣的學(xué)生,可以要求其將一篇長(zhǎng)度和難度適中的中文文章翻譯為英語(yǔ),并就翻譯過(guò)程的某個(gè)問(wèn)題寫(xiě)一篇1000英文詞左右的評(píng)論。這樣既避免畢業(yè)論文流于形式的弊病,又可以在翻譯過(guò)程中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各種翻譯能力。 四、結(jié)語(yǔ)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將中國(guó)的優(yōu)秀文化譯介到其他國(guó)家,既需西方譯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國(guó)譯者勇挑重?fù)?dān)。因此,我們自己應(yīng)該培養(yǎng)大量合格乃至優(yōu)秀的漢英翻譯人才。中國(guó)高校外語(yǔ)院系的英語(yǔ)專業(yè)是培養(yǎng)漢英翻譯人才的起點(diǎn),我們應(yīng)該重視外語(yǔ)院系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的漢譯英翻譯教學(xué),從“漢譯英”課程設(shè)置、加強(qiáng)學(xué)生漢英翻譯能力培養(yǎng)、改善翻譯教學(xué)模式三方面進(jìn)行改革。
生態(tài)翻譯學(xué)發(fā)展?fàn)顩r與前景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dòng)下,國(guó)內(nèi)的翻譯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首次提出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討會(huì)在上海海事大學(xué)召開(kāi),生態(tài)翻譯學(xué)經(jīng)歷了十年大發(fā)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jī)。正如其領(lǐng)軍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說(shuō),“生態(tài)翻譯學(xué)起初基本上是‘個(gè)人行為’,多年來(lái)的困難、困惑、挑戰(zhàn)太多;……但從現(xiàn)在起,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已經(jīng)成了‘群體行為’,或者說(shuō)是‘組織行為’了”[1]。目前,生態(tài)翻譯學(xué)已引起了國(guó)際翻譯界的關(guān)注和興趣。本文擬簡(jiǎn)述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十年發(fā)展歷程及其研究現(xiàn)狀,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未來(lái)展望一二。 一、生態(tài)翻譯學(xué)十年發(fā)展回顧 生態(tài)翻譯學(xué)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的啟發(fā),將其中的“自然選擇”即“適應(yīng)/選擇”學(xué)說(shuō)引入翻譯學(xué)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2]。在此基礎(chǔ)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劍,建構(gòu)并發(fā)展了從生態(tài)學(xué)視角對(duì)翻譯進(jìn)行綜觀整合性研究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擴(kuò)大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胡教授曾撰文說(shuō):“在全球性生態(tài)思潮的影響之下,由于中國(guó)古代生態(tài)智慧的啟發(fā)、相關(guān)領(lǐng)域?qū)W科發(fā)展的激勵(lì)以及譯學(xué)界生態(tài)取向翻譯研究的促進(jìn),再加上現(xiàn)有譯學(xué)理論研究的局限與缺失所產(chǎn)生需要,生態(tài)翻譯學(xué)便應(yīng)運(yùn)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專著《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這部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闡釋了該理論體系的哲學(xué)理?yè)?jù)(即達(dá)爾文“適應(yīng)/選擇”學(xué)說(shuō)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從“適應(yīng)”與“選擇”的視角對(duì)翻譯的本質(zhì)、原則、過(guò)程、方法和譯評(píng)標(biāo)準(zhǔn)等作出了新的描述與解釋,并以其在兩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實(shí)證調(diào)查對(duì)該理論體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檢驗(yàn)和證實(shí)。胡教授將“譯者為中心”作為該理論體系的核心翻譯觀,從譯者的角度出發(fā),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yīng)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選擇活動(dòng)”,將“多維度適應(yīng)”與“適應(yīng)性選擇”作為翻譯的原則,提出并例證了“三維”轉(zhuǎn)換的翻譯方法。胡教授認(rèn)為,評(píng)價(jià)翻譯主要看譯品的“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理論上講,“最佳的翻譯就是‘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144。而評(píng)價(jià)和測(cè)定“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有三個(gè)參考指標(biāo):即多維轉(zhuǎn)換程度(尤其是“三維”轉(zhuǎn)換程度)、讀者反饋和譯者素質(zhì)。 之后的幾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每年都有生態(tài)翻譯學(xué)方面的學(xué)術(shù)文章發(fā)表在國(guó)內(nèi)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課題“生態(tài)翻譯學(xué):譯學(xué)的生態(tài)視角研究”獲得國(guó)家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立項(xiàng)資助;2009年,《上海翻譯》開(kāi)辟“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專欄”,胡教授在該刊第二期撰文,將翻譯的定義擴(kuò)展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dǎo)、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zhuǎn)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yīng)與譯者選擇行為”[4]6;2010年4月,“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會(huì)”在中國(guó)澳門(mén)成立,創(chuàng)辦了會(huì)刊《生態(tài)翻譯學(xué)學(xué)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門(mén)理工學(xué)院召開(kāi)首屆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討會(huì)。來(lái)自世界各地的56位專家學(xué)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huì),并對(duì)這次大會(huì)的召開(kāi)、對(duì)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對(duì)國(guó)際生態(tài)學(xué)研究會(huì)的成立給予了高度評(píng)價(jià)。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會(huì)顧問(wèn)、《視角:翻譯學(xué)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雜志原主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xué)教授凱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態(tài)翻譯學(xué)是成長(zhǎng)于歐洲語(yǔ)境之外的第一個(gè)真正具有“原創(chuàng)”意義的翻譯理論[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討會(huì)在中國(guó)上海召開(kāi),以“生態(tài)翻譯學(xué)十年:回眸與展望”為主題。來(lái)自世界各地的60位專家學(xué)者參加了這次大會(huì)。由此可見(jiàn),肇始于中國(guó)、由中國(guó)翻譯界學(xué)者首倡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已引起了國(guó)外譯界越來(lái)越多的關(guān)注和興趣,正在向著更大的范圍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dòng)下,國(guó)內(nèi)的翻譯研究者不斷加入到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理論研究和應(yīng)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tài)翻譯學(xué)歸類和直接以生態(tài)翻譯學(xué)命名的各項(xiàng)研究逐年增加。“近年來(lái)已有逾百篇有關(guān)生態(tài)翻譯學(xué)理論研究和應(yīng)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內(nèi)外發(fā)表,全國(guó)也有60余所高校師生(碩士/博士)運(yùn)用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基礎(chǔ)理論作為整體的理論框架完成學(xué)位論文和發(fā)表研究論文”[6]5。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生態(tài)翻譯學(xué)”,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yōu)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0篇題名含有“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文章,其中碩士論文3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guān)召開(kāi)首屆、第二屆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討會(huì)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13篇,約占總論文的29%;應(yīng)用研究型論文32篇,約占總論文的71%。筆者又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yīng)選擇論”,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yōu)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9篇題名含有“適應(yīng)選擇論”的文章(與前述50篇題名含有“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文章無(wú)一重復(fù)),其中碩士論文14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guān)《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一書(shū)的書(shū)評(píng)4篇;除書(shū)評(píng)外的其余5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7篇,約占總論文的13%;應(yīng)用研究型論文48篇,約占總論文的87%。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yīng)選擇”,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yōu)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196篇題名含有“適應(yīng)選擇”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與生態(tài)翻譯學(xué)或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無(wú)關(guān);有2篇博士論文,一篇與生態(tài)翻譯學(xué)無(wú)關(guān),另一篇題名為“譯者的適應(yīng)與選擇:外宣翻譯過(guò)程研究”,是國(guó)內(nèi)首篇運(yùn)用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完成的博士論文。 二、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現(xiàn)狀分析 筆者利用google引擎“學(xué)術(shù)搜索”“生態(tài)翻譯”,用時(shí)0.09秒找到27,200條相關(guān)結(jié)果。但用google引擎“學(xué)術(shù)搜索”“eco-translation”,用時(shí)0.05秒只找到26條相關(guān)結(jié)果(2011/11/28)。這說(shuō)明雖然生態(tài)翻譯學(xué)已引起國(guó)際譯界的關(guān)注和興趣,但在國(guó)際上仍未產(chǎn)生較大影響。上述檢索結(jié)果和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jié)果也說(shuō)明,目前生態(tài)翻譯學(xué)在國(guó)內(nèi)已產(chǎn)生較大影響,越來(lái)越多的中國(guó)學(xué)者及翻譯研究者開(kāi)始從事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從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jié)果來(lái)看,在檢索到的100篇學(xué)術(shù)論文中,目前大多數(shù)有關(guān)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研究都是應(yīng)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數(shù)是理論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闡述的九個(gè)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焦點(diǎn)與理論視角中[6]5-9,這些論文較多選取適應(yīng)/選擇、“三維”轉(zhuǎn)換、譯者中心、譯有所為等理論視角以及生態(tài)范式、生態(tài)翻譯環(huán)境等命題,較少關(guān)注生態(tài)理性、關(guān)聯(lián)序鏈、“事后追懲”等理論視角,這方面的理論應(yīng)用研究還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p#分頁(yè)標(biāo)題#e# 胡教授在首屆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討會(huì)上指出,生態(tài)翻譯學(xué)至多是普通翻譯學(xué)下屬的一個(gè)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認(rèn)可[1]。筆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檢索結(jié)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態(tài)翻譯學(xué)要在國(guó)內(nèi)外譯界牢牢地確立自身學(xué)科地位并獲得長(zhǎng)足發(fā)展,還有待更多生態(tài)翻譯學(xué)人在理論、應(yīng)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態(tài)翻譯學(xué)理論研究方面耕耘不綴。正如王寧教授所言,“生態(tài)翻譯學(xué)還任重道遠(yuǎn),它距離一個(gè)成熟的翻譯學(xué)子學(xué)科還有著相當(dāng)漫長(zhǎng)的路要走。在這方面,美國(guó)生態(tài)批評(píng)發(fā)展的成功經(jīng)驗(yàn)足資參考借鑒”[7]。 三、生態(tài)翻譯學(xué)未來(lái)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筆者撰寫(xiě)本文時(shí),讀到了思創(chuàng)•哈格斯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R&D報(bào)告:十年研究十大進(jìn)展》一文。該文提到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下一步發(fā)展計(jì)劃,如他們“將于近年內(nèi)出版《生態(tài)翻譯學(xué)導(dǎo)論》、《生態(tài)翻譯學(xué):理論應(yīng)用與評(píng)析》、《生態(tài)翻譯學(xué):理念大“觀”園》、《生態(tài)翻譯學(xué)學(xué)派透視》、《生態(tài)翻譯學(xué):下一個(gè)轉(zhuǎn)向》等專題著作。……將繼續(xù)建立和健全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會(huì)的工作機(jī)制,利用好‘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網(wǎng)站,召開(kāi)好序列性的國(guó)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討會(huì),并努力辦好《生態(tài)翻譯學(xué)學(xué)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內(nèi),我們將通過(guò)多種方式集中培養(yǎng)多名生態(tài)翻譯學(xué)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員,從而使‘生態(tài)翻譯學(xué)學(xué)派’在國(guó)際翻譯學(xué)界享有一席之地”[8]。這是一個(gè)宏偉藍(lán)圖,也只有如此,中國(guó)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才能實(shí)現(xiàn)“先國(guó)內(nèi)、后國(guó)際”的發(fā)展戰(zhàn)略,才能通過(guò)生態(tài)翻譯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國(guó)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者才能像美國(guó)生態(tài)批評(píng)家在中國(guó)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樣,在國(guó)際譯界覓得知音。斷加入到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理論研究和應(yīng)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tài)翻譯學(xué)歸類和直接
科技期刊英文水平影響因素探析
當(dāng)今時(shí)代,隨著電子信息產(chǎn)業(yè)的迅速崛起,人們的閱讀習(xí)慣和獲取信息的方式發(fā)生了很大的轉(zhuǎn)變。傳統(tǒng)期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同樣也在面對(duì)著更新一輪的機(jī)遇。為提升期刊的國(guó)際影響力,眾多期刊進(jìn)入SCI等國(guó)際知名索引,其英文題目、英文摘要及關(guān)鍵詞作為檢索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直接影響了期刊被檢索的準(zhǔn)確度和被引用率。作為衡量科技期刊水平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英文水平的高低從側(cè)面顯示了文章的質(zhì)量,也反應(yīng)了整本刊物的水平。文章從期刊編輯的角度,對(duì)影響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因素進(jìn)行分析,以期為提升科技期刊質(zhì)量提供可行的參考途徑。
一、影響因素
(一)作者。作為影響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最根本因素,作者的教育程度、科研水平及寫(xiě)作能力都是不容忽視的。良好的教育程度是影響科技論文英文水平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這也與作者的科研水平和寫(xiě)作能力息息相關(guān)。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所提供的是基礎(chǔ),寫(xiě)作能力則是濃縮、提煉、表述和總結(jié)的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因素。優(yōu)秀的寫(xiě)作能力可以使文章錦上添花,有些作者有著深厚的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自身學(xué)術(shù)水平較高。但受個(gè)人寫(xiě)作能力限制,或者英文水平限制,無(wú)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好地用文字表述出來(lái),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章的質(zhì)量。而一些作者的寫(xiě)作能力雖然不錯(cuò),但受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制約,或者不通曉科技論文的寫(xiě)作規(guī)則,寫(xiě)出的文章沒(méi)有科技論文的語(yǔ)感,影響了文章的整體水平。應(yīng)注意理論與實(shí)踐的結(jié)合,把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和研究成果用簡(jiǎn)練的語(yǔ)句總結(jié)出來(lái),提煉精進(jìn),避免贅余和口語(yǔ)化表述,使文章更符合科技論文的要求。有了良好的寫(xiě)作能力,也仍需英文寫(xiě)作能力的支撐。英文不是簡(jiǎn)單的從中文到英文的轉(zhuǎn)換,而是要根據(jù)語(yǔ)境和科技論文的要求進(jìn)行轉(zhuǎn)譯,切不可生硬直譯。應(yīng)注意第三人稱、科技論文常用的詞匯和時(shí)態(tài)的使用,保持行文通暢,語(yǔ)法準(zhǔn)確。注意中英文差異,從行文差異、語(yǔ)法結(jié)構(gòu)等方面考慮英文的行文和句式,以表達(dá)清晰、流暢為主。英文的參考文獻(xiàn)也是影響文章質(zhì)量的重要因素,應(yīng)引用得當(dāng),盡量選取可信的一手資料,以提升文章的研究?jī)r(jià)值和參考價(jià)值。英文的原版資料更具有參考價(jià)值,在引用時(shí)應(yīng)盡量選用原文,而不是只看轉(zhuǎn)譯或轉(zhuǎn)引的資料。
(二)編輯。除作者外,一篇好的文章也離不開(kāi)編輯的貢獻(xiàn),好的編輯可以使文章錦上添花。雖然不直接參與文章的創(chuàng)作,但編輯在編排和文字處理上可以依靠編輯專業(yè)知識(shí)和文字處理技巧,幫助作者對(duì)英文部分進(jìn)行加工整理。作為編輯,拿到一篇文章,首先要對(duì)其進(jìn)行整體判定,根據(jù)具體情況設(shè)計(jì)編修方案,以確保文章的英文質(zhì)量。部分作者不重視英文摘要,會(huì)選擇用翻譯軟件一鍵轉(zhuǎn)換,也會(huì)出現(xiàn)一些詞不達(dá)意的現(xiàn)象。翻譯軟件雖然在專業(yè)詞匯上有一定優(yōu)勢(shì),但不了解中英文的語(yǔ)句結(jié)構(gòu)的不同,翻譯較為生硬、機(jī)械。翻譯軟件容易因?yàn)槌绦蚧瘮嗑洌巡幌嚓P(guān)的詞語(yǔ)拼湊在一起,翻譯出來(lái)的文字也就與原文相去甚遠(yuǎn)了,這就需要編輯對(duì)英文質(zhì)量進(jìn)行整體的把關(guān)。其次,科技論文對(duì)詞匯和語(yǔ)法也有一些特定的要求,編校時(shí)需幫助作者進(jìn)行核對(duì)。由于科技論文專業(yè)詞匯較多,涉及的專業(yè)性較強(qiáng),所以進(jìn)行修正的時(shí)候要保持與作者的溝通,避免發(fā)生偏差。編輯科技論文需要較高的科學(xué)素養(yǎng),對(duì)一篇文章的內(nèi)容應(yīng)有清晰的判斷。英文編輯的英文水平雖然較高,但科技論文的專業(yè)詞匯偏多,專業(yè)科技英語(yǔ)的應(yīng)用并不一定熟練,需要在關(guān)注英文的基礎(chǔ)上,注意科技論文的特殊性,表述應(yīng)簡(jiǎn)潔客觀。再次,英文參考文獻(xiàn)也需遵從國(guó)家規(guī)定的參考文獻(xiàn)著錄規(guī)則,不可缺失必要的著錄項(xiàng)目。編輯需認(rèn)真進(jìn)行核對(duì),填補(bǔ)缺漏,同時(shí)要確保參考文獻(xiàn)的真實(shí)性和合理性。
(三)溝通和交流。文章的成功與否與作者和編輯的溝通也是密不可分的。適當(dāng)?shù)臏贤ń涣饔欣诶砬逦恼碌拿}絡(luò),使文字通順,也可以提高專業(yè)性和準(zhǔn)確性。對(duì)于編輯而言,一方面需要核對(duì)文章的準(zhǔn)確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與作者的交流,避免誤改、誤譯英文摘要。編輯的工作依附于作者及其作品,工作的創(chuàng)新性也離不開(kāi)作者及作者本身[1],因此更應(yīng)注意與作者的溝通交流。
二、結(jié)論與建議
(一)堅(jiān)定文化自信,做好英文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要做好一本期刊,尤其是一本英文科技期刊,就要首先有自己的“底氣”,樹(shù)立良好的辦刊信念,從精神的層面先做好“走出去”的準(zhǔn)備。打好思想基礎(chǔ),明確目標(biāo)和方向,堅(jiān)持黨的領(lǐng)導(dǎo)、堅(jiān)持正確的出版方向,傳承和發(fā)揚(yáng)中華文化,在堅(jiān)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綜合學(xué)習(xí)中外辦刊理念的精華,遵循國(guó)際編輯出版的要求和規(guī)范的同時(shí),探索符合我國(guó)國(guó)情的辦刊道路,建設(shè)符合新時(shí)代新需求的英文科技期刊,為推進(jìn)中華民族的文化繁榮做出貢獻(xiàn),努力向通往出版強(qiáng)國(guó)的道路奮進(jìn)。
茶文化內(nèi)涵及翻譯
摘要:
隨著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的不斷發(fā)展,世界呈現(xiàn)出包容性發(fā)展的趨勢(shì),西方茶文化在這一趨勢(shì)的推動(dòng)下迅速傳播到中國(guó),中國(guó)的茶文化也隨著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發(fā)展趨勢(shì)迅速走向世界,影響了越來(lái)越多的外國(guó)友人。在中西茶文化碰撞、交匯、相互影響的過(guò)程中,中西方茶文化各自的深刻內(nèi)涵以及相互差異,引發(fā)了廣泛的關(guān)注和討論,并直接對(duì)茶文化的翻譯問(wèn)題產(chǎn)生了顯著影響。基于這一背景,在現(xiàn)階段對(duì)中西方茶文化的內(nèi)涵及翻譯進(jìn)行科學(xué)分析,是非常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并將非常有助于中國(guó)茶文化影響力的繼續(xù)擴(kuò)大、提升。
關(guān)鍵詞:
中西方;茶文化;內(nèi)涵;翻譯
中國(guó)是茶葉大國(guó),是茶葉的原產(chǎn)地,也是茶文化的發(fā)源地。在茶葉長(zhǎng)途跋涉?zhèn)鞑サ轿鞣絿?guó)家后,通過(guò)長(zhǎng)期的歷史積淀,西方也逐漸形成了與中國(guó)茶文化截然不同、獨(dú)具特色的茶文化內(nèi)涵與體系,并主要通過(guò)飲茶習(xí)慣、飲茶方式、飲茶禮儀等表現(xiàn)出來(lái),讓茶葉這一古老的中國(guó)飲品在西方土地上煥發(fā)出異域風(fēng)情。本文在參考相關(guān)文獻(xiàn)、資料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當(dāng)前中西方茶文化的客觀現(xiàn)狀,對(duì)中西方茶文化的內(nèi)涵進(jìn)行了分析和比較,并對(duì)茶文化的翻譯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議,希望對(duì)相關(guān)人士有所啟示。
1中西方茶文化的內(nèi)涵分析
中國(guó)是茶葉的故鄉(xiāng),是茶文化生根發(fā)芽的地方,有著深厚的茶文化積淀,茶文化也顯著地影響著由古至今的中國(guó)人的行為禮儀、性格品質(zhì),可以說(shuō),中國(guó)茶文化是中國(guó)人的一個(gè)鮮明標(biāo)簽和深刻烙印。西方雖然接觸茶葉、茶文化的時(shí)間和中國(guó)相比少得多,但近代以來(lái),以英國(guó)為首的西方國(guó)家,也逐漸形成了一套獨(dú)具特色的、和中國(guó)乃至東方國(guó)家有顯著區(qū)分的茶文化體系。早在十六世紀(jì)的時(shí)候,英國(guó)在強(qiáng)大的生產(chǎn)力、軍事實(shí)力的支撐下,戰(zhàn)勝了西班牙戰(zhàn)隊(duì)進(jìn)而獲得了海上霸權(quán),走上了向外擴(kuò)張的歷史征程。從那時(shí)開(kāi)始,英國(guó)和世界范圍內(nèi)其他國(guó)家的物質(zhì)、經(jīng)濟(jì)往來(lái)日益頻繁,也是在這一時(shí)期,官方色彩鮮明的東印度公司首次將東方茶葉帶入了英國(guó),并作為商品銷售。這種珍貴的東方樹(shù)葉,當(dāng)時(shí)由于在英國(guó)數(shù)量稀缺而價(jià)值不菲,主要作為藥品和養(yǎng)生飲品而存在,流傳于英國(guó)皇家貴族當(dāng)中,并很快獲得了越來(lái)越多英國(guó)人的喜愛(ài)。因此,英國(guó)的茶葉供應(yīng)量逐漸增加,開(kāi)始越來(lái)越多地影響到英國(guó)的中下層人民,獲得了廣泛的民間人士的喜愛(ài),成為英國(guó)人休閑、社交中使用到的重要飲品。隨后,隨著英國(guó)的不斷擴(kuò)張,英國(guó)的茶葉供應(yīng)量越來(lái)越多,逐漸在英國(guó)人當(dāng)中得以普及,英國(guó)人和茶葉產(chǎn)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這種英國(guó)茶文化也開(kāi)始逐漸滲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國(guó)家當(dāng)中,產(chǎn)生越來(lái)越深刻的文化基礎(chǔ)。由于西方國(guó)家和中國(guó)在文化差異、民族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國(guó)家逐漸形成了顯著區(qū)別于中國(guó)的茶文化內(nèi)涵,并逐漸形成完善的西方茶文化體系。茶文化在西方國(guó)家從萌芽逐漸走向成熟,散發(fā)出強(qiáng)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和中國(guó)的農(nóng)耕文明不同,在西方國(guó)家的文化領(lǐng)域中,茶文化更多扮演的是一種開(kāi)放的、優(yōu)雅的角色。西方人對(duì)于茶葉飲品的感受,不僅在于味覺(jué),更在于品茶過(guò)程中的自我精神實(shí)現(xiàn)和與他人的精神交流,茶文化在西方國(guó)家的內(nèi)涵變得非常集中而深刻,這和西方國(guó)家商業(yè)文明的發(fā)展是息息相關(guān)的,也表現(xiàn)出西方人對(duì)茶葉的深刻喜愛(ài)和情有獨(dú)鐘。在此基礎(chǔ)上,西方茶文化的內(nèi)涵逐漸擴(kuò)散而細(xì)化,英國(guó)形成了喝下午茶的習(xí)慣,飲茶這一極具文化氛圍的活動(dòng)已經(jīng)成為了英國(guó)人乃至西方人生活、工作、社交、休閑過(guò)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說(shuō)英國(guó)的茶文化專注于文化“點(diǎn)”魅力的綻放,那么中國(guó)茶文化則更加傾向于從千年歷史中緩緩走來(lái)的極具民族文化積淀的茶文化普遍影響及成熟形式的展現(xiàn)。中國(guó)的茶文化經(jīng)歷了千年歷史的塑造,已經(jīng)和中國(guó)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完美融合,極具中華文化魅力與特色,成為中國(guó)的標(biāo)志性文化載體與文化形式。在中國(guó)人眼中,茶文化的內(nèi)涵是廣泛而深刻的,涉及到茶葉的種植、采摘、制作、飲用、茶具選擇、茶室布置、茶服搭配、茶事活動(dòng)等與茶葉相關(guān)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上升到精神層面。茶文化的內(nèi)涵之于中國(guó)人,兼具了形式美、內(nèi)容美、精神美,在飲茶活動(dòng)的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上,中國(guó)人都樂(lè)在其中,并自覺(jué)實(shí)現(xiàn)了肢體活動(dòng)和精神活動(dòng)的交融。中國(guó)茶文化的內(nèi)涵之龐大、含義之深刻、形式之優(yōu)美、影響之深遠(yuǎn),是只言片語(yǔ)難以描述的,它已經(jīng)深入到中國(guó)的文化當(dāng)中,深入到中國(guó)人的骨髓當(dāng)中。
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建構(gòu)
1.引言 佛典漢譯始于東漢,終于宋朝,歷時(shí)一千多年,期間佛教高僧研習(xí)佛典,講經(jīng)布道,翻譯佛典近六千卷,闡述的翻譯思想如同天空的星星熠熠生輝。這些是中華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duì)一脈相承的明清實(shí)學(xué)翻譯和近代西學(xué)翻譯具有直接的影響,是嚴(yán)復(fù)“信達(dá)雅”翻譯思想誕生的土壤,是我國(guó)翻譯學(xué)的根基和傳統(tǒng)。所謂“典籍”,“主要指經(jīng)過(guò)歷史的淘汰選擇,被人們所公認(rèn)的、代表一個(gè)民族的文化水平所達(dá)到的高度、深度和廣度的著作。”(魏曉紅、李清源2010:109)佛典就是指佛教的根本典籍,涵蓋經(jīng)、律、論“三藏”。翻譯學(xué)成為獨(dú)立學(xué)科伊始,我們一方面要吸納西方譯學(xué)精華,做到洋為中用;另一方面更要繼承我國(guó)傳統(tǒng)譯論“勘稱典范的學(xué)術(shù)成就”,做到古為今用。只有古今打通,中外融通之后,我國(guó)翻譯學(xué)才能健康發(fā)展,我國(guó)才能從翻譯大國(guó)質(zhì)變?yōu)榉g強(qiáng)國(guó)。本論文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dǎo)下,從學(xué)術(shù)范式視角研究佛典漢譯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什么? 2.范式 范式(paradigm),有時(shí)譯作“規(guī)范”和“典范”,是1962年托馬斯•庫(kù)恩在《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一書(shū)中提出的概念,通常指一個(gè)學(xué)術(shù)共同體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傳統(tǒng),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理論模式和規(guī)則體系(ThomasKuhn1962)。1989年科爾勒把學(xué)術(shù)范式引入到語(yǔ)言學(xué)研究中,縮小了范式的內(nèi)涵和外延,用來(lái)指語(yǔ)言學(xué)史上堪稱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傳統(tǒng)語(yǔ)言觀念的理論體系(KoernerKonrad1989)。1984年余英時(shí)的著作《中國(guó)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借用庫(kù)恩的范式理論,解釋胡適《中國(guó)哲學(xué)史大綱》在中國(guó)近代史學(xué)革命上的中心意義(余英時(shí)1984:19-21,77-91)。自此,學(xué)術(shù)范式在我國(guó)學(xué)術(shù)界逐漸得到推廣。1999年傅勇林先生把學(xué)術(shù)范式引入到翻譯研究中,采用庫(kù)恩關(guān)于范式的經(jīng)典定義,認(rèn)為“在范式的上述四個(gè)要素中,精神信念關(guān)乎譯學(xué)思想與學(xué)術(shù)品位,研究傳統(tǒng)關(guān)乎譯學(xué)知識(shí)的探索過(guò)程及其‘層累疊加’,理論模式和規(guī)則體系則直接涉及譯學(xué)研究的學(xué)術(shù)層面,四者藕合,才可構(gòu)成譯學(xué)研究的學(xué)術(shù)范式并借以形成譯學(xué)研究的學(xué)術(shù)面貌,因此絕對(duì)不可偏廢。”(傅勇林、朱志瑜1999:30)本論文沿襲庫(kù)恩關(guān)于范式的經(jīng)典定義,擬構(gòu)建佛典漢譯的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 3.文章學(xué) “文章”在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是頗具考究的詞匯,錦繡文章是中華文化智慧的結(jié)晶,是我國(guó)文人墨客才華的精髓,《千家詩(shī)》首章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之說(shuō)。“文章”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先秦文獻(xiàn)中,其本義是色彩之間的錯(cuò)雜搭配。后來(lái)在《論語(yǔ)•公治長(zhǎng)》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開(kāi)始表現(xiàn)為文字作品之義,兩漢時(shí)期這一概念已經(jīng)比較成熟,如:“漢之得人,以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tǒng),纂修洪業(yè),亦講論六義招選茂才。而肖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yán)彭祖、尹更始以儒術(shù)進(jìn),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班固1962:58)“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yáng)子云,其才能若奇,其稱不由人。”(王充1954:275)我國(guó)古代文章的范圍很廣,清人章學(xué)誠(chéng)感嘆“六經(jīng)皆史”,后人對(duì)曰“四庫(kù)皆文”,因?yàn)椤端膸?kù)》經(jīng)、史、子、集無(wú)一不是文章。“中國(guó)的文章,歷三千年之久,存在于中國(guó)的經(jīng)、史、子、集四部典籍之中,舉凡哲學(xué)、政治、歷史、宗教、藝術(shù)、民事、風(fēng)俗,以及個(gè)人抒懷述志,無(wú)不借文章以傳布和存留。”(毛慶耆2002:113)這句話說(shuō)明文章在我國(guó)走過(guò)的歲月之長(zhǎng),涵蓋的范圍之廣。文章學(xué)是指研究文章的學(xué)問(wèn),通俗地說(shuō),文章學(xué)就是文章研究。佛典漢譯深深植根于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中華文明,深受我國(guó)古代文章學(xué)、史學(xué)、佛學(xué)和中華文化的浸染熏陶,我國(guó)古代把翻譯納入文章學(xué)范疇,衡量譯文與評(píng)價(jià)文章都采用文質(zhì)標(biāo)準(zhǔn)。嚴(yán)復(fù)說(shuō):“(信、達(dá)、雅)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嚴(yán)復(fù)1981:11)這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經(jīng)典話語(yǔ),文章正軌就是譯事楷模,“信、達(dá)、雅”三者既是文章要求,也是翻譯標(biāo)準(zhǔn),佛典漢譯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究其根源,合作翻譯傳統(tǒng)使然。 4.佛典漢譯的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構(gòu)建 4.1合作翻譯是佛典漢譯的傳統(tǒng),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成因 佛典漢譯歷時(shí)千年,一直采取合作翻譯方式進(jìn)行,無(wú)論是初期的私人合作,還是后來(lái)的譯場(chǎng)合作,合作翻譯是根本,佛典漢譯形成了合作翻譯傳統(tǒng)。一是因?yàn)榉鸬錆h譯初期沒(méi)有原本,外國(guó)僧人根據(jù)記憶口誦佛典,即使在印度本國(guó),當(dāng)時(shí)也無(wú)佛典寫(xiě)本。《分別功德論》云:“外國(guó)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tīng)載文。”梁?jiǎn)⒊治銎湓?“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傳寫(xiě)困難,故如我國(guó)漢代傳經(jīng),皆憑口說(shuō)。(二)含有宗教神秘的觀念,認(rèn)書(shū)寫(xiě)為瀆經(jīng);如羅馬舊教之禁寫(xiě)《新舊約》也。”(梁?jiǎn)⒊?984:53-54)竹帛攜帶不便和宗教禁寫(xiě)是造成印度佛典沒(méi)有寫(xiě)本,佛典漢譯沒(méi)有原本的原因。印度佛典何時(shí)才有寫(xiě)本?這個(gè)問(wèn)題學(xué)界尚未解決,據(jù)梁氏研究,“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guó),皆師師口傳,無(wú)本可寫(xiě)。”(梁?jiǎn)⒊?984:54)說(shuō)明至少在5世紀(jì)初法顯西游之時(shí),印度等國(guó)尚無(wú)佛典寫(xiě)本。二是因?yàn)榉鸬錆h譯初期譯者多為單語(yǔ)者,梵漢兩種語(yǔ)言不能兼通,外國(guó)僧人負(fù)責(zé)口誦佛典,本土漢人負(fù)責(zé)潤(rùn)飾加工,形成譯文,佛典漢譯由外國(guó)僧人和本土僧人合作翻譯完成。釋贊寧對(duì)佛典漢譯做過(guò)概述:“初則梵客華僧,聽(tīng)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shuō),十得八九,時(shí)有差違,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無(wú)極’矣。后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器請(qǐng)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內(nèi)豎對(duì)文王之問(wèn),揚(yáng)雄的絕代之文,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斯謂之大備矣。”(釋贊寧1987:52-53)是說(shuō)佛典漢譯初期梵僧未諳漢語(yǔ),漢僧不通梵文,加上沒(méi)有原本,只能進(jìn)行合作翻譯。先由梵僧口誦佛經(jīng),進(jìn)行傳言,初步譯成漢語(yǔ);再由華僧筆受潤(rùn)飾,加工成文,這是簡(jiǎn)單的私人合作形式。佛典漢譯中后期,梵僧習(xí)得漢語(yǔ),漢人學(xué)習(xí)梵文,玄奘、不空更是梵漢皆通,“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dú)斷,出語(yǔ)成章。詞人隨寫(xiě),即可披玩。”(釋道宣1984:48)但是即使個(gè)人翻譯水平達(dá)到很高境界,很多佛典原本也從印度帶回,佛典漢譯還是沿襲了合作翻譯傳統(tǒng),依然采取梵文理解和漢語(yǔ)表達(dá)分步進(jìn)行,梵僧和漢僧合作完成的方式,只不過(guò)由初期的私人合作發(fā)展為頗具規(guī)模的譯場(chǎng)合作。以唐朝玄奘組織的譯場(chǎng)為例,翻譯程序就有十一道,包括:“一、譯主:執(zhí)筆人,胸懷全局,貫徹始終;二、證文:朗誦原文佛經(jīng),斟酌原文是否有錯(cuò);三、筆受:根據(jù)梵音錄本譯出毛稿;四、度語(yǔ):音譯暫無(wú)對(duì)等信息的事物,據(jù)母本正音;五、綴文:按漢語(yǔ)字法、句法進(jìn)行整理;六、證義:譯出初稿與原文對(duì)照,看本旨是否偏移歪曲或有遺漏;七、參詳:再回證原文是否有紕漏、錯(cuò)誤;八、利洗:去蕪冗、重復(fù),梳整譯文;九、潤(rùn)文:修辭、潤(rùn)飾;十、梵唄:由于佛經(jīng)是要供人誦讀的,所以再據(jù)母語(yǔ)(梵文)的誦經(jīng)方式誦讀漢譯經(jīng)文,看是否有不適合誦讀之句;十一、監(jiān)閱:最后有欽命大臣監(jiān)閱(終審)。”(李全安1993:806-807)整套程序非常嚴(yán)謹(jǐn),第二、六、七條強(qiáng)調(diào)原文理解,第五、八、九、十條重視譯文表達(dá),譯場(chǎng)翻譯的重心仍是加工譯文,形成文章。事實(shí)上,無(wú)論是初期的私人合作,還是中后期的譯場(chǎng)合作,合作翻譯一直是佛典漢譯的傳統(tǒng),梵僧負(fù)責(zé)原文理解,漢人負(fù)責(zé)譯文表達(dá),原文理解和譯文表達(dá)的分步進(jìn)行使佛典漢譯選擇了合作翻譯方式,而合作翻譯傳統(tǒng)的形成又進(jìn)一步細(xì)化了原文理解和譯文表達(dá)的分工。對(duì)于漢人來(lái)說(shuō),如何根據(jù)佛典原文意思用漢語(yǔ)表達(dá)成文才是關(guān)注的重心和焦點(diǎn),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佛典漢譯的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p#分頁(yè)標(biāo)題#e# 4.2“文以載道”是佛典漢譯的信念,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內(nèi)核 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非常重視文章,視其為治國(guó)、傳世之大業(yè),正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言:“蓋文章者,經(jīng)國(guó)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shí)而盡,榮樂(lè)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wú)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jiàn)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shì),而聲名自傳于后。”(郭紹虞2001:159)我國(guó)文章學(xué)的核心思想是“文以載道”,道是文章的精神所在,是衡量文章的內(nèi)在準(zhǔn)則,因道設(shè)器、道因器顯,道決定了文章的體式,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質(zhì),造成了文章學(xué)上的“言不盡意”和“得意忘言”。文與道的關(guān)系和“文以載道”的實(shí)施都以人為紐帶,通過(guò)作者實(shí)現(xiàn),文與道的關(guān)系隱含了人與道、人與文的關(guān)系。“在中國(guó)文化中,‘道———人———文’是三個(gè)緊密相連的三環(huán),其中,人是核心與根本,以人立極是中國(guó)人文精神的最顯著特色,中國(guó)文化的重文意識(shí)的根本是重人意識(shí),因此中國(guó)文章的功能實(shí)施,是靠對(duì)人影響完成的,以文觀人是中國(guó)文章品鑒論的核心,并由此推衍出鑒文知人、文如其人等相關(guān)命題。”(楊廣敏2001:39)關(guān)系到人,就會(huì)牽涉到人品因素,孔子曰“修辭立其城”,是說(shuō)寫(xiě)文章要講心里話,言為心聲,文如其人,這是我國(guó)古代對(duì)作者人品提出的要求。同樣,佛典漢譯對(duì)譯者人品也有要求,釋彥琮在《辯證論》中提出了著名的“八備”:“誠(chéng)心愛(ài)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時(shí),其備一也。將踐覺(jué)場(chǎng),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guò)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zhí),其備五也。耽于道術(shù),淡于名利,不欲高玄,其備六也。要識(shí)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xué),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釋彥琮1991:118)“八備”是彥琮對(duì)譯者提出的八項(xiàng)條件,其中“四備”針對(duì)譯者人品。具體是:一備要求譯者誠(chéng)心愛(ài)護(hù)佛法,志愿救世幫人,即使歷時(shí)長(zhǎng)久,也絕不懈怠;二備要求譯者牢守佛教戒條,具備良好的操行;五備要求譯者寬容平和,謙虛待人,不可固執(zhí)己見(jiàn);六備要求譯者鉆研佛學(xué),淡泊名利,不事炫耀。這四項(xiàng)對(duì)譯者人品的要求與另外四項(xiàng)對(duì)譯者學(xué)業(yè)上的要求結(jié)合起來(lái),就是完整的“八備”,彥琮認(rèn)為譯者的人品與學(xué)業(yè)同等重要,一個(gè)譯者必須同時(shí)具備這八項(xiàng)條件,才有可能是個(gè)翻譯人才,所謂“八者備矣,方是得人”。釋彥琮首次把譯者人品與翻譯好壞聯(lián)系起來(lái),這是我國(guó),也是世界翻譯史上最早談?wù)撟g者人品的文章。“文以載道”既是文章學(xué)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國(guó)傳統(tǒng)譯學(xué)的精神信念,是佛典漢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內(nèi)核。 4.3“文質(zhì)之爭(zhēng)”涉及佛典漢譯的理論模式和規(guī)則體系,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表征 我國(guó)古代把翻譯納入文章學(xué)范疇,文、質(zhì)原是我國(guó)古代評(píng)判文章好壞的一對(duì)概念,移用到佛典漢譯中,指譯文語(yǔ)言風(fēng)格的文麗和質(zhì)樸。“在中國(guó)佛經(jīng)翻譯史上,始終存在‘質(zhì)樸’和‘文麗’兩派。”(任繼愈1981:174)“文質(zhì)之爭(zhēng)”是貫穿我國(guó)佛典漢譯思想的一條主線(趙巍、馬艷姿2010:93),始于公元224年支謙的《法句經(jīng)序》,終于7世紀(jì)玄奘的“新譯”,歷時(shí)四百多年。“文質(zhì)之爭(zhēng)”之前,我國(guó)最早的佛典漢譯家安世高和支讖屬于“質(zhì)”派人物,其譯本給人總體印象是“辭質(zhì)多胡音”,音譯較多,譯文樸拙,不加潤(rùn)飾,不合漢語(yǔ)習(xí)慣。質(zhì)派有所不足的局面為文派的產(chǎn)生提供了契機(jī),支謙和康僧會(huì)是三國(guó)時(shí)期的文派代表人物,二人精通梵文和漢語(yǔ),主張對(duì)譯文加工潤(rùn)飾,所譯佛典簡(jiǎn)略文麗。支謙《法句經(jīng)序》拉開(kāi)了佛典漢譯“文質(zhì)之爭(zhēng)”的帷幕,文質(zhì)自此成為譯者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文派譯風(fēng)在三國(guó)和西晉時(shí)期占據(jù)重要地位,對(duì)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文派過(guò)于追求譯文的文采美巧,有時(shí)不免脫離佛典原意,造成“理滯于文”,遭至后人詬病。之后佛典漢譯又偏向質(zhì)派,竺法護(hù)、趙政等都是質(zhì)派代表。竺法護(hù)譯經(jīng)力求詳盡,存真偏質(zhì),“凡所譯經(jīng),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dá)欣暢,特善無(wú)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釋慧皎1994:24)對(duì)比竺法護(hù)的譯本和安世高、支讖的譯本,很容易發(fā)現(xiàn):雖然同屬質(zhì)派,但是安、支二人的“質(zhì)”胡音較多,不合漢語(yǔ)語(yǔ)法習(xí)慣,只能算是“樸拙”;而竺法護(hù)的譯文質(zhì)量明顯提高,“質(zhì)”的內(nèi)涵有所提升,譯文流暢,符合漢語(yǔ)習(xí)慣,質(zhì)派翻譯由樸拙走向質(zhì)樸,克服了譯文結(jié)構(gòu)僵硬、義理晦澀等不足之處。趙政也認(rèn)為:“昔來(lái)出經(jīng)者,多嫌胡言方質(zhì),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zhì)?文質(zhì)是時(shí),幸勿易之,經(jīng)之巧質(zhì),有自來(lái)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釋道安1995:382)趙政批評(píng)譯者嫌棄梵文語(yǔ)言質(zhì)樸,趨于時(shí)尚追求譯文文麗的思想,主張譯文應(yīng)像原文一樣保持質(zhì)樸的語(yǔ)言,因?yàn)橘|(zhì)樸是經(jīng)文本身的特點(diǎn),何必改之?佛學(xué)大師釋道安則主張文質(zhì)兼?zhèn)洌岢?ldquo;合本”,融合文、質(zhì)兩派的優(yōu)點(diǎn)進(jìn)行翻譯。道安認(rèn)為梵文佛典語(yǔ)言質(zhì)樸,而當(dāng)時(shí)的讀者喜好文麗,佛典漢譯“文質(zhì)之爭(zhēng)”變成是照顧原文,保持質(zhì)樸;還是照顧讀者,使之文麗的爭(zhēng)論。質(zhì)派認(rèn)為“經(jīng)之巧質(zhì),有自來(lái)矣”,認(rèn)為譯文應(yīng)該保持質(zhì)樸的語(yǔ)言風(fēng)格。但文派鳩摩羅什卻認(rèn)為:“天竺國(guó)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釋僧祐1995:534)原來(lái)梵文也非常重視文采,佛典原本也有文麗和質(zhì)樸之分,那些繁瑣的偈頌是梵文體裁的一種形式。鳩摩羅什認(rèn)為“改梵為秦”不應(yīng)“失其藻蔚”,主張譯文應(yīng)向原文一樣注重文飾,翻譯不僅要準(zhǔn)確傳達(dá)原文意思,而且要再現(xiàn)原文的文采和風(fēng)韻。此時(shí)的文派與三國(guó)時(shí)期相比有了明顯的進(jìn)步,在強(qiáng)調(diào)譯文流暢、具有文采的基礎(chǔ)上,文派開(kāi)始重視準(zhǔn)確傳達(dá)原文意思。鳩摩羅什的譯文不僅語(yǔ)言精美,而且內(nèi)容準(zhǔn)確,其翻譯的《法華經(jīng)》被譽(yù)為具有“天然西域之語(yǔ)趣”。但是如同支謙一樣,羅什譯本依然存在“刪削原文”的缺點(diǎn),后人對(duì)其也有“理滯于文”的評(píng)價(jià)。關(guān)于譯文是否需要文飾,語(yǔ)言風(fēng)格是文麗還是質(zhì)樸的爭(zhēng)論持續(xù)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文、質(zhì)兩派在爭(zhēng)論中前行,在磨合中發(fā)展,文質(zhì)矛盾得到調(diào)和,翻譯質(zhì)量有所提高。那么如何融合文、質(zhì)兩派的優(yōu)勢(shì),克服不足之處?“文質(zhì)之爭(zhēng)”的出路在哪?東晉高僧慧遠(yuǎn)主張文質(zhì)“厥中”,提倡文質(zhì)兼?zhèn)涞乃枷耄J(rèn)為“文質(zhì)殊體,若以文應(yīng)質(zhì),則疑者眾。以質(zhì)應(yīng)文,則悅者寡。”(釋慧遠(yuǎn)1995:391)是說(shuō)文麗和質(zhì)樸屬于不同文體,質(zhì)樸的原文若用文麗去譯,懷疑的人就很多;文麗的原文若用質(zhì)樸去譯,感興趣的人則很少,因此譯者應(yīng)該遵循原文文體,做到以文應(yīng)文,以質(zhì)應(yīng)質(zhì),文質(zhì)厥中。釋僧祐也說(shuō):“文過(guò)則傷艷,質(zhì)甚則患野,野艷為弊,同失經(jīng)體。”(釋僧祐1995:14-15)認(rèn)為文過(guò)和質(zhì)甚都是翻譯的弊端,同樣有損經(jīng)文文體,主張譯文“質(zhì)文允正”。這一說(shuō)法其實(shí)是孔子“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的思想在翻譯領(lǐng)域的延伸和拓展。此時(shí),人們開(kāi)始從翻譯思想上解決文質(zhì)矛盾,尋求“文質(zhì)之爭(zhēng)”的出路。不過(guò),具體到翻譯實(shí)踐,直到玄奘“新譯”才從根本上解決文質(zhì)問(wèn)題。“這是因?yàn)樾首g文融合了文質(zhì)兩派的優(yōu)點(diǎn),真正做到了‘案本而傳’,‘以質(zhì)應(yīng)質(zhì),以文應(yīng)文’,不但傳達(dá)了原文意義,而且能夠再現(xiàn)原文風(fēng)格,譯文語(yǔ)言流暢,適合誦讀,遠(yuǎn)遠(yuǎn)超出前人所譯,其翻譯被世人尊稱為‘新譯’”。(汪東萍、傅勇林2010:99)玄奘“新譯”是“文質(zhì)之爭(zhēng)”的圓滿結(jié)果,從此“文質(zhì)彬彬”、“文質(zhì)相半”成為衡量佛典漢譯譯文好壞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p#分頁(yè)標(biāo)題#e# 5.結(jié)語(yǔ) 佛典漢譯植根于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中華文明,深受我國(guó)古代文章學(xué)的浸染熏陶,合作翻譯是佛典漢譯的傳統(tǒng),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成因;“文以載道”是佛典漢譯的信念,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內(nèi)核;“文質(zhì)之爭(zhēng)”涉及佛典漢譯的理論模式和規(guī)則體系,是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的表征。幾方面藕合,共同構(gòu)建了佛典漢譯的文章學(xué)譯學(xué)范式。這一飽含中華智慧的譯學(xué)范式必將為世界翻譯學(xué)提供新類型,補(bǔ)充新動(dòng)力,我國(guó)翻譯研究者應(yīng)該抓住契機(jī),深入研究我國(guó)翻譯傳統(tǒng),吸取養(yǎng)分精華,借中國(guó)翻譯之“道”走世界翻譯之“路”,為世界翻譯學(xué)的發(fā)展做出中國(guó)這一文化古國(guó)和翻譯大國(guó)應(yīng)有的貢獻(xiàn)。
外國(guó)文學(xué)翻譯思想分析
蘭臺(tái)縱橫lantaizongheng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 著名的古文字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東方學(xué)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xué)家、作家。 精通12國(guó)語(yǔ)言。 在語(yǔ)言學(xué)、佛教學(xué)、印度學(xué)、文化學(xué)、歷史學(xué)和比較文學(xué)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詣,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guó)的多部經(jīng)典,2006年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jiǎng)。 一、季羨林的成就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zhèn),10歲時(shí)開(kāi)始正式學(xué)習(xí)英文,高中開(kāi)始學(xué)習(xí)德文,并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發(fā)生興趣。 18歲時(shí)在省立濟(jì)南高中求學(xué),其國(guó)學(xué)老師,翻譯家與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決定了季羨林一生的寫(xiě)作活動(dòng)。1930年進(jìn)入清華大學(xué)西洋文學(xué)系,專業(yè)方向是德文。向吳宓、葉公超學(xué)習(xí)東西詩(shī)比較、英文,同時(shí)選修陳寅恪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xué)等,在此期間對(duì)梵文產(chǎn)生了深厚的興趣。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xué)與德國(guó)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guó)至哥廷根大學(xué)學(xué)習(xí)。在長(zhǎng)期的學(xué)習(xí)研究中,季羨林認(rèn)為中國(guó)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巨大,1936年決定選擇梵文,對(duì)中印文化關(guān)系進(jìn)行徹底的研究。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xué)梵文研究所期間主修印度學(xué),學(xué)習(xí)梵文及巴利文。同時(shí)選修英國(guó)語(yǔ)言學(xué)、斯拉夫語(yǔ)言學(xué),加學(xué)南斯拉夫文。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xué)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時(shí)也是他唯一的聽(tīng)課者。1941年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斯拉夫語(yǔ)言、印度學(xué)、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gè)優(yōu),獲得博士學(xué)位。同年成為語(yǔ)言學(xué)家艾密爾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羅語(yǔ)。10月在哥廷根大學(xué)漢學(xué)研究所擔(dān)任教員并繼續(xù)研究佛教及梵語(yǔ),在德國(guó)期間季羨林發(fā)表了多篇重要論文,獲得了高度評(píng)價(jià),奠定了其在國(guó)際東方學(xué)和印度學(xué)界的地位。因戰(zhàn)爭(zhēng)歸國(guó)無(wú)路的季羨林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不久經(jīng)瑞士輾轉(zhuǎn)取道東歸,經(jīng)恩師陳寅恪推薦于1946年進(jìn)入北京大學(xué)任教至1983年,創(chuàng)建東方語(yǔ)言文學(xué)并一直擔(dān)任系主任,從事系務(wù)、科研和翻譯工作。北大是我國(guó)最早成立東方語(yǔ)文系的大學(xué),培養(yǎng)出了大量東方學(xué)的專業(yè)人才。1956年季羨林任中國(guó)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委員。期間歷經(jīng)磨難受盡屈辱。結(jié)束后于1978年復(fù)出任北京大學(xué)副校長(zhǎng)、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及北京大學(xué)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zhǎng)。1984年,改任北京大學(xué)南亞?wèn)|南亞研究所所長(zhǎng)。2009年7月11日因病辭世[1]50。 二、成為享譽(yù)海內(nèi)外的東方學(xué)大師。季羨林曾評(píng)價(jià)自己是雜家,梵學(xué)、佛學(xué)、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guó)文學(xué)、比較文學(xué)、文藝?yán)碚撗芯魁R飛。季羨林一生著述頗豐,著作書(shū)目有《中印文化關(guān)系史論叢》、《〈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rùn)集》、《季羨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羨林文集》中。其中翻譯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譯自德文的馬克思所著《論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shuō)集》;譯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樂(lè)》等;譯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長(zhǎng)篇史詩(shī)《羅摩衍那》、印度著名劇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詩(shī)劇《沙恭達(dá)羅》和五幕詩(shī)劇《優(yōu)哩婆濕》、反映印度民間故事的《五卷書(shū)》等等,涵蓋了印度古代語(yǔ)言、佛經(jīng)、梵語(yǔ)、吐火羅語(yǔ)、印度的歷史和文化等內(nèi)容。《羅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史詩(shī)之一,被奉為印度敘事詩(shī)的典范,在印度文學(xué)史上占據(jù)著崇高的地位,對(duì)整個(gè)南亞地區(qū)和宗教都產(chǎn)生過(guò)深遠(yuǎn)廣泛的影響。在中飽受折磨,被下放看門(mén)的季羨林在創(chuàng)作與研究都不能進(jìn)行的困境中,繼續(xù)堅(jiān)持翻譯方面的工作,并選中了這部氣勢(shì)恢宏的史詩(shī)巨篇《羅摩衍那》,由于歷史環(huán)境的限制,季羨林只能偷偷地進(jìn)行翻譯,由于《羅摩衍那》是以詩(shī)體的形式寫(xiě)就,季羨林堅(jiān)持譯文也應(yīng)是詩(shī)體,要將每首三十二音節(jié)的頌譯成四行漢詩(shī)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況還要考慮到八萬(wàn)行詩(shī)的押韻,常常為了找到一個(gè)合適的詞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時(shí)間里,七篇的《羅摩衍那》譯了還不到三篇。結(jié)束后,季羨林的翻譯工作才光明正大地進(jìn)行,終于在1983年2月將《羅摩衍那》翻譯完畢,這是除英譯本之外世界上僅有的外文全譯本。 十年風(fēng)雨、十載心血,方鑄就了這部長(zhǎng)達(dá)兩萬(wàn)頌,譯文達(dá)九萬(wàn)行,五千余頁(yè)的巨著。 《羅摩衍那》的翻譯是中國(guó)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印的文化交流鑄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因此被印度指定為印度和亞洲文學(xué)會(huì)分會(huì)主席,被印度文學(xué)院授予名譽(yù)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將印度公民榮譽(yù)獎(jiǎng)授予當(dāng)時(shí)已97歲高齡的季羨林[2]101。 季羨林在梵文翻譯上的成就眾所周知,而在吐火羅文的譯述上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本已經(jīng)失傳的語(yǔ)言,僅憑著20世紀(jì)初在中國(guó)新疆發(fā)現(xiàn)的一些殘卷而重新面世。季羨林在德國(guó)留學(xué)時(shí)曾經(jīng)師從艾密爾西克對(duì)吐火羅文進(jìn)行過(guò)學(xué)習(xí)與研究。1974年時(shí),在新疆又出土了44頁(yè)88面殘卷,當(dāng)時(shí)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個(gè)人懂這種語(yǔ)言,而整個(gè)中國(guó)只有季羨林懂這些文字,時(shí)年63歲的季羨林經(jīng)過(guò)17年的研究,終于破譯了全部殘卷,并譯著出《彌勒會(huì)見(jiàn)記》,那時(shí)候他已經(jīng)是80歲高齡的老人了。《彌勒會(huì)見(jiàn)記》的譯釋,對(duì)佛教傳入中國(guó)的經(jīng)歷,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據(jù)。季羨林多年從事各種文字文學(xué)作品的研究與翻譯,出版的譯作將近四百萬(wàn)字。中國(guó)翻譯協(xié)會(huì)2006年將首次頒發(fā)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jiǎng)給予了季羨林,是對(duì)他為中國(guó)翻譯事業(yè)所作貢獻(xiàn)的一種肯定。 三、季羨林的翻譯思想 季羨林一生所獲榮譽(yù)與頭銜非常多,但他自己樂(lè)于接受并承認(rèn)的只有兩個(gè),一是教授,一是翻譯家。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季羨林謝絕所有聘任,唯獨(dú)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國(guó)翻譯協(xié)會(huì)名譽(yù)會(huì)長(zhǎng),其目的竟是為了便于為翻譯工作提意見(jiàn)。季羨林認(rèn)為,中國(guó)文化從未枯竭的原因是因?yàn)椴煌5赜行滤枷胱⑷耄畲蟮膬纱嗡枷胱⑷耄淮问莵?lái)自印度,一次是來(lái)自西方。這兩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因此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與他在清華的恩師之一吳宓一樣,贊同嚴(yán)復(fù)在翻譯上提出的信、達(dá)、雅的標(biāo)準(zhǔn)。他認(rèn)為信是忠于原著,達(dá)是忠于讀者,雅則是對(duì)于文學(xué)語(yǔ)言的忠誠(chéng)。即譯者需要同時(shí)忠于作品、作者和語(yǔ)言。同時(shí)做到這三個(gè)字,就是上等,可以說(shuō)是盡翻譯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達(dá)雅不足,則是中等,而不信不達(dá)不雅則為下等。他認(rèn)為信是翻譯的基礎(chǔ),如果不能做到忠實(shí)于原文,就不叫翻譯。#p#分頁(yè)標(biāo)題#e# 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原則。 這點(diǎn)在他翻譯《羅摩衍那》這部印度原始的詩(shī)時(sh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為了將原文的詩(shī)體譯成中國(guó)的詩(shī)體,他決定采用順口溜似的民歌體。 同時(shí)將原文分兩行寫(xiě)的32個(gè)章節(jié)的頌譯成四行,每行的字?jǐn)?shù)基本整齊,并且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季羨林可謂用心良苦。 譯至第六篇《戰(zhàn)斗篇》下半部時(shí),季羨林更為嚴(yán)格地將每行定為七言絕句,間或也有五言,從而更接近于民歌體。除了譯文更加簡(jiǎn)潔精練,保留了原文的節(jié)奏,盡可能地忠實(shí)于原文。季羨林在翻譯中不但忠實(shí)保留了原詩(shī)的信息,還盡量押大致上口的韻,在忠實(shí)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體之雅[3]133。 在音韻上以偶數(shù)行押韻,韻腳靈活,音韻協(xié)調(diào)上口,譯文達(dá)到了信與美的效果。 季羨林的翻譯思想還體現(xiàn)在《羅摩衍那》的音譯上。 為了保持忠實(shí)于原文,能準(zhǔn)確地選擇譯音,他通過(guò)研究中國(guó)古代佛經(jīng)翻譯的實(shí)踐與翻譯文化,基本上使用過(guò)去中國(guó)和外國(guó)和尚翻譯經(jīng)文時(shí)使用的對(duì)音方法,盡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羨林所主張的直譯,在信的基礎(chǔ)上,還在漢語(yǔ)習(xí)慣以及文法允許的范圍之內(nèi),適當(dāng)引進(jìn)一些外國(guó)語(yǔ)法中比較周密的表達(dá)方式,使?jié)h語(yǔ)表達(dá)方式更加豐富,從而更適應(yīng)需要。這與魯迅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觀頗有相似之處。但與魯迅不同的是,季羨林反對(duì)重譯,即不通過(guò)原文而對(duì)某國(guó)譯文進(jìn)行的二次翻譯。他認(rèn)為科學(xué)與哲學(xué)類必要時(shí)可以進(jìn)行重譯,文學(xué)作品則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來(lái)形容重譯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影響。 季羨林認(rèn)為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關(guān)重要的,否則思想就無(wú)法溝通、文化無(wú)法交流、人類社會(huì)就難以前進(jìn)。正因?yàn)榉g的重要性,季羨林十分重視翻譯職業(yè)的道德,主張翻譯行業(yè)的工作者,應(yīng)該多學(xué)幾門(mén)外語(yǔ),提高自己的專業(yè)水平,同時(shí)改革大學(xué)外語(yǔ)學(xué)法,大力培養(yǎng)職業(yè)翻譯家,建立保證翻譯質(zhì)量機(jī)制,并再三公開(kāi)請(qǐng)?jiān)O(shè)國(guó)家翻譯獎(jiǎng),足見(jiàn)他對(duì)中國(guó)翻譯事業(yè)的關(guān)切與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