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中國古代哲學生態化分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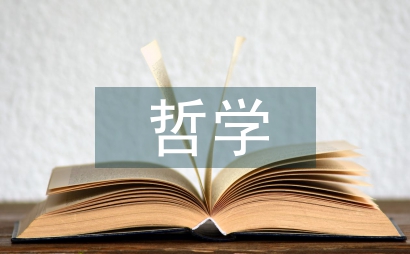
摘要: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對西方哲學的譯介、中國哲學的反思與重構以及“以西釋中”的中國哲學傳統研究范式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生態化轉向的歷史基礎。使得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古代哲學的生態化轉向得以可能,并逐步發展至今,形成一系列學術成果。
關鍵詞:中國古代哲學生態化;歷史基礎;中國哲學史;生態化
中國古代哲學的生態化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發展至今已形成儒家生態哲學、道家生態哲學、佛家生態哲學,不僅有力的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同時也擴展了生態哲學研究的范圍,對于今天的生態文明實踐也有著重大現實意義。而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中國古代哲學生態化得以可能,必然伴隨著一定的歷史基礎。因此,在中國哲學史的視角對其溯源,探尋發軔背后的歷史基礎。
一、突破“兩個對子”的窠臼
回顧中國哲學史的發展歷程。在20世紀50年代對于蘇聯“一邊倒”的學習中,以1957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全國哲學大會為起始。唯物主義——進步階級——辯證法;唯心主義——反動階級——形而上學的邏輯鏈條的確立,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辯證法同形而上學、進步階級同反動階級相互對壘的兩大陣營形成。此后的中國哲學研究大都以此為綱,在“”時更是演變為“儒法之爭”。這種機械、簡單的劃分和錯誤的解讀致使中國哲學研究處于混亂、徘徊之中。而轉機出現在改革開放后。在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等老一輩學人的帶領下中國哲學界開始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科學化”。在80年代早期回答了如何建設學科、如何處理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等重大議題并開展了范疇史研究。在如何建設學科,如何處理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上。以任繼愈先生《克服兩個缺點》(1982)一文為代表,試圖回答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如何回到中國哲學史內部研究中國思想這兩個問題。提出:一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不能滿足于只找出某家某派哲學產生的根源,指出它是它為什么階級、為什么人服務的就完成任務了,但哲學史真正關心的是應當是哲學家的思想體系,因此必須對哲學家的思想進行細致的剖析。此外,哲學史事實上講的是思想,哲學史的發展因而只能是思想的發展,這就要求將思想發展的脈絡講清楚;二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就只使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而不顧理論本意,模糊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同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界限。以張岱年先生為代表的“范疇史”研究則主張回到中國哲學本身,回到中國哲學文本本身,回到不同時期的思想家、思想體系、文本中去。這對打破二元對立,以及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道”等概念、范疇的系統梳理,為后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為生態化關于“天人合一”“生生”等的討論奠定基礎。基于此,給中國哲學史從內史出發,從多種角度出發解讀中國古代哲學破除了理論障礙使生態化得以可能。
二、中國古代哲學的現代面向
20世紀80年代國門再度開啟,理論視野得以開闊。以“蕪湖會議”“太原會議”為標志,中國學者開始認真的對待、研究西方哲學。在1978-1990這段時期開展了“人的哲學”研究、完善了教材體系和學科體系。而為了擺脫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突破二元對立的窠臼,透過西方哲學對照自身,亦是一個時期內中國哲學史界的關切。以《中國哲學史研究》雜志為代表,開辟了“中國哲學史研究在國外”等專欄密切關注海外相關動態,同時發表了《黑格爾論中國哲學》(1983)、《類概念:亞里士多德邏輯和墨家邏輯的鎖鑰》(1989)等文章,或關注西方哲學如何看待中國哲學,或嘗試進行中西哲學比較。此外,以杜維明、牟宗三等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學說也在這一時期得以引進。而放眼整個哲學界,隨著全面的撥亂反正,關于哲學的未來在哪里的討論亦不絕于耳,現代化便在此背景下展開。1985年《哲學動態》雜志社“哲學與現代化”研討會;安徽省哲學現代化討論會;“沈陽哲學與現代化高級講習班”分別召開,在對于“現代化”的談論中雖然各有各的側重點,但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一要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講“哲學現代化”,不能離開現實基礎而空談哲學的“中國化”。更要弘揚傳統辯證思維方式,深化中國古代哲學、近代哲學以及現代哲學的研究,取其精華,使之融會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之中;二是哲學“現代化”,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象、范疇、體系等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否則就無法正確處理哲學同現代化的關系,從而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一個封閉的、僵化的體系;三是注意吸收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社會科學的成果,保持哲學應有的活力中國哲學史在8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討論從某種程度上呼應了現代化的“要求”,中國哲學史得以開始“講自己,自己講”。生態化便是從中國古代哲學出發的中國哲學史的生態面向、是對于現世代的環境與發展問題的中國的哲學思考,從某種程度而言是中國現代哲學的一類。
三、“以西釋中”的傳統方法
中國哲學創立伊始,有關于古代中國是否有哲學的合法性爭論便一直存在。從某種程度上關于中國有無哲學這一爭論,一是因為中國古代本無哲學這一概念,二是因為“以西釋中”的傳統研究范式。正如喬清舉教授所言: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為分界,將之前的這一學科草創時的各國相關的哲學通史著作和此后的包括中國臺港地區在內的代表性著作視作整體進行考察,目前為止的中國哲學研究,某種意義上只存在以西釋中一種模式,不存在本土化的研究模式。盡管除了“以西釋中”外,還有如:張岱年于《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一文中所表述的將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的解析方法相結合,即創新綜合的模式,亦或是郝樸寧《莊子的生態觀》等文在此基礎上,針對某一具體的方面利用辯證思維對傳統的思想觀點進行重新解釋和注解的方式,但從源頭考察,始終包含著一定的以西釋中的研究思想、方式,更多的是對于以西釋中范式的一種發展、延伸。因此很難受是一種完全獨立的研究范式。中國哲學“以西釋中“的傳統范式,一方面為中國古代哲學同西方環境相關的哲學理論的聯系建立與相互比照確立方法論的前提。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哲學同西方哲學間比照、融會,關于中國哲學研究的范式的討論以及合法性的問題在80年代末進入學界視野,并延續至今為曾中斷。但無論怎樣,就中國古代哲學的生態化研究來看“以西釋中”這一基本的研究范式無疑是中國古代哲學生態化的重要歷史前提。
四、結語
中國哲學史的視角下,古代哲學的生態化研究的歷史基礎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在20世紀80年代,突破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兩個對子以及中國哲學史學科科學化;西方哲學引入與哲學現代化;“以西釋中”的傳統方法與中國哲學的研究范式分別確立了內容、現實、方法上的歷史前提,才使得中國古代哲學生態化的研究得以可能。
作者:張勁松 單位: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