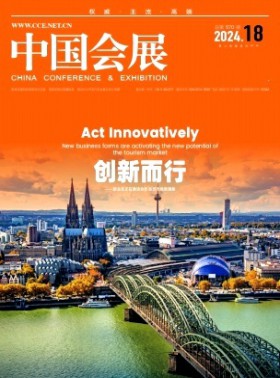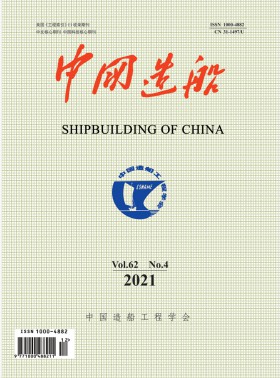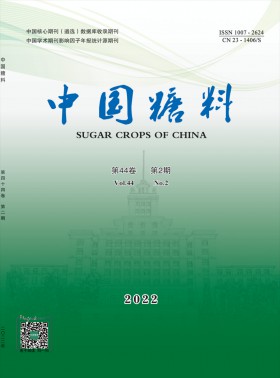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中國基礎教育70年識字教學探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回顧基礎教育識字教學改革歷程,其發(fā)展邏輯清晰可辨。通過對20世紀中葉以來基礎教育領域識字教學方法發(fā)展歷程的梳理,可將其分為沿襲繼承、初成體系、改良完善和孳乳派生四個關鍵階段。對基礎教育識字教學演變軌跡的回顧,有助于我們更為理性地審視基礎教育識字教學改革的內外因素,更為清晰地把握基礎教育識字教學改革的未來走向。
關鍵詞:基礎教育70年;識字教學:漢字識記
自古至今,漢字教學一直是語文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封建時代傳統(tǒng)漢字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訓詁,重漢字的構造和字體的演變而輕現(xiàn)實的文字應用。新中國成立后,社會語文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由于實際應用需求和外部環(huán)境變化,使識字教學相關理論向更高階段推進,基礎教育識字教學的實驗和研究也打開了新的局面。
一、中國基礎教育
70年識字教學的變革歷程自20世紀中葉以來,基礎教育領域識字教學方法的變革與其他一般事物的發(fā)展一樣,是前進性和回復性的統(tǒng)一,其發(fā)展的總趨勢契合了事物發(fā)展前進上升的螺旋式,大體可以被梳理為沿襲繼承、初成體系、改良完善和孳乳派生四個階段。
1.沿襲繼承。20世紀中葉之前,各類關于漢字學的專著已奠定了漢字識字研究的基礎,如姜建邦所著的《識字心理》、艾偉所著的《漢字問題》等,其中《識字心理》首開從心理學角度對現(xiàn)代漢字教育教學進行研究的先河。自20世紀50—80年代,研究者在沿襲和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提高了對識字教學效率和效果的重視,將視野聚焦于識字教學方法的探索,這標志著漢字的識字教學研究歷史將開辟新紀元。
2.初成體系。自20世紀80年代有關現(xiàn)代漢字學與現(xiàn)代漢字教學的研究開始覺醒,識字教學相關理論體系的雛形初步顯現(xiàn),如蘇培成所著的《現(xiàn)代漢字學綱要》、傅永和所著的《規(guī)范漢字》。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將漢字學理論體系與其他學科理論體系交叉耦合的學術現(xiàn)象,如現(xiàn)代漢字學與心理學交叉耦合,有昌學湯所著的《漢語錯別字心理分析》;現(xiàn)代漢字學與教學論交叉耦合,有戴汝潛所著的《漢字教與學》。
3.改良完善。進入21世紀,國外諸如布魯姆的教學目標分類理論、加涅的學習結果分類理論等基于科學心理學的理論被引入國內進行翻譯及出版,皮連生、戴汝潛等人均從科學心理學的角度進行了包含識字教學的基礎教育語文學科教學設計的本土化探究,識字教學相關理論體系得到了科學化的改良。1994年“首屆小學漢字識字教學國際研討會”、2006年“第二屆漢字教育國際研討會”、2018年“第三屆漢字教育科學化國際研討會”等諸多會議的召開,意味著學界開始將研究視野聚焦于探索漢字教育教學的科學化發(fā)展道路上。
4.孳乳派生。隨著教育部2001年印發(fā)《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2001年印發(fā)《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2011年修訂印發(fā)《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基礎教育識字教學也面臨著改革的迫切要求,研究者結合時代要求和小學語文的學科前沿與學術熱點,從不同角度圍繞如何改善識字教學效果展開了深入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其一,重新審視漢字學習的意義,尤其強調其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意義;其二,針對某種識字法在基礎教育識字教學領域的應用研究;其三,針對我國基礎教育領域識字教學現(xiàn)狀的調查研究;其四,針對以漢語言作為交流語言、以漢字作為交流文字的漢語言區(qū)識字教學現(xiàn)狀的比較研究等。
二、中國基礎教育
70年識字教學的經驗梳理基礎教育識字教學發(fā)展的70年間,教師在教學與研究過程中有意識地引介有關現(xiàn)代漢字構形、學生識字心理的相關理論,進行了多場教研實驗,通過實驗總結出許多經驗方法。
1.分散識字。分散識字也可稱隨課文識字,起源于后的20世紀20年代。分散識字講究“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1],教學內容按“生字—課文”的順序講授。分散識字重視把生字放在特定的語境中,旨在實現(xiàn)生字與課文、識字教學與閱讀教學的兼顧與耦合。
2.集中識字。集中識字的教學試驗始于小學,起初的遼寧黑山北關小學與后期加入的景山學校、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發(fā)展為“兩山一所”的集中識字教學流派。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蘇培成在《現(xiàn)代漢字學綱要》中將集中識字教學法的要點總結為:先識字,后讀書;“基本字帶字”是歸類識字的好方式;識字與讀書相輔相成,有分有合等等。
3.注音識字法。注音識字法并非始自基礎教育的教學實踐中,而是始自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成人掃盲運動。為快速有效地完成艱巨的掃盲任務,探索一種能夠適應全國范圍內掃盲運動的識字教學方法成為了問題的切入點。1982年注音識字被應用于基礎教育實踐,黑龍江省首先在小學開展了“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教學實驗。
4.字理識字法字理識字法起源于1994年湖南省岳陽市小學的教學實驗。該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先教獨體字,后教合體字”[1],象形字和指事字屬于獨體字,會意字和形聲字屬于合體字,然后如庖丁解牛一般地對漢字進行解構、重組,以每一個析出的部分為單位,以每一個“結構—重組”為識記的基礎。
5.炳人識字法。炳人識字法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是一種針對兒童學前教育階段的識字方法,基本思路是使用歌謠幫助兒童初步認識字形并記憶讀音。這里所指的歌謠是一種講究合轍押韻、頂針連環(huán)的七言一句的韻文,配有專門對應每句韻文的律動操,強調邊說邊做,并且適用于小組學習或集體學習。
6.字族文識字法。“字族文”是以某一字族為主要生字而創(chuàng)編的文情并茂的新型課文文體,含韻文體、散文體和韻散體三類[2]。字族文識字法則是要根據(jù)漢字的孳生繁衍規(guī)律,圍繞著“母體字”這一邏輯起點,將一組結構規(guī)律化的漢字編為一族童謠,使分散的識字教學資源序列化。20世紀90年代四川省井研縣教育局課題組著手進行了第一輪實驗,并且按漢字的構字規(guī)律編制了配套教材。
7.部件識字法。部件識字法也可稱部件析形識字法。1965年部件識字構想在《文字改革》上被提出。現(xiàn)代漢字結構層次分為筆畫、部件和整字,而部件識字的基本思路是對漢字進行外部結構分析,析出部件,以漢字部件為線索進行識記。部件識字不僅能夠提高學習者瞬時識記效率,還能提高平時工具書檢索效率。
8.雙腦識字法。“雙腦”是指人腦和電腦的配合,基本思路是將識字與用計算機打字相結合,所用的是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一套區(qū)別于全拼輸入的雙拼碼,采用26個英文字母拼出漢字,由上海實驗學校于1991年首先引進。雙腦識字符合漢字本身聲韻雙拼的特點,能提高學習者單位時間生字初學和后續(xù)復習的效率,優(yōu)化學習者的識字學習效果。
9.韻語識字法。韻語是一種包含豐富語意而又合轍押韻的詞句。該方法依托一系列具有適當密度漢字的韻語,對漢字的形與音進行多次復現(xiàn),基本思路是韻語識字—盡早閱讀—循序作文。該方法重視對兒童讀、寫、說能力的培養(yǎng),將漢字識記與適度抄寫相結合,將循序作文視為發(fā)展預期,并設計了配套的教材和教法,于1995年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且受到廣泛好評。
10.其他方法。除此之外,還有張繼賢根據(jù)字根將漢字編為字組的字根識字法,黃劍杰以現(xiàn)代科學分類為基礎的科學分類識字法,李衛(wèi)民聯(lián)想串字成文的聯(lián)想識字法,趙明德利用漢字智力游戲教具的立體識字法,解構出偏旁帶字的解形識字法,以形示義的成群分級識字法,以漢字啟蒙代拼音啟蒙的漢標識字法等等。
三、中國基礎教育識字教學
70年對新時代的啟示教師是教學的引導者、組織者及合作者,教師教學工作的關鍵績效指標KPI可以通過學生的學習效率與學習效果間接體現(xiàn)。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的癥結,了解識字教學的嬗變史,有助于得到以追求識字教學質量、應對新時代基礎教育發(fā)展要求為指歸的啟示。
1.引入基礎的現(xiàn)代漢字學理論。“所謂識字者謂見形而知聲、義,聞聲而知義,形也。”[3]在文字學習“識”和“記”的過程中,拼音文字的單位是字母,它的教學側重點在于引導學習者記憶字母序列;而漢字作為一種表意體系的文字,它的單位是一種語素,關照在教學中,就是側重引導學習者掌握漢字的表意方式。基礎教育識字教學要有意識地援引有關現(xiàn)代漢字學相關理論,適當講解漢字文化,利用漢字的系統(tǒng)性,引導學生借助漢字學習形音義,逐步達成“認識—理解—記憶—應用”的學習期望。
2.整合多元的識字教學資源。漢字知識和識字教學資源的雜亂無序或模糊不清,也是兒童學習者識字學習效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提高識字教學效率,需要整合基礎教育領域的識字教學資源,使其序列化、體系化。“學校要有強烈的資源意識,認真分析本地和本校的特點,積極開發(fā)潛在的資源”[4],同時“語文教師應高度重視課程資源的開發(fā)與利用,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各類活動”[4]。落實在教學實踐中,可以從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漢字文化、探索云環(huán)境下區(qū)域教育資源共享、利用校本文化中的隱性識字教學資源以及融合多樣的先進多媒體教學手段等方面入手。
3.順應兒童的識字心理機制。“語文學習不僅遵循認知結構發(fā)展的普適規(guī)律,也有其特殊性。”[5]由于兒童學習者認識外界事物、對外界信息進行加工的認知能力發(fā)展的特殊性,極易出現(xiàn)筆畫增刪、筆畫形態(tài)錯誤、部件偷換、整字形態(tài)錯誤等漢字使用偏誤。基礎教育識字教學應遵循學習者的認知發(fā)展規(guī)律,以追求高效率為指歸,又兼顧高質量,從漢字形音義規(guī)律入手展開教學,充分了解學習者的識字心理機制,探索認識與記憶漢字過程中形、音、義之間聯(lián)系的建立過程。
4.重構智能的識字教學模式新樣態(tài)。人工智能正以清晰的路徑變革著基礎教育識字教學生態(tài)系統(tǒng),探討如何實現(xiàn)以教學模式的新樣態(tài)對接新時代,存在著邏輯合理性與現(xiàn)實需求。理論層面上,對我國傳統(tǒng)的識字教學模式進行繼承與創(chuàng)新,能夠為選擇識字教學的實踐攻關方向、確定識字教學“應然”的科研課題以及進一步制定基礎教育識字教學發(fā)展長遠規(guī)劃等提供導向性情報。實踐層面上,重視建立針對錯字、別字及不規(guī)范字的應急機制,實現(xiàn)基礎教育識字教學信息化從融合發(fā)展向創(chuàng)新發(fā)展轉變,實現(xiàn)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的代際躍升。
5.科學評價兒童的錯別字現(xiàn)象。第一,評價要引導學生正確歸因,教學過程中的獎懲從來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第二,評價要合理運用診斷性—形成性—終結性的、定性—定量的、自評—互評—師評的多元評價方式。第三,評價要尊重學習者的個體差異。第四,評價要正確認識語文學科素養(yǎng)的整體性,識字寫字要兼顧閱讀、習作、口語交際及語文綜合性學習等,不能將學習者的綜合素質割裂開來。第五,評價要講究語言藝術。
參考文獻:
[1]蘇培成.現(xiàn)代漢字學綱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250.
[2]四川省井研縣教育局課題組.“字族文識字”教學實驗研究[J].教育研究,1994(5):49—53.
[3]艾偉.漢字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5.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34.
[5]董蓓菲.語文識字心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48.
作者:單琪雅 單位:通化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