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方式問題,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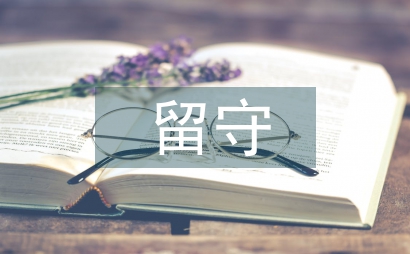
摘要:問題解決是當前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基本方式。但是,問題解決式的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是對家庭教育的狹隘化理解,易使家庭教育遭遇“次級越軌”危機,不利于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家庭成長教育,以農村留守兒童為中心,注重發揮其“心理彈性”作用,建立積極的自我認同;盡力為農村留守兒童成長教育創設“保護性因素”:組建積極的同伴群體,創設有針對性的家庭、學校、社會環境,幫助農村留守兒童健康成長。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需要實現從問題解決到成長教育的積極轉變。
關鍵詞: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問題解決;成長教育
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員及家庭環境對兒童成長的影響過程,也是家長與子女之間進行的一種雙向成長的過程。[1]當前農村留守兒童存在的一系列心理、學業、安全問題成為其家庭教育的關注焦點,牽引、滯絆著家庭教育的進行。因此,“問題解決”成為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務及內容。幫助兒童成長是家庭教育的最根本任務,問題解決不等同于兒童的成長,也不應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需要以發展的視角來解決問題,以兒童為中心、為主體,為其發展創設環境,幫助兒童健康成長,實現從“問題解決”到“成長教育”的轉變。
一、“問題解決”式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及其弊端
問題解決即通過社會化、非正式團體的壓力、獎懲等方式進行社會控制的過程與方法。社會通過社會規范來約束其成員,與社會規范不一致的個人或群體被稱為偏差者,成為需要管束制約的對象。[2]留守兒童因其行為特征較普通兒童存在偏差,被貼上“問題兒童”標簽,成為被管束的對象。因此,“問題解決”式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是以普通兒童為社會規范,對留守兒童進行家庭管束的過程。
(一)“問題解決”成為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
農村留守兒童泛指父母雙方或單方外出而被留置在農村的6—16周歲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群體。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問題既包括留守兒童自身存在學業落后、安全保障缺失、行為失范,監護人家庭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方法不當等顯性問題;又包括一些具有隱蔽性、潛伏性的隱性問題,即受家庭環境、家長觀念等因素的局限,難以意識到或者被忽視的問題。例如,兒童藝術審美、創造性思維、創造能力的培養,早戀、閑暇教育等。現存問題的解決困難重重,新生問題源源不斷。《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相關數據顯示: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且增加趨勢明顯,46.74%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單獨居住的農村留守兒童高達205.7萬,與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業已成為政府、社會團體組織、學術界等共同面臨的難題,問題解決也成為當務之急。在整個社會努力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背景下,受“問題”及“解決問題促進留守兒童健康發展愿望”的驅動,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關注焦點也轉移到問題解決之上,“問題解決”成為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中心。留守兒童家庭多分布在我國中西部經濟欠發達省份以及東部經濟發達省份的欠發達地區,家庭教育資本相對匱乏,難以為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持與保障。家長外出務工,子女隨遷遇阻,留守兒童必須接受隔代監護、單親監護或者同輩監護,而監護人教育觀念、教育方式方法參差不齊,家庭教育完整性、科學合理性難以得到保障。家庭教育難以順利實施,問題源源不斷,解決問題成為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應對方式,也成為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基本內容。
(二)“問題解決”式家庭教育的弊端
家庭是自然形成的教育環境,也是個體生活最為放松的場所。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一般缺少專門計劃,家長及孩子的家庭行為較為隨意,多在日常活動中對孩子進行教育和訓練。家庭教育的生活屬性本就容易滋生問題,并且出現問題而不能自察。以“問題解決”為中心,使得家庭教育陷入問題情境,兒童成為被管制約束的對象,窄化家庭教育的應有作用,不利于更好地實現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發展。一是窄化家庭教育內涵。解決兒童成長中遇到的問題,是家庭教育應有之意。問題解決有助于兒童成長,但是問題解決不等同于兒童的成長教育,更不是家庭教育的最終目標。未來社會對個體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學會學習、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發展”成為兒童成長過程中需要培養的基本素質,這些基本素質的培養需要通過教育來輔助實現,家庭教育必然要承擔起應有的職責,這也是家庭教育的應有之意:要通過注意力、記憶力、思維能力的培養幫助兒童學會學習,激發兒童好奇心、批判精神、獨立思辨能力;未來“先進經濟”的非物質化使得關系能力成為兒童成長、進入社會生活的必要“資格”,家庭教育要幫助兒童增強這種基于交往、與他人共處、解決沖突的“關系能力”;要增強兒童自我認識,培養“情感同化態度”,以實現共同的目標,實現兒童與他人一起幫扶成長;要幫助孩子盡可能參與到美學、藝術體育、科學、文化和社會方面的發現和試驗機會”中去[3],成為未來社會有責任感、有知識、有自我標準的建設者。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經濟、文化資本相對貧乏,或許難以為留守兒童的成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與保障。但是,應該意識到并摒棄“把問題解決等同于兒童成長的偏頗觀念”。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家庭教育,是對家庭教育作用的窄化。家庭教育需要解決留守兒童成長問題,更需要幫助兒童在家庭教育中提高,在生活中獲得基本的素養,鍛煉提升其學習、做事、交往、生活等各方面能力,為未來發展提供無限可能。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家庭教育無疑窄化了家庭教育的應有作用。二是造成“問題兒童”暈輪效應。社會標簽理論認為“越軌”即社會大眾賦予某些特殊群體的標簽[4],一旦某人被貼上越軌標簽,就容易遭遇“次級越軌”危機,即被他人標定為“越軌者”,且自身也逐漸接受這種標定。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家庭教育會形成一種消極標定,即留守兒童是“弱勢群體”“問題兒童”,并無意識作用于監護人的態度和行為,不僅會對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帶來不利影響,而且無益于留守兒童問題最終的、有效的解決。[5]“弱勢群體”“問題兒童”的標定,更多地關注留守兒童人格成分中消極的特質,相對忽視其中積極的成分;模糊了留守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的界限,留守兒童本身被看作“解決”的對象,這一認識易對監護人家庭教育觀念與行為造成錯誤的引導,對家庭教育的實施造成負面影響。家庭之中,監護人與留守兒童朝夕相處,作為留守兒童的“重要他人”,對留守兒童自我標定,即認識、評估自我行為,形成自我認識具有重要作用。美國社會學家庫利提出“鏡中我”概念,認為“兒童總是設想或理解外界對自己行為的評價,并根據自己對外界評價的想象來評價自己的行為,作出反應,進而形成自我認識”“人之所以認為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乃是因為周圍的人,一再以同樣的詞語來描述自己”。[6]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家庭教育,監護人在無意識中把孩子當作“問題兒童”更會嚴重阻礙留守兒童自尊、自我效能感及積極自我認識的形成,這種無意識的危險教育觀念必須剔除,問題解決式的家庭教育觀念也必須摒棄。
二、從“問題解決”到“成長教育”的轉變
問題解決是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前提與基礎,也是成長教育的應有之意。但是,“問題解決”式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以問題為基礎,又以解決問題為基本目標,既依賴問題,又否定問題,把問題解決等同于家庭教育,本身具有不合理性。成長教育以兒童為中心,為主體,用發展的意識來指導家庭教育,解決問題,更有利于兒童的健康發展。因此,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需要完成從“問題解決”到“成長教育”的積極轉變。
(一)問題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前提與基礎
需要影響著人的行為方式與方向。馬斯洛提出“需要層次理論”,把人的基本需要劃分為五個層次,由低到高依次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較高層次需要才會出現。農村留守兒童父母雙方或者單方外出,缺少父母關愛;面臨單親監護、隔代監護、同輩監護,監護人安全意識較弱,安全問題頻發;被貼上“問題兒童”標簽,自尊心受挫,自我效能感降低。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安全、行為問題的產生,多因生理、安全、社交、尊重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問題解決有利于滿足兒童缺失的需要,這是兒童成長的前提條件,也是家庭教育順利進行的基礎與保障。但是,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更具社會價值,是完美人格的體現。缺失性需要的滿足僅僅保障人的生存,成長性需要的滿足才能使人更好地生活。問題解決式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無意識地把留守兒童作為問題兒童,僅關注兒童基本的需要,而忽視了留守兒童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要,窄化了家庭教育的應有之意,不利于兒童的健康成長。因此,問題解決僅是成長教育的前提與基礎,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需要完成由“問題解決”到“成長教育”的積極轉變。
(二)兒童成長: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本質追求
成長是兒童的天性,是兒童身心由未成熟狀態不斷趨向成熟狀態的動態過程,而且這一未成熟狀態蘊含生長的力量———可塑性和社會交往的本能。[7]因此,成長教育是以兒童的成長為取向的教育,要以兒童為中心,發揮兒童本身的力量,通過教育,幫助兒童由未成熟狀態不斷趨向成熟狀態,健康發展。家庭教育是以血緣為紐帶聯結的關愛教育。家長角色(父親、母親、爺爺、奶奶等)是以“孩子”的存在為基礎生成的,并以滿足孩子需求,促進孩子健康成長的關愛活動獲得意義。家長懷著對孩子本能的、生命性的關愛,家庭教育就成為這種關愛的一種表達方式。[8]因此,成長教育以兒童為中心,把兒童的發展放在首要位置。另外,家庭成長教育從兒童發展的視角出發,強調外在環境的指導控制作用,但也認同環境中的自我調節與自我適應。[9]因此,成長教育既注重外在環境的創設、改善,又重視留守兒童自我調節、適應、更新、擴展,形成積極自我認識,發揮主體積極作用。[10]
三、農村留守兒童成長教育的實施
留守兒童成長教育面臨重重問題,需要留守兒童對自我、對環境有客觀的認識,積極的理解,建構積極的自我認同;需要積極的同伴群體、適合兒童的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等“保護性因素”的建設,幫助留守兒童在困境中健康成長。
(一)引導農村留守兒童建構積極的自我認同
“心理彈性”指在顯著不利的背景中積極適應的動態過程。[11]該理論認為,處境不利兒童可以通過“克服逆境”“創傷積極恢復”,減少不利環境影響,實現良好發展。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經濟、文化資本貧乏,影響子女現在及未來教育資本的獲得,對子女的成長及未來發展將產生深刻影響。完整家庭結構及父母親情關愛的缺失使得這些影響更加復雜。但是,不利環境只是一種客觀狀態,并不等同于消極結果。從發展的機制考慮,不平衡的形式幫助形成“一種新的能力或實現某種再定向”。兒童需要從先前的自我中脫離出來,從他的環境中撤退出來,以積蓄前進的力量。[12]困難的家庭現狀,更需要農村留守兒童積極的自我能動作用的發揮,提升自我效能感,自信積極地面對困境,解決困難。健康的身體、強健的精神、良好的習慣、具備基本的生活技能等都有利于兒童積極自我認同的建構。健康的教育寓于健康的身體,留守兒童監護人要督促孩子注意飲食、少用藥、多運動、睡眠充足,保證身體的健康;要“珍惜、培植孩子的優點,溫和的改正與消除其不良傾向,養成良好習慣”[13]。在生活中鼓勵兒童堅強勇敢、不怕困難,培養兒童“強健的精神”,堅強應對逆境與困難、積極進行自我調控;進行基本生活技能訓練,例如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等生活技能;培養兒童多方面興趣與技能,讀書、繪畫、音樂等,預防留守兒童養成不良嗜好。
(二)引導農村留守兒童組建積極的同伴群體
兒童“心理彈性”作用的發揮,需要保護性因素(指能夠減少不利環境影響,實現積極發展的因素)的積極作用。積極的同伴群體作為一種“保護性因素”[14]對留守兒童擴充知識經驗,滿足社交需要,獲得友誼、支持與安全感,習得行為規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少年階段,兒童不斷發展成熟,對家長從依賴到獨立,從順從到自主,努力擺脫家長的束縛,進入“心里斷乳期”,親子關系隨之進入危機期,這一時期也是兒童發展的關鍵時期,極易形成不良習慣、嗜好。積極的同伴群體能幫助留守兒童時刻獲得幫助與支持,獲得源源不斷的積極動力,彌補這一階段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度過發展的關鍵敏感階段。積極同伴群體的建設需要留守兒童監護人相互支持配合、引導幫助。監護人要積極鼓勵留守兒童走出家門,多與同伴、朋友交流、交往;教導孩子尊重理解他人、樂于助人,形成親密的伙伴關系,建立一個互相尊重、互相幫助的群體;鼓勵兒童承擔群體管理職責,進行必要的監督,引導群體建立積極的群體文化、風氣、氛圍,通過共同完成作業、閑暇時間一起娛樂、發展相似愛好,遇到困難互相幫助等方式,讓群體成為留守兒童與朋友、同學之間互相鼓勵、監督、幫助、自我管理的樂園,成為留守兒童精神、學習、娛樂、交流溝通的樂園;號召留守兒童監護人積極參與,組織群體進行爬山、野炊等活動,增進親子關系、伙伴友誼,鍛煉兒童能力。
(三)為留守兒童積極創設“保護性”的家庭環境
兒童是積極主動的個體,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斷成長。家庭對留守兒童發展產生最直接影響。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教師,也是最容易犯錯的教師,問題兒童的背后總會存在問題家長、問題家庭。同時,家庭之外,學校、政府等相互作用形成了留守兒童成長更為廣泛的環境系統與資源,需要關注和利用,為農村留守兒童成長教育爭取更多保護性因素,幫助其健康成長。一要填補父母陪伴缺失導致的心理洼地。父母的陪伴是兒童成長過程中最溫暖的依靠,但是農村留守兒童面臨著父母外出、家長陪伴缺失的問題,易導致兒童缺少安全感。父母要意識到不在身邊并不代表陪伴的完全缺失,可以通過網絡、電話等方式多與孩子進行交流溝通,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要注意交流的方式方法與技巧,多鼓勵表揚,但不溺愛、放縱,慎用批評,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愛,愿意與父母溝通、做孩子的朋友。談話的主題不要一直圍繞成績,應關注孩子多方面的情況等。二要建設良好家風。家庭教育是一種“生活式”的教育,監護人在日常生活中對兒童進行教育,兒童在耳濡目染中獲得教育,是家長與孩子一起成長的過程。但是,家庭教育是自發形成,本身帶有隨意性,需要對留守兒童及其監護人進行家庭規范的建設。監護人需要引導,或與留守兒童一起制定家庭規約,共同遵守,并把這種規約內化為留守兒童及監護人的基本意識。家訓、家規、家誡等是我國家庭悠久的傳統,德教為先、修己安人、勤勉學習、起居有常等觀念仍有借鑒意義。監護人與兒童可以從生活瑣事著手,不斷完善,不斷升華。留守兒童家庭要注重培養“嚴慈相濟”的親子關系。“嚴”指督促留守兒童監護人嚴于律己,同時樹立必要的家長權威。關愛孩子是家長的本能,監護人也不要過于溺愛,使“慈”失去應有的界限。嚴慈相濟的親子關系,有利于兒童健康成長,避免過于嬌弱或放縱,尤其在“心里斷乳期”等關鍵階段,留守兒童開始嘗試建立自我判斷與價值標準,懷疑、反抗家長,嚴慈相濟能夠更好地幫助留守兒童實現平穩過渡。
(四)為留守兒童創建“保護性”學校、社會環境
留守兒童生活中絕大部分時間在學校度過,在課堂學習及課外活動中度過。施教者、教學內容、課外活動對留守兒童的影響意義重大且深遠。教師要與留守兒童建立一種真誠、接受、互相理解的關系。教師要清楚地認識留守兒童的現狀,并對其進行真誠的批評或鼓勵,促進留守兒童不斷改善提高。在教育內容方面,學校可以嘗試多種內容與活動。如,可以借鑒臺灣“融入式課程設計”,通過合適的教育主題融入,把家庭教育觀念及內容與課程教學有機融合起來進行;組織“家庭之日”活動,對監護人進行家庭教育指導,同時引導兒童積極理解留守現狀,并嘗試解決現有問題。政府應該在更高層次上進行家庭教育社會支持保障系統建設,聯合組織更多的社會團體,對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給以支持、指導,比如家庭教育志愿者活動,農村圖書館建設等。
參考文獻:
[1]宗秋榮.“中國家庭教育發展論壇”綜述[J].教育研究,2004(8):92-94.
[2]蔡文輝,李紹榮.社會學概論[M].臺北:三民書局,2013:58、129-138.
[3]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教育:財富蘊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1996:12.
[4]李紅,劉洪.組織中的建設性越軌行為研究回顧與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4(8):45-52.
[5]魏曉娟.積極青少年發展觀視角下的留守兒童“問題”與出路[J].青年探索,2015(4):106-111.
[6]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49—54.
[7]張進峰.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哲學新論[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5(1):52-57.
[8]雷堯珠,王佩雄.教育與人的發展[A].瞿寶魁,主編.教育學文集(2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92—198.
[9]田春.成長取向的兒童教育[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8:16-18.[11]
[10]曾守錘,李其維.兒童心理彈性發展的研究綜述[J].心理科學,2003(6):1091、1094.
作者:郭方濤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