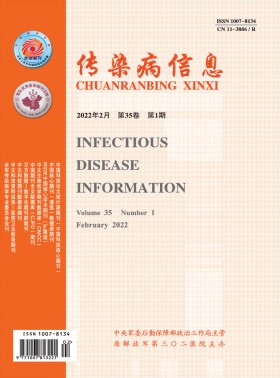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傳染病防治法制建構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為完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染病防治法制建構歷程,對不同時期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情況進行了梳理,總結了取得的主要成就及不足。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取得成效的關鍵在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法價值觀,堅持預防為主的立法指導思想,堅持集中統一領導、依法防疫的基本原則。為補齊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短板,應創新法律調控機制、完善配套立法及地方立法、重視立法中的技術性因素。
關鍵詞:傳染病防治;法制構建;法律保障
縱觀我國漫長的傳染病防治法制史,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傳染病防治法制史,在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領域,我國具有鮮明的特色和優勢。通過系統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傳染病防治法制建構歷程,能夠更為清醒地認識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巨大成效及其不足,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體系,提升我國傳染病防控能力現代化水平提供經驗及啟示。
1新中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歷程
1.1新中國成立初期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1949年~1965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關于衛生工作的一個重難點即疫病叢生、缺醫少藥。當時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威脅最大的主要疾病是各類急慢性傳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蟲病。以鼠疫為例,1950年5月15日~11月5日,東北地區暴發鼠疫,流行75天,流行范圍至吉林、內蒙古、黑龍江、松江、熱河、遼西等省(自治區),發病357人,死亡達176人,死亡率高達49.3%[1]。在當時經濟十分落后,缺醫少藥情況嚴重的歷史背景下,黨和政府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下大力氣解決傳染病肆虐的情況。早在1951年,主席就對傳染病防治與醫療工作做出過指示,他指出,衛生防疫等醫療工作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必須將其看作重大政治任務,努力完成。此階段關于常見傳染病的調查研究工作主要委托中華醫學會進行。并且,對傳染病防治工作給予了持續不斷的關注,指出傳染病防治不是孤立的衛生工作,應將其與當時的經濟社會宏觀趨勢緊密結合[2]。主席對當時全國防治血吸蟲病進展情況、“除四害、講衛生”運動發展情況、反細菌戰實施情況、華北地區傳染病防治情況等均作出過重要批示。、董必武等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高度重視傳染病防治工作,董必武還直接領導察蒙地區的鼠疫防治工作。這一時期我國國民經濟逐步恢復,但國家整體財力、物力仍然非常困難,黨中央和人民政府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突出地位,尤其注重傳染病防治工作,為此了一系列衛生行政法規,逐步建立了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醫療機構管理制度、醫務人員管理制度。在醫療法律制度基本建成之后,國家加快了公共衛生尤其是傳染病防治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設。1957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衛生法律《國境衛生檢疫條例》。20世紀50年代后期,因受“法律虛無主義”影響,發展勢頭良好的衛生立法腳步開始放緩,但仍出臺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行政法規。
1.2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恢復與發展(1966年~1988年)
在這一時期,許多相關法規與條例均因為被視為“管、卡、壓”的條條框框而被棄用。我國初步建立起來的傳染病防治法律規范體系遭到嚴重破壞,已經形成的傳染病防治法制框架被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勢頭良好的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遭遇到重大阻礙,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體系建設亟需恢復、重建和繼續發展。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我國開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征程。各項傳染病防治工作開始逐漸恢復,相關的傳染病防治法律、法規與標準也逐步發展起來。從1978年的《急性傳染病管理條例》開始,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的傳染病防治法律、法規陸續出臺。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來,傳染病防治事業也隨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在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方面,1977年底,原衛生部召開會議研討修訂、補充、完善之前的《傳染病管理辦法》。1978年,原衛生部組織召開座談會,為加強各地傳染病防治機構建設、積極開展傳染病防治研究工作等方面進行了部署,以期快速恢復傳染病防治事業,著力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提供優質勞動力。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歷史階段后,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也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起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3]。從1978年開始,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進入了恢復重建、快速發展的歷史階段。
1.3首部《傳染病防治法》的誕生及實施(1989年~2003年)
相比新中國成立初期而言,20世紀80年代導致我國人口死亡的因素發生了巨大變化。急性傳染病致死因素由原來的第二、三位下降到第七、八位,甚至十位以后。根據原衛生部的統計顯示,1985年我國傳染病發病人數總計9035567人,死亡人數20732人[4],傳染病致死率不足0.23%。但是,我國仍然遭受傳染病疫情的危害,某些已經滅絕的傳染病也死灰復燃。傳染病特別是急性傳染病仍極大地危害著我國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每年有相當一部分民眾受到各種傳染病的侵害。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我國與世界各國交往的逐漸擴大、深入,傳染病的輸入機會也逐漸上升,因此我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工作必須進一步提速、加強。這一時期,多年貫徹執行《傳染病管理辦法》《急性傳染病管理條例》的實踐經驗,為傳染病防治立法奠定了堅實基礎。1985年10月,在原衛生部的領導下,我國組建了《傳染防治法》起草小組。1988年12月13日,在李鵬總理的主持下,國務院召開第二十九次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傳染病防治法》草案。1989年2月2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傳染病防治法》。同日,原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發第15號主席令,公布《傳染病防治法》,1989年9月1日起施行。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傳染病防治法》問世,標志著我國傳染病防治事業進入全新階段,深刻地影響著此后的傳染病防治工作。
1.4傳染病防治法制體系的充實與完善(2004年至今)
鑒于2003年抗擊“非典”疫情過程中法律制度不完善導致的一系列問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對1989年《傳染病防治法》進行了修訂,修訂后的《傳染病防治法》于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5]。修訂后的《傳染病防治法》重點解決了抗擊“非典”過程中暴露出來的法律缺陷,對于傳染病防治工作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體現出一些特色和亮點,構建起了傳染病預防制度,報告、通報和公布制度,監督制度,控制及救助制度,財政支持制度等五類法律保障制度,是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重大進步。自此,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進入充實與完善階段。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對《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但修改內容較少。因此,2004年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成為了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體系的基礎。修訂后的《傳染病防治法》將傳染病防治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顯著提高了傳染病防治工作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監督指導力度加強,各部門、各地區堅持“以人為本、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傳染病預防控制指導原則,認真貫徹落實《傳染病防治法》,不斷健全傳染病防治體系,提升工作能力,強化保障措施,完善工作機制,新的傳染病防治法制體系建立起來,我國傳染病防治事業形成了由政府主導、各相關部門緊密協同合作、全社會積極主動參與的新局面,傳染病防治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2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成效
自2003年我國“非典”疫情暴發以來,黨中央和人民政府更加重視傳染病防治工作,全社會對傳染病的認識也不斷深化,我國傳染病防治工作進入了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時期: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發展最快、整體防治控制能力提升最快、經費投入力度最大、體系建設最完善。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4年對《傳染病防治法》進行修訂后,國務院依據此法,陸續頒布了一系列配套行政法規。國務院還對結核病、艾滋病等危害廣泛的傳染病制定了專項行動計劃或規劃。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再次對《傳染病防治法》進行了修改,優化了傳染病預防控制工作資源配置,完善了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調整了法定傳染病病種。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認真貫徹《傳染病防治法》的基礎上,陸續公布了多部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制度。其他相關部委也加快制定相關傳染病防治規章制度、相關病種診斷標準等。這一系列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從法律制度層面保障了我國傳染病防治事業的快速發展,我國傳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效。2004年以來,我國成功控制了包括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在內的各類新發傳染病疫情;我國重大傳染病得以有效控制,血吸蟲病疫情降至歷史最低水平;肺結核患病率和死亡率下降明顯;艾滋病疫情總體處于低流行水平。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發生后,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實現了大災之后無大疫的目標。2007年在全球率先消滅絲蟲病,2012年我國成功消滅了新生兒破傷風,繼續保持了無脊髓灰質炎疫情。甲類、乙類法定傳染病報告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低于272/10萬和1.25/10萬[6]。2013年上半年,我國暴發了新的傳染病疫情———人感染H7N9禽流感,在應對這一新發傳染病的過程中,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的功用得以充分發揮,傳染病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體系通過了實踐的檢驗。2015年,廣東省在應對我國第一例輸入性中東呼吸綜合征過程中,嚴格履行《傳染病防治法》,措施得力,反應迅速,疫情得以快速控制,社會反響良好。近年來,我國傳染病暴發流行情況整體上有所下降,艾滋病、結核病發病率穩步下降,兒童乙肝病毒防控成效突出。國家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率穩定保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絕大多數傳染病的發病率降至歷史最低水平[7]。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帶來的巨大成效進一步凸顯。
3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不足
隨著健康中國戰略的加快推進,公共衛生職能得以進一步拓展,對傳染病防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明顯短板。具體來看,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配套法律法規不健全,造成法律實施執行不到位。在我國整個衛生法規體系中,《傳染病防治法》與其他法律(如《食品衛生法》)相比,顯得缺乏全面性與系統性,亟需充實與完善。《傳染病防治法》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與監督執法程序等相關配套的法規條例,也缺少專用的監督文書。在傳染病防治的實際工作中只能按照《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借用衛生監督文書進行執法監督工作。傳染病防治是一項綜合的系統工程,當前我國傳染病防治相關領域的立法不夠完善,《傳染病防治法》與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協同性不強,野生動物保護、生物安全等領域立法滯后。第二,對《傳染病防治法》的重視程度不夠、宣傳不力,導致貫徹不力。《傳染病防治法》的貫徹與實施是極為重要的,關系到傳染病防治工作的有效開展。部分地方政府將經濟效益作為工作中的重心,未能充分認識傳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對傳染病防治工作重視不夠,未能及時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傳染病防治法律法規,《傳染病防治法》宣傳力度不夠,導致在防控重大疫情時治理能力有限,傳染病防治工作進展不順利,某些傳染病發病率回升等嚴重后果。第三,行政執法效率有待提高,傳染病防治管理機制不夠完善。《傳染病防治法》的貫徹實施有賴于傳染病防治管理機制的健全,因為該法所規定的內容大都隸屬衛生系統。醫療衛生單位不僅需要治療傳染病患者,還需要登記和上報疫情,如因為各種原因造成了交叉感染或者因為漏報、遲報導致了疫情流行等嚴重后果,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由于醫療衛生單位的上級機關也是《傳染病防治法》的執法機關,導致外部監管機制缺失。總體來看,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體系的調控機制屬于行政主導型,傳染病防治管理機制不夠完善,社會力量的參與度和能動性有待進一步提高。第四,傳染病防治保障體系不健全,缺乏優質持續的“人、財、物”支撐。目前,我國的傳染病監督管理隊伍從數量與質量上看,都無法滿足各項監督管理的需要。長期以來,衛生行政部門沒有建設一支固定的專職監督隊伍,同時也沒有委托其他組織行使職能,因此行政執法機關力量薄弱,行政執法效率不高。再加上部分監督管理人員專業知識不足、執法水平不高,完成監督管理指導任務存在困難。同時,傳染病防治屬于社會福利性事業,因此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以保障人員工資、辦公經費、儀器設備等方面。然而,國家財政對傳染病防治事業投入偏少,傳染病防治經費逐漸降低,全額補助逐漸變成差額補助甚至不補助,導致傳染病防治機構留不住人才、無力購置新型設備,軟件、硬件都不夠硬的局面。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之所以存在上述不足,從根本原因來看,是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分不開的。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經濟建設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市場化改革節奏加快,傳染病防治體系也面臨新的轉型。人們更多地看到了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成就,過于注重經濟效益、“重治療、輕預防”的思想在一定范圍內占據上風,對于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隨著價值觀的偏離和指導思想的偏差,傳染病防治法律體系的實用價值勢必大打折扣,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領域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日益凸顯。
4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的啟示
4.1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歷程揭示了這一現象:人民健康水平改善較快的歷史時期,健康政策基本都堅持了以人民健康為目標,以人民為中心,健康政策地位較高。作為全面依法治國、建設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加強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提高傳染病防治立法水平,不斷提升城鄉居民的健康水平,有效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暴發和流行,防止“因疫致貧、因疫返貧”的發生。當前我國加快建設健康中國,就是要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提高國民的基本身體素質,改善公共衛生服務能力,預防和控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有效預防傳染病暴發流行。
4.2必須堅持“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
長期以來,“預防為主”一直是我國衛生工作的總方針。預防,是控制傳染病的最優手段,“預防為主”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確定的衛生工作方針,為適應當時衛生工作的實際需要,我國開展了第一次衛生革命,主要防治對象為急性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病。第一次衛生革命是“預防為主”衛生工作方針在傳染病防治工作中的成功典范,我國在經濟條件非常艱苦的情況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先于世界衛生組織16年宣布消滅天花。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快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極大提高,傳統的疾病譜、死亡譜發生了重大改變,我國及時對衛生體制進行了改革,適時制定了新的衛生方針,增加了一些適應時代需求的內容,但“預防為主”基本原則仍然堅持了下來。新中國成立至今,“預防為主”一直是我國衛生與健康工作的基本原則,不僅是對衛生與健康工作寶貴經驗的總結與繼承,也體現了當前世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趨勢。
4.3堅持集中統一領導、依法防疫的基本原則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主席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就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傳染病的嚴重危害及其與其他社會因素的關系。、、董必武等黨和國家的奠基人、領導者多次親自批示傳染病防治工作,甚至直接指揮和領導傳染病防治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傳染病防治事業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重視傳染病防治工作這一傳統在歷屆領導集體中得到了保持和發揚。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要將健康融入一切政策之中。傳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同時,黨中央和人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依法防疫,改革開放以來,傳染病防治領域的法制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基本形成了與我國傳染病防治事業相適應的法制體系。除《傳染病防治法》《國境衛生檢疫法》等法律外,還有一系列針對具體病種的規章制度,如《艾滋病監督管理的若干規定》等。此外,國家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也根據當時當地傳染病防治事業的具體情況,制定了大量關于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法律法規。
5完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的具體舉措
5.1創新法律調控模式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傳染病防控工作,將突發急性傳染病防治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高度,不斷建立健全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但在立法過程中仍然主要使用行政主導型思維和手段,因此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主要依靠國家權力機關進行調控。傳染病防治工作是一項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的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存在法律調控機制單一,社會組織、市場機制、個人權益等方面主觀能動性受限的短板[8]。在我國應對重大傳染病疫情的實踐中,舉全國之力,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動員全社會參與,最終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一現實啟示我們,完善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必須不斷創新法律調控模式,充分調動社會、市場、個體積極性,從法律層面改變單純依靠政府公權力的傳染病防控機制。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建設應更加重視非政府組織的廣泛參與,不僅要與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行緊密結合,更要與社會化網絡緊密結合、與優化資源調配機制相結合。
5.2統籌考慮與傳染病防治有關的配套立法建設
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醫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大健康”、“大公共衛生”的概念逐漸形成,成為當前全球醫療衛生工作的基本共識。傳染病防治工作是最為重要的公共衛生職能,其涉及范圍非常廣泛。一方面,誘發突發重大傳染病疫情的因素極多,可能來自生產生活各個領域;另一方面,一旦暴發突發重大傳染病疫情,生產生活各個領域都將受到嚴重影響,給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生命健康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因此,完善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必須統籌考慮與傳染病防治工作相關的其他領域的立法修法工作,完善配套法律法規,如環境保護、動物檢驗檢疫、生物安全等領域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從更為廣泛的視野來看,醫療衛生、教育宣傳、食藥品監管、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等領域都與傳染病防治有較為緊密的聯系。因此,加快完善與《傳染病防治法》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確保《傳染病防治法》與相關法律法規的協調統一是完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的關鍵[9]。完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必須加強和完善傳染病防治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加快制定和修訂生物安全法、動物免疫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配套法律法規。
5.3加強地方傳染病防治立法
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國情復雜,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風俗習慣、文化傳統、醫療衛生條件都存在較大差異。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必須要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才能更好地適應我國傳染病防治工作實際,切實提高重大疫情防控能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傳染病防治法》是對全國范圍內傳染病防治工作的綱領性、整體性、原則性的法律規范,因其全局性的立法思路,對于具體地區而言,可能存在過于宏觀、不適應地方實際的問題,法律實施就可能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歷次應對重大疫情的過程中,部分地方政府暴露出依法防疫能力缺乏的問題,反映出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存在地方立法執法水平不足的短板。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不僅是國家層面出臺的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更需要各地政府或衛生行政部門基于本地實際情況,出臺相關配套的《傳染病防治法》實施細則或其他法規條例,并且制定各類相關監督文書,以推動《傳染病防治法》的貫徹實施,確保傳染病防治工作的法治化管理,賦予傳染病監督執法的科學性與規范性,完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切實提高法律實施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5.4重視傳染病防治立法中的技術性因素
加快完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事關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健康和國家生物安全,除了上述三點舉措外,在立法過程中應更加重視醫學、生物學等學科發展,立法工作應更加體現學科發展趨勢,實現前瞻性立法。隨著醫學模式、疾病譜的轉變,醫學、生物學的快速發展,生物威脅已經成為人類文明最為重大的威脅之一。隨著全球化的加快發展,傳染病防治領域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工作實踐,均出現了全新變化,從重大傳染病疫情發生發展趨勢來看,疫情防控工作早已由關注于“治療疾病”的單一模式,擴展至關注人的生理、心理、社會等多維度模式;以“治療為主”的靜態防控模式也轉變為以“預防為主”、“關口前移”、“防治結合”的動態調控模式;同時,突發新型傳染病暴發風險加劇,與傳統傳染病的交叉、變異,給傳染病防治工作帶來了全新的挑戰[10]。因此,傳染病防治立法要充分重視技術性因素,深刻認識生物安全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系統研究傳染病學和生物技術發展前沿對傳染病防治立法的影響,推動國家生物安全立法,才能構建起更為完善的傳染病防治法律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1]武衡.東北區科學技術發展史資料: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醫藥衛生卷[M].北京:中國學術出版社,1988:201.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0.
[3]汪建榮.30年衛生立法的發展進程[J].中國衛生法制,2009,17(1):8-9.
[4]《中國衛生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衛生年鑒:1985[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121-130.
[5]方寄惠.貫徹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的進展與問題[J].安徽預防醫學雜志,2011,17(4):303-304.
[6]李斌.國務院關于傳染病防治工作和傳染病防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J].首都公共衛生,2013,7(5):193-195.
[7]王晨.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傳染病防治法執法檢查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J].中國人大,2018(11):8-11.
[8]申衛星.醫患關系的重塑與我國《醫療法》的制定[J].法學,2015(12):79-91.
[9]胡偉力.加快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的現實意義[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8):116-119.
[10]蔣艷艷.現代醫療技術的“身體”倫理[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8(6):35-39.
作者:胡偉力 單位:西南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