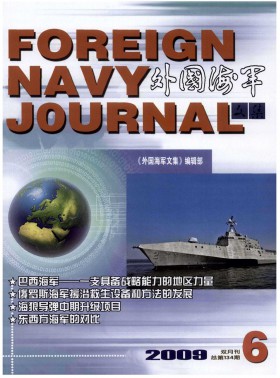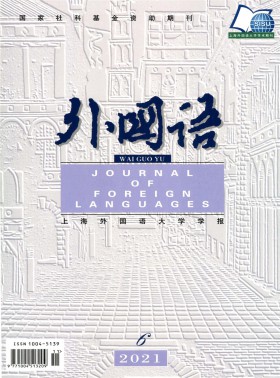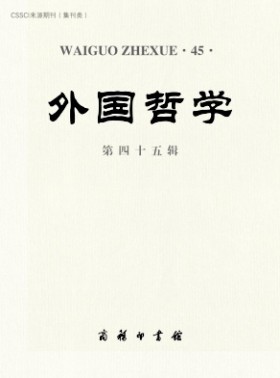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外國民族音樂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外國民族音樂論文范文1
中圖分類號:J602文獻標識碼:A
子曰:“三十而立”。從1980年6月13日在南京藝術學院召開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以下簡稱“南京會議”)正式在我國大陸提出民族音樂學的口號以來,30年過去了,民族音樂學在中國已到而立之年。高厚永先生在南京會議上發表的《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形成和發展》一文中指出:“中國民族音樂在世界民族音樂文化中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加強對外學術交流活動,參加到世界民族音樂學的行列,讓我們肩負起發展民族音樂學的重任,團結向前,迅步走向新的廣闊途程。我們堅信,國際音樂學的講壇,必將閃耀中國民族音樂瑰寶的燦爛光輝。”[1]現在,我們應響亮地提出建立民族音樂學中國學派的口號,并為之努力奮斗。為達此目的,應做好繼承傳統、把握方向和面向世界三方面的工作。筆者不揣冒昧,草成此文,以此紀念南京會議30周年。
一
要建立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學派,首先必須繼承好兩個傳統,一是中國人綜合思維模式的傳統,二是民族音樂學從文化背景入手研究音樂的傳統。
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在分析東、西方思維模式的不同特點后指出:“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它抓住一個東西,特別是物質的東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極其細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略了整體聯系,物我兩者的對立十分尖銳”而“東方文化本質上是講綜合的,講聯系的,它照顧了事物的總體。”[2]
我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綜合性、整體性,這兩種性質在先秦學者的著述中已有所顯現。孔子辦學,教授“六藝”,施行的就是綜合性教育,后來用此種方式培育出的歷代文人,多為“琴棋書畫,無不精通”。在“五•四”運動以前,我國知識分子所仰慕的,除“專才”外,是在許多領域里都有精深造詣、取得相當成就的“通才”。這些現象都證明中國人對綜合思維模式的推崇和重視。
中國音樂是中國文化中的音樂。中國傳統音樂更是在我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至今始終保持著與傳統文化、傳統藝術方方面面血肉相連、息息相關的親緣關系。
與音樂聯系最為緊密的,莫過于與之同源的語言。漢藏語系諸語言聲調升降起伏所具有的旋律意義,不但使中國傳統音樂突出地使用了種種“腔音”,也使中國音樂的橫向線性陳述方式得到高度的發展,從而與西洋音樂有著顯著不同的形態和韻味。我國各民族語言的不同、各地區方言的差別,也是產生各民族、各地區音樂風格差異的重要原因。
中國傳統音樂向來與詩歌、舞蹈、表演融為一體。盛唐時的“九部樂”、“十部樂”以及稍后的“坐部樂”、“立部樂”等樂舞,都是詩歌、舞蹈、器樂的組合,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綜合藝術”。歷來的宮廷音樂、宗教音樂、興盛于明清時期的戲曲、長期流傳于民間的歌舞音樂及各少數民族的音樂等,亦多取詩、歌、舞(或再加上器樂)的綜合表演形式。因有此傳統,“載歌載舞”為各族人民喜聞樂見,當前的音樂演唱,依然常見“歌伴舞”的形式,甚至一些器樂演奏,也以舞蹈相配合,歌舞一體的傳統仍在傳承。
音樂與文學(尤其是詩歌)在內容、意境、創作手法以及哲學、美學等深層次上,都緊密相關。在西洋音樂傳入、中國新音樂產生之前,中國人的“詩”與“歌”是不分的,“詩”總是可“歌”(唱)的,可“歌”(唱)的必是“詩”,在文學語言里,便常把“詩”稱做“歌”。現今我們不論是采錄民間的詩,還是歌,一概稱之為“采風”。“四句頭”和“起承轉合”,是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定型于唐代的五、七言絕句)的基本結構形態,也是中國音樂(尤其是民歌)最常見的結構形態。
我國古代總是把音樂與歷法、數學、度量衡乃至自然界、人類社會、國家、人生、習俗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很多音樂家、樂律學家,同時也是文學家、詩人、學者、數學家、科技發明家等。中國音樂的這一優良傳統,自上古時代起,一直延續到西洋音樂大規模地傳入我國的20世紀初。音樂與繪畫、雕塑、建筑、園林、書法、工藝美術等幾乎所有的文化門類也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把音樂作為一門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獨立藝術門類,建立專業音樂教育機構、造就專業音樂人才,是西洋音樂文化的產物,不是中國音樂文化的傳統。
從世界范圍來看,20世紀音樂學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民族音樂學的確立和發展。1950年,荷蘭音樂學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提出這一學科名稱后,“民族音樂學”便取代了以往人們習慣稱呼的“比較音樂學”,先后進入一些西方國家高等學校和音樂學院的課堂,成為與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并重的專業。不少國家相繼成立了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機構,出版了大量民族音樂學的學術著作。20世紀結束之時,民族音樂學在全世界已成為音樂學諸學科中最活躍、最具生命力、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在南京會議以后,這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也非常迅速。
民族音樂學不是以特定的區域和范圍與音樂學中的其他學科分界,而是以一種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點、著重點為其主要標志。它將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從音樂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環境入手進一步觀察其特征、探索其規律。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是文化中的人,每一種音樂都是文化中的音樂,每一個與音樂有關的學術研究成果也都是文化中的成果。因為民族音樂學把音樂作為一種文化和文化中的一個類別進行研究,音樂作品就不再被看作是某個作曲家或某一社會群體對其人生感悟的“獨白”,而是被解釋成作曲家或這一群體在當時社會背景下所作的一次文化發言;音樂現象不再是孤立的歷史現象,而是被看作是整個社會形態中的一種文化現象;與音樂有關的科學研究成果也不再被簡單地看作是某一位或某幾位專家學者苦思冥想的產物,而是整個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個成果。
民族音樂學主要是在西方國家里發展起來的。正如我曾經指出的那樣,將音樂當成一種文化,把它放在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中去進行研究的方法,實際上是西方民族音樂學界在學習、研究非西方民族音樂,特別是東方民族音樂的過程中,借鑒東方民族綜合性思維模式的成果,是對西方分析性思維模式的否定和對東方民族綜合性思維模式的肯定。[3]西方民族音樂家的這種做法對西方音樂學中其他兩個學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少從事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學研究的專家都借鑒了民族音樂學的方法,將其研究對象放在其所處文化環境中進行探討。他們不再簡單地依據某一種科學體系,對過去的音樂現象和音樂學研究成果作出若干解釋和評價,而是從當時的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文化狀況入手,對音樂現象本身和音樂學研究成果作出文化學方面的闡釋。他們首先把音樂作品、音樂現象和音樂學研究成果看成文化現象,并將它們放到所發生、發展的背景中來,探索其起源、形成、發展、繁榮、演變等問題。西方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學專家們的做法對其他地區和其他國家的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學界影響很大。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廣泛采用了使研究對象回歸于文化的做法,極大地推動了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學中的各個分支學科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要繼承好中國傳統文化綜合思維模式和民族音樂學從文化背景研究音樂的傳統,不僅要打破以往學科的界限,而且要從綜合思維模式的角度進行研究。筆者想用一個實例來說明自己的觀點。
按照西方通用的音樂學分類方法,由于“律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數學有密切關系,被看作是體系音樂學中的一個分支學科。我國古代的律學研究十分發達,王光祈先生曾在《東西樂制之研究》一書的序言中指出,中國人“數千年以來,學者輩出,講求樂理,不遺余力,故今日中國雖萬事落他人之后,而樂理一項,猶可列諸世界作者之林,而無愧色。”[4]王光祈在這里說的“樂理”就包括了律學研究成果在內。我國古代的律學研究除和數學研究密切相聯外,還有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三個特點:一是由于受“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影響,和天文學、歷法相聯系,故班固撰《漢書》,將律、歷合一,設《律歷志》,后來的一些史家亦效法班固;二是受主張“禮樂治國”的儒家思想影響,把律和度、量、衡聯系在一起,并認為音樂中的律是生活中度、量、衡的先導;三是受我國古代綜合性思維和科學觀點的影響,把律學研究和陰陽五行學說相聯系。第三個特點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特點。王光祈說,自秦代以降,“后世言律之人除極少數例外,多以陰陽五行為大本營”。[5]此特點所以能最突出,有深刻的歷史淵源。漢文文獻中“音樂”第一次出現是在《呂氏春秋》中,這本書的《大樂》篇說:“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6]由此可知,我們的祖先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把“音”、“樂”與陰陽五行相聯系。后來的律學研究,更是和陰陽五行、氣、象數、義理等哲學、科學的概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具有綜合性思維和博大精深的特征。
因此,無論從當代音樂學研究的時代潮流,還是從我國律學的歷史發展特點,我們在對中國樂律學史進行研究時,都不能脫離其文化背景,特別是不能脫離陰陽五行學說。然而,由于我國音樂學界受歐洲科學主義的影響,在整個20世紀研究古代樂律時,幾乎所有的專家都把陰陽五行學說拋在一邊,甚至把這個學說看成“迷信”和“偽科學”。20世紀20年代,童斐說:“凡論陰陽五行,聚訟甚多,徒蹈于虛玄,無當于物理,足為言樂之障。”[7]20世紀30年代,許之衡講:“夫宮商律呂等字,自宋以來,既知為即工尺等字矣。與陰陽五行,有何關系?《漢志》多本之劉歆,劉歆偽儒,以陰陽五行,比附作樂。不外以作樂為王者之事,務極玄奧,令人神秘莫測,以逢迎人主耳。”[8]因為沈括《夢溪筆談》中的律論部分和陰陽五行有關,60年代被楊蔭瀏先生批評為“神秘主義”,[9]王光祈先生也認為律學研究中陰陽五行是“穿鑿附會,令人討厭”[10]。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筆者在拙作《中國民族樂理》一書中將宮、商、角、徵、羽五聲和東、西、南、北、中五方等放在一起加以介紹,還被人批評成“奇談怪論”、“江湖庸醫的叫賣”[11]。
科學不是唯一的,而且具有民族性。我們不能認為只有西醫才是科學,中醫就不是科學。如果我們能夠同意中醫也是科學,那么作為中醫基礎理論的陰陽五行學說當然也是科學,它是一種具有強烈民族特征的、不同于西醫基礎理論的科學。另外,先民們把音樂和陰陽五行學說聯系在一起也不一定都是穿鑿附會,而其中也可能有一些道理。如宮與中、商與西、角與東、徵與南、羽與北相對應,很可能和當時不同地區的民間音樂不同風格、主要采用不同的調式有關。直到現代,長城以北的民歌以羽調式為主,長江以南的民歌以徵調式為主,陜西、甘肅、青海民歌中商調式占有較高的比例,河南民歌中宮調式較多,而浙江等東部沿海省份角調式民歌顯然比其他地區多,難道不是五個方位和五聲聯系的具體事實嗎?另外,五聲和五行在音樂治療學方面的聯系,亦需要從中醫學的角度進行深入探討,不能一概輕易加以否定。
如果我們能夠承認陰陽五行學說也是科學,而且它和音樂的聯系也不一定完全是穿鑿附會,在研究我國古代樂律學成果的時候,就一定要按照民族音樂學的方法,把這些成果放在產生它們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絕對不能避開陰陽五行學說。既然古代研究律學的學者“多以陰陽五行為大本營”,不入此大本營,焉能知道他們的學說是否正確?不入此大本營,豈能揭開律學史上的眾多懸疑?不入此大本營,又怎么樣批判地繼承我國古代的樂律學遺產?不入此大本營,也就不可能讓“數千年以來”,無數先輩“不遺余力”研究出來的中國樂律學和“猶可列諸世界作者之林,而無愧色”的古代樂理知識在今天的音樂學研究和音樂教育中發揮作用。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黃大同先生最近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化與〈夢溪筆談〉律論》[12]一書,就是采用民族音樂學的方法,把古代樂律學的成果放在產生它的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并將陰陽五行學說當作古代大科學家沈括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認真地、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并解決了中國樂律史的一些懸疑問題。
我以為黃大同先生的研究,不僅符合從西方興起的表現出整體性特征的民族音樂學的特征,實際上也是對我國古代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肯定和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值得肯定,值得效法。
二
要建立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學派,除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綜合思維模式和民族音樂學從文化背景研究音樂的傳統之外,還必須牢牢把握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向,而不要越俎代庖地去搞音樂人類學的研究。
在漢文中,音樂學各分支學科的名稱都是不同的偏正短語。偏正短語也叫偏正詞組,一般由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是“修飾語”,對后一部分修飾或限制,后半部分是“中心語”,是整個短語的核心。一般來說,表示研究手段的詞放在前面為修飾語,表示研究目的之詞則放在后面為中心詞。在“民族音樂學”這個詞組中,“民族”是修飾語,“音樂學”是中心詞,它是采用民族學的方法,對音樂進行研究的一個學科。而在“音樂人類學”中,“音樂”是修飾語,“人類學”是中心詞,它是以音樂為手段,進行人類學研究的一門學科。
近年來,由于學科急速的發展和各個音樂院校盲目擴大招生,音樂學界出現了越俎代庖的現象,如一些音樂院校辦起了“音樂治療學”專業。“音樂治療學”是以音樂為手段,研究如何治療精神方面疾病的學科,其研究的主要方面不是音樂,而是治療。音樂學院沒有條件為這一專業的學生提供醫學方面的訓練,音樂學專業的教師也不是精神病專家,不可能教給他們有關精神病學方面的知識。因此,音樂治療學專業應當放在醫學院里,由精神病學專業的學生學習,而不應放在音樂學院中,由音樂學專業的學生學習。
雖然民族音樂學和音樂人類學研究范圍和方法很接近,但民族音樂學是從民族學的角度研究音樂的一個學科,而音樂人類學則是將音樂作為手段,要達到人類學研究的目的。“民族音樂學”的主要任務并不是要解決民族學方面的問題,只是采用民族學的方法對音樂進行調研,所以由音樂學院的學生來學習,由音樂學家進行研究。“音樂人類學”研究的主要方面不是音樂,音樂學院一般也沒有條件為學生提供人類學訓練,音樂學院的教師也不是人類學家。因此,音樂人類學專業應當放在人類學、民族學或民俗學的系科中,由這些學科的學生學習,由人類學家進行研究。
據我所知,30年前高厚永先生之所以倡導民族音樂學,是因為他看到這門學科的觀念和方法不僅完全適用于我國從20世紀30年代起發展起來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和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亞非拉音樂研究”等學術領域,而且能夠把我國當時尚處在閉塞狀態的這些領域的研究引向一個更加宏觀、更具開放性和科學性的境界,從而把中受到摧殘、當時尚處在蕭條之中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和“亞非拉音樂研究”專業復興起來。南京會議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我國音樂學家借鑒國外民族音樂學理論、方法及最新成果,進行了扎實地研究工作,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然而近年來也出現了“去音樂化”的壞風氣。有些民族音樂學家拋棄“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名稱,將其改為“音樂人類學”,這也是“去音樂化”的一個具體表現形式。
我以為造成“去音樂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對美國學術界的盲目模仿和追隨;二是我國民族音樂學界本身音樂修養的欠缺。
近些年來,美國音樂學界的種種成果和不同思潮被源源不斷地介紹到我國來,這是一件好事。我們應很好地向美國同行學習,對這些成果進行分析之后,再加以借鑒、運用、采納,而不能盲目地追隨幾個僑居海外的、以學術規范的執行人自居的“新理論”“搬運工”,不加分析地模仿和附和。
美國只有200多年的歷史,幾乎沒有本國的傳統音樂文化遺產,沒有音樂學傳統,美國音樂界也沒有繼承、發揚古老音樂文化遺產的任務。但美國人類學有較長的歷史和較強的研究力量,美國人創立并發展“音樂人類學”不僅是一個聰明之舉,而且也是美國國情所需要的,這一點我在《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一文中已經進行了詳細分析。[13]中國不是美國,我們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有著豐富的音樂文化遺產,我國音樂學界面臨如何繼承、發揚56個民族的古老音樂文化遺產的任務。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不深入研究和了解各民族、各地區的音樂形態是不行的。要說向美國人學習,我們最需要學習的就是他們因地制宜,逐漸改變歐洲人提出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向,創建并發展音樂人類學這個新學科的精神。我們絕對不應當跟在美國人后面跑,而是要從我國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大一統多民族的中華文化脈絡的實際出發,堅持民族音樂學以音樂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大方向。
中國民族音樂界“去音樂化”的表現,還說明目前我國民族音樂界的音樂整體水平較之我們的前輩有所降低。要建立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學派必須克服“去音樂化”的不良傾向,大力提倡“民族音樂學”,而不要越俎代庖的去搞“音樂人類學”。“音樂人類學”應當由人類學界和民族學界進行研究,各院校的人類學系應當努力培養這方面人才。三
關于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國內外學術界都有過爭論。在國外,曾有人認為民族音樂學是研究非歐音樂的學科,后來又認為研究范圍應當擴大,把歐洲民間音樂包括在內,但不包括歐洲的專業創作音樂。目前,學術界已經傾向于應包括一切音樂,不僅包括非歐音樂,也要包括歐洲音樂,不僅要包括歐洲各國的民間音樂,還要包括歐洲各個時代作曲家的作品。在國內,曾有人認為民族音樂學是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學問,建議用“中國音樂學”來替代“民族音樂學”。[14]經過長期爭論,目前大家的認識已基本統一,同意民族音樂學不是以特定的區域和范圍與音樂學中的其他學科分界,而是以特殊的角度為其主要標志,它和音樂學中的許多學科一樣,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既然如此,我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就一定要“面向世界”。我們的研究對象不應僅局限于我國傳統音樂或中國音樂,而應擴大到全世界各民族的各種音樂,還要加強與各國民族音樂學界的交流,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推向全世界。
南京會議上所有代表的論文,都發表在《民族音樂學論文集》中,它們都是研究中國民族音樂,特別是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這就是我國民族音樂學的起點。30年來,我們在研究中國音樂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為中國效法歐洲建立起近現代音樂教育體系,所以我國近現代音樂學家最早也“以西格中”,用西洋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音樂。在對中國傳統音樂有較多了解后,也開始“以中格中”,用中國傳統音樂的概念進行研究。“格”就是“格物”,即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即是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將其總結為理性認識的過程。
研究范圍要擴大,就產生了一個立場和方法問題。具體地講,在研究外國音樂時,我們應如何去做?是“以外格外”還是“以中格外”?
民族音樂學研究以田野工作為起點,在研究任何一個外國的音樂時,一定要到那里去做田野工作,而且應當盡量了解該國的文化,爭取對它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從理論上講,我們對該國音樂及文化了解的程度最好能達到與其本國專家平等對話的水平。但從我國音樂學界研究西方音樂文化的狀況就可以知道,要想達到這種境界非常困難,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不可能做到。要“以外格外”,在研究方面得到超過其本國專家水平的成果,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所占有的資料應不少于本國專家,二是對該國音樂現象的領悟能力不低于本國專家。然而在這兩方面,本國專家都占有絕對優勢。就拿我們的鄰國俄羅斯民間音樂來說,上至歷史上記錄民歌的手稿,下至當代的最新論著,幾乎都在俄國專家可及的范圍之內,而我們進行一、兩次田野工作能搜集多少資料?第二方面的挑戰更大,就算我們精通俄文,在領悟俄羅斯音樂方面,俄國專家更占有絕對的優勢,無論是對歌詞的理解和對曲調的分析、藝術特色的把握,他們都比我們強。看俄文資料,我們也要比他們慢。“以外格外”的結果使我們只能以學生的身份出現,在討論歐美音樂時,出現“失語癥”,只有聽話的資格,沒有說話的權力。再者,西方人的研究也會不斷進步,而絕不會停滯不前地等著我們去追趕。如果采用“以外格外”的方法,本國專家總是跑在前面,而跟在后面的我們,能達到二、三流水平已屬不易,幾乎沒有可能達到第一流水平。我國研究西方音樂文化的歷史,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外國人能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研究中國音樂,我們也應當能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研究外國音樂,即采用“以中格外”的方法。一旦采用這種方法,情況就會改變,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觀察,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就有可能看到外國人看不到的東西。王耀華先生在日本進行田野工作時,對琉球和我國民間音樂進行比較研究后,用日文發表《琉球――中國音樂文化比較論》一書,指出中國民間音樂是琉球音樂的一個重要淵源,并具體說明一些中國民間音樂作品是如何日本化的。只有十分熟悉我國民間音樂的人,才能進行這樣的比較研究。任何一位日本民族音樂學家,即便是研究中國音樂的專家,對我國民間音樂的熟悉程度都不可能和王耀華先生比,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達到王先生的水平。此書曾在日本獲獎,王先生后來用中文發表的《琉球三線“揚調子”考》一文,便是這本日文專著中的一章。[15]20世紀80年代,筆者曾在匈牙利研究匈牙利的民歌,因為我對中國北方各少數民族的民歌比較熟悉,把這些民族的民歌和匈牙利民歌進行比較,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系,提出匈牙利民間音樂中有匈奴音樂遺傳因素的觀點,而這一點也是匈牙利音樂家所沒有看到的。
“以中格外”不僅能使我們看到外國學者看不到的東西,它還能導致進攻性的學術行為。采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用中國人的智慧進行研究,彌補外國學者的不足。洛秦先生旅美期間,做了大量田野工作,回國后發表了《街頭音樂:美國社會和文化的一個縮影》一書[16]。書中表現出對街頭音樂的關注,本身就是對視歐洲古典音樂為“精英文化”,視非西方音樂文化為“低級”的看法的批判。洛先生還以人物、地域為線索,獨特地闡述了自己對美國街頭音樂這種大眾音樂文化的看法,加之文字清新,可讀性強,非常具有感染力。這本書發表之后,美國著名的民族音樂學家泰瑞•米勒博士撰文指出:“(洛秦)不僅將在美國所學到的知識帶回了中國,而且也極大地刺激了我們美國學者。他‘搶占’我們家門口的‘街頭’田野,以中國學者的身份成為了研究美國街頭音樂的第一人。”[17]洛秦的研究說明如果我們能夠采用“以中格外”的方法來“以中格美”,就能不受制于美國學者的話語霸權,不僅能和他們進行平等對話,而且能取得超越美國學者水平的研究成果。
20世紀末日本漢學界已在提倡“以中格外”的方法。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在《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一書中對國際漢學界的一些專家把西方的某種理論作為準繩解剖中國的做法非常不滿,指出:“以世界為基準來衡量中國,這個世界就因此而成為一個完全被當作基準的‘世界’,只不過是個作為既成方法的‘世界’。以‘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為例,這種‘世界’即是歐洲。”他認為應提倡“以中格歐”的方法,說道:“如果我們愿意的話,不論它是好是壞,我們可以透過中國這個獨立的世界,即戴著中國的眼鏡來觀察歐洲,對以往的‘世界’加以批判了。”[18]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于連說:“為了能夠在哲學中找到一個缺口(邊緣),或者說為了整理創建性理論,我選擇了不是西方國家的中國,也就是相異于西方希臘思想傳統的中國。我的選擇出于這樣的考慮:離開我的希臘哲學家園,去接近遙遠的中國。通過中國――這是一種策略上的迂回,目的是為了對隱藏在歐洲理性中的成見重新進行質疑,為的是發現我們西方人沒有注意的事情,打開思想的可能性”[19]。日本人和歐洲人尚且提倡運用“以中格外”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我們自己就更應當有信心,從中國文化里吸收營養,用中國人的智慧去研究其他民族的音樂,為我國民族音樂學走向世界而努力。
要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就一定要加強與各國民族音樂學界的交流。我們不僅要了解各國同行的研究狀況,還要讓各國同行了解我們的研究狀況。因為國際學術界最通行的交際工具是英語,而各國民族音樂學家中懂中文的人又非常少,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學好英語,不僅能讀英語的文獻資料,更要能用英語寫作論文和專著,用英語發表研究成果。這樣在國際音樂學的講壇上,中國學者的聲音必將越來越響亮,取得的成績也會越來越輝煌。
30年來,我國在民族音樂學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問題也還不少。如果我們能繼承好綜合思維模式和從文化背景研究音樂的傳統,能堅持民族音樂學以音樂為中心的研究方向,并能用“以中格外”的方法,把研究范圍擴大到全世界,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學派就一定能建立起來,世界民族音樂學的講壇上,必將閃耀中國民族音樂學的燦爛光輝,我們也一定能為中國音樂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責任編輯:陳娟娟)
參考文獻:
[1]高厚永.萬古文明的見證[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35.
[2]季羨林.東方文化將再現輝煌[J].音樂信息,2001,(10).
[3]杜亞雄.從分析到綜合――西方民族音樂學思維模式的歷史發展軌跡[J].音樂研究,2002,(3).
[4]王光祈.東西樂制之研究[M].上海:中華書局,1936.9.
[5]王光祈.中國古代音樂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5.
[6]音樂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樂論選輯[C].北京:音樂出版社,1981.35.
[7]童斐.中樂尋源[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17.
[8]許之衡.中國音樂小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141.
[9]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132.
[10]王光祈.中國古代音樂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5.
[11]周勤如.研究中國音樂基本理論需要科學的態度――從杜亞雄《中國民族基本樂理》的謬誤談起[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9,(3).
[12]黃大同.中國古代文化與《夢溪筆談》律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
[13]杜亞雄.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J].中國音樂,2009,(3).
[14]魏廷格.對民族音樂學概念的思考與建議[J].人民音樂,1985,(2).
[15]王耀華.琉球三線“揚調子”考[J].音樂研究,1989,(4).
[16]洛秦.街頭音樂:美國社會和文化的一個縮影[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1.
[17]洛秦.省略[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2.
[18]溝口雄三著,李蘇平等譯.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94.
[19]杜小真.遠去與歸來――希臘與中國的對話[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4.
Fighting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School of Folk Musicology:
Commemo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Nanjing Conference
DU Ya-xiong1,2
(1, China Conservatory, Beijing 100101;
2. School of Music,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