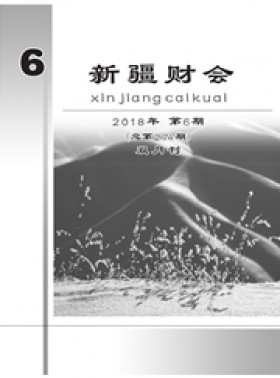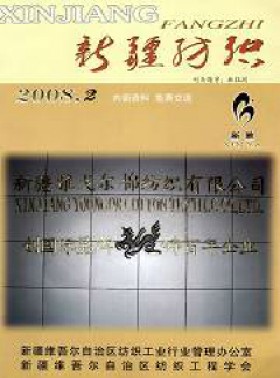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wǎng)精心挑選了新疆民族音樂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xué)習(xí),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fā)你的文章創(chuàng)作靈感,歡迎閱讀。

新疆民族音樂論文范文1
【關(guān)鍵詞】新疆衛(wèi)拉特蒙古族 托布秀爾
一、托布秀爾
托布秀爾系新疆衛(wèi)拉特蒙古族古老的民間樂器之一。“托布秀爾”又稱“圖布舒爾”,即二弦琴,其音色美、演奏方便、表現(xiàn)力強(qiáng),深受各族人民喜愛,也是新疆衛(wèi)拉特蒙古族特有的彈撥樂器。
托布秀爾,由共鳴箱、琴桿、弦扭、琴馬等部分組成,全長約78.85厘米,用兩根羊腸弦分別作為內(nèi)外弦,其定弦為四度音程,琴桿上沒音品,用右手五指技巧性的撥奏與左手靈活的指法配合,便能奏出旋律豐滿、節(jié)奏多變的旋律。
“托布”或“托克”意為彈撥,“秀爾”與“修爾”是“潮爾”的地方變音。合意為“彈撥琴弦的共鳴”。主要流傳于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以及塔城地區(qū)。該樂器構(gòu)造簡單,有多種彈奏法,如正彈、反彈、肩彈等。
對“托布秀爾”一詞的內(nèi)涵,專家和民間藝人持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有專家認(rèn)為“托布秀爾”是衛(wèi)拉特蒙古族方言中的音譯,譯為“敲的東西”。并從語言學(xué)發(fā)展的角度,分析了托布秀爾在最初發(fā)現(xiàn)的時候就具有彈和撥的特點。另外一種說法則來自民間藝人,他們主要從托布秀爾的形制考慮,認(rèn)為該琴似蒙古袍上的紐扣,琴桿與蒙古袍扣子上的“西勒布”(扣上的繩帶)極其相似。因此,將托布秀爾譯為“像扣子一樣的琴”。雖然民間有這種說法,但僅從形制上相似就狹義地把它譯為“像扣子一樣的琴”是沒有理論依據(jù)的。因此,隨著知識的不斷豐富,人們開始認(rèn)同專家對“托布秀爾”內(nèi)涵的解釋,并流傳至今。
二、史料中的托布秀爾
蒙古各部落統(tǒng)一之前,對曾使用過的樂器有一些文字資料記載,但關(guān)于托布秀爾的史料記載較少。加之,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jìn)步,以及多元文化的互相融合,樂器會產(chǎn)生名稱和形制的變異。雖然關(guān)于托布秀爾產(chǎn)生的最早年代現(xiàn)已無法考證,但從現(xiàn)存的史料記載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托布秀爾的蛛絲馬跡。
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記載:“12世紀(jì)蒙古族的祖先韃靼人中流行一種二弦琴。”他從意大利經(jīng)西域去上都時曾在蒙古族草原見到過與托布秀爾完全相同的二弦彈撥樂器。《明英宗實錄》記載:“西域蒙古汗普遍喜好音樂歌舞,每宰馬設(shè)宴,必先奉上黃酒,自彈虎撥思兒唱曲,達(dá)子齊聲和之。”《續(xù)文獻(xiàn)通考》記載:“明英宗正統(tǒng)(六年正月)又賜(斡拉達(dá)達(dá)汗)箜篌、和必斯、三弦各一。”其中《明英宗實錄》中的“虎撥思兒”與《續(xù)文獻(xiàn)通考》中的“和必斯”(即“火不思”),后都演變成為了現(xiàn)代衛(wèi)拉特蒙古人使用的主奏樂器“托布秀爾”。
《四庫全書》第六百六十五冊《皇朝禮器圖式》中,搜集到了史料中記載的“火不思”的形制,并在史料中搜集到了關(guān)于“火不思”的形制描述。它與現(xiàn)今衛(wèi)拉特蒙古族使用的樂器托布秀爾相差甚遠(yuǎn)。因此,我們無法肯定現(xiàn)今在衛(wèi)拉特蒙古人中使用的托布秀爾樂器是由“火不思”演變的。除上述兩篇明朝史料中提到了關(guān)于托布秀爾的記載之外,目前沒有搜集到明朝以前關(guān)于托布秀爾歷史記載的文獻(xiàn)。
清朝《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史料中記載:“當(dāng)時準(zhǔn)噶爾部為其歡會宴飲所用的樂器有雅托噶、伊奇里呼爾、披帕呼爾、特木爾呼爾、圖布呼爾、綽爾等6種。”其中,圖布呼爾就是現(xiàn)在衛(wèi)拉特蒙古族保留下來的彈撥樂器托布秀爾。倪志書撰寫的《新疆之蒙族》一書中記載:“關(guān)于樂器,種類甚多,其歡會宴飲所用者,以絲為主,而竹附之。若胡琴曰‘伊奇爾呼爾’,二弦曰‘圖布舒爾’等。”倪志書文中提到的圖布舒爾就是現(xiàn)在蒙古族沿用的樂器托布秀爾。
從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確定清朝歷史文獻(xiàn)資料中的二弦“圖布舒爾”就是現(xiàn)今衛(wèi)拉特蒙古族使用的樂器托布秀爾的前身。托布秀爾琴在漫長的歷史中,以其獨具特色的形式反映著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習(xí)俗和精神風(fēng)貌。關(guān)于宴會中提到的六種樂器的名稱,雅托噶即現(xiàn)今彈奏的蒙古箏,伊奇里呼爾即現(xiàn)今使用的蒙古胡琴,披帕呼爾即現(xiàn)今演奏的蒙古四胡,特木爾呼爾即現(xiàn)在吹奏的蒙古口弦。
另外,在《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40)“準(zhǔn)噶爾章”內(nèi)對托布秀爾的各部件的大小尺寸做了較為詳細(xì)的描述:“圖布舒爾即二弦也,以木為槽,形方,底有孔。面長六寸八分二厘六毫,闊五寸三分九厘三毫,邊長七寸八分八厘五毫,闊六寸四分八厘。以木為柄,自山口至槽邊內(nèi)際,長一尺七寸二分八厘,上闊九分一厘,下闊一寸零七厘八毫。曲首長與槽面闊等,后開槽以設(shè)弦軸。槽長二寸零四厘。闊三分,軸長四寸零四厘,弦自山口至覆手內(nèi)際,長二尺三寸零四厘。通常用樟木,槽面用桐木。施弦二,以羊腸為之,系于左右兩小軸。以手冒撥指彈之取聲。”現(xiàn)今這種樂器仍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地區(qū)流傳,并被后人譯為“托布秀爾”,其形制與《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中記載的基本相同。
此外,陳婷婷發(fā)表的論文《清代乾隆年間官修文獻(xiàn)中西域準(zhǔn)噶爾部與回部樂器狀況》中對《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中記載的圖布舒爾樂器各部件的尺寸進(jìn)行了換算:“槽面長21.8432cm.闊29.9296 cm;邊長25.232cm.闊20.736cm;柄自山口至槽邊內(nèi)際長55.296cm;上闊0.5696cm;軸槽長6.528cm;軸長1.2928cm;弦長73.728cm。從上述史料記載的關(guān)于托布秀爾的各部件精確的尺寸,與現(xiàn)存的托布秀爾的尺寸有些不同,其中較突出的有現(xiàn)今流傳的托布秀爾琴共鳴箱的尺寸較史料記載的要略微偏小一些,此外整個琴頸的長度較史料記載的要略微的長一些。由此可以看出經(jīng)過時代的變遷,托布秀爾琴部分尺寸也會有所變化。
在新疆阿爾泰地區(qū)流行有“抄爾”的音樂,其產(chǎn)生發(fā)展對蒙古音樂觀念有特殊的意義。它不僅反映著器樂抄爾歌曲或抄爾樂器的存在,還反映著“抄爾”一詞已概括了蒙古人關(guān)于多聲音樂的含義。它的產(chǎn)生更反映著蒙古人高度審美觀的形成,以及關(guān)于多聲音樂感的神奇感知,就是我們常說的“抄爾”音樂。蒙古人所說的“彈撥抄爾”,蒙語里俗語稱“托布秀爾”。專家考察發(fā)現(xiàn),新疆蒙古族至今使用的彈撥樂器――托布秀爾一語,是由兩個關(guān)鍵詞組組成,認(rèn)為:蒙語“tog”與“tob”“ton”有諧韻變音節(jié)的可能,“秀爾”是“抄爾”在新疆蒙古語里的語音變異,二者合一,就成了“托布秀爾”的稱謂了。至于喀拉沁王府曾用過的“登抄爾”,只是“d”與“ton”諧韻變交音節(jié)的可能。托布秀爾,雙弦,本制挖槽而成,蒙本面板,頸細(xì)而短,無品,琴軸分置之于琴首兩側(cè),彈撥時,細(xì)弦奏旋律,粗弦同時奏響,低音與旋律音形成“抄爾”的雙音,也有雙弦奏出雙音的。如“薩布日丁”樂曲,其低音就是由固定節(jié)奏的“La、do”組成。
追溯其歷史淵源,“托布秀爾”與唐代的胡琴有關(guān)聯(lián)。“胡琴”主要是指西域的彈撥樂器,傳入中原的胡雷、琵琶等像梨形音箱的彈撥樂器,有時也專指琵琶或胡琴。唐代,琵琶在中原地帶空前繁榮,很多中原的漢族人早已不把它當(dāng)作胡人的樂器。我們在唐代的文獻(xiàn)中直接可以看到琵琶的名稱。宋代至今,這個名字就沿襲下來了。又《契丹國志》載:“每謁拜木蘭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敢前導(dǎo),彈胡琴和之”,契丹所建遼國,文化藝術(shù)相當(dāng)發(fā)達(dá)。其時,契丹族樂舞不分;所以從當(dāng)時的雕塑、繪畫和墓葬壁畫上的舞蹈中查找器樂蹤跡,據(jù)隗芾著文介紹,契丹族盛行反彈胡琴舞,即將胡琴舉在頭后方,雙手反彈歌之、舞之。云居寺塔北面和西面浮雕、薊縣白塔北面浮雕形象地記錄了這一樂舞,從浮雕中看胡琴是長方形音箱的彈撥樂器,有兩根弦,這是公元10世紀(jì)的歷史文物。
以上資料均可證明,宋朝“胡琴”含義還是泛指我國北方少數(shù)民族和西域地區(qū)的彈撥樂器,由此圖看來,與新疆衛(wèi)拉特蒙古人使用的托布秀爾非常相似。我們再看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的記載:“12世紀(jì)蒙古族的祖先韃靼人中流行一種二弦琴,從意大利經(jīng)西域去上都時曾在蒙古族草原見到過。”我們認(rèn)為:契丹的反彈胡琴與馬可波羅記載中的二弦琴,與托布秀爾是完全相同的彈撥樂器。
莫爾吉胡先生在考察新疆時發(fā)現(xiàn)有反彈托布秀爾的演奏方式:“巴彥陶海把椅子推開,在屋子中間雙叉而立,將托布修爾放在身后彈奏起來――反彈托布修爾。請注意!托布修爾是在演奏者身后,不但位置已經(jīng)倒轉(zhuǎn),雙手操琴演奏的方向也完全是逆向的。這就為演奏帶來極大的不便。然而,巴彥陶海為我們演奏的反彈的6首樂曲,無論是音準(zhǔn),樂曲的速度以及力度都聽不出和正面彈奏時有什么不同。還是那般明快,那般動人。是少見多怪,還是醉眼蒙?剎那間,我被此景所深深感動,熱淚盈眶,思緒萬千。是呵!人們從敦煌壁畫上,曾見到反彈琵琶的形象,然而,這是遙遠(yuǎn)的歷史。近年從舞劇《絲路花雨》中,見到反彈琵琶的美姿,那也是想象的形象。那么,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誰目睹過‘反彈琵琶’的‘’呢?然而,奇跡卻發(fā)生在自己的眼前。我目睹了這個事實――反彈托普修爾。更不可想象的是,這奇跡的創(chuàng)造者,竟是生活在僻靜的博爾塔拉山村中一位極為普通的蒙古族勞動婦女。這難道不令人振奮嗎?――在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亦是如此。曾經(jīng)有過的輝煌年月里所創(chuàng)造的燦爛文明,大部分可能會隨著歷史的變遷,時光的流逝而消失、泯滅,但也會有相當(dāng)?shù)牟糠至阈堑乇4嬖谌嗣裰虚g。我們從巴彥陶海身上所目睹了的事實,不正是一個極好的印證嗎?”
蒙古人在戰(zhàn)斗前,經(jīng)常引吭高歌,鼓舞斗志。《馬可?波羅游記》中有記載:“當(dāng)兩軍列陣時,種種樂器之聲及歌聲群起,緣韃靼人作戰(zhàn)以前,各人習(xí)為歌唱,彈兩弦樂器,其聲頗悅耳。彈唱久之,迄於鳴鼓之時,兩軍戰(zhàn)爭乃起”。這里所說的兩弦樂器應(yīng)是托布秀爾。其歌聲鏗鏘有力,豪壯氣魄。蒙古族這種戰(zhàn)爭組舞形式彼此獨立而又內(nèi)在聯(lián)系,生動體現(xiàn)了古代蒙古樂舞的特征。
有學(xué)者說西蒙古使用的托布秀爾樂器在內(nèi)蒙古中沒有,它是衛(wèi)拉特蒙古人從哈薩克族樂器借鑒創(chuàng)造的。莫爾吉胡先生對此表示質(zhì)疑。他說:關(guān)于民間樂器托布秀爾的來源,其說不一。筆者覺得有些說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如“托布秀爾就是冬不拉”說,即是其中一例。誠然,某一種民間樂器在幾個不同民族中,甚至在幾個鄰近的國家中間同時流傳的現(xiàn)象,過去有之,現(xiàn)在依然有之。如“三弦”“竹笛”,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否定民間樂器的民族性。托布秀爾這一彈撥樂器,無論在樂器形制、演奏方法、樂曲風(fēng)格方面,均有鮮明的蒙古族特征。而且,人們自古以來命其名為托布秀爾。這就表明,或應(yīng)當(dāng)說,托布秀爾是一件地地道道的蒙古族民間樂器。所謂“托布秀爾就是冬不拉”之說,恐怕連哈薩克族自己也不會承認(rèn)。
為什么內(nèi)蒙古沒有托布秀爾樂器呢?莫爾吉胡先生說:“蒙古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音樂文化,是極其豐富多彩的。但我們音樂理論工作者對蒙古音樂的研究,現(xiàn)在只是剛剛邁出了步伐。從縱的方面來看,蒙古音樂在歷史上曾有過輝煌的年代。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使許多音樂遺產(chǎn)已經(jīng)失傳了。從橫的方面來看,蒙古民族散居在自我國至中亞,由西伯利亞至伏爾加河畔的廣袤地帶。在這些蒙古人中間尚流傳著相當(dāng)數(shù)量的民間歌曲、不少的民間樂器和樂曲舞曲。有意思的是,某些古老的民間音樂形式,在這一地區(qū)已經(jīng)失傳了,但在另一地區(qū)則還在人民群眾中繼續(xù)流傳著。例如,新疆地區(qū)的蒙古族,人口雖然很少(和的蒙古族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相比),但那里卻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民間音樂遺產(chǎn)。所以,厄魯特四部的獨特音樂在蒙古音樂文化中的地位,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它的人口比例。”上述觀點基本認(rèn)為內(nèi)蒙古的馬頭琴是在新疆葉克勒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的,說明新疆地區(qū)保留了古老的蒙古人的歷史文化。由此看來,托布秀爾這個樂器保存在新疆地區(qū)就不奇怪了。內(nèi)蒙古人最終選擇了演奏技巧更豐富的三弦,而放棄了比較原始的托布秀爾這個樂器,所以目前只能在新疆地區(qū)看見托布秀爾。
托布秀爾是蒙古族音樂文化的重要遺產(chǎn),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新疆蒙古人中非常普及的樂器,對它的研究將會推動新疆蒙古族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宋博年,李強(qiáng).西域音樂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243.
[2]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游記[M].格日勒朝格圖,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