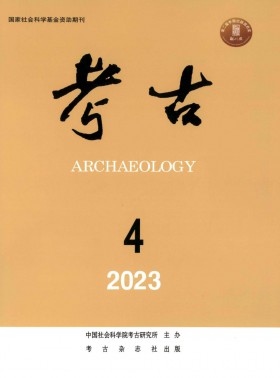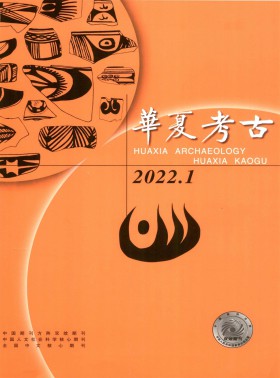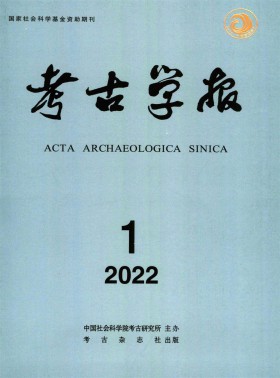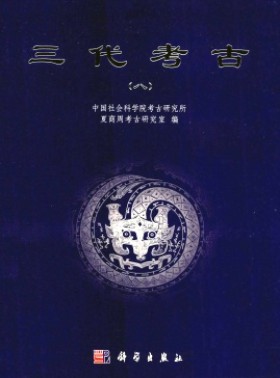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wǎng)精心挑選了考古學(xué)的分支范文供你參考和學(xué)習(xí),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fā)你的文章創(chuàng)作靈感,歡迎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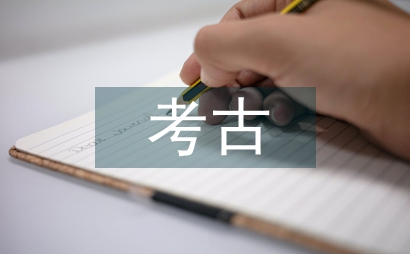
考古學(xué)的分支范文1
就學(xué)科名稱而言,音樂考古學(xué)是一個(gè)合成詞,它反映了“音樂”與“考古”二者的交叉與聯(lián)系,清晰地表明“音樂”與“考古”是構(gòu)成其學(xué)科概念的二元結(jié)構(gòu)。
1982年初,筆者在初用“音樂考古”一詞時(shí),曾嘗試著解釋為:“音樂考古,是利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音樂文物和文獻(xiàn)對(duì)古代音樂所進(jìn)行的研究,是古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音樂史界、考古界共同開辟的一個(gè)科學(xué)新領(lǐng)域。”這只是對(duì)一個(gè)新興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詞強(qiáng)調(diào)了考古之于音樂考古的重要關(guān)系。
更多學(xué)者先后從學(xué)科的高度定義“音樂考古學(xué)”,大多數(shù)也凸現(xiàn)了這種關(guān)系。
秦序:“音樂考古學(xué)是根據(jù)出土和傳世的古代音樂實(shí)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xué),它既是考古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又是音樂史學(xué)的一個(gè)部門。換言之,它是考古學(xué)與音樂史學(xué)相互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發(fā)展起來的專門學(xué)科。”
蔣定穗:“‘音樂考古學(xué)’是近年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音樂文物大量出土和音樂史學(xué)研究的不斷深入而逐漸形成的一門‘潛科學(xué)’”。“音樂考古發(fā)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學(xué)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樂史學(xué)方法研究出土樂器,也已顯得不夠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學(xué)和音樂史學(xué)相互結(jié)合而形成的新學(xué)科。……音樂考古學(xué)是根據(jù)古代人類活動(dòng)中遺留下來的音樂方面實(shí)物,運(yùn)用考古學(xué)的方法研究古代音樂歷史的學(xué)科。”
譚若冰、黃翔鵬:“音樂考古學(xué)是音樂學(xué)的一個(gè)新興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圍與考古學(xué)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對(duì)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為考古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而與美術(shù)考古、絲綢考古、陶瓷考古、青銅器考古等學(xué)科并立的,國際上稱為音樂考古學(xué)。中國當(dāng)代的音樂考古學(xué)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duì)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shí)際內(nèi)容已越出考古學(xué)的范圍。”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xué)是根據(jù)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zhì)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fā)展歷程及其規(guī)律的科學(xué)。”“作為音樂史學(xué)的一門分支學(xué)科,音樂考古學(xué)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bǔ)、充實(shí)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nèi)容。”
李純一:“從研究對(duì)象、方法和目標(biāo)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xué)乃至音樂考古學(xué)應(yīng)該既是普通考古學(xué)的一個(gè)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當(dāng)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duì)獨(dú)立性。”
王子初:“音樂考古學(xué)是音樂史學(xué)的一個(gè)部門。是根據(jù)與音樂有關(guān)的實(shí)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shù)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shù)的歷史的科學(xué)。”
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xué)是音樂學(xué)和考古學(xué)的交叉學(xué)科,它要求從業(yè)者不僅具備音樂學(xué)(特別是音樂史學(xué)、音樂形態(tài)學(xué)和樂器學(xué))方面的知識(shí),還要掌握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fā)掘作業(yè)的全部技能與經(jīng)驗(yàn)。”
李幼平:“音樂考古學(xué)是音樂學(xué)、考古學(xué)、歷史學(xué)、人類學(xué)等學(xué)科在交叉、融合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xué)科”,“考古學(xué)與音樂學(xué)研究應(yīng)該是它的兩個(gè)基本立足點(diǎn)。”
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xué)脫胎于一般考古學(xué),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guān)系”,“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xué)界之驥尾。”“音樂考古學(xué)是考古學(xué)和音樂學(xué)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是一門跨學(xué)科的邊緣學(xué)科。……音樂考古學(xué)是考古學(xué)的組成部分,其時(shí)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xué)的地層學(xué)和類型學(xué)以及考古學(xué)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shí),音樂學(xué)的理論應(yīng)該是音樂考古學(xué)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dǎo)。”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xué)主要是考古學(xué)與音樂學(xué)尤其是音樂史學(xué)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xué)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xué)和音樂史學(xué)的雙重性質(zhì),但又具有相對(duì)的獨(dú)立性。”“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則從普通考古學(xué)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xué)滋養(yǎng)下本土化的產(chǎn)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也受到了考古學(xué)和音樂學(xué)(尤其是歷史音樂學(xué))的雙重影響。”
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xué)是音樂考古學(xué)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yǎng)的基礎(chǔ),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diǎn)之一,等等。
這種深刻的認(rèn)識(shí),基于音樂考古學(xué)萌芽期的實(shí)踐總結(jié)。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xué)界在文物、考古學(xué)界的幫助和推動(dòng)下,創(chuàng)立了音樂考古學(xué)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xué)科已經(jīng)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duì)培養(yǎng)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fā)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chǔ)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shè)了專門的研究機(jī)構(gòu);建立了國際性的學(xué)術(shù)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xué)術(shù)交流活動(dòng)。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呈現(xiàn)著繁榮、活躍的學(xué)術(shù)景象。
不過,從理論和實(shí)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與普通考古學(xué)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xué)科發(fā)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xué)的正式認(rèn)同。在考古學(xué)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xué)”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xué)影響所產(chǎn)生的特殊考古學(xué)分支現(xiàn)已包括了諸如美術(shù)考古學(xué)、宗教考古學(xué)、古錢學(xué)、古文字學(xué)和銘刻學(xué)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xué)”。
在實(shí)踐上,中國現(xiàn)行的考古事業(yè)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yè)才有考古發(fā)掘權(quán)。以音樂學(xué)學(xué)術(shù)身份出現(xiàn)的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家從身份和職業(yè)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jìn)入考古學(xué)的田野考古發(fā)掘領(lǐng)域。而在考古事業(yè)的機(jī)構(gòu)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樂考古學(xué)與普通考古學(xué)在田野發(fā)掘的交叉重合區(qū)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yè)脫節(jié)。音樂考古學(xué)與普通考古學(xué)的學(xué)術(shù)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fā)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xué)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jù)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fā)掘項(xiàng)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shù)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tài)工作。
這種情況對(duì)于兩個(gè)學(xué)科和藝術(shù)及文化遺產(chǎn)事業(yè)都是不利的。
考古學(xué)的分支范文2
[關(guān)鍵詞]音樂考古學(xué);考古學(xué);音樂學(xué);音樂學(xué)學(xué)科體系
一、音樂考古學(xué)在中國
雖然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來的“金石學(xué)”,但近代學(xué)科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xué)當(dāng)始于劉復(fù)在1930—1931年間,對(duì)故宮和天壇所藏清宮古樂器的測(cè)音研究,正是劉復(fù)將“以科學(xué)方法整理國故”的理想付諸于研究中國古代音樂的實(shí)踐,并在此基礎(chǔ)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開了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新的篇章,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學(xué)之堂,入音樂學(xué)之室”。譬如:楊蔭瀏在20世紀(jì)50年代出版的《中國音樂史綱》一書中,援引了當(dāng)時(shí)許多有關(guān)出土文物的發(fā)掘資料和研究成果;李純一搜集了大量考古發(fā)掘的古代樂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將這些成果運(yùn)用到《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cè)•夏商)一書中,這兩位學(xué)者對(duì)考古資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運(yùn)用改變了自葉伯和以來的中國音樂史研究“從文獻(xiàn)到文獻(xiàn)”的舊傳統(tǒng),音樂考古學(xué)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學(xué)界的重視。
二、音樂考古學(xué)作用于他種音樂學(xué)分支學(xué)科
音樂考古學(xué)作為一門交叉學(xué)科,是在考古學(xué)和音樂學(xué)的羽翼下逐漸形成的。于音樂學(xué)而言,音樂考古學(xué)是音樂史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這也得到國內(nèi)外學(xué)者一致的認(rèn)識(shí),例如,德國學(xué)者德列格將音樂學(xué)分為歷史音樂學(xué)、體系音樂學(xué)、音樂民族學(xué)(民俗學(xué))、音樂社會(huì)學(xué)和應(yīng)用音樂學(xué)五大類,其中,音樂考古學(xué)是作為歷史音樂學(xué)的一個(gè)部門而存在的;音樂史學(xué)家李純一認(rèn)為:“它(音樂考古學(xué))應(yīng)該既是普通考古學(xué)的一個(gè)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樂史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1]雖然音樂考古學(xué)是歷史音樂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但其在整個(gè)音樂學(xué)體系中的地位卻并非僅僅只作用于音樂史學(xué)的研究,其對(duì)中國古代音樂美學(xué)史,以及當(dāng)下的民族音樂學(xué)的研究依然有著促進(jìn)作用。
三、音樂考古學(xué)作用于音樂史學(xué)
較之于其他音樂學(xué)科而言,音樂考古學(xué)與音樂史學(xué)的關(guān)系尤為密切,這是因?yàn)?其一,在研究對(duì)象的時(shí)間維度上,它們都是指向于過去,研究歷史上的音樂事項(xiàng),以了解古代的音樂社會(huì)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時(shí)期,音樂考古學(xué)研究是音樂史學(xué)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出現(xiàn)之后,有關(guān)音樂的考古實(shí)物和文獻(xiàn)典籍是音樂史研究的兩大史料來源。具體來說,音樂考古學(xué)對(duì)音樂史學(xué)的作用大致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彌補(bǔ)文獻(xiàn)的不足
人類發(fā)展的歷史是極其漫長的,即便是從舊石器時(shí)代算起,也大約有300萬年的歷史;而人類用文字記載的歷史,也就是說有比較確切的資料可以證明的信史,就中國而言,大約是從公元前17世紀(jì)的商代開始的,距今不過4000年左右。從300萬年前到4000年前,這么漫長的歷史,除了通過神話傳說獲得一鱗半爪的模糊的認(rèn)識(shí)之外,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如《呂氏春秋•古樂篇》載:“帝堯立,乃命質(zhì)為樂。質(zhì)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載:“開(夏后啟)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開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過這些記載認(rèn)識(shí)商以前的歷史不僅模糊不清、無法得以考證,而且也是一種無奈。可見,通過文字了解人類音樂的歷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樂實(shí)物以及對(duì)它們所進(jìn)行的科學(xué)研究,不僅改變了我們對(duì)史前音樂歷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話傳說的尷尬局面,也改變了我們對(duì)史前音樂歷史的認(rèn)識(shí)。例如,1987年,河南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shí)代遺址出土的25支骨笛,據(jù)碳14測(cè)定和樹輪校正,距今約8000—9000年;根據(jù)測(cè)音和實(shí)際的演奏實(shí)驗(yàn)表明,這些音已包括了六聲音階和七聲音階,并且可以吹奏較為復(fù)雜的曲調(diào)。這一結(jié)果不僅改變了我們之前對(duì)新石器時(shí)期音樂認(rèn)識(shí)上的空白,而且也改變了對(duì)已有的中國古代音樂諸多研究成果的認(rèn)識(shí),促使我們對(duì)其進(jìn)行重新考量,如學(xué)界很長一段時(shí)期都在爭(zhēng)論的“戰(zhàn)國時(shí)期有無五聲音階以外的偏音”的問題;音階發(fā)展史是由少漸多,還是一個(gè)從多到少不斷規(guī)范的過程的問題等。這方面的音樂考古發(fā)現(xiàn)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塤等。可以說,從科學(xué)的意義上研究史前音樂歷史,考古實(shí)物是唯一的途徑和手段。它不僅是我們了解史前音樂歷史的不二法門,也對(duì)其后有文字記載的音樂歷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進(jìn)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獻(xiàn)互證
考古史料和文獻(xiàn)史料互證,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源于20世紀(jì)20年代王國維對(duì)古代歷史的研究。他主張研究古史當(dāng)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xiàn)史料,這在歷史學(xué)界有很大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被學(xué)界稱之為“二重證據(jù)法”。“二重證據(jù)法”的提出,一方面導(dǎo)源于對(duì)科學(xué)研究實(shí)證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考古學(xué)在中國的不斷發(fā)展與成熟。這一研究方法對(duì)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也有很大的影響和促進(jìn)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國音樂史》一書就曾指出:“研究古代歷史,當(dāng)以‘實(shí)物’為重,‘典籍’次之,‘類推’又次之。”[2]其后,學(xué)者們都自覺和不自覺地將此方法運(yùn)用到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實(shí)踐中,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為之一變,它不僅改變了傳統(tǒng)史學(xué)“從文獻(xiàn)到文獻(xiàn)”的舊傳統(tǒng),也使研究所得之結(jié)論多了些許的實(shí)證面貌。例如,古書中有關(guān)鼉鼓的記載甚多,《呂氏春秋•古樂篇》:“帝顓頊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詩經(jīng)•大雅》:“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諫逐客書》和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提到的“靈鼉之鼓”。鱷魚在古代被稱作鼉,鼉鼓即是用鱷魚皮制作的鼓。在沒有有關(guān)鼉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學(xué)界對(duì)這些記載多半持將信將疑的態(tài)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3015號(hào)大墓木鼉鼓的出土,釋解了人們心中的疑團(tuán),從而確信鼉鼓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真實(shí)存在。
3.匡正用文獻(xiàn)研究可能出現(xiàn)的謬誤
翻開歷朝歷代正史樂志可知,其中有關(guān)音樂的記載多出于統(tǒng)治階級(jí)之手,所載內(nèi)容側(cè)重于宮廷雅樂,對(duì)宮廷之外豐富多彩的民間音樂記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為了取悅于統(tǒng)治者甚至?xí)崆鷼v史,因而必然有階級(jí)的和時(shí)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輕器”的古代,記載音樂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樂專業(yè)知識(shí)的樂工,而是一些對(duì)音樂一知半解的文人,這也必然會(huì)使有關(guān)音樂的記述含混不清,乃至錯(cuò)誤失實(shí),以訛傳訛,貽害千年。如此,考證、校讎等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一籌莫展,考古史料則表現(xiàn)出其特有的參證和糾錯(cuò)的作用。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樂器的出土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發(fā)掘及其大量精美的樂器的出土不僅向世人展示了一個(gè)“地下音樂宮殿”的輝煌,其重大的意義在于改變了我們對(duì)已有的通過文獻(xiàn)研究而獲得的中國古代音樂史一些偏頗的認(rèn)識(shí):其一,對(duì)一鐘雙音現(xiàn)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腳。1977年,呂驥、黃翔鵬等音樂家去甘肅、山西、陜西、河南四省做音樂考古調(diào)查研究時(shí),發(fā)現(xiàn)了中國古代的鐘,在敲擊鐘的不同位置時(shí)可發(fā)兩個(gè)相距三度的音,但這一理論在提出時(shí)遭當(dāng)時(shí)學(xué)界眾多人的懷疑,人們普遍持否定態(tài)度。次年,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讓世人承認(rèn)并接受了“一鐘雙音”的事實(shí)。其二,對(duì)于中國古代音樂史上一直爭(zhēng)論不休的“古音階”和“新音階”的問題。其三,對(duì)于中國只有首調(diào)唱名法而沒有固定調(diào)唱名法的問題以及工尺譜的淵源、中國的樂律學(xué)理論等諸多有爭(zhēng)議的問題都作了很好地解釋。
4.扭轉(zhuǎn)了用文字描述音樂史非直觀形象的不足
音樂是一門時(shí)間藝術(shù),也是一門聲音的藝術(shù)。撰寫一部有聲的中國古代音樂史一直是音樂史學(xué)家的追求,從楊蔭瀏“音樂史是不能沒有音樂的歷史”[3]的治史觀到黃翔鵬“曲調(diào)考證”研究的身體力行,無數(shù)學(xué)人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著;但我們同時(shí)也應(yīng)知道,音樂生活的畫面并非僅有聲音組成,在三維空間里尚有樂器的形制、樂隊(duì)的組織、器樂的編排以及樂人的服飾和奏樂的場(chǎng)景等,考古出土的遺跡、樂器實(shí)物以及音樂圖像,包括繪畫、畫像磚、編織圖、樂舞俑、洞窟壁畫、器皿飾繪、墓葬壁畫、畫像石、石刻、書譜等,則可以直觀地以立體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現(xiàn)歷史上的音樂畫面。例如,文獻(xiàn)中有關(guān)先秦瑟的形制的記載語焉不詳,甚至有分歧之處,我們?nèi)缛魞H僅通過文獻(xiàn)并不能對(duì)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關(guān)先秦瑟的實(shí)物,則能立即給予我們非常明確的感官認(rèn)識(shí):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再如,李榮有《漢畫像的音樂學(xué)研究》一書通過對(duì)大量出土的漢畫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漢朝音樂生活的諸多層面;《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觀地展示出了各地區(qū)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所出現(xiàn)的樂器的類型、特征等,并可以對(duì)不同省的出土樂器進(jìn)行比照,揭示其間的異同之處和源流動(dòng)向。可以說,考古史料讓音樂史的研究具有了現(xiàn)場(chǎng)感和親切感,讓人如置身于歷史的語境之中。
綜上可知,音樂考古學(xué)雖然是考古學(xué)和音樂學(xué)的交叉學(xué)科,其下屬于歷史音樂學(xué),但其在整個(gè)音樂學(xué)學(xué)科體系中的作用,并非僅僅局限于音樂史學(xué),其對(duì)于拓寬和延展音樂美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豐富音樂美學(xué)的研究?jī)?nèi)容;對(duì)于改變民族音樂學(xué)在研究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時(shí)文獻(xiàn)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闡釋音樂背后的文化意蘊(yùn)等都有很大的促進(jìn)作用。
作者:于珊珊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xué)
[參考文獻(xiàn)]
[1]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總論•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考古學(xué)的分支范文3
關(guān)鍵詞:人類學(xué);考古;本科
中圖分類號(hào):G642.0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4-9324(2017)07-0215-02
體質(zhì)人類學(xué)是廣義人類學(xué)下的分支學(xué)科,是研究人類的體質(zhì)特征和類型,在時(shí)間和空間上的變化和規(guī)律的一門學(xué)科,它的研究對(duì)象分為對(duì)現(xiàn)代人的體質(zhì)調(diào)查和對(duì)古代遺骨的研究,從而獲得更多的人類學(xué)信息[1]。考古學(xué)是根據(jù)古代人類活動(dòng)遺留下來的實(shí)物來研究人類古代情況的一門科學(xué),其研究對(duì)象是古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zhì)遺存,目的是透物見人,認(rèn)識(shí)當(dāng)時(shí)人類的社會(huì)發(fā)展?fàn)顩r,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社會(huì)習(xí)俗等信息[2]。兩個(gè)學(xué)科之間的研究對(duì)象都是以人為主體,前者是直接的以研究人類遺骸為對(duì)象,分析其體質(zhì)特征,了解當(dāng)時(shí)的人類學(xué)信息,更多地認(rèn)識(shí)到的是人類的自然屬性特征。后者是通過研究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東西,間接地去推測(cè)過去的社會(huì)情況,人類生存和生活環(huán)境,側(cè)重于了解人類的社會(huì)屬性。中國考古學(xué)按縱向劃分為若干個(gè)分支學(xué)科,如舊石器時(shí)代考古、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商周考古、戰(zhàn)國秦漢考古、魏晉隋唐考古和宋元考古等。不管哪一個(gè)考古學(xué)階段,研究對(duì)象的主體都是當(dāng)時(shí)進(jìn)行社會(huì)活動(dòng)的古代人類。因此,體質(zhì)人類學(xué)的研究是貫穿于整個(gè)考古學(xué)研究的始終的。
體質(zhì)人類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大體上可以分為對(duì)古人類化石的研究,對(duì)古人種的研究和對(duì)現(xiàn)代人的研究,以及新興的分子生物學(xué)的研究等。不同的體質(zhì)人類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在不同的考古學(xué)階段中都有所體現(xiàn)[3]。舊石器時(shí)代考古中出土的人類化石為人類學(xué)者們研究人類的起源和現(xiàn)代人的起源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jù)和材料,新石器時(shí)代以后的人骨多用于研究古代人種的形成、分布、遷徙和消亡的過程。考古學(xué)可以為體質(zhì)人類學(xué)提供研究材料,無論是舊石器時(shí)代的人類化石,還是新石器時(shí)代及以后各個(gè)歷史時(shí)期的人類學(xué)標(biāo)本均要靠田野考古發(fā)掘來提供。體質(zhì)人類學(xué)的研究也有助于考古學(xué)研究的深入開展。古人類化石可以作為舊石器時(shí)代考古中判斷底層年代的一種依據(jù):對(duì)古代人骨的性別、年齡鑒定有利于人們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性質(zhì)、勞動(dòng)分工等情況的探討;對(duì)古代居民人種歸屬的研究可以從一個(gè)側(cè)面為解決考古學(xué)文化的譜系淵源和族屬等問題提供若干參考的佐證[4]。
一、透骨見人
所謂的透骨見人就是通過觀察和測(cè)量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分析其體質(zhì)特征和類型,獲取當(dāng)時(shí)人類的人類學(xué)信息。具體地講,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對(duì)其性別的鑒定。人類學(xué)家們根據(jù)骨盆、顱骨的形態(tài)觀察和分子生物學(xué)的方法,準(zhǔn)確地判定其性別。其次是對(duì)人骨死亡年齡的鑒定,通常專家們根據(jù)牙齒的萌出時(shí)間、磨耗程度、骨縫愈合情況、恥骨聯(lián)合面的關(guān)系等多項(xiàng)參數(shù),判定人骨的死亡年齡。我們要做到對(duì)性別和年齡最為準(zhǔn)確的判定,就要結(jié)合各項(xiàng)參數(shù),并結(jié)合現(xiàn)代分子生物學(xué)的方法綜合分析人骨標(biāo)本,慎重地給以結(jié)果[5]。
另外對(duì)人骨身高的推算和病理、死因和食譜的分析也是體質(zhì)人類學(xué)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身高的推算一般借助于股骨矢狀徑的長度和其他長骨參數(shù)相結(jié)合的模式,而最近也有學(xué)者提出用第二、第三掌骨的矢狀徑長度的推算身高的方法也能達(dá)到近九成的正確率。病理和死因的研究,則主要依據(jù)人骨某個(gè)部位的變異和缺失情況而判定。通過研究人骨內(nèi)含微量元素的變化,對(duì)一些諸如骨質(zhì)疏松、氟骨癥、營養(yǎng)不良等古代疾病也提供了重要的科學(xué)研究方法。通常對(duì)死因的判定,主要?jiǎng)澐譃槭且蚬莻遣《缒曦舱鄣模€是屬于非骨傷骨病而自然死亡的兩大類。
對(duì)一定數(shù)量的人骨進(jìn)行食譜分析,可以為了解當(dāng)?shù)厝说慕?jīng)濟(jì)生業(yè)模式提供重要的線索,目前食譜分析方法主要是分析遺留在古人類牙齒上的食物殘?jiān)蛯?duì)人骨成分的微量元素進(jìn)行分析,來確定當(dāng)時(shí)人類的主要食性。
二、透人見骨
透人見骨研究對(duì)象是現(xiàn)代人群。我們通過對(duì)現(xiàn)代人群體質(zhì)特征的形態(tài)觀察和測(cè)量,按照一定的遺傳學(xué)特征劃分為若干個(gè)人種類型。如蒙古人種、歐羅巴人種和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在我國對(duì)現(xiàn)代人體質(zhì)特征的調(diào)查多結(jié)合民族學(xué)材料,探究民族起源、遷徙以及彼此的基因交流等重要課題。但是我過現(xiàn)在的人種學(xué)研究方面還有許多空白領(lǐng)域有待填補(bǔ),現(xiàn)代各民族的體質(zhì)調(diào)查工作還沒有全面展開,人種學(xué)研究的力量就顯得更加薄弱。如果我們將來能夠在時(shí)間和空間兩個(gè)范圍內(nèi)搞清楚我國各民族人民的人種構(gòu)成方面的來龍去脈,以后必將會(huì)加深人們對(duì)我國古今民族的起源、發(fā)展、分化和如何問題的了解,進(jìn)而有助于我們正確認(rèn)識(shí)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過程。
三、透骨見骨
透骨見骨是將不同個(gè)體或不同群體的人骨標(biāo)本各項(xiàng)體質(zhì)特征參數(shù)相對(duì)比,從而確定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遺傳學(xué)關(guān)系,對(duì)判定人群的遷徙、融合、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學(xué)根據(jù)。人骨的體質(zhì)特征的觀察主要集中在對(duì)顱型和面型的測(cè)量和形態(tài)學(xué)觀察上。在此研究的基礎(chǔ)之上劃分出一個(gè)可以比對(duì)的標(biāo)準(zhǔn)。將不同組人群的體質(zhì)特征進(jìn)行想必對(duì)后,確定其關(guān)系的遠(yuǎn)近以及族群之間的基因交流情況。
四、透人見人
透人見人的研究對(duì)象也是現(xiàn)代人群。是以研究人群和人群之間的關(guān)系為主要內(nèi)容的人類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即我們?cè)诟髅褡宓捏w質(zhì)調(diào)查和古代文化譜系、種族情況的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之上,把某個(gè)或某些現(xiàn)代人劃入某些已知共有的遺傳學(xué)特征的地域或民族中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根據(jù)這個(gè)人的形態(tài)學(xué)特征,可以推測(cè)他就是“四川人”等。在此,也需要提一下朱泓老師在1996年提出的將我國古代居民的人種成分劃分為幾個(gè)古老的類型,并解釋了其源流過程。我們對(duì)現(xiàn)代中國民族的研究,也要認(rèn)識(shí)到其古代人種類型和特征,了解其演變過程,對(duì)“透人見人”的認(rèn)識(shí)會(huì)達(dá)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對(duì)大學(xué)本科考古專業(yè)學(xué)生教學(xué)過程中,我們要弄清楚現(xiàn)代人的人類學(xué)結(jié)構(gòu),不只需要對(duì)現(xiàn)代人進(jìn)行體質(zhì)調(diào)查,也需要對(duì)古代材料有一定的把握,知其淵源和變遷,從而才能更好地解釋各民族形成的人類需基礎(chǔ)。
參考文獻(xiàn):
[1]朱泓.體質(zhì)人類學(xu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2-106.
[2]科林?倫福儒,保_?巴恩.考古學(xué)理論方法與實(shí)踐[M].第6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21.
[3]邵象清.人體測(cè)量手冊(cè)[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34-56.
[4]周亞威.論體質(zhì)人類學(xué)研究解決的若干考古學(xué)問題[J].江漢考古,2015,(6).
[5]周亞威.北京延慶西屯墓地人骨研究[D].吉林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4.
考古學(xué)的分支范文4
關(guān)鍵詞:海龍囤 公眾考古 實(shí)踐
中國分類號(hào):K87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8705(2014)01-103-107
在古代文化遺產(chǎn)與現(xiàn)代公眾之間,考古學(xué)無疑像一座橋梁,溝通古今。但這一切并不會(huì)無端端地發(fā)生,而且隨學(xué)科專業(yè)化的逐步加強(qiáng),原本有趣的發(fā)現(xiàn)往往被轉(zhuǎn)述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內(nèi)流傳,成為“考古方言”,很難成為“普通話”而走進(jìn)公眾的視野,被廣泛認(rèn)知。如何使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成果惠及大眾,轉(zhuǎn)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護(hù)與利用?這屬“公眾考古學(xué)”(public archaeology)討論的范疇。
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對(duì)播州羈縻·土司遺存海龍囤遺址展開首次大規(guī)模考古發(fā)掘的過程中,我們依托考古現(xiàn)場(chǎng),開展了一系列公眾考古實(shí)踐活動(dòng),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文即擬以之為例,試對(duì)公眾考古相關(guān)問題進(jìn)行初步剖析。
一
海龍囤位于遵義老城西北約30里的龍巖山巔,又稱龍巖囤,是一處宋明時(shí)期的羈縻·土司城堡遺址。遺址三面環(huán)溪,一面銜山,僅東西各有仄徑可上下,地勢(shì)十分險(xiǎn)要,《明史》稱其為“飛鳥騰猿不能逾者”。遵義舊屬播州,公元9-17世紀(jì)為楊氏所據(jù),世守其土達(dá)724年,共傳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統(tǒng)領(lǐng)。據(jù)現(xiàn)有文獻(xiàn),海龍囤始建于宋寶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毀于明萬歷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1982年公布為省級(jí)文物保護(hù)單位,2001年晉升為全國重點(diǎn)文物保護(hù)單位,2012年11月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chǎn)預(yù)備名單”。
2012年度的發(fā)掘取得了重要收獲,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diǎn):
第一,基本廓清了海龍囤的整體格局。經(jīng)過多年的調(diào)查與試掘,現(xiàn)已探明海龍囤有約6公里長的環(huán)囤城墻,其所圍合的面積達(dá)1.59平方公里。囤東有銅柱、鐵柱、飛虎(三十六步)、飛龍、朝天、飛鳳(五鳳樓)六關(guān);囤西有后關(guān)、西關(guān)、萬安三關(guān),彼此圍合的空間形成兩個(gè)甕城。囤頂平闊,“老王宮”和“新王宮”,是其中最大的兩組建筑群,面積均在2萬平方米左右。另有軍營(俗稱“金銀庫”)、敵樓(如“四角亭”與“繡花樓”等)、校場(chǎng)壩等遺跡。
第二,發(fā)現(xiàn)環(huán)繞“新王宮”的城墻,框定了“新王宮”的范圍,基本厘清了其格局、性質(zhì)和年代。環(huán)“宮”城墻長504米,其圍合的“新王宮”面積達(dá)1.8萬平方米,探明其內(nèi)建筑20余組,并對(duì)其中的F1、F2、F7、F8、F9、F10、F11等數(shù)組進(jìn)行了重點(diǎn)清理,出土青花、青瓷、勾頭、滴水、石構(gòu)件、礌石、彈丸、鐵鎧甲片、石硯臺(tái)、錢幣等遺物上萬件。發(fā)掘揭示,“新王宮”具有中軸線、大堂居中、前朝后寢等特點(diǎn),與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獻(xiàn)中亦明確稱其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新王宮”實(shí)質(zhì)上是一處土司衙署遺址。從出土遺物看,它是一組明代建筑群,嘉靖、萬歷時(shí)期是其鼎盛時(shí)期,最后毀棄于萬歷年間的大火。
第三,基本確認(rèn)了石、磚、瓦等建筑材料的來源。為了解磚、瓦和石料的來源,對(duì)海龍囤及其周邊展開了針對(duì)窯址和采石場(chǎng)的調(diào)查和清理,發(fā)現(xiàn)民間傳說的“采石場(chǎng)”確系一處采石遺跡,清理出采石所遺的各類楔眼上百個(gè),與“新王宮”建筑石材上所見楔眼完全一致。另在“老王宮”東北角發(fā)現(xiàn)窯址數(shù)座,對(duì)其中一座進(jìn)行清理(Y1),系一座明代磚窯。由此可知,建囤過程中石材、磚瓦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第四,通過調(diào)查與發(fā)掘,對(duì)海龍囤的性質(zhì)有了更深的認(rèn)識(shí)。海龍囤是一處融保衛(wèi)國家利益與維護(hù)土司家族利益于一體,集關(guān)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羈縻·土司城堡。特殊時(shí)期,堅(jiān)不可摧的海龍囤是土司的重要軍事防御據(jù)點(diǎn);和平年代,風(fēng)景秀麗、氣候怡人的海龍囤則可能成為土司的別館離宮。從南宋中期開始,穆家川(今遵義老城)一直便是楊氏統(tǒng)領(lǐng)播州的政治中樞,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龍囤與之并行不悖,前者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為山城,偏重于軍事,它們一起構(gòu)成了播州楊氏完備的城邑體系。
發(fā)掘的意義表現(xiàn)于:
第一,海龍囤特別是“新王宮”的整體格局與明故宮契合(同時(shí)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點(diǎn)),反映了土司在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國家認(rèn)同,這種一致性在一定的歷史時(shí)期有效維護(hù)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
第二,海龍囤是我國羈縻·土司制度的實(shí)物遺存,它完整見證了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政策由唐宋時(shí)期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時(shí)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變遷,它的發(fā)掘?yàn)閺目脊艑W(xué)的角度深化中國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討中央與地方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換言之,其對(duì)推行羈縻之治以來,中央如何開發(fā)、經(jīng)營與管理西南疆,邊地又是如何逐步漢化而與華夏漸趨一體等問題的深化有著積極的意義。
第三,這處設(shè)有衙署的軍事屯堡,是中國西南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續(xù)時(shí)間最長的羈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點(diǎn),對(duì)中國西南同期以及后來的同類建筑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第四,海龍囤的發(fā)掘可能引發(fā)考古學(xué)界新的學(xué)術(shù)關(guān)注點(diǎn),即將視線從中原的、早期的遺存更多的投向邊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遺存中來,從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領(lǐng)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學(xué)方法與理論的發(fā)展。
該發(fā)掘榮膺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并入選“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學(xué)論壇——2012年中國考古新發(fā)現(xiàn)”(俗稱“六大發(fā)現(xiàn)”),在學(xué)界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
二
如何在這樣一個(gè)遺址上開展公眾考古活動(dòng)?首先牽扯到我們對(duì)“公眾考古學(xué)”的理解。
多數(shù)人將“公眾考古學(xué)”理解為考古科普。中國考古學(xué)的科普工作起步較早,曾以“考古學(xué)的大眾化”示人,但現(xiàn)在流行的“公眾考古學(xué)”卻是一個(gè)舶來品,內(nèi)涵也較前者豐富。換言之,考古科普只是公眾考古學(xué)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到底何為“公眾考古學(xué)”?
20世紀(jì)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學(xué)家對(duì)考古學(xué)與社會(huì)的相互關(guān)系以及考古學(xué)家社會(huì)責(zé)任的思考所引發(fā)的討論,最終產(chǎn)生了考古學(xué)一個(gè)新的分支——“公眾考古學(xué)”(puhlic archaeology)。它將焦點(diǎn)聚集在“我們?yōu)槭裁匆私膺^去”,“過去對(duì)我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等責(zé)任感問題上,因而超越了對(duì)“過去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的學(xué)理探討而上升到對(duì)“過去為何發(fā)生某事及其對(duì)于當(dāng)下的意義”的闡釋的哲學(xué)層面,以及具體踐行活動(dòng)中。其目的是通過參與式的實(shí)踐,調(diào)合各利益相關(guān)者的矛盾與利益,從而助益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
問題在于,誰是“公眾”?他們又如何能為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貢獻(xiàn)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詞,是一個(gè)與私人領(lǐng)域?qū)α⒌墓窦象w,譯作漢文,有“公共”(國家及其公共機(jī)構(gòu))和“公眾”(彼此間有爭(zhēng)論并消費(fèi)文化產(chǎn)品的大眾群體)兩層含義。相應(yīng)的,“puhlic archaeology”也存在“公眾考古”和“公共考古”兩譯。雖然強(qiáng)調(diào)的對(duì)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眾、考古學(xué)家和行政部門這三個(gè)主體。公眾考古的實(shí)踐,實(shí)際上就是這三方圍繞著考古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展開的一系列博弈活動(dòng)。考古學(xué)家通過推動(dòng)行政部門的制度供給,達(dá)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資源保護(hù)和管理的相關(guān)法規(guī)的目的;通過與民眾的合作,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動(dòng)中得到體現(xiàn),從而實(shí)現(xiàn)其了解自身過去的公共權(quán)力。
關(guān)系錯(cuò)綜復(fù)雜,但對(duì)考古者而言,公眾“這一名詞只是方便用來指代一個(gè)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為職業(yè)的人群。在我們的語境中,‘公眾’只是因非專業(yè)考古學(xué)者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個(gè)概念”。具體到某一個(gè)遺址中,我們認(rèn)為除了在此開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體,包括外來的考古學(xué)家均可稱之為“公眾”。進(jìn)而言之,在具體考古活動(dòng)中,凡發(fā)掘團(tuán)隊(duì)與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眾”的互動(dòng),均屬公眾考古的范疇。此時(shí),開展考古活動(dòng)的遺產(chǎn)地就變成了“交流”與“解釋”的一個(gè)重要場(chǎng)域,來自遠(yuǎn)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擴(kuò)散,利益相關(guān)者的訴求得到適當(dāng)滿足。被視作公眾考古學(xué)核心思想的“交流”、“解釋”與“考古學(xué)利益相關(guān)者”均在此場(chǎng)域中得以呈現(xiàn)。相對(duì)于博物館、陳列室等傳統(tǒng)展示渠道,考占現(xiàn)場(chǎng)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三
2012年5月起,土司城堡海龍囤遺址的考古現(xiàn)場(chǎng)就變成了這樣一個(gè)重要的場(chǎng)域。借配合“申遺”而對(duì)海龍囤展開大規(guī)模考古發(fā)掘之機(jī),經(jīng)過周密的籌劃,我們?cè)诤}埗诳脊努F(xiàn)場(chǎng)開展了一系列公眾考古的實(shí)踐活動(dòng),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為遵義重要旅游目的地海龍囤,因?yàn)榕c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關(guān)系,對(duì)包括考古學(xué)家在內(nèi)的公眾都充滿誘惑,這是相關(guān)活動(dòng)能順利開展、各方利益得以體現(xiàn)的重要前提。加之此次考古工作是在“申遺”背景下開展的,地方政府對(duì)此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并積極投入到考古活動(dòng)中來。匯川區(qū)人民政府通過專題會(huì)議、現(xiàn)場(chǎng)辦公、文件等方式,極力推進(jìn)考古發(fā)掘工作的順利進(jìn)行,行政部門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體現(xiàn)。而針對(duì)專業(yè)化和公眾直接參與的不和諧,我們則通過講座、媒體宣傳、現(xiàn)場(chǎng)體驗(yàn)等方式,讓公眾了解自身過去的公共權(quán)力得到部分滿足。
首先,在中國第七個(gè)“文化遺產(chǎn)日”之際,策劃了“親歷考古,觸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的系列公眾考古活動(dòng)。于6月10日文化遺產(chǎn)日當(dāng)天,邀請(qǐng)著名學(xué)者在貴州省圖書館舉行主題為“聆聽海龍囤”的大型學(xué)術(shù)講座,并從聽眾中產(chǎn)生70余名幸運(yùn)者,于次日與考古者一起登囤,在考古現(xiàn)場(chǎng)“觸摸海龍囤”。此后又組織了黔籍知名畫家進(jìn)海龍囤,用他們手中的畫筆描摹400年前的土司生活的“畫中海龍囤”活動(dòng);組織遺址所在地的高坪鎮(zhèn)中小學(xué)生將課堂搬至考古現(xiàn)場(chǎng)的“愛我家鄉(xiāng),考古進(jìn)課堂”活動(dòng);以及與遵義市政協(xié)共同組織了政協(xié)委員參觀考察與文藝演出相結(jié)合的“走近考古,支持申遺”的活動(dòng)。當(dāng)考古工作接近尾聲時(shí),我們邀請(qǐng)了全國20余位知名的考古學(xué)家親赴海龍囤,并召開現(xiàn)場(chǎng)座談會(huì),請(qǐng)他們?yōu)楹}埗诘陌l(fā)掘、研究與保護(hù)出謀劃策,此舉在“交流”中實(shí)現(xiàn)了海龍囤價(jià)值于更大范圍內(nèi)的傳播。如果說“聆聽”只是一個(gè)引子,其后開展的“觸摸”則是活動(dòng)的重點(diǎn)。包括外來考古學(xué)家在內(nèi)的“公眾”通過現(xiàn)場(chǎng)的觀摩與體驗(yàn),對(duì)海龍囤有了更為深入的認(rèn)知,相關(guān)感受又通過他們傳達(dá)給更廣的“公眾”。
但能到現(xiàn)場(chǎng)“親歷考古”者畢竟少數(shù),如何進(jìn)一步調(diào)適專業(yè)化發(fā)掘與公眾參與的不和諧?無疑,通過媒體與公眾形成互動(dòng)是最佳的選擇。因此,在“親歷考古”活動(dòng)之外,我們與媒體開展了密切的合作,使海龍囤的最新發(fā)現(xiàn)得以及時(shí)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盡可能滿足了其解自身過去的公共權(quán)力。通過媒體與公眾的互動(dòng),從“非專業(yè)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專業(yè)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兩個(gè)方面展開:前者是報(bào)紙、網(wǎng)絡(luò)、電臺(tái)及電視臺(tái)的記者在田野一線采寫稿件,在相應(yīng)的媒體持續(xù)刊播;后者則是發(fā)掘者親自撰寫“考古手記”,對(duì)相關(guān)發(fā)現(xiàn)作出權(quán)威解讀,在當(dāng)?shù)孛襟w連續(xù)刊登。其廣度、深度及長度,貴州此前所未有;所取得的社會(huì)影響也是空前的。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在發(fā)掘期間及獲獎(jiǎng)前后的近一年時(shí)間里,全國各媒體共推出關(guān)于海龍囤的各類報(bào)道140余篇(則),曾三上央視、三上“貴州新聞聯(lián)播”、數(shù)次登省內(nèi)媒體頭版,并有多篇深度解讀海龍囤考古的大版塊文章,使海龍囤的最新考古成果得以迅速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甚至出現(xiàn)讀者收集“考古手記”登囤請(qǐng)教的插曲。
國內(nèi)外近百家媒體通過報(bào)刊對(duì)海龍屯的考古發(fā)掘進(jìn)行了報(bào)道;海龍屯聲名鵲起,成為國內(nèi)外考古界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
而基于考古發(fā)現(xiàn)的專題學(xué)術(shù)講座,實(shí)現(xiàn)了另一個(gè)渠道的傳播與互動(dòng)。第一期發(fā)掘過程中及發(fā)掘結(jié)束以后,我們?cè)诤}埗凇⒆窳x、北京和貴陽舉行了多場(chǎng)面對(duì)不同聽者的學(xué)術(shù)演講,廣受好評(píng)。如9月22日,應(yīng)遵義“名城大講壇”之邀,在遵義市圖書館舉行《海龍囤:兩千里疆土家與國》的專題學(xué)術(shù)講演,數(shù)百名聽眾出席。10月16日,在“中國海龍囤·婁山關(guān)國際戶外挑戰(zhàn)賽”舉行期間,在海龍囤巔向來自澳大利亞、新西蘭、臺(tái)灣、香港、北京等地的約200名運(yùn)動(dòng)員、教練員講述海龍囤故事。2013年1月9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學(xué)論壇——2012年中國考古新發(fā)現(xiàn)”頒獎(jiǎng)儀式上發(fā)表《貴州遵義海龍囤遺址2012年度發(fā)掘》的學(xué)術(shù)講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龍囤遺址榮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后,走進(jìn)社區(qū)、走進(jìn)校園,與社區(qū)居民和大中學(xué)生進(jìn)行交流與互動(dòng),受到普遍歡迎。
所有“公眾”中,當(dāng)?shù)卮迕駸o疑是與遺產(chǎn)地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利益相關(guān)者,他們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動(dòng)中得以體現(xiàn)?相當(dāng)部分當(dāng)?shù)卮迕裨诳脊殴さ刈龉ぃ谠黾邮杖氲耐瑫r(shí)也完成了與海龍囤事實(shí)上的“親密接觸”。部分村民則長期在海龍囤從事牽馬、導(dǎo)游、餐飲等旅游服務(wù),考古工作開展后劇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們的經(jīng)濟(jì)收入。這些都是考古活動(dòng)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此外,發(fā)掘期間,針對(duì)當(dāng)?shù)卮迕竦呢毨顩r,我們聯(lián)合媒體通過微博發(fā)起“考古探秘+公益慈善”活動(dòng),使城市中人在進(jìn)行海龍囤考古探秘的精神之旅的同時(shí),也能對(duì)當(dāng)?shù)刎毨Т迕裼枰跃柚_@一活動(dòng)被新華社等媒體譽(yù)為“走出文化扶貧新路”,予以高度評(píng)價(jià)。更有當(dāng)?shù)卮迕駥懺妭鲹P(yáng)此舉,稱“楊雀記得千年樹,乞丐記得賢惠人”。我們相信,當(dāng)?shù)卣畷?huì)充分考慮村民的利益訴求,未來海龍囤“申遺”一旦成功,他們的生活條件將會(huì)得到進(jìn)一步改善。
三
貴州具有影響力的公眾考古實(shí)踐始于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樂:2000年發(fā)掘報(bào)告》。為便于普通讀者的閱讀,該書在傳統(tǒng)考古報(bào)告里開設(shè)了一些小窗口,用通俗的語言來描述相關(guān)章節(jié)的內(nèi)容,即在“考古方言”里穿插了“普通話”的環(huán)節(jié),使其曉暢易讀。這一嘗試引發(fā)了圈內(nèi)圈外的廣泛討論,先后有約10篇書評(píng)公開發(fā)表。貴州省文物局從2011年開始策劃的“貴州文化遺產(chǎn)叢書·考古貴州系列”,計(jì)劃推出解普及性讀物8本,將貴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眾能夠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學(xué)化的筆觸來表述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成果,從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產(chǎn)生更為廣泛的影響。叢書目前已完成撰稿工作,預(yù)計(jì)2014年初能推出部分成果。這兩項(xiàng)實(shí)踐,應(yīng)屬“考古科普”的范疇,無疑也是公眾考古的一個(gè)有機(jī)組成部分。
而以考古現(xiàn)場(chǎng)為依托,開展深度的、廣泛的公眾考古活動(dòng),海龍囤開貴州先河。基于海龍囤的公眾考古實(shí)踐,在面對(duì)面或通過媒體與大眾的互動(dòng)中回應(yīng)了社會(huì)的關(guān)切,盡可能調(diào)適了各方利益,對(du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有著正面的、積極的意義;同時(shí)強(qiáng)化了考古學(xué)科存在的價(jià)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會(huì)效應(yīng)。
考古學(xué)的分支范文5
音樂考古學(xué)與音樂圖像學(xué)的關(guān)系,目前在學(xué)界認(rèn)識(shí)尚不一致。有學(xué)者認(rèn)為音樂圖像學(xué)是音樂考古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因?yàn)閳D像,作為音樂圖像學(xué)所研究的對(duì)象,都是古代的遺跡而非現(xiàn)代作品。對(duì)這些古代遺跡進(jìn)行研究自然也就屬于音樂考古學(xué)的一支了。也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音樂圖像學(xué)不像音樂考古學(xué)的對(duì)象那樣龐雜,有自己專門的研究對(duì)象,也有相對(duì)獨(dú)立的研究方法,所以應(yīng)該自成一個(gè)學(xué)科。
學(xué)術(shù)界類似的爭(zhēng)論并不少見,但多數(shù)情況下是一邊爭(zhēng)論,一邊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并不會(huì)對(duì)各自的發(fā)展有太大影響。雖然如此,學(xué)科的定位也還是要講的。因?yàn)楦闱宄W(xué)科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使研究者的工作更加自覺和清醒。筆者的觀點(diǎn)是,就像音樂考古學(xué)是考古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一樣,音樂圖像學(xué)也應(yīng)是音樂考古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其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比較清楚的:音樂考古學(xué)與大考古學(xué)之間,對(duì)象和方法都有特殊性;音樂圖像學(xué)和音樂考古學(xué)直接的關(guān)系也是如此。而且,在以往的音樂考古工作中,也包括了大量的圖像研究。
音樂圖像學(xué)在我國目前尚不發(fā)達(dá),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對(duì)器物的考古。所以,有些基本理論問題,需要提出來加以討論。其中,圖像的辨?zhèn)危褪且粋€(gè)值得注意的問題。本人沒有專門做過很多音樂圖像學(xué)方面的研究,但是在其他的研究中接觸過這個(gè)領(lǐng)域的問題。以下就筆者在研究嗩吶的歷史時(shí)遇到過的兩個(gè)案例,談一談圖像材料的辨?zhèn)螁栴}。
一、克孜爾天宮伎樂壁畫
第一個(gè)案例發(fā)生在1998年。那時(shí)我正在寫博士論文《中國嗩吶音樂研究》,其中一部分內(nèi)容是考證嗩吶的來路以及傳人中國的時(shí)間。當(dāng)時(shí)接觸到的最早的材料是新疆克孜爾石窟第38窟壁畫中的兩支“嗩吶”。這個(gè)窟被稱為音樂窟,因?yàn)楸诋嫷闹饕獌?nèi)容是天宮伎樂。在室內(nèi)左右兩壁上,各有14個(gè)奏樂天人,兩兩成對(duì),表演著“二重奏”。其中右壁第六對(duì)(圖見封三)和左壁第六對(duì),是同樣的畫面:兩個(gè)奏樂天人—個(gè)操琵琶,—個(gè)吹嗩吶。
該窟建于公元4世紀(jì),大約在十六國時(shí)期。在發(fā)現(xiàn)這個(gè)材料之前,最早的嗩吶圖像出現(xiàn)在明代,最早的文字記載即明徐渭《南詞敘錄》中所提到的“至于喇叭、嗩吶之流,并其器皆金、無遺物矣”。這些材料與克孜爾的壁畫相距一千年左右。根據(jù)徐渭的記述,人們通常認(rèn)為嗩吶在元代才在中國出現(xiàn)。
一般認(rèn)為,考古所得的實(shí)物比文獻(xiàn)更具有可信度,且往往可填補(bǔ)文字記載的空白。例如,大量先秦編鐘的出土,證明了一鐘雙音的技術(shù)確曾存在于先秦并且十分成熟,而這些在文獻(xiàn)上是沒有記載的。但是,壁畫與出自地下的器物有所不同。地下文物出土前不見天日,人們接觸不到,因而沒有機(jī)會(huì)改變它的樣貌。即或會(huì)有被盜后再現(xiàn)于世的情況,但作偽的情況絕對(duì)少見。因?yàn)楸I墓是為了出手倒賣,如果作假反倒弄巧成拙。壁畫就大不相同。不管是在寺廟還是在石窟,壁畫都要暴露在各色人物面前,人們會(huì)有很多機(jī)會(huì)接觸到它,所以就有改變它的可能性。特別是有的洞窟曾長期無人管理,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了。
那么,第38窟的這幅壁畫反映的信息可靠嗎?某些學(xué)者已經(jīng)在著作中肯定這就是嗩吶。如果嗩吶真的在4世紀(jì)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中國,那么在從4世紀(jì)到徐渭之間的千年時(shí)間里,文獻(xiàn)中和其他地方的壁畫中會(huì)找不到一點(diǎn)蛛絲馬跡嗎?
早在筆者注意到這幅壁畫之前,在克孜爾研究院工作的老專家霍旭初先生已經(jīng)對(duì)此壁畫產(chǎn)生了懷疑。他在近距離觀察這幅壁畫時(shí),發(fā)現(xiàn)嗩吶桿和下端的喇叭口顏色有所區(qū)別;從自己所掌握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中,找不到與嗩吶有關(guān)的記載;附近其他洞窟壁畫中的同類樂器,也都沒有喇叭口。(見封三相關(guān)圖片)由于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的師生曾來石窟臨摹,他也曾向帶隊(duì)老師調(diào)查有沒有人涂改過壁畫,但回答是否定的。盡管暫時(shí)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jù),霍先生還是憑借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否定了這件樂器是嗩吶。他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新疆卷》中這樣說:“在龜茲石窟中,只在38窟伎樂中出現(xiàn)此形制的樂器,應(yīng)為篳篥之類。”《中國音樂史圖鑒》也收錄了這幅壁畫,但采取了審慎的態(tài)度:“如果克孜爾石窟后來沒有更新過,此圖像說明嗩吶早在公元三、四世紀(jì)已流行于新疆地區(qū)。”
但是,這些畢竟都是憑借經(jīng)驗(yàn)做出的推斷,而不是根據(jù)證據(jù)做出的定論。所以,霍先生用了“應(yīng)為”一詞,《圖鑒》用了“如果”一詞,為自己留出了余地。如果有了證據(jù),這些推斷便可轉(zhuǎn)化為定論。
柳暗花明的時(shí)刻來了。正在霍先生苦尋證據(jù)之時(shí),德國同行送來了“及時(shí)雨”。原來在20世紀(jì)初,德國的考察隊(duì)曾來到克孜爾石窟。他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并為洞窟編了號(hào)。此外,他們還為某些洞窟中的壁畫拍了照,最后又剝走了一些壁畫。1998年,德國客人重訪克孜爾,帶來了他們的前輩們拍攝的照片(見封三,左壁暫未找出),其中就有38窟中的這幅琵琶和“嗩吶”的重奏。
真是大喜過望。原來,這支所謂“嗩吶”的原貌是沒有喇叭口的,當(dāng)屬篳篥無疑。至于這個(gè)喇叭口的來歷,當(dāng)不難推斷。肯定是有人來洞窟臨摹壁畫,陡升好事之心,畫筆一揮,一支篳篥就變成了嗩吶。也恰在這個(gè)時(shí)候,我通過周吉先生的介紹,與霍先生取得了聯(lián)系,和他分享了這一信息,順利地把我的文章繼續(xù)下去。霍先生后來也專門撰文說明了這幅壁畫“變臉”的過程。
二、濟(jì)南石棺
后來,我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中又看到了一個(gè)石棺,名曰“靈魂升天圖石棺”(見封三)。據(jù)書中介紹,這是一件宋代的石棺。石棺兩側(cè)的浮雕,都是超度亡靈的僧人樂隊(duì)。樂隊(duì)中的嗩吶十分清楚,還有云鑼、笙、鼓等。
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個(gè)宋代嗩吶的證據(jù)。因?yàn)槲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找到唐代嗩吶的證據(jù),如果宋代再有,不但可以和后面的元代連接起來,而且還可以說明在宋代的山東地區(qū),僧人的樂隊(duì)是使用嗩吶的,這種現(xiàn)象并不多見。
這件石棺藏在濟(jì)南博物館。我專程趕到那里,仔細(xì)了解了這個(gè)石棺的情況。石棺很小,像常見的瓷枕頭那樣大。博物館的學(xué)者告訴我,這是一件從民間收集來的藏品,準(zhǔn)確年代并不明了。根據(jù)民俗學(xué)家對(duì)喪葬風(fēng)俗的研究,他們認(rèn)為宋代可能使用過這種石棺,所以就將年代定為宋代。也就是說,這并不是一個(gè)確定的年代。這個(gè)石棺本身以及上面的圖像的真實(shí)性沒有問題,問題在于無法準(zhǔn)確斷代。它是個(gè)孤證,在附近以及更遠(yuǎn)的地方都沒有相近的實(shí)物可以參照。它又不是動(dòng)植物,不能使用碳14方法測(cè)其年代。又是一樁無頭案。
考古學(xué)的分支范文6
關(guān)鍵詞:中國古代音樂史;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文獻(xiàn)學(xué);音樂考古學(xué);史學(xué)史
中圖分類號(hào):J609.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國深受儒術(shù)思想的影響,漢代甚至獨(dú)尊儒術(shù),而儒家思想的音樂觀又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為追求,這種將音樂與政治高度結(jié)合的音樂觀成為了中國歷朝的音樂思想傳統(tǒng),史家治史往往將“樂”作為“政”的一部分記錄在正史之中。同時(shí),在歷代野史、筆記雜談、傳奇小說中,也有汗牛充棟的音樂史料。但我國近代具有科學(xué)意義的音樂史學(xué)研究卻出現(xiàn)較晚,從20世紀(jì)20年代起才出現(xiàn)了中國音樂史學(xué)的萌芽,代表作是葉伯和、朱謙之、鄭覲文、王光祈等人的專著。及至20世紀(jì)40年代末,以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為代表,古代音樂史的研究已成為音樂學(xué)領(lǐng)域的一個(gè)重要分支。當(dāng)代學(xué)界,古代音樂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出現(xiàn)了百花齊放的景象。本文通過對(duì)中國古代音樂史學(xué)現(xiàn)狀的粗略梳理,在史學(xué)史發(fā)展、當(dāng)前的研究特點(diǎn)、學(xué)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點(diǎn)思考。
一、中國古代音樂史學(xué)史發(fā)展歷程管窺
20世紀(jì)20年代是中國音樂史學(xué)的發(fā)源期,出現(xiàn)的論著主要有:葉伯和《中國音樂史》(1922年)、朱謙之《音樂的文學(xué)小史》(1925年)、童斐《中樂尋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1926年)、鄭覲文《中國音樂史》(1929年)等。這些音樂史類著作的出版,標(biāo)志著中國音樂史學(xué)萌芽的同時(shí)也提出了一個(gè)新的音樂歷史觀念:“音樂史是供給人類精神生活的需要,與衣食住為供給人類物質(zhì)生活的需要是一樣的,所以編寫音樂史,第一項(xiàng)是要注意一個(gè)時(shí)代人文的發(fā)展,第二項(xiàng)才是考證歷代作品的成績(jī)。”①不同時(shí)代的新思維學(xué)者們不斷地想擺脫研究歷史的傳統(tǒng)觀念束縛,提倡用科學(xué)的、新型的、哲學(xué)的眼光來審視和觀察,擯棄舊觀念推進(jìn)新理論,呈現(xiàn)出時(shí)代性強(qiáng)的音樂史發(fā)展觀。諸多先行者意識(shí)到音樂史學(xué)學(xué)科的獨(dú)立性,無疑具有非凡意義,但是,建立一門獨(dú)立的學(xué)科談何容易。音樂史學(xué)如果要從一般的歷史學(xué)中獨(dú)立出來,首先只能從現(xiàn)存的浩如煙海的史籍入手而別無他法;而對(duì)歷史資料的鑒別、整理、審定,使音樂史學(xué)的先輩們只能采取考校、匯集等一系列傳統(tǒng)研究歷史的方式方法。
我們從許之衡、王光祈、繆天瑞等人的音樂史著作可以看出,他們明顯不滿于傳統(tǒng)治學(xué)史觀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國音樂史·自序》中講到:“吾國歷史一學(xué),向來比較其他各學(xué)發(fā)達(dá),但在事實(shí)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xué)家’(如司馬遷之流仍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掛帳式’的史書,而無‘談進(jìn)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圖用進(jìn)化論思想貫穿于自己的著作,為后學(xué)開啟一種全新的治學(xué)思維。建國后,以楊蔭瀏、廖輔叔、李純一等為代表的研究隊(duì)伍,為中國音樂史學(xué)發(fā)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豐富了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成果。在音樂史學(xué)觀念上產(chǎn)生了一次變革,引導(dǎo)著研究者們轉(zhuǎn)向從現(xiàn)實(shí)的民間音樂實(shí)體來充實(shí)史學(xué)本身,努力使音樂史成為真正的音樂的歷史,而不是在一般書籍里的音樂文學(xué)史。基于此,音樂史學(xué)學(xué)者們開始意識(shí)到一個(gè)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學(xué)者深入到考古學(xué)的領(lǐng)域,以出土的文物來驗(yàn)證史籍中關(guān)于音樂方面的記述,用考古學(xué)的新發(fā)現(xiàn)來不斷補(bǔ)充史料記載的不足。經(jīng)過這些學(xué)者的不斷努力,音樂史學(xué)又有了新的進(jìn)展,逐漸開始充實(shí)起來并走上了獨(dú)立學(xué)科的發(fā)展道路。
音樂史學(xué)真正作為一門系統(tǒng)的、科學(xué)意義上的學(xué)科,是在“”之后。研究隊(duì)伍不斷擴(kuò)大,一批論文與專著的發(fā)表和出版,若干專題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的舉行,促使對(duì)中國音樂史探討與商榷的爭(zhēng)鳴,更使音樂史學(xué)界呈現(xiàn)出生機(jī)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樂學(xué)概念被提高到應(yīng)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從而在基礎(chǔ)上大大加強(qiáng)了音樂史學(xué)的研究。這一時(shí)期,研究者們開始向音樂史學(xué)的深層挖掘,努力在音樂史實(shí)之間、史實(shí)與當(dāng)今存留的樂聲之間尋找必然的聯(lián)系。同時(shí)注意到音樂形態(tài)的流動(dòng)性,從而論及到中外音樂史、各民族之間的音樂流變關(guān)系,“中外音樂交流”等專題得到廣泛討論。這些積極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樂史學(xué)工作者的歷史觀念達(dá)到了新高度,使中國音樂史學(xué)逐步發(fā)展成為科學(xué)的音樂歷史學(xué)。
二、對(duì)當(dāng)下史學(xué)研究方法的思考
從宏觀角度來分析,中國音樂史研究到現(xiàn)今為止經(jīng)歷了以下幾種史學(xué)觀念與方法的演進(jìn):
(一)上世紀(jì)40年代之前,中國音樂史學(xué)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從古代文獻(xiàn)里尋找痕跡進(jìn)行考據(jù)論證。如乾嘉學(xué)派通過訓(xùn)詁、校勘、注釋、輯佚、辨?zhèn)蔚确绞剑砹藘汕Ф嗄暌詠淼姆饨ㄎ幕浼婕敖鹗⒖脊拧⒔?jīng)學(xué)、小學(xué)等各學(xué)術(shù)方面,以及叢書、類書等的研究編撰等方面,給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近代國學(xué)宗師梁?jiǎn)⒊⑼鯂S、陳垣、陳寅恪深受影響,對(duì)史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的全新構(gòu)建,如梁?jiǎn)⒊摹敖穼W(xué)新構(gòu)想”、王國維的“二重證據(jù)法”、陳垣的“史源學(xué)”、陳寅恪的“史詩互證”等等。這些真知灼見的全新理論模式使傳統(tǒng)治史方式獲得深入的發(fā)展,對(duì)推進(jìn)音樂史學(xué)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導(dǎo)。
(二)20世紀(jì)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duì)音樂文獻(xiàn)結(jié)合民間音樂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視,如楊蔭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個(gè)案調(diào)查”“地區(qū)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將民間早已存在的傳統(tǒng)與歷史文化結(jié)合起來進(jìn)行考察,使用錄音技術(shù)搶救遺存的聲音,建立民間樂器展覽,迄今為止,這仍被視為最先進(jìn)的考察方法。這種方式搶救性地記錄下一系列不為世人重視的音樂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他們所記錄的這一時(shí)期的原生態(tài)藝術(shù)及其所處的社會(huì)氛圍還尚未遭到外來強(qiáng)勢(shì)文化的破壞。如上世紀(jì)50年代,楊蔭瀏、曹安和赴無錫采訪“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藝人,發(fā)掘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出版《蘇南吹打曲》等等。這一系列的調(diào)查把中國器樂史的當(dāng)下活態(tài)狀況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幾乎把所有錄音演奏記錄成譜。這些成果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中國建立了一整套20世紀(jì)后半期以來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三)20世紀(jì)80~90年代,對(duì)音樂史進(jìn)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樂學(xué)、音樂文獻(xiàn)學(xué)、音樂考古學(xué)、音樂圖像學(xué)等學(xué)科資源相互結(jié)合、滲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熱潮,黃翔鵬先生提出了“音樂形態(tài)學(xué)”這個(gè)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階級(jí)等政治觀念劃分中國音樂史的慣例,創(chuàng)造性地依照中國音樂史發(fā)展形態(tài)的嬗變過程,將之劃分為“先秦樂舞時(shí)代”“中古伎樂時(shí)代”和“劇曲音樂時(shí)代”三個(gè)階段,充分考慮到了音樂文化內(nèi)涵及其性質(zhì),音樂自身要素、風(fēng)格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特征,著眼于社會(huì)的變遷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樂分期更為趨于合理。音樂史學(xué)在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多學(xué)科視角理念的增強(qiáng)導(dǎo)致了對(duì)學(xué)科發(fā)展的重新審視,特別是考古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地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民族學(xué)、民俗學(xué)等學(xué)科對(duì)中國音樂史學(xué)的發(fā)展貢獻(xiàn)巨大。
以上三種研究方式,形成了當(dāng)下中國音樂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yàn)闅v代各種史籍中大量的音樂史料記載并不能等于音樂史學(xué);況且有些記載又是極其模糊、不明確,甚至是謬誤的。隨著近代以來大量考古出土的實(shí)物史料來看,我們對(duì)古代社會(huì)各個(gè)方面、各個(gè)層面的認(rèn)識(shí)在不斷地超越著前人,所以傳統(tǒng)音樂史學(xué)的史料結(jié)構(gòu)在不斷地發(fā)生著改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孕育出了一個(gè)立體的史料系統(tǒng),只是建立在音樂文獻(xiàn)史料基礎(chǔ)上的傳統(tǒng)音樂史學(xué)已明顯不能適應(yīng)新形勢(shì)下的研究需要了。與此同時(shí),我們還需要清楚地意識(shí)到,雖然一部全新的中國音樂史可以被考古學(xué)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證構(gòu)建,但還遠(yuǎn)不足以填補(bǔ)漫長歷史的空白,歷史的真實(shí)面貌只能不斷地去接近它,而永遠(yuǎn)不能達(dá)到它。不同學(xué)科領(lǐng)域,多層次、多角度進(jìn)行綜合論證,方能得出比較接近事實(shí)的結(jié)論,這是一個(gè)“創(chuàng)史”“補(bǔ)史”“正史”“證史”的過程。
三、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筆者認(rèn)為,只是建立在文獻(xiàn)史料上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史學(xué)有居多明顯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彎路,具體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國用來記錄歷史文獻(xiàn)的載體在東漢造紙術(shù)發(fā)明之前的西漢和先秦時(shí)期,都用絹帛、竹簡(jiǎn)、木牘、龜甲、動(dòng)物骨片等(石刻、鐘磬、器皿銘文除外),極易受周邊環(huán)境中濕度、溫度、酸堿度、氣壓和風(fēng)化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東漢造紙術(shù)、隋唐雕版印刷術(shù)、北宋活字印刷術(shù)等新技術(shù)手段的出現(xiàn),仍然難以實(shí)現(xiàn)歷史文獻(xiàn)在自然無干擾狀態(tài)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紙草記錄載體以及古巴比倫的泥版、石版紀(jì)事。埃及、巴比倫屬熱帶沙漠氣候,干燥炎熱,因此為紙草、泥版等載體在地下或廢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年以上提供了條件。
(二)文字的記載并不能反映出歷史的全貌。與中國久遠(yuǎn)人類歷史相比,文字的出現(xiàn)僅為短短的數(shù)千年,即使是從中國較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過三千多年,之前并沒有任何文獻(xiàn)可查。人類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只是一部分,而書籍能在漫長歷史過程中存留下來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文獻(xiàn)的積聚和傳承經(jīng)歷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書坑儒”,當(dāng)時(shí)究竟焚毀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說,但僅從曾侯乙編鐘上的銘文內(nèi)容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時(shí)至今日,我們對(duì)于先秦樂律理論的了解也實(shí)屬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實(shí)性還存在疑問。
(三)人的社會(huì)屬性決定了人類中個(gè)體,不管是哪個(gè)階層的人,都要受到當(dāng)時(shí)所處社會(huì)的制約。歷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當(dāng)政者所左右的狀況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經(jīng)常遇見的。我們可以看出,在撰寫歷史的文人中,既懂樂律理論,又有音樂實(shí)踐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我們知道,所謂的正史所記載的音樂內(nèi)容主要是服務(wù)于宮廷的,而關(guān)于廣大社會(huì)下層音樂生活的內(nèi)容不多。我們姑且想象假若這些史官“他們對(duì)音樂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樂的人居多”,在這些正史中,被這些文人記錄下來的音樂文字,扭曲當(dāng)時(shí)音樂本貌的情況就不難得知了。中國古代音樂的發(fā)展從未斷裂,即使改朝換代,宮廷音樂形態(tài)轉(zhuǎn)型為民間音樂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發(fā)展,古代文人們通過到民間尋訪前代散失的宮廷樂工,就會(huì)將斷裂的音樂歷史重續(xù),楊蔭瀏先生對(duì)于智化寺“京音樂”的調(diào)查就是這種再續(xù)前弦的舉動(dòng)。以往過度關(guān)注王侯將相等貴族化的音樂、宮廷生活相關(guān)的內(nèi)容以及上層政治綱領(lǐng)相符合的內(nèi)容,從而忽略了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宗教音樂、民間俗樂、地方歌舞戲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生活史,對(duì)于原生態(tài)民歌為代表的音樂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研究正好可以彌補(bǔ)此方面的空白,展現(xiàn)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關(guān)的音樂風(fēng)格,勾畫出濃郁鄉(xiāng)土氣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很關(guān)注事物與時(shí)間的關(guān)系,歷史學(xué)更是傾向于時(shí)間分期,20世紀(jì)中葉起,“法國年鑒學(xué)派”給史學(xué)研究帶來啟示:發(fā)現(xiàn)了政治史以外的社會(huì)史與生活史;發(fā)現(xiàn)了歷史學(xué)的“時(shí)間”特質(zhì),“長時(shí)段”概念被引入史學(xué)研究方法之中,時(shí)間是一種序列,它的綿延帶來諸多變化。目前中國音樂史分期大致有三種: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樂分期來講,政治變遷無法一夜之間使音樂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社會(huì)突變之初,音樂大致仍會(huì)沿著以往的規(guī)律的慣性向前發(fā)展,然后再依據(jù)外部影響的大小而逐漸嬗變。從音樂文化的內(nèi)部,找尋音樂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進(jìn)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對(duì)于音樂史實(shí)的認(rèn)定,西方音樂史更為側(cè)重樂譜的音樂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而中國音樂史更側(cè)重于文化要素。
四、對(duì)學(xué)科發(fā)展的憧憬與展望
當(dāng)前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越來越細(xì)化,許多研究從總的音樂史研究領(lǐng)域中日益凸顯,逐漸形成了相對(duì)獨(dú)立的分支學(xué)科,如樂律學(xué)、音樂考古學(xué)、琴學(xué)、古譜學(xué)等。中國古代音樂史學(xué)研究方法呈現(xiàn)出多樣性的特點(diǎn),這就要求學(xué)者既要加強(qiáng)史學(xué)文獻(xiàn)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學(xué)”(整體史、生活史、社會(huì)史等)的視角,力求展開豐富的音樂歷史的各個(gè)層面。新史學(xué)的一個(gè)關(guān)注熱點(diǎn)是“社會(huì)生活”,從社會(huì)史角度將社會(huì)不同現(xiàn)象納入到音樂史學(xué)研究中來,如制度中的音樂、生活中的音樂、音樂如何建構(gòu)生活、都市生活與市民音樂等等。這一方面在近年來也是成果顯赫,比如“樂戶”研究,從制度到樂制、樂戶、樂籍等等音樂現(xiàn)象予以考察,力求展開豐富的音樂歷史各層面。
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當(dāng)今這個(gè)知識(shí)爆炸的信息時(shí)代,考古史料的信息來源十分豐富,考古學(xué)史料與文獻(xiàn)史料并駕齊驅(qū),成為當(dāng)前中國古代音樂史學(xué)發(fā)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領(lǐng)域。時(shí)至21世紀(jì)的今日,在全球一體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方面逐漸寬松的背景下,人們對(duì)歷史的認(rèn)識(shí)不斷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課題不斷涌現(xiàn),盡管如此,文獻(xiàn)史料仍然是當(dāng)今中國音樂史學(xué)研究的側(cè)重點(diǎn),隨著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進(jìn)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現(xiàn),從基礎(chǔ)上動(dòng)搖和改變了傳統(tǒng)音樂史學(xué)的史料結(jié)構(gòu),從而確立起一個(gè)全新的文獻(xiàn)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輔相成的史料系統(tǒng)。在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家響亮倡導(dǎo)文化強(qiáng)國的新形勢(shì)下,作為文化強(qiáng)國戰(zhàn)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熱切期盼能有反映時(shí)代特征的、權(quán)威的“中國音樂通史”,這將是我們這些從事研究中國音樂史學(xué)學(xué)者的夙愿!
注釋:
①鄭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話中國古代音樂史學(xué)的現(xiàn)狀》,《音樂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紀(jì)以來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xué)研究》,《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年第2期。
參考文獻(xiàn):
[1]劉再生.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yuǎn)近高低各不同——20世紀(jì)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J].中國音樂學(xué),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