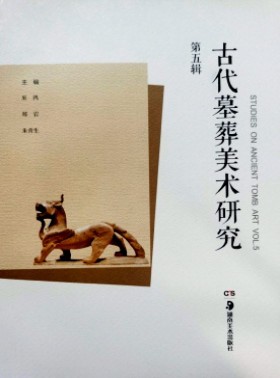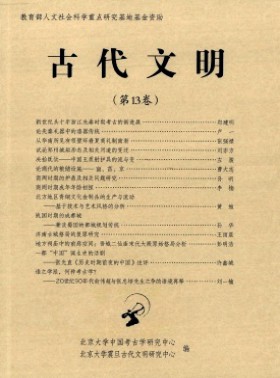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wǎng)精心挑選了古代文明發(fā)展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fā)你的文章創(chuàng)作靈感,歡迎閱讀。

古代文明發(fā)展范文1
關(guān)鍵詞:淺談 中國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圖分類號: C93 文獻標識碼: A
“文明”相對“野蠻”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對“野蠻”的揚棄。“國家”或“文明社會”是歷史前進的結(jié)果,因為“國家”作為社會機器,維持、促進了社會發(fā)展和進步,扼制了“野蠻”對社會發(fā)展的破壞。目前學術(shù)界對“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志一般歸納為城市、文字、青銅器、禮器、王陵等等。對這個標志的個案分析和綜合研究,是探討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鑒于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沒有歷史文獻留傳下來,這項研究所需資料只能依靠考古學解決。考古學對上述文明形成諸多標志的基礎(chǔ)資料界定、取得、分析、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不一,難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學性各異。
“文字”對于“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當前關(guān)于“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并不統(tǒng)一,“符號”成為“文字”的質(zhì)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志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yōu)槲淖趾蛷摹耙靶U”變?yōu)椤拔拿鳌保鼈儾豢赡茉谕弧皶r空”臨界點發(fā)生“突變”、“質(zhì)變”的。它們的“質(zhì)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chǎn)技術(shù)發(fā)展的產(chǎn)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xiàn)在人類生產(chǎn)活動中發(fā)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jīng)濟領(lǐng)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chǎn)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xiàn)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guān)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chǎn)物,祭祀用品的產(chǎn)生要早于國家出現(xiàn)。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fā)展,假以時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chǔ)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xiàn)“國家”。關(guān)于“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一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于“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一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志,最易操作的學術(shù)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tǒng)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xiàn)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筑城以衛(wèi)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diào)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xiàn)在各地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于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目前,關(guān)于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標志的“城”,也存在著科學界定的問題。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礎(chǔ)工作。這里我講“城”不講“城市”,就是區(qū)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業(yè)功能,因此城中有相當數(shù)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眾”,這種“城”實際是一部“國家機器”。當前在有關(guān)“城”的考古學研究中,更應注意區(qū)別“城”、“城堡”和“村寨”。它們都在其周圍筑有“墻”,這種墻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規(guī)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墻”是“衛(wèi)君”的,即保護國家集團的;“城堡”之墻是用于軍事防御的,它們可以是“國家”的軍事設施,也可以作為“野蠻社會”軍事?lián)c;“村寨”之墻是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以城墻作為“城”的唯一或主要標志。如何區(qū)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僅據(jù)其占地面積大小、墻垣規(guī)模等,更重要的應剖析其空間范圍的內(nèi)容。“城”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統(tǒng)治集團的政治中樞,主要應是城中“國家機器”物化載體――宮廟建筑。“城堡”之內(nèi)主要為軍事設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說明各自的社會作用。因此,對有墻垣圍繞的大面積建筑遺址,究明其內(nèi)涵十分必要。這些恰恰是我們目前考古工作中應該更多予以關(guān)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現(xiàn)的城之宮廟是什么樣子,現(xiàn)在我們還不清楚,但可以通過對已知資料的了解、已知規(guī)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對目前尚存的明清時代的宮殿、宮廟我們可以考察。對唐宋、秦漢時代的宮廟遺址,通過考古發(fā)掘、結(jié)合歷史文獻記載,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經(jīng)考古發(fā)掘的商周宮廟遺址,夏代偃題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二號宮殿建筑遺址,又為我們認識更早以前的“文明社會”城址中的宮廟遺址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參照物”。
關(guān)于“宮”和“廟”的界定要有嚴格的學術(shù)標準。我認為中國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廟是“宗廟”,而不是“神廟”。中國古代文明與地中海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羅馬古代文明重要的區(qū)別是,前者以“宗廟”為主體。后者以“神廟”為主體。造成這種結(jié)果的原因是前者社會以農(nóng)業(yè)為主要產(chǎn)業(yè),以血緣政治為主;后者商、工、農(nóng)多種產(chǎn)業(yè)并存,以地緣政治為主。因此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廟時,對此應給以加倍重視。
中國“文明形成”時期的宮殿與史前時期的“公共建筑”有著本質(zhì)不同。從布局形制上說,前者是封閉的,后者是開放的;從結(jié)構(gòu)上看,前者是強調(diào)等級、突出個人的;后者是面向“大眾”的。如時代較早的偃師商城的宮殿遺址,其周圍筑有“宮城”,每座宮殿或幾座宮殿還要有單獨的圍墻;屬于夏代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一、第二號宮殿遺址各自圍筑有單獨的院墻。
古代文明發(fā)展范文2
早在9000年前,兩河流域地區(qū)就已經(jīng)有了農(nóng)業(yè)。由于兩河流域地勢是北高南低,南部更有河水灌溉農(nóng)田之便。但早期人類尚無抗御洪水威脅的能力,因而最早的“天然農(nóng)業(yè)”開始于北部山地。大約6000年前,隨著農(nóng)業(yè)逐步向南轉(zhuǎn)移及灌溉農(nóng)業(yè)的興起,在南部河谷地帶才逐步開創(chuàng)了最早的人類文明。
創(chuàng)兩河流域文明之先的是蘇美爾人。蘇美爾人是外來居民。他們大約在公元前4500年到達兩河流域南部地區(qū)。在蘇美爾文明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農(nóng)書和農(nóng)具,有人類最早的文字、歷史書寫記錄和文學作品,還有歷史上最古老的學校。蘇美爾文明時期的烏魯克城,還是兩河流域乃至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城市,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它曾在兩河流域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扮演過宗教、政治和經(jīng)濟中心的重要角色。古人的生活極度依靠水源,古代烏魯克就位于幼發(fā)拉底河岸邊。由于河流數(shù)次遷徙、改道,烏魯克城逐步衰落,最后終被淹沒在黃沙之中。現(xiàn)在的烏魯克遺址距幼發(fā)拉底河已有12英里距離。
世界歷史上最主要的文明發(fā)源地幾乎都靠近河流。但是,像幼發(fā)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樣,兩條河流如此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卻是絕無僅有的。幼發(fā)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像一對親密的兄弟,相互扶持著見證了這個地區(qū)7000多年的風云變幻。只是古代兩河流域人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國及早期人類一樣,對河流的認識有一個從恐懼逃遁到親近依附進而開發(fā)利用的過程,也正是這一過程促進了古代文明的發(fā)展。最早來到兩河流域創(chuàng)造文明的蘇美爾人,對洪水泛濫的恐懼不僅僅是洪泛的周期性,還有它的不可預見性。他們常常唉嘆:“猖獗的洪水呀,沒人能和它對抗,它使蒼天動搖,使大地顫抖……”兩河流域人的人生觀帶有恐懼和悲觀的色彩,就反映了自然環(huán)境的不安全。在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中,關(guān)于水的話題層出不窮,著名的《吉爾伽美什史詩》里,講述的諾亞方舟的故事,說的就是烏特?那皮什圖如何在神的旨意下在洪水泛濫的一片中,獲得了永生的權(quán)利。這說明,早期兩河流域人面對滔滔的洪水,想象逃生的辦法只能仰賴于“神”了。
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先后歷經(jīng)數(shù)個王朝時期的統(tǒng)治,為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作出過偉大的貢獻。亞述學者曾經(jīng)列舉過蘇美爾人創(chuàng)造的數(shù)十項世界第~。直到大約公元前1942年,以巴比倫城為中心,一個新的王朝――古巴比倫王朝興起,蘇美爾文明才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并最終深埋地下,蘇美爾人和蘇美爾文化也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載入史冊。
從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早的蘇美爾城邦國家誕生起,兩河流域經(jīng)歷了一次次的移民浪潮,歷史上曾經(jīng)有數(shù)個民族在這個地區(qū)停留、生活、爭霸,并建立國家。蘇美爾文明、阿卡德王國、烏爾第三王朝、古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更興迭起,在不斷的歷史變換和交替中書寫著最早的人類文明,演繹著戰(zhàn)爭、和平,再戰(zhàn)爭、再和平的起起落落的歷史活劇。
古代文明發(fā)展范文3
可以說沒有漢字也就不會有中國輝煌的古代文明,從某種意義上說,探討文字的起源,就是探究中國古代文明的緣起。從本期開始,讓著名語言學家李樂毅老師引導同學們一起走進漢字的神奇天地,走進中國淵博的古代文化。
“礻”是“示”用于左偏旁時的變體。“示”原是祭祀用的石制供桌,音qí,同“祗”;后來與“示”(shì)混同。“示”旁的字大都與祭祀、禱祝有關(guān)。
祝 “礻”旁不要誤寫為“衤”。音“zhù”,不要誤讀為zhū。
祀 右旁是“巳”(sì),不是“己”(jǐ)或“已”(yǐ)。音(sì)。
祈 右旁是“斤”(jīn),不是“斥”(chì)。〔對比〕與“訴”字不同。
禍 右旁是“咼”,右下角是“內(nèi)”。同一偏旁的字還有“窩”“鍋”“渦”等。〔對比〕與“禺”(以及“偶”“遇”等)“離”(以及“璃”“籬”等)“禹”(以及“屬”“囑”等)不同。
祆 古代宗教名,音xiān。“祆教”即“拜火教”。〔對比〕不要與“襖”(ǎo)字相混。
視 “ ”是聲旁,“見”是形旁。“視”不要誤解為“ ”旁。
祭 不要誤寫為“登”字頭(“登”“癸”等)。
“衤”是“衣”用于左偏旁時的變體。古代漢語把上衣叫“衣”,下衣叫“裳”。“衣”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像一件上衣。“衣”旁的字多與衣服有關(guān)。
初 從衣從刀,表示開始拿剪刀做衣服的時候,本義是“開始”。由于現(xiàn)代漢語里“初”字及其組成的詞語都似乎與“衣”無關(guān),容易把“衤”旁誤寫為“礻”。
袂 在書面語中是“袖子”的意思,音mèi。可組成“分袂”“聯(lián)袂”等詞語。不要因“快”字而誤讀為“kuài”或因“決”“缺”字而誤讀為jué,quē。
襪 右旁是“末”(mò),不是(未)(wèi)。
書面語指“單衣”,音dān。不要與“禪”(chán,shàn)相混。
褸 在“襤褸”一詞中讀lǚ。不要因“摟”而誤讀為(lǒu)。
古代文明發(fā)展范文4
【關(guān)鍵詞】中國;古代文明;世界;貢獻
印刷術(shù)讓每個中國人都有機會去學習。這些古代經(jīng)典被大量印刷,在唐朝任何一個地方都能買到。這樣,平民百姓也能參加科舉考試了,于是有了著名的中國式的成功故事,飛黃騰達。多少戲劇、小說,也都曾以此為題材。窮困的書生,日夜燈下苦讀,背誦《四書》、《五經(jīng)》,然后進京考試,后來成了總理,而不是百萬富翁。中國發(fā)明的火藥通過火器給全世界帶來了影響;中國的羅盤等為全世界航海技術(shù)的進步產(chǎn)生了巨大貢獻。中國古代文明對人類貢獻歷史,不是只有“四大發(fā)明”,以“四書”、“五經(jīng)”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于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酥會士歷經(jīng)千辛,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里曾經(jīng)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jié)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fā)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1.古典哲學。《四書五經(jīng)》對中國周邊國家如:韓國、日本、朝鮮等影響更大,這些國家都是中國文化圈的成員。啟蒙運動中,法國伏爾泰便利用了中國儒家思想,伏爾泰將儒家的哲學思想、政治理論、道德倫理、人性觀念、社會法則等加以綜合研究,建構(gòu)了一套對西方社會產(chǎn)生過很大影響的新的社會學說。明代王陽明的學說還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jù),開創(chuàng)了近代歐洲政治經(jīng)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的形成與發(fā)展,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2.科技方面。中國古代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大發(fā)明了。火藥對于粉碎西方騎士階層,建立屬于資產(chǎn)階級的政權(quán)有巨大的推動作用;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的傳入推動了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發(fā)展;指南針對于15世紀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有決定作用。除此之外,比如九章算術(shù)、圓周率對數(shù)學的貢獻;本草綱目,四診療法對醫(yī)學的完善;地動儀、日月食的觀測對天文的貢獻。。。。。。。可以說,中國古代科技對世界早期科技發(fā)展具有決定作用,中國是古代世界科技中心。中國的四大發(fā)明推動了世界的進步,近代化的開端,新航路的開辟,離不開指南針;思想解放、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離不開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而火藥又成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國的四大發(fā)明對于徹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與古代及中世紀劃分開來,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術(shù)的影響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國首先發(fā)明的。 英國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的國度》一書中動情地寫道:“中國文獻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考古證據(jù)或繪畫實物證實中國的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比歐洲的或照搬采用的發(fā)明或發(fā)現(xiàn)一般往往領(lǐng)先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是二項式系數(shù)排列,還是旋轉(zhuǎn)運動與直線運動相互轉(zhuǎn)移的方法,或是第一臺時鐘中的擒縱裝置,或韌性鑄鐵犁鏵,或植物學與土壤學的開創(chuàng),或皮膚與內(nèi)臟的關(guān)系,或天花痘苗接種的發(fā)現(xiàn)――不管你探究哪一項,中國總是一個接一個地居世界第一。”李約瑟著的長達2000萬字的《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向世界生動詳實地展示了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偉大創(chuàng)造及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與影響。
3.文化方面(狹義的)。中國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領(lǐng)先。中國的城市發(fā)展對世界也有很大影響,宋代以前,世界是許多國家學習中國的城市建造。中國中古的開放時代為世界各國培養(yǎng)了許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藝術(shù)門類內(nèi),中國的書法、國畫、詩歌獨樹一幟。中國文官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對西方文官系統(tǒng)的形成產(chǎn)生過很大的影響、推動作用。《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齋志異》、《金瓶梅》等被譯成多國文字,深深地影響著世界文壇。德國文豪歌德在比較中西文學后曾感慨地說:“當中國人已擁有小說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正在樹林里生活呢!”中國琴棋書畫對世界也有很大影響,尤其是中國文化圈內(nèi)的國家。
4.交通方面。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連接了亞歐,促進了各地的交流。四大發(fā)明除火藥是元朝軍隊帶去的其它都是經(jīng)絲綢之路傳過去的。
古代文明發(fā)展范文5
目前,中西方學者都在運用西方理論來闡釋和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在文學領(lǐng)域尤其如此。但我更想指出的是,作為研究古代中國文學的學者,我們似乎總是“接受”,卻很少“給予”。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討論中國文學,還是基于從其他文學研究里進口的理論。
“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論為導向的研究模式”
我們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論為導向的研究模式。長久以來,我們有一種固定的思維:即所有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只有西方有理論;西方理論處在上,各國的文化處在下,這 是一種不平等的狀態(tài)。
要怎么超越呢?不是超越理論本身,而是放在不同框架下運用。各地文化相互了解、連接起來找到共同和不同之處。我們承認西方理論的存在和地位,但是不應該限于它劃出的框架。我們運用它,讓它受到文化的影響,然后反過來改變它。既然這是一個全球的理論,就應該包含中國文化,不然怎么是全球的?了解彼此,才能提高,才能改進。
可以說,在宣傳中國古典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方面,我們還要多花功夫。
我見過的許多西方漢學家其實并不了解中國。我一讀他們的文章就知道,有一些觀點有失偏頗。但是現(xiàn)在中國年輕人也并不太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文明。因此,我們需要互動,共同提高。
此外,中國研究生的語言能力也需要進一步提高。我在美國的許多學生,不僅會英文,還會法文、德文、日文等,這樣閱讀的內(nèi)容才能廣泛。即使是在中國研究中國文化,也還是要看外文材料,這樣才能客觀了解別人對自己研究領(lǐng)域的看法。研究中華文明的年輕人要讀好英文,包括日文,因為日本在漢學研究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把中華文明研究放在人類文明的語境下”
另一個變化趨勢是,我們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國,這在西方的大學變得越來越明顯。否則,我們將發(fā)現(xiàn)自己在大學里變得無足輕重,無法與同事對話,到頭來無法宣傳中國文明的價值和意義。
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了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但說實話,許多人對中國文明的傳統(tǒng)并不太感興趣。如果我們想要在全球保持中國文明研究的生命力和相關(guān)性,就要向兩方面發(fā)展:一是“垂直”研究,即從中國上古一直到今天的研究;另一個方向是“橫向”研究,就是研究某一個時代,但不僅僅是研究中國,也研究其他的地方,而且這兩種方向應該是互相補充的。
古代文明發(fā)展范文6
我的祖國是中國,它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和歷史。
記得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很久很久以前,東方有一頭獅子,他睡呀睡呀,睡了近五千年。有一天它醒了……。”沒錯,中國的確是一頭猛獅,一旦蘇醒,必定要震動整個世界。我們中國的四大發(fā)明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們是指南針、火藥、印刷術(shù)和造紙術(shù)。指南針可以用來指引方向,迷路的人可以用來分辨東西南北。火藥可以用來制作槍,還可以制作煙花供人們歡樂。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是中國在人類的傳播和發(fā)展上,所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是中國化學史上的一項中的重大的成就。我們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不僅僅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shù)繁榮的標志和中國人民聰明智慧的體現(xiàn),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古代文明的進程。
我們中國還有很多名人,如、、等等,他們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們是我們所有中國人民心中崇高的、所尊敬的人。
這就是我的祖國,歡迎你來訪我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