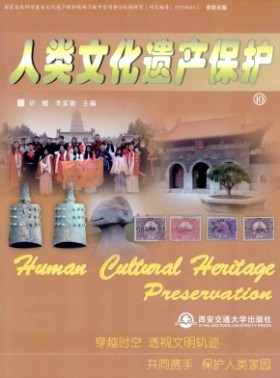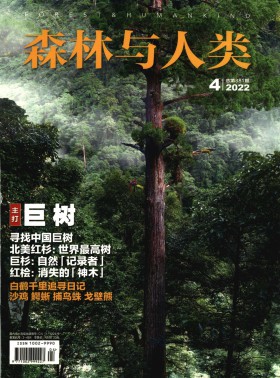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1
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人類學領域里的許多著作都是在馬林諾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啟發下寫成的。作為文化功能論學派奠基人的馬林諾夫斯基,為長期深入的實地調查開創了先例,他在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總共做了兩年的實地調查工作,創下了實地調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的居民成為民族學報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絕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該島居民的民族學資料為背景或依據寫成的。馬林諾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體”與人的需求之間的功能關系的寫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學到的哲學方法對人類學進行全面修正,并從中創造自己的科學預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時代,從德奧哲學體系中學到批判經驗主義和民俗心理學,這為他創立以經驗和整體觀念描述為特點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學基礎。他在英國的人類學訓練,使他掌握了人類學的民族探險的基本方法和人類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時代對他的故鄉波蘭的戰爭和分裂局勢的痛恨,使他力圖在異鄉尋找穩定、統一而平和的社會模式。而英國的實用主義哲學的盛行,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創造出來的民族志,強調的自然是社會一體化、人類的需求、經驗主義的描寫等等“邏輯”。雖然馬林諾夫斯基對自己作為民族志作家所處的背景深有意識,但是為了讓自己的雄心壯志得以實現,他壓抑了自我意識的表現,而只在學術圈中表現他的科學精神。
對于馬林諾夫斯基的整體民族志,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三種批評:一是來自英國,主要以阿薩德為代表,他認為人類學對落后民族的調查研究是在殖民地開展的,所有的“科學民族志”實際上與西方的殖民意識形態有密切的關系。二是來自西方對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許多學者開始意識到西方發明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實質上是通過對異文化的描述,獲得一種對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觀論證。三是“解釋人類學”,與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關系最為密切,吉爾茨認為文化人類學中的職業實踐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為通過人類學分析法獲得某一形式的知識的途徑。羅康隆博士依據馬庫思(George Marcus)和庫思曼(Dick Cushman)的分析,在其論著《文化人類學論綱》中指出,“馬林諾夫斯基及其追隨者創立的民族志可稱為一種現實主義的作品,它們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傳統民族志中最典型的敘述結構的特點是全觀性,把民族志當成回答文化或社會個別元素與整體的關系問題。為了表現現實主義民族志的所謂‘科學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稱來講述他們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類學家通過創造文化主人公來佯張自己是客觀公正的。其二,傳統民族志一開始就重視對田野作業的條件和經驗作出交代,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民族志顯出它們的論斷的權威性,使書中的觀點被讀者接受。有時,為了使人覺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現實,人類學者故意說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記、腳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經歷某事等,對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視。其三,民族志作者對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夠的詞匯。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談自己的語言能力,他們閉口不提自己對被研究者的語言掌握程度,這使人懷疑他們的解釋是否符合實際。”當人們在對傳統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時,人類學界出現了一股對民族志作出新實驗的潮流,這股潮流是把人類學者和他們的田野工作的經歷當做民族志實驗的焦點和闡述的中心,對文本的有意識的組織和藝術性的講究,把研究者當成文化的釋譯者,對文化事項進行闡釋。
在西方音樂人類學民族志研究的過程中,經歷了一條從注重紀實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闡釋的過程。在音樂人類學發展過程中,民族志的描寫方式和研究觀念始終受到人類學及民族志學者相關理論的影響。民族志研究傳統的描寫方式過去有重描述甚于闡釋、重行為過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傾向,這與人類學中美國歷史學派的學術傳統有關。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認為,民族學研究的任務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體表現,不要作理論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規律;相反,他們應該在某種文化消失之前,盡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盡可能多的資料這一工作上去。他預計,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資料的話,那么,決定文化變異的普遍規律就會從這些信息中自動產生出來。關于音樂人類學民族志的描寫,以往專家們都是把它作為音樂民族志研究報告中有關田野考察對象,音樂活動過程及音樂文化分析結論等方面內容的具體表述方式。由于音樂人類學學科曾幾度引發對學科基本性質的質疑和爭論,對于近來的音樂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著革命性的影響。楊民康教授就音樂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論取向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音樂學與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對自己研究對象進行細致描寫的功能和長處,其區別在于‘音樂的寫錄是對聲音的展現,民族志則是關于人的紀錄’。由此可見,雖然一般音樂學與音樂民族志在描寫的范圍上寬狹有別,但注重描述卻是其較基本的傳輸和表達方法。”在音樂人類學觀念下對音樂進行多維闡釋的可能性其實來自于人類學科以外的傳統學科體系內構建起來的各種理論,而作為主體學科的人類學,其于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支持與貢獻也正在于具有學科標示性意義的“民族志”。因此,音樂人類學研究有必要借鑒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為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的地位是非常合適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對“異域”的社會文化現象記述,是一個包括商人、旅行者、傳教±、殖民地官員等撰寫的關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會情況的各類文學材料在內的廣義文體概念。人類學家們隨后結合具體的研究實踐,編制了調查寫作綱要,將散漫、業余的民族志推進到了專業規范化層次,以幫助所獲得的信息能將滿足研究所需,其開始獲得某種確定的文體規范。后來,民族志就發展成為以規范的田野作業為依托的人類學學術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志具有雙重內涵――既是一種文體,也是一種方法。那么,音樂人類學對作為具體學術實踐的規范內容的民族志的討論,也應在“方法”和“文本”兩個層面展開。當代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者的方法論研討,主要是圍繞以博厄斯理論為代表的傳統人類學觀點和以吉爾茲理論為代表的闡釋人類學觀點之間的分析展開,兩種對立的觀點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補之處。
民族志是音樂人類學的下屬分支,它同音樂人類學一樣,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結合了音樂學和民族學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楊民康指出,它就像音樂人類學家西格所說的:“它并不以學科界限或理論期待來定位,而是定位于音樂的描述,它超越了聲音的記寫而去表現聲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賞和流傳至其他的個體、族群,去描寫社會和音樂的各種過程。”音樂人類學是應用一套特殊的理論,去解釋人類行為和音樂發展的歷史。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提倡微觀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這個學術傳統今天由民族志學者保存下來。有關 描述性與闡釋性方法結合較好的研究實例,如美國學者卡特林(Amy Catlin)的《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說:一種闡釋學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學民族音樂系編輯的民族音樂學論文集里,為一批有關上述東南亞國家樣傣系族群的音樂民族志研究論文所寫的導論。這些論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闡釋學、符號學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論文采用闡釋學方法得到的具體結論之一,是認為“平地老族”從13世紀始由中國南方遷到泰國,其建立的王國與印度、柬埔寨和泰國保持著密切的文化關系,其宮廷和寺廟的音樂演奏表現了這種文化的親和力,所使用的音樂則象征著王權和政治體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摻入闡釋性因素,不僅對以往民族志長期形成的固有觀念和方法論格局造成了沖擊,使其不變型。但是,如今音樂人類學中已經使用闡釋人類學和符號學等研究方法,傳統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還是一些人類學者和音樂學家堅持的方向。在音樂人類學研究進程中,音樂人類學家們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依研究者個人的學術習慣,研究路徑也可能有局部的改變。楊民康教授在研究音樂民族志時,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所創,又由許多民族音樂學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觀”等文化觀念發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類音樂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學者將梅里亞姆視為“認知民族音樂學”的代表人物,因為梅里亞姆的理論同認知人類學之間具有密切關系。在現代文化人類學中,最為關注的兩大主題是文化觀念和社會行為,而文化觀念又被認為是控制和指導種種文化行為的基礎要素。這個理論認識在認知人類學中得到了最佳的體現。認知人類學又稱民族語義學或民族語言學,是美國人類學家沃德?古德納夫和埃洛伊德?勞恩斯勃格等于20世紀50年代開展的一個頗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學派,亦是以吉爾茲為代表的闡釋人類學賴以形成的兩大理論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論中,列維?施特勞斯結構主義人類學和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轉換生成語法學派等,也是音樂人類學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論依據。
在音樂民族志的雙視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論概念中,楊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論性思考,諸如音樂的符號化活動過程;音樂的認知與創造過程和接受與反饋過程:雙視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個基本環節:本文的建構、模式的擬構、模式的闡解、模式的比較等。在國內,音樂人類學科有了很大發展,并且在介紹、引進和學習西方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輩人類學家就認識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論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對指導當時學科的發展與整合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學者們大量發表民族志的作品,他們大多數人經受過西方學術體系的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的學術訓練,十分關注研究方法,保證了民族志作品的學術質量。同時,學者們對中國音樂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論取向問題產生爭論。1984年,杜亞雄提出:“許多搞民族音樂的人都感到我們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長期處于介紹和描寫的狀態,對許多音樂形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觀念中,輕視研究過程中的資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責這種以資料收集、整理為主的‘介紹’、‘描寫’是人們對民族音樂‘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論哪一個國家在開展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活動中,都把觀察描述民族音樂現象放到頭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資料的收藏作為民族音樂研究成果的標志。”喬建中1985年指出:“據說有人不以這類‘描述性’文章為然,認為它還不夠‘民族音樂學’的格;自然,撰寫此文章者也就難以入流。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為,對于任何一種活的民間音樂作稍微系統、實在的梳理和歸納,都具有研究性質。中國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樂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紹,孰年孰月才能識其真面目呢?”在這些爭論中,不難看出中國學者們一方面意識到了博厄斯觀點在當代中國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關注到了“闡釋性”研究方法的運用,其中包括采用闡釋人類學和符號學等學科方法在內的研究手段,對研究對象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和語義象征進行進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2
【關鍵詞】經濟人類學;中國;展望
【作者】趙巧艷,廣西師范大學漓江學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2010級博士生。廣西桂林,541004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經濟人類學興起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經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學科。1941年赫斯科維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經濟人類學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專著《經濟人類學》(Economic Anthropology)。卡爾?波拉尼的兩篇論文――《作為制度過程的經濟》和《早期帝國的貿易和市場》的發表所引發的“形式――實體”論戰使得經濟人類學上升為一個學界關注的研究領域。1981年美國經濟人類學學會(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則正式標志著人類學一個重要分支學科的誕生。可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國內對經濟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進展一直缺乏關注,直到1982年,蔡振揚翻譯了達爾頓和蓋克的《經濟人類學的展望》一文,經濟人類學的概念才正式進入中國學術研究的視野。2001年和2002年陳慶德和施琳相繼出版了《經濟人類學》兩本專著,標志著國內經濟人類學研究的第一個的到來,這一點也可以從圖1看出(圖中的論文來源為中國知網學術期刊庫,檢索條件是以“經濟人類學”為標題進行精確匹配)。此后,國內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較高的關注度,在研究的理論探索和案例調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而且如今正處于第二個研究的快速上升階段(圖1)。然而迄今為止,盡管國內學界對國外經濟人類學的研究進展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理論介紹,可是關于國內的研究進展卻沒有一個系統的總結和概括,從而無法在對比的基礎上準確把握學科研究前沿以及國內外研究的差異。鑒于此,本文嘗試對國內經濟人類學的研究現狀進行系統梳理和分類概括,并結合國際上經濟人類學的研究前沿,剖析國內外研究之間的差異,展望國內研究未來的努力方向。
一、經濟人類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如果把用人類學方法剖析經濟問題全部納入經濟人類學研究范疇的話,先生的《江村經濟》無疑開創了國內經濟人類學研究之先河。但結合經濟人類學定義與內涵的演進歷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經濟學導論》和《民族經濟學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義上國內經濟人類學研究的開山之作。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經濟人類學在國內的人類學研究中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類學教科書中,經濟人類學都成為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如莊孔韶的《人類學通論》(2003)、朱炳祥的《社會人類學》(2004)、孫秋云的《文化人類學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類學教程》(2006),周大鳴的《人類學導論》(2007)等,在章節安排上都將經濟人類學作為重要的內容加以介紹。經濟人類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主要通過兩種方式:相關著作出版與學科定位、國外著述翻譯與理論引介。
(一)相關著作出版與學科定位
一門學科的理論集大成之標志離不開專著的出版,中國經濟人類學的蓬勃發展也同樣以21世紀初期兩本最重要的專著為標志和載體。2001年和2002年,陳慶德和施琳相繼出版了《經濟人類學》專著,極大地推動了經濟人類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力擴散,而且在后者的專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對該書做了簡評,發表于民族學權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時,兩本專著的出版也標志著以云南大學和中央民族大學為首的經濟人類學研究團隊的確立,兩所大學培養了一大批經濟人類學方面的研究人員,奠定了經濟人類學的學科定位,使得經濟人類學越來越為人類學界和民族學界認識和認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機構也開始將經濟人類學作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點,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等。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考察,中國臺灣的經濟人類學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規模的機構和研究人員的體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黃應貴、陳文德和新竹清華大學馬騰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黃應貴先生不僅在臺灣講授經’濟人類學的課程,而且也在大陸做過多場學術講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中安排兩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專門探討經濟人類學議題。
(二)國外著述翻譯與理論引介
學科的持續發展離不開國際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譯和理論引介,隨著國內對經濟人類學理論的引入和擴散,翻譯國外經濟人類學的著述和介紹國外的一些相關理論也成為推動理論傳播的一種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譯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譯粟本慎一郎的《經濟人類學》影響較大,也是迄今國內最為全面介紹國外經濟人類學理論的譯著。其他的譯著散見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譯高野平次耶的《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拉尼》、王慶仁翻譯哈羅德?施奈德的《經濟發展與人類學》、胡琰翻譯斯圖爾特?普拉特納的《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地方性藝術市場――經濟人類學個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對經濟人類學這一學科的通俗介紹,如田廣翻譯小艾倫德的《經濟人類學》、韋蘭春翻譯西摩-史密斯的《經濟人類學》、姚繼德和杜杉杉翻譯格雷戈里的《禮物與商品》等。也有個別針對特定研究的翻譯,如黃娟和胡琰翻譯朱迪思?馬蒂的《工業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決策之經濟人類學研究》。隨著翻譯作品的增多,也出現了一些評論性的文章,如李亞娟和戴慶中對粟本慎一郎《經濟人類學》的評介。
國內在經濟人類學的理論引介方面要較論著翻譯做得好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施琳和云南大學的陳慶德。施琳從本世紀伊始就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論文,重點介紹了美國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源起、理論演進和研究發展,如《論美國經濟人類學的歷史理論源流》、《論美國經濟人類學的誕生與早期發展》、《經濟人類學中的“形式”與“實在”之爭》、《新形式主義經濟人類學探索――斯圖爾特?普萊特納經濟人類學學術思想剖析》、《建立廣義的實在主義經濟人類學――喬治?多爾頓經濟人類學學術思想研究》、《美國經濟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美國經濟人類學與中國民族經濟學之比較》、《經濟人類學理論前沿綜論》等。陳慶德闡明了經濟人類學實體論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論隊伍、馬克思理論在經濟人類學中的拓展、經濟人類學的理論發展、理論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經濟人類學場域中的運用與演化等。其他一些學者在經濟人類學的理論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貢獻,如鄭海燕簡要回顧了國外早期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情況,并從研究領域的擴大、理論的綜合作用、研究方法的靈活多樣性以及應用性的增強幾方面介紹了經濟人類學的發展趨勢;王祖望探討了經濟人類學與波拉尼學派的關系;王燕祥對經濟人類學的定義與演化做了介紹,并簡要分析了經濟人類學和民族經濟學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李富強對經濟人類學的發展、理論、特點與功用進行了簡要評述;許婧介紹了西方經濟人類學理論的發展歷程,并對經濟人類學的理論演進進行了階段劃分。
二、針對中國情境的經濟人類學研究進展
經濟人類學是一門“情境性”很強的學科。中國民族種類繁多、民族文化歷史悠久,而且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性也非常顯著,具有天然的經濟人類學研究資源稟賦,而且也需要借助經濟人類學的理論闡釋許多社會問題并提供問題解決的理論參考借鑒,于是國內開展了大量針對中國情境的相關研究,主要圍繞社會交換、勞動力要素、民族經濟發展、其他問題等四個方面展開。
(一)社會交換
交換一直是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關注的核心主題,因此社會交換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經濟人類學的焦點研究領域。陳慶德和潘春梅從宏觀的角度探討了不同歷史時期和民族社會在交換模式上的差異,認為不同的交換模式與具體的歷史階段、社會結構或文化背景關聯為一體,從而為經濟人類學與歷史學、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個拓展研究視域的基點;馬冬梅和梁勇通過對一個村落的經濟人類學個案考察,論證了“乜貼”的流動具有類似于經濟人類學中禮物的流動特點;鄭宇和譚本玲分析了箐口村喪禮中的經濟消耗、喪禮禮物的贈予和分配等過程后證實,哈尼族喪禮的根本要義,就在于通過經濟的消耗,來實現當地基于親屬與非親屬區分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再生產;¨釗朱健剛和羨曉曼則從經濟人類學的視角探討了冀南鄉村的物物交換現象。
(二)勞動力要素
從經濟人類學視角剖析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勞動力要素也是國內經濟人類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其中以馬煒和麻勇恒的研究較為典型。馬煒認為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問題的本質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擁有的知識能夠在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資本化運用而使這些知識成為了資本,從而使自身成為了人力資本的擁有者,表明人力資本是一個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問題;麻勇恒指出勞動力的過度轉移,導致山地農耕生產、家庭養殖所需勞力難以保證,從而間接地撕裂了養殖與山地農耕生產的邏輯耦合,聯動地產生了糧食生產下降、養殖業萎縮、糧肉價格普遍上漲,以及土壤結構畸變、農村社區文化生態失衡等非預期后果。
(三)民族經濟發展
經濟人類學是探討與日常生活和生計直接相關的人性問題部分規律的學科,而生計又是經濟人類學的核心研究對象――落后地區(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涵,因此,關注民族經濟發展也自然成為經濟人類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國內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較豐富。魏樂平通過對云南省德欽縣茨中村生計模式的研究,證明生計是人類與自然交換能量,維持與社會變遷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計是人類適應環境結果,也是社會變遷的產物;張曉萍分析旅游活動中的文化商品化問題,指出旅游活動中的“舞臺真實”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行為,對傳統文化的神圣儀式等必將產生消解作用,但也帶來了文化創新和整合的機會;馬嵐從Stephen Gudeman經濟人類學視角分析民族旅游問題,并借鑒該書中的兩個案例為民族旅游發展提供新的思路;遲駿剖析了屯堡文化發展的經濟效用極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體與旅游公司的一體化;羅康隆和曾憲軍指出在民族經濟活動中,經濟是與其他種種社會因素交織在一起表現出來的,要準確地評估不同類型和不同樣式的各民族的經濟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須綜合、系統分析;黃海從經濟人類學的視角對貴州民族地區的開發問題進行了反思。
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影響是經濟人類學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一趨勢也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陳慶德從宏觀層面探討了經濟人類學的生態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則傾向于微觀的考察,從生態――經濟人類學的視角來考量鄂倫春族經濟類型、生產關系的變遷及其效應問題,描述了鄂倫春族從游居到定居、從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鎮化的演變過程,重新審視鄂倫春族的狩獵經濟,探討鄂倫春族的經濟發展問題。房艷麗和劉文江從人文的角度分別就人口素質、資源的流動以及市場經濟基本面的培養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經濟發展中需要關注的三個問題。2011年在云南大學舉行的“經濟人類學與中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發展國際研討會”上,一些國外學者(如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蘭波茲南經濟大學Katarzyna Nawrot)也對中國民族經濟問題表現出濃厚的研究熱情,與會的臺灣學者陳文德和馬騰岳,大陸學者徐黎麗、高志英、鄭宇通、呂俊彪、李忠斌和張英也分別從民族經濟的發展道路、經濟關系與民族關系、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結構發展、民族旅游開發和旅游城鎮化道路選擇等角度展現了民族經濟研究中經濟人類學的重要意義。
(四)其他問題
21世紀初,經濟人類學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諸如現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經濟人類學的這一轉變同樣受到國內研究的關注。陳慶德無疑是這一轉變的重要引導者和實踐者,他從經濟人類學的分析框架出發,反思了現代化進程的得與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經濟人類學研究中的應用、商品價值的文化內涵、貨幣的符號涵義、農業社會和農民經濟的發展演變等多個范疇。其他研究也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層面迎合了經濟人類學的研究導向變革,如冶榮夏通過伊佳企業個案對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廣華和李葉青關于中國古代朝貢關系對經濟人類學獨特價值的探討、錢國芳對民族品牌與民族文化和民族經濟之間關系的剖析、譚宏對中華傳統品牌的經濟人類學解讀、孫信茹對廣告的經濟人類學分析、葉輝以華江瑤族毛竹資源開發為個案對資源開發如何嵌合在社會制度中的探討、杜成材對潘寨與黃崗兩寨傳統制度與鄉村管理的透視、葉建芳以三寶坪“瑤族狀元村”為個案對民族教育問題的考察等。
三、中國經濟人類學研究的未來展望
與相關學科相比,經濟人類學是一門年輕有朝氣的學科,它應該在人類學研究領域中成長為一門極具發展潛力的分支學科。雖然經濟人類學進入中國學術研究視野的時間不長,可是它已經深深扎根中國學術研究的沃土里,并且開花結果,在理論深化和實踐應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也培養了一大批專業研究人員,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研究體系,在研究理論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可是就世界范圍內的趨勢而言,經濟人類學,甚至其母體學科――人類學都面臨諸多挑戰。過去30年以來,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已經出現了去核心化趨勢,如今國外許多大學甚至都沒有將經濟人類學、親屬制度和生態人類學列入教學大綱。與國外研究相比,國內的經濟人類學研究仍然處于一個不夠成熟的階段,研究的焦點基本上還沒有超越早期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范疇,理論的原創貢獻更是缺乏,在國際上也尚未形成與中國經濟人類學研究條件和資源相匹配的學術地位。實現中國經濟人類學的繁榮有待于以下四個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視域的拓展
如今,經濟人類學已經成為一門研究廣義人類社會行為的基礎與動因的學問,它的理論方法是多元的、開放的,經濟人類學進一步發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閉自己的研究領域,永不拒絕新的理論工具和方法的運用。早期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視域主要涵蓋相對狹義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原始經濟范疇,而且這種觀點一直在延續。Stephen Gudeman把經濟人類學的研究領域界定在生產、交換、交換圈、市場和消費等領域;Susana Narotzk同樣認為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范疇包括生產、分配、消費和社會再生產,然而他的這一觀點卻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嚴厲批評。跳出狹義的經濟人類學研究視域,在更廣闊、更具現實意義的范圍內解釋社會實踐并提供理論借鑒是當代經濟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轉變。2000年的經濟人類學大會首次圍繞“性別問題”展開討論;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開了主題為勞動力、貴重物品、商品、財富與金錢、人口流動與經濟,以及“快餐與慢餐:食物與食物體系的社會和經濟背景”的學術會議;2007年召開的澳大利亞人類學年會也重點討論了“當代人類學的經濟議題”,而且探討的主題也不僅僅局限在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和經濟史等傳統議題上,相當一部分論文涉及到特殊類型的供應和交易鏈范疇。
國外一些學者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探索,如Hart對非正式經濟的經典研究在變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價值;Chabal&Daloz有爭議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顯了研究導向從對秩序社會的功能主義探索到對失序現象的實用主義探討轉變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經濟人類學研究方法開創了邊疆問題研究;Janet Roitman應用經濟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了喀麥隆北部地區、尼日尼亞東北地區、乍得和中非共和國交界區域的非正式經濟活動,認為這些違法的、陰暗的經濟活動在日漸活躍,可是并不意味著這些活動都是無序的,它們同樣有著自己的行動規律和準則,而且這些規律和準則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會內并且有著嚴密規定的行動邏輯。相對而言,國內對這一轉變也表現出一定的關注,如施琳呼吁中國學者應加強關于經濟人類學學科視角與方法論的探索,積極開展新型邊疆民族志的調查研究;陳慶德雖然認同經濟人類學有別于主流經濟學經濟的觀點,但他也認為人類學研究可以拓展到歷史、現實、生態等不同層面;許婧雖然認同交換、貨幣、消費和私有化一直是經濟人類學研究主題的觀點,可是她對經濟人類學研究歷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類學,注重貨幣、市場與物的視野。但總體而言,國內的研究視域依然尚未在整體上超越傳統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范疇。
(二)研究層面的融合
關于經濟人類學定義的不同理解導致了對經濟人類學研究適用層面的不同結論。赫茲克維茨認為美國經濟人類學主要是“關于原始人的經濟行為與經濟生活”的一門學問,只是后來在許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對書中將他們與土著人相提并論的情況下才將《原始經濟》第二版改名為《經濟人類學》;《人類學詞典》的解釋是“經濟人類學研究的重點包括在跨文化比較下的生產、分配、交換問題,對特殊經濟體系的民族志記述,前資本主義或混合型經濟體的構成,分析在小型社區或農民社區中的民族經濟、多民族經濟和世界經濟體系的沖突”。似乎經濟人類學的研究層面只適合微觀層面特定群體的經濟活動規律,然而《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中的同名條目的解釋則稱其為“研究人類各種社會的經濟生活、經濟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類學分支”,從而將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視域和層面延伸到各種類型的社會制度和各個層面。比較來說,倡導在更加宏觀層面開展經濟人類學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認為經濟人類學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時拒絕形式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局限,應該采取新的問題導向的方法開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類學家不應立足于國家或地區這些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單位,而應從整個世界體視域擴展應對來自宏觀“世界視角”的挑戰;形式主義流派的學者們主張系統地、全面地在經濟人類學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規范的經濟分析方法。
除了理論的爭辯以外,國外已經在實踐中將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觸角擴大至宏觀層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個經濟人類學研究方法(理性、社會和文化)為基礎,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了挪威國家創新體系(NIH)中的專業化交易問題。理查德?羅賓斯的《全球問題和資本主義文化》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審視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觀問題,如資本主義的興起、世界糧食問題、人口增長、消費、種族沖突以及不平等問題;Gregory在展望經濟人類學的未來發展道路時指出,從次要觀點視角探討經濟、親屬與生態相互之間關系的一般理論將依然被保留在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框架內,可是經濟人類學主要的理論范式必將在更加廣泛的層面上反映歷史變革背景下社會文化圖景,經濟人類學研究的核心主題從交換到消費、再到分配、能動和金融化就體現了這樣的演進邏輯;Bill Maurer也從金融危機和債務、信用、投機、失衡本質的角度探討了經濟人類學當代的研究宗旨。國外的這種實踐無論在理論還是應用上都是有意義的,就如Chris Hann的觀點認為,經濟人類學已經跳出了20世紀60年代關于全球政治經濟和地方模式爭論的局限,而是在一個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維茨時代的研究范疇內考察當代世界的熱點議題,而且這種研究導向也極大地拉近了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學研究之間的距離。陳慶德和鄭宇也發出類似的感慨:傳統的經濟人類學分析視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設的模式應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歷史的視野固著在順應經濟科學的范圍中,無論是把經濟的涵義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質的單一層面,都實在是太狹隘了。可是在具體的經濟人類學研究層面融合上目前國內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似乎缺乏開創性的嘗試。
(三)研究范式的轉變
伴隨國外經濟人類學的研究層面從微觀向中觀和宏觀的拓展,他們的研究范式也出現了相應的改變。盡管人類學家的主題是“微觀的”而不是“宏觀的”,他們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資料的分析,而經濟學家主要依賴于官方統計來滿足其資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論上經濟人類學并非孤立和特別,它吸納了源于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鮮明的交叉與混合的方法論特色。不僅如此,由于經濟人類學對多元文化背景下復雜經濟行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進展,反過來對于人類學和經濟學研究也有一定啟發意義。伴隨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不斷“接近”,在經濟人類學的研究中應用經濟學中普遍采用的實證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為一種趨勢。由單個、局部的田野調查式研究向大范圍、定量研究范式的轉變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支持。Prattis已經明確表明他對拋棄正統經濟人類學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種追求,他認為與傳統經濟人類學研究上對人與情境邏輯影響決策過程過度關注相比,將情境邏輯與生產理論聯系起來,從而彌合微觀宏觀之間的鴻溝也許更有意義;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類學家一直受到批評,因為他們出于良心的承諾使得事情變得混亂而不是為宏大理論做出貢獻,而且為了改善到這一點,對宏大理論進行實證研究也許比理論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他指出雖然Wilk&Cliggett在書的結論部分描述了對人們決策進行實證調查的方法論,可是調查的目的應該是探求人們采取行動的理性最大化、社會或道德依據,因此理論爭辯的焦點不僅僅是引導批判或發展理論,而是提供對相關事件研究的一個更為廣泛的實證研究方法;Gregory通過對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貨幣”的概念,又進一步指出,非制度的、類血緣關系的親屬結構分析元疑是理解這種新興“轉型家庭”的關鍵,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拋棄那些過時的陳舊思維模式,通過定量的實證研究進行驗證。國內的經濟人類學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還停留在學科的早期發展階段,依靠范式轉變推動學科跨越式發展的進展依然緩慢。
(四)研究學科的整合
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3
同時,我們也應意識到兩個問題:一是歷史人類學對人類學“無時問感”的批判性,兩者之問在挑戰、對話中不斷磨合、互動發展,在白身文化研究的反思中超越近性史觀并與歷史相匯的產物。二是歷史學的歷史人類學和人類學的歷史人類學區分,區別在于前者關注如何對待歷史問題,后者更強調關注人民如何對待并處理他們的歷史匡。歷史人類學是空問文化和時問歷史的統一,因此在研究過程應注意把握文化的歷史向度、歷史的多元特征、歷史的文化解釋、記憶對歷史的制作以及歷史的力量等特征匡,將歷史人類學研究與田野調查實踐相結合,將歷史文獻的收集、了解與運用滲入田野調查。
歷史人類學的產生主要分為四個階段,即平面史的敘述模式階段、人類學與歷史學的整合階段、歷史文化的深描階段、中國歷史人類學的產生及其傳統階段匡。這也反映了中國歷史人類學無論是受到功能主義學派還是歷史具體主義論的影響,均呈現出西學東漸的中國化過程,用歷史的眼光去研究人類學發展,這是基于人類學原是具有歷史性質的,人類學所要考慮的原是歷史上的事實,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歷史的方法。在文化論與歷史學的社會協調過程中,歷史人類學還出現“南方經驗”和“北方經驗”的論戰,南、北派分別以林惠祥先生、先生為代表,論爭焦點集中在區域研究與歷史資料的建構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學展開一場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南方經驗和北方經驗論戰,圍繞不同時代的國家在不同區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與國家之問的民地關系,又將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推向新的。
歷史人類學本質體現一種歷史反思的過程,既吸收文化人類學傳統理念,同時也借鑒史學研究方法和史料的運用,反映了人類學的歷史化。它是以歷史的時問維度和文化的空問維度去發現、研究不同區域的社會群體,歷史素材與社會文化時問性并舉,將其概念化、符號化,再現人類社會歷史,符合“歷史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法納入社會人類學當中,一是透過對某一特殊歷史資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會制度時對時問觀點的認識當中”匡的論斷。此外,歷史人類學還體現了文化論與過程論的辯證關系,即人類學和歷史學的協調,從歷史人類學出發對具體的歷史個案進行重新解讀,可以使我們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識形態放回到歷史過程中去解釋,也使我們有可能賦予歷史過程本身一定的反思價位匡。因此,歷史人類學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結合,為我們全面理解人類社會現象提供理論方法,在歷史背景下,運用文獻史料,結合田野實地調查,以過去解釋當下,為進一步研究社會機制提供可能。
二、歷史人類學對唐宋婦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誠然,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均以研究日常生活為主,英國人類學家埃文斯·普理查德曾論道:“如果不把環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慮進來,就不能理解這種政治制度。因此,對日常生活史研究是歷史人類學發展的基礎,這是因為“一個社會表現在習俗中的爭論的最少的態度和行為,如對身體的照料、穿著的方式、勞動的組織和日常生活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著這個社會的表象系統;而這系統在深層上與法律、宗教觀念、哲學或科學思想等最精心構件的知識框架都緊密相連。
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4
關鍵詞:文化;人類學;危機;生命文化學
眾所周知,人類學家宣稱,人類學是關于人類歷史的科學。美國的人類學研究傳統分為四支(特別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動之后):生物人類學、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來,在文化人類學的子分支之間的聯系已經非常薄弱[2]。人類學的分支越來越專一化。過度的專業化是人類學面臨的一個問題。
人類學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文化”這個詞本身。20世紀初,人類學家把人類學界定為關于文化的科學,而現在人類學家逐漸變為文化研究方面的專家[3]。人類學家把文化界定為他們用來研究世界上不同人類群體的生活方式的理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工具。大量關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的上半個世紀[4]。盡管文化的概念眾多并且沒有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是人類學家普遍承認這樣的假設:文化是后天習得的,基于符號的歷史產物。換句話說,文化與自然相對,擁有自己存在和進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紀下半葉,文化達到了一種濫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種族中心論”的人誤用。Adam Kuper陳述了它的成功:“現在每個人都進入到文化中來。”[5]換句話說,我們正在見證這個世界的文化膨脹。
Keesing在1974年預測了未來的研究熱點:“‘雅諾馬米文化’、‘日語文化’、‘文化的發展’、‘自然與文化’:我們的人類學家仍然使用這個詞,我們仍然認為這意味著什么。但是從靈長類動物存在的學習傳統,使用工具和操縱符號,我們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號的習得性遺傳是人類所獨有的了。”
僅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他定義社會生物學為“所有社會行為生物學基礎的系統研究。[6]”同時,他宣稱社會生物學的目的是“利用當代綜合進化論的成果重新規劃社會科學。[7]”
自從70年代以來,所謂的進化派社會科學一直在學術界中發展和傳播。我用“進化的社會科學”這一標簽來稱謂用進化論的方法來研究人類文化的那一派研究。這個標簽反映了在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前沿的交叉,現在有很多學者使用這個詞。在進化的社會科學領域最先進的無疑是社會生物學、進化心理學、人類行為生態學,人類行為學,模因論、以及“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的的方法。上述學科的代表發展了他們自己關于文化的概念,我們稱之為文化進化論。
那么,早期文化人類學家把文化定義為一種后天習得的基于符號的歷史產物,而社會生物學家的定義則是完全對立的,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生物學上的適應性,或者說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進化心理學和人類行為學中也有關于文化的類似表達。
人類行為生態學和“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理論,都在文化人類學對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兩者有所不同。他們認為文化不是生物適應的產物,基因并不能操縱文化。
在行為生態學中文化是在某種特定的生態環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適應性策略。他們在人類行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對于當地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的適應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種行為的適應性。
共同進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間的相互動力系統。例如,William Durham已經列出了基因與文化作用的五種關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調節),genetic mediation(基因調節),enhancement(增強),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對).前三種是互動的,后兩種是比較的(Durham 1991,205207)。總之,他認為兩者在互動中可能會影響到對方。基因與文化的關系將參照:(1)相同的目標(增強);(2)矛盾的目標(反對);(3)不同,但目標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釋為基因進化的產物。在協同進化理論中,文化是基因與社會文化環境協同進化的產物。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體科學的人類學中的危機。首先是,人類學的過度強調分支化和跨人類學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機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類學中的滑坡,它被指責將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會中的一種中心主義的建構。第三個根源是,“文化”這個概念的膨脹,人類學成功地給出“模因”,并認為它承載了一個更為寬泛的意義,它最終將涵括任何東西。并且如果是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實際上是一個空洞的詞匯。危機的最后一個根源是,在進化社會科學中對文化這個概念的寬泛的討論。它的表征是從人類學意義上來使用這個概念,但是一般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合適的背景。
基于文化學理論框架的生命文化學,方便了人們對進化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的理解,生命文化學是一個文化學的分支。生命文化學這個概念是由美國人類學家伊諾?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個物理人類的分支的標簽,主要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關注文化和生物現象。生命文化進化從文化屬于非生物學的適應性這個前提出發,將人類與其它生物區分開來,但是它并不意味著,人類獨立于他過去的進化。
相反,文化有它進化的根源,人類是被他的特征所決定的,并且建立在人類基因的生物進化過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學處理一種更為寬泛的主題包括動物和人類的不同。生命文化學進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適應性及進化之間的關系,分析社會生活的主要因素,并關注后天PK先天討論的結論。生命文化學可以從文化人類學的傳統這一方面和從進化社會學另一方面,為了支持人類作為生命文化個體的整合性研究。簡單來講,生命文化學采用了從科學和社會科學中認識的相關的發現并從文化角度來進行解釋。
生命文化學對于目前的人類學在三個方面的難題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學支持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性學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將文化看作是在科學對人的研究中理論上、認識論上和方法論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對人類學和進化論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對人類本質的二分的難題的克服。
[參考文獻]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5
“范式”這一概念最初是由托馬斯?庫恩(Thamas Kuhn)提出來的,指的是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科學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科研范式決定了某一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基本觀點,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形成了該科學共同的傳統,并為該科學的發展規定了方向。
教育人類學在“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研究范式。這種研究范式主張從書齋的思辨式研究轉移到注重實際的調查研究。書齋思辨研究重視理論推理,重視邏輯的嚴密性、理論的普適性,但由于過分關注理論本身的邏輯結構,使得學術研究容易脫離生活實際。在田野調查基礎上的研究則完全與之相反,其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學行為,重視對教育現象的搜集和整理。因此,從書齋到田野研究范式的改變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研究者的信念和科研模式。
教育人類學研究范式主要體現為以下四點:一是“跨文化研究”。教育人類學以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為研究對象,從而發現和解釋不同民族與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差異。因此,研究者必須深入他者文化中,從該文化背景的教育實際出發,在具體的文化中進行研究、分析。二是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具體技術為實地觀察法,要求避免單純理論想象和假設推斷,主張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要求研究者長期生活在被調查的對象之中,融入其生活并與其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從而搜集、記錄和整理當地人的行為或每日發生的事情,“其目標是在基于直接觀察和準確理解當地人的真實觀點的基礎上,對教育的事件、情形作充分的描述,其目的是為對某一民族或語言等特殊問題作進一步深入了解提供信息”。三是重視個案研究。教育人類學反對那些宏大敘事的抽象論述,主張深入實際、在詳細調查基礎上的個案分析。四是理論建構。教育人類學的研究不僅僅體現在對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現象、問題的調查,同時強調在這種實地調查基礎上的理論總結與概括。也就是說,教育人類學研究者不僅是一位實踐的探索者,而且還是理論的建構者,在田野工作中通過實地觀察、訪談、問卷分析等形式,發現新問題,驗證假設,形成正確判斷,構建新理論以及為社會實踐作出貢獻。
二、田野工作:教育人類學研究范式的基本方法
田野工作最先由動物學家哈登介紹到人類學中,隨著博厄斯、摩爾根、馬林諾夫斯基等對該方法的成功運用,使其成為人類學研究區別于諸如歷史學、社會學、政治科學、文學、宗教研究的重要標志。田野工作也是教育人類學最基本的一種研究方法,它要求教育人類學研究者于某一地點或區域住上一段時間(人類學研究一般在1年以上),把握當地年度周期中教育教學的基本過程,與教師、學生形成密切的關系,參與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活動,從中了解他們的教育教學、人際活動、風俗文化等。
我國教育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對少數民族教育的研究,注重研究少數民族和原始部落人群的教育問題;二是對弱勢群體教育問題進行的田野工作,這類研究除了研究少數民族兒童的學習問題外,還注重對一些處境不利或弱勢人群的教育進行調查研究,如出生在城里的少數民族子女、進城農民子女或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問題等;三是應用人類學方法,從文化的角度對主流文化教育進行研究。因此,不同研究取向在田野點的選擇上就有較大區別。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無論哪一種田野工作,研究者必須把他感興趣的事件放在自然發生的情境中,資料的搜集來自于自然式的研究場域――田野,如教室、餐廳、學生宿舍、教師休息室、學生家庭等,通過持續地與研究對象進行接觸,獲得第一手資料。
教育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具體技術為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另外可以配合一些問卷調查等其他研究方法。參與觀察法要求研究者在調查點長期居住下來,參與被調查者的生活與學習,觀察他們的教育活動和個人言行舉止。因此,參與觀察法亦稱為“局內觀察法”或“居住體驗法”。馬林諾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對特羅布里安德群島土著文化進行的就是參與觀察式的田野工作。在教育人類學田野調查中,僅靠研究者個人的觀察是不夠的,大部分的資料須依靠一些研究對象提供,這就必須采用深度訪談的方法。訪談的對象可以是教師、學生、學生家長。訪談的內容既可以是針對訪談對象自身的教育問題,也可以是他所知曉的其他情況。一般而言,對訪談對象須精心選擇,對重點訪談對象更是如此。他(她)的年齡、性別、社會閱歷、職業、文化程度、社會地位、工作態度、語言表達能力、社會關系等都是必須予以認真考慮的。
教育人類學的迅速興起在于倡導了這種獨特的研究方法,改變了以往哲學思辨及詮釋的方法,注重田野工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建構。教育人類學研究不是從概念出發或沿用以往的解釋套路,而是依據田野工作中與調查對象共同生活所進行的參與觀察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并使之與文化背景聯系來加以分析和闡釋。“教育的田野”賦予研究鮮活的生命和時代意義,記錄了社會文化下真實而豐富的教育發展,它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愈益散發出特有的時代價值。
三、踐行?做小?求真:教育人類學研究范式的科研精神
從書齋走向田野為教育人類學提供了一個從歷史發展高度全方位考察教育發展的新方法和新維度,其科研精神體現為如下幾點:
(一)躬行實踐,深入田野
20世紀初,部分人類學家意識到要想創造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須像其他科學家研究他們的對象那樣來研究自己的對象。為了更準確地對文化進行描述,他們便開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觀察并參與他們的某些重要事務,并向土著詳細詢問他們的風俗習慣,就這樣人類學開始了它的田野調查。作為人類學的分支學科,教育人類學強調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主張深入田野,進行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深入“田野”,才會不斷創新,不斷發展;不進行調查,只顧埋頭于故紙堆里,就會因失去科研的源泉,致使創新干涸、枯竭。教育人類學研究者要進入校園、課堂、社區與家庭,與研究者長時間地交往、接觸,如有機會還要多參加一些地方的民俗活動,以更好地了解當地的文化背景。在調查過程中,研究者要以一個人類學家獨特的視角,以一定的身份,如一名老師的身份或輔導員的身份,融入教學過程中,參與到學生的活動中。“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是一個教育人類學研究者的終身理念和不懈追求。
(二)知微見著,精益求精
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提出:“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必作于細”。教育人類學研究側重于建立在個人經驗基礎上的個案研究,反對那些毫無個人經驗的宏大敘事。教育人類學主張作于“小”,“小”就是你從任何角度去放大或縮小,都不會變成模糊的視點;從任何局部去撫摩,都是豐潤飽滿的點觸;從任何時間去審視,都能成就經久不衰的優秀作品和完美演繹。“小”是一種厚積薄發的經驗積累,是一種獨辟蹊徑的敏銳角度。也就是說,研究者的研究范圍和研究對象必須是
他能夠親眼觀察到的、親身體驗到的和親自了解到的。在這種經驗基礎上,對個案進行深入調查、分析,最終目的是要由小見大。滕星先生所著《文化變遷與雙語教育――涼山彝族社區教育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文本撰述》一書可以說是國內教育人類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其以四川涼山彝族社區教育為研究對象,對20世紀后50年來語言與教育的社會變遷過程進行了描述,揭示了少數民族在力圖融入現代主流社會、分享現代化社會的權利與成果的同時,試圖保存自己的傳統語言與文化的兩難困境,并從教育人類學者的立場上給予意義上的解釋。之后,國內又有多部教育人類學方面的著作問世,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視個案的研究,充分體現知微見著、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
(三)追求本真,崇尚實學
早期的人類學者根據“野蠻人”或“原始人”的社會文化資料、殖民當局的檔案、旅行家以及傳教士的記述,在“安樂椅”上進行理論建構。人類學集大成者馬林諾夫斯基,一戰期間在新幾內亞進行了為期兩年半的三次田野調查,之后出版了一系列與調查相關的著作。其集田野調查、民族志撰寫、文化功能學說的提出于一身,奠定了科學人類學的規范,同時為崇真尚實的學科精神奠定了基礎。他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去觀察當地發生的人和事。要求融入當地社會,盡量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描述和記錄。教育人類學秉承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通過實地調查有效地搜集研究對象的行為和背景資料,在參與研究對象的各種活動中感知其文化背景,在深入調查中踐行追求本真、崇尚實學的學科精神。教育人類學在中國的迅速發展,與其重視調查的研究范式及學科精神有著必然的聯系,它如一縷清風在國內的教育學研究中掀起一絲的波瀾;又如一塊隕石,厚重而深遠,滌蕩著學術氛圍中的浮躁,代表著學術研究的航標。
四、田野工作的局限:教育人類學研究范式反思
(一)他者的聲音:能否反映真實情況
從書齋到田野,其本意就是盡可能多地接觸并了解研究對象,在這個過程中,強調主位研究(從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的研究)和客位研究(從研究者的角度進行的研究)的結合。基于田野工作,深入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共同生活、學習,在相互接觸和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主位研究的科研價值,最大程度地反映研究對象的真實情況。
但是,田野工作畢竟有其局限性――他者的聲音能否反映真實?我們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人會說:“你怎么相信他們向你陳述的東西?他們向你講述的都是編出來的謊言,除了他們自己這些謊言可以蒙騙所有人。”在調查的過程中,我們也經常地思考,研究者對教育現象或教育問題能夠較好地把握,但是能否真正理解教育現象背后的文化因素就不得而知了。另外,在有些田野工作中,還存在語言不通的情況,這就要求研究者想辦法解決語言障礙。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途徑,一是掌握這門語言,二是通過翻譯。在短時間內學習一門新的語言顯然是比較困難的,在筆者周圍的一些文化人類學研究者,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經常采取雇用當地人為翻譯的做法。這種方法,對調查固然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經過翻譯這中間環節之后,收集的信息可能已經帶有很多翻譯者主觀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研究本身的真實性。教育人類學研究者深入教育第一線與研究對象長時間交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對方的文化,爭取更加扎實的田野工作。但是無論你如何與研究對象和諧共處,你永遠無法擺脫“他者”的身份。
(二)部分與整體:個案的選擇如何具有普遍意義
教育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多是個案研究而非整體研究,這可能與因注重田野而限定了人類學的旨趣有關。由于方法論的特點,即要求參與觀察法,這就注定了研究者只能在某一個地區進行研究,因為對于一個稍大的區域進行研究是比較困難的。在回答“解剖麻雀”的微型調查在科學方法上有什么價值的問題時說:“如果只調查了一個中國農村把所調查的結果就說是中國農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如果說明這只敘述一個中國農村里的農民生活,那是實事求是的,但問題是只敘述一個中國農村的農民生活,有什么意義呢?”實際上,只是把江村調查看作是他進入這個“了解中國社會”領域的開始,他后面的調查和研究成果,如《祿村農田》、《鄉土中國》、《行行重行行》等,都是把微型研究和宏觀研究相結合,用比較的方法從局部走向整體的結果,以此來反映中國社會的全貌。
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6
審美人類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近年來在國內當代美學、文藝學以及人類學領域中值得關注的動態之一。從現代知識體系不斷互滲和融通的學術背景來看,審美人類學作為一門復合型交叉性學科,是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有效整合美學與人類學并超越其各自的局限性,激揚學科新質的有力 嘗試,同時也是深入探討審美與現實生活以及歷史進步之間關系的必然要求。
在學理上,審美人類學嘗試理清審美現象與其他文化現象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將對審美和藝術進行考察的重點聚集在特定的審美感知和活動得以形成的社會文化機制上,亦即探討人們在關于“什么是美”以及“如何審美”方面所形成的觀念和實踐是如何被建構和規范起來的,“美”又是如何在這種建構中被遮蔽和顯現的。這就必然要求在尋找美學與人類學之間深層契合點的基礎上,研究當今的文化事實,探討“美”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不同表現形態、特征、功能以及造成“美”的復雜性和特殊性的深層原因,并將關于異質文化或“他者”的研究與當代文化危機的思考結合起來,從而建構一種更加富于平衡感的審美文化觀念。
從嚴格意義上說,審美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國外大約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在西方,關于美學與人類學交叉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人類學美學”、“美學人類學”、“審美人類學”名稱出現的研究群體,一些圍繞以人類學研究方法開拓新的研究藝術的方向以及關注非西方族群的審美偏好等問題的相關著述相繼問世,并引發了一系列關于人類學與美學交叉研究的前沿論題。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學者在深入理解國內外美學與人類學著述,了解并反思當代美學與人類學前沿問題的基礎上,努力發掘這兩門學科的深層契合點,并通過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激發其生長性,審美人類學在國內才得以形成。
近年來,國內審美人類學建構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深入開展:一是研究美學與人類學的關系問題,整合二者的思想資源和研究成果;二是在學理上對審美人類學的學術淵源、學科定位、主要任務、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意義及其發展向度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三是發掘和闡釋國內外人類學與美學著述中的審美人類學思想;關注過去被忽略的或未被充分重視的文化現象和審美經驗,激活其理論生長空間,并通過選擇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區域族群文化以及能夠充分體現當代審美文化新質的個案,運用田野調查和理論闡釋的方法探討審美現象的復雜性及其深層的社會根源;四是在一些院系開設“審美人類學研究”課程,初步形成大學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的審美人類學人才培養序列,并將“審美人類學”切實納入學科形態的現代轉型之中。從國內近幾年發表的著述來看,審美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學術理念和田野實踐在國內學術界已獲得了較廣泛的支持和響應,充分顯現了審美人類學可觀的學術發展前景。 二
從根本上而言,在國內學界提出建設審美人類學,與傳統美學和中國美學研究中出現危機這一事實直接相關,如何為美學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尋找出路便成為當代美學研究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美學的概念體系需要更新,美學研究要向實證的方向發展,要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審美問題,這已經成為一部分美學研究者的共識。學者們在探討美學發展的出路時,愈益發現美學與人類學的交叉互滲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兩者的結合不僅具有深厚的學理基礎,而且首先是現實提出的要求。
美學與人類學之間存在著漫長的歷史聯系。盡管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產生比美學晚了將近一個世紀,但美學誕生伊始就天然地潛藏著濃厚的人類學性質。早在18世紀上半葉,維柯就通過對原始思維的研究提出了“詩性的智慧”,并指出它是實現人與人之間深刻交流的媒介;康德在完成批判哲學體系和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我應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這三大問題之后補充了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問題——“人是什么”,并以人類學研究作為三大批判的某種總結;席勒在對美和藝術的人類學基礎、人類學屬性、人類學結構、人類學功能和人類學特征等問題進行研究的基礎上進而探討人如何通過審美的方式才能成為人性完整的、真正的、自由的人。黑格爾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格羅塞具體考察了原始民族的人體裝飾、裝潢、造型藝術、舞蹈、詩歌、音樂等藝術類型,有力地揭示了審美和藝術的人類性和社會性;馬克思通過人類學批判將三種主要的社會形態進行嚴格的區分,同時把握它們之間的分離和連續性等等。無論是在美學體系的建構還是具體的審美問題研究中,人類學都不只是作為一種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種根本性的精神在其中發揮作用,為美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和重要思路。尤其是到了20世紀,美學與人類學都經歷了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后現代形態的轉變,即從對先驗性、普遍性、同一性、絕對性的宏大敘事轉向對文化的具體性、差異性、多樣性、特殊性等方面的關注和發掘。這使得美學與人類學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和頻繁,二者在20世紀下半葉出現了相互融合的傾向。在此過程中,審美人類學以其高度的學科際屬性和不斷磨練的敏銳的田野洞察力,為探討美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自何處、美學基本范疇的合法性、西方美學普適性神話何以走向衰微等問題提供了獨特的批判視角和廣闊的經驗解讀空間。
第一,美學是關于“美”的學科,然而,“美”意指什么,“美”是如何被建構的,“美”從何處尋等問題不是單憑對“美”的抽象玄思就可以解決的。“美”與現實生活的關系是一個首先應當被追問的問題。審美人類學要求深入到對審美和藝術存在于其中并發揮作用的文化脈絡和意義系統之中,以來源于日常生活的細膩觀察和敘事代替社會與文化的宏大理論,強調語境研究勝于對藝術風格的分析和分類,注重事實材料與理論推導的結合,使美學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找到新的觀察視角和闡釋基礎,在藝術與社會的關系及邊界上提出問題,對于傳統美學和藝術哲學的形而上學本質主義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糾偏作用,并將為關于藝術的起源、審美現象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審美偏好的變化及其原因等問題的分析和闡釋提供重要的現實依據。
第二,西方傳統美學將美學研究局囿于對“美”的本質主義探討,尤其是到了19世紀中葉,aesthetic作為“美”的定義已經非常普遍,通常與藝術有緊密的關聯。然而,審美人類學研究表明,對“美”和藝術的宗教式態度是美學話語自身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們將審美等同于“美的”,那么,就會有大部分的審美生產和接受會被排斥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之外。而只要我們把對藝術作品的審美經驗等同于對美的感知,那么,將“審美”這個詞語運用于民族學研究領域以及一般社會學中則會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學應當為各種感知的經驗和審美的領域留有一定的研究空間,這種感知經驗不僅包括“美的”事物,而且包括丑陋藝術、喜劇、悲劇及其他。于此,對“美”與“藝術”概念和范疇合法性的考察,從根本上說就是關于文化書寫如何向文本書寫轉化的問題。
第三,人類學研究表明,在人們“以什么為美”以及“如何表現美”的方式上存在著很大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僅是以語言和文字等文本的方式書寫,而且也是以政治經濟體制、習俗、慣例、親屬制度、宗教、神話、藝術、禁忌、倫理、世界觀、天文歷法、祭禮儀式等社會生活中可觀察的和不可觀察的地方性知識的文化書寫方式寫成的。如果沒有對這些地方性知識的了解和考察,我們如何能夠理解那些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長期習得的信仰十分相異的審美和藝術現象?然而,大部分西方美學話語和理論模式在被移植到非西方文化研究的過程中,由于還沒有經過語境的具體轉化,理論的架空往往造成對非西方社會想象和闡釋的混亂,這種混亂不僅無益于對日漸豐富、復雜的現實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非西方文化自身的問題及其獨特的審美及其表達方式。審美人類學通過借鑒人類學的文化整體觀、跨文化比較、主位客位轉換、動態演化與文化相對論視角等研究理念和方法對非西方族群的審美文化現象進行的深度描繪,極大地挑戰了西方美學原有的意識形態,即以二元對立為潛在邏輯,以抽象思辨為思維特征,以建構形而上的宏大敘事為目標的西方傳統美學代表美學發展的方向和基本模式這一神話將在“他者的目光”中被質詢。 三
審美是人類文化活動中最精妙的部分,人類學研究側重分析文化的存在樣態及其基本運作機制,美學善于從文化批判的角度把握這些文化事實之間的微妙聯系,兩者具有天然互補性:一方面,由于人類學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特殊而復雜的政治、歷史、文化原因,走向文化批判的人類學盡管將意識形態作為其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但如何真正消除意識形態幻象的遮蔽性僅僅依靠人類學自身是無法完成的;另一方面,盡管美學可以細致地描述一種審美狀態,但它卻無法想象自身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至此,問題的關鍵和難點在于,審美人類學如何在美學與人類學的深層契合處發掘其理論生長點,而美學的現代性也將獲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