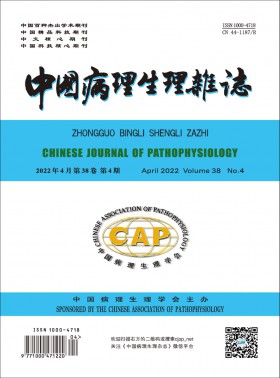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病理學報告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病理學報告范文1
高雪氏病(gaucher disease)罕見,作者發現1例,報告如下。
1 病例資料
患者 女,52歲,發現脾腫大4月余,未作治療。查體:一般情況可;牙齦出血;淋巴結無腫大;肝肋下未及,脾肋下5cm;體溫36.5℃;RBC 3.96×1012/L,Hb 111g/L,WBC 3.90×109/L,PLT 57×109/L,RET 1.3%,MCV 83.3fl,MCH 28pg,MCHC 336g/L,HCT 33%,中性粒細胞79.7%,嗜酸性粒細胞0.7%,淋巴細胞16%,單核細胞3.6%,ESR 35mm/h。該患者年輕的時候有震顫麻痹癥,外傷時皮膚有色素沉著,8年前發現脾輕度大,現達肋下5cm,血小板最近降低,牙齦出血。骨髓檢查:涂片易見高雪氏細胞,尤以涂片邊緣和尾部居多,分類,其中一張涂片達875只高雪氏細胞,其形態特征:胞體較大,呈圓形、卵圓形、多邊形或不規則形;胞核相對較小,圓形或卵圓形,多偏位,單個核居多,也可見2~3個核,染色質較粗;胞漿多,呈淡藍色,有很多粗暗的波紋狀結構或纖維樣細絲,排列如蜘蛛網或洋蔥皮樣;經過碘酸-雪夫(PAS)、酸性磷酸酶(ACP)染色,結果均為強陽性。做CD41免疫化學染色,結果為陰性(巨核細胞和血小板顯示為陽性)。診斷為高雪氏病,建議脾穿刺做病理學檢查。
2 討論
高雪氏病又稱戈謝病,為罕見疾病,Gaucher于1882年首先報道一例慢性型病例而得名。高雪氏病多見于猶太人中,黃種人罕見,國內報道少[1]。高雪氏病系一種先天性、家族性類脂質代謝障礙病,為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有報道兄弟二人同患高雪氏病[2]。由于β-葡萄糖腦苷脂酶的遺傳性缺陷,導致單核-巨噬細胞系統的細胞內大量葡萄糖腦苷脂堆積,造成肝脾腫大、骨髓受累等臨床表現,特別是脾臟更易受累。目前已知控制β-葡萄糖腦苷脂酶的基因在第一對染色體上[3]。
由于高雪氏病發病年齡和臟器受累的程度不同,臨床癥狀差異大,可分為三種類型:(1)嬰兒型(又稱急性型、嬰兒神經病變型):出生時發育正常,6個月左右出現食欲不振,發育停滯,此后病情進展迅速,出現肝脾腫大、肌張力亢進,或出現痙攣,足弓反張,最后出現吞咽、呼吸困難,大多于發病后2年內死亡;(2)幼年型(又稱慢性型、亞急性神經病變型):此型較多見,多于學齡前發病,脾腫大及貧血常為首發體征及癥狀,神經系統癥狀不及急性型嚴重,常僅有行動異常、智力減低、震顫等,病程進展甚緩慢,可存活至20歲,亦可因感染、出血等并發癥死亡;(3)成人型(又稱慢性成人型):嬰兒至成人期均可發病,主要臨床表現為發育不良和肝脾巨大,無神經系統癥狀,因脾亢而導致貧血或出血,皮膚露出部位可出現黃褐素沉著和眼球結膜黃斑,骨損害廣泛,尤以股骨下端為甚,可出現皮質變薄、骨質疏松、下端膨大、似“長頸瓶”狀,病情進展極其緩慢,多數病例能夠維持數十年[1]。本病例為成人型。
高雪氏病罕見,診斷宜謹慎,尤其是年齡大的患者。骨髓涂片當中出現少量高雪氏細胞時,更多的可能是其他情況。譚春艷等[4]觀察94例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涂片,結果有29例發現類高雪氏細胞。作者也曾在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標本中發現過類高雪氏細胞。陸續有報道在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何杰氏病、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地中海貧血、漿細胞骨髓瘤等病例中發現類高雪氏細胞[5],然而,這些疾病的臨床表現以及骨髓象和高雪氏病還是有較大的區別。高雪氏病的骨髓涂片上高雪氏細胞數量多、形態典型,而其他疾病類高雪氏細胞的數量一般為偶見,且往往有其他系列細胞的異常。也有報道高雪氏病可合并其它疾病[6]。
當臨床表現符合且骨髓象典型時,可考慮高雪氏病,血清酸性磷酸酶增高可協助診斷[3]。骨髓和脾穿刺涂片找到并確定是高雪氏細胞時可診斷為高雪氏病。
參考文獻
1 王振法著.楊崇禮審.血液學診斷及圖譜.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258.
2 蔡勇輝.兄弟二人同患高雪氏病報告.罕見疾病雜志,2001,8(2):19.
3 盧興國主編.骨髓細胞學和病理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884.
4 譚春艷,任詠薇,覃桂芳,等.類高雪氏細胞在慢性粒細胞白血病中的意義.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01,11(12):31.
病理學報告范文2
[中圖分類號] R692[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674-4721(2014)03(c)-0139-02
IgA腎病是腎小球系膜病變的一個特殊類型,指IgA或以IgA為主的免疫球蛋白彌漫沉積在腎小球系膜區及毛細血管袢引起的一系列臨床癥狀及病理改變。除IgA腎病外,一些其他的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合并IgA在腎小球系膜區的沉積及相應的臨床癥狀。因此,在確診IgA腎病前,需排除過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 purpura,HSP)、肝硬化、系統性紅斑狼瘡等疾病所致的繼發性IgA腎病。白細胞碎裂性血管炎(cutaneous leukocytoclastic vasculitis,LCV)即為皮膚小血管炎,是皮膚血管炎中最常見的類型。LCV是一種免疫復合物疾病,其發病機制是免疫復合物沉積在皮膚小血管上。LCV患者的腎臟受累多見于HSP(一般非IgA相關性LCV常不發生)。IgA腎病合并LCV臨床罕見,國內外未見報道,現報告一例如下。
1 臨床資料
患者,女,27歲,以“反復雙下肢水腫5個月,發現尿檢異常2個月,雙下肢紅斑、水皰1個月”為主訴,于2013年9月22日入院,患者肥胖,既往6~7年曾口服多種減肥藥,7個月前口服泰國某減肥藥物1月余,5個月前勞累后出現腳踝及顏面部水腫,休息后可以緩解,2個月前因左足背皮疹就診于當地醫院,診斷為濕疹,給予匹多莫得口服及外用軟膏(具體不詳)治療,當時尿常規檢測示尿蛋白3+,未系統診治。1個月前,患者于戶外納涼、進食海鮮后次日,出現雙下肢對稱性散在紅斑,壓之不褪色,逐漸蔓延至雙側大腿及腰部,紅斑逐漸融合,形成水皰,破潰。無腹痛及黑便,就診于當地醫院,查尿蛋白(++),診斷為血管炎?為求進一步診治,于2013年9月22日入本院皮膚科。既往否認肝炎、結核病史,否認高血壓、糖尿病病史,否認家族成員有類似病史。入院后查體:T 36.8℃,P 100/min,R 18/min,血壓122/84 mm Hg。神清語明,呼吸平穩,步入病房,查體合作。下頜、頸部、腋下、腹股溝淺表淋巴結未觸及。咽不赤,雙肺呼吸音清,未聞及干濕性音,心音純,律整,心率100/min,未聞及病理性雜音,腹平軟,無壓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觸及,雙下肢無水腫。皮膚科查體:雙下肢見較多瘀斑、部分有壞死和水皰。入院后完善檢查:尿PRO(+++),α1-MG 35.30 mg/L,MA 4540.00 mg/L,IgU 394.00 mg/L,TRU 288.00 mg/L;24 h尿蛋白定量6.796、4.001、4.329、3.810 g;尿Glu(++++);血WBC 8.30×109/L,HGB 134 g/L,PLT 288×109/L;EO 100×106/L,IgE 34.75 IU/ml,ALT 110 U/L,GGT 91 U/L,ALB 33.9 g/L,AST 51 U/L;Fg 4.69 g/L,Cr 45 μmol/L,K+ 3.89 mmol/L,鈣2.09 mmol/L,磷1.28 mmol/L;CRP 10 mg/L,C4 0.44 g/L,IgG 16.90 g/L,IgA 5.40 g/L,IgM 3.51 g/L;CD4 1143個/μl。0 min Glu 8.65 mmol/L,CPS 1545.48 pmol/L,IRI 21.79 mIU/L;120 min Glu 13.27 mmol/L,CPS 2105.03 pmol/L,IRI 21.03 mIU/L。HbA1c 9.10%。TG 5.34 mmol/L,TC 7.58 mmol/L,LDL-C 4.85 mmol/L。肝炎四項、ANCA、ANA組合3、風濕抗體系列、免疫固定電泳、血κ、λ輕鏈、甲功甲炎無異常。大便隱血陰性。心電圖:竇性心律,下壁導聯異常Q波,建議行心電多功能檢查。超聲示:脂肪肝,脾稍大。肺CT未見異常。入院后對癥調節免疫、抗感染及保肝治療,9月23日右小腿行病理檢查:LCV,真皮淺層C3血管陽性,IgA、IgG、IgM陰性。10月1日開始甲強龍40 mg,1次/d靜脈點滴,甲潑尼龍8 mg晚一次口服,輔以鈣劑及胃黏膜保護劑。10月10日行腎活檢,病理檢查示:IgA腎病,Lee分級Ⅱ(牛津分型M0E1S1T0)IgA(+++)、C3(+++)團塊狀沉積于系膜區IgM(+)、Fg(+)、IgG(-)、C1q(-),10月15日由皮膚科轉入本科。診斷:IgA腎病、Lee分級Ⅱ、LCV、肥胖癥、糖尿病。因患者血糖偏高,給予阿卡波糖及二甲雙胍餐中嚼服降糖,空腹血糖7~9 mmol/L,餐后血糖9~13 mmol/L。于10月18日開始給予甲強龍500 mg,1次/d靜脈點滴(連用3 d),序貫潑尼松60 mg晨起頓服。腎活檢術后復查雙腎超聲無異常,加用低分子肝素鈣注射液及雙嘧達莫抗凝治療。患者病情平穩,帶藥出院。院外繼續口服潑尼松60 mg,定期門診隨訪,激素規律減量,體重及血糖控制良好,周身無新鮮皮疹出現,尿蛋白定量逐漸減少,水腫逐漸消退,目前仍在隨訪中。
2 討論
本例患者為年輕女性,最初表現為顏面部及腳踝水腫,后因左足背皮疹就診時發現蛋白尿,進而出現雙下肢對稱性散在紅斑,逐漸蔓延至雙側大腿及腰部,紅斑逐漸融合,形成水皰,破潰。臨床表現為皮膚及腎臟均有受累,不能除外全身系統性疾病所致。為進一步明確診斷,行皮膚活檢及腎活檢。皮膚活檢示:LCV、真皮淺層C3血管陽性,IgA、IgG、IgM陰性。腎臟病理示:IgA腎病、Lee分級Ⅱ(牛津分型M0E1S1T0)IgA(+++)、C3(+++),團塊狀沉積于系膜區IgM(+)、Fib(+)、IgG(-)、C1q(-)。LCV即為皮膚小血管炎,是一種免疫復合物疾病,其發病機制是免疫復合物沉積在皮膚小血管上。LCV的腎臟受累多見于HSP中(一般非IgA相關性LCV常不發生)[1]。本例患者的皮膚活檢免疫熒光見:真皮淺層C3血管陽性,IgA、IgG、IgM陰性。非IgA沉積,可以除外HSP,非IgA相關性LCV,通常不引起腎臟受累。IgA腎病是腎小球系膜病變的一個特殊類型,指IgA或以IgA為主的免疫球蛋白彌漫沉積在腎小球系膜區及毛細血管襻引起的一系列臨床癥狀及病理改變。在確診IgA腎病前,需排除HSP、肝硬化、系統性紅斑狼瘡等疾病所致的繼發性IgA腎病[2]。本例中患者可以除外上述原因所致的繼發性IgA腎病。原發性IgA腎病是一免疫病理診斷名稱,年輕人多見,腎臟受累輕重不一,但一般不伴有系統表現[3]。IgA腎病合并LVC病例罕見,國內外尚未見報道,本例患者兼有兩病之特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IgA腎病可能就是系統性血管炎[4],兩者在壞死區域都有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VCAM-1)及纖維蛋白原等細胞因子出現,并且有單核細胞浸潤[5],這些都提示IgA腎病與小血管炎可能有關[6]。國外有ANCA相關性小血管炎(AASV)腎臟有免疫復合物(包括IgA型)沉積的報道[7]。于峰等[8]報道,AASV腎炎伴免疫復合物沉積者8例中有2例為IgA沉積。隨著對此兩類疾病關系的不斷深入研究,臨床上可能會有一類疾病同時表現出兩者的特點,可以用一元論加以解釋,進行綜合治療。也有可能是同時發生的兩種疾病,需要根據尿蛋白定量、腎臟病理改變的輕重及皮損的嚴重程度綜合考慮,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
[參考文獻]
[1]顧有守.白細胞碎裂性血管炎的分類和治療[J].中華皮膚科雜志,2006,39(9):550-552.
[2]腎臟病研究所學術委員會.IgA腎病診斷及治療規范[J].腎臟病與透析腎移植雜志,2004,13(3):253-255.
[3]王海燕.腎臟病學[M].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708-718.
[4]D′Amico G,Napodano P,Ferrario F,et al.Idiopathic IgA nephropathy with segmental necrotizing lesions of the capillary wall[J].Kidney Int,2001,59(2):682-692.
[5]Ferrario F,Rastaldi MP,Napodano P.Morphological features in IgA nephropathy[J].Ann Med Interne,1999,150(2):108-116.
[6]Richer C,Mouthon L,Cohen P,et al.IgA glomerulonephritis associated with microscopic polyangitis or churg-strauss syndrome[J].Clin Nephrol,1999,52(1):47-50.
[7]Neumann I,Regele H,Kain R,et al.Occasional immune deposits in ANCA associated crescentic glomerulonephritis[J].Clin Exp Immunol,2000,(Suppl.1):47.
[8]于峰,趙明輝,鄒萬忠,等.腎臟有免疫復合物沉積的小血管炎的臨床病理特點[J].中華腎臟病雜志,2003,19(4):219-222.
(收稿日期:2014-01-26本文編輯:林利利)
本刊個案報道欄目介紹
以科學、細致的觀察,簡潔、精煉、準確的描述,針對疾病的個體差異及特殊、罕見疾病進行相關報道。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通惠家園惠潤園5-3-602《中國當代醫藥》雜志社
郵編:100025
傳真:010-59679056
病理學報告范文3
關鍵詞:糖尿病腎病;導管感染
糖尿病腎病患者由于蛋白質合成障礙,肌肉總量下降,血清肌酐值不是很高,故著手準備腎臟替代治療的時機往往較晚,這就使得急透插管的患者相對增多。糖尿病腎病患者血管條件差,動靜脈內瘺成熟的時間較長致使臨時導管使用時間延長增加了感染的機會,現將我們臨床中遇到的這樣1例糖尿病腎病血液透析導管感染病例報告如下。
1臨床資料
患者,女,53歲,糖尿病20余年,糖尿病胃輕癱、糖尿病血管病變、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3年,發現肌酐升高(Cr366umol/L)8個月。患者2010年4月27日因血鉀7.83mmol/L,肌酐675umol/L,行臨時右側頸內靜脈置管血液透析治療。于6月23日行左前臂動靜脈造瘺術,但因血管條件差,導絲不能通過,手術未成功,6月25日改行右前臂動靜脈造瘺術。7月23日患者透析結束時出現寒戰,體溫38.5℃,急查血常規:WBC 9.3×109/L,NE% 80.92%,頸內靜脈置管處發紅,無分泌物,留血培養,予泰能控制感染,7月27日停用。7月26日體溫降至37.8℃,透析過程中再次出現寒戰,頸內靜脈置管處紅腫有膿性分泌物,考慮深靜脈置管感染,予拔管并留取管尖及外周血培養。7月28日培養均回報:MRSA,萬古霉素敏感,結合患者肌酐清除率予透后萬古霉素0.5g靜點,靜點3次后,體溫降至正常。7月30日嘗試用動靜脈瘺行血濾,因血流量不足,30min后提前回血時出現皮下血腫,并行右側股靜脈置管建立血透通路。8月4日~8月6日晚間患者低熱37~38℃。8月7日患者右前臂動靜脈瘺口出破潰,伴膿血性分泌物,體溫在38.5~37.7℃,考慮患者在感染MRSA時皮下滲血,在局部形成感染灶,細菌毒素釋放入血而形成全身炎癥反應,MRSA感染可能性大,仍予萬古霉素控制感染,并行右側閉瘺加清創引流術,并留取分泌物培養,結果回報仍為MRSA,故繼續透后靜點萬古霉素。同時用碘伏創口周圍消毒,范圍>5cm,乳酸依沙吖啶溶液紗條引流,無菌紗布覆蓋,2次/d。安爾碘消毒股靜脈置管處2次/d,范圍>10cm,并于透析結束后先用生理鹽水沖管至透亮,再用10mg/ml的萬古霉素按刻度封管,留30min后抽出萬古霉素,再用生理鹽水沖管至透亮,純肝素鈉12500/2ml,按刻度封管。清創第2d體溫正常,3d血常規正常,1w后復查創口處分泌物培養轉陰。
2 體會
2.1盡早準備動靜脈內瘺 糖尿病腎病患者血清肌酐值不能準確反應疾病的嚴重程度,所以應盡早著手準備腎臟替代治療,Ccr10~15ml/min[SCr>442umol/L]就可以作為透析治療的指征[1]。自體性動靜脈內瘺是最理想的選擇,但對于糖尿病腎病患者來說,由于廣泛糖尿病血管病變,使動-靜脈內瘺的失敗率高達30%~40%[2],所以較早進行動靜脈內瘺吻合術,給動靜脈內瘺有足夠的成熟期(8~12w),可以避免急透插管相應的減少感染機會。
2.2臨時性中心靜脈導管留置時間 臨床上對于部分未提前準備透析通路而需要緊急透析的患者往往選擇中心靜脈置管。導管的出口與血管比較近,細菌容易進血,插管在7~9d內會產生細菌移位生長,并隨著留置時間的延長感染機會增加。故導管留置時間需要嚴格掌握,并做好護理工作,對于感染導管血培養轉陰才可置入新導管。
2.3動靜脈內瘺的穿刺 成功的內瘺應嚴格無菌操作,力爭一針見血,避免發生感染、血腫等并發癥。術后4w盡可能避免使用內瘺,如必須使用,應爭取一次穿刺成功,且穿刺點不宜離吻合口太近,同時在對側選一條靜脈通路做為血液回路。菌血癥時盡可能不用內瘺,以防局部血腫造成感染。
2.4透析方式的選擇 血液透析仍是糖尿病終末期腎病患者最常用的治療方法。血液透析較腹膜透析充分、技術存活率高,但保存殘余腎功能差、存在血管通路問題。透析登記資料比較血透和腹透的存活率發現,透析開始前2年腹透患者的存活率優于血透患者,而隨著時間的延長,血透患者的存活率超過腹透患者,因此,對于ESRD患者的一體化治療提倡首選腹透治療然后再適時轉向血透。有學者還提出對于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患者可以行5~6次/w腹膜透析加一次血液透析治療[3]。
3結論
2008年USRDS報道,原發病為糖尿病的維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的5年生存率僅0.25~0.27,顯著低于原發病為慢性腎小球疾病者(0.42~0.44年)[1]。主要是由于糖尿病腎病患者血管條件差血透通路建立困難,并發癥多,容易感染,抵抗力低等。所以,對糖尿病要早發現、早治療、延緩腎損害。一旦出現腎功能不全要早做評估、早期建立合適的透析通路、早行替代治療,對于血液透析患者要嚴格管理透析通路,防止感染的發生。
糖尿病腎病患者多為中老年患者,并發癥較多,護理難度大。因此,做好有效的護理能使透析并發癥減少,并減少心血管疾病及感染的發生。預防和護理是糖尿病腎病維持性血液透析,降低病死率、改善預后的關鍵。 患者的健康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需要患者、醫生、護士及家屬的全面配合。而護士與患者及家屬的接觸最多,應做好溝通協調工作,使患者能積極主動配合治療,提高其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謝紅浪,劉志紅,季大璽,等. 糖尿病腎病維持性血液透析長期生存率及其相關因素分析[J].腎臟病與透析腎移植雜志,17(5):401-408.
病理學報告范文4
過去認為,缺血性腎臟病多發生于老年患者,但由于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影響,青年人缺血性腎臟病已不少見,現將本院2007年下半年收治的3例病例報告如下。
1 病例摘要
病例1,患者女,44歲,血壓升高10年,血糖升高1個月余。BP 180/85 mm Hg(1 mm Hg=0.133 KPa),尿潛血+++,蛋白+++,尿蛋白定量1.9 g/24 h,總膽固醇6.68 mmol/L(2.33~5.17mmol/L),三酰甘油5.77 mmol/L(0.38~1.62),血肌酐41.62 μmol/L(38~133 μmol/L),空腹血糖9.42 mmol/L,餐后2 h血糖17.36 mmol/L,眼底檢查:小動脈變細。腎活體組織穿刺結果:輕度系膜增生性IgA腎病伴缺血性腎損傷。給予降壓、調脂、降糖對癥治療18 d,血壓控制在130~135/70~80 mm Hg,空腹血糖6.0 mmol/L,餐后2 h血糖7.0 mml/L,24 h尿蛋白定量1.5 g。
病例2,患者女,38歲,體質量90 kg,間斷腰痛、雙下肢水腫10余年,夜尿增多2個月。BP 175/116 mm Hg,雙側眼瞼、雙下肢水腫。尿潛血+,蛋白+++,尿蛋白定量4.06 g/24 h,總膽固醇4.61 mmol/L,三酰甘油9.23 mmol/L,空腹血糖6.49 mmol/L,餐后2 h血糖9.84 mmol/L,腎活體組織穿刺結果:結合臨床符合肥胖相關性FSGS伴缺血性腎損傷。給予降壓、減少尿蛋白、調脂,控制血糖治療。住院60 d,患者空腹血糖5.3 mmol/L,餐后2 h血糖6.1 mmol/L,血壓130~135/70~80 mm Hg。
病例3,患者男,34歲,尿檢發現紅細胞1年。BP 140/90 mm Hg。尿蛋白:+-,紅細胞+++,總膽固醇4.11 mmol/L,三酰甘油3.01 mmol/L,血肌酐133.64 umol/L,尿酸520.92 umol/L,24 h尿蛋白定量0.5 g,腎活體組織穿刺結果符合:缺血性腎臟病。給予調脂、保護腎功能等對癥治療,住院20 d,復查血肌酐129 μmol/L,腎功能穩定。
2 討論
慢性缺血性腎病是一類因腎動脈狹窄或阻塞,腎血流動力學顯著變化而致腎小球濾過率降低,腎功能不全的慢性腎臟疾病。腎動脈主干及其分支狹窄是引起慢性缺血性腎病的主要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原因。任何一種原因引起的腎小球之前的大、中、小各級動脈病變均可引起本類疾病,近年來更重視引起腎內各級小動脈病變導致的慢性缺血性腎損傷,如高血壓引起小動脈腎硬化、糖尿病微血管病變以及某些腎臟疾病(IgA腎病、特發性膜性腎病和原發性腎小球局灶節段腎小球硬化癥)的血管病變等[1]。與動脈硬化有關的因素如高血壓、高血脂、吸煙、肥胖等更進一步加重缺血性腎臟病[2]。本報道中3例患者均存在不程度的血糖、血脂、血壓異常,存在缺血性腎臟病的易發因素。有學者研究指出,代謝綜合征中各因子并存較各因子單獨存在的慢性腎損害的危險性增加[3]。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某些現代生活方式的不良影響,缺血性腎臟病發病率上升成為必然,青年人缺血性腎臟病應引起重視,如何改進生活方式,制定合理的飲食方案,應成為社會研究的熱點。
參考文獻
[1] Greco BA , Breyer JA. Artherosclerotic ischemic renal disease. Am J Kidney Dis , 1997,29 :167-1871.
病理學報告范文5
關鍵詞:中醫特色護理;脈脹;高血壓病;預防保健
高血壓病是指血液在流動時對血管壁產生的壓力持續高于正常水平的現象,其發病多無明顯癥狀,由于血管壁長期承受較高壓力,易導致腦卒中、冠心病等嚴重心腦血管疾病[1]。高血壓病雖不可治愈但卻可控制,臨床西醫常以降壓藥物來治療高血壓病,但部分患者常因認知不足、服藥依從性差、日常生活行為習慣不佳等因素導致血壓控制不穩,甚至惡化[2]。中醫認為高血壓病屬“脈脹”范疇,可因外感六、內傷七情、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自然衰老等多種因素起病,多為本虛標實之證,中醫藥治療高血壓病療效肯定,廣受醫患認可[3,4]。高血壓病為慢性、終身性疾病,其護理與治療并重。中醫特色護理以中醫理論為基礎,運用傳統中醫藥技術和方法,基于整體觀念予以辨證施護,從而保護人群健康,具操作簡便、費用低、適用性廣等特點[5]。基于此,本研究對高血壓病實施中醫特色護理,并設計隨機對照試驗探究其應用效果,為臨床實踐提供一定參考。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研究通過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選取2018年8月—2020年8月廣州市番禺區何賢紀念醫院收治的高血壓病患者為研究對象。共入組120例,隨機(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60例。2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可比性強。見表1。1.2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①符合高血壓病診斷標準,高血壓病分級為1~2級;②高血壓病病史超過1年,需長期服用降壓藥控制血壓;③年齡<80歲;④可自理生活;⑤知情同意參與研究,且配合度高。排除標準:①繼發性高血壓病者;②合并肝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及其他嚴重心血管疾病者;③合并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礙者。1.3干預方法2組均予以常規降壓/控壓藥物治療,期間停止其他降壓治療行為,治療6個月后門診復診,接受相關測評。對照組接受常規護理,包括用藥指導、飲食指導、鍛煉指導、健康教育、心理疏導、定期隨訪等。觀察組接受中醫特色護理,具體為:①膳食護理。依高血壓病患者的證型予以個性化膳食指導,合理選用山藥、粳米、紅棗、海帶、芹菜、山楂、綠豆、天麻、決明子、何首烏、葛根粉等常見食材和藥材,肝陽上亢者多用決明子、山楂、綠豆、葛根粉、芹菜等等偏涼性食物以平肝潛陽;腎精不足者多用山藥、何首烏可固精益腎;氣血虧虛者多食山藥紅棗粥來補血益氣;痰濁中阻者可以海帶天麻湯來化痰清濁。②情志護理。按中醫五步法(測情、順志、移氣、施術、收氣)實施情志護理,通過和患者聊天來了解其病因,依據患者個性及具體病情擬定護理方法,采取音樂理療、按摩等方法進行情志疏導。③中醫技術護理。依據具體病情予以耳穴壓貼治療或足部穴位按摩,患者可根據自身適應性選擇其一,由專業人員指導患者掌握操作方法,患者每日自行按壓。④健身氣功。由專業人員指導患者學習并掌握太極拳和八段錦,發送教學視頻方便患者跟練,每日早晚進行。1.4觀察指標①血壓控制。使用電子血壓計測量2組干預前后收縮壓(SBP)、舒張壓(DBP)。②心理狀態。使用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評估2組干預前后心理狀態[6]。SAS、SDS均包含20條目,采用Likert4級評分,患者自評癥狀出現頻度由低至高分別記1、2、3、4分,各條目得分之和為粗分,將粗分轉化為標準分(標準分=粗分×1.25后取整數部分,0~100分)后作為最終評分,其中SAS<50分、SDS<53分為正常狀態,SAS、SDS的評分越高提示患者焦慮、抑郁情緒越嚴重。③心腦血管事件發生情況。記錄2組6個月隨訪期內心絞痛、腦梗死等心腦血管時間發生情況。④生活質量。使用高血壓病患者生命質量測定量表(QLICD-HY)V2.0評估2組干預前后生活質量。QLICD-HY共46條目,分為軀體功能(10條目)、心理功能(11條目)、社會功能(8條目)、高血壓病特異模塊(17條目)共4個領域,采用5點等距評分法(記1、2、3、4、5分),各領域粗分為該領域條目評分之和,隨后用極差變換法將粗分轉化為標準分(0~100分)作為該領域最終評分,評分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質量越高。1.5統計學方法使用統計學軟件SPSS22.0處理與分析研究數據。計量資料均符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記作(x珋±s),行配對t檢驗或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記作%,行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概率法。均以α=0.05為檢驗水準,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血壓控制2組干預前SBP、DBP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干預后SBP、DBP均明顯降低(P<0.05),且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SBP、DBP均更低,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2.2心理狀態2組干預前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干預后SAS、SDS評分均下降(P<0.05);且觀察組干預后SAS、SDS評分均較對照組更低(P<0.05)。見表3。2.3心腦血管事件發生情況在6個月隨訪期內,觀察組發生心絞痛1例,心腦血管事件發生率為1.67%(1/60),對照組發生腦梗死2例、心絞痛6例,心腦血管事件發生率為13.33%(8/60),組間比較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33,P值為Fisher精確概率法結果)。2.4生活質量干預前,2組QLICD-HY的各領域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干預后QLICD-HY在軀體功能領域、心理功能領域、高血壓病特異模塊領域上的評分均明顯升高(P<0.05),社會功能領域評分則無明顯提升(P>0.05);且觀察組干預后在軀體功能領域、心理功能領域、高血壓病特異模塊領域上的評分較對照組更高(P<0.05)。見表4。
3討論
病理學報告范文6
【關鍵詞】 白血病,粒細胞,急性;骨痛
1 病例簡介
患者,男,25歲,因多處骨痛9天入院。入院前9天無誘因先后出現腰部、兩肩胛及前胸部疼痛,呈持續性脹痛,陣發性加劇。無畏寒、發熱、鼻衄、牙齦出血、皮膚瘀斑及關節腫痛等癥狀,無外傷史。病后曾服非甾體解熱鎮痛藥、中草藥等治療,病狀未緩解。體檢(PE):T 37℃,P72次/min,R 28次/min,BP 15.96/10.64kPa,神清,呈急性痛苦面容。全身皮膚黏膜無黃染、出血點、瘀斑,淺表淋巴結無腫大,牙齦無腫脹,腰椎、兩肩胛及胸骨明顯壓痛,尤以胸骨中、下段明顯。心肺未見異常,腹部平軟,肝、脾無腫大。雙下肢無水腫。外周血象:Hb 127g/L,WBC 11.5×109/L,PLT 218×109/L,心肌酶譜:AST 36u/L、LDH 1 604u/L、CK 349u/L、CKMB 15u/L,血沉36mm/h,肝、腎及凝血功能未見異常,胸部及腰椎X線、心電圖、腹部B超、心臟超聲心動圖檢查正常。因查找不出多處骨痛的原因,而行骨髓穿刺涂片,作細胞形態學分析見:原始粒細胞占35%、早幼粒細胞占21%,確診為急性粒細胞性白血病(AML-M2型),而轉上級醫院行骨髓移植治療。
2 討論
急性白血病是造血干細胞的惡性克隆性疾病,發病時骨髓中異常的原始細胞及幼稚細胞(白血病細胞)大量增殖并抑制正常造血,廣泛浸潤肝、脾、淋巴結等各種臟器。臨床表現為貧血、出血、感染、淋巴結肝脾腫大,外周血白細胞多數明顯增多,血小板多數減少。該患者以劇烈的多處骨痛為首發臨床表現,而無貧血、出血、感染征象,無肝、脾、淋巴結腫大,外周血象未見明顯異常,最后經行骨髓穿刺涂片細胞學分析方確診為急性粒細胞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骨痛的原因:①白血病細胞影響骨膜;②不明原因的骨梗死和骨髓壞死;③高尿酸血癥致痛風發作;④溶骨性粒細胞肉瘤等[1]。本例患者可能與①、②點有關。臨床上這種僅僅以多處骨痛為首發臨床表現的急性粒細胞性白血病較少見,易造成誤診。因此對臨床上遇到不明原因的多處骨痛患者,要考慮到急性白血病的可能,應及早行骨髓穿刺涂片細胞學分析及外周血涂片細胞分類等檢查,以免造成過長時間的誤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