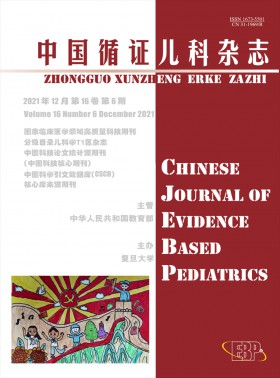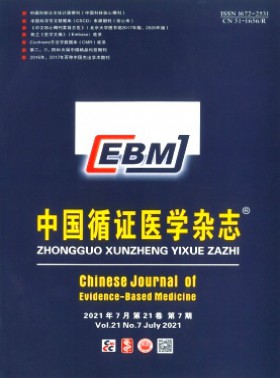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循證醫學依據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循證醫學依據范文1
[DOI]10.13939/ki.zgsc.2015.13.113
循證醫學概念的提出是人們對現代醫藥的單純根據病理生理機制指導臨床治療狀況的一種反思,它提倡的是最好的臨床研究證據與臨床實踐(臨床經驗、臨床決策)以及患者價值觀(關注,期望,需求)的結合。因此,今后的醫生,將不僅僅承擔著診治病人的職責,還將兼有醫學科學研究的重任。而如何高效快捷地獲得大量數據,科學準備地處理大量數據,使之為臨床科研提供實驗數據支持?當信息技術領域迎來大數據浪潮之際,醫院信息系統的發展也勢必將推動循證醫學步入大數據時代。
1循證醫學
1.1定義
循證醫學的主要創始人、國際著名臨床流行病學家DavidSackett曾將循證醫學定義為:“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所能獲得的最好研究證據來確定患者治療措施。”根據這一定義,循證醫學要求臨床醫師認真、明確和合理應用現有最好的證據來決定具體病人的醫療處理,作出準確的診斷,選擇最佳的治療方法,爭取最好的效果和預后。循證醫學的最新定義為:“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目前可獲取的最佳研究證據,同時結合臨床醫師個人的專業技能和長期臨床經驗,考慮患者的價值觀和意愿,完美地將三者結合在一起,制定出具體的治療方案。”顯然,現代循證醫學要求臨床醫師既要努力尋找和獲取最佳的研究證據,又要結合個人的專業知識包括疾病發生和演變的病理生理學理論以及個人的臨床工作經驗,結合他人(包括專家)的意見和研究結果;既要遵循醫療實踐的規律和需要,又要根據“病人至上”的原則,尊重患者的個人意愿和實際可能性,而后再作出診斷和治療上的決策。
1.2特征
循證醫學的核心思想是在醫療決策中將臨床證據、個人經驗與患者的實際狀況和意愿三者相結合。臨床證據主要來自大樣本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和系統性評價(Systematic Review)或薈萃分析(Meta-analysis)。
循證醫學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將最佳臨床證據、熟練的臨床經驗和患者的具體情況這三大要素緊密結合在一起尋找和收集最佳臨床證據旨在得到更敏感和更可靠的診斷方法,更有效和更安全的治療方案,力爭使患者獲得最佳治療結果。掌握熟練的臨床經驗旨在能夠識別和采用那些最好的證據,能夠迅速對患者狀況作出準確和恰當的分析與評價。考慮到患者的具體情況,要求根據患者對疾病的擔心程度、對治療方法的期望程度,設身處地地為患者著想,并真誠地尊重患者自己的選擇。只有將這三大要素密切結合,臨床醫師和患者才能在醫療上取得共識,相互理解,互相信任,從而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
第二,重視確鑿的臨床證據:這是和傳統醫學截然不同的。傳統醫學主要根據個人的臨床經驗,遵從上級或高年資醫師的意見,參考來自教科書和醫學刊物的資料等為患者制訂治療方案。顯然,傳統醫學處理患者的最主要的依據是個人或他人的實踐經驗。
2大數據
2.1定義
大數據(Big Data),或稱巨量資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透過目前主流軟件工具,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并整理成為幫助企業經營決策更積極目的的資訊。“大數據”這個術語最早期的引用可追溯到Apache Org的開源項目Nutch。當時,大數據用來描述為更新網絡搜索索引需要同時進行批量處理或分析的大量數據集。隨著谷歌MapReduce和GoogleFile System(GFS)的,大數據不再僅用來描述大量的數據,還涵蓋了處理數據的速度。對于“大數據”[1]研究機構Gartner給出了這樣的定義。“大數據”是需要新處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現力和流程優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信息資產。
2.2特征
大數據技術的戰略意義不在于掌握龐大的數據信息,而在于對這些含有意義的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
大數據的4V特征: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eracity(精確)。
3醫院信息系統在循證醫學中的應用
醫院信息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是為了醫院的效益而建立的信息管理系統。美國著名的醫學信息教授Morris Collen的定義是:HIS的目標是用計算機和通信設備采集、存儲、處理、訪問和傳輸所有和醫院相關的病人醫療信息和管理信息,滿足所有授權用戶功能上的要求。其包括臨床診療部分、藥品管理部分、費用管理部分、綜合管理與統計分析部分、外部接口部分五個組成部分。藥房管理系統、公共衛生信息系統均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3.1藥房管理系統
藥房管理系統有助于藥物經濟學的開展。藥物經濟學是衛生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藥房管理系統通過計算機實時動態數據處理,對全院藥房提供動態的藥品數據,運用藥物經濟學(Drug Economic)的理論及研究方法,包括:最小成本分析(CMA)、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用分析(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BA)等,通過研究,運用循證醫學的思想,比較評價不同的用藥計劃、方案、方法的風險及效益,以求用最低的花費而獲得最佳的療效。隨著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開展藥物經濟學研究,對于節約衛生資源、減輕病人經濟負擔、降低醫藥費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3.2醫學專家系統
醫學專家系統就是運用專家系統的設計原理與方法,模擬醫學專家診斷、治療疾病的思維過程編制的計算機程序系統,它可以幫助醫生解決復雜的醫學問題,作為醫生診斷、治療的輔助工具,同時也有助于醫學專家寶貴理論和豐富臨床經驗的保存、整理和傳播。將眾多醫學專家豐富的臨床經驗及大量病例資料存儲在計算機中,通過基于規則推理、基于案例推理、模糊數學推理、基于規則的神經網絡推理等推理方法,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將大大提高診斷的準確性和快速性。
3.3成功案例
2010年時代雜志刊載的醫學界年度十大突破中,醫療科技公司CardioDX通過對1億個基因樣本的分析,最終識別出能夠預測冠心病的23個主要基因。
2009年Google的研究人員對每日超過30億次搜索請求和網頁數據的挖掘分析,在H1N1流感爆發幾周就預測出流感傳播。
4存在問題
隨著大數據的爆炸性增長,劣質數據也隨之而來,導致數據質量低劣,極大地降低了數據的可用性。國外權威機構的統計表明,美國醫療信息系統中13.6%~81%的關鍵數據不完整或陳舊[2]。隨著大數據的不斷增長,數據可用性問題將日趨嚴重,也必將導致源于數據的知識和決策的嚴重錯誤。
數據可用性問題及其所導致的知識和決策錯誤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惡劣后果,嚴重困擾著信息社會。在美國,由于數據錯誤而引發的醫療事故,每年導致約98000名患者死亡,約占全部醫療事故致死人數的50%[3];據有關專家推算,在數據倉庫項目的開發過程中,清理不潔數據通常需要花費30%~80%的開發時間和開發預算[4]。
綜上所述,醫院信息系統強大的數據收集及分析處理能力為循證醫學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數據基礎,但在運用數據時,劣質數據所造成的損失我們也應盡力避免。要想使醫院系統真正步入大數據時代,仍有一段艱巨的道路要走。
參考文獻:
[1]維克托?邁爾-舍爾維恩,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Miller D W,Yeast J D,Evans R L.Missing Prenatal Recordsat a Birth Center:A Communication Problem Quantified[C]//Proc of AMIA Annual Symp Proceedings.Maryland: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2005:535-539.
[3]Kohn L T,Corrigan J M,Donaldson M S.To Err is Human:Building a Safer Health System[M].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0.
[4]Woolsey B,Schulz M.Credit card statistics,industry facts,debt statistics[EB/OL]. [2013-04-20].http://creditcards. Com/credit―card―news/credit―card―industry―factspersonal―debt―statistics-1276.Php.
[5]李建中,劉顯敏.大數據的一個重要方面:數據可用性[J].計算機研究與發展,2013(6):1147-1162.
[6]張九妹,曹宏亮.淺談醫學專家系統[J].醫療裝備,2008(9):10-12.
[7]徐麗麗,馬韻.循證醫學[J].中外健康文摘,2009(01X):50-51.
循證醫學依據范文2
圍術期評估
危險度評估應從病史及體檢入手,目前以校正心臟危險指數(RCRI)最為有效且方便記憶。
危險度評估配合心臟檢查能取得較好的效果。最為簡便的是心電圖檢查,高危患者如發現任何心電圖異常,其圍術期的風險增加兩倍;而心電圖正常的低危患者,則圍術期風險較低。二維超聲心動圖檢查可從多方面對病人進行評估,心室功能能夠反映心臟風險,二尖瓣返流提示患者預后較差,主動脈狹窄也會增加患者圍術期的危險。
運動心電圖最能反映術前心臟風險;但在女性患者及靜息心電圖即存在異常的患者,ST段壓低可能不具特異性。由于各種原因無法運動的患者可應用潘生丁擴張冠狀動脈后行心肌灌注掃描(DTI),如心室肌灌注缺失的面積大于30%,則術后心血管意外的發生率明顯增高。但DTI的假陰性率較高,大約是多巴酚丁胺負荷超聲心動圖(DSE)試驗的兩倍以上。
對于假陰性患者,由于認為其是安全的,就不會在這些患者應用有效降低風險的措施。而對于假陽性患者冠狀動脈造影的比例明顯升高,但并不增加冠狀動脈血運重建術的比例。
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多巴酚丁胺負荷超聲心動檢查更適合做術前篩查,并且該檢查還可以評估靜息時心室及瓣膜功能,發現室壁運動異常。
降低圍術期風險的方法
預防性冠狀動脈血運重建術
冠狀動脈左主干、三支病變及心室功能差的患者行冠狀動脈血運重建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對于非心臟手術的患者同樣有效。但預防性冠狀動脈血運重建本身也是有危險的。只有當藥物治療的患者行非心臟手術發生心血管意外的危險性高于冠狀動脈造影及血運重建的危險性時,預防性血運重建才是有益的。
冠狀動脈旁路手術(CABG)與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相比較,短期看來,PCI猝死的發生率比CABG低六倍。但CABG的遠期效果要優于PCI,其優勢在術后3-4年逐漸顯現。PCI后行擇期非心臟手術,如間隔小于6周,則心血管意外的發生率有所增加。
糖尿病患者PCI術后的死亡率較高。目前PCI術后需較長時間應用抗凝藥及抗血小板藥,因此延長了與下次手術之間的間隔。隨著冠狀動脈旁路手術的不斷發展,非轉流下行冠狀動脈旁路手術(OPCAB)可有效降低高危患者圍術期猝死、心肌梗死及心房纖顫的發生。OPCAB的一年死亡率與CABG無異,但需二次手術的可能性為CABG的兩倍。因此,就短期而言,很難明確哪種冠狀動脈血運重建方式更好。
另有研究表明冠狀動脈血運重建與藥物治療兩年死亡率無顯著差異,雖然冠狀動脈血運重建的患者術后院內心肌梗死發生率下降25%,但此差異不具顯著性,且兩組遠期療效無顯著差異。
術前負荷檢查評估的綜合分析顯示如患者負荷檢查呈陽性則應接受冠狀動脈造影檢查,可以顯著降低包括左主干病變、三支病變及左室功能差的患者圍術期心血管意外的發生率。
同時,藥物治療的有效性也是不可忽視。
藥物治療
?-受體阻滯劑
圍術期應用?-受體阻滯劑可有效降低術后心肌梗死的發生率。?-受體阻滯劑治療應在擇期手術前數日甚至數周開始,調節藥物劑量控制患者心率在50-60 bpm。
圍術期應用?-受體阻滯劑可以降低圍術期心血管意外的發生率及死亡率。其有效性與心臟危險度直接相關,即對高危患者作用明顯,對低-中危患者作用明顯下降。
長期應用?-受體阻滯劑并無積極作用。而且,術前長期服用?-受體阻滯劑的患者由于術后禁食水而停藥后可能出現撤藥現象,引起心肌缺血和心律失常,對于心臟手術的患者尤為明顯。研究表明術前長期服用?-受體阻滯劑,行心臟手術后停藥后心房纖顫的發生率最高。目前尚無數據表明?-受體阻滯劑撤藥現象發生的頻率以及程度。
作為臨床醫生我們應當牢記?-受體阻滯劑的撤藥現象并盡力防止其發生。
α2-受體激動劑
α2-受體激動劑可以降低術后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的發生。經皮給予可樂定可以降低術后心肌梗死及死亡率。可樂定具有鎮靜止痛的作用,靜脈應用可以減少嗎啡的用量,同時也可以減少術后惡心的發生率和嚴重性,相關副作用卻很少,并且不會引發充血性心力衰竭。其副作用包括低血壓和心動過緩,其發生的比例與?-受體阻滯劑相當。
鈣離子拮抗劑
首要問題是二氫吡啶類鈣離子拮抗劑- 硝苯地平會增加穩定型心絞痛患者急性心梗的發生。二氫吡啶類鈣離子拮抗劑主要是血管擴張劑,不具備負性變時作用,會增加心肌缺血、術后室上性心動過速的發生。而地爾硫卓可以降低心肌缺血、術后室上性心動過速、心肌梗死等心血管意外的發生。鈣離子拮抗劑與其他藥物配伍應用的作用我們還知之甚少。
硝酸鹽類
硝酸鹽類藥物能夠有效改善圍術期心肌缺血,其中尼可地爾的療效尤為明顯。與鈣離子拮抗劑相比較,硝酸鹽類藥物改善心肌缺血,降低心肌梗死發生的作用更為明顯。
抗血小板藥
低劑量阿司匹林(每日用藥量低于325mg)可以降低心肌梗塞及猝死的發生率約54%。如劑量超過325mg則可能對人體有害。另有研究證實低劑量阿司匹林降低患者術后血栓栓塞事件的發生率約36%,并提示非甾體類抗炎藥可以對抗抗血小板藥的作用。在以上兩項研究中,術前給以低劑量阿司匹林均未導致出血增加、增加輸血幾率。
重新分析以上數據,排除所有不明確是否應用了非甾體類抗炎藥的病例,得出以下結論,阿司匹林每日用量高于650 mg則心肌梗塞的發生率增加三倍,每日用量低于325 mg可降低圍術期心梗發生率50%。
而非甾體類抗炎藥盡管具有一定的鎮痛作用,對于具有心血管危險的患者來說,除非有進一步的證據,否則應當慎用。
他汀類降脂藥
降脂治療可降低術后心血管意外的發生率約30%。術前7天開始每日給以阿伐他汀20mg,可降低院內死亡率約50%,同時也證實了其遠期(6個月)的積極作用。另有研究表明術后兩天內接受他汀類降脂治療的患者較未行者圍術期死亡率降低30%。RCRI評分越高的高危患者其圍術期風險越大,而他汀類降脂治療的保護作用也就越明顯。
椎管內鎮痛
硬膜外腔單次給予嗎啡后24小時內患者的應激反應明顯減輕。在上個十年中,至少4項回顧性研究均證實了圍術期硬膜外鎮痛在鎮痛效果、呼吸及心血管系統并發癥等方面的優勢。其還是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證明其減少心血管意外、降低死亡率的作用。但將此項研究的數據納入關于心臟的回顧性研究中時,胸段硬膜外鎮痛降低了心肌梗死的發生,也有研究表明其可降低死亡率、肺炎和急性心梗的發生率。
各種預防方法的比較
各種阻滯交感神經的方法(包括?-受體阻滯劑,α2-受體激動劑和胸部硬膜外鎮痛)其預防心肌梗死、降低死亡率的作用是相似的。?-受體阻滯劑可能導致需要藥物干預的心動過緩;胸部硬膜外鎮痛可能導致低血壓,而這些是否與改善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率降低有關尚不明確。低劑量阿司匹林并不顯著增加輸血率。然而有研究表明?-受體阻滯劑與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發生相關。綜合各種證據支持α2-受體激動劑的應用。
聯合治療
冠心病的治療越來越趨向于多方式聯合治療。?-受體阻滯劑和降脂藥聯合應用的有效性依賴于患者術前的風險,即是說,對于術前RCRI 1分的患者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但對于RCRI 1-3分的患者可降低危險約50%,而對于高風險患者其作用更加明顯。而對于低風險患者,不僅未證實明確的積極意義,藥物副作用反而增加。因此聯合治療的方案仍需進一步研究。
麻醉方式
吸入性麻醉藥一直被認為具有預防心肌缺血的作用,而近來的研究顯示異氟醚、七氟醚和地氟醚可降低心肌梗塞的發生,而恩氟醚和氟烷卻可增加心肌梗塞的發生率。
另有研究表明笑氣可增加患者圍術期和術后心肌缺血的發生,還會增加術后至少72小時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高,繼而影響血小板反應性和內皮功能。笑氣也會成倍增加術后惡心嘔吐的發生率。此外,笑氣的麻醉效力較差。因此,對于術后出現心血管并發癥比例明顯增高的高危患者不應應用笑氣。
輸血
TRICC研究的結果指出:對于伴隨心血管疾病、血流動力學尚穩定的危重癥患者血紅蛋白濃度低于70g/L時需接受輸血治療并應維持血紅蛋白濃度在70-80g/L,可降低患者院內死亡率、心肌梗塞、充血性心力衰竭及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的發生率。
另有研究者認為冠心病患者接受輸血的限值為90-100 g/L,而目標值為100 g/L。在這一領域還需進行進一步研究。
嚴格控制血糖
將高危手術患者血糖嚴格控制于4.2-6.1mmol/dL,可使患者死亡率降低48%,腎衰發生率降低約50%,輸血率也有所下降,因此,對所有手術患者均應行嚴格控制血糖。
臨床建議
術前應行危險度評估,RCRI是最常用的方法,評分大于2分則應進一步行多巴酚丁胺負荷下超聲心動圖檢查。如發現患者兩處以上新發室壁運動異常則應進一步行冠狀動脈造影檢查。
合并冠狀動脈左主干病變或心室功能差的患者應行心臟血運重建,但血運重建的最佳方式尚無定論。
藥物治療時應采用多種藥物聯合治療,可先從抗交感神經的方法開始(?-受體阻滯劑, α2-受體激動劑或胸段硬膜外鎮痛)。如果患者心率、血壓控制不滿意可加用地爾硫卓,只要不合并禁忌癥,高危患者應當采用他汀類藥物行降脂治療,并在圍術期應用低劑量阿司匹林。
麻醉過程中不應使用笑氣,注意控制血糖,血紅蛋白低于100 g/L時則需要輸血治療。
循證醫學依據范文3
關鍵詞 心力衰竭 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抑制劑 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 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 腎素抑制劑
中圖分類號:R9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33(2013)17-0010-05
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是一種激素系統,當大量失血或血壓下降時被啟動,能協助調節體內的血壓與細胞外液量(體液平衡)。任何原因引起血壓下降時都會引起腎灌注下降和交感-腎上腺髓質系統興奮,從而促使腎臟近小球細胞分泌腎素。腎素會催化血管緊張素原水解產生血管緊張素(angiotensin, Ang)Ⅰ。AngⅠ基本沒有生物學活性,在肺循環中經血管緊張素轉化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mzyme, ACE)剪切C-末端的2個氨基酸殘基而轉化為AngⅡ。AngⅡ具有強力的血管收縮作用,可使血壓升高。此外,AngⅡ還會刺激腎上腺皮質分泌醛固酮。醛固酮能促進腎臟對水和鈉離子的重吸收,由此增加體液容量、升高血壓。
心力衰竭患者的RAS持續過度激活,使血循環及組織中的AngⅡ等縮血管物質濃度升高,導致心室后負荷增加;同時會使醛固酮過度分泌,引起水-鈉潴留,導致心室前負荷增加。因此,糾正過度激活的RAS對治療心力衰竭至關重要。
1 分類和臨床應用
根據對RAS阻斷位點的不同,RAS抑制劑主要分為如下3類。
1.1 ACE抑制劑
ACE除能將AngⅠ轉化為具有強力縮血管作用的AngⅡ外,還會催化有促血管舒張作用的緩激肽水解。ACE抑制劑的藥理作用是抑制ACE活性,減少AngⅡ的生成和緩激肽的水解,從而使血管舒張、血容量減少。因此,ACE抑制劑對血管舒張的作用來自RAS和激肽釋放酶-激肽系統(kallikrein-kinin system, KKS)這兩大調控系統,即具有雙系統保護作用。ACE抑制劑還能通過增加Ang 1~7和激活AngⅡ的1~7型受體而產生血管舒張和抗增殖等作用。
1.2 AngⅡ受體拮抗劑(angiotensinⅡreceptor blockers, ARB)
目前認為,AngⅡ的不良效應、包括血管收縮以及促進細胞增殖和醛固酮分泌等均來源于其對AngⅡ的1型受體的激活。ARB通過阻斷AngⅡ的1型受體產生藥理作用。
1.3 腎素抑制劑
AngⅡ與腎素之間存在著負反饋關系,而ACE抑制劑或ARB降低AngⅡ水平或抑制其受體后會抑制這一負反饋機制,導致腎素分泌增加。腎素抑制劑可結合到腎素活性位點,由此直接抑制腎素與血管緊張素原結合、阻斷RAS激活的限速步驟,從RAS的源頭阻止AngⅠ和AngⅡ的生成。腎素抑制劑的研發歷盡波折,直至發現第三代腎素抑制劑阿利吉侖(aliskiren)才得以進入臨床開發階段,并于2007年先后在美國和歐盟獲得批準,用于治療高血壓[2]。但腎素抑制劑治療心力衰竭的臨床證據有限。
2 治療心力衰竭的循證依據
2.1 ACE抑制劑
1987年發表的“CONSENSUS”試驗[3]雖規模不大,卻提供了ACE抑制劑治療心力衰竭有效的最早的重要臨床證據。該隨機、雙盲試驗旨在評價依那普利(2.5~40 mg/d)對嚴重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影響。患者在接受常規內科治療的基礎上分別加用依那普利(n=127)或安慰劑(n=126),主要終點為6個月內的總死亡率。結果發現,依那普利組的全因死亡率較安慰劑組降低40%(P=0.002)。12個月時依那普利組的死亡率仍較安慰劑組降低31%(P=0.001)。依那普利組患者的紐約心臟協會(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NYHA)心功能分級明顯改善。依那普利組獲得的死亡率方面的有益作用主要是由于減少了心力衰竭的進展、而不是因為減少了心臟性猝死。
1991年發表的“SOLVD-Treatment”試驗[4]旨在確定依那普利(2.5~20 mg/d)對慢性心力衰竭且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35%的患者的死亡率和因心力衰竭住院率的影響。患者被隨機分為依那普利組(n=1 285)和安慰劑組(n=1 284),平均隨訪期為41個月。結果顯示,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加用依那普利可較加用安慰劑降低16%的死亡率和減少26%的因心力衰竭住院率。
1992年發表的“SOLVD-Prevention”試驗[5]評價了依那普利(2.5~20 mg/d)對無癥狀的LVEF≤35%的患者的總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心力衰竭發生率和因心力衰竭的住院率等的影響。患者被隨機分為依那普利組(n=2 111)和安慰劑組(n=2 117),平均隨訪期為37.4個月。結果顯示與安慰劑組相比,依那普利組的總死亡率下降8%,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0);心血管死亡率下降12%,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P=0.12)。不過,依那普利能降低29%的死亡和心力衰竭復合發生率(P
“CONSENSUS”和“SOLVD”試驗奠定了ACE抑制劑治療心力衰竭的循證依據。1995年發表的一項收入當時所有已完成的ACE抑制劑的隨機、安慰劑對照試驗的薈萃分析[6]顯示,ACE抑制劑可顯著減低總死亡率(OR=0.77)和因心力衰竭的死亡或住院率(OR=0.65),且各ACE抑制劑(包括依那普利、卡托普利、雷米普利、喹那普利或賴諾普利)的作用相當,對不同的年齡、性別、病因或NYHA心功能分級亞組患者的作用也均相似。該薈萃分析還顯示,患者的LVEF越低、獲得的益處越大,最大益處出現在前3個月內。ACE抑制劑降低死亡率的作用主要歸因于減少了充血性心力衰竭所致死亡,對猝死、疑似心律失常致死和致死性心肌梗死的影響沒有統計學顯著性。
1999年發表的“ATLAS”隨機、對照、雙盲研究[7]旨在明確高劑量ACE抑制劑對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率的影響。入選的NYHA心功能分級Ⅱ~Ⅳ級、LVEF≤30%的心力衰竭患者在原治療的基礎上加用賴諾普利,分低劑量組(2.5~5.0 mg/d, n=1 596)和高劑量組(32.5~35 mg/d, n=1 568),隨訪期為39~58個月。與低劑量組相比,高劑量組的死亡率降低8%,但無統計學意義(P=0.128)。不過,對全因住院或死亡的復合終點,高劑量組較低劑量組下降12%(P=0.002)。高劑量組的頭暈和腎功能不全的發生率更高,但兩組需要停藥的患者比例相似。
2000年Flather等[8]發表了一項旨在觀察ACE抑制劑對心功能不全或心力衰竭患者長期影響的系統綜述,分析了“SOLVD-Treatment”、“SOLVD-Prevention”、“SAVE”、“AIRE”和“TRACE”試驗的數據,其中后3項試驗均僅入選急性心肌梗死后1周內的患者。對心肌梗死后患者的分析顯示,ACE抑制劑能降低死亡率(OR=0.74, P
正是這些結果高度一致的里程碑性的大型臨床研究奠定了ACE抑制劑在心力衰竭治療中的“基石”地位。
2.2 ARB
2000年發表的“ELITEⅡ”試驗[9]共入選了3 152例≥60歲的NYHA心功能分級Ⅱ~Ⅳ級、LVEF≤40%的患者,他們被隨機分為氯沙坦組(目標劑量為50 mg、qd)和卡托普利組(目標劑量為50 mg、tid),中位隨訪期為555 d。結果顯示,兩組在全因死亡率(年死亡率分別為11.7%和10.4%, P=0.16)和猝死或驟停復蘇發生率(分別為9.0%和7.3%, P=0.08)上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但氯沙坦組因不良反應、包括咳嗽(分別為0.3%和2.7%)而停藥的患者比例(分別為9.7%和14.7%, P
2001年發表的“Val-HeFT”研究[10]入選了5 010例NYHA心功能分級Ⅱ~Ⅳ級的心力衰竭患者,他們在接受原心力衰竭治療(約93%的患者在使用ACE抑制劑、約35%的患者在使用β-受體阻滯劑)的基礎上再隨機分組并分別加用纈沙坦(160 mg、bid,n=2 511)或安慰劑(n=2 499)的治療,平均隨訪期為23個月。結果發現兩組的總死亡率相當,但纈沙坦組的復合終點(總死亡或因心力衰竭住院)率降低了13.2%,主要歸因于因心力衰竭的住院率顯著減少。纈沙坦還能顯著改善患者的NYHA心功能分級、LVEF、心力衰竭的癥狀和體征以及生活質量(均P
2003年發表的“VALIANT”試驗[11]旨在觀察ARB、ACE抑制劑或兩藥聯用對急性心肌梗死后合并左心室收縮功能異常或心力衰竭、或兩者兼有患者死亡率的影響。心肌梗死后0.5~10 d的患者被隨機分為纈沙坦組(目標劑量160 mg、bid,n=4 909)、卡托普利組(50 mg、tid,n=4 909)和纈沙坦(80 mg、bid)聯用卡托普利(50 mg、tid)組(n=4 885),中位隨訪期為24.7個月。結果顯示,纈沙坦和卡托普利對心肌梗死后心血管事件高危患者的益處相當,但聯合使用這兩藥卻不會進一步改善生存率且反而會增加不良反應的發生率。2002年發表的“OPTIMAAL”試驗[12]比較了氯沙坦與卡托普利對急性心肌梗死后高危患者死亡率的影響,結果與“VALIANT”試驗相似,也證明ARB的作用不劣于ACE抑制劑。此外,這兩項試驗都觀察到ARB治療的耐受性明顯優于ACE抑制劑。
2003年發表了“CHARM”系列研究“CHARM-Added”試驗[13]、“CHARM-Alternative”試驗[14]和“CHARM-Preserved”試驗[15]結果。“CHARM-Added”試驗旨在從臨床上驗證基礎實驗中所觀察到的現象,即在ACE抑制劑治療的基礎上加用ARB治療慢性心力衰竭能在血流動力學、神經體液水平和左心室重構方面獲得更好的結果。該試驗入選了NYHA心功能分級Ⅱ~Ⅳ級、LVEF≤40%且正在接受ACE抑制劑治療的患者,他們被隨機分為坎地沙坦組(目標劑量為32 mg、qd, n=1 276)和安慰劑組(n=1 272),中位隨訪期為41個月。結果顯示,坎地沙坦能較安慰劑顯著降低主要終點(心血管死亡或因慢性心力衰竭住院)的發生率(分別為38%和42%, P=0.011)。
“CHARM-Alternative”試驗旨在觀察對ACE抑制劑不能耐受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能否因使用ARB而獲得益處。該試驗入選了LVEF≤40%且因以往不能耐受而沒有接受ACE抑制劑治療的有癥狀的心力衰竭患者,他們被隨機分為坎地沙坦組(目標劑量為32 mg、qd, n=1 013)和安慰劑組(n=1 015),中位隨訪期為33.7個月。患者對ACE抑制劑不能耐受的原因72%為咳嗽、13%為有癥狀的低血壓、12%為腎功能損害。結果顯示,坎地沙坦能較安慰劑顯著降低主要終點(心血管死亡或因慢性心力衰竭住院)的發生率(分別為33%和40%, P=0.000 4)。這兩項“CHARM”研究結果都是陽性的,其中“CHARM-Added”試驗支持心力衰竭患者在使用ACE抑制劑治療的基礎上加用ARB可能有益;而“CHARM-Alternative”試驗提示,對ACE抑制劑不能耐受的患者使用ARB可以獲益,即ARB是ACE抑制劑的有效替代品。
“CHARM-Preserved”試驗旨在觀察ARB對LVEF正常的心力衰竭(NYHA心功能分級Ⅱ~Ⅳ級、但LVEF>40%)患者的影響。患者被分為坎地沙坦組(目標劑量為32 mg、qd, n=1 514)和安慰劑組(n=1 509),中位隨訪期為36.6個月。結果顯示,兩組在主要終點(因心血管原因死亡或住院)率上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分別為22%和24%, P=0.051);坎地沙坦能減少因心力衰竭的住院率、但不能減少心血管死亡率。結合“CHARM-Added”試驗結果可以看出,坎地沙坦對LVEF≤40%的心力衰竭患者有益,對LVEF>40%的心力衰竭患者則益處不明顯。此后又有兩項隨機、對照臨床試驗[16-17]對LVEF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進行了相似研究,結果也都沒有得到陽性結果。
2009年發表的“HEAAL”試驗[18]比較了ARB高、低劑量治療對心力衰竭患者的影響。有30余個國家的255個臨床中心參加這一試驗,共入選了3 846例NYHA心功能分級Ⅱ~Ⅳ級、LVEF≤40%且不能耐受ACE抑制劑治療的患者,他們被隨機分為氯沙坦150 mg、qd組和50 mg、qd組,中位隨訪期為4.7年。結果顯示,高劑量組的復合終點(死亡或因心力衰竭住院)率較低劑量組降低(分別為43%和46%, P=0.027),腎臟損害、低血壓和高鉀血癥雖更常見,但這些不良反應沒有導致停藥率提高。該試驗結果提示,增加ARB劑量或許能使心力衰竭患者的獲益增加。結合“ATLAS”試驗結果可以看出,增加RAS抑制劑劑量可能對心力衰竭治療有益。
盡管之前已有3項大型隨機、對照臨床試驗未在LVEF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中得到RAS抑制劑有效的陽性結果[15-17],但2012年發表的一項前瞻性研究[19]卻得到了陽性結果。該研究共有64家醫院和84家診所參加,共入選16 216例LVEF正常(LVEF≥40%)的心力衰竭患者,分為RAS抑制劑治療組(n=12 543)和未接受RAS抑制劑治療組(n=3 673)。在配對的LVEF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的隊列研究中,RAS抑制劑治療組和非治療組的1年生存率分別為77%和72%(P=0.08);在總LVEF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人群中,RAS抑制劑治療組和非治療組的1年生存率分別為86%和69%(P=0.001)。但該試驗為觀察性研究,其作者認為隨機、對照臨床研究仍為評價干預的真實有效性的金標準。
2.3 腎素抑制劑
“ASTRONAUT”試驗[20]是評價腎素抑制劑在心力衰竭治療中的作用的第一項隨機、雙盲、對照臨床試驗,共有南美洲、北美洲、歐洲和亞洲國家的316個臨床中心參加研究,入選了1 639例≥18歲、LVEF≤40%、腦鈉肽≥400 pg/ml或N-端腦鈉肽前體≥1 600 pg/ml并伴有體液潴留癥狀和體征的患者,分為阿利吉侖組(150 mg/d;如能耐受,則300 mg/d)和安慰劑組。所有患者均繼續接受原心力衰竭標準治療(使用ACE抑制劑或ARB治療者占84.2%)。結果顯示,6個月時的主要終點事件(因心血管原因死亡或因心力衰竭住院)率,阿利吉侖組為24.9%、安慰劑組為26.5%(P=0.41);隨訪12個月時,阿利吉侖組的主要終點事件率為35%、安慰劑組為37.3%(P=0.36)。兩指標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且阿利吉侖組的高鉀血癥、低血壓和腎臟損害發生率都明顯高于安慰劑組。因此,目前尚無臨床證據支持腎素抑制劑用于心力衰竭治療。
3 結語
RAS抑制劑是心力衰竭治療的重要藥物,大量的循證證據已證實其在心力衰竭治療中的有效性。ACE抑制劑作為心力衰竭治療的“基石”,其地位尚無其他RAS抑制劑能夠替代;ARB的療效不劣于ACE抑制劑,可用于對ACE抑制劑不能耐受的患者。腎素抑制劑是一類新藥,目前還缺乏治療心力衰竭有效的證據,且其不良反應也值得關注。
參考文獻
[1] Ramrakha P, Hill J. Oxford handbook of cardiolog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12.
[2] 許文艷, 郭曄堃, 鐘靜芬, 等. 腎素抑制劑阿利吉侖及其臨床研究進展[J]. 上海醫藥, 2009, 30(11): 517-520.
[3] The CONSENSUS Trial Study Group. Effects of enalapril on mortality in severe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Results of the Cooperative North Scandinavian Enalapril Survival Study (CONSENSUS) [J]. N Engl J Med, 1987, 316(23): 1429-1435.
[4] The SOLVD Investigators. Effect of enalapril on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reduce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s and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J]. N Engl J Med, 1991, 325(5): 293-302.
[5] The SOLVD Investigators. Effect of enalapril on mort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failure in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reduce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s [J]. N Engl J Med, 1992, 327(10): 685-691.
[6] Garg R, Yusuf S. Overview of randomized trials of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Collaborative Group on ACE Inhibitor Trials [J]. JAMA, 1995, 273(18): 1450-1456.
[7] Packer M, Poole-Wilson PA, Armstrong PW, et al. Comparative effects of low and high doses of the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lisinopril, on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ATLAS Study Group [J]. Circulation, 1999, 100(23): 2312-2318.
[8] Flather MD, Yusuf S, Kober L, et al. Long-term ACE-inhibitor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or left-ventricular dysfunction: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data from individual patients. ACE-Inhibit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llaborative Group [J]. Lancet, 2000, 355(9215): 1575-1581.
[9] Pitt B, Poole-Wilson PA, Segal R, et al. Effect of losartan compared with captopril on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heart failure: randomised trial — the Losartan Heart Failure Survival Study ELITE II [J]. Lancet, 2000, 355(9215):1582-1587.
[10] Cohn JN, Tognoni G. A randomized trial of the angiotensin-receptor blocker valsartan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J]. N Engl J Med, 2001, 345(23): 1667-1675.
[11] Pfeffer MA, McMurray JJ, Velazquez EJ, et al. Valsartan, captopril, or both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by heart failure,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or both [J]. N Engl J Med, 2003, 349(20): 1893-1906.
[12] Dickstein K, Kjekshus J, OPTIMA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OPTIMAAL Study Group. Effects of losartan and captopril 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high-risk patients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he OPTIMAAL randomised trial. Optimal Trial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Angiotensin II Antagonist Losartan [J]. Lancet, 2002, 360(9335): 752-760.
[13] McMurray JJ, Ostergren J, Swedberg K, et al. Effects of candesarta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reduced left-ventricular systolic function taking angiotensin-converting-enzyme inhibitors: the CHARM-Added trial [J]. Lancet, 2003, 362(9386): 767-771.
[14] Granger CB, McMurray JJ, Yusuf S, et al. Effects of candesarta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reduced left-ventricular systolic function intolerant to angiotensin-converting-enzyme inhibitors: the CHARM-Alternative trial [J]. Lancet, 2003, 362(9386): 772-776.
[15] Yusuf S, Pfeffer MA, Swedberg K, et al. Effects of candesarta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preserved left-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the CHARM-preserved trial [J]. Lancet, 2003, 362(9386): 777-781.
[16] Cleland JG, Tendera M, Adamus J, et al. The perindopril in elderly people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PEP-CHF) study [J]. Eur Heart J, 2006, 27(19): 2338-2345.
[17] Massie BM, Carson PE, McMurray JJ, et al. Irbesartan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J]. N Engl J Med, 2008, 359(23): 2456-2467.
[18] Konstam MA, Neaton JD, Dickstein K, et al. Effects of high-dose versus low-dose losartan on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HEAAL study):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trial [J]. Lancet, 2009, 374(9704): 1840-1848.
[19] Lund LH, Benson L, Dahlstrom U,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use of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antagonists and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J]. JAMA, 2012, 308(20): 2108-2117.
循證醫學依據范文4
發展形勢令人鼓舞
循證醫學在我國的起步要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我國連續派出數批臨床醫師到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學習臨床流行病學,而且有多名醫師跟隨著循證醫學創始人之一薩克特查房,學習怎樣運用流行病學觀點解決臨床問題,這是循證醫學的雛形。同時我國在上海醫科大學和華西醫科大學分別建立了臨床流行病培訓中心,開展這方面工作。1996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引進了循證醫學和Cochrane系統評價,創建了中國循證醫學中心,1997年該中心獲得衛生部正式批準,1999年正式注冊成為國際Cochrane協作網的第十四個成員國,這是中國也是亞洲第一個中心。Cochrane協作網這一國際性組織,通過制作、保存、傳播和更新醫學各領域的系統評價,為臨床治療實踐和醫療衛生決策提供可靠的科學依據。參與國際Cochrane協作網后,促進了循證醫學在我國的實現與發展,可幫助政府衛生決策者做出科學決策以及改善臨床實踐質量,提高醫療服務水平,保證有限衛生資源的合理使用,對我國乃至世界都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循證醫學中心負責收集、翻譯本地區發表的和未發表的臨床試驗報告,建立中國循證醫學臨床試驗資料庫,為中國和世界各國提供中國的臨床研究信息;開展系統評價、隨機對照試驗、衛生技術評估以及循證醫學有關的方法學研究,為臨床實踐和政府的衛生決策提供可靠依據;該中心還提供循證醫學方法與技術培訓,為我國培養高質量、全方位的循證醫學骨干人才,傳播循證醫學的學術思想,推動了循證醫學在中國的發展。
另外,隨著各種循證醫學專著、循證醫學普及讀物、循證醫學雜志、循證醫學信息以及循證醫學網頁等傳播載體的相繼出現,對我國的循證醫學迅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藥有了循證的“金鑰匙”
可以開啟國際“鎖”
循證醫學對藥物療效評價的科學性、公正性和客觀性,能真正為醫生和患者提供可以信賴的用藥依據。因此,專家們指出,循證醫學的發展是讓我國中醫藥療效得到世界認可的一個重要契機,中醫藥學有了循證醫學這把“金鑰匙”就可以開啟國際“鎖”,真正實現國際化。北京協和醫院肖新華教授就曾經滿懷信心地指出:“如果中藥治療能經循證醫學證明,在(治療)指南中得以體現,我們的一些中藥品種有可能像阿司匹林一樣成為常規用藥。”
循證醫學依據范文5
二戰后,軍用科技轉向民用產業,由此催生“基于依據的實踐”。EBP(Evidence-BasedPolicy)先始于醫學,后滲透至多種學科,有人稱之為“循證運動”,主張通過“基于依據決策”的觀念來替代基于理想的傳統決策模式[1]。這是循證教育學的根本起因。1948年,英國流行病學家Hill發表關于鏈霉素治療肺結核的論文,被公認為世上首篇隨機對照試驗文獻;1972年,蘇格蘭醫生Cochrane運用系統綜述,檢討英國健康保險制嚴重失衡現象,開“循證實踐”之先河;1976年,美國統計學家Glass創建術語“薈萃分析”;1990年,加拿大McMaster大學成立循證醫學工作小組,首次推出“循證醫學”術語;1993年,英國成立國際組織TheCochraneCollaboration;1996年,加拿大醫生Sackett為《英國醫學雜志》撰寫社論《循證醫學:孰是與孰非》,成為國際循證醫學工作的里程碑文獻[2]。
二、循證教育學的興起
(一)美國的基于科學的教育。1996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制定《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影響美國各州的學習標準與標準化考試。2002年,美國頒布《2001年有教無類法案》,支持中小學的“基于科學的教育改革”[3]。為美國開展循證教育學奠定了基礎。
(二)英國的循證教育學。劍橋大學教授DavidH.Hargreaves于1996年在“年度教師培訓機構講座”上,發表題為“教學作為基于研究專業的可能性和前景”的系統研究,它是英國循證教育學興起的標志性文獻[4]。
(三)英美教育界的異見。劍橋大學教授DavidH.Hargreaves的演講否定當時整個英國的教育研究狀況。持異議者也不見少,其中以英國開放大學的MartynHammersley教授與埃克塞特大學的GertBies-ta為代表人物[5-6]。《美國有教無類法案》頒布后,批評聲不絕于耳,認為法案過度僵化而犧牲完整的通識教育,更為人詬病的就是標準化測驗,誤導學校走上應試教育的歧路。
(四)循證教育學的發展。經調查發現,2011年全國四年級學生的閱讀評分與2009相比無改變,但高出1992年4個百分點;八年級學生平均閱讀評分高出2009年1個百分點,高出1992年4個百分點[7]。反對者認為,視為金標準的隨機對照試驗不可作為惟一的研究標準。美國學者Whitehurst提出教學智慧與實證依據平行的“基于依據的教育”的基本框架,使循證教育學框架日趨完善[8]。可見,美國的“基于科學的教育”與英國的“循證教育學”存在差異。
三、國外循證教育學的現狀
(一)文獻計量分析。在ERIC教育文獻庫中,檢得循證教育學文獻3940篇。其文獻分布曲線在2004年后驟然上升并呈持續態勢(見附圖)。說明循證教育學已受到國際教育界的高度關注。
(二)學者。荷蘭醫生CeesVanDerVleuten是首位發表循證教育學者,而英國的DavidHHargreaves是首位提出循證教育學學科建設者。英國杜倫大學RobertCoe教授于1999發表的“循證教育學的宣言”,對奠定英國的循證教育學起了重要的作用[9]。
(三)著作與期刊。在Google引擎中的“圖書”欄中檢得循證教育學專著共359部,大部分出版于2009年之后。比較突出的是JohnHat-tie領銜新西蘭研究團隊編寫的《可見的學習》與美國RobertJ.Marzano領銜編寫的的《有效的課堂指導》。在ERIC文獻庫中,檢得文獻438篇,主要集中于20種期刊。其中收錄該類文獻最多的期刊是《ResearchonSocialWorkPractice》,影響因子最大的是《AmericanPsychologist》。
(四)專業網站。英美有關循證教育學的著名網站有:美國的WhatWorksClearinghouse、美國的BestEvidenceEncyclopedia、英國的CenterforEvaluationandAssessment、英國的CoalitionforEvi-dence-basedEducation等。
(五)循證教育研究的成果。美國學者RobertJ.Marzano運用薈萃分析方法,證實10種課堂教學方法呈高效應值(見附表)。新西蘭學者JohnHattie顯示,受許多國家政府青睞的多種干預措施實際上效應值低而成本高。
四、國內循證教育學展望
結合本系統循證醫學的成敗之鑒,對我國開展循證教育學的三個層面提出如下建議:
(一)決策者。1.編譯循證教育學專業詞匯表:編譯專業詞匯表,旨在要求學科帶頭機構能對該學科的本體概念了如指掌。2.確定我國循證教育學工作模式:循證教育學的工作模式迄今尚未得到統一認識。3.創建循證教育學文獻數據庫:創建教育研究文獻庫,是隨機對照與薈萃分析的絕對必需的外部條件。4.抉擇國家級教育擬定方案:首先要確定當前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開展循證教育學。
(二)培訓者。1.普及推廣循證教育學歸屬成人繼續教育,教師發展中心是國內普及推廣循證教育學的橋頭堡。2.學校的循證教育學應該有經過全面論證的校本預案,也可借鑒國外已確定的高效應值教學法。
循證醫學依據范文6
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medicine)是指最佳證據、臨床經驗和患者的具體情況三大要素緊密結合在一起,尋找和收集最佳臨床證據,旨在得到更敏感和更可靠的診斷方法,更有效和更安全的治療方案,力爭使患者獲得最佳治療結果。近20年來循證醫學正在逐漸成為一種被廣為接受的連接醫學研究和醫學實踐的有效方法,循證醫學的原則和思想也逐漸滲透到職業醫學領域。本文就循證醫學在職業病診斷中的應用闡述如下。
1職業病診斷中的最佳證據
職業病診斷中需要遵守循證醫學的基本原則,循證醫學重視確鑿的臨床證據。職業病診斷的可靠性和把握度的研究應在循證醫學的基礎上更加關注職業史和職業危害因素的接觸證據和患者的臨床表現,并對這些證據進行系統評價。Verbeek等[1]在職業病和工作有關疾病的診斷處理過程中應用循證醫學原則進行嘗試。
2塵肺病診斷主要遵循的原則
“根據可靠的生產性粉塵接觸史、現場勞動衛生學調查資料、以及技術質量合格的X線后前位胸片作為主要依據,參考動態的觀察資料及塵肺流行病學調查情況,結合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查,排除其他肺部類似疾病后,對照塵肺診斷標準片作出塵肺病診斷和X射線分期”[2]。可靠的生產性粉塵接觸史、現場勞動衛生學調查資料,即工人接觸粉塵作業的時間和作業場所的粉塵濃度、分散度是診斷塵肺病的最佳證據,是診斷塵肺病的前提條件,患者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查(質量合格的X線后前位胸片),排除其他肺部類似疾病,是依據醫生的臨床經驗,結合患者的具體情況,形成完整的塵肺病診斷。這也是多年來職業病診斷工作一直遵循的原則。國際勞工組織(LPO)161次大會指出需要向消費者提供循質服務和循證服務[3]。
3職業中毒的診斷原則也依據了循證醫學的基本思想
1)首先明確病因的證據,即職業接觸史,現場調查,獲得接觸的生物標志物以及反映機體生物材料中毒物或其代謝產物的含量,例如:尿鉛、尿汞、尿砷等。
2)疾病(中毒)的證據:取得完整的病史記錄,歷年職業性健康檢查記錄,效應性生物標志物等。
3)在職業性急性中毒診斷中,重點強調吸收毒物的時間與發病時間是否符合該毒物急性中毒的發病規律;毒物的作用時間與患者的臨床表現是否符合;估計吸收的劑量與疾病的嚴重程度是否相一致。
4)慢性中毒診斷需要了解有毒作業者在上崗前至接觸毒物后,逐年來的健康狀況改變,即健康監護,是通過系統地定期收集、整理、分析和評價有關的健康資料,從而連續性地監視職業病和工作有關疾病的分布和發展趨勢,是重要的客觀依據,為診斷慢性中毒提供有價值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