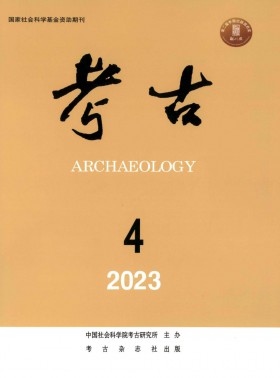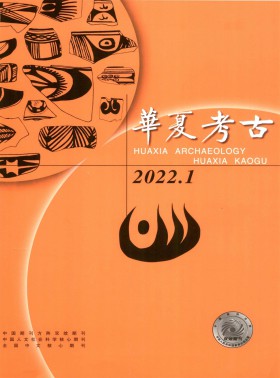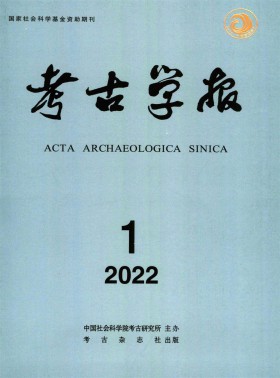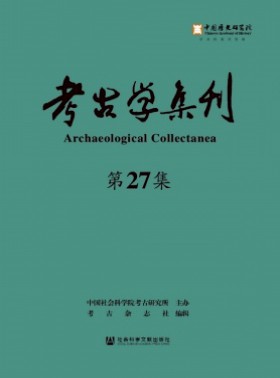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wǎng)精心挑選了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范文供你參考和學(xué)習(xí),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fā)你的文章創(chuàng)作靈感,歡迎閱讀。
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范文1
山東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fā)現(xiàn),如今經(jīng)過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東地區(qū)的考古學(xué)文化譜系已經(jīng)基本建立,為深化這一區(qū)域的考古學(xué)研究創(chuàng)造了條件。伴隨著山東地區(qū)考古發(fā)掘工作的開展,該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jìn)展。山東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統(tǒng)的研究則始于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吳詩池概述了山東新石器時(shí)代農(nóng)業(yè)考古發(fā)展情況(2),隨后又系統(tǒng)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狀況(3)。隨著考古發(fā)掘資料的不斷增多,吳詩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對(duì)山東地區(qū)出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資料進(jìn)行了綜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關(guān)于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在整體分析的基礎(chǔ)上,出現(xiàn)了一些區(qū)域性的系統(tǒng)研究,如石敬東利用出土文物資料研究了棗莊地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5);房道國(guó)概述了濟(jì)南地區(qū)古代農(nóng)業(yè)考古發(fā)展情況(6)。同時(shí),這一時(shí)期的單個(gè)文化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研究得到了發(fā)展,有學(xué)者在系統(tǒng)梳理海岱龍山文化生產(chǎn)工具資料的基礎(chǔ)上,對(duì)海岱地區(qū)龍山文化的生產(chǎn)工具進(jìn)行了類型學(xué)的考察,并進(jìn)而對(duì)區(qū)域間的生產(chǎn)方式的差異進(jìn)行了解釋(7)。另外,還有學(xué)者綜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農(nóng)具,認(rèn)為岳石文化的農(nóng)具較之龍山文化農(nóng)具有了很大的進(jìn)步,而不是像一些學(xué)者所認(rèn)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散見于各類有關(guān)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山東地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的文章鮮見于各類刊物之上,綜合系統(tǒng)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區(qū)域性的個(gè)案研究成果則未見發(fā)表。
從以上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研究的發(fā)展?fàn)顩r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gè)案研究,尤其是生產(chǎn)工具的個(gè)案研究。區(qū)域性的農(nóng)業(yè)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lǐng)域還有待擴(kuò)展。總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基礎(chǔ)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lǐng)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jìn)展,但是存在的幾個(gè)現(xiàn)實(shí)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發(fā)展。這些問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qū)史前考古發(fā)掘資料中,多數(shù)側(cè)重于陶器的統(tǒng)計(jì)分析,對(duì)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diào)查資料中,鮮有對(duì)石器的全面系統(tǒng)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fā)掘器物的數(shù)量上體現(xiàn)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fā)表的資料中陶器數(shù)以萬計(jì),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shù)量上的巨大差距說明了學(xué)者們以往對(duì)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dāng)然,這可能是時(shí)代的原因造成的,因?yàn)檫^去學(xué)者們偏重于對(duì)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yōu)越性。另外,山東地區(qū)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dòng)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fā)表的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和簡(jiǎn)報(bào)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tǒng)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過去多從生產(chǎn)工具入手來研究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fàn)顩r。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的本質(zhì)。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gè)主要問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gè)案深入研究;側(cè)重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史的研究,缺乏農(nóng)業(yè)發(fā)展動(dòng)因的合理解釋;農(nóng)業(yè)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gè)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guān)鍵。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是一項(xiàng)綜合的系統(tǒng)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yùn)用是必然趨勢(shì)。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沒有文獻(xiàn)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xué)資料進(jìn)行分析。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來,新考古學(xué)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tǒng)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正呈現(xiàn)"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tǒng)化、技術(shù)國(guó)際化"的趨勢(shì),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guó)外一些先進(jìn)的技術(shù)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shí)也相應(yīng)地?cái)U(kuò)展了研究的領(lǐng)域。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應(yīng)該以此為契機(jī),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jìn)技術(shù)方法。這其中民族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數(shù)學(xué)統(tǒng)計(jì)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xué)中有關(guān)原始民族以及現(xiàn)代晚進(jìn)民族的資料是進(jìn)行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nóng)業(yè)研究提供參考;經(jīng)濟(jì)學(xué)中有關(guān)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研究的原理,對(duì)史前農(nóng)業(yè)發(fā)展進(jìn)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shù)學(xué)中統(tǒng)計(jì)方法對(duì)史前農(nóng)業(yè)進(jìn)行量化研究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去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gè)案深入研究,而個(gè)案深入研究中一個(gè)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進(jìn)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gè)時(shí)期的農(nóng)業(yè)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yàn)榱炕治瞿軌蚋宄亓私飧鞣N因素的比例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隱藏于實(shí)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dòng)因。例如,我們過去將目光過多地集中于生產(chǎn)工具的發(fā)展變化上,從生產(chǎn)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huì)變化發(fā)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chǎn)工具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并未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nóng)具不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diǎn)。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不僅要復(fù)原古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史,還要對(duì)此進(jìn)行解釋。既然農(nóng)具不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yīng)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qū)史前遺址的發(fā)現(xiàn)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qū)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遺址數(shù)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shí)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shù)。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沒有質(zhì)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huì)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shí)期遺址達(dá)1300余處,表明此時(shí)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xiàn)象還需聯(lián)系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發(fā)展情況。龍山文化時(shí)期社會(huì)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xiàn)、等級(jí)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guó)的歷史實(shí)際進(jìn)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huì)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qiáng)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huì)反映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分工協(xié)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擴(kuò)大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另外,農(nóng)作物栽培技術(shù)的改善也會(huì)相應(yīng)的增加產(chǎn)量,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發(fā)展。因此可以說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可見,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chǔ)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huì)發(fā)展的真正動(dòng)因。
總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無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gè)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zhuǎn)換傳統(tǒng)的研究視角,從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的實(shí)際出發(fā),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chǔ)上,揭示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規(guī)律,闡釋中國(guó)文明的本質(zhì)動(dòng)因。
三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huì)逐步得到改善。現(xiàn)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fā)掘者在意識(shí)上形成主動(dòng)收集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biāo)去從事考古發(fā)掘工作。考古發(fā)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xué)資料的關(guān)鍵。近年來,有關(guān)考古學(xué)分支學(xué)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fā)掘者的主觀意識(shí)是分不開的。在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中植物考古學(xué)、動(dòng)物考古學(xué)等分支學(xué)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shí)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yàn)檠芯康纳钊雽?duì)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tǒng)考古學(xué)資料中有些是無法獲得的。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yīng)用以及相關(guān)研究的開展(12),為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資料的收集工作創(chuàng)造了條件。無疑新方法的應(yīng)用擴(kuò)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資料收集的精細(xì)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gè)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chǔ)上,能夠了解個(gè)別區(qū)域乃至整個(gè)山東地區(qū)生產(chǎn)工具的特點(diǎn)和具體的生產(chǎn)方式,不同地區(qū)、不同地域的生產(chǎn)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zhì)以及環(huán)境有直接的關(guān)系,而只有深化個(gè)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qū)間的差異。其次是農(nóng)業(yè)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nóng)業(yè)是如何起源的問題歷來為學(xué)術(shù)界所關(guān)注,山東地區(qū)地理環(huán)境較為封閉,其區(qū)域的系統(tǒng)研究必將對(duì)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yàn)。這里民族學(xué)、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程中的綜合應(yīng)用,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最后是農(nóng)業(yè)與文明的關(guān)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zhǎng)足的進(jìn)展。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保證,但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不一定就能導(dǎo)致文明的產(chǎn)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解釋文明的產(chǎn)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發(fā)展過程并結(jié)合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的問題還相當(dāng)多,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理論、方法、技術(shù)的改進(jìn)。國(guó)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shù)是在總結(jié)西方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對(duì)于中國(guó)的考古學(xué)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guó)實(shí)踐的檢驗(yàn)。因此,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在應(yīng)用這些方法進(jìn)行研究的時(shí)候,對(duì)總結(jié)中國(guó)自己的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陳文華:《簡(jiǎn)論農(nóng)業(yè)考古》,《農(nóng)業(yè)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池:《山東新石器時(shí)代農(nóng)業(yè)考古概述》,《農(nóng)業(yè)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池:《海岱文化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農(nóng)業(yè)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農(nóng)業(yè)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農(nóng)業(yè)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guó):《濟(jì)南地區(qū)古代農(nóng)業(yè)考古概述》,《農(nóng)業(yè)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qū)龍山文化生產(chǎn)工具的類型學(xué)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nóng)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qū)新石器時(shí)代的養(yǎng)豬業(yè)》,《農(nóng)業(yè)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jīng)濟(jì)》,《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shí)期自然環(huán)境的考古學(xué)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qū)原始農(nóng)業(yè)初探》,《慶祝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qū)的原始農(nóng)業(yè)》,《慶祝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guó)青銅時(shí)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及其考察》,《農(nóng)業(yè)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guān)山東地區(qū)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guān)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特點(diǎn)》,《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植物遺存及其在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上的意義》,《考古》1999年第7期。
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范文2
一
十九世紀(jì)中葉,丹麥著名的考古學(xué)家湯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學(xué)中以石器時(shí)代、青銅時(shí)代、鐵器時(shí)代分期法作為歐洲史前技術(shù)發(fā)展史的三個(gè)階段,通過生產(chǎn)工具和生活用具質(zhì)料的演變,說明原始社會(huì)的發(fā)展歷程。這一分期方法具有較強(qiáng)的科學(xué)性,為考古學(xué)界普遍接受。湯姆森的三期說于1848年被譯成英文出版后,對(duì)歐洲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影響巨大。時(shí)隔半個(gè)世紀(jì)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學(xué)思想的影響,梁?jiǎn)⒊壮?新史學(xué)",激烈批判中國(guó)傳統(tǒng)史學(xué),并擬撰寫一部新的中國(guó)通史。在《中國(guó)史敘論》中,他說明了編寫中國(guó)史的理論、思想、體例和分期等問題,其中第五節(jié)"有史以前之時(shí)代"即介紹了當(dāng)時(shí)正在歐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學(xué)理論--湯姆森的三期說。"1847年以來,歐洲考古學(xué)會(huì)專派人發(fā)掘地中遺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xué)遂成為一學(xué)派。近所訂定而公認(rèn)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又分為新舊兩期,此進(jìn)化之一定階段也。雖各地長(zhǎng)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梁?jiǎn)⒊瑢⑹鳌~器、鐵器三時(shí)代劃分理論與中國(guó)古代神話傳說相比附"中國(guó)雖學(xué)術(shù)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jīng)發(fā)現(xiàn),然物質(zhì)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xué)說為比例,以考中國(guó)史前之史,決不為過。據(jù)此種學(xué)者所稱舊新石刀兩期,其所歷年代最綿遠(yuǎn),其時(shí)無家畜、無陶器、無農(nóng)產(chǎn)業(yè),中國(guó)當(dāng)黃帝以前。神農(nóng)已作耒sì@①,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jīng)過石器時(shí)代,交入銅器時(shí)代之證據(jù)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yuǎn)在洪水之前者斷然也。"(注: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cè),中華書局,1989年。)很遺憾,梁?jiǎn)⒊茨苓\(yùn)用史前三期說寫出一部中國(guó)通史的遠(yuǎn)古時(shí)代篇,但是,他相當(dāng)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學(xué)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發(fā)掘的作用。這種用歐洲近代考古學(xué)理論對(duì)中國(guó)歷史進(jìn)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紀(jì)初期的中國(guó)確實(shí)是一種十分進(jìn)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學(xué)在中國(guó)古代被稱為金石學(xué)。具有悠久的歷史,宋代以來就很發(fā)達(dá),漸漸形成一種專門的學(xué)問。降及清朝,金石學(xué)隨考據(jù)之風(fēng)的興盛而蔚為大觀,尤其是乾嘉以來的學(xué)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銘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輩出,著述如林。梁?jiǎn)⒊凇肚宕鷮W(xué)術(shù)》第十六部分專論清代的金石學(xué)。他認(rèn)為"金石學(xué)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種學(xué)問",并列舉了一些研治金石學(xué)的犖犖大家,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shí)》等名家名作。梁?jiǎn)⒊亚宕鹗瘜W(xué)研究分作幾派:其中顧、錢一派"專務(wù)以金石為考證經(jīng)史之資料";黃宗羲一派從金石中"研究文史義例";此外尚有翁方綱一派"專講鑒別,則其考證非以助經(jīng)史矣";包世臣一派"專講書勢(shì),則美術(shù)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學(xué)范圍擴(kuò)大,考證商周銅器的"金文字興,而小學(xué)起一革命。"因?yàn)?儲(chǔ)器文字既可讀,其事跡出古經(jīng)以外者甚多,因此增無數(shù)史料。"同時(shí)對(duì)美術(shù)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jiǎn)⒊貏e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雖然"惜文至簡(jiǎn),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變遷異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簡(jiǎn)牘的發(fā)現(xiàn),不僅擴(kuò)大了金石學(xué)的研究范圍,而且為傳統(tǒng)金石學(xué)向近代考古學(xué)的轉(zhuǎn)變起了推進(jìn)作用。
此外,梁?jiǎn)⒊凇吨袊?guó)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論史料》中評(píng)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對(duì)于歷史研究的重大價(jià)值。他說意大利龐培古城發(fā)現(xiàn)后,"意人發(fā)掘熱驟盛,羅馬城中續(xù)得之遺跡,相繼不絕。而羅馬古史乃起一革命,舊史謬誤,匡正什九。"對(duì)中國(guó)古代遺跡遭到破壞則深表惋惜。例如鉅鹿城"茍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學(xué)的整理,則吾儕最少可以對(duì)于宋代生活狀況得一明確印象。"(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在這里,梁?jiǎn)⒊咽妨系墨@得分作兩部分:即在文字記錄以外者和文字記錄者。前者的性質(zhì),又可分三類:現(xiàn)存之實(shí)跡,傳述之口碑及遺下之古物。這些史料均屬于考古學(xué)、人類學(xué)、民族學(xué)和民俗學(xué)的范疇。梁?jiǎn)⒊粌H重視歷史文獻(xiàn),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這在當(dāng)時(shí)實(shí)具先鋒意義。 轉(zhuǎn)貼于
1922年10月22日,萬國(guó)考古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瑞典皇太子訪問中國(guó),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會(huì)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huì),中外學(xué)者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關(guān)于考古學(xué)的論文。受聘于中國(guó)農(nóng)商部地質(zhì)調(diào)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時(shí)在清華國(guó)學(xué)院擔(dān)任導(dǎo)師的梁?jiǎn)⒊矐?yīng)邀參加了會(huì)議,并做了《中國(guó)考古學(xué)之過去及將來》(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0一。 )的講演,在這篇演講中,梁?jiǎn)⒊紫然仡櫫酥袊?guó)考古學(xué)的萌芽時(shí)期,即北宋的金石學(xué),列舉了幾位著名的金石學(xué)家及其著作。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chéng)、李清照夫婦《金石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shí)》、呂大臨《考古圖》等。接著,梁?jiǎn)⒊攸c(diǎn)介紹了清代金石學(xué)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學(xué)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類,分別概述了各類研究對(duì)象,內(nèi)容及成果。最后,梁?jiǎn)⒊髁苏雇J(rèn)為考古學(xué)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仍很幼稚,可以發(fā)展之處很多,進(jìn)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強(qiáng)田野考古發(fā)掘,并圈定中國(guó)幾處最有潛力的發(fā)掘地區(qū)(新疆、黃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墳?zāi)埂⒋蟪敲肌U墟等);二是方法的進(jìn)步,包括繼承傳統(tǒng)金石學(xué)研究方法,引進(jìn)西方考古學(xué)新理論(如地質(zhì)學(xué)、古生物學(xué)、人類學(xué)等)。最后,梁?jiǎn)⒊M痪玫膶恚珖?guó)高等教育機(jī)關(guān)均設(shè)考古學(xué)科,以期開辟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新紀(jì)元。
三
"現(xiàn)代考古學(xué),最要者為田野工作,包括遺址的搜尋和發(fā)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學(xué)基礎(chǔ)》,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學(xué)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jiǎn)⒊€非常關(guān)注田野發(fā)掘。1926年冬,清華研究院和美國(guó)弗利爾藝術(shù)陳列館共同組織,李濟(jì)、袁復(fù)禮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考古發(fā)掘,這是中國(guó)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發(fā)掘。梁?jiǎn)⒊瑢?duì)此次合作極感興趣,并給予大力贊助。他曾兩度親筆寫信給山西軍閥閻錫山,請(qǐng)他對(duì)這一新興科學(xué)事業(yè)給予官方支持。李濟(jì)后來深情地回憶道:"梁?jiǎn)⒊淌谑欠浅嵝挠谔镆翱脊诺娜耍鲃?dòng)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范省長(zhǎng)閻錫山。"(注:李濟(jì):《安陽--殷商古都發(fā)現(xiàn)、發(fā)掘、復(fù)原記》,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在當(dāng)?shù)卣膮f(xié)助下,這次考古發(fā)掘非常順利。1926年12月10日,梁?jiǎn)⒊趯懡o時(shí)在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研究院攻讀考古和人類學(xué)專業(yè)的兒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濟(jì)的田野發(fā)掘,"李濟(jì)之現(xiàn)在山西鄉(xiāng)下(非陜西)正采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jīng)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愿及條件,大約十日內(nèi)外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實(shí)在職務(wù),得有實(shí)習(xí)機(jī)會(huì),盤費(fèi)、食住費(fèi)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問題。"(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jiǎn)⒊曜V長(zhǎng)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來梁思永在美國(guó)留學(xué)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fā)掘,寫信給父親梁?jiǎn)⒊硎鞠牖貒?guó)實(shí)習(xí)并搜集一些中國(guó)田野考古資料。這時(shí),李濟(jì)也從山西發(fā)掘地回到北平,開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華園與梁?jiǎn)⒊嘁姡瑑扇苏劶把?qǐng)梁思永回國(guó)參加考古發(fā)掘事宜。后來,李濟(jì)把西陰村發(fā)掘所得實(shí)物的一部分在清華大學(xué)校園內(nèi)做公開展覽,王維國(guó)、梁?jiǎn)⒊瑓⒂^了展覽,并與李濟(jì)做了熱烈的交談。
1917年1月10日, 清華國(guó)學(xué)研究院為歡迎李濟(jì)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fā)掘的勝利歸來,舉行了茶話會(huì)。梁?jiǎn)⒊鱿⒙犎×死顫?jì)、袁復(fù)禮二人所作的長(zhǎng)篇報(bào)告。當(dāng)天晚上,梁?jiǎn)⒊d致極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寫了一封長(zhǎng)信給梁思永。信中他首先報(bào)告了西陰村考古發(fā)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績(jī)平平安安運(yùn)到本校,陸續(xù)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shè)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談到出土的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等,還提到了著名的半個(gè)繭殼,以及復(fù)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梁?jiǎn)⒊貏e提到了這次考古發(fā)掘的重大意義:"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國(guó)文化西來'之說,自經(jīng)這回的發(fā)掘,他們(指李濟(jì)、袁復(fù)禮二人)想翻這個(gè)案。"并認(rèn)為"(李濟(jì))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guó),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huì)揀'真不錯(cuò)。"建議梁思永回國(guó)"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時(shí)局動(dòng)蕩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fā)掘,在室內(nèi)整理那76箱東西,"也斷不致白費(fèi)這一年光陰。"(注:上引均見《梁?jiǎn)⒊纯瘯攀舟E》,中華書局,1994年。)梁?jiǎn)⒊€打算讓梁思永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shí),多參觀幾個(gè)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后再去歐美深造幾年,一定會(huì)受益更多。 轉(zhuǎn)貼于
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范文3
20世紀(jì)初,瑞典學(xué)者安特生(圖1)主持發(fā)掘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文化遺址(圖2),不僅翻開了中國(guó)考古學(xué)史的第一頁,拉開了探索中華文明的序幕,同時(shí)也揭開了中國(guó)史前陶器文化神秘的面紗。此后的幾十年里,特別是近三十年,隨著各地新石器時(shí)代遺址發(fā)掘的增多和考古研究的進(jìn)一步深入,中國(guó)的考古工作者把雜亂無序、錯(cuò)綜復(fù)雜的各地區(qū)史前遺址分為幾個(gè)大區(qū)系和幾十種文化,使中國(guó)史前陶器文化發(fā)展脈絡(luò)非常清晰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xiāng)仙人洞遺址(圖3)地處贛東北萬年縣大源鄉(xiāng)的東南角,距長(zhǎng)江南148公里,地質(zhì)上屬于喀斯特地形,高低起伏的石灰?guī)r峰巒環(huán)繞著一塊狹長(zhǎng)的山間小盆地。仙人洞洞口呈外弧內(nèi)凹狀,開闊并向前平鋪伸展,外高內(nèi)底,入口處2米高,最寬2.5米,洞穴深40米,洞內(nèi)面積較大,分成南北4個(gè)支穴。洞外郁郁蔥蔥的灌木林覆蓋了整個(gè)山體,洞穴周圍樹木林立,小河流淌,山清水秀,一片片隨風(fēng)搖曳的油菜花在陽光的映照下,熠熠地閃爍著金色的光芒。很難想象20000年前我們的遠(yuǎn)古先民就居住在這座洞穴里,那時(shí)這里還生長(zhǎng)著茂密的森林,滿布湖泊、沼澤,他們主要靠漁獵為生,采集野生植物果實(shí)和螺蚌一類水生動(dòng)物充饑。盡管居住環(huán)境十分險(xiǎn)惡,生活非常艱辛,先民卻憑藉著粗笨的石器和棍棒,依靠群體的力量,堅(jiān)忍不拔的毅力,英勇無畏的精神和智慧,同心協(xié)力,與大自然抗?fàn)帲B強(qiáng)地在這座洞穴里生存了下來。早在上世紀(jì)60年代初期考古人員就對(duì)遺址有過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1993年、1995年、1999年和2000年由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guó)安德沃考古基金會(huì)(AFAR)組成聯(lián)合考古隊(duì)先后進(jìn)行了五次發(fā)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動(dòng)物骨骼,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標(biāo)本就發(fā)現(xiàn)于此。
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的吳小紅教授、張弛教授、曲彤麗博士與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人類學(xué)系歐弗?巴爾?約瑟夫教授、美國(guó)波士頓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維.科恩(David Cohen)博士等2009年在重新清理出來的考古地層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測(cè)年樣品和地層微結(jié)構(gòu)樣品,確定碳十四測(cè)年樣品與陶片的地層等時(shí)關(guān)系,證實(shí)以前發(fā)掘的考古地層是人類活動(dòng)形成的原生堆積,不存在自然過程或者后期活動(dòng)的攪擾,所測(cè)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層位陶器的年代。由此證實(shí)仙人洞遺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發(fā)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圖4),并將這一研究成果發(fā)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國(guó)的《科學(xué)》雜志上,入選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北京大學(xué)新聞網(wǎng))。
經(jīng)過對(duì)地處中國(guó)長(zhǎng)江以南的江西仙人洞、吊桶環(huán)和湖南玉蟾巖早期陶器測(cè)年結(jié)果表明(圖5、圖6),其年代都不晚于公元前16000年,中國(guó)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現(xiàn)最早的地區(qū),并在冰期時(shí)才傳播到日本和遠(yuǎn)東等鄰近地區(qū)。此后,陶器在中國(guó)一直延續(xù)使用發(fā)展到今天,始終就沒有中斷過。當(dāng)仙人洞陶器制成時(shí),地球正處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時(shí)期,陶器是由采集狩獵者制造,最初可能是被用作炊煮器,因此,測(cè)定顛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來臨后才出現(xiàn),并帶動(dòng)了農(nóng)業(yè)、家畜馴養(yǎng)以及磨制石器發(fā)展的觀點(diǎn)。那時(shí)顯然還沒有農(nóng)業(yè),人類應(yīng)該處于狩獵或漁獵階段。所以,仙人洞陶器的發(fā)現(xiàn)在早期人類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為探討現(xiàn)代人應(yīng)對(duì)環(huán)境變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演化中的作用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shí)也確立了中國(guó)史前陶器在人類陶器文化發(fā)展史上獨(dú)特的地位。
陶器是為了適應(yīng)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和遠(yuǎn)古先民穴居生活的需要而逐漸產(chǎn)生發(fā)展起來的,中國(guó)古代有“神農(nóng)耕而作陶”或“神農(nóng)作瓦器”、“女媧摶黃土做人”的動(dòng)人故事。在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人類從“攝取性經(jīng)濟(jì)”過渡到“生產(chǎn)性經(jīng)濟(jì)”,迎來了新石器時(shí)代的曙光。在太陽升起的東方,人們已積累了用火的經(jīng)驗(yàn),他們從偶然的發(fā)現(xiàn)中認(rèn)識(shí)了水、土、火相融的特點(diǎn),又從葫蘆和枝條編成籃、筐的方法中獲得了靈感,用原始模制技術(shù)和泥片貼塑法、泥條疊筑法開始制陶,燒制出了大量造型各異、美觀實(shí)用、絢麗多姿、獨(dú)具東方韻味的生活器皿、工具、禮器、樂器、人物、動(dòng)物、玩具等陶器。
從簡(jiǎn)單到復(fù)雜,從幼稚到成熟,中國(guó)史前陶器經(jīng)歷了長(zhǎng)期探索、反復(fù)試驗(yàn)、不斷改進(jìn)、逐漸完善的漫漫歷程,延續(xù)發(fā)展了16000多年。
公元前18000~公元前6000年是中國(guó)史前陶器的早期――萌芽初始期。
屬于中國(guó)史前陶器早期的遺址有:地處長(zhǎng)江流域的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xiāng)仙人洞、吊桶環(huán)兩遺址和湖南省南部道縣玉蟾巖遺址、浙江上山遺址,北方地區(qū)的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遺址、陽原縣的泥河灣虎頭梁遺址,華南地區(qū)廣西桂林市南郊的甄皮巖遺址、大巖遺址、嶺南貝丘遺址,柳州大龍?zhí)朵圁~嘴第一期文化,廣東翁源青塘幾處洞穴遺址、潮安石尾山等。而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xiāng)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是人類迄今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的陶器。
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范文4
關(guān) 鍵 詞:設(shè)計(jì)史教師 文化素養(yǎng) 作用
高等院校藝術(shù)設(shè)計(jì)專業(yè)藝術(shù)設(shè)計(jì)史課程,在整個(gè)教學(xué)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設(shè)計(jì)史課程不僅為藝術(shù)學(xué)其他課程的教學(xué)提供理論上的支撐,同時(shí)也為其他課程的學(xué)習(xí)作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識(shí)的鋪墊。然而,在具體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設(shè)計(jì)史所體現(xiàn)的多學(xué)科交織的特點(diǎn)、部分與整體的關(guān)系、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多元性”與“開放性”等問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些問題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設(shè)計(jì)史教師的文化素養(yǎng)在教學(xué)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值得探討。
一
設(shè)計(jì)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有利于對(duì)設(shè)計(jì)史教材的整體把握。設(shè)計(jì)史課程的特點(diǎn)首先應(yīng)該是歷史,歷史學(xué)的素養(yǎng)在設(shè)計(jì)史教學(xué)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歷史的一般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設(shè)計(jì)史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具有指導(dǎo)作用。古代設(shè)計(jì)的發(fā)展史與古代歷史的發(fā)展演變的線索、脈絡(luò)基本上是一致的,盡管設(shè)計(jì)的發(fā)展不以社會(huì)性質(zhì)的變遷和社會(huì)變革為依據(jù),但是影響設(shè)計(jì)發(fā)展的決定作用應(yīng)該是生產(chǎn)力水平的發(fā)展和變化。歷史上的社會(huì)變遷和人口遷移對(duì)設(shè)計(jì)的影響也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
從社會(huì)和文化的角度介紹設(shè)計(jì)發(fā)展的歷史條件,對(duì)于正確理解設(shè)計(jì)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力與源泉是十分必要的。設(shè)計(jì)發(fā)展史同這一時(shí)期政治史、經(jīng)濟(jì)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關(guān)的。相反,設(shè)計(jì)運(yùn)動(dòng)的迭起、設(shè)計(jì)探索的推進(jìn),與整個(gè)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的演進(jìn)是分不開的。阿伯特·博姆認(rèn)為:“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史把物象孤立起來研究,把它作為幾乎獨(dú)立存在的現(xiàn)象來對(duì)待。而社會(huì)藝術(shù)史在探索把藝術(shù)家和藝術(shù)作品置于廣泛的、歷史的和經(jīng)濟(jì)的背景中來研究。”①因此,具有社會(huì)歷史學(xué)的理論素養(yǎng),就可以對(duì)設(shè)計(jì)史的內(nèi)容進(jìn)行高度綜合和概括,進(jìn)而在宏觀方面對(duì)其內(nèi)容進(jìn)行把握。
二
設(shè)計(jì)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有利于對(duì)設(shè)計(jì)史和設(shè)計(jì)作品的時(shí)代特征進(jìn)行正確的闡釋和評(píng)價(jià)。對(duì)傳統(tǒng)文物藝術(shù)品及物質(zhì)文化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不僅僅是教學(xué)過程中的背景知識(shí),而且還是準(zhǔn)確理解和闡釋設(shè)計(jì)史有關(guān)問題的必要知識(shí)。藝術(shù)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認(rèn)為:“有些藝術(shù)教員不單向?qū)W生展示歷代的藝術(shù)作品……把孤立的畫家及作品和時(shí)代、地域聯(lián)系起來,這樣理解藝術(shù)史就有了基礎(chǔ)。”②歸根到底,藝術(shù)設(shè)計(jì)是通過藝術(shù)與科學(xué)共同的合成手段,創(chuàng)造著人們的全新生活,其中體現(xiàn)的就是一種文化。
中國(guó)古代的藝術(shù)設(shè)計(jì)與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特征密切相關(guān)。夏商周的禮制性設(shè)計(jì)藝術(shù),政治和經(jīng)濟(jì)方面的關(guān)系是其設(shè)計(jì)的內(nèi)在根源。中國(guó)古代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發(fā)展變化在許多歷史時(shí)期都和周邊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統(tǒng)治有關(guān),形成了多個(gè)時(shí)期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多元交融的時(shí)代特色。這種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對(duì)當(dāng)時(shí)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和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發(fā)展都具有深遠(yuǎn)的影響。
在設(shè)計(jì)史教學(xué)中,教師應(yīng)該對(duì)藝術(shù)設(shè)計(jì)史中的多種文化因素進(jìn)行分析和評(píng)價(jià),才能完整而透徹地闡釋影響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深層次的時(shí)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學(xué)生才能在一個(gè)較高的層面上理解當(dāng)時(shí)的藝術(shù)設(shè)計(jì)。可以說,設(shè)計(jì)史教師文化品位的高低是決定設(shè)計(jì)史課程教學(xué)質(zhì)量高低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三
設(shè)計(jì)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有利于設(shè)計(jì)史文獻(xiàn)史料和設(shè)計(jì)史術(shù)語的正確解讀。在教學(xué)和研究中,設(shè)計(jì)史課程也要使用多種學(xué)科的教學(xué)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國(guó)古代設(shè)計(jì)史的內(nèi)容和材料大多為考古出土的藝術(shù)品,對(duì)考古藝術(shù)品的研究離不開文獻(xiàn)史料,設(shè)計(jì)史學(xué)與考古學(xué)和歷史文獻(xiàn)學(xué)具有直接的連帶關(guān)系。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美術(shù)考古學(xué)所研究的內(nèi)容有相當(dāng)?shù)牟糠峙c設(shè)計(jì)史研究的內(nèi)容相重合,其對(duì)新興的設(shè)計(jì)史課程的教學(xué)與研究的參照作用不言而喻。
對(duì)設(shè)計(jì)史的研究離不開文獻(xiàn)史料,而對(duì)文獻(xiàn)史料的準(zhǔn)確理解又需要?dú)v史文獻(xiàn)學(xué)的相關(guān)知識(shí),所以,歷史文獻(xiàn)學(xué)對(duì)中國(guó)古代設(shè)計(jì)史的研究與教學(xué)就顯得非常重要。在設(shè)計(jì)史教學(xué)和研究中經(jīng)常會(huì)遇到很多難以解讀的史料。因此,設(shè)計(jì)史教師加強(qiáng)歷史文獻(xiàn)學(xué)的學(xué)習(xí)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設(shè)計(jì)史教學(xué)中還會(huì)遇到很多考古學(xué)、古生物學(xué)、神話學(xué)及歷史文獻(xiàn)學(xué)等學(xué)科的專有名詞和術(shù)語,對(duì)這些專有名詞和術(shù)語的解釋,關(guān)系到學(xué)生對(duì)設(shè)計(jì)史內(nèi)容的正確理解和教師教學(xué)任務(wù)的圓滿完成。鑒于此,對(duì)多學(xué)科和交叉學(xué)科知識(shí)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是設(shè)計(jì)史教師應(yīng)該負(fù)有的責(zé)任。
四
設(shè)計(jì)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有利于對(duì)設(shè)計(jì)思想和設(shè)計(jì)觀念的理論概括與升華。藝術(shù)設(shè)計(jì)包括多方面的內(nèi)容,既涉及材料、技術(shù),又涉及方法、觀念;既是藝術(shù),又是科學(xué);既有人文學(xué)科的屬性,又與自然科學(xué)相關(guān);既有實(shí)用功能的限定,又有審美的心理的要求;既有文化的傳承,又要求創(chuàng)新。因此,如何對(duì)以往的設(shè)計(jì)思想進(jìn)行概括與提煉,關(guān)系到在教學(xué)中能否達(dá)到因材施教、深入淺出的良好教學(xué)效果。
對(duì)設(shè)計(jì)思想和觀念的理論概括與升華,教師必須掌握和了解哲學(xué)、美學(xué)、宗教學(xué)等學(xué)科知識(shí)。陳樂民先生說:“任何學(xué)問就像剝筍一樣,一層一層地剝下去,剝到核心,是哲學(xué)。”③黑茲爾·康威也說過:“雖然對(duì)于設(shè)計(jì)史不同領(lǐng)域的劃分反映了設(shè)計(jì)者的專業(yè)結(jié)構(gòu),但是在實(shí)踐和理論中,各個(gè)領(lǐng)域之間都存在著很多聯(lián)系。”④在對(duì)待歷史文化與藝術(shù)傳統(tǒng)上,不能采取斷章取義的態(tài)度,應(yīng)該從一個(gè)更為廣闊的視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綜上所述,藝術(shù)專業(yè)學(xué)生綜合素質(zhì)的提高與教師的文化素養(yǎng)有著比較密切的關(guān)系。從長(zhǎng)遠(yuǎn)來看,學(xué)生的理論水平和創(chuàng)意能力的培養(yǎng)要比技能教育更為重要。設(shè)計(jì)史是一門多學(xué)科交叉的課程,尤其是文史哲諸學(xué)科,對(duì)這些學(xué)科的學(xué)習(xí)和了解是設(shè)計(jì)史教師提高文化素養(yǎng)、達(dá)到良好教學(xué)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釋:
①Albert Boime.Art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00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②艾迪斯·埃里克森著.宋獻(xiàn)春,伍桂紅譯.藝術(shù)史與藝術(shù)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范文5
在群星璀璨的區(qū)域文化中,河洛文化無疑是其中一個(gè)耀眼的明星。與三晉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點(diǎn)?又如何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成與發(fā)展?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對(duì)本報(bào)記者的提問進(jìn)行了一一解答。
區(qū)域文化中的核心區(qū)域文化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作為一種區(qū)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圍涵蓋哪些地方?我們應(yīng)該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華歷史文化中的位置?劉慶柱:河洛文化是中國(guó)古代歷史上的區(qū)域文化之一,學(xué)術(shù)界一般認(rèn)為河洛地區(qū)以今洛陽為中心,地理范圍包括今豫西、晉南一帶。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國(guó)古代區(qū)域文化,它是中國(guó)古代歷史上區(qū)域文化中的核心區(qū)域文化,屬于中國(guó)古代歷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謂核心區(qū)域文化,就是影響整個(gè)國(guó)家的文化;所謂根文化,就是國(guó)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區(qū)南部山區(qū)一帶,近年來發(fā)現(xiàn)了多處舊石器時(shí)代的古人類遺存,這些舊石器時(shí)代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被評(píng)為當(dāng)年度全國(guó)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豫西地區(qū)新石器時(shí)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是中國(guó)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當(dāng)今中國(guó)地理范圍之內(nèi)考古學(xué)文化影響最大、最深遠(yuǎn)的史前區(qū)域文化。廟底溝文化(即廟底溝類型)孕育出河南龍山文化,繼之又在廟底溝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基礎(chǔ)上產(chǎn)生了夏文化及中國(guó)古代歷史文獻(xiàn)記載的第一個(gè)王朝夏。
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在河洛地區(qū)考古發(fā)現(xiàn)的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被學(xué)術(shù)界認(rèn)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遺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國(guó)家的政治統(tǒng)治中心、軍事指揮中心、經(jīng)濟(jì)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dòng)中心,是古代國(guó)家歷史的縮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國(guó)家的中心地區(qū),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遺址充分證實(shí)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區(qū)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區(qū)。從河南龍山文化時(shí)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遺址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說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龍山文化,而從河南龍山文化發(fā)展到夏文化的主要?dú)v史平臺(tái)就在河洛地區(qū)。如果說廟底溝文化在河洛地區(qū)孕育了華夏文化,那么華夏文化的形成與早期發(fā)展,則在河洛地區(qū)夏商都城遺址得到考古發(fā)現(xiàn)的科學(xué)佐證。從三代的華夏文化,到漢唐時(shí)代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河洛地區(qū)在中國(guó)歷史上發(fā)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漢武帝時(shí)期,伴隨著函谷關(guān)從靈寶東移至新安,促進(jìn)了漢唐時(shí)代河洛地區(qū)與關(guān)中地區(qū)的一體化,使?jié)h唐兩京成為漢唐盛世的中心。漢唐時(shí)代河洛地區(qū)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禮制建筑與宗教遺存等許多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使我們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形成與發(fā)展中的歷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陽城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我國(guó)歷史上的很多都城誕生在河洛地區(qū),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對(duì)我國(guó)古代都城建制的影響?劉慶柱:從中國(guó)古都發(fā)展史看,河洛地區(qū)考古發(fā)現(xiàn)的二里頭宮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歷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的都城以宮城為核心的布局,宮城之中宮殿與宗廟的二元格局,宮廟政治性建筑的一門三道與一門四塾規(guī)制。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是中國(guó)古代都城宮城中最早的擇中而立的典型,它們確立的范式一直為中國(guó)古代歷代王朝都城之宮城所延續(xù)。作為從王國(guó)時(shí)代到帝國(guó)時(shí)代國(guó)家歷史物化載體的中國(guó)古代都城,河洛地區(qū)的東漢雒陽城從漢長(zhǎng)安城宮城與亞宮城并存發(fā)展為雙宮城至單宮城,都城從西漢時(shí)代的坐西朝東改為坐北朝南。與古代都城變化相對(duì)應(yīng)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從西漢帝陵的坐西朝東改為東漢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園結(jié)構(gòu)由西漢帝陵陵園的帝陵與皇后陵的同塋不同穴、二者各置一個(gè)陵園,變?yōu)闁|漢帝陵的帝后同穴。東漢都城與帝陵的上述規(guī)制變化影響深遠(yuǎn),為東漢以后歷代王朝所基本繼承。
夏商周時(shí)代的華夏文化,至秦漢時(shí)代統(tǒng)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quán)帝國(guó)的建立,中華民族文化形成。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河洛地區(qū)發(fā)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們集中反映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時(shí)從長(zhǎng)城地帶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陽,開創(chuàng)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發(fā)展的政治、文化格局,從華夏文化發(fā)展而來的中華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區(qū)被北魏王朝認(rèn)同,河洛文化也成為多民族形成的國(guó)族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鮮卑人統(tǒng)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區(qū),無疑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有著里程碑意義。孝文帝營(yíng)建的北魏洛陽城,由宮城、內(nèi)城和郭城組成,北魏洛陽城三城制取代魏晉洛陽城、兩漢都城與先秦都城的雙城制,從古代國(guó)家層面完成了從王國(guó)時(shí)代到帝國(guó)時(shí)代的根本性轉(zhuǎn)變(作為帝國(guó)時(shí)代的兩漢都城與魏晉洛陽城的雙城制和帝國(guó)時(shí)代的時(shí)間差,應(yīng)該是物質(zhì)文化與政治文化發(fā)展中的相對(duì)滯后性決定的),并為此后隋大興城、唐長(zhǎng)安城、宋開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襲。
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范文6
關(guān)鍵詞:春秋時(shí)期;美金,惡金;青銅;
一、問題的提起
“美金”、“惡金”二詞,出自《國(guó)語》等先秦古籍。《國(guó)語·齊語》載:“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nèi)政矣,齊國(guó)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duì)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鞺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詛、夷、斤、斫,試諸壤土。甲兵大足”。相似的文字,還見:廠《管子·小匡》:管子答曰“夫齊國(guó)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詛、夷、鋸、斯,試諸木土”。《管子》的記述,約源出于《國(guó)語》。文中所記,乃春秋中葉齊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與管仲的問答之語。
關(guān)于文中“美金”、“惡金”之所指,1952年郭沫若先生在有關(guān)中國(guó)奴隸制時(shí)代的論述中曾做了如下解釋:“所謂‘美金’是指青銅。劍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銅鑄造的。所謂‘惡金’便當(dāng)是鐵。鐵,在未能鍛煉成鋼以前,不能作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銅貴美,在古代不用以鑄耕具”。[2](P33)來,郭沫若先生又多次重申這一解釋,“美金是指青銅,惡金是指鐵,也是毫無疑問的。鐵在未能鍛煉成鋼之前,品質(zhì)趕不上青銅,故有美惡之分”。[2](P203)并以鐵器的出現(xiàn)和使用作為春秋戰(zhàn)國(guó)之交奴隸制和封建制分界的一個(gè)鐵證。此外,還有不少學(xué)者持與此類似的觀點(diǎn)。如李劍農(nóng)先生也認(rèn)為:《國(guó)語·齊語》的“所謂美金,即為青銅器,惡金當(dāng)為易于酸化之鐵。《國(guó)語》所言若可信,則在春秋時(shí)期,農(nóng)器已有用鐵為之者”。[3](P26)楊寬先生也贊同此說。[4]史學(xué)大家的上述解釋,在學(xué)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從之者甚眾。對(duì)于這樣的解釋,雖然也有考古學(xué)家提出過質(zhì)疑,認(rèn)為:《國(guó)語》所言之“美金是指優(yōu)質(zhì)銅,惡金是指劣質(zhì)銅”,[5]但終未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重視。
那么,先秦古籍中的“美金”和“惡金”究竟應(yīng)當(dāng)做何種解釋呢?尤其是“惡金”究竟是指青銅還是鐵呢?雖然有三國(guó)韋昭“惡,粗也”的注釋,但僅僅從文獻(xiàn)到文獻(xiàn)進(jìn)行考證,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難以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釋。有鑒于此,這里擬從考古學(xué)上對(duì)“美金”和“惡金”進(jìn)行新的解釋,作為一種嘗試,以就正于學(xué)術(shù)界。
二、“美金”是青銅、“惡金”也是青銅的考古學(xué)闡釋
將“美金”釋為青銅、“惡金”釋為鐵的立論依據(jù),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diǎn):其一,先秦時(shí)期,劍、戟等上等兵器都是用青銅鑄造而不用鐵制造;其二,青銅貴美,在古代不用以鑄農(nóng)耕具;其三,未鍛煉成鋼的鐵,品質(zhì)不如青銅且易于氧化,故有美、惡之分。如果歷史事實(shí)確如此,將“美金”和“惡金”分別解釋為青銅和鐵未嘗不可。然而,大量考古發(fā)現(xiàn)所反映的歷史圖景,卻與上述認(rèn)識(shí)相去甚遠(yuǎn),甚至是相反,促使我們不能不對(duì)前人的解釋進(jìn)行反思。
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表明:我國(guó)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就中原地區(qū)來說,①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銅器的冶鑄已趨向成熟,從而進(jìn)入到青銅器時(shí)代。[6]至于我國(guó)古代的人工冶鐵,就中原地區(qū)來說大致始于公元前8世紀(jì)初的西周晚期,春秋戰(zhàn)國(guó)之交的公元前5世紀(jì)進(jìn)入到高速發(fā)展時(shí)期。[7]因此,公元前8世紀(jì)—公元前5世紀(jì)的春秋時(shí)期,是我國(guó)鐵器時(shí)代的初期階段,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銅鐵并用時(shí)期”。齊桓公和管仲主要活動(dòng)于春秋中葉,《國(guó)語·齊語》所記管仲相齊之事正發(fā)生于這一時(shí)期。因此,本文對(duì)有關(guān)考古發(fā)現(xiàn)的梳理和考察即以春秋時(shí)期為主,前后兼及商代、西周和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
首先,考察先秦時(shí)期的兵器。在我國(guó)古代,隨著青銅時(shí)代的到來,兵器就開始了它的青銅器化進(jìn)程。在整個(gè)青銅器時(shí)代,無論是戈、矛、劍、戟、斧、鉞還是箭鏃等,各種兵器主要都是用青銅制造的。即使進(jìn)入到鐵器時(shí)代的初期階段,各種兵器仍然主要是青銅制品。這已經(jīng)為大量的考古發(fā)現(xiàn)所證明,是毫無疑問的。但不容忽視的是,隨著人工冶鐵的出現(xiàn)和鐵器時(shí)代的到來,兵器隨之開始了它的鐵器化進(jìn)程。我國(guó)目前發(fā)現(xiàn)的中原地區(qū)最:為古老的人工冶鐵制品,主要是兵器。如河南省三門峽虢國(guó)墓地出土的3件人工鐵器,年代為西周晚期,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鐵制品,其中包括玉柄鐵葉劍、銅內(nèi)鐵援戈和銅骰鐵葉矛各1件,均為兵器。[8](P126、530)就整個(gè)春秋時(shí)期的鐵器來說,鐵兵器也有相當(dāng)數(shù)量。據(jù)初步統(tǒng)計(jì),迄今發(fā)現(xiàn)的可辨器形的春秋鐵器計(jì)51件,其中鐵兵器為18件,約占總數(shù)的35%左右,包括鐵劍、銅柄或金柄或玉柄鐵葉劍、銅內(nèi)鐵援戈、鐵鋌銅鏃等。長(zhǎng)沙楊家山65號(hào)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鐵劍,整器用碳鋼鍛造加工而成,[9]是目前所知最為古老的全鐵制兵器,說明春秋晚期全鐵制兵器已經(jīng)出現(xiàn)。進(jìn)入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兵器的鐵器化進(jìn)程大大加快,到戰(zhàn)國(guó)晚期鐵兵器已經(jīng)發(fā)展到較高水平,全鐵制劍、戟、矛、殳等大量應(yīng)用,并且出現(xiàn)了鐵制防護(hù)裝備——胄。如河北易縣燕下都戰(zhàn)國(guó)晚期的44號(hào)墓,就一次性出土鐵胄、劍、矛、戟、短劍等鐵兵器51件。[10]正是西周晚期以來鐵兵器的逐步發(fā)展,為我國(guó)古代兵器在漢代基本實(shí)現(xiàn)鐵器化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11]這就表明,商代、西周的金屬兵器的確主要是青銅制造的,但西周晚期隨著人工冶鐵的發(fā)生,鐵制兵器也隨之登上了歷史舞臺(tái);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兵器不僅用鐵來制造,并且隨著鐵器工業(yè)的發(fā)展,鐵制兵器的種類和數(shù)量都在與日俱增,開始了逐步取代青銅兵器的進(jìn)程。
其次,考察先秦時(shí)期的青銅農(nóng)耕具。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表明,我國(guó)商周時(shí)期創(chuàng)造了高度發(fā)達(dá)的青銅文明,青銅冶鑄業(yè)獲得了高度發(fā)展,但青銅農(nóng)耕具的發(fā)展相對(duì)遲緩。我國(guó)青銅時(shí)代的開始雖然始于公元前2l世紀(jì)前后,但早于公元前16世紀(jì)的青銅農(nóng)耕具迄今在中原地區(qū)尚未被發(fā)現(xiàn)。商代和西周時(shí)期,與青銅禮器、兵器及車馬器的普遍應(yīng)用相比,青銅農(nóng)耕具無論種類還是數(shù)量雖然都十分有限,并且在當(dāng)時(shí)的農(nóng)耕活動(dòng)中沒有大量應(yīng)用,[12]但青銅農(nóng)耕具的確是存在的,主要是用作砍伐的斧和錛,用于土作和田間管理的鏟、鍤、鋤、鑊、鎬和犁鏵等,以及收割工具鐮刀和铚刀等。尤其是到了春秋時(shí)期,青銅農(nóng)耕具的種類雖然沒有發(fā)生大的變化,但這一時(shí)期青銅農(nóng)耕具的考古發(fā)現(xiàn)地點(diǎn)大大增加,出土數(shù)量明顯增多,類型也趨于多樣化了。[13]譬如,江蘇六合縣程橋2號(hào)春秋晚期墓出土青銅鍤、鏟、鑿、齒刃鐮刀各1件;[14]安徽舒城縣九里墩春秋晚期墓出土銅斧、錛、鏟、齒刃鐮刀等青銅工具計(jì)15件;[15]安徽渦陽圣方樓一個(gè)東周時(shí)期的銅器窖藏出土銅鍤、鑊、鐮刀和侄刀等農(nóng)耕具80余件以及其他青銅器。僅就青銅鐮刀來說,春秋時(shí)期既有鋒刃鐮,又有齒刃鐮,僅齒刃鐮刀(據(jù)1985年的統(tǒng)計(jì))就至少在20多個(gè)地點(diǎn)發(fā)現(xiàn)55件以上,并且包括三種不同的形式。[16]到了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青銅農(nóng)耕具才同其他非金屬農(nóng)耕具一起,隨著鐵制農(nóng)耕具的逐步普及而趨于消失。很顯然,青銅雖然貴美,但在商周時(shí)期同樣用于農(nóng)耕具的鑄造——盡管其種類、數(shù)量及應(yīng)用程度遠(yuǎn)遠(yuǎn)不及青銅禮器、兵器及車馬器等,尤其是春秋時(shí)期青銅農(nóng)耕具獲得了較大的發(fā)展,是農(nóng)耕活動(dòng)中金屬農(nóng)耕具的主體。
最后,考察先秦時(shí)期人們對(duì)青銅和鐵是否存在“美”與“惡”的認(rèn)識(shí)問題。一般說來,未鍛煉成鋼的鐵,其性能的確不如青銅且易于氧化,這是事實(shí)。但如上所述,鐵器出現(xiàn)之后的春秋時(shí)期,青銅和鐵同樣都用于兵器和工具的制造,由此看不出當(dāng)時(shí)的人們對(duì)青銅和鐵存在著美與惡的認(rèn)識(shí),因此也就無法得出青銅是美金、鐵是惡金的結(jié)論。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西周晚期虢國(guó)墓出土的玉柄鐵葉劍和銅膠鐵葉矛,經(jīng)金相鑒定,鐵葉部分均為塊煉滲碳鋼制品,也就是說至遲在西周晚期我國(guó)先民已經(jīng)掌握了煉鋼技術(shù)。[17]所以,以為春秋時(shí)期尚未掌握將鐵鍛煉成鋼的技術(shù)而將鐵指稱為“惡金”的推論,顯然不符合當(dāng)時(shí)冶鐵技術(shù)發(fā)展的歷史實(shí)際。
————————
① 這里的中原地區(qū),是相對(duì)于周邊地區(qū)而言、以黃河中游為中心并包括長(zhǎng)江中下游等周圍地區(qū)在內(nèi)的廣義的中原地區(qū),亦即東周列國(guó)的統(tǒng)治區(qū)域。
考古發(fā)現(xiàn)的鐵器的出土狀況,為我們了解當(dāng)時(shí)的人們對(duì)鐵的認(rèn)識(shí)和鐵器的使用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信息。三門峽虢國(guó)墓地西周晚期的2001號(hào)墓為一座七鼎墓,并附葬一座埋葬13輛車和64匹馬的車馬坑,墓主人為虢季,是虢國(guó)的一代國(guó)君。該墓出土玉柄鐵葉劍1件,發(fā)現(xiàn)于槨室西南隅,與銅箭矢等銅兵器放置在一起;銅內(nèi)鐵援戈1件,與其他銅戈一起混放在槨室西北隅。三門峽虢國(guó)墓地2009號(hào)墓出土銅內(nèi)鐵援戈、銅膠鐵葉矛、銅銎鐵錛和銅柄鐵削刀各1件,墓主人為虢國(guó)一代國(guó)君的虢仲。甘肅靈臺(tái)景家莊春秋早期的1號(hào)墓,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有銅柄鐵葉劍工件,以及銅鼎、甎、戈等銅禮器和兵器等,墓主人為秦國(guó)貴族。[18]陜西寶雞益門村春秋晚期的2號(hào)墓,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兵器、工具、裝飾品及馬具等隨葬品計(jì)200余件,其中包括金柄鐵劍3件、金環(huán)首鐵刀13件、金方首鐵刀2件、金環(huán)首料背鐵刃刀2件等鐵器20件,以及大量黃金制品和玉器,墓主人為秦國(guó)貴族。[19]河南淅川縣下寺春秋晚期的10號(hào)墓為一槨兩棺墓,隨葬有銅鼎4件、編鐘兩套17件、石磬13件等170余件隨葬品,附葬一座車馬坑,墓葬的南側(cè)棺室內(nèi)出土玉柄鐵匕首1件,墓主人為楚國(guó)貴族。[20]山東長(zhǎng)清縣仙人臺(tái)春秋早期的6號(hào)墓,葬具為木制棺槨,隨葬有銅鼎15件、簋8件、編鐘兩套20件、石磬10件等大量禮樂器,槨室內(nèi)出土1件鐵援銅戈,墓主人為鄰國(guó)的一代國(guó)君。[21]其他出土有鐵器的春秋墓葬,也大都是貴族墓。上述各墓中的鐵制品,都是作為隨葬品與其他青銅禮器、兵器和工具等一起被隨葬的,并且墓主人都是貴族,甚至是一國(guó)之君。相反,春秋時(shí)期的大量小型墓葬中,卻很少見到用鐵制品隨葬。或可認(rèn)為,在春秋時(shí)期的人們看來,鐵不僅不是粗劣的“惡金”,反而可能是一種貴重金屬,為大小貴族所喜愛。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鐵制品仍為貴族所喜用。河南信陽長(zhǎng)臺(tái)關(guān)戰(zhàn)國(guó)早期的工號(hào)墓,墓葬主室木棺內(nèi)入骨近旁出土鐵帶鉤5件,形制各異,大小有別,或鑲嵌有金板和玉片,或用金粒和金銀絲錯(cuò)出夔龍、卷云、蟬紋等精美的圖案,墓主人為相當(dāng)于士大夫的貴族。[22]湖北江陵望山戰(zhàn)國(guó)中期的1號(hào)楚墓,墓主人身份為下大夫,墓葬的槨室中出土鐵質(zhì)帶鉤2件,均用金片和金銀絲鑲嵌出精美的花紋。[23]類似的錯(cuò)金銀鐵帶鉤,在河南汲縣山彪鎮(zhèn)、鄭州二里崗、輝縣褚邱村、山東曲阜魯故城等地的戰(zhàn)國(guó)墓中也有發(fā)現(xiàn),并且這些墓葬大都屬于大小貴族墓。墓葬中發(fā)現(xiàn)的這些鐵帶鉤,與一般的隨葬品有所不同,它們是作為墓主人的服飾穿戴在死者身上被埋葬的,一般說來是墓主人生前的實(shí)用物品。很明顯,在當(dāng)時(shí)的人們看來,鐵并不是一種劣質(zhì)金屬,否則,人們是不會(huì)在鐵制品上鑲嵌美玉或用金銀錯(cuò)飾出精美花紋的,統(tǒng)治者更是不會(huì)日常使用的。
綜合起來看,在春秋時(shí)期,戈、矛、劍、戟等兵器不僅大量用青銅鑄造,而且同樣用鐵制作;鐵被用于農(nóng)耕具的制作,青銅同樣也用于農(nóng)耕具的鑄造,尤其是當(dāng)時(shí)的金屬農(nóng)耕具主要是青銅制品;[24](P12)隨著西周晚期煉鋼技術(shù)的發(fā)明,人們不僅沒有把鐵視為劣質(zhì)金屬,反而在一定情況下可能將其視作貴重金屬,至少是與青銅等而觀之的。因此,把“美金”和“惡金”分別解釋為青銅和鐵,尤其是把“惡金”解釋為鐵,顯然是缺乏歷史根據(jù)的。
那么,“美金”和“惡金”究竟所指何物呢?或許所指皆青銅也。一方面,春秋時(shí)期人工冶鐵尚處于初步發(fā)展階段,人們對(duì)于鐵的認(rèn)識(shí)還不夠完善,鐵器的生產(chǎn)和在社會(huì)生活中的應(yīng)用還有限。另一方面,春秋時(shí)期社會(huì)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屬仍然主要是青銅,青銅冶鑄技術(shù)和生產(chǎn)發(fā)展到了高峰階段,人們對(duì)青銅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相當(dāng)成熟。《周禮·考工記》“金有六齊”的記載和現(xiàn)代冶金史學(xué)對(duì)青銅器合金成分的研究表明,當(dāng)時(shí)的青銅工匠對(duì)青銅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間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有了較為全面的認(rèn)識(shí),并能根據(jù)不同的需要通過控制銅、錫和鉛的配比鑄造出具有不同性能特點(diǎn)和用途的各種青銅器,[25](P72—74)青銅器在材質(zhì)上是有優(yōu)劣之分的。有鑒于此,或可認(rèn)為《國(guó)語·齊語》中的“美金”和“惡金”指的都是青銅,“美金”是優(yōu)質(zhì)青銅,“惡金”是劣質(zhì)粗銅。
三、余論
如果上述關(guān)于“美金”和“惡金”分別是指優(yōu)質(zhì)青銅和劣質(zhì)粗銅的考古學(xué)闡釋可以成立,那么就提出了相關(guān)的另外一個(gè)問題,即先秦古籍考釋的方法問題。
我國(guó)的先秦古籍?dāng)?shù)量大,內(nèi)容豐富,是我們研究先秦歷史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從總體上說,先秦古籍大多言有所據(jù),是可信的。但是,有不少先秦古籍或因?yàn)樗浿履甏眠h(yuǎn),或因?yàn)槌蓵鴷r(shí)間較晚,致使材料真?zhèn)坞s糅,論述有同有異,或者語言過于簡(jiǎn)略而語焉不明,雖經(jīng)漢代以來歷代史家對(duì)先秦古籍不斷進(jìn)行整理、注疏和校勘,但仍有不少內(nèi)容不甚明了或不知應(yīng)作何種解釋,成為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某些歷史問題長(zhǎng)期爭(zhēng)論不休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物質(zhì)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近代考古學(xué)產(chǎn)生之前,對(duì)先秦古籍的研究只能采用從文獻(xiàn)到文獻(xiàn)的辦法去注疏、辨?zhèn)魏涂紦?jù)。在考古學(xué)已經(jīng)取得豐碩成果并不斷發(fā)展的今天,采用文獻(xiàn)記載與考古學(xué)成果相結(jié)合的方法研究先秦古籍,一些長(zhǎng)期以來眾說紛紜或難以解決的難題,可能就會(huì)易于解決了。
自王國(guó)維先生提出以地下實(shí)物資料與歷史文獻(xiàn)資料相互印證研究古史的“二重證據(jù)法”以來,研究先秦歷史的史學(xué)家們,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注重文獻(xiàn)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的結(jié)合了,并且實(shí)踐證明這種研究方法是科學(xué)的,有效的。正如李學(xué)勤先生所指出的:充分運(yùn)用文獻(xiàn)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結(jié)合的方法,“將能開拓出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對(duì)整個(gè)中國(guó)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jià)”。[26](P19)同樣,在先秦古籍的考釋上,盡量吸收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并與傳統(tǒng)的方法有機(jī)結(jié)合,應(yīng)當(dāng)說是實(shí)現(xiàn)先秦古籍研究不斷創(chuàng)新的重要途徑和方法,有必要大力倡導(dǎo)之。
參考文獻(xiàn)
[1]郭沫若.奴隸制時(shí)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郭沫若.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鐵器出土——關(guān)于古代分期問題的一個(gè)關(guān)鍵[A].奴隸制時(shí)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李劍農(nóng).先秦兩漢經(jīng)濟(jì)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楊寬.試論中國(guó)古代冶鐵技術(shù)的發(fā)明和發(fā)展[J].文史哲,1955,(2):26—30.[5]黃展岳.關(guān)于中國(guó)開始冶鐵和使用鐵器的問題[J].文物,1976.,(8):62—70.
[6]白云翔.中國(guó)的早期銅器與青銅器的起源[J].東南文化,2002,(7):25—37.
[7]白云翔.中國(guó)的早期鐵器與冶鐵的起源[A].慶祝安志敏八十壽辰考古論文集[C].香港: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2003.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門峽虢國(guó)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9]長(zhǎng)沙鐵路車站建設(shè)工程文物發(fā)掘隊(duì).長(zhǎng)沙新發(fā)現(xiàn)春秋晚期的鋼劍和鐵器[J].文物,1978,(10):44—48.
[10]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易縣燕下都44號(hào)墓發(fā)掘報(bào)告[J].考古。1975,(4):228—248.
[11]楊泓.漢代兵器綜論[J].中國(guó)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12):55—66.
[12]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銅農(nóng)具的考古學(xué)觀察[J].農(nóng)業(yè)考古,1985,(1):70—81.
[13]白云翔.我國(guó)青銅時(shí)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及其考察[J].農(nóng)業(yè)考古,2002,(3):165—171.
[14]南京博物院.江蘇六合程橋二號(hào)東周墓[J].考古,1974,(2):105—115.
[15]安徽省文物工作隊(duì).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J].考古學(xué)報(bào),1982,(2):229—241.
[16]云翔.齒刃銅鐮初論[J].考古,1985,(3):257—266.
[17]韓汝玢.中國(guó)早期鐵器(公元前5世紀(jì)以前)的金相學(xué)研究[J].文物,1998,(2):87—96.
[18]劉得禎等.甘肅靈臺(tái)縣景家莊春秋墓[J].考古,198l,(4):298—301.
[19]寶雞市考古工作隊(duì).寶雞市益門村二號(hào)春秋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文物,1993,(10):l—19.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1]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山東長(zhǎng)清仙人臺(tái)周代墓地[J].考古,1998,(9):11—25.
[2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4]童書業(yè).中國(guó)手工業(yè)商業(yè)發(fā)展史[M].濟(jì)南:齊魯書社,1981.
[25]北京鋼鐵學(xué)院.中國(guó)冶金簡(jiǎn)史[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78.
[26]李學(xué)勤.走出疑古時(shí)代[M].沈陽: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1997.
A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good metal" and "bad 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