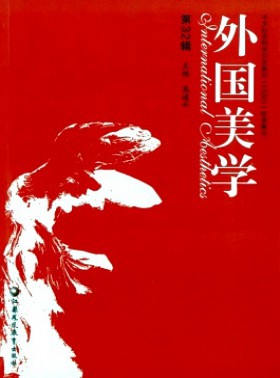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審美意象的形象特征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審美意象的形象特征范文1
康德首次從理論上闡明了審美意象的主體性、超越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在《判斷力批判》的第49節里,康德將審美意象界定為構成藝術天才的某種獨特的“心意能力”。康德說,藝術天才就是“表達審美意象的功能”,“我所說的審美意象是指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種形象顯現,它能引人想到很多的東西,卻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確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達出來,因此也沒有語言能完全適合它,把它變成可以理解的。”在康德看來,審美意象乃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表象,“它是理性的觀念的一個對立物”,聯系于“不可名狀的感情,”體現著“一個主體在他的認識諸機能的自由運用里表現著他的天賦才能的典范式的獨創性”。所以在審美意象里,形象的內蘊往往大于我們所能確切說明的部分,“以致于在一個表象里的思想,大大多過于在這表象里所能把握和明白理解的。”
意象理論是克羅齊直覺主義美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克羅齊站在直覺主義立場繼承和發展了康德關于審美意象的主體性、超越性和非理性的觀點。克羅齊的意象理論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將審美意象的非理性特征推演到極端,批評了康德企圖用美學“彌合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裂口”的做法。克羅齊說:“據說在藝術的意象里可以見出感性與理性的統一,這種意象表現出一種理念。但是‘理性’、‘理念’這些詞只能指概念”,這樣一來,又把藝術附庸于哲學,把想象歸結為邏輯,于是“故意造西方美學意成了二元性,因為在這種并列之中,思想仍是思想,意象仍是意象,兩者之間毫無聯系。”克羅齊在這里不僅是對康德美學的批評,而且是對黑格爾美學的批評。德國古典美學雖然敏銳而深刻地發現審美意象內在的感性因索與理性因素的矛盾,并且千方百計地企圖協調統一這種矛盾.但由于缺乏心理科學的實證材料,他們設想的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始終帶有空泛的思辨與猜想的性質,所以受到克羅齊的批評。克羅齊將審美意象列入純粹感性范疇,特別強調它的非理性的直覺特征。他說:“意象性這個特征把直覺和概念區別開來,把藝術和哲學、歷史區別開來,也把藝術同對一般的肯定及對所發生的事情的知覺或敘述區別開來。意象性是藝術固有的優點,意象性中剛一產生出思考和判斷,藝術就消散,就死去。”是直覺力而非想象力賦予了審美意象的整體。克羅齊認為,紛繁雜沓的感覺印象在審美過程中匯聚融合為一個具有共同中心的“綜合的意象整體”,這是審美意象區別于一般表象活動的根本特征。但審美意象的整體性的獲得,不是憑想象,更不是憑理智,而是憑象,但并不是由回憶先前的意象而得來的一大堆支離破碎的意象,”“直覺確實是藝術的,但只有當直覺具有能使它生氣蓬勃的一個有力原則,靠這個原則把直覺變成一個整體時,它才確實是直覺。”所以克羅齊反復強調,只有當直覺與意象相融相合“構成一個有機體”時,真正的藝術才能產生。三是審美意象與審美情感在直覺中的先驗綜合構成藝術的本質。克羅齊比前人更深入地考察了意象與情感的關系。他說:“藝術是直覺中的情感與意象的真正審美的先驗綜合,對此可以重復一句:沒有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沒有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康德和克羅齊分別從先驗主體論和非理性直覺論的角度奠定了近、現代西方美學審美意象理論的基礎。
情感與形式的辯證,歷來是審美意象的核心問題。科林伍德作為克羅齊的追隨者,同樣重視
情感的表現。他認為情感是通過有意識的想象性活動而得以表現。日常粗糙的、生理性的情感經由想象,變成了“理想化的情感”,即審美情感。這種情感不是直接表露的,而是在想象過程中與感覺材料、思維熔為一爐,形成受意識統轄的“想象性經驗”,即審美意象。美國著名美學家蘇珊·朗格認為,審美意象起源于由感知而得來的表象,表象訴之于想象,經過再造,成為“浸透著情感的表象”,即意象。在審美意象中,情感是形式化了的情感,形式是情感自身的形式,兩者合二為一,無可分割。意象作為表現情感的形式,即是直接可感的,又具有幻象的性質。審美意象來自生活的表象。對藝術品的欣賞,同樣是通過審美意象實現的。從這一點來看,西方的審美意象學說與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觀點可謂是殊途同歸,不謀而合。
審美意象既不同于普通表象,它已經經過出于審美需要的初步加工,具有鮮明的形象與情思相交融的特征;又不同于完成了的藝術形象,因為它尚未付諸物態化與符號化,仍是孕育于腦海中的無確定媒介、非實體、不定形的想象性形象。然而,審美意象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結構,包含著從變形趨向定形,從不確定媒介到固定媒介,從非物化到物態化和符號化的許多演變的層次。對于審美意象本身內在運動規律的研究,是20世紀興起的審美心理學的中心課題。
現代審美心理學從各個角度探討了審美意象特征與成因。弗洛伊德從精神動力學的角度解釋了審美意象的下意識深層心理的動因,韋特海默從知覺完形的角度為審美意象的綜合創造的心理機制提供了漂亮的假說,威廉·詹姆斯從意識流的角度啟迪人們將審美意象作為心理整體的一部分來掌握,皮亞杰從心理建構的角度設計了一個解釋主客體關系的新的理論框架。在現代各派心理學中,直接以審美意象為研究對象并取得顯著進展,影響較大的學說,是榮格的“原型意象”說。
榮格在《我與弗洛伊德之異同》一文里說:“主體本身其實也就是一種客觀事實,仍然是屬于世界的一部分。凡是自主體源生出來的,亦是從大地生出的。”弗洛伊德單純從主體,從個人的心理經驗,而且往往是個人病態心理經驗的角度來描述意象(夢境與幻想)與無意識深層心理的關系,特別強調意象的無意識的情感動因與本能動因;而榮格則換了一個新的角度,著重從客體、從歷史的積淀,從集體心理經驗的角度來研究意象的生成與發展,探索經驗與本能、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轉化關系與轉化條件,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他的“原型意象”說(或譯作“原始意象”說)。因此,從某種意義看,榮格的“原型意象”說彌補了弗洛伊德理論體系之不足,包含了比弗洛伊德更深更廣的客觀意義與社會歷史內容。
“原型意象”范疇的內涵是復雜的。從生理心理層面看,榮格將“原型意象”規定為可以“通過腦組織由一代傳給下一代”的某種經驗積淀而成的深層心理印跡。榮格認為,原型意象可以設想為一種記憶埋藏,一種印記或記憶痕跡,它源自同類體驗的無數過程的凝聚。從哲學層面看,榮格的原型意象理論深受康德關于精神“先驗綜合”的假說的影響,原型意象被榮格界定為
審美意象的形象特征范文2
關鍵詞:漁父;隱世;審美情結
中圖分類號:J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8-0167-01
在中國繪畫和文學史上,“漁父”形象最早出自于屈原的《漁父》之中。在古代,漁、樵、耕、讀這四種生活方式是文人、士大夫“歸隱”的理想選擇,因而漁夫的意象,也早已超出了新石器時代的那種以捕魚為生的表層含義,而被賦予了隱逸、避世脫俗的思想蘊涵,同時也寄予畫家淡泊名利、遁隱俗世和與世無爭的心境,而“漁父”也作為一個極富文人士大夫喜愛的形象在不同的時代被賦予獨特的審美意象。
在唐代,漁父的形象多數是以閑適者的身份出現的,這是由于當時的社會形勢每況愈下,因此許多文人、士大夫的抱負得不到實現,為了排遣內心的苦悶,他們只好利用繪畫來逃避現實。如王維的《輞川圖》,畫中描繪了平靜的湖水,群山環抱著的亭臺樓榭,樹林掩映下偶爾有舟楫過往的背景以及閑適的漁夫,這是一幅極富有詩意的山水畫,呈現出悠然超塵的意境,給人精神上的審美愉悅。單從畫面上看,很明顯“漁夫”并不是畫面重點,他被安排在畫面的角落;其次作者也并沒有對漁夫進行細致的刻畫,而是將他與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從而表達了畫家隱居的安寧的精神狀態。所以在唐代山水畫中的“漁父”,往往表現出文人泛舟江湖、歸隱山林的隱逸情結。
而到了北宋,畫家所表現“漁父”形象多是以捕魚來謀生的勞動者的形象。比如北宋王詵的《漁村小雪圖》、趙的《江行初雪圖卷》。而到了南宋,在“漁父”的意象中,我們卻體會不到真正的漁父之樂,而是帶有一種更為復雜的無奈,馬遠的《秋江漁隱圖》,一葉小舟停泊在蘆葦叢中,一位老漁翁懷中抱著船槳,雙目閉合蜷伏在船頭酣睡,其狀態安詳。船蓬上斜插著魚竿,左邊有乾隆帝題詩:“月落江天罷釣魚,倚舷坐睡夢華胥。蘆叢何必偏舟系,波漾風吹任所如。”這個孤獨、苦悶的“漁父”形象何嘗不是當時殘酷的現實在畫家心里的投射,在五代或者宋代的“漁父”形象中,我們體會不到真正的漁父之樂,而是帶有一種更為復雜的無奈。
相比于唐代和宋代,元代則是中國繪畫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人雅士不愿追逐名利、走仕途,而均愿隱逸山林,潛心書畫,聊以自娛。元代出現了大量的漁父圖,不管是江湖文人還是職業畫家或者是朝廷的重臣,大都是借助“漁父”形象來傾述自己的避世的情緒。
在元朝特定的政治氛圍中,士階層尤其是江南文人普遍存在著一種心靈上的壓抑感和失落感,而進取無門的士人尤其容易滋生厭世和逃世的情緒。一部分文人耽情于書畫,寄情山水林石,以求得心態上的平衡和情緒上的舒散。所以元代的“漁父”形象多是孤傲的,表現出文人、士大夫對自由、飄逸生活的向往。
到了明代,文人、士大夫塑造的“漁父”的形象,更多的是反映出世俗化傾向,并開始注重個性特征的表現。顯然宋人創作的畫面中,不僅僅有勞動人民的形象,同時也包含了知識階層的“漁隱”形象,如吳偉的《漁樂圖》中所刻劃的人物,也不再只是閑適的隱者形象,而是描繪世俗的生活場景,表現市井百姓的喜怒哀樂。漁父從畫面的點景成為畫家表現的主體,表明創作者開始注重個性特征的表達。在明代中期,隨著社會的穩定,富裕階層的日益增多,他們大多縱情享樂,追求物質,關注世俗人情,具有強烈的競爭意識。
審美意象的形象特征范文3
關鍵詞:西域各民族情歌審美思維原始思維
東方各民族很早就進入了文明時代,但發展卻較緩慢。古代人類早期的社會結構、思維方式、倫理習俗、、生產生活方式、審美情趣、藝術表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東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來了。直至近現代,東方各民族的社會心理結構、思維特點以及藝術表現特點,仍在許多方面留下了遠古時代的深刻的歷史痕跡。東方美學思想和藝術表現方法同原始思維和原始藝術結有不解之緣,甚至可以說東方各民族的審美思維是原始思維的自然延伸和發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審美思維,我們也不難發現,它的審美思維與原始思維是暗合與重疊的。
一、原始思維的具體性與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審美思維的形象化特征暗合與重疊
原始思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體性。所謂“具體性思維”,是指思維對象和內容是個別的、具體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體形態的變化運動。在這種思維過程中,始終不脫離具體的物質形象。并且這種思維還有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觀念性的東西都盡力轉化為個別的、感性的形象,并通過直觀的方式來表達。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時候,只能隨主觀心意接納萬物。“心物不分”,以客觀物質表現情感。對于原始思維的具體性特點,18世紀意大利思想家維柯在《新科學》中論證到:原始人類就好似“人類的兒童”,原始思維就好似“兒童的思維”。也就是說,原始思維不僅用形象作為思維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類比表現方式來思維。因此,原始思維的具體性特點決定了早期人類的思維方式只能是用形象來思維,從而也大大激發了原始人類的形象思維能力和豐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審美思維中,就保留著大量的具體形象思維的例子,審美思維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個重要特點。從古到今,愛情是亙古不變的話題。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對復雜、抽象、看不見的、摸不著的、無法用語言來確切表達的愛情,都有一個共同的表達特點,就是通過具體直觀的、可感受的事物來形象化地表達,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觀念性的東西都盡力轉化為個別的、感性的形象,并通過直觀的方式來表達。例如,維吾爾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鶯》中:假如我是一只夜鶯/我愿日夜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條鯉魚/我情愿投入你的網羅/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窩。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見的、摸不著的、無法用語言來確切表達的熾熱的愛情,通過具體形象的事物轉化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爾情歌:“姑娘像魚兒敏捷/我撒下的網你已看著/為什么你總從我身邊滑過?”這首情歌,表現了一位小伙子對姑娘充滿愛慕與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卻對小伙子充滿智慧的拒絕的復雜而美好的情感。這些情感復雜、抽象,無法用語言來確切表達,只可意會很難言傳。而該情歌卻用“魚兒敏捷”“撒下的網”“從我身邊滑過”等這些具體的事物,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只可意會很難言傳的深刻情感。通過上述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原始思維的具體性與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審美思維的形象化特征暗合與重疊。
二、原始思維的象征性與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審美思維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與重疊
所謂“象征性思維”,就是借用某一事物來表達具有類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質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說來,象征的事物與被象征的事物之間往往沒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類似而已。象征的含義不是從事物的本身看,而是從它所暗示的更深層的意義上看。因此,原始思維的象征性從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說從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質”的真實。但追求每一種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義,這些象征意義都是某一社會群體共同認可的,是集體無意識的表現。可見,原始思維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運用“象”來間接地表達思想、觀念,即“意”。以“意”為主,以“象”為輔,“象”隨心變,“象”隨“意”動。例如,古代中國人往往從象征性和生殖的意義上看待“石陶”“魚”“棗子”“蓮蓬”之美。象征性思維在對具體可感的形象的依賴方面,在形象和含義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上,在通過形象或符號來表達觀念的間接方法上,都同藝術的審美方式發生了重疊、重合。東方各民族在藝術表現過程中,大量運用象征、擬人、比喻、比興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擬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與人相互轉化、幻趣無窮,形成了東方藝術形象即審美意象的特征。這種審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觀”的制約、支配下,運用象征、擬人、比喻、比興等手法,按照主觀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創造出來的形象。通俗地說,意象就是用來表達某種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國的“九頭鳥”“人首蛇身像”“千手觀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審美思維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與原始思維象征性暗合與重疊。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經常運用花朵、蘋果、月亮、天鵝等意象來贊美姑娘,用夜鶯、百靈鳥等意象來表現姑娘動聽的聲音或姑娘的聰明伶俐,即用“花朵”“蘋果”“月亮”“天鵝”“夜鶯”“百靈鳥”等“象”,來表達“贊美姑娘”“贊美愛情”等“意”。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隨意性,不受客觀事物固有狀態和所謂的“物理真實性”的束縛,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達的真實和審美欣賞中個人情感體驗的真實。比如,維吾爾族情歌:“人人都喜歡紅蘋果/因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愛上了一位姑娘/因為她在姑娘中是最聰明的。”
三、原始思維的情感性與西域各民族情歌審美思維中意象的選擇性暗合與重疊
原始思維的種種特點最早集中地體現在原始宗教觀念中。原始宗教的本質是對外界進行虛幻的猜測、(轉第79頁)(接第73頁)想象和變形,而猜測、想象的核心卻是激情和欲望。在圖騰崇拜活動中,原始人類利用圖騰象征來表達主觀情緒、意念。圖騰形式就成為愿望、企圖、肯定性的情感和欲望的物化表現。這種形式直接喚起激情和欲望,激情和欲望通過圖騰形式得到充分地表現和展示。由于在原始宗教的圖騰崇拜活動中情感貫穿始終,因此,原始思維具有情感性的特征。就是說這種思維形式本身就是以情感傾向作為行動的動力的,以情感傾向去選擇喜愛或憎恨的象征物,從而表達主觀意愿的。原始思維這一特征同其他特征融匯在一起,滲透在思維的全部過程和思維的各個方面。原始思維的情感性對東方審美思維和藝術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圖騰、巫術活動促成了東方各民族敏銳的形式美感。例如,中國八卦陰陽魚形圖、漢墓磚石上雕刻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媧交尾圖形,富于裝飾意味的蓮花、桃花、梅、蘭、竹、松等形式都反映出了人們對生命力、健康、旺盛、青春、力量和美的追求。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審美思維中,我們發現以下幾種與愛情主題表面關聯不密切的自然事物,都經常被作為審美意象的選擇。比如蘋果、魚、馬、月亮等。蘋果之所以經常被作為審美意象的選擇,是因為蘋果是新疆主產的水果之一,種植歷史非常悠久。一方面,蘋果香甜可口,營養豐富,容易保存,可供食用半年以上;另一方面,蘋果外皮的漂亮、圓潤的形狀、沁人心脾的芳香都特別的誘人喜愛。以蘋果作為象征物,不僅能反映出健康、旺盛、青春和美,而且也能反映出人們對旺盛生命力的追求。所以,蘋果成為“美好”一詞的象征物,被經常運用于對姑娘的歌詠之中。以蘋果唱姑娘,在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塔塔爾族、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情歌中都流行通用。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以魚來比喻姑娘,極為常見。比如,維吾爾情歌:“白魚啊,白魚姑娘,為什么不見你沐浴陽光?嫌我不稱心嗎,比我更稱心的人又在何方?”崇拜魚的風俗及觀念,是整個中亞西亞文化圈的文化現象,是原始動物崇拜的文化沉淀。馬為什么經常被作為審美意象的選擇呢?這與西域民族的經濟生活的特定方式是分不開的。馬在游牧或半農牧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馬是牧民的第二生命。馬在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觀念中,具有比較固定的含義。一般馬的意象描寫都是為歌詠情人或意中人服務,對于各種各樣的馬以及馬的各種動態的贊頌,都是歌者為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而出現的。比如,塔塔爾情歌:瞎子渴望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騎士渴望有匹奔馳的駿馬/心上的人兒/你是我明亮的眼睛/你是我的駿馬。可見,歌手對駿馬意象的選擇,真切地渲染和表現了熱烈的愛情生活。
綜上所述,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審美思維的形象化特征、注重意象的特征,以及意象的選擇性特征,分別與原始思維的具體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特征暗合與重疊,這也充分說明了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審美思維是與原始思維暗合與重疊的。
參考文獻:
[1]邱紫華.東方美學史[M].商務印書館,北京:2003.
審美意象的形象特征范文4
中國寫意畫與中國工筆畫亦有不同,工筆畫創作雖然也有藝術直覺思維的參與,但往往要精心描畫,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表現及渲染線條節奏時,對火候的把握也都需要畫者透過以往的經驗,在感覺上、直覺上予以控制,在色彩、線條的變化和對構圖的調整上也是靠感覺,而不是用筆如飛。寫意(花鳥)畫更是徹頭徹尾地靠直覺來完成。從“置陳布勢”“經營位置”,到繪畫過程中協調畫面的“爭”與“讓”“疏”與“密”的平衡關系,每填一筆,皆為當下經驗感覺。中國寫意畫工具比較特殊,它只有依靠人的感覺和直覺來掌握其筆性,從而發揮出它的性能;比如對筆吃水上墨的控制,對用筆的輕重緩急,都是人的直覺意念客觀化的表現,也是人的情感的表達。
一、藝術直覺感知、追求的對象——氣韻生動、取象不惑
藝術直覺、藝術感知決定了寫意畫的審美取向,那就是謝赫六法中的首條——氣韻生動。畫者是如何駕馭筆墨這個載體,透過畫面來表達其內心情感,并表達宇宙萬象的活潑潑的生機的?荊浩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儀不俗。”寫意畫完全追逐畫中之“氣”也。
二、筆墨當下感覺
清人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中說:“因有所觸,乘興而動,則兔起鶻落,欲罷不能。急起而隨之,蓋恐其一往而不復再觀也。”他講的是長期積累一朝得之的繪畫經驗。在臨紙揮毫之際,不假思索,憑借的完全是藝術直覺。何處該輕描淡寫,何處精工細雕,都不靠分析,而是一看就覺得該當如此如彼,如果沒有這種藝術直覺能力是根本畫不出神采飛揚的作品的。
三、審美意象的生成
審美意象是中國畫傳統美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那么,在審美意象生成的過程中,藝術直覺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在寫意畫中,古人認為“熟視”的活動便是直覺活動。
“畫竹必先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近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蘇軾《墨竹賦》)“胸中之竹”就是“熟視”所得。“熟視”是主觀情感與外部信息相互作用的過程。換言之,“胸中之竹”是畫家的思想感情、審美趣味、創作意圖與他所獲得的表象相融而形成的審美意象,而不是一般的視覺表象。繪畫能否“傳神”寫照、“以形寫形”,關鍵一環就在于此。張作畫時說:“當其有事,已知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應于心,孤姿絕伏,融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為徒。”這是繪畫中主、客觀因素相交匯的過程的具體描繪。“物在靈府”就是指客觀事物與“心”相合而成的“審美意象”。張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也是這個意思。庸人作畫或許酷似外形物,但無神氣、無韻致,原因就在于其心中的表象未上升到審美意象。而表象要升華為審美意象,則必須靠藝術直覺作用。19世紀,法國著名畫家柯羅特別重視“即興印象”的作用。他教導他的學生們說:“你們要彌補自己的不足,要畫、要磨煉形式技巧,這對你們的繪畫是有好處的,但是,你們首要信守自己的敏感和直覺印象。”①這個敏感和直覺印象就是審美意象,依靠直覺來實現。
畫者在將其胸中意象傾瀉于紙面的過程中,為了表達心中的逸氣,常常是拋卻或脫離了筆、墨、水、色等元素,進入了一種傳統認識論中的高級狀態。海德格爾曾講過用錘子的事,認為錘子越使用越得心應手,越使人感覺不到有錘子這個工具的存在,人與對象能達到一體。工具表現的是一種“技術”、一種外在形式,這種“技術”能使人自然地達到天人一體。“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莊子),這個道理在寫意畫創作中是相通的,“形與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沈周)。當畫者在表達書寫心中美的意象的時候,往往忘記了筆墨水色這些外在技術技法,而是酣暢淋漓地一路揮灑,手心相應,與神共舞。所見精妙之處,不知何以得。這個技就是指功力,年久功力深。技一旦到了火候,便不是畫者依賴的對象,而是以即興的速度,滲透激情,精神控制,嚴謹而灑脫地一氣呵成。所有的意象皆天然生發,自然表達,瞬乎之間,神形皆得,可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嚴羽)
四、藝術直覺的無功利性特征
我們知道,一個真正的寫意畫家,他們的藝術直覺能夠通過心、眼、手配合,創造出大量的形神俱備的作品。中國畫中也有很多的程式,在程式歸納之后,對所表達的物象不需再作知性分析和了解,只是整體感悟自應;而在寫意過程當中,只有具備不受污染無功利之心的審美心胸方可直覺到藝術的妙處,畫面形象的創造才能心手無礙地互應互合,這樣方可“書寫胸中逸氣”。由于墨濕易散,紙質吸墨又極其迅速,筆觸必須不可遲疑地快速完成,因此,體內由手到紙的氣的流動,一定要無阻無礙。如同太極拳的每一個動作,都必須讓體內的氣自由無阻地流動,才可以使我們復歸自然。道家崇尚自然,認為自然態產生自然生機。張彥遠曾概括:“運思揮毫,意不在畫,故得手于畫……不滯于手,不凝于心,不知然而然。”
所以,藝術直覺只在無功利思想的狀態下才最能體驗到審美對象的本質內涵,直覺在認知當中,都要進入一個絕對集中而忘我的情境之中去,一旦有了功利之雜念,就會極大地影響心與物的交流與對應,從而很難生成審美意象。
注釋 :
①(前蘇聯)阿爾巴托夫,羅斯托夫采夫編.佟景韓譯.美術史文選.人民出版社. 1982-11-01
參考文獻 :
[1]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第4卷).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第2版.
[2]馮家程.康德與中國現代美學. 上海百花出版社,2004.第1版.
[3]李青春.藝術直覺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第1版.
[4]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版.
[5]陳新漢.審美認識機制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第1版.
[6]陳鴻祥.人間詞話.三聯出版社,2001.第1版
審美意象的形象特征范文5
關鍵詞: 中國古典詩歌 審美 意象 翻譯
1.引言
意象是文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概念。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蘇珊?朗格在《藝術問題》一書中指出:“藝術符號確是一種終極的意象――一種非理性和不可用言語表達的意象,一種訴諸與感受的東西。”那么究竟意象是什么?它又具備哪些美學特征?譯者如何從審美心理的三要素出發來傳譯意象美?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2.意象的涵義及其美學特征
中國詩的審美,如戴容州所云:“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司空圖,《與極浦書》);也如嚴羽所言,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話?詩辯》)。正因為如此,漢語詩歌的意象就不是“目擊可圖”的文字語詞所指的表面形象及內容,而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圖,《與極浦書》)。
3.從審美心理三要素來看意象的傳譯
構成審美要素的第一個要素是感知。感知包括簡單的感覺和較復雜的知覺。而其中知覺又是較為抽象的,它是對完整形象的整體性把握,甚至還包含著對這一完整形象所具有的種種含義和情感表現性的把握。藝術家在創作中有時就是利用知覺按照對象所揭示的情感表現性去分類,而不是按照它們原本的客觀屬性,如“枯藤,老樹,昏鴉”雖是三種不同的事物,但由于它們的情感表現形式相同,所以詩人就把它們排列在了一起。審美知覺在表面上是迅速和直覺地完成的,但在它的后面卻隱藏著觀察者的全部生活經驗,包括他的信仰、偏見、記憶、愛好,從而不可避免地有著想象、情感和理解的參與。
試舉一例分析:
原文:竹里館
?搖?搖?搖 王維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譯文(1):A Bamboo Grove
In the quite bamboo grove,I sat alone.
There I played my cither;whistled long and low.
To the people in the woods,such was not known.
The bright moon sets the grove,with romance,aglow.
?搖?搖?搖?搖?搖――tr.Xu Zhongjie
譯文(2):Hut among the Bamboos
Sitting among the bamboos alone,
I play my lute and croon carefree.
In the deep woods when I’m unknown,
Only the bright moon peeps at me.
?搖?搖?搖?搖?搖――tr.Xu Yuanzhong
譯文(3):Bamboo Mile Lodge
Alone I sit in the dark bamboo,
strumming the lute,whistling away;
deep woods that no one knows,
where a bright moon comes to shine on me.
?搖?搖?搖?搖?搖――tr.B.Watson
竹里館也是輞川一“景”。此詩寫隱居者在極為幽靜環境中的高雅自由。這是王維的一首典型的表現靜謐的田園詩,但這種靜又不是單純的靜,而是以動襯靜,一種超凡脫俗的“虛靜”狀態。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三種譯文的特色。首先是意象“幽篁”的傳譯:“幽”是一個多義詞,用“dark”來譯顧及它的幽暗、幽深而顧不到幽靜、幽雅,而用“quiet”則正好相反。“幽篁”辭出自《楚歌?九歌?山鬼》:“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終不見天”正表現出篁竹折天蔽日的深幽。許氏干脆舍去這種矛盾處理而不譯,不失為一個小小的遺憾。因為幽篁正是詩人所處的大背景,是宣泄后來一切情愫的基調,是整個以動襯靜意象的大前提。因為用此種格式塔意象中介來建構立體的視覺圖象,能在語言轉換的同時,塑造一個完整和諧的情景畫面,使譯文讀者獲取語言意義和情景因素雙重體驗。而格式塔意象中還特別強調一種連貫一致性,因為后來的“獨坐”已反映出“冷寂”的一面,這里的“幽篁”何不補足另一面的特質“幽暗”呢?這樣從色彩光線和整體環境兩個方面都做了渲染,加深了悠閑怡悅的氛圍。
“彈琴”這個意象在唐詩中一般用來表示一種不合時宜的清高脫俗的情感,這里主要是形容詩人獨處時的悠閑自在、無拘無束的情態。Watson的“strum”一詞正傳達了這種漫不經心的清閑感,一種超脫的情境躍然紙上,可謂妙手偶得之。而兩個現在分詞的連用,也似乎要將這種無邊無際的清寂繼續下去,以至無窮,給人以無限遐想和回味,將這種萬“靜”叢中一點“聲”的意境又向前推了一步。而許譯“croon carefree”也給人一種輕松愉快、無憂無慮的感覺,但似乎表達得過于透,沒有給讀者自我體驗的余地。另外,徐譯的“played my cither”也是直譯,客觀地模擬事實,而“whistled long and low”有所彌補,吹蕭聲猶如詩人的處境般悠長而孤清。
而第三句“深林人不知”是一句典型的漢語意識流的組織排列結構。人不知“什么”,是人不知詩人還是不知深林?從表面上看是不知“林”,可是詩人處于這幽林之中,不知“林”就等于是不知“人”,可謂一語雙關。徐譯可謂聰明,大約體會到了作者的用心,但又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方法,干脆用“such”關系代詞把“人”和“林”都包括進去了。而許選擇不知人,Watson則選擇不知林,都可謂言之有理。因為二者的歸屬都是一樣的,再現林子的深幽偏僻,是對前兩句的一個總結,體現了詩人雖不是“不吾知其亦已兮”的牢騷話,卻也對自身的處境小有遺憾。
最后一句可謂是三、四兩句之間的一個小小的蕩漾,其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來相照”與“人不知”意義正好相對,正好彌補了詩人那小小的遺憾而歸于圓滿。Watson和徐忠杰都強調了月亮照射的靜態描寫,這樣不免顯得沒有活力,沒有做到以動襯靜,而是以靜寫靜,更加不會給人以月亮像小人兒跳出的那種小小的意外感。Watson還稍微略勝一籌,用“come”一詞展現了些許動態感。而許淵沖的“peep”一詞,可謂神來之筆,把月亮那種無意中顯露、若隱若現的情態刻畫得惟妙惟肖,似乎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如小姑娘般的害羞臉龐探出頭來,增添了無數情趣和動感。將整個之前的“幽簧”“深林”等靜謐的意象群一下子升華到具有生命流動氣息的可愛月亮上,可謂有生命活躍氣息的“靜”,而非死“靜”。讀者也仿佛走入了那個幽林中,看到那皎潔的明月打那篁竹的空隙間鉆出來,脈脈相窺,直令人心境為之澄徹。
4.結語
詩歌翻譯是文學翻譯中最難的,也是“有翻譯中層次最高的一種翻譯”。之所以難,就在于詩的表面文字可譯而詩的意象和意境卻很難翻譯,本文從構成審美心理的三要素出發,分析了審美意象產生的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實際的審美活動中這三種要素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滲透和相互融合的,而沒有截然的分界線。接著再通過剖析諸譯例審美意象的傳譯的得失成敗,揭示了如何從審美角度出發較好傳譯詩歌意象的某些策略和方法,這對更好地展開詩歌翻譯實踐和批評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1]陳銘.意與境――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味[M].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
[2]陳植鍔.詩歌意象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3]胡經之.文藝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姜秋霞權曉輝.文學翻譯過程與格式塔意象模式[J].中國翻譯,2000,(1).
[5]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鑒賞辭典編纂中心編.古詩文鑒賞辭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6]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7]騰守饒.審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8]文殊選注.詩詞英譯選[Z].北京:外語研究與教學出版社,1989.
[9]許淵沖.唐詩三百首新譯[Z].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
[10]徐忠杰.唐詩二百首英譯[Z].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
[11]張保紅.論詩味的翻譯[J].外語教學,2004,(6).
審美意象的形象特征范文6
一、 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詩中發生的形態
民俗文化是杜詩創作的重要文學對象。從語料學角度看,其在杜詩中存在的形態大致可歸納為三類。
1、審美意象形態。所謂審美意象,是“一種由主體感知的語義形象”。這種語義形象“借助于主體的心理與文學語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體的頭腦中呈現”。它“不指涉實在,它是文學語言的指歸,又是文學語言創造文學世界的實體和手段”。[1]
審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詩中存在的基本形態。它以寫物圖貌為其顯現的基本途徑。
如龍的意象。龍是中國原始社會形成的一個綜合圖騰意象。在其傳承的過程中,積淀了豐富的飽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義。杜甫在其1457首詩中,有80多首詩中以龍為意象塑造文學對象。這個意象出現近100次[2],可見,杜甫十分喜歡以“龍”的意象構建其文學客體。
詩人以“龍”寫音樂之動人是“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渼陂行》)。著一“龍”字,樂之仙韻,宛如耳畔。
詩人以“龍”寫水勢是“蛟龍不自謀”(《江漲》);“蛟螭乘九皋”(《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狀樹木的造形是“偃蓋反走虬龍形”(《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白摧朽骨龍虎死”(《戲為韋偃雙松圖歌》),“虎倒龍顛委榛棘”(《楠樹為風雨所拔嘆》)。著一“龍”字,整句詩可謂靈氣飛動,意蘊盎然。
此外,同類的如鳳凰、麒麟等圖騰意象,其他如神話、仙話、傳說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廣泛地以審美意象的形態存在于杜詩之中。
杜甫選用民俗意象為其詩歌載體,使其傳達的體驗能準確地在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雙方找到契合點,從而引發較大的聯想空間,產生較好的藝術效果。
2、典故形態。典故即“故事”。它在傳承過程中其意義指向較意象直接而穩固。杜甫賦詩,不僅喜尚經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語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類。
以民俗典故寫志。最典型的當推“稷契”兩個傳說人物。稷,五谷之神。《禮記·祭法》中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契是傳說中的商之遠祖,亦知農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將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謂“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稷契易為力”(《客居》),便是明證。
以民俗典故寫情。民俗故事與經典文化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會的有序化,相對忽略個體價值;前者則更傾向于個人感性的滿足與對社會羈絆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寫情,主要是借以寫怨情。
例如,天寶十四年(755),詩人游宦長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大志受辱,慨然而嘆:“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去矣行》)。
《魏書》載:“李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訪藍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傳說,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說,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寫一己牢騷,頗為傳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過程中,往往攜帶大量的集體無意識、社會心理內容。杜詩將個體情緒依托到這類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義更具穿透力。
3、文學對象形態。杜甫以民俗文化作為文學對象,是詩歌國度中比較獨特的一幟。而他以民俗文化作為文學對象,又主要是對其進行價值評判。
從杜詩中整理出的幾個民俗文化因素的發生形態來看,杜甫對民俗的認識基本上是客觀準確的,也是比較完整的。這說明杜甫對待民俗文化的認識是具有一定的自覺性的。以民俗文化為觀照對象,往往要求認識主體具有強有力的判斷力。杜甫自幼精熟內典,以此優勢,吸收民俗文化專題入詩,在客觀上形成了觀點鮮明,情感豐厚,意義蘊藉的特征。
中國古典詩歌,自魏晉進入自覺期,其主要特征即個人寫作取代群體寫作而成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識為貴族階層壟斷的時代,文人創作者往往因其階級局限與時代影響,視貴族情感為人類情感的全部,視精英文化為人類文化的全部。而文學面對的對象世界是人類的整體情感世界,創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結構的缺失,無意會影響其作品的文學性與人類性的功能發揮。魏晉以降,寫作個人化在當時特定背景下所成的兩個直接流弊即玄言詩派和宮體詩派的生成。這兩個詩派正是因其輻射的情感世界涵蓋的文化視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現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敗。
杜甫詩歌創作的民俗文化視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國詩歌的一些偏頗走向。對后人創作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可以說,杜甫創作對民俗文化視角的建構,從某些方面看正是變盛唐之音者。從整個詩史看,這一建構無疑又具有提升整個中國古典詩歌品質的意義。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