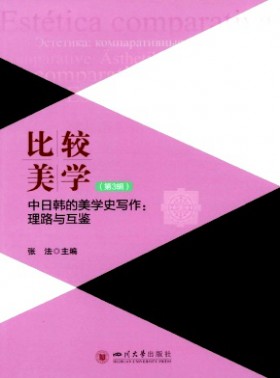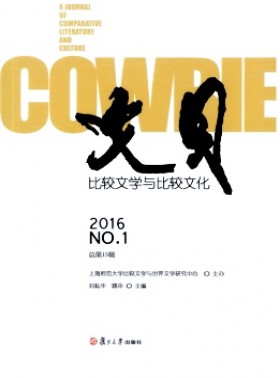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wǎng)精心挑選了比較文學(xué)范文供你參考和學(xué)習(xí),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fā)你的文章創(chuàng)作靈感,歡迎閱讀。
比較文學(xué)范文1
對(duì)于國(guó)際比較文學(xué)界的發(fā)展趨勢(shì),中國(guó)學(xué)界也做出了積極的應(yīng)答,由此形成了1996、1997年國(guó)內(nèi)討論的幾大熱點(diǎn)話題。
比較“文學(xué)”與“文化”談
早在1994年,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樂黛云教授就在《比較文學(xué)新視野》一文中指出“當(dāng)前比較文學(xué)發(fā)展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就是和文化研究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越來(lái)越“趨向于一種多元文化的總體研究;圍繞一個(gè)問(wèn)題或一種現(xiàn)象,在不同文化體系中進(jìn)行相互比照和闡釋”。〔2〕劉象愚、曹順慶等學(xué)者也相繼提出,“當(dāng)代比較文學(xué)的論爭(zhēng)已經(jīng)離開了文學(xué)的領(lǐng)域,爭(zhēng)論的要點(diǎn)已經(jīng)不是在文學(xué)的范圍內(nèi)比較文學(xué)如何進(jìn)行的問(wèn)題,而是比較文學(xué)究竟是一種文學(xué)研究還是文化研究的問(wèn)題”〔3〕,“在比較文化大潮涌起之時(shí),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為了能夠盡快融入國(guó)際化的文化語(yǔ)境之中,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所舉行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也均以此為題。如主題為“文化:中西對(duì)話中的差異與共存”的1996年南京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學(xué)者們將討論的焦點(diǎn)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識(shí)的觀照下由差異走向共存,并通過(guò)中西文字在言、象、義三個(gè)方面的對(duì)比,探討其對(duì)于中西不同思維方式的影響。此外,與會(huì)者還圍繞著人文精神對(duì)于中西不同的時(shí)空觀與生死觀進(jìn)行了剖析,并強(qiáng)調(diào)了在全球表面趨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異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東大學(xué)召開的“跨世紀(jì)的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研討會(huì)上,學(xué)者們普遍認(rèn)為比較文學(xué)向比較文化的轉(zhuǎn)變,拓寬了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范疇,這是一個(gè)機(jī)遇,但同時(shí)由于本學(xué)科所特有的不確定性,從而亦面臨著嚴(yán)峻的挑戰(zhàn)。
影響最為廣泛的則是在歷屆年會(huì)中規(guī)模最為盛大的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學(xué)會(huì)第五屆年會(huì)暨國(guó)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會(huì)議的主題定為“文學(xué)與 文化對(duì)話的距離”。在這次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上,中外學(xué)者大力倡導(dǎo)東西方文化、文學(xué)平等對(duì)話,并認(rèn)為在世界范圍內(nèi),比較文學(xué)走向比較文化是大勢(shì)所趨,世界人文科學(xué)的發(fā)展正經(jīng)歷著一次新的科際整合。與會(huì)者還對(duì)中西詩(shī)學(xué)的異同、闡發(fā)、對(duì)話等問(wèn)題作了較為全面的探討,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及文論話語(yǔ)應(yīng)盡快完成現(xiàn)代化轉(zhuǎn)換,通過(guò)與西方對(duì)話發(fā)現(xiàn)差異,從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發(fā)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一切都表明,“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界也已經(jīng)加入了國(guó)際比較文學(xué)界從比較文學(xué)向比較文化發(fā)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將在世紀(jì)之交成為國(guó)際國(guó)內(nèi)比較文學(xué)研究更新發(fā)展的顯性話語(yǔ)”。〔6〕
就此,樂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較文學(xué)的國(guó)際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對(duì)于比較文學(xué)之所以“呈現(xiàn)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機(jī)”、發(fā)生歷史性轉(zhuǎn)化的前提條件進(jìn)行了分析。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論的隱退帶來(lái)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從而使得比較文學(xué)新的國(guó)際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義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歸原充分發(fā)掘本民族的文化特點(diǎn),大大豐富和發(fā)揮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會(huì)因素則是信息時(shí)代的來(lái)臨,使得“任何自我封閉、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圖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這一切為比較文學(xué)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較文學(xué)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質(zhì)的西方文化體系內(nèi)部,而是在歐美、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異質(zhì)文化的比較中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廣闊空間。事實(shí)上,我們正經(jīng)歷著一場(chǎng)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偉的工業(yè)革命和文化轉(zhuǎn)型,過(guò)去得到廣泛認(rèn)同,認(rèn)為無(wú)可置疑的默認(rèn)常規(guī)都已受到挑戰(zhàn)而變得不確定。”由此,樂先生做出了相應(yīng)的預(yù)測(cè),盡管如今比較文學(xué)“面臨著民族文化復(fù)興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種種復(fù)雜的新問(wèn)題和悖論”,但“只要迎接挑戰(zhàn),提出新的理論和解決問(wèn)題的辦法,比較文學(xué)就會(huì)發(fā)展到一個(gè)嶄新的階段”。〔7〕只是在這個(gè)新階段到來(lái)之前,還有諸多問(wèn)題亟待解決。
例如,比較文學(xué)是應(yīng)以文學(xué)研究還是以文化研究為本?文化研究會(huì)不會(huì)導(dǎo)致文學(xué)本體的失落?學(xué)科邊界的泛化將會(huì)對(duì)比較文學(xué)自身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話題都是頗有爭(zhēng)議的。
對(duì)于“文化研究是對(duì)文學(xué)研究的一種開拓”這一命題,國(guó)內(nèi)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并對(duì)其發(fā)展前景相當(dāng)樂觀。如樂黛云教授認(rèn)為,“比較文學(xué)通過(guò)文學(xué)文本研究、文化對(duì)話和文化誤讀現(xiàn)象,研究時(shí)代、社會(huì)及諸種文化因素在接受異質(zhì)文化中對(duì)文學(xué)文本所起的過(guò)濾作用,以及一種文學(xué)文本在他種文化中所發(fā)生的變形。這種研究既豐富了客體文化,拓展了客體文化的影響范圍,也有益于主體文化的更新”。〔8〕葉舒憲教授也提出“比較的視界僅僅停留在‘文學(xué)’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華到比較文化的透視高度……‘文化’視角的引入是解放學(xué)科本位主義囚徒的有效途徑,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遠(yuǎn)……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說(shuō):比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較文學(xué),但有深度有洞見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自然是比較文化。換言之,比較文學(xué)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義的結(jié)論,那將是其學(xué)術(shù)深度的最好證明。”〔9〕
但是,同樣的命題在另一些學(xué)者眼中卻意味著新的危機(jī)與挑戰(zhàn)。正如當(dāng)代美國(guó)著名文藝?yán)碚摷摇⒖的螤柎髮W(xué)比較文學(xué)系主任喬納森·卡勒針對(duì)有些學(xué)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幟指出的那樣:“如果將比較文學(xué)擴(kuò)大為全球文化研究,就會(huì)面臨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機(jī)”,因?yàn)椤罢沾税l(fā)展下去,比較文學(xué)的學(xué)科范圍將會(huì)大得無(wú)所不包,其研究對(duì)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種類的話語(yǔ)和文化產(chǎn)品”。〔10〕事實(shí)上,比較文學(xué)是不可能涵蓋所有的人文科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的,那么其所設(shè)想的比較文學(xué)的廣泛性也就無(wú)異于鏡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較文學(xué),那比較文學(xué)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說(shuō),劉象愚、曹順慶等教授對(duì)這一問(wèn)題如此重視并非是空穴來(lái)風(fēng)。劉象愚在《比較文學(xué)的危機(jī)和挑戰(zhàn)》一文中,將這種“研究目的不是為了說(shuō)明文學(xué)本身,而是要說(shuō)明不同文化間的聯(lián)系和沖撞”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jī)A向稱為“比較文學(xué)的非文學(xué)化和泛文化化”。并強(qiáng)調(diào),“這種傾向使比較文學(xué)喪失了作為文學(xué)研究的規(guī)定性,進(jìn)入了比較文化的疆域,導(dǎo)致了比較文化湮沒、取代比較文學(xué)的嚴(yán)重后果。”同時(shí),他也對(duì)這種“泛文化”出現(xiàn)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認(rèn)為其哲學(xué)背景是后現(xiàn)代的各種思潮。“其中以解構(gòu)主義思潮對(duì)文學(xué)和文學(xué)研究的消解為最烈。”當(dāng)強(qiáng)勁的解構(gòu)主義浪潮將文學(xué)的自身本質(zhì)特征消解殆盡,“文學(xué)變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語(yǔ)言的游戲’”之后,文學(xué)自身的失落必會(huì)令比較文學(xué)變成純語(yǔ)言學(xué)、符號(hào)學(xué)、修辭學(xué)的研究,呈現(xiàn)出非文學(xué)化的傾向。此外,打破了學(xué)科界限卻缺乏理論上的有機(jī)統(tǒng)一性、將文學(xué)文本與非文學(xué)文本混為一談的新歷史主義,關(guān)注焦點(diǎn)始終停留在文化層面上的女性主義和新,也都是令比較文學(xué)向比較文化轉(zhuǎn)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比較文學(xué)必須固守文學(xué)研究的立場(chǎng),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當(dāng)然要跨越民族文學(xué)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學(xué)科的界限,但不論跨到哪里去,都必須以文學(xué)為中心,以文學(xué)為本位。換言之,研究者的出發(fā)點(diǎn)和指歸,必須是文學(xué)。在比較文學(xué)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為文學(xué)研究的補(bǔ)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較文化中,它才能成為核心。”“比較文學(xué)和比較文化是兩個(gè)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領(lǐng)域,比較文學(xué)是比較文化的一個(gè)層面,比較文化是比較文學(xué)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這一論點(diǎn)得到了許多學(xué)者的認(rèn)同。謝天振在《面對(duì)西方比較文學(xué)界的大爭(zhēng)論》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較文學(xué)向跨學(xué)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發(fā)展,這是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本身特點(diǎn)所早已決定了的”。但是,跨學(xué)科、跨文化的研究不應(yīng)抹殺或混淆比較文學(xué)作為一門文學(xué)研究學(xué)科的性質(zhì)。“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應(yīng)該以文學(xué)文本為其出發(fā)點(diǎn),并且最后仍然歸宿到文學(xué)(即說(shuō)明文學(xué)現(xiàn)象),而不是如有些學(xué)者那樣,把文學(xué)僅作為其研究的材料,卻并不想說(shuō)明或解決文學(xué)問(wèn)題”。總而言之,比較文學(xué)與比較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定位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較文學(xué),而不是以比較文化取代比較文學(xué)”,否則,“必然導(dǎo)致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危機(jī),甚至導(dǎo)向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消亡”。〔1 3〕
那么,這場(chǎng)由比較文學(xué)與比較文化關(guān)系問(wèn)題所引發(fā)的討論,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樣的問(wèn)題呢?謝天振等學(xué)者認(rèn)為,這些爭(zhēng)議均來(lái)自“對(duì)比較文學(xué)自身學(xué)科理論研究的闕如和忽視”。比較文學(xué)自身所特有的邊緣性,“一方面使它充滿活力,成為本世紀(jì)文學(xué)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點(diǎn)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顯得范圍空泛、方法繁雜”。這既“擴(kuò)大了學(xué)科之前的新領(lǐng)地”,也“使一個(gè)國(guó)家的學(xué)科與他國(guó)學(xué)科之間的界限模糊”。〔14〕前國(guó)際比較文學(xué)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福克瑪?shù)热松踔琳J(rèn)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必要去專門談比較文學(xué)理論了,甚至沒有必要去討論比較文學(xué)作為一門獨(dú)立學(xué)科的意義,因?yàn)槲乃嚴(yán)碚撗芯客耆梢詫⑵淙《?duì)于比較文學(xué)究竟是作為獨(dú)立的學(xué)科還是作為方法論更為適當(dāng),學(xué)科理論究竟存在何種特征與疏漏,中國(guó)學(xué)者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由于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所獨(dú)具的邊緣交叉性、開放性,為其劃定學(xué)科界限是相當(dāng)困難的。正如樂黛云教授所說(shuō):“不設(shè)限,不成其為學(xué)科,固定設(shè)限又妨礙學(xué)科的發(fā)展”,這門學(xué)科注定在“名”與“實(shí)”的不斷發(fā)展中走向成熟。〔15〕劉象愚教授更是認(rèn)為,比較文學(xué)作為一門新興學(xué)科,“自身的理論建設(shè)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解決,從這一學(xué)科具有開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說(shuō)它永遠(yuǎn)不可能獲得徹底解決,這就是說(shuō),它的界定將處于一個(gè)永無(wú)終結(jié)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中。它將永遠(yuǎn)面對(duì)來(lái)自各方面的挑戰(zhàn),永遠(yuǎn)需要說(shuō)明自己是什么。”〔16〕對(duì)于這個(gè)問(wèn)題,饒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們現(xiàn)在所應(yīng)該做的,是“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wèn)題”,從一個(gè)個(gè)具體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入手進(jìn)行研究。
當(dāng)然,學(xué)科理論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著理論的可有可無(wú),而是表明這種理論“具有一種開放性的體系,它能不斷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斷地吸納其他學(xué)科的理論來(lái)豐富自己。”正如謝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探討比較文學(xué)自身的學(xué)科理論,并不意味著要求人們圍繞著所謂的比較文學(xué)定義進(jìn)行無(wú)休止的概念游戲,而是要求對(duì)比較文學(xué)的基本概念、研究對(duì)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進(jìn)行探討,尋找比較文學(xué)之所以區(qū)別于其他學(xué)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對(duì)在新形勢(shì)下如何開展比較文學(xué)研究進(jìn)行深入的、具體的思考,并作出有實(shí)踐指導(dǎo)意義的理論總結(jié)。”〔17〕陳悖進(jìn)而將學(xué)科的理論建設(shè)具體限定在了兩個(gè)方面,“一是關(guān)于建立學(xué)科的理論基礎(chǔ)和指導(dǎo)思想的研究,二是關(guān)于本學(xué)科學(xué)術(shù)研究和自身發(fā)展的各種問(wèn)題的理論探討。”〔18〕至于學(xué)科理論的核心規(guī)范,劉象愚教授則將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學(xué)、跨學(xué)科、文化、語(yǔ)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學(xué)性、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質(zhì)之上,正是這二者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和辯證互動(dòng)構(gòu)成了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理論的核心”。〔19〕
總而言之,以往作為理論背景出現(xiàn)的文化在文學(xué)研究中將凸顯出來(lái),這已是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后文學(xué)時(shí)代”的全球話語(yǔ)的普遍定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轉(zhuǎn)型。文化研究對(duì)于比較文學(xué)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實(shí)的雙刃劍,至于其是否能夠切實(shí)起到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將其淡化甚至是湮沒,還在于用劍之人,即比較文學(xué)研究者自身對(duì)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與應(yīng)用。
“后殖民主義”與“中國(guó)學(xué)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與文論》上,有兩組代表了文學(xué)研究新趨勢(shì)、極為重要的筆談,分別是圍繞“后殖民主義”與“中國(guó)學(xué)派”這兩個(gè)話題展開的。
與“比較文化”對(duì)于學(xué)科影響的本質(zhì)性相比,“后殖民主義”對(duì)于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沖擊似乎來(lái)的更為外在,也更為直接。對(duì)于這一思潮力量之強(qiáng)勁,學(xué)者張頤武究其原因,認(rèn)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yǔ)所編碼的那種普遍性/特殊性、時(shí)間上的滯后/空間上的特異的二元對(duì)立,有力地切入當(dāng)下中國(guó)的“狀態(tài)”及歷史之中。這種中西雙向的闡釋策略能夠“以理論獲得對(duì)當(dāng)下狀態(tài)的分析,以當(dāng)下的狀態(tài)反思理論”,從而“獲得一種新的、打破舊框框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性”。〔20〕王寧、陳躍紅等教授則對(duì)于“后殖民主義”的本質(zhì)進(jìn)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們認(rèn)為,盡管其從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構(gòu)的特質(zhì),對(duì)于西方的中心主義與第三世界所處于的“他者”角色有較為清醒的認(rèn)識(shí),但仍是對(duì)“以往的舊殖民體系的一種‘新殖民主義’之內(nèi)部的批判”的繼承和強(qiáng)化。這是由后殖民主義批評(píng)家本身所具有的兩重性決定的,應(yīng)該引起學(xué)者們的關(guān)注。〔21〕陶東風(fēng)在對(duì)“后殖民批評(píng)”流行于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浪潮的現(xiàn)象進(jìn)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檢視西方中心主義或東西文化關(guān)系時(shí),必須有一種超越民族主義之上的文化價(jià)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標(biāo)準(zhǔn)或文化相對(duì)主義來(lái)消解文化價(jià)值的普遍標(biāo)準(zhǔn)”的獨(dú)到見解,并認(rèn)為“這是擺脫我們?cè)谖幕拿褡寤c世界化兩種訴求間緊張關(guān)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體到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lái),許多中外比較文學(xué)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論與殖民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的桎梏。這對(duì)于歐洲知識(shí)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擺脫自身的殖民傾向,努力接受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較,意味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píng)及學(xué)習(xí)的形式”。而對(duì)于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界,則是面臨著“在后殖民的全球語(yǔ)境下,如何對(duì)待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的問(wèn)題。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談到的那樣,“世紀(jì)之交后殖民階段的到來(lái)促使民族文化復(fù)興、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為全球主流話語(yǔ)的一個(gè)重要原因”,人們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異態(tài)分布,都有其獨(dú)特的價(jià)值,因此在尋求全球共享文化價(jià)值的過(guò)程之中進(jìn)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話語(yǔ)以求異質(zhì)文化的交融共鑄便成了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23〕
對(duì)此,樂黛云教授認(rèn)為,西方中心的隱退并不意味著另一個(gè)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只能是“以互補(bǔ)、互識(shí)、互用為原則的雙向自愿交流”,而這正是后殖民時(shí)代比較文學(xué)的基礎(chǔ)。這就推衍出與其密切相關(guān)的兩個(gè)問(wèn)題,“其一是如何理解傳統(tǒng)文化,用什么樣的傳統(tǒng)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過(guò)何種方式交流。”樂先生提出,“我們用以和世界交流的,應(yīng)是經(jīng)過(guò)當(dāng)代意識(shí)詮釋的、現(xiàn)代的、能為現(xiàn)代世界所理解、并在與世界的交流中不斷變化和完善的中國(guó)文化”。至于如何交流,這主要取決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溝通的話語(yǔ),“雙方都能認(rèn)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談規(guī)則”。各個(gè)文化群體或個(gè)人之間所進(jìn)行的自由對(duì)話是在各自的話語(yǔ)中完成的。“這里所用的話語(yǔ)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對(duì)方的文化場(chǎng)中經(jīng)過(guò)了變形的。”在多種文化體系間進(jìn)行平等對(duì)話中,“可能會(huì)借助舊的話語(yǔ),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話語(yǔ)也會(huì)逐漸形成。這種新的話語(yǔ)既是過(guò)去的,也是現(xiàn)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這樣的話語(yǔ)逐步形成的過(guò)程中,世界各民族就會(huì)達(dá)到相互的真誠(chéng)理解。”〔24〕與樂先生從國(guó)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義時(shí)期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不同,劉象愚教授則將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國(guó)家的不同種族之間。他側(cè)重于“族群”,即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研究,認(rèn)為“后殖民主義在解構(gòu)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quán)主義,力圖重新審視東方的同時(shí),也催發(fā)了比較文學(xué)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現(xiàn)為從互為他者的立場(chǎng)出發(fā)重新審視、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對(duì)事實(shí)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從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權(quán)和差異的根源”。族群研究所體現(xiàn)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邊緣的關(guān)系。對(duì)于這種少數(shù)族裔文學(xué)與文化的研究,如今業(yè)已成為比較文學(xué)中一個(gè)極其重要的領(lǐng)域。〔25〕
至于比較文學(xué)的“中國(guó)學(xué)派”問(wèn)題,自李達(dá)三、陳鵬翔等著名學(xué)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幾十年間一直是學(xué)界討論的熱點(diǎn)所在。“中國(guó)學(xué)派”這一提法有無(wú)必要、其理論特征與方法論體系何在成為爭(zhēng)論的中心。以樂黛云、劉象愚為代表的部分學(xué)者對(duì)于“中國(guó)學(xué)派”的說(shuō)法并不以為然,認(rèn)為刻意地追求一種派別上的劃分是毫無(wú)任何意義可言的。即便如此,他們也同樣堅(jiān)持,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曉濤曾提出比較文學(xué)研究要超越傳統(tǒng)必經(jīng)的幾個(gè)轉(zhuǎn)變:“一是從學(xué)院里走出來(lái),走向交流與發(fā)展;二是從歐洲中心論走出來(lái),走向世界與全球;三是從文學(xué)里走出來(lái),走向歷史與綜合;四是從方法論里走出來(lái),走向目標(biāo)與創(chuàng)造;五是從民族、種族文化對(duì)峙中走出來(lái),走向互補(bǔ)與完善;六是從純學(xué)術(shù)中走出來(lái),走向人文與文化。”〔26〕這也同樣為比較文學(xué)的“中國(guó)學(xué)派”的走向問(wèn)題奠定了基礎(chǔ)。
在“中國(guó)學(xué)派”的贊同者中,曹順慶教授率先為其作出了較為完整系統(tǒng)的闡述與界定。他認(rèn)為,“如果說(shuō)比較文學(xué)的第一階段(法國(guó)學(xué)派)所倡導(dǎo)的‘影響研究’跨越了國(guó)家界線(或稱國(guó)家‘墻’),溝通了各國(guó)文學(xué)之間的影響關(guān)系;第二階段(美國(guó)學(xué)派)所倡導(dǎo)的‘平行研究’則進(jìn)一步跨越了學(xué)科界線(學(xué)科‘墻’),并溝通了互相沒有影響的各國(guó)文學(xué)關(guān)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較文學(xué)的第三階段(中國(guó)學(xué)派)所倡導(dǎo)的‘跨文化研究’必將跨越東西方異質(zhì)文化這堵巨大的‘墻’,必將穿透這數(shù)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溝通東西方文化與文學(xué),以真正國(guó)際性的胸懷和眼光來(lái)從事比較文學(xué)研究”。此外,他還提出了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所面臨的主要任務(wù),即“在跨越異質(zhì)文化的闡釋之中認(rèn)識(shí)中國(guó)文學(xué)與文論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礎(chǔ)上尋求跨文化的對(duì)話和溝通,尋求中西文論的互補(bǔ)與互釋,在民族特色探討與共通規(guī)律尋求的基礎(chǔ)之上,達(dá)到中西的融會(huì)、貫通以及文學(xué)觀念的重建。”〔27〕在方法論層面上,他認(rèn)為“中國(guó)學(xué)派”應(yīng)以跨文化的“闡發(fā)法”、中西互補(bǔ)的“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尋根法”、促進(jìn)中西溝通的“對(duì)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gòu)的“整合與建構(gòu)”等五種方法為支柱,從而深化和發(fā)展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
總之,惟新是鶩、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態(tài)固然不可取,但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同樣會(huì)阻住我們研究和發(fā)展的腳步。因此,我們應(yīng)該盡快擺脫東西方二元對(duì)立的既定思維模式,從全球化的角度進(jìn)行平等的文化對(duì)話,并將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進(jìn)行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建構(gòu)真正能夠跨文化的學(xué)術(shù)話語(yǔ),在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界中起到“中國(guó)學(xué)派”所應(yīng)當(dāng)起到的作用。
新領(lǐng)域、新方向——文學(xué)人類學(xué)
具體到研究方法層面,除了傳統(tǒng)的異質(zhì)詩(shī)學(xué)比較之外,另有以葉舒憲和蕭兵等為代表的部分學(xué)者,他們借鑒當(dāng)代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從具有相對(duì)普遍適應(yīng)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發(fā),力圖從總體文化的角度、從富有歷史縱深感和闡釋力度的深層破譯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將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發(fā)現(xiàn)與概括。這就是將文學(xué)與人類學(xué)兩門不同的學(xué)科進(jìn)行有機(jī)地結(jié)合的文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所謂文學(xué)人類學(xué),就是以人類學(xué)的方法和視野對(duì)文學(xué)作品和文學(xué)現(xiàn)象進(jìn)行研究”。〔28〕這對(duì)于文學(xué)是大有裨益的,因?yàn)椤叭祟悓W(xué)是最沒有邊界的學(xué)科”,“它最不怕迷失個(gè)性、迷失自我,因?yàn)樗茄芯咳祟惣捌潴w質(zhì)、文化發(fā)生發(fā)展和轉(zhuǎn)換、生成的科學(xué)。”〔29〕
文學(xué)人類學(xué)是一門非常有潛力的學(xué)科,因?yàn)樗芯康氖俏幕氨尽保菍?duì)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讀。現(xiàn)階段的文學(xué)人類學(xué),就研究對(duì)象而言,還主要是神話與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側(cè)重于形態(tài)比較分析,側(cè)重于以人類學(xué)的一般模式研究具體的文本,再由具體歸于一般,由此尋得人類的普遍規(guī)則。因此,正如劉毓慶所言,我們應(yīng)當(dāng)“將人類學(xué)的一般文化模式與具體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分析(背景還原)相結(jié)合,考察民族文化獨(dú)特的內(nèi)涵,從而對(duì)民族文化與文學(xué)做出新的認(rèn)識(shí)。這樣由普遍返回具體,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實(shí)處”〔30〕,這樣文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才會(huì)更有意義。
如今,這門新興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學(xué)界的充分重視。1996年8月,在長(zhǎng)春召開的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學(xué)會(huì)第五屆年會(huì)上成立了“中國(guó)文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會(huì)”,從而在學(xué)術(shù)體制上保證了文藝學(xué)與人類學(xué)的溝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屆中國(guó)文學(xué)人類學(xué)研討會(huì)在廈門舉行,多位專家學(xué)者就科際整合課題進(jìn)行了具有建設(shè)性意義的討論。《文藝研究》與《新華文摘》也先后刊發(fā)了以“探討文學(xué)人類學(xué),拓展研究新領(lǐng)域”為題的專欄,在學(xué)者中引起廣泛關(guān)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說(shuō),文學(xué)人類學(xué)的特點(diǎn),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綜合和對(duì)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視。“在文學(xué)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對(duì)事物內(nèi)在關(guān)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學(xué)科,又是兼容考古學(xué)、民族學(xué)、語(yǔ)言學(xué)、民俗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擁有最豐富的技術(shù)手段的學(xué)科。也許,中國(guó)文學(xué)研究的現(xiàn)代形式,就將以文學(xué)人類學(xué)的興起為開端。”〔31〕
與理論的蓬勃發(fā)展相應(yīng)的是,1996、1997年度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成果也是頗豐的。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其中屬于比較文學(xué)理論研究方法與比較詩(shī)學(xué)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數(shù)量與過(guò)去幾年相比明顯增加,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理論研討的重視。其中包括李達(dá)三、羅鋼主編的《中外比較文學(xué)的里程碑》(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xué)新開拓》(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等論文集著,梳理了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發(fā)展脈絡(luò),并傳達(dá)了最新的學(xué)術(shù)成果與信息。
對(duì)文學(xué)關(guān)系、接受、影響的研究,如今仍是國(guó)內(nèi)比較文學(xué)研究主體之一。關(guān)于這方面的研究論著約有43篇(本),如黃鳴奮的著作《英語(yǔ)世界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之傳播》(學(xué)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試論三大宗教經(jīng)典對(duì)文學(xué)的積極影響》(《江漢論壇》1996年第二期),謝瑩瑩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國(guó)文學(xué)》1996年第一期)等。學(xué)者們通過(guò)對(duì)于文學(xué)影響研究上的比較與闡發(fā),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視角對(duì)文學(xué)、宗教、戲劇等藝術(shù)形式在異質(zhì)文化圈中的跨文化傳播進(jìn)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們還通過(guò)這種對(duì)比,反觀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自身,并將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視野中重新加以觀照,從而對(duì)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體作家與文本的“兩兩比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樹”,1996、 1997兩年約有76篇(本)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發(fā)表。為了與學(xué)科理論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體文本的研究也都紛紛從人類的共同的生命和體驗(yàn)出發(fā),對(duì)不同文化體系中的主體根據(jù)其不同的歷史經(jīng)驗(yàn)、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對(duì)這些共同問(wèn)題所做出的獨(dú)特解答進(jìn)行分析,從而由點(diǎn)及面地應(yīng)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進(jìn)行深層模式的比較。如王瑜琨的《從〈喧嘩與騷動(dòng)〉和〈紅樓夢(mèng)〉看中西挽歌式悲劇精神》(《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6年第二期),鄭萬(wàn)鵬的《〈白鹿原〉的史詩(shī)構(gòu)造:與托爾斯泰長(zhǎng)篇藝術(shù)比較談》(《東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與比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學(xué)科研究與形象學(xué)研究,作為新興的學(xué)術(shù)門類也已獲得長(zhǎng)足的發(fā)展。比較學(xué)者們紛紛著文,對(duì)其學(xué)科發(fā)展態(tài)勢(shì)進(jìn)行展望、學(xué)科理論進(jìn)行建設(shè)。但遺憾的是,研究者們對(duì)這兩門學(xué)科的探討僅止于理論層面,真正能將理論付諸實(shí)踐、進(jìn)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學(xué)術(shù)著作也不過(guò)是寥寥數(shù)篇而已。盡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樂〉中的獅子形象》、劉陽(yáng)的《唐詩(shī)中所見外來(lái)樂舞及其流傳——兼論唐人詩(shī)中的“何滿子”》等文章仍為這一舶來(lái)理論向中國(guó)文本分析的轉(zhuǎn)化作了有益的嘗試。
總而言之,對(duì)于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而言,1996、1997兩年是一個(gè)必不可少的過(guò)渡階段。這一時(shí)期上承“后殖民主義”影響研究,從而形成了有關(guān)“中國(guó)學(xué)派”應(yīng)如何在全球化語(yǔ)境中堅(jiān)持話語(yǔ)權(quán)的討論;下啟文學(xué)人類學(xué)、形象學(xué)等新興學(xué)科方法的理論探討與具體應(yīng)用,體現(xiàn)出了比較文學(xué)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為世紀(jì)之交比較文學(xué)即將進(jìn)行的文化轉(zhuǎn)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1〕〔5〕謝天振《從比較文學(xué)到比較文化——對(duì)當(dāng)代國(guó)際比較文學(xué)研究趨勢(shì)的思考》,《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1996年第3期。
〔2〕〔8〕《比較文學(xué)新視野》(代序),《多元文化語(yǔ)境中的文學(xué)》,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劉象愚《比較文學(xué)的危機(jī)和挑戰(zhàn)》,《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4〕〔11〕〔27〕曹順慶《是“泛文化”還是“跨文化”》,《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西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7年第6期。
〔7〕《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1996年第4期。
〔9〕葉舒憲轉(zhuǎn)引自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西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7年第6期。
〔10〕喬納森·卡勒《歸根到底,比較文學(xué)是比較“文學(xué)”》,《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通訊》1996年第2期。
〔13〕〔14〕〔17〕謝天振《面對(duì)西方比較文學(xué)界的大爭(zhēng)論》,《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15〕《比較文學(xué)——在名與實(shí)之間》,《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8〕《三個(gè)值得探討的理論問(wèn)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語(yǔ)境之中尋求》,《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1〕王寧《后殖民理論和后殖民地文學(xué)》,《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2〕《中國(guó)當(dāng)代后殖民批評(píng)之我見》,《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義時(shí)期的比較文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25〕《“后”字號(hào)理論與歐洲中心主義》,《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1996年第4期。
〔26〕《發(fā)展研究與中國(guó)比較學(xué)派》,《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28〕彭兆榮《邊界不設(shè)防:人類學(xué)與文學(xué)研究》,《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
〔29〕蕭兵《文學(xué)人類學(xué):走向“人類”,回歸“文學(xué)”》,《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
比較文學(xué)范文2
參考國(guó)內(nèi)有先進(jìn)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院校的比較文學(xué)雙語(yǔ)教學(xué)大綱制定情況,結(jié)合各校教師及學(xué)生能力實(shí)際,制定適合本校高年級(jí)專業(yè)必修課的比較文學(xué)雙語(yǔ)課程教學(xué)大綱及教學(xué)計(jì)劃。通過(guò)講授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基本理論,使學(xué)生掌握比較文學(xué)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并在其中貫穿比較文學(xué)范例式教學(xué)。在教學(xué)事例選擇上,側(cè)重國(guó)外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的專業(yè)論述,進(jìn)行雙語(yǔ)講解,以起到導(dǎo)讀、“研讀”英文原著的作用。所謂,借助導(dǎo)讀去分析閱讀英文原著,借助“研讀”著力于對(duì)其邏輯論述和層次結(jié)構(gòu)的解讀和理解,以便直接具體地認(rèn)識(shí)領(lǐng)會(huì)西方學(xué)者的研究思維過(guò)程和表述特點(diǎn),從中學(xué)習(xí)研究問(wèn)題、發(fā)現(xiàn)問(wèn)題和論述問(wèn)題的創(chuàng)新能力及其實(shí)踐運(yùn)作。
二、師資水平的提高
雙語(yǔ)教學(xué)對(duì)師資水平要求很高,教師不僅要掌握英語(yǔ)這門語(yǔ)言,還要懂得比較文學(xué)的學(xué)科理論知識(shí)。而在我國(guó)國(guó)內(nèi),解決這一問(wèn)題的主要途徑是吸收海歸教師充實(shí)語(yǔ)言師資建設(shè),主要是在首都師范大學(xué)和四川大學(xué),但是難道普通高校不具備這方面師資力量就不能從事雙語(yǔ)教學(xué)了嗎?答案不是這樣的。隨著網(wǎng)絡(luò)、多媒體技術(shù)的普及,高校教師可充分利用高科技條件解決雙語(yǔ)教學(xué)師資力量不足的問(wèn)題。利用網(wǎng)絡(luò)、多媒體形式進(jìn)行輔助教學(xué)。在比較文學(xué)多媒體、網(wǎng)絡(luò)雙語(yǔ)教學(xué)課堂上營(yíng)造良好的雙語(yǔ)環(huán)境和氛圍,在短期內(nèi)迅速提高師生的教與學(xué)能力。在具體實(shí)施過(guò)程中可引入專業(yè)理論術(shù)語(yǔ)英漢雙語(yǔ)匯釋;播放一些國(guó)內(nèi)外著名學(xué)者的解讀文學(xué)、文論原典、英文詩(shī)歌朗誦錄像;欣賞一些代表性的、具較高藝術(shù)價(jià)值的英語(yǔ)影視作品片斷等。
三、教材體系的構(gòu)建
針對(duì)非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的英語(yǔ)水平實(shí)際,采取的授課教材普遍有三種模式。一種是以英文原著為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授課。如SusanBassnett.的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出版時(shí)間:1993。(蘇珊•波斯奈特:《比較文學(xué)批評(píng)導(dǎo)論》,Blackwell出版社)但是存在的問(wèn)題一是英文原著教材價(jià)格昂貴,讓一般學(xué)生難以承受;其次是由于出版和傳播的關(guān)系,英文原版教材進(jìn)入中國(guó)要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造成版本太舊。再次,據(jù)說(shuō)國(guó)外比較文學(xué)授課是沒有教材的,由于原教材者往往在某一方面領(lǐng)域研究的過(guò)于深透,多是專著性質(zhì),上課都是老師自己整理講義。這就造成部分內(nèi)容過(guò)于詳細(xì),有些地方涉及不到。不符合我國(guó)學(xué)生通習(xí)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領(lǐng)域的現(xiàn)狀。第二種模式就是選用中國(guó)人編寫的英文教材,再選用原版英文教材和國(guó)內(nèi)中文教材作為輔助。由于編寫者、教師和學(xué)生的國(guó)學(xué)和英文能力水平差異,很難保證取得高效的教學(xué)質(zhì)量。第三種教材模式是以中文教材為主,選取英美比較文學(xué)名師的論著進(jìn)行講解。兩者起到一種相輔相成的作用。如上海師范大學(xué)孫景堯的AStudyofImportantWorksinEnglishComparativeLiterature《比較文學(xué)名著研讀(雙語(yǔ)版)》,在實(shí)踐教學(xué)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各高校可根據(jù)本校教師和學(xué)生的實(shí)際水平編訂相應(yīng)的比較文學(xué)雙語(yǔ)教材,解決學(xué)生聽課無(wú)的放矢的困境。
四、教學(xué)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創(chuàng)新
1.課堂教學(xué)方法要豐富
推行范例式教學(xué)法。在比較文學(xué)雙語(yǔ)教學(xué)中采用了事例教學(xué)法。選擇范例時(shí),要突出范例的綜合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抓范例庫(kù)的建設(shè)。搜集、整理和編寫比較文學(xué)教學(xué)范例,注重國(guó)外范例的引進(jìn)和翻譯工作。進(jìn)行參與式教學(xué)。主張學(xué)生能夠自主翻譯,嘗試用自己的感受先代替名家名譯,然后再和名家名譯做對(duì)比,學(xué)習(xí)經(jīng)典翻譯文本的文學(xué)魅力,同時(shí)也知曉在感受相同的情況下如何參照寫作的文化背景來(lái)理解和復(fù)述作品原有的思想意義。實(shí)施任務(wù)式教學(xué)。在教學(xué)中開展以任務(wù)為中心的、形式多樣的教學(xué)活動(dòng),利用啟發(fā)式、討論式、發(fā)現(xiàn)式和研究式的教學(xué)方法,充分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積極性,激發(fā)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最大限度地讓學(xué)生參與學(xué)習(xí)的全過(guò)程。同時(shí),相應(yīng)運(yùn)用情景模擬、辯論等教學(xué)方式。讓學(xué)生參與其中,改變傳統(tǒng)的教師滿堂灌、學(xué)生埋頭記的方式,有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興趣,引導(dǎo)學(xué)生思維,增強(qiáng)學(xué)生學(xué)以致用的能力,教學(xué)效果顯著。
2.教學(xué)手段要多樣
(1)多媒體教學(xué)方式。首先在課件制作過(guò)程中,保證人名、篇目、書名的原文附著和對(duì)譯名的統(tǒng)一和糾正,使用關(guān)鍵詞教學(xué)方式。其次,經(jīng)典作家的重點(diǎn)篇目當(dāng)中的精品段落盡量采用原文、譯文雙對(duì)照。第三,對(duì)于重要西方文藝?yán)碚撚^點(diǎn)嘗試進(jìn)行按3:7(英文:中文)劃分的課堂內(nèi)容比例的本專業(yè)英文教學(xué),同時(shí)用中文再次強(qiáng)調(diào),避免譯文造成的觀點(diǎn)誤讀。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比較文學(xué)專有名詞解釋、人名、書名及重要段落的雙語(yǔ)模式進(jìn)行沉浸式教學(xué),欣賞英文視音頻片段,如在對(duì)2008級(jí)講授Psychoanalyticalcriticism的內(nèi)容時(shí),為加深學(xué)生對(duì)Oedipuscomplex的理解,首先讓學(xué)生觀看一段TheKingofOedipus的視頻材料,從而加深了學(xué)生對(duì)這一概念的領(lǐng)會(huì)。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的引進(jìn),增強(qiáng)了直觀性,化抽象為具體,調(diào)動(dòng)了學(xué)生的積極性,提高的學(xué)習(xí)興趣,進(jìn)一步訓(xùn)練了論文寫作和雙語(yǔ)思維能力。(2)課程教學(xué)平臺(tái)建設(shè)。課程教學(xué)平臺(tái)建設(shè)內(nèi)容包括以比較文學(xué)課程各知識(shí)點(diǎn)為單元的開放式的網(wǎng)絡(luò)課件庫(kù)、事例庫(kù)和試題庫(kù)。并將專業(yè)教師與學(xué)生的科研成果也放在網(wǎng)站上,鼓勵(lì)學(xué)生就相關(guān)問(wèn)題進(jìn)行探討,引導(dǎo)學(xué)生思考。課程規(guī)劃、教學(xué)大綱、電子教案、教學(xué)課件、師資隊(duì)伍、習(xí)題解答、參考文獻(xiàn)等欄目基本成型,并配備了文字的資料,只要連接上校內(nèi)網(wǎng),便可達(dá)到資源共享。通過(guò)“學(xué)術(shù)動(dòng)態(tài)”、“學(xué)術(shù)著述”、“經(jīng)典專題”和“資源下載”等分欄,不僅能夠獲取學(xué)習(xí)所需的各種資源,而且使教與學(xué)始終能夠洞悉學(xué)科發(fā)展和研究的前沿。此外,通過(guò)該網(wǎng)站上備有的友情連接網(wǎng)址,可以登錄其他專業(yè)學(xué)術(shù)網(wǎng)和其他院校了解最新的學(xué)術(shù)和教學(xué)動(dòng)態(tài)。
3.實(shí)踐性教學(xué)環(huán)境要完善
(1)建立起比較文學(xué)研究方法與學(xué)生課程論文、畢業(yè)論文寫作的實(shí)踐連接,例如學(xué)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如05級(jí)學(xué)生王朝的《幻想文學(xué)的發(fā)展及演變》直接涉及了比較文學(xué)的影響研究領(lǐng)域,其他如漢語(yǔ)言文學(xué)06級(jí)學(xué)生“解析《金粉世家》中的女性觀”和“<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的自由意志抒寫”等論文都從不同角度將比較文學(xué)的平行研究和跨學(xué)科研究理論付諸實(shí)踐。(2)利用專業(yè)實(shí)習(xí)基地的資源,加強(qiáng)與其他雙語(yǔ)教學(xué)部門的聯(lián)系,保證講座、參觀等教學(xué)方式的穩(wěn)定。如,帶領(lǐng)學(xué)生聽取外語(yǔ)系教師的課堂教學(xué)、語(yǔ)音室學(xué)習(xí),鼓勵(lì)學(xué)生參加或聆聽各種英語(yǔ)演講、辯論、表演比賽,如鼓勵(lì)學(xué)生參加2011年10月在我校舉辦的“外研社杯”全國(guó)英語(yǔ)演講大賽黑龍江省決賽選拔賽,并在外國(guó)專家學(xué)者到校做英文講座時(shí),鼓勵(lì)教師學(xué)生積極參與。如聆聽2011年10月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邀請(qǐng)美國(guó)國(guó)際教育委員會(huì)首席執(zhí)行官DonPetry博士來(lái)校做關(guān)于《教育國(guó)際化》的專題講座等。在授課形式和方法上進(jìn)行大膽改革,采用多種現(xiàn)代教學(xué)方式,能有效調(diào)動(dòng)了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積極性,收到較好的效果。體現(xiàn)出“老課程,新內(nèi)容”的時(shí)代特色。
五、教學(xué)實(shí)踐效果
比較文學(xué)范文3
比較文學(xué)作為一門獨(dú)立的學(xué)科起源于法國(guó)。為了避免盲目的比附,給比較文學(xué)“取得一個(gè)科學(xué)的涵義”[1],法國(guó)派學(xué)者把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范圍人為縮小,其代表人物基亞明確地將其歸為“國(guó)際文學(xué)關(guān)系史”。這樣的研究思路把比較文學(xué)研究引入了死胡同,似乎比較文學(xué)研究就僅限于無(wú)休無(wú)止的實(shí)證,因而導(dǎo)致“一潭死水”局面的產(chǎn)生,其對(duì)比較文學(xué)所下的定義今天自然被摒棄了。鑒于這種情況,美國(guó)派學(xué)者把平行研究引入比較文學(xué),將比較文學(xué)擴(kuò)展定義為:“一國(guó)文學(xué)與另一國(guó)文學(xué)或多國(guó)文學(xué)的比較,把文學(xué)和人類表達(dá)的其他領(lǐng)域相比較”。[1]此種定義把比較文學(xué)研究從“國(guó)際文學(xué)關(guān)系史”的局限中解放了出來(lái),極大地拓展了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可這個(gè)定義也有不夠完善之處。首先,研究的區(qū)分基礎(chǔ)是不同國(guó)別,這種區(qū)分忽視了國(guó)界的多變性,忽視了同一國(guó)家內(nèi)存在不同文化乃至文明的可能;其次,此定義把比較文學(xué)引入了一個(gè)大而無(wú)當(dāng)?shù)木车兀坪跏裁炊伎梢阅脕?lái)比較了。在此基礎(chǔ)上,中國(guó)學(xué)者總結(jié)了前人的經(jīng)驗(yàn)與做法,針對(duì)自身具體情況也提出各種比較文學(xué)定義。總的來(lái)說(shuō),比較文學(xué)的中國(guó)學(xué)派致力于不同文化(或文明)間的交流與溝通,異質(zhì)與互補(bǔ)。曹順慶教授認(rèn)為:“跨文化研究(跨中西異質(zhì)文化)是比較文學(xué)中國(guó)學(xué)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優(yōu)勢(shì)之所在;是中國(guó)學(xué)派區(qū)別于法、美學(xué)派的最基本的理論和學(xué)術(shù)特征”[2]。因此國(guó)內(nèi)的比較文學(xué)定義大都強(qiáng)調(diào)比較文學(xué)的“跨越性”,其具體表述有“兩跨”、“三跨”、“四跨”、“五跨”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名目繁多的“跨越”著重點(diǎn)都在強(qiáng)調(diào)異質(zhì)性,但實(shí)際上每個(gè)“跨越”后面都隱藏著許多問(wèn)題,也不禁給學(xué)習(xí)者帶來(lái)疑惑,到底哪些是比較文學(xué)應(yīng)該“跨越”的?應(yīng)該怎樣“跨越”?
二、定義之爭(zhēng)根源
造成定義之爭(zhēng)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研究?jī)?nèi)容和方法論的模糊不清。下面就結(jié)合中國(guó)學(xué)派的具體情況,對(duì)比較文學(xué)作定義的過(guò)程中存在的問(wèn)題作一個(gè)具體的闡述。
1.跨越性的模糊不清
既然把“跨越性”作為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本質(zhì)特征之一,那“跨越”就不能是一個(gè)泛化無(wú)界定的詞匯,必須要對(duì)跨越度有所規(guī)定,我們才能明確研究?jī)?nèi)容。比如,“跨民族”里的民族是以國(guó)家為單位呢,還是以種群為單位?而對(duì)“跨文化”的理解更是眾說(shuō)紛紜,莫衷一是。這是由于“文化”一詞的多重內(nèi)涵和人們對(duì)文化的不同理解,從而導(dǎo)致對(duì)文化跨度的難以把握。有的學(xué)者為了避免這種歧義,把“文化”改成“文明”,并特別說(shuō)明:“‘文明’在‘跨文明研究’中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傳承(信仰體系、價(jià)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等)的社會(huì)共同體”。[3]這樣的修改企圖從大的方面、源頭上來(lái)把握,其實(shí)這樣還是有歧義。因?yàn)橐粋€(gè)國(guó)家在不同的時(shí)期會(huì)接受不同的文明。比如韓國(guó)以前接受的是中國(guó)儒家文化,而到了近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痕跡處處可見。那么韓國(guó)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古代文學(xué)和受西方文明影響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相比較可以劃作比較文學(xué)范疇嗎?由此可見,如果我們的定義僅是一味注重跨越的領(lǐng)域問(wèn)題而不對(duì)跨越性本身有所限制說(shuō)明,那么無(wú)論怎樣精確描述,都會(huì)有漏洞。因此,作為定義,我們必須對(duì)跨越度作出一些符合學(xué)科特點(diǎn)與發(fā)展規(guī)律的具體限定,才能完善并明確定義,從而形成一個(gè)相對(duì)一致的理解。另外,跨越性的模糊之處還在于眾多的“跨越”之間是邏輯關(guān)系是“且”的關(guān)系還是“或”的關(guān)系。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材料是同時(shí)要滿足這些條件,還是只需滿足其中幾個(gè)甚至是只需滿足一個(gè)?它們之間有主次之分嗎?好像定義中的一個(gè)個(gè)小小的頓號(hào)并不能解決這些疑問(wèn)。現(xiàn)在有的定義前面幾個(gè)“跨越”是“且”關(guān)系,可對(duì)后面幾個(gè)“跨越”又是“或”的關(guān)系。如果沒有明確的說(shuō)明,讀者是難以把握的,這也是造成混淆的原因之一。綜上所述,要明確定義中的“跨越性”,我們?cè)谧鞫x時(shí)必須有所說(shuō)明,不但要明確其內(nèi)涵外延,還要理順各個(gè)層面的關(guān)系。
2.對(duì)跨越性的過(guò)分注重
現(xiàn)在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普遍認(rèn)同跨越性是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學(xué)派的基本特征,眾多的定義已可以簡(jiǎn)化為“Ⅹ跨”。盡管跨越性是比較文學(xué)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它并不是比較文學(xué)的唯一特征,也不是它獨(dú)具的特質(zhì)———許多其它以“比較”為名的科目,其著重點(diǎn)也在跨越性。因此對(duì)比較文學(xué)的定義固然應(yīng)當(dāng)強(qiáng)調(diào)其跨越性,而對(duì)其它屬性也不能忽視。畢竟,比較文學(xué)的目的是為了“尋求各民族文學(xué)的特點(diǎn)和文學(xué)發(fā)展的共同規(guī)律”,[4]跨越只是手段之一,不是目的。對(duì)跨越的過(guò)分注重,會(huì)導(dǎo)致對(duì)比較文學(xué)其它屬性的忽視,也混淆了比較文學(xué)和其他學(xué)科的界限,不能從整體上把握該學(xué)科的根本特征。僅以“跨越性”或者說(shuō)跨越異質(zhì)文化(或文明)作為中國(guó)學(xué)派的基本特征,其實(shí)是不能建立比較文學(xué)的中國(guó)學(xué)派的。事實(shí)上,任何一個(gè)比較文學(xué)學(xué)派都可以說(shuō)自己是“跨越”的。即使法國(guó)學(xué)派、美國(guó)學(xué)派也是有“跨越性”的———畢竟,沒有“跨越”就沒有“比較”。比如,梵•第根就曾指出,“比較文學(xué)研究對(duì)象應(yīng)該超出一元性而具有跨越性”。[5]只不過(guò)他們所認(rèn)為的“跨越”和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的概念有所不同而已。當(dāng)然,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還強(qiáng)調(diào)跨越的異質(zhì)性,但是我們也可以對(duì)“異質(zhì)”有不同理解。雖然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是以跨越異質(zhì)文化(或文明)為基本特征的,但是任何一個(gè)不屬于西方文明的比較文學(xué)學(xué)派都可以稱自己是在“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關(guān)注世界各大文明”[6],都可以把這一特征納入自己名下,那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的特殊之處在哪里?雖然“比較文學(xué)不是文學(xué)比較”,但是至少比較的重點(diǎn)要放在文學(xué)性上,否則我們這個(gè)學(xué)科就不能成立。楊恒達(dá)教授給比較文學(xué)下的定義可以說(shuō)是這方面的一個(gè)嘗試:“比較文學(xué)應(yīng)該是重點(diǎn)在于探討各文學(xué)現(xiàn)象(包括文學(xué)理論)之間文化差異及其人文精神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一種文學(xué)研究。”[7]該定義避免了眾多“跨越”類定義所產(chǎn)生的漏洞與概念混淆,把定義重點(diǎn)轉(zhuǎn)到文學(xué)性上。“根據(jù)這個(gè)定義,比較文學(xué)雖然以文化探討為重點(diǎn),但是畢竟同文化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學(xué)科不同,因?yàn)樗那腥朦c(diǎn)是文學(xué)現(xiàn)象,它的研究對(duì)象是‘各文學(xué)現(xiàn)象之間’的文化差異及其人文精神內(nèi)在聯(lián)系,嚴(yán)格限定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所以這門學(xué)科只能是文學(xué)研究,而不是別的。”[7]雖然學(xué)者們對(duì)此種定義還有不同看法,但這畢竟是從另外一個(gè)角度思考。楊氏定義為我們解決“跨越”類定義問(wèn)題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3.中國(guó)學(xué)派沒有相對(duì)統(tǒng)一的方法論
既然跨越異質(zhì)文化(或文明)不能成為中國(guó)學(xué)派的基本特征,那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要立足并發(fā)展,必須建立一套自己的方法論,并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我們自己的文化特征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別具特色的方法。方法論不同于具體方法,它是關(guān)于認(rèn)識(shí)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細(xì)化到具體學(xué)科上,方法論特指研究某一具體學(xué)科,涉及某一具體領(lǐng)域的方法理論是具體科學(xué)的方法論。因此,比較文學(xué)的方法論可以理解為指導(dǎo)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研究的總的原則和方法理論。雖然在對(duì)比較文學(xué)定義的描述中,一般不會(huì)涉及到方法論,但是方法論的明確,對(duì)我們整體地把握這門學(xué)科,有效地界定比較文學(xué),甚至對(duì)比較文學(xué)中國(guó)學(xué)派的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都會(huì)有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法國(guó)學(xué)派、美國(guó)學(xué)派之所以站得住腳是因?yàn)槠溆袌?jiān)實(shí)的方法論作為基礎(chǔ),而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的方法論似乎就不是那么特征鮮明。比較文學(xué)作為一門學(xué)科起源于西方,在西方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而中國(guó)的比較文學(xué)理論研究則相對(duì)滯后,這就使中國(guó)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打上了西方烙印,甚至有的早期學(xué)者認(rèn)為“援用西方文學(xué)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yàn)、調(diào)整以用之于中國(guó)文學(xué)的研究,是比較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學(xué)派。”[8]因此,比較文學(xué)的中國(guó)學(xué)派要站穩(wěn)腳跟,要建立一套有中國(guó)特色的理論體系,而要建立一套理論體系,必須要有方法論為指導(dǎo)。沒有方法論,我們不管寫多少論文,其實(shí)還是圍著西方研究轉(zhuǎn)。由于沒有基本的統(tǒng)一認(rèn)識(shí),導(dǎo)致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對(duì)比較文學(xué)定義眾說(shuō)紛紜。方法論對(duì)具體研究也會(huì)起到指導(dǎo)作用。雖然“比較文學(xué)不是文學(xué)比較”這句名言在比較文學(xué)界盡人皆知,但究竟怎樣做才不是“文學(xué)比較”?比附性文學(xué)研究固然淺薄,可怎樣才能走向深層次的研究?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方法和其它文學(xué)的分支學(xué)科有什么區(qū)別?曹順慶教授曾給出這樣的“藥方”:“文化異質(zhì)性與互補(bǔ)性應(yīng)當(dāng)成為關(guān)注焦點(diǎn)。只有這樣,才能避免“X+Y”型的淺度比附文學(xué),從而走向深層次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9]但是用這個(gè)“藥方”還是可以進(jìn)行淺度比附的———其實(shí)用任何有效的研究方法都可以進(jìn)行淺度比附。因此還是要用方法論作指導(dǎo)。這里并非倡導(dǎo)學(xué)者們盡量多地探索方法,而是意在我們要首先確立方法論,這樣我們才會(huì)知道可與不可,才明確我們所研究的目的,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們要知道,一種有效的研究方法雖然給研究者指明了一條路,但畢竟只是一條,還有別的路可走?難道要全讓別人指出來(lái)?如果沒有一套方法論,我們只能是舉步維艱。沒有一個(gè)鮮明、堅(jiān)實(shí)的方法論為基礎(chǔ),而想摸索出為大家所認(rèn)可的研究方法是事倍功半的。說(shuō)到明確方法論,就不能不考慮我們中國(guó)的文化實(shí)力,我們?cè)谶x擇或創(chuàng)立方法論時(shí)是應(yīng)考慮到中國(guó)特色的。我們中國(guó)學(xué)派方法論的立足點(diǎn)應(yīng)該考慮到我們中國(guó)(尤其是大陸)的現(xiàn)實(shí)與歷史情況。既然現(xiàn)在我們中國(guó)大陸的主導(dǎo)文化是以為指導(dǎo)的社會(huì)主義文化,那我們的方法論就應(yīng)以此為基礎(chǔ),結(jié)合我們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因素,再綜合我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共同規(guī)律,建立起一套別具特色的方法論。
比較文學(xué)范文4
【關(guān)鍵詞】比較文學(xué);新聞;真實(shí)性
文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是具有藝術(shù)性,有唯美性。新聞可以是文學(xué)的來(lái)源之處,經(jīng)過(guò)作者的藝術(shù)加工變成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此作品根據(jù)文學(xué)的內(nèi)在尺度修改潤(rùn)色是對(duì)真實(shí)存在的新聞事實(shí)的超越,用唯美的手法揭示社會(huì)生活,是讀者產(chǎn)生信任感認(rèn)同感并在情感上產(chǎn)生共鳴由此受到啟迪,這就是文學(xué)的真實(shí)性的體現(xiàn)。而新聞的真實(shí)性就是要報(bào)道真真切切發(fā)生的事件,不存在什么主觀的修飾法,只是客觀的再現(xiàn)事件的過(guò)程。為此,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和新聞從業(yè)者的職責(zé)在短時(shí)間內(nèi)是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的,但其最終的目的是有共同之處的。
新聞的真實(shí)性的具體含義是指在新聞報(bào)道中的每一個(gè)具體事實(shí)必須合乎客觀實(shí)際。即表現(xiàn)在新聞報(bào)道中的時(shí)間(when),地點(diǎn)(where),人物(who),事情(what),原因(why)和經(jīng)過(guò)(how)都經(jīng)得起核對(duì)。這個(gè)要求看上去很簡(jiǎn)單,但一到實(shí)際工作中就顯得很復(fù)雜。這種復(fù)雜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任何新聞報(bào)道都是經(jīng)過(guò)選擇的。這種選擇有兩個(gè)層面的含義:一是新聞工作者必須從每時(shí)每刻變化著的世界之中選擇及其有限的事件用以公開傳播;二是對(duì)選擇中的每一個(gè)事件還得再選擇其中的部分事實(shí)公開傳播,這里有個(gè)主次,輕重,緩急的選擇。在這樣的選擇過(guò)程中,必定會(huì)有不同的認(rèn)識(shí),不同的價(jià)值取向。于是,同一事件,不同的傳媒,報(bào)道出來(lái)的新聞可能會(huì)大相徑庭,但誰(shuí)都會(huì)宣稱自己的新聞是唯一真實(shí)的。
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真實(shí)性是作家對(duì)對(duì)象世界的理解,反映和闡釋,只要合情合理,他的作品就會(huì)具有“真實(shí)性”的品格;而具有“真實(shí)性”品格的作品,能讓讀者產(chǎn)生信任感和認(rèn)同感,并且因其與“善”,“美”相統(tǒng)一而為之所吸引,所感動(dòng),從而獲得思想上的啟迪和精神上的享受。“真”是文學(xué)審美追求的基礎(chǔ)。高爾基說(shuō):“文學(xué)是巨大而又重要的事業(yè),它是建立在真實(shí)上面的,而且在與它有關(guān)的一切方面,要的就是真實(shí)!” [1]
凡是歷史上出現(xiàn)過(guò)和現(xiàn)實(shí)中存在的一切事物與現(xiàn)象(有些即為新聞事件)都是生活真實(shí)。生活真實(shí)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原形啟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藝術(shù)真實(shí)是對(duì)生活真實(shí)的超越,它在假定性情境中,揭示社會(huì)生活的本質(zhì)及其必然性,以此作為自己的目標(biāo)。從這個(gè)側(cè)面上說(shuō),藝術(shù)真實(shí)是內(nèi)蘊(yùn)的真實(shí),假定的真實(shí)。藝術(shù)真實(shí)是作家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認(rèn)識(shí)和感悟的產(chǎn)物。文學(xué)創(chuàng)作正是在既有理智體察又有直覺把握的心理機(jī)制和思維活動(dòng)中,透過(guò)生活真實(shí)的表層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內(nèi)蘊(yùn)做出藝術(shù)的揭示和表現(xiàn)。誠(chéng)然,所謂社會(huì)生活的內(nèi)蘊(yùn)是個(gè)十分豐富的概念可以分出許多層次,并且由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個(gè)性不同,其認(rèn)識(shí)和感悟的側(cè)面及其深廣度也會(huì)有很大的差別。而且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造的審美價(jià)值的體現(xiàn)方式,藝術(shù)真實(shí)總是與發(fā)掘和表現(xiàn)社會(huì)生活的本質(zhì)與規(guī)律聯(lián)系在一起。《三國(guó)演義》雖然取材于歷史事實(shí),但其對(duì)三國(guó)時(shí)代的戰(zhàn)亂的場(chǎng)面的描繪并非真如史實(shí)。而是三分虛假七分真實(shí)的比例予以生發(fā),改造,夸張,夸飾,變形的表現(xiàn)――“擁劉反曹”為主體意識(shí)的封建正統(tǒng)觀念與勞動(dòng)大眾的是非善惡美丑標(biāo)準(zhǔn)的混合所滲透。正如列寧說(shuō)的,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藝術(shù)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會(huì)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zhì)的方面。[2]因此,用歷史的眼光,發(fā)現(xiàn)和反映社會(huì)生活的本質(zhì),遂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價(jià)值”要求而為藝術(shù)家和美學(xué)家所看重。
文學(xué)的真實(shí)性是“假定的真實(shí)”這是由于文學(xué)既然不是對(duì)生活真實(shí)的照搬照抄,作家就必然會(huì)從自己的認(rèn)識(shí)和感悟出發(fā),對(duì)生活真實(shí)進(jìn)行選擇,發(fā)掘,提煉,補(bǔ)充,集中,概括,通過(guò)想象和虛構(gòu)予以重組,變形及再塑。如果說(shuō)表現(xiàn)社會(huì)生活中某些本質(zhì)性東西的價(jià)值取向是藝術(shù)真實(shí)的內(nèi)在要求,那么藝術(shù)情境的假定性是藝術(shù)真實(shí)的外部特征。以假定性情境反映或表現(xiàn)社會(huì)生活的內(nèi)蘊(yùn)是一切文藝的共同特征。的《雷雨》讓兩個(gè)家庭八個(gè)人物之間的矛盾糾葛發(fā)生在兩個(gè)場(chǎng)合及一晝夜之內(nèi),沖突又那么集中而強(qiáng)烈,這并非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常態(tài),然而正是這種假定性的情境,使它成為20世紀(jì)20年代初期中國(guó)都市社會(huì)生活某些本質(zhì)方面的真實(shí)縮影。可見,假定性情境是藝術(shù)真實(shí)呈現(xiàn)的基本方式,是文學(xué)反映生活本質(zhì)這一求“真”價(jià)值取向存在的普遍形態(tài)。因此,魯迅說(shuō),藝術(shù)是“假中見真”的。[3]當(dāng)然,“假中見真”的藝術(shù)效應(yīng),建立在它們符合事理邏輯或者符合情感邏輯的基礎(chǔ)上,建立在能為讀者所接受的基礎(chǔ)上。
求“真”是文學(xué)創(chuàng)造的審美價(jià)值追求之一,藝術(shù)真實(shí)的概念可以做以下表述: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觀性感知與詩(shī)意性創(chuàng)造,達(dá)到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內(nèi)蘊(yùn),特別是那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的把握,體現(xiàn)著作家的認(rèn)識(shí)和感悟。無(wú)疑,這是一種特殊的真實(shí),是主體把自己的“內(nèi)在尺度”運(yùn)用到對(duì)象上去而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審美化真實(shí)。它既不像生活真實(shí)那樣與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學(xué)真實(shí)那樣能夠驗(yàn)證和還原。
新聞報(bào)道要真實(shí)地反映一個(gè)事件,必須注意它上下左右的聯(lián)系,這就要求新聞工作者從事實(shí)的全部總和中去抽取事實(shí),而不是帶著固定的觀點(diǎn)到現(xiàn)實(shí)中找例子,或者孤零零地表現(xiàn)一個(gè)事件。新聞的本質(zhì)真實(shí)其一指的是反映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應(yīng)做到事實(shí)的準(zhǔn)確和本質(zhì)的真實(shí);其二是指全面反映情況,應(yīng)當(dāng)全面,客觀,公正的報(bào)道;其三,是指正確的立場(chǎng);其四是指舍去假象,偶然性的事實(shí),而必須報(bào)道真實(shí),必然性的事實(shí)。
縱觀文學(xué)中追求的真實(shí)性與新聞中所追求的真實(shí)性,兩者存在著交集,但也有極大區(qū)別。各自的特性由其各自的目的所限制所規(guī)定。文學(xué)是藝術(shù)的唯美體現(xiàn)方式,而新聞是事實(shí)的真實(shí)體現(xiàn)方式。
注釋:
[1](蘇)高爾基.給安?葉?托勃羅伏爾斯基[A].文學(xué)書簡(jiǎn)(上卷)[C].曹葆華,渠建明,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2:217.
比較文學(xué)范文5
比較文學(xué)作為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一門新興學(xué)科,具有鮮明的綜合性、跨越性、交叉性等特點(diǎn)。它一方面與文學(xué)專業(yè)的所有學(xué)科都有聯(lián)系,另一方面又不以眾多學(xué)科本身為研究對(duì)象,而是以多門學(xué)科中與跨越和比較有關(guān)的那些內(nèi)容為研究對(duì)象。這一特殊的學(xué)科性質(zhì)使比較文學(xué)在文學(xué)專業(yè)中的身份非常類似于專門處理國(guó)際事務(wù)的“聯(lián)合國(guó)”。它的實(shí)際教學(xué)與科研功效有時(shí)雖不直接地體現(xiàn)在自身的具體行為中,但卻可以通過(guò)許多間接的影響使整個(gè)集體受益。而這也意味著構(gòu)建有效的比較文學(xué)教學(xué)創(chuàng)新體系,不僅可以極大地提高整個(gè)文學(xué)專業(yè)的整體水平,同時(shí)這一體系的成功構(gòu)建,也必須要以整個(gè)文學(xué)專業(yè)為依托,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統(tǒng)籌規(guī)劃。就濰坊學(xué)院而言,在主體要素層,濰坊學(xué)院文學(xué)院專職比較文學(xué)老師共有三人,其中兩人為博士,一人為碩士,隊(duì)伍建設(shè)整體層次較高。但除了對(duì)自身素質(zhì)的嚴(yán)格要求外,比較文學(xué)教研室還尤其關(guān)注對(duì)眾多教學(xué)輔助力量的爭(zhēng)取和吸納。目前,除了三位專職老師外,在我院實(shí)際參與這一學(xué)科建設(shè)工作的老師還另有五人。這五位老師有的來(lái)自于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有的來(lái)自于古代文學(xué),有的來(lái)自于文學(xué)理論,有的來(lái)自于新聞學(xué),而且身份也各不相同,有普通老師,也有行政人員。這些老師最初大都是出于對(duì)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好奇而初涉這一領(lǐng)域的,但是在長(zhǎng)期的課題合作與教學(xué)研討中,他們現(xiàn)在也都成了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中堅(jiān)力量,并在實(shí)際工作中承擔(dān)起了比較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智囊團(tuán)的任務(wù),從多個(gè)方面為我院比較文學(xué)的課程建設(shè)與教學(xué)改革群策群力,共謀發(fā)展。而在學(xué)生方面,比較文學(xué)所面向的學(xué)生在以漢語(yǔ)言文學(xué)專業(yè)學(xué)生為主體的同時(shí),還通過(guò)選修課的形式把對(duì)外漢語(yǔ)、新聞學(xué)等多個(gè)專業(yè)領(lǐng)域的學(xué)生也吸引了過(guò)來(lái)。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shuō),濰坊學(xué)院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的比較文學(xué)在主體層面的建構(gòu)上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gè)“舉院參與”的局面。而這種“舉院參與”的模式無(wú)疑對(duì)我院比較文學(xué)的發(fā)展起了一個(gè)非常好的推動(dòng)作用。首先這一模式不僅使我們有效地把整個(gè)文學(xué)院最精華的教師力量凝聚到了一起,從學(xué)術(shù)資源、人才資源上為比較文學(xué)創(chuàng)設(shè)了一個(gè)較高的發(fā)展平臺(tái),而且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學(xué)科壁壘,促進(jìn)了其他學(xué)科老師對(duì)比較文學(xué)的了解,為比較文學(xué)在文學(xué)院的總體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較為和諧的人文環(huán)境。其次多領(lǐng)域、多方向?qū)W生的參與,也極大地提高了比較文學(xué)在學(xué)生群中的影響力和關(guān)注度。這不僅為我們教學(xué)改革的順利進(jìn)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同時(shí)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們的努力成果。
二、環(huán)境要素層:以重點(diǎn)學(xué)科與精品課程建設(shè)為契機(jī),改善教學(xué)條件,完善監(jiān)控機(jī)制
比較文學(xué)作為文學(xué)院的一門專業(yè)基礎(chǔ)課程,是其他專業(yè)基礎(chǔ)課程的后續(xù)理論發(fā)展,它的教學(xué)往往是奠基在其他專業(yè)課程如古代文學(xué)、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外國(guó)文學(xué)等的先行授課的基礎(chǔ)上的,涉及面很廣并具有較強(qiáng)的理論性。它不比文學(xué)史課程從文學(xué)思潮、文學(xué)流派到經(jīng)典的作家作品分析,都有許多動(dòng)人的故事,有利于激發(fā)學(xué)生的情趣,吸引學(xué)生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共鳴。比較文學(xué)一定意義上講是抽象的、枯燥的、不易消化的。而另一方面受學(xué)科和研究方向的限制,高等學(xué)校比較文學(xué)的教研經(jīng)費(fèi)來(lái)源往往十分有限,長(zhǎng)期以來(lái)教學(xué)條件簡(jiǎn)陋、教學(xué)資源不足,是困擾這一學(xué)科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的一個(gè)重要問(wèn)題,尤其是傳統(tǒng)的粉筆加黑板的簡(jiǎn)陋教學(xué)條件無(wú)疑也更加加重了這門學(xué)科的抽象性、枯燥性,并增加了教師講授的難度和學(xué)生接受的難度。因此如何擺脫困境,尋找突破口,優(yōu)化教學(xué)資源,改善教學(xué)環(huán)境,全面推進(jìn)學(xué)科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是擺在每個(gè)比較文學(xué)教學(xué)單位面前的一個(gè)重要問(wèn)題。就我院比較文學(xué)而言,作為對(duì)困境的反撥,從2003年起,我們就確定了以高起點(diǎn)的課程建設(shè)目標(biāo)來(lái)實(shí)現(xiàn)自身超越的思路。契合當(dāng)時(shí)學(xué)校大力建設(shè)重點(diǎn)學(xué)科和精品課程的需要,我院比較文學(xué)抓住時(shí)機(jī),率先投入競(jìng)爭(zhēng)、建設(shè),經(jīng)過(guò)一定的籌備,從2004年起,我院比較文學(xué)便被評(píng)為濰坊學(xué)院的校級(jí)重點(diǎn)學(xué)科,同時(shí)還是校極精品課程的重點(diǎn)發(fā)展對(duì)象。以此為依托,比較文學(xué)相對(duì)也就獲得了較多的校方資金支持。現(xiàn)在我院比較文學(xué)教研室不僅單獨(dú)享有一定的科研、教學(xué)活動(dòng)基金,同時(shí)還擁有一個(gè)獨(dú)立的比較文學(xué)圖書資料室,藏書5000余冊(cè),另外還配有專門的電腦儀器和上網(wǎng)設(shè)施。這些資源、設(shè)備有效地保證了比較文學(xué)教師教研活動(dòng)的持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而作為一種制度保障,我院比較文學(xué)教研室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監(jiān)控措施來(lái)督促和規(guī)范比較文學(xué)的教學(xué)能持續(xù)不斷地向一個(gè)好的方向發(fā)展,如制定了各項(xiàng)教學(xué)管理規(guī)章制度,對(duì)影響教學(xué)質(zhì)量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作了具體規(guī)定;如改革了課堂教學(xué)效果的考評(píng)主體,把考評(píng)主體由過(guò)去的學(xué)生單一主體改變?yōu)轭I(lǐng)導(dǎo)、專家、同行、學(xué)生“四位一體”。以一種多元、立體的考評(píng)方法糾正了以往考評(píng)制度視角單一的弊端。另外根據(jù)師生互動(dòng)原理,我們還建立了師生互動(dòng)反饋制度,每學(xué)期授課過(guò)程中任課老師都會(huì)通過(guò)各種渠道和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及時(shí)獲取學(xué)生反饋的信息。此后不斷調(diào)整并完善教學(xué)活動(dòng)并再反饋給學(xué)生。這種互動(dòng)反饋,不僅有效地提高了教師單位時(shí)間的教學(xué)效率,而且還能及時(shí)地幫助教師找準(zhǔn)教學(xué)創(chuàng)新的方向,同時(shí)也為教師發(fā)揮學(xué)生潛力和進(jìn)一步地重點(diǎn)培養(yǎng)學(xué)生提供了條件。
三、功能要素層:弘揚(yáng)對(duì)話精神,培養(yǎng)學(xué)生的人文意識(shí)
作為人文學(xué)科中一門兼具對(duì)比性、跨越性和開放性等諸多學(xué)科性質(zhì)的課程,比較文學(xué)的具體學(xué)科功能無(wú)疑也是多重的,如它可以給學(xué)生提供一個(gè)新的學(xué)習(xí)平臺(tái),幫助他們把已經(jīng)學(xué)過(guò)的中外文學(xué)知識(shí)統(tǒng)領(lǐng)起來(lái);它可以給學(xué)生提供一種新的文學(xué)研究視角,讓他們能從一個(gè)嶄新的角度切入文學(xué)研究;它還可以建構(gòu)起文學(xué)與其他社會(huì)科學(xué)甚至是與自然科學(xué)之間的相互溝通的橋梁,大大開拓學(xué)生的知識(shí)視野。但在比較文學(xué)的眾多學(xué)科性質(zhì)與學(xué)科功能中,開放性以及對(duì)話精神可謂是其核心本質(zhì)。首先比較文學(xué)對(duì)跨越性文學(xué)現(xiàn)象和文化現(xiàn)象的研究,不以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異同對(duì)照為目的,而是通過(guò)聯(lián)系和比較,來(lái)尋求不同文化、文學(xué)的理解與和諧共處。其次,比較文學(xué)自身也是一門動(dòng)態(tài)的、以理論的不斷創(chuàng)新為特色的學(xué)科,它既易于吸收人文學(xué)科的最新知識(shí)成果,也較少受學(xué)科壁壘的拘囿。因此,誠(chéng)如樂黛云先生所說(shuō),比較文學(xué)所體現(xiàn)的實(shí)際上是一種人文精神,一種對(duì)話精神,它對(duì)于“培養(yǎng)國(guó)際精神,提高人文素質(zhì),促進(jìn)跨文化溝通”[1]具有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勢(shì)和條件。無(wú)獨(dú)有偶,李達(dá)三先生也同樣指出:比較文學(xué)的開放性、對(duì)話性思維“能把我們從個(gè)人的心智形式與傳統(tǒng)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來(lái)。比較的思維習(xí)慣使我們的心智更有彈性,它伸展了我們的才能,拓展了我們的視界,使我們能超越自己狹窄的地平線(文學(xué)及其他的)看到其他的關(guān)系。……比較文學(xué)的主要貢獻(xiàn)在于創(chuàng)造個(gè)人與社會(huì)之間的新平衡,求得人與機(jī)器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庶幾乎建立一種新的人文主義。”[2]在這兩位比較文學(xué)大師的理解中,一種以對(duì)話性思維為主要特征的人文精神的弘揚(yáng)都不約而同地被確立為是比較文學(xué)的終極培養(yǎng)目標(biāo)。與比較文學(xué)以對(duì)話為代表的人文精神相適應(yīng),我院比較文學(xué)在功能因素層的建設(shè)上,始終把握比較文學(xué)的基本特點(diǎn),從教學(xué)理念、課程內(nèi)容、課堂教學(xué)到綜合測(cè)評(píng)都非常重視比較視閾和對(duì)話式思維習(xí)慣的培養(yǎng)。如在具體的比較文學(xué)課程教授過(guò)程中,老師往往非常注重引導(dǎo)學(xué)生通過(guò)區(qū)分不同的學(xué)派特點(diǎn)看到比較文學(xué)的發(fā)展性與開放性;在講解文類學(xué)、主題學(xué)、形象學(xué)等比較文學(xué)的基本研究方法時(shí),也有意識(shí)地引導(dǎo)學(xué)生通過(guò)對(duì)話式思維去尋找、分辨和歸納不同文化、不同文學(xué)的同異點(diǎn),使學(xué)生學(xué)會(huì)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比較視域進(jìn)行文學(xué)對(duì)話或文化對(duì)話。顯然,這種對(duì)話式思維訓(xùn)練將非常有助于培養(yǎng)大學(xué)生成為國(guó)家需要的復(fù)合型人才。無(wú)論他們未來(lái)所從事的職業(yè)、生活方式如何的千差萬(wàn)別,這種對(duì)話式思維習(xí)慣以及隨之而來(lái)的理解、寬容和博愛的精神將伴隨他們終生,成為其內(nèi)在人格的一個(gè)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是比較文學(xué)課程的終極教育意義所在。#p#分頁(yè)標(biāo)題#e#
四、實(shí)踐要素層:以學(xué)生為本,重實(shí)效,求突破
教學(xué)方式的現(xiàn)代化,首先必須是教學(xué)思想的現(xiàn)代化。多年的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告訴我們,引導(dǎo)學(xué)生喜歡一門課程是保證和提高教學(xué)質(zhì)量的重要一環(huán)。只有當(dāng)學(xué)生喜歡這門課程的時(shí)候,他才會(huì)有學(xué)習(xí)的主動(dòng)性,才會(huì)進(jìn)入積極思維的狀態(tài),而不是僅僅為了應(yīng)付考試。作為一種教學(xué)實(shí)踐,新時(shí)期我院比較文學(xué)本科教學(xué)的創(chuàng)新,在教學(xué)理念的設(shè)定上,突出地貫徹了以學(xué)生為本的現(xiàn)代化教學(xué)思想,并在多項(xiàng)工作中予以了凸現(xiàn)。首先在教學(xué)內(nèi)容的設(shè)定上。在反思傳統(tǒng)比較文學(xué)教學(xué)內(nèi)容過(guò)于晦澀、難懂的弊端,我院比較文學(xué)新的課程內(nèi)容尤其強(qiáng)調(diào)教學(xué)內(nèi)容的縱橫兩維鏈接。即一方面注重比較文學(xué)與外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古典文學(xué)等傳統(tǒng)課程之間的縱向鏈接,另一方面注重比較文學(xué)與本院開設(shè)的非漢語(yǔ)言文學(xué)專業(yè)課程如廣播電視新聞、對(duì)外漢語(yǔ)等的橫向鏈接。如在談到比較文學(xué)的影響研究時(shí),我們的具體授課內(nèi)容既有純文學(xué)領(lǐng)域多國(guó)文學(xué)的交流影響,也有中外知名記者對(duì)比較視閾的采用所產(chǎn)生的實(shí)際效果介紹,同時(shí)還也糅合進(jìn)我院留學(xué)生在具體文化、文學(xué)交流中的收獲和感受。授課內(nèi)容生動(dòng)、廣博,并富有時(shí)代氣息,這種縱橫兩維鏈接模式極大地調(diào)動(dòng)了學(xué)生深入鉆研人文學(xué)科的興趣,也有效地?cái)U(kuò)充了學(xué)生的知識(shí)視野,并擴(kuò)大了比較文學(xué)在學(xué)生群中的知名度和美譽(yù)度。其次在課堂建設(shè)方面,我院比較文學(xué)教研室開創(chuàng)性地構(gòu)建了教室課堂和虛擬課堂兩類課堂,其中“教室課堂”主要是指教學(xué)課堂,它強(qiáng)調(diào)“知、行、研”相結(jié)合,把基礎(chǔ)理論的系統(tǒng)教學(xué)與科學(xué)方法的訓(xùn)練相糅合,把基礎(chǔ)理論轉(zhuǎn)化為多個(gè)具有較強(qiáng)實(shí)踐性、操作性的教學(xué)知識(shí)點(diǎn),鼓勵(lì)學(xué)生通過(guò)分組討論、個(gè)案研習(xí)、專題演講等方式參與課堂教學(xué),并以此來(lái)培養(yǎng)學(xué)生分析與解難的能力。而“虛擬課堂”,則是指建立虛擬網(wǎng)絡(luò)課堂平臺(tái),它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建設(shè),把問(wèn)題咨詢、互動(dòng)交流、學(xué)生作業(yè)、參考文獻(xiàn)、教學(xué)錄像等放到網(wǎng)上。使教學(xué)過(guò)程突破了有限課時(shí)的限制,擴(kuò)大了學(xué)生課外自主學(xué)習(xí)的空間。虛擬課堂為我院比較文學(xué)師生交流、學(xué)生自主學(xué)習(xí)提供了重要的平臺(tái),并也成為了我院教學(xué)信息傳遞與反饋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從學(xué)生角度而言“,教室課堂”與“虛擬課堂”的聯(lián)合使用則為學(xué)生提供了全方位的學(xué)習(xí)場(chǎng)景及大量的學(xué)習(xí)素材。這一方法在學(xué)生中的反響非常好。另外,在測(cè)評(píng)方法上。鑒于文學(xué)的審美本質(zhì)以及文學(xué)所特有的不確定性、不精確性和模糊性特征,我院比較文學(xué)課程在測(cè)評(píng)方法上也有意識(shí)地摒棄了以往過(guò)于絕對(duì)化的價(jià)值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如在考試內(nèi)容上,我們?cè)谠嚲碇屑哟罅私處熥杂擅}的份量,不僅考察學(xué)生的記憶、理解的程度,還關(guān)注他們的知識(shí)應(yīng)用與創(chuàng)新水平。另外在學(xué)生個(gè)人課程總成績(jī)中不僅包括期中和期末的考試成績(jī),還包括平時(shí)作業(yè)和課堂練習(xí)結(jié)果。現(xiàn)在我們這種全新的評(píng)價(jià)方式正有力地推動(dòng)著教學(xué)模式朝著素質(zhì)化教育的方向轉(zhuǎn)變,同時(shí)也形成了兩者互動(dòng)互進(jìn),共同發(fā)展的良好態(tài)勢(shì)。
五、教學(xué)創(chuàng)新的初期效果
比較文學(xué)范文6
【關(guān)鍵詞】文學(xué)翻譯;創(chuàng)造性叛逆;不可避免性;可接受性;文化差異
1.引言
二十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以來(lái),翻譯研究中的一個(gè)重要進(jìn)展是它的“文化轉(zhuǎn)向”。轉(zhuǎn)向文化意味著翻譯研究突破了傳統(tǒng)的美學(xué)或語(yǔ)言學(xué)的模式,上升為一種文化的反思。在跨文化交流日益繁盛、全球化趨勢(shì)不斷加強(qiáng)的當(dāng)今世界,翻譯充當(dāng)著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橋梁、溝通的樞紐。在表層語(yǔ)言轉(zhuǎn)換的背后,是深層的文化理解、溝通與互動(dòng),因而翻譯中文化研究的意義也日益受到重視。
曹順慶(2010a)指出,翻譯是文化交往中的常見現(xiàn)象,也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徑。他更指出,翻譯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純語(yǔ)言學(xué)問(wèn)題,兩個(gè)語(yǔ)言文本背后是兩種迥然不同的異質(zhì)文化體系……翻譯本身就是一種異質(zhì)文化的潛在對(duì)話(曹順慶,2010a)。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作為文學(xué)翻譯中的一種文學(xué)現(xiàn)象和文化現(xiàn)象,更是比較文學(xué)中一個(gè)具有獨(dú)特研究?jī)r(jià)值的課題。巴斯內(nèi)特和勒菲弗爾指出:翻譯研究實(shí)際就是文化互動(dòng)的研究。在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中,來(lái)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學(xué)發(fā)生碰撞、改鑄,變形等現(xiàn)象表現(xiàn)得特別集中,也特別鮮明。創(chuàng)造性叛逆反映了譯者自覺的文化意識(shí)和審美創(chuàng)造性,其最根本的特點(diǎn)是把原作引入了一個(gè)原作者沒有預(yù)料到的接受環(huán)境,并且改變了原作者最初賦予作品的形式。創(chuàng)造性叛逆發(fā)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異質(zhì)文化的差異性。一方面,它是譯者尋求跨越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去理解和再現(xiàn)迥異于自身文化體系的文學(xué)和文化現(xiàn)象時(shí)的一種必然選擇。譯者對(duì)原作的選擇、改變和增刪,既體現(xiàn)了譯者對(duì)原作的興趣和欣賞程度,也體現(xiàn)了譯者對(duì)媒介作品的理解與評(píng)價(jià)(曹順慶,2010b)。另一方面,它是翻譯活動(dòng)在主體文化環(huán)境規(guī)范和制約下的產(chǎn)物。在當(dāng)前比較文學(xué)研究發(fā)生文化轉(zhuǎn)向的背景下,從研究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入手,不但可以為比較文化研究提供一個(gè)理想的切入點(diǎn),由此深入到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譯和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文化研究之層面,而且有助于我們尋找出中外文化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優(yōu)化結(jié)合點(diǎn)和建設(shè)性的融合方式,避免“淮桔成枳” 式的移植可能引起的中外文化的劣化結(jié)合,從而促進(jìn)中外文化更好地對(duì)話、溝通與交流,使我們自己在這一過(guò)程中獲得更為豐富和強(qiáng)大的發(fā)展。通過(guò)從文化角度對(duì)文學(xué)翻譯中叛逆現(xiàn)象的研究,能反映出譯者的美學(xué)、文學(xué)素質(zhì)和取向、寫作風(fēng)格、文化身份及其翻譯主張。而且,譯文讀者、接受文化中的文學(xué)規(guī)范、意識(shí)形態(tài)規(guī)范、以及翻譯文學(xué)在接受文化中的地位也都對(duì)叛逆的發(fā)生起影響和制約作用,并在其中有所反映。翻譯在叛逆中孕育了創(chuàng)造性。正是通過(guò)譯本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原著的藝術(shù)生命才得以延續(xù)。正如龐德譯《落葉哀蟬曲》所增加的“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一行,才使中國(guó)讀者去了解原詩(shī)。而與“A wet leaf”意象相似的“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比喻眼前所閃現(xiàn)的臉,反映出詩(shī)人令人折服的想象力,使意象主義成為20世紀(jì)英美詩(shī)壇最重要的運(yùn)動(dòng)。叛逆作為翻譯中不可避免的屬性與現(xiàn)象,同翻譯本身一樣,既對(duì)接受文化中的文學(xué)系統(tǒng)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也參與了接受文化系統(tǒng)本身的構(gòu)建。
2.文學(xué)翻譯是創(chuàng)造性叛逆
從形式上看,翻譯似乎只是一種原語(yǔ)與譯語(yǔ)之間的代碼轉(zhuǎn)換。譯者首先對(duì)原語(yǔ)的信息代碼進(jìn)行解碼,然后用譯語(yǔ)的形式進(jìn)行重新編碼。翻譯看似簡(jiǎn)單,實(shí)際上卻是一個(gè)極為復(fù)雜的思維和心理活動(dòng)過(guò)程,它包括了對(duì)信息的接受、解讀、加工、創(chuàng)制這樣的復(fù)雜過(guò)程。郭沫若先生認(rèn)為,文學(xué)翻譯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chuàng)作,甚至還可能超過(guò)原作。當(dāng)然,理想的翻譯是既不要不及原文,也不要超過(guò)原文,所謂“過(guò)猶不及”,但這只是理想化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實(shí)際上是永遠(yuǎn)不可能達(dá)到的一個(gè)目標(biāo),這是由譯者在翻譯過(guò)程中主體作用的必然性所決定的。“從本質(zhì)上看,文學(xué)翻譯只是一種閱讀,是一種具有一定的文化藝術(shù)素質(zhì)、特定的時(shí)代歷史背景的讀者的解讀”(夏仲翼,1998)。在文學(xué)翻譯過(guò)程中,譯者首先是原作的讀者,然后才是譯者。讀者在文本閱讀過(guò)程中的主體作用意味著譯者首先是一個(gè)獨(dú)立主體。文學(xué)翻譯活動(dòng)自始至終必須通過(guò)譯者主體意識(shí)的作用才能完成。興起于20世紀(jì)60年代的讀者中心論認(rèn)為,讀者對(duì)文本的接受過(guò)程意味對(duì)文本的創(chuàng)造過(guò)程。作為接受主體,每一個(gè)讀者都與文本構(gòu)成一種獨(dú)特的關(guān)系,即不同的讀者會(huì)對(duì)文本產(chǎn)生不同的具體化,這就是王文斌(2001)所說(shuō)的“文本本無(wú)定旨,旨隨讀者而生”、“文本在被接受的過(guò)程中所遇到的是具有不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心理結(jié)構(gòu)、個(gè)性氣質(zhì)、審美意向、鑒賞定勢(shì)的接受主體。每一個(gè)接受主體都會(huì)能動(dòng)而不會(huì)受動(dòng)地參與文本的再創(chuàng)造,從而使文本解讀過(guò)程不可避免地留下接受者具有獨(dú)特個(gè)性創(chuàng)造力的主體痕跡”。
3.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美國(guó)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dá)依照接受美學(xué)的理論指出,譯文必須能夠被讀者接受,翻譯過(guò)程才算真正完成。因此,譯者在翻譯時(shí)必須考慮到譯文的可接受性。鑒于文學(xué)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特點(diǎn),筆者認(rèn)為,要使翻譯界長(zhǎng)期爭(zhēng)論不休的“直譯、意譯”、“歸化、異化”、“等值、等效”這些矛盾得到緩解,除了必須用動(dòng)態(tài)的、多元的讀者反應(yīng)論來(lái)指導(dǎo)翻譯實(shí)踐之外,還必須給文學(xué)翻譯制定一些最低標(biāo)準(zhǔn)。這些標(biāo)準(zhǔn)不是要求譯者必須做什么,而是引導(dǎo)譯者怎么做。在翻譯過(guò)程中,不僅譯者的理解和詮釋與其他譯者有所區(qū)別,而且任何兩種異質(zhì)文化都難以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進(jìn)行對(duì)話,如強(qiáng)勢(shì)文化與弱勢(shì)文化之間、中心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等,某一信息從一種文化傳輸?shù)搅硪晃幕瘯r(shí)變形、改造、重塑的情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譯者與讀者受各自傳統(tǒng)與價(jià)值觀等因素的制約,譯者的價(jià)值取向也會(huì)有所不同,加之不同的翻譯目的性以及期待讀者群的不同,文本本身的性質(zhì)也對(duì)譯者有不同要求,因此,對(duì)紛繁復(fù)雜的翻譯活動(dòng)就需要建立一個(gè)開放的、多元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相結(jié)合的標(biāo)準(zhǔn)。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程度與可接受性就建立在這些標(biāo)準(zhǔn)上,即:符合知識(shí)的客觀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3.1 符合知識(shí)的客觀性。知識(shí)的客觀性是一切理解活動(dòng)的基礎(chǔ)。翻譯活動(dòng)中,在強(qiáng)調(diào)譯者主體作用的同時(shí),還必須注意知識(shí)的客觀性等問(wèn)題。原文文本視域本身就包括了知識(shí)的客觀性,是作者生存環(huán)境與生存方式的反映。對(duì)譯者而言,他的理解中也包括了這種知識(shí)的客觀性。所以,在譯者與作者通過(guò)文本的對(duì)話交流中,由于兩個(gè)視域的沖突與碰撞而產(chǎn)生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其可接受性很大程度上依靠譯入語(yǔ)讀者知識(shí)的客觀性作為評(píng)判的尺度。
楊巨源詩(shī)《城東早春》:
詩(shī)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
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
英國(guó)漢學(xué)家Herbert A. Giles譯文:
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
When bud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
That beautiful embroidery the days of summer yield,
Appeals to every bumpkin who may take his walks a field.
可以看出,譯者以early May譯“新春”一詞是對(duì)原詩(shī)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因?yàn)樵谥袊?guó),五月初已經(jīng)將近暮春了”。
各地地理不同,氣候不一。以“May”(五月)譯“新春”,其實(shí)是隱喻功能的體現(xiàn),就是表達(dá)譯入語(yǔ)文化里的“新春”概念。“我們所接受的不可能是純粹的、原汁原味的異域文化,也不可能是與本民族文化毫不相關(guān)的文化”(曹順慶,2010:101f)。因此,表面上譯文不符原作,但符合譯文讀者的認(rèn)知。以early May譯“新春”也與下文中的willow spray構(gòu)成尾韻,符合英詩(shī)的閱讀習(xí)慣。
3.2 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原文文本是一個(gè)開放系統(tǒng),譯者對(duì)一些問(wèn)題可以有不同的闡釋。但翻譯活動(dòng)不同于一般的解釋活動(dòng),它不是完全自主性的活動(dòng),有文本的定向性與框架的制約。例如,雖然文學(xué)評(píng)論家說(shuō),“有一千個(gè)讀者,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還是哈姆雷特,不會(huì)是羅密歐,也不會(huì)是奧賽羅,絕不會(huì)成為另一種文學(xué)形象,其身份、地位、為父報(bào)仇這些事實(shí)是不可改動(dòng)的。至于他為父報(bào)仇為何延宕時(shí)日、遲疑不決可能各人有各人的解釋,這一點(diǎn)是開放的,因?yàn)樯勘葋啿]有明明白白告訴我們,這就是空白和不定點(diǎn)。譯者可以在這些空白處發(fā)揮想象,并用自己的知識(shí)去解釋與填充,在不定點(diǎn)之處用自己的理解去確定,但這并不是要改變?cè)鞯膱D式框架,文本對(duì)譯者有一定的制約性,譯者要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結(jié)構(gòu),尊重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原文文本的定向功能與框架制約是理解活動(dòng)和解釋活動(dòng)的前提和基礎(chǔ),作為譯者必須給予尊重,否則翻譯就不是翻譯而純粹是創(chuàng)作了,而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特點(diǎn)就失去了其依據(jù)和價(jià)值。例如,近代翻譯家蘇曼殊在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時(shí),開始前六章是照原作翻譯的,但后來(lái)便越來(lái)越偏離原作而隨意發(fā)揮了。他為了批判孔子的話,竟自己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一個(gè)人物,借此人之口吐自己之言:“那支那國(guó)孔子的奴隸教訓(xùn),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guó)民也要聽那些狗屁嗎?”這種翻譯顯然帶著譯者主觀意志的痕跡,在作品內(nèi)容的傳達(dá)上發(fā)生了變形,因而違背了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對(duì)這種失敗的翻譯所有譯者都應(yīng)該引以為戒。
4.創(chuàng)造性叛逆與文化差異
翻譯是跨文化的語(yǔ)言轉(zhuǎn)換藝術(shù)。文學(xué)作品通過(guò)翻譯超越了語(yǔ)種,跨越國(guó)界,進(jìn)而越過(guò)地域和歷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社會(huì)習(xí)俗和人際關(guān)系,進(jìn)入一個(gè)嶄新的接受環(huán)境。在這一過(guò)程中,譯者要面對(duì)的絕不僅僅是兩種語(yǔ)言如何轉(zhuǎn)換的問(wèn)題。語(yǔ)言是文化的載體,同時(shí)又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的困難,就在于文化翻譯、文化再現(xiàn)的困難。譯者的難題在于要從某種語(yǔ)言的創(chuàng)作中,窺探到使用該語(yǔ)言的社會(huì)之獨(dú)特的文化,并在將這種文化信息傳遞到譯入語(yǔ)文化語(yǔ)境中時(shí),如何根據(jù)自己獨(dú)特的追求和讀者接受的需要,以創(chuàng)造性的手段跨越文化差異給文學(xué)翻譯和文學(xué)接受帶來(lái)的障礙,從而達(dá)到文學(xué)傳播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就文化意義而言,翻譯是尋求將某一特定文化語(yǔ)境中的作品的意義、精神、內(nèi)蘊(yùn)再現(xiàn)于另一文化語(yǔ)境中,但事實(shí)上,不折不扣地再現(xiàn)原作中的文化涵義幾乎是不可能的。“就跨異質(zhì)文明的文學(xué)文本交流與對(duì)話而言,其根本的變異還是滋生于兩種語(yǔ)言之間的差異性”(曹順慶,2010,:106g)。譬如,松、竹、梅“歲寒三友”,在中國(guó)文化中象征著堅(jiān)韌不拔的優(yōu)良品質(zhì),而對(duì)西方人來(lái)說(shuō),它們不過(guò)是三種普通的植物,沒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涵義。如果譯者想通過(guò)翻譯在西方文化中準(zhǔn)確地傳達(dá)它們?cè)械奈幕瘍?nèi)涵,就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要解脫語(yǔ)言的束縛和制約,必然要把各種不同的語(yǔ)言世界中所體驗(yàn)到的“細(xì)微差別”帶入對(duì)方,這就意味著創(chuàng)新(ibid)。翻譯所必然遭遇到的文化上的差異和語(yǔ)言轉(zhuǎn)換過(guò)程中表述上的困境,決定了任何翻譯都必定是一種跨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如何跨越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去理解與再現(xiàn)迥異于自身文化體系的文學(xué)和文化現(xiàn)象,是譯者根本無(wú)法回避的一個(gè)挑戰(zhàn)。在面對(duì)挑戰(zhàn)時(shí),創(chuàng)造性叛逆往往成為譯者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這種選擇反映出譯者一種自覺的文化意識(shí),它源于譯者對(duì)跨文化文學(xué)翻譯中不同文化體系之間將會(huì)產(chǎn)生的碰撞、沖突和影響以及接受過(guò)程中的文化因素等問(wèn)題的體認(rèn)。
舉例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名著《水滸傳》的英譯本,目前的三個(gè)版本在書名上就大異其趣。賽珍珠(Pearl S.Buck)譯為“All Men Are Brothers”(1933),杰克遜(J.N.Jackson)將其譯為“The Water Margin” (1937),沙博里(Sidney Shapiro)則譯為“Outlaws of the Marsh”(1980)。孰優(yōu)孰劣,不是這里討論的重點(diǎn)。我們關(guān)注的是,在面對(duì)異質(zhì)文化的差異性給文學(xué)翻譯造成的困難時(shí),譯者是如何作出選擇的。請(qǐng)看賽珍珠在譯序中的一段自述:
英文書名自然不是中文小說(shuō)名字的意思,因?yàn)橹形拿制嫣氐仉y譯。Shui字是水的意思,Hu字是水泊或水邊的意思,Zhuan字與英文小說(shuō)之意相同。把這些字用英語(yǔ)并列在一起幾乎是無(wú)意義的,至少以我看來(lái),那將會(huì)使讀者對(duì)此書得到一種不正確的印象。因此,我專斷地選擇了孔夫子的一句名言作為英譯本的書名,此書名含義的廣度和深度,都符合水滸山寨里這伙正義強(qiáng)盜所具有的精神。
賽珍珠熟悉中國(guó)文化,精通漢語(yǔ),被譽(yù)為“中國(guó)通”。她譯《水滸傳》,用她自己的話說(shuō),是“盡力逐字逐句地譯出”,好讓那些不懂中文的讀者在讀她的譯本時(shí),能產(chǎn)生像讀中文小說(shuō)一樣的幻覺。但在翻譯書名時(shí),卻不得不將其置于中西文化差異的前提下,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加以闡釋,最后以孔子的一句名言“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曲達(dá)原書名之意,以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手段,尋求跨越文化上的差異和表述上的困境給文學(xué)翻譯帶來(lái)的障礙。
讓我們?cè)偻ㄟ^(guò)Herbert A. Giles英譯《聊齋志異》時(shí),對(duì)其中一段文字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來(lái)體會(huì)譯者如何以“歸化”手法使譯文適應(yīng)譯入語(yǔ)文化的。《羅剎海市》中提到馬驥得到龍女書信一封,在信的后半部分,龍女重溫了她與馬驥許下的諾言,并云:“君似征人,妾作,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這里,“征人”是指常年在外,不能返鄉(xiāng)的游子,而“”為蕩子之婦的省略,非作現(xiàn)今意義上的解。請(qǐng)看Giles的譯文:
You are my Ulysses, I am your Penelope; though not actually leading a married life, how can it be said that we are not husband and wife.
原文用琴瑟喻指夫婦,語(yǔ)出《詩(shī)?周南?關(guān)雌》:“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是以琴瑟諧和喻夫婦和合;用“置而不御” 比喻夫妻兩地遠(yuǎn)隔,不能相守。這種用喻顯然是中國(guó)文化所特有的。為了使譯入語(yǔ)讀者能夠毫不費(fèi)力地理解原文,譯者用Ulysses,Penelope這兩個(gè)希臘、羅馬神話中的著名人物來(lái)代替與之有相似特征的“征人”及“”,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不僅從形式上縮短了譯入語(yǔ)讀者與譯作的距離,而且巧妙地傳達(dá)出了人物在作品中的特定身份與處境。當(dāng)然,這樣處理究竟帶給譯入語(yǔ)讀者什么樣的文化心理反映,我們不好考察;也許這樣翻譯可以避免譯入語(yǔ)讀者對(duì)中國(guó)文化可能產(chǎn)生的不必要的誤解,也許他們會(huì)認(rèn)為中西文化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有一點(diǎn)是肯定的,那就是它拉近了譯入語(yǔ)讀者與譯本之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