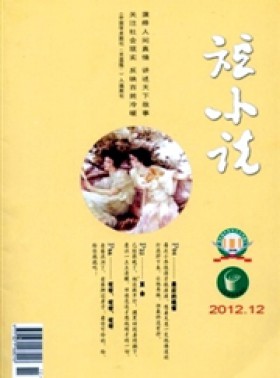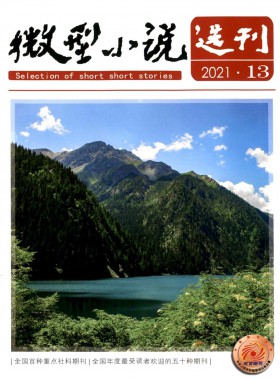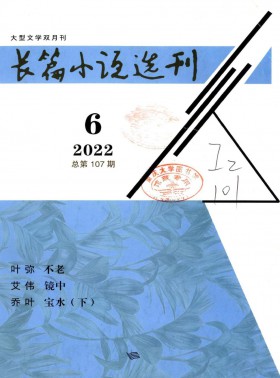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小說的結構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小說的結構范文1
關鍵詞:白行簡;藝術結構;審美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5-0194-03
白行簡是我國唐代的文學家,字退之,是我國著名文學家、詩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不像其兄白居易那樣對后世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他在唐傳奇方面的成就卻非常高。
白行簡和白居易很長時間都生活在一起,在白居易的指導下讀書、寫作,在文章風格上也就不可避免的帶有白居易的特點。白行簡一生都生活在其兄白居易的光環下,他的風采被白居易所掩蓋,但是,歷史的塵埃在時間的吹拂下慢慢散去,歷史露出了本來的面目,白行簡的文學成就不斷被后人發掘發現,他的文學作品在唐傳奇小說中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一、白行簡文學作品內容簡介
白行簡擅長辭賦,尤其以傳奇小說最為著名。傳奇小說代表作為《李娃傳》。《李娃傳》描寫了滎陽大族鄭生在赴京趕考途中,愛上了長安風塵女子李娃,在青樓流連中,鄭生把錢財揮霍殆盡被趕出來。鄭生憤恨交加身染重病,后來不得已成為唱挽歌的歌郎。有一次在和別人比賽唱歌的時候被他的父親認出來,他的父親覺得鄭生辱沒門風,因此把鄭生鞭打一頓,鄭生差點命喪鞭下,然后被趕出了家門。鄭生后來被同伴救活,淪為全身潰爛的一個乞丐。有一次,鄭生由于饑寒交迫在風雪中痛哭被李娃看見并認出來,李娃感念其對自己的真情,也覺得鄭生的狀況自己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自己贖身和鄭生生活在一起。李娃鼓勵鄭生考取功名,鄭生發奮讀書終于進士及第,后來父子相認,家人也接受了李娃,李娃也被封為國夫人,成就了一曲文人的愛情佳話。
說到白行簡的文學作品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大樂賦》。《大樂賦》出自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石窟,在1908年被法國漢學家伯西購得。作品用俚語描寫了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敘述了的過程,心理與的細膩描寫,為人們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文學參照。
二、白行簡小說完整清晰地藝術結構,成為唐傳奇成熟的標志
文學作品的藝術結構是文學家藝術水平和藝術審美的表現,清代文學家李漁就曾經在《閑情偶記》中這樣描述藝術結構“文學作品的藝術結構就像是建筑師建造的宅院”。因此,藝術結構設計關系到文學作品的整體框架,也體現了文學家的獨特創造力,文學作品的藝術結構體現作者的創作意圖、藝術風格等,可以說作品的藝術結構就是作品生命力的體現,好的藝術結構會煥發文學作品的生命力,有多著名的文學作品如《紅樓夢》、《西游記》等其藝術魅力也通過其成功的藝術結構得以體現。
白行簡的小說大部分是以時間為序,直線推進,脈絡清楚,人物描寫,事件的發展都在時間的主線引導串聯下不斷推進,構成一個個藝術沖突。以白行簡小說《李娃傳》為例:
(一)小說開始和結尾相呼應,體現小說的完整性
小說開始交這篇小說的意圖和原因“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小說結尾和開頭相呼應重申寫作的背景“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小說開始和結尾的呼應增加了小說的真實性,也為小說的展開鋪墊了可信性。
(二)小說建構中多個藝術沖突,成為小說藝術結構的又一特點
小說剛開始的描寫并沒有脫離“誘引賓客”的老套路,“嘗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小說描寫鄭生在拜訪友人途中看到一所開著一扇門的宅院,宅院中有一個姿容嬌美的少女,鄭生一見之下竟舍不得離去,少女看起來也對鄭生心存愛慕。可以說小說開始并沒有很新穎的故事沖突,但是卻符合當時的社會背景。隨著情節的展開,小說的沖突也越來越引人入勝。鄭生打探出李娃的住處前去拜訪,李娃和老鴇假意推辭挽留。當鄭生的錢財耗盡,李娃假意說自己無法懷孕需要到廟里祈禱,回來的路上,李娃讓鄭生拜訪自己的姨娘,自己因為母親突然得病先回去,等鄭生再回到他們原來的住處時已是人去樓空,“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處,曰:‘不詳其所。’”鄭生趕往李娃姨母的住處同樣被告知“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至此,騙局方被揭開,也使得故事沖突達到一個小的。
作者構建的藝術沖突遠不止這些:鄭生由于身無分文,被邸主救起淪為挽歌歌郎,在賽歌時被家中的老管家認出,被其父責備“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鄭生再次被自己的親人拋棄。鄭生在這種狀況下乞討為生,被李娃發現,“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小說的藝術沖突一環緊扣一環,環環引人入勝,讀者的心也被這些藝術沖突反復地在“緊張――放松”的循環中一波波的牽引著。小說描寫鄭生在李娃的激勵下考取功名,當讀者以為李娃和鄭生終于修成正果時,李娃卻說“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愿以殘年,歸養小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至此,一個善良、美貌、自知的藝術形象躍然紙上,小說的藝術沖突也再次引起新的懸念。
三、細致逼真地描寫和寫實手法的結合,構建出獨特的審美意境
以《李娃傳》為例:首先,小說塑造了一批善良美好的人物,與當時社會的門第觀念和等級制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無論在哪個時代,的地位都是低下的,唐傳奇小說塑造了一批心地善良,品行高潔,敢愛敢恨的形象,用的地位低下反襯其品行的高潔,《李娃傳》中李娃的形象塑造也是如此。李娃愛戀鄭生后因門第觀念又拋棄了鄭生,但是看到落魄中的鄭生后,自贖其身,鼓勵鄭生上進,重新參加科舉,在鄭生考取功名后,又因自己低微的出身會影響鄭生的前途,從而要求離開鄭生,女性對愛情全身心的付出躍然紙上。
小說還塑造了一批同樣處于社會底層的善良的群體。鄭生在李娃不辭而別后,已經身無分文,回到布政里原來的住所,邸主同情的遭遇給他飯吃,鄭生由于怨恨交加而得了重病,邸主把鄭生搬到殯儀館中,“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在鄭生身體稍微好些后,這些人讓鄭生牽引靈帳養活自己,以生存。這些社會底層人們人性的善良和鄭生父親的因為辱沒家門而置鄭生的生死與不顧,形成鮮明對比,突出了底層勞動人民的人性光輝。
其次,人物塑造形象飽滿鮮活,內涵豐厚,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白行簡的小說《李娃傳》重點塑造了李娃的藝術形象。李娃的形象是通過情節的展開一點點表現出來的。作品剛開始描寫了李娃的美貌,“妖姿要妙,絕代未有。”小說描寫鄭生想看又羞于看的情態“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假借馬鞭墜地等待侍從撿拾,多次偷看少女,把鄭生青年情竇初開,對李娃的愛慕情態刻畫的細致入微,也從一個側面描寫出李娃的美貌。李娃的美貌只是一個方面,作品中對李娃性格冷靜,機智、沉著也進行了細致的刻畫。李娃對自己和鄭生的愛情是不抱任何希望的,這也是當時社會制度,等級觀念造成的,自己和鄭生的關系就是一場交易,當鄭生錢財耗盡,他們的關系也就會隨之終結。基于這個原因才有了后來李娃和鴇母設計驅逐鄭生,在實施計劃的過程中顯示出李娃的機智和沉著、冷靜。
李娃也是善良的,當李娃看到風雪中渾身潰爛、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殆非人狀的鄭生,抱著鄭生的頭,用華美的棉襖把鄭生抱進房間,失聲痛哭,自贖自身來救鄭生,展現了李娃富于人性的一面,對鄭生悉心地照顧,也逐步展現出李娃對鄭生的真愛。此后,李娃幫助并激勵鄭生重新考取功名,這一點實際表現了李娃的志向追求。當鄭生進士及第后,李娃又告訴鄭生,因為以前的行為不好,因此應該更加努力。顯示出李娃眼界的開闊,思慮長遠,見識的不同尋常。
唐傳奇小說中刻畫了幾個著名的女性形象;李娃、崔鶯鶯、霍小玉。崔鶯鶯自薦枕席被張生拋棄,霍小玉把愛情和命運系于一人,但遇人不淑,含恨而死。唯有李娃理性和感情并存,并且理性一直支配著感情。當鄭生功成名就時,李娃選擇了離開,用自己的離開映射了當時封建社會的等級門閥制度的殘酷,也用自己的離開,完成自己自尊獨立的人格,可以說,李娃的形象才是女性表現自己地位平等的形象。
最后,小說表現的對戀愛自由,婚姻平等的追求,成為小說美好愛情觀的獨特審美效果。封建禮教,等級制度是不可能成就李娃和鄭生的愛情的,但是作者卻塑造了幫助鄭生求取功名后默默隱退的李娃,當滎陽公知道這一切后,感念李娃的善良、器識和志向最終接納了李娃,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成就了才子佳人的美好愛情,小說的這種情節安排,表現出底層勞動人民對等級制度的反抗,也表現出對美好愛情的向往。
此外小說在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上,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交互使用,使得人物形象立體豐滿。例如對于李娃的美貌既有直接描寫“妖姿要妙,絕代未有;明眸皓腕,舉步艷冶,”又有側面描寫“生遂驚起,莫敢仰視;觸類妍媚,目所未睹。”正反面人物的刻畫相互映襯,善者更善,惡者更惡。例如在對待與鄭生相認一事上,管家老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但是滎陽公卻以辱沒門庭而鞭之數百,棄之而去。反映出門風等級觀念對人性的扭曲,也更加襯托出底層人物的人性光輝。
寫實手法和細節描寫表現出唐傳奇的高度藝術成就。如鄭生再次拜訪李娃時,李娃的侍女聽見鄭生問“此誰之第耶?”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通過這個細節可以看出,第一次見面后,李娃對鄭生也是日思夜想,心生愛慕,她的侍女也是知道的,才有這句遺策郎的出現。鄭生作為歌郎與人比賽的場景描寫,表現出唐代城市生活的背景。
四、作品情節架構曲折跌宕,引人入勝
白行簡的小說《三夢記》盡管篇幅短小,但是情節離奇,通過同一個敘事理念把三個夢貫穿連綴起來,現代電影《盜夢空間》于此有異曲同工之妙。《三夢記》中情節的構建夢中有夢,現實和夢相通,夢和夢相通,情節虛幻離奇,表現了現實和夢境的融合。小說語言質樸簡練,情節離奇,使人拍案。
白行簡的小說擺脫了唐傳奇初期志怪小說的桎梏,開始描寫社會人情,故事結構完整,情節曲折跌宕,百轉千回,情深意切,體現出白行簡高超的文學造詣。《李娃傳》描寫滎陽公老來得子,鄭生聰慧無比,但是在趕考途中遇到美麗的李娃,散盡千金后被李娃設計拋棄,流落街頭成為挽歌歌郎。《李娃傳》總是在一個情節看似走到盡頭時,峰回路轉出現另一個情節,例如在賽歌會上,鄭生被管家認出,本可以擺脫窮困的日子回家,卻又被其父鞭撻拋棄,在鄭生走投無路時李娃重新出現,當鄭生取得功名后,本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但李娃決意請辭。一波三折的情節充滿戲劇性的變化,使得故事情節波瀾起伏,引人入勝。盡管《李娃傳》在結局的安排上回避了尖銳的社會現實和社會矛盾,但是表現了人們對美好愿望的追求,對愛情自由,婚姻平等的美好祝福,成為唐傳奇中的千古絕唱,也代表著白行簡最高的文學藝術成就。
白行簡的小說描寫細膩,虛實結合,情節曲折,人物刻畫生動鮮活、飽滿,細節描寫逼真傳神,字里行間感情真摯,代表了唐傳奇的最高藝術成就,其文學審美價值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的明珠。
參考文獻:
〔1〕劉艷.淺論中國小說的成熟――白行簡《李娃傳》賞析[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4,2(1):148-150.
小說的結構范文2
流浪漢小說影響下的《圍城》敘事結構分析
摘要:若要尋找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將審美觀照指向人之在世終極困境的著作,我們的目光甚至無需搜索便會為錢鐘書《圍城》的耀眼光芒而停落。在圍城中,作者通過對方鴻漸人生體驗的描寫,在現代意識的覆蓋下喚回了一個古老的哲理命題,即,人類存在的困境狀態以及人生出路何去何從的問題。作者對象征和隱喻層出不窮的運用,使其特色鮮明的話語表達在一個恰當的程度上契合了《圍城》主題意蘊的深度和思想批判的高度。除此之外,這樣一個博大而莊嚴的命題,若是沒有一個獨特的敘事結構來支撐,也便絕無屹立的可能。本文正是要分析《圍城》在沿襲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之外,是怎樣通過適當的借鑒西方流浪漢小說的某些敘事結構特點,以形成作品自身獨特的敘事風格的。
關鍵詞:《圍城》敘事結構特點、流浪漢小說、借鑒與發揚
作者簡介:方茜,女,籍貫山西,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文藝學專業研究生
小說的結構范文3
2.七夕那天,我的狗要是出去拍拖,我負責看門等狗回家。
3.第二杯半價這種福利從老沒享受過。
4.別再說自己有孤獨和烈酒,其實你就是一條單身狗。
5.人家老婆都會生氣了,我老婆還在充氣。。。
6.請叫我單身龜!這個年齡的狗都死了幾條好嗎!
7.如果說女人是衣服,那我已經裸奔了三十年了!
8.我把10086備注成了男朋友,這樣每天能感受到男朋友的關心。
9.七夕那天我會玩一整天的連連看,消滅一對是一對。
10.七夕,我好友里誰秀恩愛,我就截圖,將來你結婚對方如果不是ta,我就把照片塞紅包里送給你們!
11.秀恩愛沒有那么容易,單身狗也有Ta的脾氣。
小說的結構范文4
關鍵詞:莫言;小說;敘事學;敘事倫理
莫言是我國現當代優秀作家,其作品眾多,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同時,莫言也是我國一位倍受爭議的作家,人們對其作品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但是盡管莫言小說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但是盡管如此,不可否認其對我國敘事文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論是作品內容還是敘事方面的外在表現形式,莫言的小說作品都體現了我國現代文學藝術與傳統文學的完美融合,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下面本文就結合莫言小說的敘事倫理,對其敘事學價值進行具體分析。
一、莫言小說的敘事倫理――“作為老百姓的寫作”
研究莫言小說的敘事倫理可以從讀者角度對莫言小說作品進行分析,能夠發現其小說不僅能以文本話語的形式客觀存在于社會上,還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閱讀經典的機會,并且表現出一種體驗和感受的力量,而小說的倫理性正蘊含于這種力量之中。通過這種倫理層面的觀察和解析,可以真正明確一位作家對社會乃至文學歷史產生的創作價值。從敘事倫理層面對莫言的小說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敘事學和倫理學的結合分析中,莫言所闡述的意境不是單純空間意義上的倫理,而是將倫理學放置在敘事學的維度中進行分析和考察,在精神指向方面表現出一種生命的存在性領域。莫言的小說作品幾乎都包含著濃郁的生命氣息,向讀者講述了關于生命的故事,《透明的紅蘿卜》中生命頑強的男孩眼中重要的“紅蘿卜”意象,《紅高粱》中“爺爺奶奶”不拒禮法、轟轟烈烈的愛情以及《檀香刑》中孫丙的戲子英雄等,都在痛徹心扉的故事敘述中表現出“生命存在”的倫理。而這種生命存在的感覺是社會理性的道德法則難以明確解析的,從更深層面上探尋,莫言小說中的敘事倫理正如《文學創作的民間資源》中所說,在本質上表現為“作為老百姓的寫作”,并且正是莫言的這種敘事倫理特征,鞏固了莫言在“民間”敘事領域的重要地位[1]。張清華先生也極度推崇莫言小說的敘事倫理,在《敘述的極限》中曾對莫言小說中敘述倫理的表現進行了梳理,認為莫言敘事中的民間倫理原則在其早期作品《紅高粱家族》中就應該出現雛形,在家族敘事中,以民間化和野史化取代了傳統敘事中較為權威的國家歷史中心地位,在我國當代敘事文學歷史中具有一定的終結意義。而莫言的其他作品如《白狗秋千架》和《球形閃電》等則表現出敘事倫理中民間的生機,與代表作《天堂蒜墓之歌》中所呈現出的民間被施暴屈辱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莫言最基本的民間寫作敘事倫理。同時,莫言的代表作《豐乳肥臀》、《檀香刑》等也促使莫言小說中的民間敘事倫理等到了進一步升華,最終使莫言的文學創作超越了我國現當代鄉村敘事中無法擺脫的風俗趣味和道德沖突等,在精神層面構建了一個全然凌駕于道德世界至上的“生命大地”。因此可以說,莫言小說在敘事學上的價值在于其以人類學的博大以及人類原始追求為依托沖破了倫理學的限制,極大的拓展了敘事世界的發展局面,幾乎終結了我國傳統小說敘事中單一的歷史史學思想,構建了一種基于生命本體論的歷史詩學。
二、莫言小說的敘事學價值
(一)敘事方式
縱觀我國文學發展歷程,不同歷史時期作家的敘述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從整體上看仍然基本處于不斷地進步和調整過程中,表現了作家對敘述方式的深入探索。而對于莫言小說來說,如果對莫言不同時期的作品進行縱向分析,則可以發現,其小說敘事方式也處于一種不斷的探索和進步過程中,較之于早期的小說作品,莫言后期小說的敘事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敘事結構也逐漸變得更為復雜多變,對敘事方式的掌握更為合理[2]。在莫言的小說中,一般在表面上會將第一與第三人稱的敘事進行對立,但是在作品的精神層面則表現出二者的自由轉換和辯證統一,兩者在文中的緊密合作將主人公的主觀意識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同時,莫言小說敘事中的主觀情緒化特征一般表現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其長篇小說的典型代表就是綜合運用各種敘事方式的完美體現。根據莫言小說的創作特點,其敘事方式具體特色表現在三個方面:使用人稱代詞“我”、敘事方式與環境緊密結合、能夠運用多種表現形式展現作者的主觀思想。莫言小說對于多種敘事方式的使用,不僅增加了小說的趣味性,還能夠將生活中場景科學合理的展現出來,幫助讀者根據細節理解小說的內涵,進而感受小說中的情感變化。
(二)敘事結構
小說敘事結構一般可以根據其發揮的作用具體劃分為內外部兩種結構,莫言小說的敘事結構具有一定的個性特征,對其進行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莫言在進行小說創作過程中,高度重視選擇和結合合理的敘事結構,在不斷變化中表現故事的精神內涵和主人公的真情實感,進而幫助作者體會小說的微妙變化,準確抓住作品靈魂。同時,莫言的小說也強調對故事進行合理表述,旨在通過情感的變化與多種敘事結構的結合,在彰顯小說中心思想的基礎上凸顯出一定的文學價值。
(三)敘事學價值
綜合上述分析,莫言小說作為我國現當代文學的典型代表,其在創作中運用的敘事方式和結構具有較高的敘事學研究價值。各種敘事方式之間的結合和聯系,不僅表現了我國現當代小說的敘事創作史,還在未來敘事學思想在高校內的傳播方面具有一定的參照價值[3]。可以說,莫言開辟了我國小說創作的特殊道路,既沒有完全摒棄傳統小說的敘事方式,也沒有忘記對現代小說思想進行創新,而是在傳統和現代之間適當取舍,凝練出小說創作的精華。因此可以認為,莫言通過對小說敘事技巧的創新發展,將小說創作中的敘事學價值不斷的積累下來,在提升自身小說質量的同時,為我國小說的敘事學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參考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
結語:
總而言之,莫言作為我國現當代代表性作家,其小說創作在敘事方面表現出了獨特的個性,對我國小說創作的發展和小說敘事學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所以,相關莫言小說研究者應該加強對莫言小說敘事學研究的重視,為我國高校學生對于莫言小說敘事學的學習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作者單位:南陽理工學院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1]高文霞,任慧芳.莫言小說敘事空間研究[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8(6):22-24.
小說的結構范文5
關鍵詞:傳統小說 魯迅作品 結構星途
20世紀初,我國的小說創作。從總體上而言,就其結構形態上仍然停留在簡單的線性章回體,以情節取勝的形式上,與整個社會以及整個世界的發展步伐顯然是不適應的。當《新青年》上陸續出現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等小說后。傳統小說的鎖閉性機構被完全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開放式的小說結構,這種結構:情節面向生活面向讀者心靈,小說本身只能是半個世界卻延伸在生活中和讀者的心靈中,兩者結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其作品在作品之外開拓空間,大大超越了本身的容量,豐富了小說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創作中結構形態的變異,標志著中國現代小說的誕生。也正是從這一層面上講,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成熟。那么,他的作品為什么能夠產生深刻的效果和感人的力量呢?就在于作者在作品中超越了一般的現實形態,體現出高度的象征結構形態,把人物的性格及其社會關系提高到一個哲學的高度加以表現。筆者謹以《藥》淺析一下魯迅小說結構方面的獨到之處。
一、看與被看的二元關系
看與被看的結構模式是魯迅小說的兩大模式之一。這種關系體現在先驅者與群眾之間,啟蒙者與被啟蒙者、醫生與病人、犧牲者與受益者之間,在中國的現實中變成了看與被看的關系,這是魯迅充滿苦澀的發現。《藥》中人們爭先恐后的到刑場去看殺夏瑜“頸項卻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子,被無形手捏住了向上提著”。茶館中夏瑜成為茶客們的談資,先驅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實奮斗在民眾的眼中只是茶余飯后的笑料,甚至覺得他“瘋了”。在這里小說構成民眾看夏瑜,夏瑜被看的二元關系。但在這一關系中小說沒有去深入體察人物的性感和命運,而是從不同的人生世相之中提起共同的一面-----病態。魯迅大華夏兩家的悲劇置于這種加以展示,我們不難發現,病態是雙重的,批判也是雙重性的,既有麻木吃人的群眾,也有悲哀的啟蒙者、革命先驅,小說采用這一結構形態,釀成作品內容的豐富性,作品的含蓄性得到了極大地提高,以此同時,還帶來了作品題旨的多義性。
二、結構的雙線性與象征性
眾所周知《藥》有一明一暗兩條線索,明線是華老栓一家,暗線是夏瑜一家。明線:華老栓買藥----華小栓吃藥----茶客們談藥---華大媽上墳。暗線:夏瑜就義---夏瑜的血被吃----茶客們談夏瑜----夏四奶上墳。
針對明暗兩條線索的作用頗存爭議,但筆者贊同沒有主次之分這一說法:首先,從小說人物姓氏的取名,華夏即華夏民族,再現的華夏兩家的悲劇,這就意味著悲劇不是個體的,而是整個民族性的。再結合作品內容來看,夏瑜的血浸入饅頭被華小栓吃進肚子;夏母羞愧的神情。群眾是無知、麻木的,革命先驅是悲哀的,二者不存在絕對的因果關系,站在現實歷史角度,這不存在誰是誰非,傳達給我們的只是一個時代的處境的普遍意義,是中國國民的一種普遍生存狀態。既然悲劇是民族性的,再現的是整個國民的生存狀態,那么作者“引起療救注意”的就不主要是民眾,同時也有啟蒙者、先驅們。也不存在主要批判誰的問題,二者都是療治批判的對象。因此兩條線索的平等性更加彰顯了小說內涵的深度和廣度,蘊含著濃郁的象征性-----民族悲劇的整體性。
再次,“藥”作為兩線的交接物,已非實物意義上的藥了,而是作為一種象征性的線索貫穿于小說之中,即革命者鮮血浸漬的饅頭不是療治小栓之病的良藥;夏瑜所從事的革命也不是救治中國社會的良藥。所以“藥”不僅作為小說情節進步的有機內容,而且作為作品氣質與力量的象征而貫穿在作品中,圍繞“藥”小說升騰起一種總性的寓意,作者的情思(悲憫、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同時得到了升華。
三、結構的不和諧性
小說的結構范文6
關鍵詞: 小說《大淖記事》 文體學 詩話小說 散文化小說
汪曾祺是一個文體意識非常強的作家,也是一個文體上有著獨特風格的作家。曾有法國記者就他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提問,汪答曰:“我大概算是一個文體家。”[1]P295筆者就試著從題材、結構、敘事方式、人物、語言等方面對這部被視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進行文本細讀。
一、題材方面的特點
《大淖記事》這篇小說基本上符合汪曾祺小說題材方面“回憶即小說”的特點。汪曾祺說:“我寫舊題材,只是因為我對舊社會的生活比較熟悉,對我舊時鄰里有較真切的了解和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寫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為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復沉淀,除盡火氣,特別是除盡感傷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說。”[2]P189
《大淖記事》在《大家小集——汪曾祺集》中被收入“故鄉雜記”,就是說作家是以一種回憶的姿態寫的發生在故鄉背景里的故事。這個題材的特點決定了這篇小說的整體氛圍、整體情調。回憶型的小說一般來說都帶有懷舊色彩,人物也置身于一種比較遠距離的時空里,這些都增添了小說的詩化色彩。
二、結構方面的特點
《大淖記事》結構方面的特點可以用“近似隨筆”來概括。汪曾祺主張小說貼著生活來寫,生活的樣式就是小說的樣式。為此,他主張打破傳統小說的情節觀念,實現小說結構的散文化。他認為,散文化是現代小說結構的必然趨勢。汪曾祺曾以“水”來喻示文化小說的結構,“水”是舒緩有致、宛轉自如的,與生活現實相適應。汪曾祺對小說結構的這種認識深受古記體小說的影響,像他所崇尚的《閱微草堂筆記》、《世說新語》、《聊齋志異》等作品,都是“筆記”或類似“筆記”的小品。
《大淖記事》不似傳統小說有鮮明的開端、發展、、結局,而是很少有懸念的設置,敘述節奏也永遠是那么的不緊不慢,舒緩有致。在巧云被,十一子被號長帶的一群人打得半死不活的時候,小說也沒有出現讀者預想中的。文章的節奏仍舊是那樣的從容不迫,特別是巧云和十一子之間的一段對話,讓人有無語之感。對話是這樣的:
十一子能進一點飲食,能說話了。巧云問他:
“他們打你,你只要說不再進我家的門,就不打你了,你就不會吃這樣大的苦了。你為什么不說?”
“你要我說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歡你!你快點好。”
“你親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親你!”
我們為男女主人公提心吊膽、擔驚受怕的時候,他倆卻在你儂我愛、卿卿我我,讓人忍俊不禁,卻也只能舒心地一笑,有一種“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挫敗感。其實,這是小說獨特的散文化的結構產生的奇特效果。
三、敘事方式方面的特點
(一)從環境中推出故事,鋪張背景描寫。
《大淖記事》的開頭不露聲色地、執著地臨摹民俗地圖,故意躲開人物的敘述,讀起來令人驚奇。小說前三節,寫的是大淖風情、錫匠行當、挑夫生涯,都是寫風土人情,宛如一幅幅精彩細致的民俗畫,直到第四節,人物才姍姍出場。這種從環境中推出故事、鋪張背景描寫的手法增添了小說的意境美,同時也增添了小說的文化意味。因而,小說的詩化美得以體現。
(二)意象敘事。
“意象敘事”是與意象抒情密切相關的一種敘事方式,是強化詩化氛圍的重要手段。它依靠不斷出現的意象來結構,并推動敘事作品情節的發展或情感的演變。意象承載著豐富的情思內涵并拓展出廣闊的審美空間,使敘事和抒情融為一體。例如小說中出現的“雞鴨炕房”、“鮮活行”、“魚行”、“茅草”、“蘆荻”、“挑夫”、“荸薺”、“菱角”、“連枝藕”等獨特意象就構成了一幅獨特的民間風俗圖,同時也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
四、人物方面的特點
在汪曾祺看來,散文化小說不是直接寫人,而是寫氣氛,借氣氛來寫人。傳統的小說以人物塑造為中心,緊緊圍繞著人物來組織情節,布局謀篇,而汪曾祺則突破了這種觀念,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現代小說的人物描寫。他的“氣氛即人物”的人物描寫理論是緊承其散文化的小說主張而來的。
散文化小說從根本上講是一種“情緒化”小說,這種小說不編織故事,不注重情節的發展,而著意于營造一種意境,抒發一種情緒,營造一種氣氛。散文化小說也寫人,但不直接寫人,而是融人于氣氛之中,借氣氛來寫人。[3]
《大淖記事》多采用描述和表現性的語言,這樣的語言充滿了作者的主觀情感,其目的是在文本中營造出一種情調和意境。在小說中,巧云和十一子的性格都隱藏在一種深深的文化氛圍中,使讀者產生一種亦真亦幻、虛無縹緲的感覺。但是在那樣美的氛圍之中,我們還是感受到了巧云的美麗純真,十一子的勇敢真誠,以及他們之間至純至美的感情。
五、語言方面的特點
(一)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
中國古代文論歷來推崇“重含蓄”之理,受其影響,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具有暗示性,呈現出含蓄婉約之美。汪曾祺的小說都很短,語言也經濟。為了用經濟的語言表現豐富的內容,作者常常選用凝縮性句子,并利用詞際句際空白,讓簡短的語言形式承載復雜的語義內容。[4]
小說中描寫巧云和十一子半夜幽會在沙洲的那一段,就充滿暗示和模糊性。小說只這樣寫了一句:“他們在沙洲的茅草叢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這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的語言很像詩歌的語言,這如詩的語言使得小說充滿意境美,同時也增加了讀者的想象空間,使得小說的內容得以無限延伸和擴展。
(二)氣韻生動,兼具音樂性和繪畫美。
汪曾祺的《大淖記事》,無論從情感節奏還是語言節奏來看,其音樂性都很強。例如文中有這么一段:
一二十個姑娘媳婦,挑著一擔擔紫紅的荸薺、碧綠的菱角、雪白的連枝藕,走成一長串,風擺柳似的嚓嚓走過,好看得很。
這一段文字描寫,不僅讓我們聽到了扁擔的“嚓嚓”聲,而且我們似乎能看到姑娘媳婦們裊娜的身姿和綻放在她們臉上的明媚的笑容。她們和她們肩上的五顏六色的挑貨一起,構成了一幅和諧美妙的圖景。
小說中大量短句的運用,長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變換,形成了如詩詞般的節奏回旋,實現了文章的和諧美。同時,語句中暗合的韻腳,疊音、疊字的使用造就的韻律變化和協調,形成了內部節奏的和諧美。疊言形式本身具有音樂性,能給人以聲音的美感,同時具有描繪作用,可以增強語言的形象性。
(三)語言的文化性。
《大淖記事》的小說語言富含文化氣息,由此形成了小說獨特的文化風貌。小說中獨特意象的使用、獨特生活場景的展現、獨特的具有地域色彩的語言使小說的文化意蘊深厚。
這里所謂的文化,既有俗的一面又有雅的一面。小說描述十一子外貌神態的那一段就極具古典氣息:“因為他太聰明,長得又太好看了,他長得挺拔四稱,肩寬腰細,唇紅齒白,濃眉大眼,頭戴遮陽草帽,青鞋凈襪,合身衣服整齊合體。”[5]P40
這段文字描寫當然是極雅的,然而小說中俗的文字也是有的,例如姑娘媳婦們喊老光棍黃海龍“老騷胡子”的諢名就具有口語化的色彩,富含濃郁的生活氣息。這種雅俗共賞的文字大概就是汪曾祺的小說散發持久魅力,并被廣大讀者所喜愛的原因之一。
《大淖記事》作為汪曾祺詩化小說的代表作之一,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情緒,它把情節淡化,人物化虛,結構散化,卻并不意味著將這些要素化無,它與舊小說有所不同,卻又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小說特質。在1980年左右就能寫出具有如此獨特文體魅力的汪曾祺,的確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文體家”。
參考文獻:
[1]汪曾祺.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2]盧軍.汪曾祺小說創作論[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3]熊修雨.當代性寫作與汪曾祺的小說文體觀[J].新疆大學學報,2001.12,第29卷,(4).
[4]伏斐.靈動詩意和諧純美——汪曾祺小說語言魅力述略[J].作家雜志,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