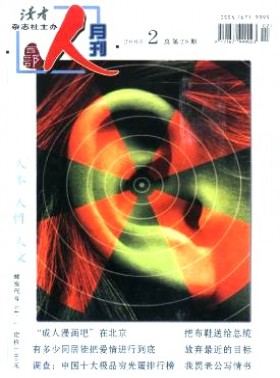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山水風光的詩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山水風光的詩范文1
2、宋-僧志南《絕句》:古木陰中系短篷,杖藜扶我過橋東。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3、唐-李白《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穎是銀河落九天。
4、唐-李白《望天門山》: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5、唐-張繼《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6、宋-蘇軾《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山水風光的詩范文2
【關鍵詞】唐代桂林山水詩審美自覺
“桂林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山水與文化緊密結合,自然旅游資源與人文旅游資源相得益彰。奇特的山水促進了文化名城的形成,悠久的文化又充實了山水的人文內涵。”「1這樣優厚的條件給桂林旅游以很高的起點,“今散見于史籍及市內諸山石刻的古詩詞多達5000多首。「2南朝齊永明年間(483——490)留在蘆笛巖內的墨書題名及隋朝開皇十年(590)名僧曇遷在七星巖洞口留下的摩巖石刻‘棲霞洞’榜書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從中原來桂林觀光的旅游事跡”。「3這說明了桂林景區的開發建設和旅游業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到興盛的發展過程。那么弄清桂林山水于何時進入世人自覺的審美視域是非常必要的。從歷代留存的山水詩歌分析,唐代是桂林山水旅游審美走向自覺化的發軔期。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從桂林山水詩的數量和質量來看,一直到唐代的桂林山水詩才能充分表明桂林山水旅游審美的自覺化。
最早涉及桂林山水的詩句是顏延之的“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邑間。”這句詩被認為是“獨秀峰之名有文字可考的開始”,“肇始了桂林山水詩風”。但這并布意味著桂林山水審美已經走向自覺。據《粵西詩載》「4收錄詩歌情況看,唐以前有關桂林山水的詩歌不足十首,其中能在嚴格意義視為山水詩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顏氏的詩句在當時只不過是孤篇絕響,而且還是殘篇孤句。因而不具普遍性,不能表明當時整個桂林山水審美主體群的審美自覺。當時桂林的奇山秀水仍是待字閨中的少女“藏在閨中人未識”。這種情況直到唐代之后才有改變。據不完全統計,唐代涉及桂林山水的詩歌有近百首,其中半數以上的作品是山水詩,且佳作數量不少。因而我們不能無視唐以前桂林山水詩在數量、質量上與唐代桂林山水詩存在的差距,更不能通過夸大顏氏詩句的地位和意義來說明當時桂林山水旅游審美已走向自覺。事實表明唐代才是詩人們對桂林山水旅游的審美自覺化的發軔期。
二,從唐代桂林山水詩的景點描寫及開發的行動,充分表明唐代是桂林山水審美自覺化的發軔期。
雖然“早在南朝時期顏延于宋景平二年(424年)在任始安郡太守的時候就對獨秀峰進行了開發”「5,但他的開發僅限于獨秀峰,景點范圍明顯不廣,也沒有帶動當時其他人進行開發,因而并未形成規模,因而,未能表明桂林的旅游審美走向自覺。這種情況到了唐代則有了明顯改觀。李渤的《留別隱山》、《留別南溪》,元晦的《除浙東留題越亭》,曹鄴的《東洲》,李商隱的《桂林》等詩歌都表達了詩人對桂林山水的欣賞、留戀甚至歸隱的情感。李渤的《南溪詩(并序)》還敘述了詩人于寶歷二年(公元826年)開發南溪山,使這個千百年來不載于前籍的山巖變成了旅游勝地。隱山原名盤龍崗,藏于茫茫西湖(唐代桂林的西湖很大,隱山完全被西湖水包圍,像座孤島一樣,與現在西湖的情況有所不同。此材料可參閱唐代吳武陵的《新開隱山記》和唐代韋宗卿的《隱山六洞記》),桂管觀察使李渤于唐敬宗寶歷二年親手開發使之得以聞名。在唐代像李渤這樣對桂林山水著手開發的事例并不鮮見。例如,元晦對疊彩山的開發始于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完工于會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辟山、修路、建亭,歷時一年零兩個月。次年元晦又開寶積山華景洞,建巖光亭,留下了《巖光亭詩》。裴行立曾在訾洲建起樓臺亭榭,還請柳宗元為之屬文,(見柳宗元《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不僅如此,這些詩人們還以極大的熱情給這些景點命名,并留下了吟詠的詩句。南溪山及南溪山諸洞之名、隱山六洞之名、疊彩山之名的由來與這些詩人有密切關系。強烈的喜愛之情是促使這些詩人有如此舉動的主要原因,而這些強烈的喜好之情是與詩人的審美自覺分不開的。
三、,從唐代桂林山水詩中景點描寫涉及的范圍看,也能充分表明這種審美自覺。
唐代桂林山水詩所描寫的景點主要集中在三大區域:桂林城區、漓江流域、陽朔城區。首先,關于描寫桂林城區景點的詩作。宋之問《桂州黃潭舜祠》所詠的黃潭又叫皇澤灣,位于虞山附近,舜祠則在虞山腳下,這些景點就是現在虞山公園的一部分。元晦《越亭二十韻》、《除浙東留題越亭》及《題越亭》所詠的越亭在疊彩山上。李渤《南溪詩》及《留別南溪》和其兄李涉的《南溪元巖銘序》則描寫了南溪山的獨特魅力。從盧順之與張固相互贈答的《七星山東觀席上贈張侍郎》和《東觀席上和盧從事》以及張固的《游東觀》可以看出當時的七星山(現在的七星公園的主體部分)已經成為詩人們呼朋引伴外出游賞的好去處。唐代陸宏休與歐陽實都有同名的《訾家洲》對訾家洲進行了描繪。李渤《留別隱山》所詠的隱山位于今西山公園。張固的《獨秀山》描寫的獨秀峰位于王城。這些詩歌所詠的景點都是桂林旅游景點中的精華。即使在“大力發展大桂林旅游圈”的大潮之下,這些景點的獨特地位仍不可替代。其次,漓江流域。張九齡的《巡按自漓水南行》、曹松的《桂江》、劉長卿的《入桂渚次沙牛石穴》、宋之問的《下桂江懸黎壁》和《下桂江龍目灘》等都是描寫漓江流域風光的詩作。雖然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些詩作描寫的主要區域是由靈渠至桂林這一段,并不集中在從桂林到陽朔的83公里水程范圍之內,與現在漓江旅游的游程有差異,因而沒有涉及重點刻畫出像九馬畫山、黃瀑倒影、半邊奇渡之類的著名景點,但是這些詩卻已經基本刻畫出了漓江流域風景秀麗的特點。再次,描寫陽朔風光的詩主要有沈彬的《碧蓮峰》,曹鄴的《東郎山》、《西郎山》、《東洲》、《廣福巖》。這些詩中描寫的景點同樣也基本被后人繼承發展為現在陽朔景點中的精華。
從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唐代桂林山水詩中描寫的景點不僅都被繼承為現在桂林旅游中的精華,而且在區域范圍上也與今天桂林旅游景點的分布區域基本相似。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并非基于巧合。“揮毫當得江山助”,如果說秀美的審美客體——桂林山水是客觀原因,那么唐代詩人對桂林山水的審美的自覺則是主觀原因。唐代詩人在這種審美自覺的催使之下有意識地欣賞吟詠桂林山水并開發景點,桂林山水之美才從“藏在深閨人不識”的狀態,走進世人的審美視野,缺少這種審美自覺,唐代桂林山水詩描寫的景點只能是零星的,不會成格局。所以從唐代桂林山水詩景點描寫的分布區域來看,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唐代是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發軔期。
四、從那些詩人自己未到過桂林,但因送友人到桂林而創作的涉及桂林山水的詩來看,唐代桂林山水審美已經走向自覺。
雖然這些詩旨在送別贈答,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山水詩,但也能從某些側面反映唐人眼中的桂林山水。例如鄭谷的《送曹鄴吏部歸桂林》全詩長達四十余言,只有一句“觸目成幽興,全家是勝游”涉及桂林山水,但足以表明作者對桂林山水的審美是自覺的。因為這種自覺是使“觸目”能產生“幽興”的前提條件,否則不可能“全家是勝游”。鄭谷是中原人,一生未到過桂林,他怎知桂林風光是“觸目成幽興,全家是勝游”。一定是有人特意給他介紹過,這一介紹的過程就是審美自覺的充分表現。無獨有偶,韓愈的詩句“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送桂州嚴大夫》)也屬此例。詩人同樣一生未到桂林,但兩句詩卻非常形象地概括出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6的特點,成為評價桂林山水的著名詩句。白居易《送嚴大夫至桂州》也寫到“山水衙門外,旌旗艛艓中。”這句詩形象地概括桂林的另一個特點——秀美的山水風光在城市之中,“皆出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遍至”,并非“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幾杖間可得”。「7除此之外,趙嘏的“遙聞桂水繞城域,城上江山滿書畫”(《寄桂府楊中丞》),許渾的“桂州南去與誰同,處處山連水自通”(《送杜秀才往桂林》),張籍的“旌旗過湘潭,幽奇得遍探”(《送嚴大夫之桂州》),都能在未到桂林的情況下以精辟的詩句描繪桂林山水之美,這表明當時桂林的山水妙勝已聞名遐邇,而人們對桂林山水的審美自覺正是使之聲名遠播的重要原因。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唐代桂林山水詩體現了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發軔。
“遍觀中國人文山水名勝的形成過程,大量的山水景觀被文人發現和欣賞是在唐宋時期。”「8桂林也不例外,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由桂林獨特歷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中國山水審美的自覺到魏晉才才開始涌動,而代表當時山水審美自覺的詩人群主要集中江浙一帶。并且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大分裂大動蕩時期,這樣的環境不利于審美自覺的傳播。其次,桂林地處嶺南,層層阻隔不利于這種自覺的傳播。再次,自南越政權趙佗首創“以夷制夷”政策之后,這種政策或多或少都被歷代統治者沿用。他們利用當地土司及一些少數民族文化來管理夷人,派駐的中原地方官并不多,故而文化啟蒙程度不高。到了唐代之后,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條件已經具備了。經濟上,經過歷代的開發,桂林及周邊地區農業、手工業都有了長足發展。唐憲宗時(806年)著名詩人白居易就用桂管布做棉衣,并題詩贊之“桂布白如雪,吳棉軟如云,布重棉且厚,為裘有余溫”。文宗時左拾遺夏侯孜穿桂管布,皇帝也跟著穿,于是滿朝恩武紛紛效仿,以致于桂管布因暢銷京城而價格暴漲「9。文化上,唐代派駐或貶往桂林的中原官吏數量大增,與中原文化的交流進一步加深。詩人的不幸變成了桂林的幸運。這些“中州偉人碩士,或遷謫之經從,或宦游之僑寓”「10,與桂林結下不解之緣。大歷十一年觀察使李昌巎在獨秀山下創建了桂林第一座府學,興起了文教之學。同時這些詩人大量的文學創作也給桂林的文學以極大促進。所以汪森在《粵西通載發凡》中指出“然茍非諸君子,則無以開辟其榛蕪,發泄其靈異。”經濟與文化上有如此之進步,加上遷謫詩人的山水審美啟蒙,桂林山水旅游審美終于開始走向自覺。新晨
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獨特意義在于表明了桂林這座城市第一次以旅游勝地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由于歷史、地理的原因,唐代以前的桂林城市的特征帶有濃重的政治、軍事、經濟色彩。桂林是嶺南與中原之間的交通要道,水路與陸路交匯,枕山帶水,地勢險要,便于進攻退守,被稱為“自孫吳以后,湖廣之間或生,未有不爭始安者……用兵譴將之樞機”(《讀史方輿記要》107卷顧方禹)這說明在統治者眼中桂林上是一座“地壓坤方重”(《送嚴大夫之桂州》白居易)的軍事重鎮。另外由于桂林“所處延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珍異瑋”(《〈隋書?地理志〉》)據《三國志?吳書》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記載,魏文帝曾“譴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鴨、長鳴雞……”。于此可見桂林的經濟意義。總之,當時的桂林(始安城)的城市特征帶有濃重的政治、軍事、經濟色彩,但旅游功能還未顯現,一直到唐代,桂林山水審美才開始走向自覺。這種山水審美自覺開發了桂林的山水之美,使桂林旅游勝地特征日益突顯,改變了“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逾臨源嶺,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就吏者,其加少也固宜”(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師序》)的情況。終于讓世人認識到桂林山水甲天下,人們開始自覺的來桂林旅游,至此也掀開了桂林旅游勝地的發展史。
參考資料:
[1]顏邦英.桂林市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清)汪森,桂苑書林編輯委員會校注.《粵西詩載》[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3](宋)范成大,齊治平校補.桂海虞蘅志[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
山水風光的詩范文3
例1:《我的伯父魯迅先生》
學了魯迅的侄女周曄寫的《我的伯父魯迅先生》課文后,為了讓學生對魯迅有深刻的認識,就可以用這篇教材作為一個點,引發開去,布置《我心目中的魯迅》作業,讓學生通過上網、請教別人,讀有關寫魯迅的和魯迅著的書籍,培養學生獲取信息、收集資料、處理文字的能力。幾天后,組織讀書交流會,讓學生大膽自由地闡述自己的看法及理由。這不僅使學生在心目中樹立一個鮮活的多維立體的魯迅形象,而且引導學生多渠道地學習語言。
±?:《氣象學家竺可楨》
學了《氣象學家竺可楨》后,讓學生小組合作,憑借課文為竺可楨舉辦一次事跡展覽。合作提綱可以這樣列:“展覽內容分幾部分?每部分的標題怎么定?該選擇哪些典型事例?怎么編排?展覽名叫什么?”這樣的作業,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和應用性,它源于課文,跟課文緊密相連又高于課文,能培養學生探究能力與語文實踐能力。
例3:《春》
學習朱自清的《春》之前,布置學生收集有關春天的諺語、古詩、文章、成語等,再帶領學生走出課堂去體驗春之美。學習課文時,讓學生背背有關春的詩句,看看在大自然中攝下的活動照、風光照。學了課文后,讓學生用自己喜愛的方式吟春頌春,“音樂能手”選擇唱歌,“語言能手”選擇配樂朗誦,“繪畫能手”選擇畫圖,“寫作能手”選擇作詩……學生在這樣開放的作業中,自主參與,不僅豐富了春的知識,又使學生個性得以展示,潛能得以開發。
例4:《桂林山水》
學習《桂林山水》,看了桂林風光錄像后,引導學生展開想象:“假如有一天,你真的蕩舟在漓江上,面對如此秀美的風光,你最想做些什么?假如你是一名畫家,假如你是一名歌手,假如你是一位攝影師,假如你是一位文學愛好者,假如……能把自己的感受表達出來嗎?”學生閉上眼睛很快地入情入境了。在學生交流的基礎上,教學韓愈贊美桂林山水的詩句——“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也水到渠成。然后,再引導學生課外搜集、閱讀、背誦有關歌頌祖國名山大川的篇章,進而培養學生的讀書習慣,增加學生對語文的吸收與積累。
例5:《筍芽兒》
學習“筍芽兒鉆出地面來了,她睜開眼睛一看,哎呀,地面上多么明亮,多么美麗!桃花笑紅了臉,柳枝搖著綠色的長辨子,小燕子嘰嘰喳喳地叫著……這一段時,先理解省略號的作用:表示列舉的省略。然后,請學生結合古詩80首,結合課文插圖,補充省略號內容:“筍芽兒還看到了怎樣美麗的景色?”這樣,能培養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例6:《落地的紅棗也不能吃》
學了《落地的紅棗也不能吃》,要求學生對故事中的文物說幾句話,可以對文中的小戰士說,也可以對說,或者對老鄉說。以此引導學生進一步領悟課文內涵,同時又能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
山水風光的詩范文4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的歷史源遠流長,名家輩出,名篇佳作卷帖浩繁,在中華文明中蔚為壯觀。
從小學到現在,我學過不少的古詩。古詩中的離別情緒,古詩中的春夏秋冬,古詩中的名勝古跡……讓我感到驚嘆。短短幾十個字,卻表達了詩人的思想感情,山水風光。李白的,《行路難》其中有一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只有短短十幾個字,卻表達了作者他即使仕途有所阻礙,卻依然對未來充滿堅定的理想。王安石的《登飛來峰》中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寫出了他登上高山之塔,極目遠望的豪情滿懷。
有人評價唐代王維的詩和畫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就像他的《竹里館》一樣,“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獨坐、彈琴、長嘯、明月,讓我想到了這么一個畫面。“一位詩人在竹林里獨自彈琴,長嘯。夜靜人寂,與明月相伴的一個畫面。那么的高雅、寧靜。
山水風光的詩范文5
長江三峽位于重慶市和湖北省境內的長江干流上,西起重慶奉節縣白帝城,東至湖北宜昌市南津關,全長193千米,沿途兩岸奇峰陡立、峭壁對峙,自西向東由瞿塘峽、巫峽、西陵峽組成。
長江三峽是中國十大名勝之一,世界最著名的大峽谷之一,重慶十大文化符號之一,“長江三峽---夔門”還是是第五套人民幣10元紙幣背面的風景圖案。
三峽地跨重慶、湖北兩省市。兩岸崇山峻嶺,懸崖絕壁,風光奇絕,兩岸陡峭連綿的山峰,一般高出江面700-800米左右。江面最狹處有100米左右;隨著規模巨大的三峽工程的興建,這里更成了世界知名的旅游熱線。
三峽旅游區景區眾多,其中最著名的豐都鬼城,忠縣石寶寨,云陽張飛廟,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宏偉的三峽工程,大寧河小三峽等。
游三峽有三條路線可選:1、從重慶順江而下快節奏地觀賞三峽的奇特風光;2、從上海、南京、武漢逆流而上游覽長江沿途美景;3、從三峽的東口宜昌出發飽覽神奇美麗的長江三峽風光。長江三峽,無限風光。瞿塘峽的雄偉,巫峽的秀麗,西陵峽的險峻,還有三段峽谷中的大寧河、香溪、神農溪的神奇與古樸,使這馳名世界的山水畫廊氣象萬千——這里的群峰,重巖疊嶂,峭壁對峙,煙籠霧鎖;這里的江水,洶涌奔騰,驚濤拍岸,百折不回;這里的奇石,嶙峋崢嶸,千姿百態,似人若物;這里的溶洞,奇形怪狀,空曠深邃,神秘莫測……三峽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無不如詩如畫,并伴隨著許多美麗的神話和動人的傳說,令人心馳神往。
山水風光的詩范文6
廬山山水文化的客觀性
大自然賦予了廬山奇異的風光及自然風貌,只有通過人的感知,通過人的認識才能產生美感,大自然是客觀存在的,而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留下許多文化的積累,也是客觀存在的。廬山山水文化的客觀性就體現在廬山的文化遺存和遺跡之中,其中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廬山的田園詩、山水詩、山水畫。它們所體現的精神美感和情結,就是廬山山水文化的載體。因為它們雖然是廬山自然美的體現,也是廬山山水的文化表現形式。它的客觀性體現在多種以山水、田園及山水畫的題材的藝術美當中,并且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它的客觀性離不開這些客觀形式。
據統計,留存于今的古代詩詞,以表現廬山題材的多達四千余首,其中包括各種形式的田園詩、山水詩,自晉代的陶淵明、謝靈運,唐代的李白、白居易、王維、杜甫,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坡、朱熹,明代的李夢陽、唐寅,清代的康有為等諸多名家,以及近現代政治名人和文化名人、郭沫若等都有不同題材的詩詞表現廬山。這些詩詞無疑是廬山山水詩和田園詩的載體,是千古文化的見證。
而山水畫的留存也不計其數,代表性的有東晉顧愷之的《雪霽望五老峰》、五代荊浩的《匡廬圖》、明代沈周的《廬山高圖》、明代唐寅的《三峽橋》、清代石濤的《廬山觀瀑圖》和清末張大千的《廬山圖》等。現代的畫家表現廬山的作品更是難以計數,著名的有傅抱石、劉海粟、吳湖帆、應野平、陸儼少、錢松巖、白雪石、黃秋園等眾多大家。
這些名家、名人、名詩、名作當中從多方位對廬山美進行了描述,表達了作者的豐富感情,從多角度體現出廬山山水文化的豐富性、精彩性和它們的影響力。很多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流傳很廣是廬山山水文化的保存形式,體現了廬山的自然美,藝術美。
當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表現廬山美的藝術形式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傳統的古典田園詩、山水詩被新的自由詩體,以及其他文學形式所代替,山水畫亦出現了代表時代特征的表現形式,其他的繪畫形式為油畫、水粉、水彩、版畫等多種形式,也有眾多的表現廬山風光和廬山情懷的作品。除此以外,廬山的風光攝影也是一種十分豐富而美感很強的藝術形式。近年來,出版的大量廬山風光題材的攝影作品,對于傳播廬山山水文化起的積極作用,成為當代廬山山水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這些攝影作品無疑也同廬山的詩歌、繪畫的形式一樣,代表了作者的思想情感,表現廬山的美感,應當說是新時代廬山山水文化的重要形式。
廬山山水文化的傳承精神
在中國美術史上出現過多種的傳承性,以山水畫為例。中國山水畫發展出現了多次的文化閃光點,成為沿襲和傳承中國山水文化的推動力,形成了多樣的藝術流派。如明代的“吳門畫派”,清代浙江的“婁東派”“虞山派”以及“新安派”,現代中國亦出現多種畫派,如“嶺南派”“海派”“黃土畫派”“京派”等。這些多種畫派在不同時期的出現,代表了當時社會文化的發展狀態,體現出中國山水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山水文化的傳承精神。就廬山范疇而論,未曾出現過何種畫派,但不等于廬山的山水文化不夠豐富和深厚;相反,廬山山水文化中的傳承中依然出現諸多“亮點”,成為廬山山水文化的一條鮮明的文化脈絡。眾多的古代、現代和當代名家,大家都鐘情于廬山,為廬山留下驚世之作,可以說是廬山山水文化的“鎮山”之寶,代表了廬山山水文化的傳承精神。這種精神體現了廬山山水文化的豐厚性、唯美性和抒情性。
廬山山水文化的豐厚性,體現在廬山文化的開放性上。歷代的文化在廬山都留下痕跡,如廬山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廬山不同時期,先后占據了不同地位。而殖民地時期的西方文化侵入又帶來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文化。同時,不同時期廬山的山水文化也有不同的表現,并遺留下深刻的時代文化痕跡,從而也體現出廬山山水文化的豐厚性。
廬山山水文化的唯美性,可以說是廬山山水文化的又一主要特征。廬山山水本身的秀美雄奇,為廬山的山水藝術鋪墊了唯美的特征,許多畫家是有感而作,他們被廬山的山水秀美所征服,被留存于世的經典詩句所折服。所以創作的作品具有很強的藝術性,具有較高的唯美特征。可以說他們的藝術美來自于自然美的感化,藝術的感染力來自于自然美的沖擊,反映出廬山山水文化中的情景交融、物我兩忘的美的境界。
廬山山水文化體現了抒情性。從古典的山水詩、田園詩中,廬山的山水畫受到極大影響。詩中的情懷,詩中的意境,往往用山水畫來表現更為直接、更為痛快。可以說山水畫和山水詩、田園詩是孿生的姊妹,它們彼此吸納互為傳播、互相影響,因為它們都是真情的流露,都是真切的感受所傾瀉。廬山的自然之美,不能不喚起詩人畫家的情懷,不能不叫詩人畫家所動心,所以“詩情畫意”是廬山山水文化的一個特征。
可以說,在廬山山水文化中,其豐厚性、唯美性和抒情性構成了廬山山水文化的“文脈”。
廬山山水文化的形成因素
研究廬山山水文化的客觀性、傳承性,對于我們了解廬山山水文化的形成因素和基礎有著重要意義。廬山的山水文化的客觀性體現在古今中外的有關廬山題材的山水文化作品的內涵之中,廬山山水文化的形成因素和基礎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廬山山水的自然之美是廬山山水文化的“本”,廬山自然山水具有區位優勢、氣候優勢、美學優勢。
由于廬山地處長江中下游,周圍是廣袤的平原及眾多湖泊,又北依長江,東臨鄱陽湖。這里經濟發達,文化深厚,歷史悠久,佛、道、儒三家文化較早傳播于此,形成了廬山交通方便、文化豐富的有利發展基礎。而廬山美麗的自然風光足以吸引人們,成為人的向往,在此繁衍生息的因素。宜人的氣候更是成為令人神往的動力。因此,廬山較早地吸引了中華歷代的眾多精英,他們鐘情廬山,紛紛登臨廬山,同時也為廬山留下許多的文化遺產,其中詩、書、畫成為傳承文化的最好方式。
(二)歷代名人名作中顯現出來的廬山山水“奇境”所表現的美學內涵,推動了廬山山水文化“內美”的發展。
如果說自然之美是廬山山水文化之本,那么廬山歷代名家名作所體現出來的藝術之美是廬山自然之美以外的另一“美學范疇”,可將其稱為廬山山水藝術文化的“內美”。這種美是對自然之外的一種“美”的體現,體現了作者的情懷和情感,是自然之美的補充,是藝術美的體現。這種“美”的表現形式,在廬山歷代文化中呈現出異彩紛呈的景象,如晉代的陶淵明,以田園詩表現對廬山的眷念,呈現出田園之美。“結廬在人境,而無東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而唐代大詩人李白,則以山水詩的情懷,表現廬山的雄奇壯麗:“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云松。”宋代大文豪坡則以豪放之情,將廬山的雄闊和神奇加以描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些詩歌無不充滿了作者的情感,又無不從中描繪出了一個廬山山水美妙幻境。通過這些美妙幻境,又將廬山披上了神奇亮麗的面紗,讓人從中體味出廬山山水的文化魅力。
詩人以詩描繪廬山,而畫家亦情有所依,從歷代名家表現廬山山水之作中,我們不僅可以體味到其中的詩情,而且可體驗到畫家心中的廬山之魂。五代荊浩的《匡廬圖》,將廬山山水表現得雄偉壯麗。山的雄闊、水的峻秀、云霧的迷茫、人家的靜寂,無不得以體現。明代的沈周以細致手法描繪的佳作《廬山高》,不僅描繪出廬山的雄險,而且將奇松怪石、泉流飛瀑蒼山峻峰,無不融入畫中,將廬山表現得高大雄險,飛瀑直下,讓人產生不盡遐思。清末張大千終生未曾登臨廬山,竟在八十高齡,奮筆創作了巨幅山水畫《廬山圖》,以其雄強渾樸、氣勢磅礴的畫境,表現出神奇無比的廬山圖景,了卻了他一生向往廬山的夙愿。當代名家傅抱石、張仃、黃秋園、陸儼少、錢松巖等也都采用不同的筆墨技法,打造心中的廬山形象,把一個廬山山水文化的“精魂”描繪得讓人魂牽夢繞。
由此可見,自然的廬山山水之美是廬山山水文化之“形”。而詩人畫家表現出來的廬山山水之美是廬山山水文化之“魂”。廬山山水文化的“形與魂”是自然之美和藝術之美的完美結合之產物。如果廬山僅有自然之美,而無藝術之美又怎么談得上廬山山水的文化!只有“形”和“魂”相結合的廬山,才可稱得上“名山”,才可體現廬山“山水文化”的魅力,才能體現文化的“精神”。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是指這座山具有內在精神和文化內涵。否則它只是一座普通的山而已。可見廬山作為一座名山,如果它沒有豐厚的文化底蘊,沒有多彩的文化背景,沒有山水文化的精神,它就決不可能成為一座名山。打造廬山的山水文化無非也是要挖掘廬山的千年遺存的山水文化精神,這也是廬山的山體之“魂”,是傳承廬山山水文化之美的“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