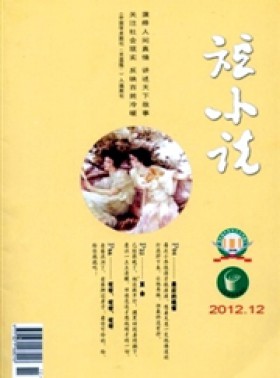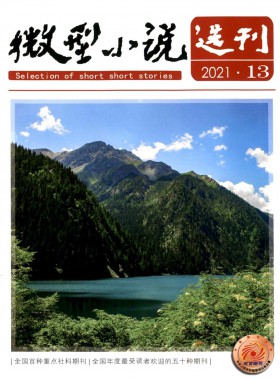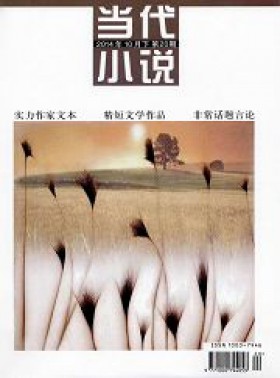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小說翻譯觀照下社會實踐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介紹
布迪厄社會學理論框架下的實踐活動不同于馬克思常用的實踐,是包括生產勞動、經濟交換、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動在內的人類實際活動,三個重要的概念與實踐活動緊密相連,分別是場域、資本和慣習。場域表示行動者從事實踐的空間,表示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網絡或構型。社會是由相對自主的場域組成,每個場域具備各自的運作邏輯。布迪厄強調場域內部的關系性和沖突性。場域之內的行動者處于各種動態關系之中,利用各自所掌握的資本依靠行動者的慣習在場域內進行斗爭。資本是行動者實踐活動的工具。資本需要在場域中體現價值,既是行動者爭斗的工具,同時又是爭斗的對象。當資本被個體或群體作為私有財產占有時,就表示資本占有者占用了社會資源。資本可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象征資本。經濟資本是最根本的資本形式,可以直接轉化為金錢;社會資本由各種社會關系組成,行動者可以憑借這種關系網將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以三種形式存在,即身體化形式、物體化形式和體制化形式。身體化資本是指行動者在實踐活動中內化的社會世界的實踐邏輯,以精神或肉體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包括行動者氣質、秉性、習慣等,根本上來說是行動者的文化價值觀念;物體化資本表現為各種文化產品,如圖書、工具、藝術品等;體制化資本是得到國家制度保障的文化資本,并不是以客觀有形的形式存在,而是超越了具體化形式,使特定行動者占有的資本得到制度上的認可。慣習可以了解為行動者實踐的邏輯,即行動者如何實踐。慣習產生于長期的實踐活動,經過一定時期的累積,實踐經驗內化為行動者的意識,進而引導行動者的行為,體現為行動者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策略等。慣習一方面會組構并影響行動者的社會實踐,是“具有結構能力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同時,也是行動者先前社會實踐的烙印,是“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對于場域、資本和慣習的關系,布迪厄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公式:[(慣習)(資本)]+場域=實踐。可以理解為行動者憑借慣習和掌握的資本,在某一場域中做斗爭,從而形成特定的社會實踐活動。這一公式投射到翻譯研究,則可闡釋為譯者依靠慣習和資本,在某一場域作斗爭,進而形成翻譯場域。
布迪厄提出了研究人文與藝術領域的三步驟:第一,對特定場域的研究應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的研究結合。這體現了社會等級與權力在布迪厄社會學框架中至高的地位。在人文藝術領域,文學場域鑲嵌在權力場域之中。第二,應該辨別個人或群體在爭奪知識或藝術的合法化中所占據的對抗性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結構。特定場域中的經濟和文化資本是什么?資本如何分配?場域中行動者的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如何?第三,要分析行動者的階級關系以及在斗爭場域中的地位和社會軌跡。這一研究方法同樣適用于小說翻譯實踐活動,在此觀照下,可按照以下步驟分析小說翻譯實踐活動。第一,對小說翻譯活動的研究要放在更大的權力場域—翻譯場域中,翻譯場域同時又置身于文化場域這一更大的權力場域中,所以,要考查特定歷史時期的小說翻譯活動,必須首先考查翻譯和文化活動中的權力斗爭。第二,研究譯者在爭奪資本過程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分析譯者所掌握的資本以及如何利用這些資本之間的轉化改變所處客觀關系結構。第三,分析譯者的慣習。當然,譯者的慣習不僅是個體的秉性和社會軌跡的表征,也體現了社會群體在個體譯者身上打下的烙印。
三、晚清小說翻譯活動的社會學解讀
1.場域斗爭分析。
晚清的小說翻譯活動要放置在翻譯場域和文化場域中進行考查。文中所指的晚清翻譯場域時間段為1894年甲午戰爭起至1916年,這是中國近代翻譯場域的時間段。甲午戰爭后翻譯的方式、數量等與之前大不相同,而1917年開始的文學革命開始了中國小說的現代化。在這一過渡轉型階段,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包括翻譯活動在內的各種社會實踐都體現了極其復雜的矛盾與斗爭。在文化和翻譯場域中,如果從宏觀向微觀挪移,主要存在以下斗爭:華夏文明與外夷文明、小說與其他文類、翻譯與創作。中國自古就存在華夷之辨,中華文明與外夷文明之間斗爭隨著甲午戰敗而愈演愈烈。甲午之前,西方的堅船利炮攻破了清政府的閉關鎖國,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是作為向西方學習的官方代表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中國文明的居高地位。把西人比作蠻夷,自然西方文明在國內仍受貶斥。而甲午戰敗的恥辱,使國內士大夫階層認識到,受西方文明影響的日本真正讓國人感到民族危機和亡國之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國人的夜郎自大,不得不接受一個新的世界觀,自古被認為的西夷蠻邦,其文明程度不亞于中華。在中外文明到底孰優孰劣的斗爭中,部分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不斷提升地位的西方文明,他們聲稱,西方世界取得的巨大文明,小說功不可沒。嚴復和夏曾佑在1897年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中闡明了小說價值所在:“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翻譯西洋小說隨之成為學習西方文明見效最快的辦法。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相對于其他文類,小說處于社會邊緣的地位,是“小道”,魯訊感嘆過“在中國,小說向來不算文學家的”。班固在《漢書•文志志》里把諸子之書歸納為九流十家,小說不入九流,十家之中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小說雖列十家之中,然“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由此得出,小說不僅不入九流,而且被排斥在十家之外,僅為“道聽途說,街談巷語”。而在晚晴的翻譯場域中,卻產生了小說界革命。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識語》(1897)中借上海點石者之口,指出“書”“經”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說,因為小說可以啟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輸,當以小說輸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清末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中,小說形式占絕大多數,翻譯過來的散文僅有4篇,詩歌也屈指可數,而小說卻有1000多種。士人通過論證小說在歐美國家的開化民智功能證明翻譯小說的合理性。在小說地位被抬高到“文學之上乘”之時,按理說,小說的創作應該也是如火如荼的。但是翻譯小說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創作小說的數量,1906-1908年為晚清小說翻譯的高峰期,這三年分別有105、135、94種小說翻譯,大致等于創作小說的兩倍。翻譯小說的廣泛接受性也可以從假借譯本之名而創作小說的現象中體現。從事小說翻譯的文人及出版翻譯小說的雜志更是數不勝數。造成這一現象主要是因為小說創作需要費時費力,而小說翻譯卻相對高效,同時想要實現向西人學習、改良群治的宣傳效果,非翻譯小說莫屬。
2.譯者資本占有及其爭奪。
權力斗爭是場域最鮮明的特點,而行動者賴以斗爭的基礎就是所占有的資本,通過對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及象征資本的占有、爭奪及轉化,行動者掌握更多的社會權力,從而構建并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在小說翻譯場域,不同的譯者占據不同的資本,為了使小說翻譯的社會學解讀更加具體化,文章將選取晚晴典型的小說譯者林紓為例,對其所占有的文化資本及其利用轉化情況做以分析。文化資本包括人際交往技巧、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水平、品味與生活方式。大致可以概括為文化能力、文化產品和文化體制。文化能力表現為行動者的身體或精神方面的持久性請,是后天習得的。文化產品包括圖書、雕塑、繪畫等客觀存在的形式化實體,一旦被制造出來,就可以被更多的潛在主體占有;文化產品的有效性體現在作為投資形式參與文化生產斗爭。文化體制以制度化形式存在,為行動者所掌握的文化資本合法化提供制度性保障。具體到作為小說譯者的林紓,他所掌握的文化資本主要是其語言能力。語言能力并不是指林紓的外語表達能力,相反,林紓不懂外文。所以,這種語言能力是指林紓的古文修養。林紓的古文修養受到桐城派主將吳汝綸的賞識,稱道其古文“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林紓在古文詞方面確實頗有造詣,他于光緒八年(1882年)中舉。周作人論其翻譯時可以“筆墨腴潤輕圓”,魯迅也評論其“文章確實很好”,樹玨認為林紓的譯筆能夠做到“高尚淡遠”。林紓本人更是強調了古文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認為是中華文化的根基,“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辭盡奪其故,是并文字而亡矣。”基于對這種文化資本的占有與強化,可以得知林紓旨在維護自身的傳統文化身份,其小說翻譯目的并不是文學性的,而是社會性的。他的小說翻譯也為其帶來了大量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實現了文化資本向其他資本形式的轉化。林紓的稿酬相對其他譯者較為優厚,以每千字六圓計算,而包天笑譯《三千里尋親記》和《鐵世界》,每千字兩圓,共得稿酬一百圓,“除了到上海的旅費以外,還可以供幾個月的家用”。同時,林紓譯稿的備受好評,也為其帶來大量的社會和象征資本。林紓的翻譯思想、翻譯原則、對古文的推動作用以及所取得的“今世小說屆之泰斗”的社會地位,可以說都根源于他的古文造詣。
3.譯者慣習分析。
慣習是一種穩定的性情傾向體系,譯者的慣習是譯者在翻譯及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思維傾向,受到特定的歷史環境的影響,是社會實踐在譯者意識結構中的內化,同時又指揮和調整譯者的翻譯實踐,比如翻譯選題、翻譯策略等。文章仍以林紓為例,分析其慣習及其影響。林紓的古文翻譯慣習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在長期的知識活動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林紓自稱崇尚程朱理學,以“讀書則生,不則入棺”為自勵,自幼養成了用古文寫作的習慣,古文已經成了林紓的思維模式,雖然一生翻譯180余種作品,但毫不受到外文的影響。古文的思維模式決定了在翻譯中的詞章句法,框架結構均遵循古文義法。傳統的語言文字不僅影響了譯作的措辭章法及其結構輪廓,更影響了譯者對文學作品的態度。“文以載道”是自古以來士人的文學觀和社會觀,林紓在翻譯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傾向同樣體現了這一點。比如,翻譯文本的選擇格外體現了林紓的文學社會觀。他每譯一書,都要鄭重其事,作序,跋尾,再三表明他希望人們學習西方、救國保種的良苦用心。翻譯《黑奴吁天錄》,正是反美華工禁約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小說中美國黑奴的悲慘遭遇很容易使國人產生唇亡齒寒之心,激發國人救國保種之志。譯者慣是與譯者所擁有并爭奪的資本千絲萬縷地聯系在一起。林紓的這種翻譯慣習給他帶來的成功是他始料未及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一經出版,則“書出而眾嘩悅”“一時洛陽紙貴”“不脛走萬本”。可見特定的翻譯慣習會帶來的出乎意料的社會和符號資本,這也從側面擴大了小說的社會改良和開啟民智的作用,帶來了了晚晴小說翻譯的高潮。
四、結語
文章以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為框架,分析了晚晴小說翻譯的場域斗爭、資本占有及爭奪和譯者慣習,再次證明了以社會學為基礎的翻譯研究,不僅能從宏觀社會歷史背景的角度考查翻譯活動的盛行,而且能從微觀的譯者特性層面解釋譯本的傳播情況。在翻譯場域進行的各種斗爭、協商、妥協或勝出,充分體現了翻譯從來就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僅僅地描寫翻譯現象是不夠的,對各類翻譯現象的社會性解釋研究才能真正推動翻譯研究領域的發展。
作者:鄒素 單位:許昌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