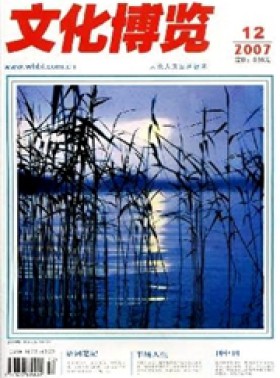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文化語境下的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運(yùn)用主題學(xué)研究理論,從主題、母題視角探究民間藝術(shù),是當(dāng)代文化語境下民間藝術(shù)研究的新視域。民間藝術(shù)與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有密切聯(lián)系,是這三種藝術(shù)的基礎(chǔ),具有母型性質(zhì)。民間藝術(shù)也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是母體文化,具有典型的文化礦藏性質(zhì)。從多維度思考,以主題學(xué)視角探討民間藝術(shù),研究傳統(tǒng)民間藝術(shù)發(fā)展演變的文化路徑和真實(shí)脈絡(luò),是更立體地看待民間藝術(shù)的有效途徑。在當(dāng)代文化語境下,研究民間藝術(shù)相關(guān)主題、母題,不僅能豐富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而且更有利于深層了解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真正做到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
關(guān)鍵詞: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文化語境;藝術(shù)史主題學(xué)
研究方法在現(xiàn)代比較文學(xué)領(lǐng)域運(yùn)用較多,通常用于分析文學(xué)主題的發(fā)展脈絡(luò),以及主題發(fā)展變化中母題的演變路徑、主題和母題的深層次關(guān)系。目前,主題學(xué)在藝術(shù)理論上運(yùn)用較少,民間藝術(shù)領(lǐng)域更容易被忽視。在比較藝術(shù)學(xué)中,主題學(xué)是對藝術(shù)主題的相關(guān)流變進(jìn)行研究。具體到民間藝術(shù)領(lǐng)域,主要研究某個民間藝術(shù)主題在不同的時間(歷史)和空間(地域)所呈現(xiàn)的不同藝術(shù)形態(tài)與相應(yīng)的主題流變,及其母題與主題演變的相關(guān)理論問題。當(dāng)代文化語境下,研究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值和社會意義,不僅可以梳理歷史上主要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流變脈絡(luò),分析相關(guān)主題和母題發(fā)展的相互影響,豐富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而且可深層探究蘊(yùn)藏在民間藝術(shù)中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增強(qiáng)民族文化自信,引領(lǐng)新時代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
一、民間藝術(shù)的基礎(chǔ)文化層次
大多數(shù)藝術(shù)史論家重視藝術(shù)史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但長期以來民間藝術(shù)易受輕視,未納入古代、近現(xiàn)代藝術(shù)史編撰視野。從學(xué)科建設(shè)看,2013年藝術(shù)學(xué)升格為第十三大學(xué)科門類,藝術(shù)史也被列為一級學(xué)科藝術(shù)學(xué)理論下的二級學(xué)科。目前已有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藝術(shù)史中的民間藝術(shù)研究,如長北的《中國藝術(shù)史綱》、李倍雷的《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理論與方法研究》等,為民間藝術(shù)領(lǐng)域注入一股清新的學(xué)術(shù)暖流。“民藝”概念最早由日本學(xué)者柳宗悅提出:“‘民藝’一詞……誰都能理解民藝的‘民’就是‘民眾’的‘民’和‘平民’的‘民’。”[1]柳宗悅將民眾、平民所使用的藝術(shù)鎖定為民藝的基本范圍,所謂“民藝”實(shí)質(zhì)上就是民間的造型藝術(shù),即民間工藝美術(shù)。目前中國學(xué)術(shù)界的“民藝”研究范疇,比柳宗悅的“民藝”概念寬泛得多,不僅包括大量具有實(shí)用功能的民間工藝,還囊括代表人民群眾審美情趣的若干民間藝術(shù),如大眾熟知的年畫、剪紙等。當(dāng)然,民間藝術(shù)和民風(fēng)民俗的發(fā)展是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的,容易被混淆。民俗藝術(shù)主要指特定區(qū)域內(nèi)與民風(fēng)民俗相關(guān)的藝術(shù),而民間藝術(shù)的范疇更大,通常包括民俗藝術(shù)在內(nèi)。雖然國內(nèi)學(xué)界研究民間藝術(shù)已有近百年歷史,但“民間藝術(shù)”一詞作為學(xué)科出現(xiàn),最初是由藝術(shù)學(xué)家張道一先生于1988年提出:“‘藝術(shù)’冠以‘民間’加以限定,不是作為藝術(shù)的一個門類,而是標(biāo)志著一個層次,一個最基礎(chǔ)的層次。”[2]他深入探討了人類歷史上民間藝術(shù)的發(fā)生發(fā)展,認(rèn)為民間藝術(shù)不單是藝術(shù)發(fā)展的重要分支,更是藝術(shù)的一個最基礎(chǔ)的層次,是一種具有母型性質(zhì)的本元文化。這一理論觀點(diǎn)在藝術(shù)史論領(lǐng)域影響重大,逐漸被學(xué)界認(rèn)同。一般將中國古代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發(fā)生發(fā)展分為四個分支: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和民間藝術(shù)。其中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民間藝術(shù)具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四種藝術(shù)都是在原始藝術(shù)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前三種藝術(shù)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從民間藝術(shù)中汲取營養(yǎng),為其所用。不管是題材內(nèi)容,還是藝術(shù)風(fēng)格,民間藝術(shù)都是其他三種藝術(shù)取材的源頭,如民間的頂棚剪紙樣式,就被吸納進(jìn)皇家家居的設(shè)計(jì)和制作中。民間藝術(shù)是一種母型藝術(shù),是其他藝術(shù)的母體,具有典型的礦藏性質(zhì)。民間藝術(shù)大多是實(shí)用的民間工藝,作者都是民間匠人。由于不像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那樣高雅且有品位,民間藝術(shù)往往被社會輕視,民間工匠也多被人鄙夷,歷史上鮮有留名。在學(xué)術(shù)理論層面,民間藝術(shù)的關(guān)注度也遠(yuǎn)不如文人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張道一先生指出:“由于民間文化帶有原發(fā)性,面大量廣,一直成為其他文化攝取滋養(yǎng)的基地,因而帶有‘母型’文化的性質(zhì)。”[3]也就是說,民間藝術(shù)是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化不單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內(nèi)容,更是民族文化的基礎(chǔ)層次。民間藝術(shù)是其他藝術(shù)形態(tài)發(fā)展取之不盡的礦藏,民間文化是其他文化形態(tài)發(fā)展的滋養(yǎng)之地,具有典型的“母型”性質(zhì)。民間藝術(shù)和文人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這四種藝術(shù)形態(tài)形成四個大的文化圈,可以作為研究中國藝術(shù)史的大框架,這四種藝術(shù)形態(tài)即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主要-60-結(jié)構(gòu)線。應(yīng)當(dāng)在這四條藝術(shù)史主要結(jié)構(gòu)線的研究基礎(chǔ)上,深入開展相關(guān)的藝術(shù)理論研究,從而構(gòu)成藝術(shù)學(xué)理論學(xué)科“史”與“論”的基本研究路徑。民間藝術(shù)的價值不僅不能忽略,反而應(yīng)更加重視,備受全社會關(guān)注。民間藝術(shù)是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和理論體系最基礎(chǔ)的文化圈,但中國自古以來奉行“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很明顯的重道輕器觀念,民間工藝占民間藝術(shù)相當(dāng)大的數(shù)量,自然被視為“器”之列。雖然文人藝術(shù)的若干素材及表現(xiàn)形式來源于民間藝術(shù),而這種特殊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往往不為文人所認(rèn)可。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從專業(yè)和業(yè)余角度分為“隸家”和“行家”,文人不愿與民間匠人為伍。在古代,文人藝術(shù)家也常與民間藝人一起完成藝術(shù)作品。如明清時期的小說版畫,文人繪制版畫圖稿后,交由民間工匠刻版完成,并印刷成品。也就是說,文人藝術(shù)家只完成前期的繪圖,后續(xù)的刻印等一系列工作都由民間工匠承擔(dān)。古代宮廷藝術(shù)大多也由民間藝人完成,只不過挑選其中技術(shù)最好的能工巧匠,按照宮廷材質(zhì)、工藝、創(chuàng)作題材等要求完成藝術(shù)作品,仍會不自覺地加入民間藝術(shù)的技巧和觀念。民間藝人無形中也影響著宮廷藝術(shù)的發(fā)展,比如宮廷陶瓷做得精美復(fù)雜,這些工作大都是由民間藝人完成的。宮廷藝術(shù)與民間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的觀念和審美并無絕對的高低之分,只是從制作方面來看,宮廷藝術(shù)相較其他兩種藝術(shù)更為煩瑣,工藝要求更高。宗教藝術(shù)中的眾多陵墓雕刻、石窟造像、寺廟彩塑、道觀壁畫等,也基本上出自底層工匠之手,他們同樣是按照宗教藝術(shù)的題材內(nèi)容及工藝程式進(jìn)行制作。可見,無論文人藝術(shù),還是宮廷藝術(shù)和宗教藝術(shù),其制作都離不開民間藝人,民間藝術(shù)對文人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在技術(shù)、觀念以及作品表現(xiàn)的主題內(nèi)容、表現(xiàn)形式、技藝手法等方面產(chǎn)生重要影響。在浩蕩的歷史長河中,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不容易被察覺,所以民間藝術(shù)易受忽視。追根溯源,民間藝術(shù)的“母型”性質(zhì)在影響文人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的發(fā)展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作為民族文化之根,民間藝術(shù)理應(yīng)形成良性發(fā)展趨勢。從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開始,便有了古代的“采風(fēng)”機(jī)制,其中的“國風(fēng)”即為民間歌謠。也就是說,《詩經(jīng)》最初的藝術(shù)材料源自民間藝術(shù)。西漢時成立的漢樂府,工作任務(wù)之一即是采集民間歌謠。民間藝術(shù)和文人的審美趣味相去甚遠(yuǎn),古代文人一般沒有將民間藝術(shù)納入他們所謂的“藝術(shù)”范圍之內(nèi)。但文人藝術(shù)受民間藝術(shù)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如唐代劉禹錫將原為民間藝術(shù)的巴渝竹枝詞,加工創(chuàng)作成具有民間風(fēng)味的文人詩,從三峽風(fēng)靡全國,甚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產(chǎn)生了西湖竹枝詞、嶺南竹枝詞、京都竹枝詞和海外竹枝詞等分支。至于中國文人畫的淵源,極有可能是隨著唐宋青花瓷的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顏色清新淡雅的青花瓷,與追求情趣意境的文人畫確實(shí)有著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內(nèi)在一致性。宗教藝術(shù)主要宣傳佛教、道教教義,表現(xiàn)儒家教化思想,一般采用民間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手法,這可能源于民間藝術(shù)是老百姓最熟悉、最能接受的藝術(shù)形態(tài)。宗教雕塑、繪畫、壁畫的制作者——民間工匠群體龐大,最易于尋找,民間又存在大規(guī)模的宗教信仰群體,某些帶有宗教信仰的官商、民眾也自發(fā)地進(jìn)行宗教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可見,民間藝術(shù)作為一種具有“母型”性質(zhì)的藝術(shù)形態(tài),對古代的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唐代張彥遠(yuǎn)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到:“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為也。”[4]卷一《論畫六法》此書在中國藝術(shù)史中享有重要地位,其藝術(shù)觀點(diǎn)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中足以看出民間工匠的低下地位,也不難理解中國古代藝術(shù)史上民間藝術(shù)的缺失。古代民間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者,大部分是普通群眾,以農(nóng)民為主,以及牧民、漁民等,還包括一些師承或家傳的民間作坊藝人。他們創(chuàng)作的年畫、剪紙、糖人、挑花、刺繡、紙馬、石刻、木雕等民間藝術(shù)作品,大多是出于自發(fā)性的,具有自娛性和業(yè)余性,或?yàn)槿粘?shí)用,或?yàn)檠b點(diǎn)環(huán)境,又或者愉悅身心,具有非功利性的特點(diǎn)。這些民間藝術(shù)作品和藝術(shù)活動,反映了人民大眾的精神信仰和審美需求,是民眾精神生活最真實(shí)的反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其他藝術(shù)形態(tài),具有本元性,是“母型”性質(zhì)的文化形態(tài)。在當(dāng)今傳承與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偉業(yè)中,無論是提升文化自信,還是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的重構(gòu)與建設(shè),民間藝術(shù)都不可或缺。
二、主題學(xué)視角的民間藝術(shù)
美國學(xué)者弗列特里契(W.P.Friedech)、馬龍(D.H.Malone)將文學(xué)的主題學(xué)研究方法歸納為:“打破時空的界限來處理共同的主題,或者,將類似的文學(xué)類型采納為表達(dá)規(guī)范。”[5]也就是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探究同一個主題。主題學(xué)最初運(yùn)用于比較文學(xué)領(lǐng)域的民俗學(xué)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可以應(yīng)用在藝術(shù)學(xué)理論學(xué)科中,比如研究藝術(shù)史的相關(guān)主題流變。民間藝術(shù)是藝術(shù)史的重要部分,當(dāng)然可以利用主題學(xué)方法研究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母題流變,打破時間和空間的界限,探討某個民間藝術(shù)主題,歸納總結(jié)出眾多民間藝術(shù)主題在不同時空(歷史和地域)中的發(fā)展路徑和流變原因。從主題學(xué)視角審視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將主題、母題介入民間藝術(shù)理論系統(tǒng),首先必須明了通過主題、母題的理論研究方法,能夠梳理民間藝術(shù)領(lǐng)域的主題流變問題,以及母題的發(fā)展變化會引起主題的演變,這樣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譜系形成一個由小及大的系統(tǒng),成為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的基礎(chǔ)部分。其次,主題學(xué)的研究視角能解決民間藝術(shù)領(lǐng)域的相關(guān)理論問題,怎么解決?這就涉及主題學(xué)介入民間藝術(shù)理論的具體方法問題。主題和母題角度的民間藝術(shù)理論研究,已有學(xué)者進(jìn)行篳路藍(lán)縷的探索。張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書中,對“麒麟”這一藝術(shù)母題的原型進(jìn)行追溯,探究歷史上“麒麟”圖像屢次出現(xiàn)的原因,考證母題“麒麟”為何向“麒麟送子”轉(zhuǎn)變。實(shí)際上,張道一先生對民間年畫藝術(shù)“麒麟”母題的發(fā)展引起主題變化的研究方法,與主題學(xué)理論不謀而合。他對民間藝術(shù)中的一個母題脈絡(luò)進(jìn)行分析,屬于藝術(shù)史學(xué)譜系若干分支的組成部分。從主題的角度著眼,若干主題譜系構(gòu)成一部藝術(shù)史,當(dāng)然有些主題是相對重要的,有些則相對次要,這樣就形成了較大的譜系和較小的譜系。藝術(shù)史可以看作一個宏大的藝術(shù)主題脈絡(luò),民間藝術(shù)則是其中一個藝術(shù)主題脈絡(luò)的分支。這個民間藝術(shù)主題脈絡(luò)又可分為眾多的次級藝術(shù)主題脈絡(luò),如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衣、食、住、行、用,便可以分別架構(gòu)各自的主題脈絡(luò)。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民間藝術(shù)有各自的藝術(shù)形態(tài),也存在相同的題材、母題、母題意象,有時表達(dá)的主題也趨于相同,或者是主題譜系在發(fā)展過程中存在交叉現(xiàn)象。當(dāng)然大部分情況下,文人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民間藝術(shù)中的人物、花鳥、山水這些相同的母題和題材,所表達(dá)的主題、意境又截然不同。比如花鳥題材,宮廷藝術(shù)表現(xiàn)嚴(yán)謹(jǐn)富麗,文人藝術(shù)表現(xiàn)輕松淡雅,民間藝術(shù)表現(xiàn)自然樸實(shí)。從一個具體的民間藝術(shù)母題出發(fā),追溯本源,羅列它在發(fā)展過程中所涉及的主題變化,以及它與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宗教藝術(shù)的母題、主題發(fā)展變化的內(nèi)在脈絡(luò)關(guān)系,這種清晰的主題耙梳是藝術(shù)史學(xué)研究的有效內(nèi)容。主題學(xué)視域的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是研究民間藝術(shù)史中那些相同母題或主題在不同時空(歷史和地域)中所發(fā)生的發(fā)展演變。張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書中,重點(diǎn)對民間藝術(shù)母題“麒麟”的演變路徑進(jìn)行細(xì)致考索。“麒麟”的原型為自然界中的“鹿”,它是一種性情溫順的動物,是“麒麟”的母題原型。經(jīng)考證,最早的“麒麟”圖形出現(xiàn)在西漢時期,為畫像石中的圖案。西漢“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儒家思想已經(jīng)確立為全社會的主導(dǎo)思想地位。《說文解字》將麒麟解釋為一種“仁獸”,而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愛”。很顯然,作為仁獸的麒麟,正是漢王朝推崇的儒家思想的具體化形態(tài)呈現(xiàn)。“鹿”作為一個藝術(shù)母題,有若干個主題發(fā)展方向,比如“長壽”主題,此處重點(diǎn)探討這一母題向“仁愛”主題的發(fā)展。可以說,母題“鹿”發(fā)展為具有仁愛主題的“麒麟”,母題的形象產(chǎn)生了巨大變化,相應(yīng)地它產(chǎn)生了一個全新的藝術(shù)主題。麒麟母題發(fā)展的另一個路徑為“麟之趾”,人們祈愿自己聰慧的孩童為“麒麟兒”。自此,麒麟和兒童的母題便形成了緊密的聯(lián)系,諸多的“麒麟送子”“天上麒麟子”等年畫,便是人們求子、祝愿孩子如“麟之趾”般美好前程在中國民間藝術(shù)中的具體呈現(xiàn)。古時傳說芣苡具有宜生功能,聞一多先生曾從《詩經(jīng)?周南?芣苡》入手,深入分析古代婦女采集芣苡風(fēng)俗的神圣與嚴(yán)肅。古代佛教的“磨侯羅”“化生兒”以及民間流行的“蓮生童子”“大阿福”等,也是人們求子心理在精神上的反映。不同的歷史階段受儒釋道思想的影響程度不同,也相應(yīng)出現(xiàn)了不同的求子母題意象群,如“送子觀音”“泰山娘娘”等。由此可見,麒麟的母題在歷史中不斷發(fā)展變化,形成了“多子多福”的主題。另外,民間有“天上麒麟兒,民間狀元郎”的說法,也是“麒麟”和“兒童”的母題結(jié)合形成的“望子成龍”主題。張道一先生從母題、主題發(fā)展變化角度追溯“麒麟”的原始母題“鹿”,而后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發(fā)展環(huán)境中,“麒麟”母題(意象)和不同的母題相結(jié)合,演變?yōu)椤镑梓胨妥印币约啊镑胪掠駮薄镑胫骸钡饶割}意象群。同時相應(yīng)的民間藝術(shù)主題也不斷演變,從最初的儒家核心思想“仁”,發(fā)展到“望子成龍”“多子多福”等民間藝術(shù)主題,以至演變?yōu)楝F(xiàn)代民眾祈愿的“吉祥”主題。“吉祥”主題在民間藝術(shù)中廣泛出現(xiàn),追溯這一主題在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中的發(fā)展演變譜系,可以發(fā)現(xiàn)“麒麟”便是這一藝術(shù)史學(xué)譜系中的一個母題原型。對此張道一先生感嘆道:“當(dāng)陳舊的思想意識隨著日月流逝,只剩下一個美麗的外殼時……由此轉(zhuǎn)化為一種符號和標(biāo)志,成為吉祥的象征。”[6]中國古代“吉祥”主題或許有若干主題、母題的脈絡(luò)譜系,但在此呈現(xiàn)的是藝術(shù)史學(xué)中“吉祥”主題其中一個民間藝術(shù)主題譜系的演變路徑。張道一先生對“麒麟”母題(或者說母題意象)如何發(fā)展演變?yōu)椤凹椤敝黝}的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譜系作專題研究,為主題學(xué)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介入民間藝術(shù)學(xué)的嘗試提供了理論佐證。把主題學(xué)運(yùn)用于民間藝術(shù)研究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意義。民間藝術(shù)與原始藝術(shù)存在緊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shù)發(fā)展的基石,也和宮廷藝術(shù)、文人藝術(shù)等藝術(shù)形態(tài)有著重要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在藝術(shù)史學(xué)領(lǐng)域,從主題學(xué)視角窺探民間藝術(shù)作品的主題思想,具體包括探究眾多民間藝術(shù)涉及的母題、題材、主題,以及母題變化和主題流變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以此厘清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譜系演變。民間藝術(shù)主題和母題演變形成的眾多譜系,是民間藝術(shù)史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和方法,也是藝術(shù)史研究的重要路徑,對整個人類藝術(shù)史主題譜系的演變也有著重要影響。當(dāng)然需特別注意,一定要將民間藝術(shù)主題置于大的藝術(shù)史學(xué)因果鏈中考察。主題學(xué)中的母題、題材、意象等因素,應(yīng)當(dāng)放在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的因果鏈中進(jìn)行考察。“主題譜系”概念準(zhǔn)確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為研究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母題譜系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徑。藝術(shù)主題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可以追根溯源,并且不斷向前發(fā)展。探究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脈絡(luò)發(fā)展變化路徑,正是藝術(shù)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探討民間藝術(shù)中眾多的主題與其母題之間的關(guān)系,分析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譜系與其史學(xué)路徑的脈絡(luò)關(guān)系,捋清民間藝術(shù)主題、母題的發(fā)展演變與大的藝術(shù)史學(xué)的關(guān)系,有助于研究主題學(xué)和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的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從而將主題學(xué)介入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研究的方法得以有效實(shí)施并產(chǎn)生積極作用。
三、當(dāng)代文化語境下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的研究意義
在當(dāng)代文化語境下,作為藝術(shù)學(xué)理論范疇的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研究,最主要的意義是從主題學(xué)視角分析民間藝術(shù)主題譜系的演變脈絡(luò),構(gòu)建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進(jìn)而豐富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的架構(gòu)。在整個社會文化范疇中,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的研究,無疑對深入了解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在基因,科學(xué)建構(gòu)民族文化的體系結(jié)構(gòu),為中華民族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民間藝術(shù)理論研究中,主題學(xué)視角容易被學(xué)者忽視。在藝術(shù)史學(xué)研究中,民間藝術(shù)板塊也經(jīng)常缺失。當(dāng)代學(xué)者主要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保護(hù)、藝術(shù)造型特點(diǎn)出發(fā),對民間藝術(shù)的流布與傳承進(jìn)行調(diào)研整理并思考對策,如各地的花紙年畫、門神紙馬、剪紙皮影、印染織繡、編織扎作等富有濃郁“鄉(xiāng)土”氣息的民間藝術(shù),無形中流露出人民大眾淳厚、率真、誠實(shí)、樂觀的情感,表現(xiàn)出鮮明夸張的形式特點(diǎn),映射出人民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路徑。民間藝術(shù)是農(nóng)耕時代的特有產(chǎn)物,是人們利用農(nóng)閑時間自發(fā)的藝術(shù)行為結(jié)果。作為一種文化藝術(shù)形態(tài),民間藝術(shù)是一條傳統(tǒng)之鏈,是一個時代的代表,可以看到特定時代民眾的人文精神,代表一個民族的過去,是一個民族文化歷史的見證。假如這些民間藝術(shù)消失,民族文化就沒有了實(shí)物見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民間藝術(shù)被稱為活化石就是這個道理。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期,不僅改變著生產(chǎn)方式和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更對人們的生活產(chǎn)生強(qiáng)烈沖擊,大部分民間藝術(shù)會悄然退出社會舞臺或進(jìn)行現(xiàn)代轉(zhuǎn)型。保護(hù)這些民間藝術(shù)固然重要,更需要從民間藝術(shù)深層次的主題流變進(jìn)行研究,提煉潛藏于民間藝術(shù)中廣大民眾的審美情趣,挖掘深植于民間藝術(shù)中的精神內(nèi)涵,這對于當(dāng)代社會文化語境的民間藝術(shù)研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遺憾的是民間藝術(shù)常常缺位于中國古代藝術(shù)史學(xué)研究,學(xué)者們更多地關(guān)注文人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的發(fā)展史。藝術(shù)的主題、母題研究,同樣是藝術(shù)史領(lǐng)域的絕響。唐代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記》是目前公認(rèn)的中西方藝術(shù)發(fā)展史中體例結(jié)構(gòu)相對較完善的史學(xué)著作,對中晚唐以前繪畫史及其理論做了詳盡梳理,全面敘述畫作的鑒品與收藏,并為自軒轅時代以來的372名有代表性的藝術(shù)家進(jìn)行傳記著錄。其他藝術(shù)理論著作如裴孝源的《貞觀公私畫史》、郭熙的《臨泉高致集》、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黃休復(fù)的《益州名畫錄》、笪重光的《畫筌》、鄒一桂的《小山畫譜》等,都是按照對藝術(shù)家及其作品評品的方式著述,沒有關(guān)于主題、母題方面的研究。無獨(dú)有偶,西方的藝術(shù)史撰寫路徑也沒有主題學(xué)的參與。瓦薩里的《藝苑名人傳》以產(chǎn)生、成熟、衰老、死亡的“再生進(jìn)程”藝術(shù)史觀為框架進(jìn)行撰寫,更多的是記錄了藝術(shù)家的生活及其與作品相關(guān)的事情。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shù)史》、沃爾夫林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學(xué):美術(shù)史的基本概念》、貢布里希的《藝術(shù)發(fā)展史》等,也都沒有涉及主題學(xué)。潘諾夫斯基的《視覺藝術(shù)的含義》《圖像學(xué)研究》用圣像學(xué)和圖像學(xué)探討藝術(shù)作品中的母題轉(zhuǎn)變問題,已經(jīng)涉及藝術(shù)主題學(xué)中的母題因素,但并沒有從主題學(xué)的視角進(jìn)行母題、主題的發(fā)展路徑研究。對于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研究在中西方藝術(shù)史學(xué)理論體系中的缺失,李倍雷教授提出:“缺乏民間藝術(shù)的‘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史學(xué)的這種現(xiàn)象,在今天必須加以糾正,讓民間藝術(shù)成為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的基本部分和架構(gòu)史學(xué)體系與體例的史料。”[7]目前大部分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理論是套用西方史學(xué)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撰寫,或者用西方美學(xué)理論架構(gòu)中國藝術(shù)史,或者用貝爾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藝術(shù)理論研究中國的藝術(shù)形態(tài)和藝術(shù)發(fā)展路徑,這些都不能準(zhǔn)確地解釋中國的藝術(shù)發(fā)展,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在這種構(gòu)架下更不可行。將主題學(xué)的研究方法介入中國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研究,探究藝術(shù)母題、主題的發(fā)展脈絡(luò),不僅是當(dāng)代藝術(shù)學(xué)理論研究的新視野,而且還可以窺探到中華民族文化自身的發(fā)展路徑。特別是在當(dāng)代社會文化語境中,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學(xué)研究不能缺席。通過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的研究,可以深層次地認(rèn)識中華民族精神和民眾文化信仰,對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自我覺醒、自我審視。“文化自覺”是費(fèi)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學(xué)首次提出來的,主要內(nèi)涵建立在對“根”的找尋與繼承上,建立在對“真”的批判與發(fā)展上,對發(fā)展趨向的規(guī)律把握與持續(xù)指引上。文化自覺要求對文化地位作用的認(rèn)識、對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的把握、對文化歷史責(zé)任的擔(dān)當(dāng)應(yīng)是深刻而正確的。民間藝術(shù)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對民族文化“根”的找尋與繼承上,比如關(guān)于“生育”“求子”主題的民間藝術(shù)有“送子娘娘”和“麒麟送子”等母題(意象群),廣泛分布于年畫、長命鎖、百家衣、百家被、虎頭鞋、虎頭帽、豬頭鞋等眾多民間藝術(shù)中。對這些民間藝術(shù)母題進(jìn)行全面梳理,可以找出它們的發(fā)展路徑,理清藝術(shù)母題影響主題演變的諸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藝術(shù)母題不管怎么發(fā)展,它們的共同主題始終是求子、保子平安健康等關(guān)于孩童的題材,都屬于吉祥文化主題的大范疇。文化自覺要求個人、民族都要對自身文化歷史圈子的藝術(shù)文化有自知之明,做到心中有數(shù),“各美其美”。雖然這個過程很艱巨,但只有對自己的文化有清醒的認(rèn)識,才可以在世界諸多文化類型中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文化觀,有條件地“美人之美”,理性思考民族本土文化在當(dāng)代社會文化轉(zhuǎn)型中的文化自主性,實(shí)現(xiàn)“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當(dāng)代社會文化語境中,以主題學(xué)視角研究民間藝術(shù),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一條有效路徑。文化自覺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自覺的基礎(chǔ)上,是民眾主體對自身所處文化的認(rèn)同和堅(jiān)守。我國的民間藝術(shù)豐富繁雜,是一個龐大的藝術(shù)文化圈,是中華民族的“根”之所在。一個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越深厚,它的凝聚力也就越強(qiáng)。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8]可以堅(jiān)信,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理論的研究,能讓整個民族更自覺地全面深入了解自身文化,由文化自覺逐漸建立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四、結(jié)語
民間藝術(shù)服務(wù)于最廣大的社會民眾,是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在當(dāng)代社會文化語境下,嘗試從主題學(xué)視角對民間藝術(shù)進(jìn)行理論研究,對民間藝術(shù)的主題、母題演變脈絡(luò)進(jìn)行有效整合,探究民間藝術(shù)主題學(xué)的發(fā)展路徑,不僅是民間藝術(shù)史學(xué)研究的新方法,也可以極大地豐富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體系。通過挖掘民間藝術(shù)背后的文化主題思想,總結(jié)提煉民族傳統(tǒng)文化基因,探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效實(shí)現(xiàn)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文化建設(shè),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
作者:李兵 單位:重慶三峽學(xué)院美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