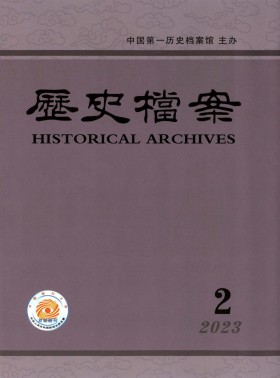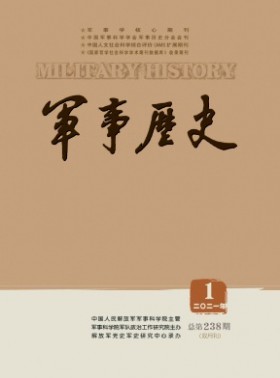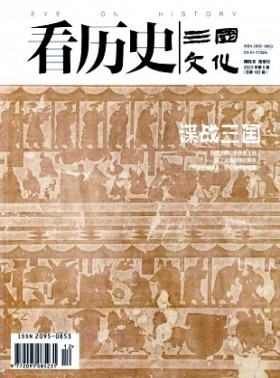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編精選了8篇?dú)v史研究范例,供您參考,期待您的閱讀。

戲曲音樂(lè)歷史研究模式
作者:潘林紫 馮彩媚 單位:廣西藝術(shù)學(xué)院音樂(lè)學(xué)院
引言歷史研究,以其探究事物的歷史發(fā)展軌跡和溯求根本,成為人類全面認(rèn)識(shí)世界的基礎(chǔ)步驟。戲曲音樂(lè)的歷史觀察是戲曲音樂(lè)研究的學(xué)術(shù)架構(gòu)基礎(chǔ)。戲曲是一種以文學(xué)、音樂(lè)、表演為核心形態(tài)要素的綜合藝術(shù)形式。戲曲音樂(lè)的歷史學(xué)研究并非僅有音樂(lè)而孤立其他,而是從音樂(lè)入手,觀察在音樂(lè)制約之下的文學(xué)、唱腔、念白、板式、曲牌、器樂(lè)等。歷史研究是以史料作為結(jié)論的提取素材,戲曲音樂(lè)的歷史關(guān)照,其文字性史料,體現(xiàn)為文學(xué)形態(tài)的劇本、戲詞,輯錄于各類文獻(xiàn)中相關(guān)“演劇”景況的描述性文字。曲譜屬于符號(hào)性與文字性共有的史料。此外,演劇圖像史料、文物、遺演劇址等實(shí)物,都可以作為論證過(guò)程中重要的論據(jù)。另有口述傳說(shuō),也可作為相互作證而用。本文所論,側(cè)重在文字性史料及樂(lè)譜史料的關(guān)照。音樂(lè)研究是不能脫離曲譜的,戲曲音樂(lè)如是。但戲曲音樂(lè)直接相關(guān)的樂(lè)譜史料,比其文字性史料來(lái)說(shuō),數(shù)量匱乏,地方戲曲更是難見(jiàn)晚清以前的曲譜存世。因此,戲曲音樂(lè)的歷史研究,進(jìn)展緩慢,目前只能在形態(tài)學(xué)上進(jìn)行曲體結(jié)構(gòu)分析、表演藝術(shù)上進(jìn)行唱腔分析等研究角度有所積累。本文所指歷史研究,即立足史料,對(duì)某劇種或其下屬某聲腔、某板式等結(jié)構(gòu)單位的音樂(lè)形態(tài)進(jìn)行其風(fēng)格、特色的歷時(shí)性動(dòng)態(tài)的演進(jìn),觀其變化等學(xué)術(shù)論證。本文僅提出“構(gòu)想”,因廣西戲曲音樂(lè)以文字史料和曲譜結(jié)合進(jìn)行體系化研究尚未形成,遂提出構(gòu)想及論證,呼吁未來(lái)有更多同仁關(guān)注研究并參與其中。廣西曾可見(jiàn)有桂劇、壯劇、彩調(diào)劇、邕劇、絲弦戲(劇)、采茶戲(劇)、牛娘戲、牛歌戲、鹿兒戲、客家戲、文場(chǎng)戲、唱燈戲、師公戲、壯師劇(戲)、侗戲(劇)、毛南戲(劇)、苗戲(劇)、鷯戲、仫佬戲①等20個(gè)戲曲劇種。目前,在廣西區(qū)圖書館的文學(xué)書庫(kù)、地方文獻(xiàn)庫(kù)和廣西地方報(bào)刊庫(kù)進(jìn)行史料搜集工作所獲史料所記載的信息,其內(nèi)容主要集中于劇本、音樂(lè)曲譜、演劇情況、源流、戲俗、科班藝人等,下文將對(duì)此進(jìn)行簡(jiǎn)要陳述。
一、文字史料與曲譜概述
(一)劇目劇目即劇本。現(xiàn)有桂劇、彩調(diào)、邕劇等劇種的傳統(tǒng)劇目匯編書籍中,如1963年的《廣西戲曲傳統(tǒng)劇目匯編》(共64集),包含了彩調(diào)、桂劇、邕劇三個(gè)劇種上千個(gè)劇目。這些劇目劇本,描述故事并有簡(jiǎn)單提示演員的動(dòng)作、走位。其他劇種的劇本,主要在《中國(guó)戲曲志•廣西卷》中,如苗劇、仫佬劇等建國(guó)才產(chǎn)生的劇種。現(xiàn)刊行的劇目,基本為故事講述的戲劇臺(tái)本,少見(jiàn)曲譜隨附。在廣西上世紀(jì)50-80年代的期刊,如《廣西藝術(shù)》、《廣西文藝》、《廣西戲劇通訊》、《漓江》,這些期刊選登有粵劇(當(dāng)時(shí)分為小型粵劇、新粵曲)、彩調(diào)(當(dāng)時(shí)1955年前稱調(diào)子戲)、桂劇、采茶劇的劇目劇本。《廣西文藝》僅在1954-1956兩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個(gè)劇目劇本。另外還有專門刊登某一劇種劇目的刊物,如《彩調(diào)叢刊》(1-6)《桂劇叢刊》(1-4)。這些刊載或有重復(fù),但劇目的數(shù)量也是巨大的,還有大量的單個(gè)劇目成冊(cè)出版。
(二)唱腔收錄及曲譜匯編現(xiàn)有唱腔曲譜以彩調(diào)、桂劇最多,其次有采茶戲、壯劇;其他劇種較少。主要集中于《彩調(diào)常用曲調(diào)集》(1964)《桂劇音樂(lè)》(1961)等書中,有一小部分則見(jiàn)于《廣西文藝》等期刊中。《中國(guó)戲曲音樂(lè)集成•廣西卷》《中國(guó)戲曲志•廣西卷》兩部大型集成,收錄了上述彩調(diào)、桂劇等廣西可見(jiàn)的,相對(duì)成熟①的所有劇種。戲曲唱腔因流派風(fēng)格有異,演員傳譜有異,常見(jiàn)同一唱段有多個(gè)版本記譜,體現(xiàn)不同藝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記譜。不同版本記譜,會(huì)有旋律片段、唱詞上的差別。這是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的一大特點(diǎn),也可給研究帶來(lái)困難,但也是比較研究的寬廣空間。地方性劇種,如桂南采茶戲的曲目曲譜,則曲譜比較多且集中。在廣西藝術(shù)研究所編寫的《桂南采茶音樂(lè)》(1985年)一書中,就有廣西各地區(qū)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調(diào))、曲牌、鑼鼓音樂(lè)的曲譜,此輯曲譜的學(xué)術(shù)性較強(qiáng),記譜者不僅盡量再現(xiàn)音樂(lè)及歌詞原貌,甚至顧及到方言的差異,體現(xiàn)地方戲音樂(lè)的核心特色:地方語(yǔ)言與音樂(lè)的結(jié)合。
(三)記載演劇、戲俗的志書在《廣西戲劇史料集》(下文稱《史料集》)和《廣西戲劇史料散論集》(下文稱《散論集》)中,《史料集》收錄私人著作中相關(guān)廣西戲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廣西戲劇活動(dòng)的各項(xiàng)文件和啟示、藝人墓碑碑文、各地區(qū)歷代縣志中描述戲劇的片段摘錄。《散論集》有編者對(duì)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對(duì)照論述以及部分桂劇科班史料。志書、筆記、游記中所錄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劇,這類文字如遠(yuǎn)觀異事,一言帶過(guò)。唐宋時(shí)期,此地多見(jiàn)為傀儡、儺等屬于民間歌舞戲形態(tài)階段的戲曲雛形、多附在祭祀巫卜這樣功能性較強(qiáng)的行為中,其藝術(shù)形態(tài)較為簡(jiǎn)單,與現(xiàn)今可見(jiàn)的儀式音樂(lè)較接近,音樂(lè)性不強(qiáng)。而且史料中所述景況,更多可明確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備了戲曲的必須特性尚不明確。這樣的史料記載為今日的地方戲曲研究帶來(lái)一些爭(zhēng)議性的問(wèn)題,有些藝術(shù)種類,如文場(chǎng),應(yīng)歸其為戲曲還是曲藝②,在一些后人所編文獻(xiàn)的分類中,有將文場(chǎng)歸置于戲曲類,也有歸置于曲藝類,雖然今天將其視為曲藝的居多,但既有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存在,可見(jiàn)學(xué)術(shù)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還不夠充分。在布告所錄文字這類史料中,“劇”之針對(duì)性就比較強(qiáng),如《宣傳部函知南寧市各戲院聽候派員審查戲劇文》,《廣西省戲劇審查會(huì)為改良禁演桂劇先行試演征求社會(huì)公評(píng)啟事》這樣的篇目,前例應(yīng)還包含了話劇等劇類,而后例就比較明確是針對(duì)桂劇所發(fā)。此類史料,描述事由、條例等較為周詳,甚至還能涉及劇目羅列,但音樂(lè)風(fēng)格、藝術(shù)形式等,就不得所見(jiàn)。各地方的縣志所錄文字中,有各種民間演劇風(fēng)俗,體現(xiàn)了民間崇拜、節(jié)慶、文化聯(lián)誼等不同層面的演劇模式,大都簡(jiǎn)單明了的,信息相對(duì)齊全。
(四)科班、藝人傳略專門將此單獨(dú)呈現(xiàn),因這類內(nèi)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較大,且關(guān)于科班的記載,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藝人兼地方文化部門工作者執(zhí)筆而作,即現(xiàn)今所指“口述史”。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區(qū)戲劇研究室或市戲劇研究室研究員,采集于上世紀(jì)50~60年代。藝人傳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藝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資料為主。如《廣西地方戲曲史料匯編》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劇、彩調(diào)、粵劇和壯劇的科班與藝人史料相對(duì)要多,主要呈現(xiàn)科班開辦時(shí)間地點(diǎn)、科班教師、教學(xué)情況以及各行當(dāng)演員。口述史料一般作為佐證而用,也有些專題,只見(jiàn)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須多有佐證,下結(jié)論便更為強(qiáng)調(diào)“客觀”以衡定。(五)《中國(guó)戲曲志•廣西卷》中所呈戲曲“所有事”作為編撰針對(duì)性較強(qiáng)的志書,《中國(guó)戲曲志•廣西卷》(下文稱《戲曲志》)史料呈分類式輯錄。《戲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劇種表、廣西地方劇種分布圖、志略、劇種、劇目、音樂(lè)(聲腔與腔調(diào)、劇種音樂(lè))、表演(腳色行當(dāng)體制與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臺(tái)美術(shù)(化妝與臉譜、服裝、裝扮選例、砌末道具、舞臺(tái)陳設(shè)與布景、舞臺(tái)布景選例、舞臺(tái)燈光與效果)、機(jī)構(gòu)(科班、學(xué)校及訓(xùn)練班;班社、劇團(tuán);業(yè)余劇團(tuán);作坊與工廠;群眾團(tuán)體、研究機(jī)構(gòu);演出公司)、演出場(chǎng)所、演出習(xí)俗、文物古跡、報(bào)刊專著、軼聞傳說(shuō)、諺語(yǔ)•口訣•行話、詩(shī)詞•楹聯(lián)、傳記等18個(gè)類項(xiàng),以及附錄中有戲曲會(huì)演、調(diào)演、攝制電影、錄音唱片、磁帶名錄等。該分類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相當(dāng)完備的戲曲研究學(xué)術(shù)構(gòu)架,附錄的學(xué)術(shù)參考價(jià)值也非常高。《戲曲志》所錄史料,雖不盡然齊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義是非凡的。#p#分頁(yè)標(biāo)題#e#
我國(guó)煤炭歷史研究困難
作者:薛毅 單位:中國(guó)礦業(yè)大學(xué)中國(guó)煤礦史研究所
煤炭是地球上蘊(yùn)藏量最豐富、分布地域最廣的化石燃料。中國(guó)是世界上發(fā)現(xiàn)、開采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國(guó)家之一。煤炭的開采和利用為人類帶來(lái)了光和熱,提供了新的能源,對(duì)于中國(guó)的社會(huì)進(jìn)步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產(chǎn)生過(guò)重要的作用。截止目前,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中國(guó)古代煤炭的開發(fā)和利用及相關(guān)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著作主要有夏湘蓉等編著的《中國(guó)古代礦業(yè)開發(fā)史》(地質(zhì)出版社1980年版)、《中國(guó)古代煤炭開發(fā)史》編寫組著的《中國(guó)古代煤炭開發(fā)史》(煤炭工業(yè)出版社1986年版)、李進(jìn)堯等著:《中國(guó)古代金屬礦和煤礦開采工程技術(shù)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資料匯編主要有章鴻釗遺著:《古礦錄》(地質(zhì)出版社1954年版)、祁守華等編的《中國(guó)地方志煤炭史料選輯》(煤炭工業(yè)出版社1990年版)、吳曉煜編著的《中國(guó)煤炭碑刻》(煤炭工業(yè)出版社2010年版)等。論文主要有周藍(lán)田:《中國(guó)古代人民使用煤炭歷史的研究》(《北京礦業(y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56年2期);趙承澤等:《關(guān)于西周的一批煤玉雕刻》(《文物》1978年5期);許惠民:《北宋時(shí)期煤炭的開發(fā)利用》(《中國(guó)史研究》1987年2期);李仲均等:《中國(guó)古代用煤的歷史》(《文史知識(shí)》1987年3期);黃啟臣:《萬(wàn)歷年間礦業(yè)政策的論爭(zhēng)》(《史學(xué)集刊》1988年3期);楊濤:《礦稅大興與明政權(quán)的解體》(《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88年3期);官美堞:《古代工礦市鎮(zhèn)———顏神鎮(zhèn)的形成和發(fā)展》(《文史哲》1988年6期);李進(jìn)堯:《中國(guó)采煤技術(shù)的形成和發(fā)展》(《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1期);許惠民等:《北宋時(shí)期開封的燃料問(wèn)題———宋人能源問(wèn)題研究之二》(《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1988年6期);華覺(jué)明:《煤、制團(tuán)和燒結(jié)在中國(guó)古代冶金中的應(yīng)用》(《中國(guó)科技史料》1989年第4期);王開璽:《清前期礦務(wù)政策述評(píng)》(《安徽史學(xué)》1992年2期);元廷植:《清中期的北京煤炭不足和清朝的對(duì)策》(《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8年3期);吳曉煜:《中國(guó)古代煤礦史的基本脈絡(luò)和煤炭開發(fā)利用的主要特征》(《中國(guó)礦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年3期)等。由此可見(jiàn),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煤炭的開發(fā)利用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有目共睹,十分可喜的成績(jī)。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從縱向研究古代中國(guó)煤炭開采和利用的發(fā)展歷程,也有側(cè)重研究某一朝代對(duì)煤炭的開采政策。有的專注于某一個(gè)案的考證,有的就古代煤炭開采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進(jìn)行論述等。根據(jù)以往研究中國(guó)古代煤炭開發(fā)利用存在的問(wèn)題和不足,結(jié)合最近的研究成果,本文擬就煤炭的形成、中國(guó)古代煤炭名稱的演進(jìn)、煤窯與煤礦的考辨、古代對(duì)煤炭的發(fā)現(xiàn)和利用等幾個(gè)基本問(wèn)題進(jìn)行探討,以就教于各位專家學(xué)者。
一、關(guān)于煤炭的形成
在中國(guó),關(guān)于煤炭是怎樣形成的?人們的認(rèn)識(shí)經(jīng)歷了一個(gè)漫長(zhǎng)的過(guò)程。“漢代有人說(shuō)煤是‘天火劫燒之灰’。唐代有人認(rèn)為煤是‘天火燒石而成’,是由石頭變來(lái)的。還有人則求助于神,認(rèn)為煤是太上老君‘煉海燒山’的結(jié)果,甚至編造出‘神仙種煤’、‘老君爺撒籽種煤’、‘黑龍入地變化成煤’的種種神話傳說(shuō)。”[1]80就目前而言,絕大多數(shù)相關(guān)專著和教科書認(rèn)為:煤炭是一種化石燃料,它是植物遺體在覆蓋地層下,壓實(shí)、轉(zhuǎn)化而成的固體有機(jī)可燃沉積巖,蘊(yùn)藏于地層之間。煤炭是由數(shù)億年前植物大量繁殖生長(zhǎng)之后形成的。從植物死亡、堆積到轉(zhuǎn)化成煤炭,經(jīng)過(guò)了漫長(zhǎng)的極其復(fù)雜的生物化學(xué)、物理化學(xué)作用演變過(guò)程。這個(gè)過(guò)程包括泥炭化作用、腐泥化作用,最終形成為煤炭。“隨著近代地質(zhì)學(xué)及生物地質(zhì)學(xué)的發(fā)展,人們可以在煤層及其附近巖層中發(fā)現(xiàn)大量保存完好、可以鑒定屬種的古代植物化石;在煤層中可以發(fā)現(xiàn)碳化了的樹干;在煤層頂?shù)装宓恼惩令悗r石中可以發(fā)現(xiàn)植物根、莖、葉部的印痕和遺跡;如果把煤磨成薄片置于顯微鏡下觀察,還可以看到植物細(xì)胞組織的殘留痕跡以及孢子、花粉、樹脂、角質(zhì)層等植物殘留物。所有這一切,都無(wú)可辯駁地證實(shí)了腐殖煤是由高等植物變來(lái)的。”[2]2除了植物條件,煤炭的形成還需要具備氣候、地殼運(yùn)動(dòng)和地理?xiàng)l件,四者缺一不可。關(guān)于氣候條件,潮濕是沼澤最主要的特征;只有溫暖的氣候才有利于泥炭的大量堆積;泥炭的保存需要適當(dāng)?shù)母菜畻l件,而覆水程度與濕度有關(guān)。關(guān)于地質(zhì)條件,形成煤田最主要的地質(zhì)條件是地殼上升或下沉的垂直運(yùn)動(dòng),正是由于這種垂直運(yùn)動(dòng),在地球上才出現(xiàn)了高山和海洋、陸地和湖泊。當(dāng)?shù)貧は陆档貌惶顣r(shí),就形成了沼澤。在沼澤中生長(zhǎng)的水生植物死亡后就堆積在沼澤中,這種沼澤就逐步變成了泥炭沼。泥炭化作用是在泥炭沼中進(jìn)行的,在自然界中進(jìn)行著植物的生長(zhǎng)和死亡,死亡植物堆積起來(lái),其殘骸與空氣隔離,加上有足夠的水分注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泥炭。泥炭在地下熱力和壓力的作用下逐步形成褐煤和煙煤。地理?xiàng)l件是指成煤場(chǎng)所。
地史上有相當(dāng)多的植物死亡后,因沒(méi)有有利的堆積場(chǎng)所而被氧化分解。所以,要形成分布面較廣的煤層,還必須有適宜于發(fā)生大面積沼澤化的自然地理場(chǎng)所,如濱海平原、內(nèi)陸盆地、山間盆地等。同時(shí)具備植物、氣候、地質(zhì)、地理四個(gè)條件的時(shí)間越長(zhǎng),形成的煤層就越厚。“其中地殼運(yùn)動(dòng)為主導(dǎo)因素,對(duì)植物的生長(zhǎng)及其遺體的保存、氣候的形成、成煤場(chǎng)所、煤層厚度等都有控制作用。”[3]116關(guān)于植物演變成煤炭的時(shí)間,古代學(xué)者多語(yǔ)焉不詳,多以“洪荒以來(lái)”、“古之山林洪荒之世”、“太初之世”、“無(wú)算年代”等一筆代過(guò)。清代學(xué)者檀萃在分析云南煤炭生成原因時(shí)認(rèn)為:“滇多地震,地裂盡開,兩旁之木,震而倒下,旋即復(fù)合如平地,林木人居皆不見(jiàn),閱千年化為煤”。[1]81關(guān)于植物演變成煤炭的時(shí)間,美國(guó)學(xué)者約翰•R•麥克尼爾認(rèn)為:“在合適的條件下,埋在地下的植物經(jīng)過(guò)數(shù)百萬(wàn)年的壓力就會(huì)形成煤炭。”他還認(rèn)為:“如果時(shí)間不夠,就是泥炭。大部分的泥炭都是在過(guò)去6000年形成的,濕冷的氣候是泥炭形成和保存的必要條件。因此,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泥炭都蘊(yùn)藏在高緯度和高海拔的地區(qū),如加拿大、斯堪的納維亞和西伯利亞。”[4]中國(guó)學(xué)者向英溫和楊先林認(rèn)為:“煤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在缺氧和某些細(xì)菌的作用下,經(jīng)過(guò)幾千年的漫長(zhǎng)時(shí)間,在溫度、壓力及地質(zhì)化學(xué)作用條件下而變成的。”[5]1#p#分頁(yè)標(biāo)題#e#
總之,煤炭起源于植物是學(xué)術(shù)界普遍認(rèn)為并根深蒂固的觀點(diǎn),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現(xiàn)代漢語(yǔ)辭典》(第5版)對(duì)煤炭的解釋:“一種可以燃燒的黑色固體,主要成分是碳、氫、氧和氮。是古代植物埋在地下,經(jīng)歷復(fù)雜的化學(xué)變化和高溫高壓而形成的。按形成階段和煤化程度的不同,可分為泥煤、褐煤、煙煤和無(wú)煙煤。主要用做燃料和化工原料。”[6]928這個(gè)解釋可以視為目前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煤炭的基本認(rèn)識(shí)。近年來(lái),國(guó)內(nèi)一些學(xué)者和長(zhǎng)期從事煤礦工程技術(shù)的人員對(duì)煤炭的成因提出了新的觀點(diǎn),質(zhì)疑并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王成學(xué)先生認(rèn)為:“如果煤炭真由樹木堆積而成,那他的頂?shù)装寰筒粫?huì)那么平,光滑的如鏡子一般……樹木的根部約占整個(gè)樹木體積的1/4~1/5左右,這不是個(gè)小數(shù)字,如果有當(dāng)?shù)貥淠緟⑴c形成煤炭,那它根部所形成的煤炭則應(yīng)在地板內(nèi),而且地板就不可能那么平,更不用說(shuō)平滑如鏡的頂板了。”他還認(rèn)為:“有的煤層特別厚,而有的煤層又特別薄,薄的地方厚度僅幾厘米甚至幾毫米,想想看,如果是1cm厚的煤層那是怎么形成的?難道是由6cm厚的樹木形成的嗎?難道當(dāng)時(shí)茂密的森林僅有6cm?有人說(shuō)是草或灌木形成的,如果真是那樣,草和灌木又是那里來(lái)的?如果是本地生長(zhǎng)的,那土又在那里?因?yàn)楹芏鄻O薄煤層下面僅是一層薄薄的夾矸,夾矸下面又是煤炭,如果草真的長(zhǎng)在這薄薄的土地上,而且一般不是一年二年,那它下面形成煤炭的樹木既不處于高溫高壓和隔氧的情況下,那為什么不會(huì)腐爛呢?有人講那是在水下形成的。那更不可能,夾矸下面的煤層有時(shí)很厚,需要很多樹木來(lái)形成,它怎么不被水漂浮起來(lái)而甘愿被薄薄一層泥沙壓住而形成夾矸呢?另外在頂板內(nèi)和巖層中,經(jīng)常有和紙一樣薄的煤層而常被稱作煤線的,它們又是怎樣形成的?”王成學(xué)先生在文章中進(jìn)一步質(zhì)疑,如果說(shuō)煤炭來(lái)源于植物,那么“金、銀、銅、鐵、錫等各式各樣的礦物又是怎樣形成的?”他的結(jié)論是:“煤炭不可能是由植物或樹木形成的。”[7]34、427年后,王成學(xué)先生又發(fā)表了《再論“煤的形成質(zhì)疑”》一文。作者在文章中自稱曾長(zhǎng)年在井下與煤打交道,非常熟悉煤層賦存狀態(tài)。在文章中,作者分別以新疆特厚煤層和山西沁水煤田特薄煤層為例證提出:“最近有報(bào)道說(shuō),新疆發(fā)現(xiàn)有50m、150m、甚至750m的特厚煤層,按照6m實(shí)木形成1m煤的理論,那得需要750m×6m=4500m厚的實(shí)木才能形成,大家認(rèn)為可能嗎?……最薄的夾矸僅有3cm,卻沒(méi)有一根木頭將其穿透,這能讓人相信嗎?”關(guān)于形成煤炭的原因,作者認(rèn)為:“在宇宙大爆炸后,宇宙物質(zhì)急速向四周擴(kuò)散,在不同的區(qū)域,由于萬(wàn)有引力的作用,物質(zhì)逐步聚攏,就形成了各個(gè)星球,其中也包括地球。地球由多種物質(zhì)構(gòu)成,其中也包括形成煤的物質(zhì),于是與形成其它巖層一樣形成了煤層。”[8]28刊登這兩篇文章的是由山西潞安礦業(yè)(集團(tuán))公司主辦的《煤》雜志。該刊之所以兩次發(fā)表王成學(xué)先生質(zhì)疑煤炭形成原因的文章,是因?yàn)樵摽l(fā)表了王成學(xué)先生第一篇質(zhì)疑文章后,“許多讀者紛紛來(lái)電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一致認(rèn)為煤確實(shí)不是由木頭形成的,但是如何形成的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diǎn)。”[8]29其中荀洪菲等人認(rèn)為:“距今66億年前,在銀河系的一場(chǎng)大爆炸之后,地球形成的過(guò)程當(dāng)中形成了煤。煤是包含各種碳?xì)浠衔铩⒘蚧锖吞嫉仍氐膲m埃星云氣體被地球吸引并隨球體的形成埋藏于地下沉積而成。”[9]91由此可見(jiàn),關(guān)于煤炭形成的原因尚無(wú)定論,各家的觀點(diǎn)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而最終形成具有充分說(shuō)服力的共識(shí)不僅對(duì)于研究中國(guó)煤炭史至關(guān)重要,而且對(duì)世界煤炭史研究也是一大貢獻(xiàn)。
二、關(guān)于煤炭名稱的演進(jìn)
空間思維之于歷史研究思考
不同形態(tài)的空間通常是不同的建構(gòu)邏輯運(yùn)作的結(jié)果。不同形態(tài)的空間通常也是不同權(quán)利資源實(shí)踐的結(jié)果。比如說(shuō),抗戰(zhàn)時(shí)期日軍占領(lǐng)了北京,把北大的紅樓變成駐軍的場(chǎng)所。戰(zhàn)時(shí)北大清華舉校南遷,到了南方,把廟宇變成教室,把民居變成宿舍。從物質(zhì)觀點(diǎn)來(lái)看,校園或廟宇,公主府第或軍隊(duì)營(yíng)房,各種不同空間在形成或建構(gòu)的時(shí)候常有若干內(nèi)在的規(guī)劃或則律,并且依循這些原則安排門戶或者墻壁。各類空間秩序一旦形成,這個(gè)秩序?qū)τ谄溟g所將要開展的活動(dòng),也常常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規(guī)范性。人們一旦進(jìn)入或使用這個(gè)空間,就不得不跟這個(gè)規(guī)劃邏輯進(jìn)行某種有意或無(wú)意的對(duì)話。這種對(duì)話往往是具有文化以及社會(huì)意義的,我們?nèi)绻_發(fā)這個(gè)意義,應(yīng)當(dāng)可以為歷史研究開辟新的視角。
我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我們談史學(xué)研究中的空間思維,目的并不在于狹義的提倡城市研究。我認(rèn)為,空間思維可以為一般史學(xué)研究加分,正是因?yàn)橐话惴卜蛩鬃硬荒軌蛏裥校蠹矣侄枷胂蠡蛳M裥小D芘c不能、以及想與不想,其間有個(gè)張力。這個(gè)張力十分有趣,能為史學(xué)研究增色。至于如何增色,進(jìn)而發(fā)揮宏旨,則關(guān)鍵在于我們?cè)谘芯康脑O(shè)計(jì)之中,是否能把空間結(jié)構(gòu)看作權(quán)利以及資源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把空間形態(tài)解讀成具有社會(huì)文化經(jīng)濟(jì)意義的歷史積淀,把歷史人物的空間經(jīng)歷開發(fā)為一種特定歷史時(shí)期社會(huì)文化實(shí)踐與物質(zhì)權(quán)利秩序建構(gòu)邏輯之間的對(duì)抗或?qū)υ挕N覀兓仡欀腥A民國(guó)史的研究,這類把“空間建構(gòu)”與“社會(huì)實(shí)踐”看待成對(duì)抗或?qū)υ掃^(guò)程的作品似乎還不算多。中國(guó)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這回的論壇,既然以中華民國(guó)史的回顧與前瞻作為題目,我想我們?nèi)绻谑穼W(xué)領(lǐng)域中開發(fā)空間思維,今后或者可以開辟出一個(gè)新的史學(xué)維度。
以上已經(jīng)指出,我所論述的民國(guó)史學(xué)中的空間思維,雖然離不開對(duì)于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理解,但是這并不等于主張把民國(guó)史研究變成民國(guó)時(shí)期城市史研究。為了進(jìn)一步說(shuō)明這個(gè)觀點(diǎn),以下我想以伯克利加州大學(xué)20世紀(jì)中期歷史學(xué)系的列文孫教授的作品作為例子,透過(guò)對(duì)他的思想史論述的重讀,思索他的作品中的空間思維,著墨以上所描述的空間思維。
列文孫的《儒家中國(guó)及其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三卷本,不但提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guān)系,同時(shí)也著眼西方與中國(guó)之間文化上的張力。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所以斷裂,在他看來(lái),其中一個(gè)重大的原因,便是東西交匯、中國(guó)的世界空間秩序被動(dòng)地被重組。這個(gè)傳統(tǒng)空間秩序所指的不只是眾所周知的朝貢體系以及明清帝國(guó)所圖繪想象的天下,同時(shí)對(duì)內(nèi)而言,也是以科舉為制度、以儒學(xué)士人為干部團(tuán)隊(duì)的政治社會(huì)秩序。這個(gè)以四書五經(jīng)為課本的秩序建構(gòu)在一個(gè)區(qū)分夷狄華夏、核心邊陲的文明想象之上。晚清時(shí)期這個(gè)秩序被動(dòng)的被重組,打破了中國(guó)世界內(nèi)部原有的文化社會(huì)資源利益的分配,也打破了中國(guó)對(duì)外關(guān)系的一貫論述。戊戌以后,中國(guó)面臨空前的文明挑戰(zhàn),傳統(tǒng)知識(shí)人也面臨權(quán)利話語(yǔ)的挑戰(zhàn)。根據(jù)列文孫的看法,這樣的雙重挑戰(zhàn)促成了中國(guó)歷史千年以來(lái)首次的根本斷裂。
列文孫的文化論述粗枝大葉,他的結(jié)論在過(guò)去半個(gè)世紀(jì)中遭受到許多學(xué)者提出來(lái)的許多辯駁。我們只能說(shuō),他的作品產(chǎn)生在20世紀(jì)中期,無(wú)可避免的遭受到當(dāng)時(shí)的不少時(shí)代局限。但是他提出來(lái)的問(wèn)題,也就是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國(guó)作為東方與歐美作為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全球化過(guò)程中碰撞的問(wèn)題,則仍然是至今沒(méi)有完善解決的史學(xué)問(wèn)題,這個(gè)問(wèn)題在21世紀(jì)的今天,仍然以各種面貌繼續(xù)衍生存在。列文孫可以重讀,正因?yàn)樗岢龅臍v史問(wèn)題不但至今還沒(méi)有解決,而且他的論述方式,正可以幫助我們檢視這些問(wèn)題今天之所以繼續(xù)是問(wèn)題,其中在西方學(xué)界所曾經(jīng)走過(guò)的話語(yǔ)建構(gòu)的道路。
列文孫所運(yùn)用的歷史分析方法,一方面具有時(shí)間縱深,在時(shí)間跨度上從晚明一直關(guān)注到人民共和國(guó),一方面具有空間跨度,把中國(guó)放進(jìn)世界地圖,透過(guò)這個(gè)地圖在近現(xiàn)代的重新繪制,來(lái)談文明以及國(guó)家問(wèn)題。他說(shuō)16世紀(jì)的東西交通,是耶穌會(huì)傳教士積極尋求被中國(guó)士人接納的過(guò)程。中國(guó)是天下,歐西是外洋。而19世紀(jì)晚期以后的東西交通,則成為中國(guó)知識(shí)人一力尋求加入西方世界的過(guò)程。以歐西為核心以及主導(dǎo)的世界成為世界,以中國(guó)為疆界的傳統(tǒng)天下淪為這個(gè)世界中的一個(gè)次要的特定地區(qū)或省份。這種空間關(guān)系的變化具有極大的現(xiàn)實(shí)文明以及政治上的意義。列文孫的空間思維,體現(xiàn)在他對(duì)空間結(jié)構(gòu)及其變化的關(guān)注,以及其間所引發(fā)的權(quán)利關(guān)系位置轉(zhuǎn)移的現(xiàn)象。我們姑且把他所使用的闡釋方法稱之為“位移”。
列文孫說(shuō)過(guò),一個(gè)人如果在沙漠之中迷途,他如果想知道他在哪,他所該用的方式并不是描述自己的所在,因?yàn)樗粫?huì)不知道他的存身地點(diǎn)。他所該知道的是其他的人在哪,知道了以后才能定出自己該行進(jìn)的方向。他又說(shuō),我們?nèi)绻暾J(rèn)識(shí)一個(gè)提法的內(nèi)涵,就不能只看這個(gè)提法的字面意義,而需要看這個(gè)提法所針對(duì)解答的問(wèn)題,以及當(dāng)這個(gè)提法被肯定的時(shí)候,有哪些其他相關(guān)的提法遭受否定。換言之,一個(gè)話語(yǔ)的意涵,包含它所肯定與否定的多元層面,也包含它的功利指向。
探析國(guó)內(nèi)古城歷史研究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正式承認(rèn)為諸侯,安邑也成為了魏國(guó)的都城。文侯之子魏武侯在位時(shí),“城安邑”(《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jì)年》:“魏武侯十一年(前385年),城洛陽(yáng)及安邑、王垣。”)魏武侯的“城安邑”,當(dāng)是出于軍事防御的需要。安邑的地理位置靠近秦國(guó),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秦國(guó)強(qiáng)大以后受到嚴(yán)重威脅。在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時(shí),“城安邑”已不足以解決問(wèn)題,終于迫使魏國(guó)做出了遷都舉動(dòng)。《水經(jīng)注》引《竹書紀(jì)年》:“梁惠成王六年(前364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惠王遷都大梁后,魏也稱梁,魏惠王也被稱為梁惠王)從魏絳徙治安邑到魏惠王遷都大梁,魏在安邑經(jīng)營(yíng)的時(shí)間約兩百年。
梁惠王遷都后,安邑仍不失為河?xùn)|地區(qū)的一座重鎮(zhèn)。秦、魏兩國(guó)為此發(fā)生了長(zhǎng)期的爭(zhēng)奪。《史記•秦本紀(jì)》:“(孝公)十年,衛(wèi)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但秦國(guó)并沒(méi)有能一直占領(lǐng)此城。直至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魏國(guó)才被迫獻(xiàn)出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xùn)|賜爵,赦罪人遷之”。《史記•秦本紀(jì)》二十二年,“河?xùn)|為九縣。”秦國(guó)以安邑為中心建立了河?xùn)|郡。
秦漢的河?xùn)|郡一直以安邑為郡治,河?xùn)|治下的縣最多時(shí)達(dá)到二十八個(gè)(《漢書•尹翁歸傳》)。魏正始八年五月,“分河?xùn)|之汾北十縣為平陽(yáng)郡。”(《三國(guó)志•魏書•三少帝紀(jì)》),河?xùn)|郡被一分為二,北部成立了新郡平陽(yáng),南部仍稱河?xùn)|郡,郡治仍在安邑。
南北安邑考
北魏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南北安邑”。《魏書•地理志》“河北郡”下面有“北安邑”,注云:“二漢、晉曰安邑,屬河?xùn)|,后改。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為郡,十八年復(fù)屬”;有“南安邑”,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條山。”可見(jiàn)北安邑是原安邑,而南安邑是北魏時(shí)期新置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中沿襲了明《一統(tǒng)志》里的說(shuō)法,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的安邑縣(今鹽湖區(qū)安邑鎮(zhèn))是北安邑,與《魏書》中的說(shuō)法明顯不和,當(dāng)屬誤斷)。由于今夏縣縣治在禹王城(原安邑)南,所以有人認(rèn)為夏縣即是“南安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西通志》(雍正版,卷一百七十九)里的一種說(shuō)法,該書援引《通典》云:“后魏神元年別置南安邑城,在禹都舊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之東立夏縣。”此說(shuō)看似與《魏書•地理志》的說(shuō)法不同,其實(shí)并不矛盾,甚至是可以相互佐證的。因?yàn)榇苏f(shuō)中僅僅提到在神元年別置南安邑“城”,而并未言明在此置縣。按《魏書•世祖紀(jì)》,神元年前后,北魏正與占據(jù)關(guān)中的赫連氏作戰(zhàn),雖然北魏在之前始光四年(427年)的戰(zhàn)斗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神元年的戰(zhàn)局一度不利,置南安邑城多是出于軍事目的,意在鞏固在河?xùn)|的戰(zhàn)果,而直至六十年后的太和十一年,南安邑才正式立縣,南安邑應(yīng)是后來(lái)安邑縣(現(xiàn)已并入鹽湖區(qū))的前身。而北安邑的治所后來(lái)移到東南方向,成為今天的夏縣。也正是在神元年,北魏太武帝自安邑移郡于蒲坂(《太平寰宇記》,卷四十六),安邑從此失去了郡治的地位。
禹王城城郭布局
禹王城的主要遺存是東周至漢代的城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臺(tái)四個(gè)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臺(tái)在小城的東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
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院
學(xué)術(shù)精神是學(xué)術(shù)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chéng)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xiàn)在學(xué)者執(zhí)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wèn)題意識(shí)、強(qiáng)烈的批判意識(shí),以及整體的學(xué)術(shù)思想之中。在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術(shù)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xué)問(wèn)家,然而,關(guān)注世界、關(guān)注時(shí)代、關(guān)注當(dāng)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xué)術(shù)胸襟博采眾家之長(zhǎng),兼容并蓄,同時(shí)在其學(xué)術(shù)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xué)術(shù)責(zé)任感與學(xué)術(shù)使命感的學(xué)者,恐并不多見(jiàn)。本文通過(guò)對(duì)于潤(rùn)洋先生20世紀(jì)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xué)術(shù)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發(fā)展的基本脈絡(luò)及其重要學(xué)說(shuō)在當(dāng)代中國(guó)的西方音樂(lè)史學(xué)、音樂(lè)美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的理論價(jià)值與學(xué)術(shù)意義,以表達(dá)筆者對(duì)于潤(rùn)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xué)術(shù)生涯的誠(chéng)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jì)70年代末至整個(gè)80年代是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史上意識(shí)形態(tài)的“撥亂反正”期,同時(shí)也是于先生學(xué)術(shù)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中予以強(qiáng)調(diào)的兩個(gè)研究范疇,同時(shí)也是于先生構(gòu)建理論學(xué)說(shuō)的“兩大基石”。然而,對(duì)于這一學(xué)術(shù)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xué)術(shù)著述之中。《器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藝術(shù)規(guī)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fā)表的一篇論文。當(dāng)時(shí),雖然“”已經(jīng)被粉碎,但在我國(guó)音樂(lè)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內(nèi)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標(biāo)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xiàn)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lǐng)袖時(shí)采用《東方紅》的曲調(diào);寄托對(duì)革命者的哀思時(shí)采用《國(guó)際歌》的動(dòng)機(jī);表現(xiàn)人民軍隊(duì)時(shí)則采用《三大紀(jì)律八項(xiàng)注意》……對(duì)此,于先生運(yùn)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lè)學(xué)的角度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象提出了批評(píng):器樂(lè)的認(rèn)識(shí)作用和社會(huì)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rèn)識(shí),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rèn)識(shí)能力,進(jìn)而影響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感情態(tài)度。這是音樂(lè)、特別是器樂(lè)所具有的獨(dú)特作用。忽視了這個(gè)特點(diǎn),勢(shì)必造成對(duì)器樂(lè)的政治內(nèi)容、器樂(lè)為政治服務(wù)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yùn)動(dòng)”、“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chǎn)物……要求器樂(lè)直接表現(xiàn)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lè)必須直接為政治運(yùn)動(dòng)服務(wù),這難免要導(dǎo)致器樂(lè)創(chuàng)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lè)所特有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量,同時(shí)也就喪失了器樂(lè)真正應(yīng)該具有的政治內(nèi)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jié)尾處,以音樂(lè)學(xué)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yuǎn)見(jiàn)卓識(shí)特別提到了音樂(lè)學(xué)學(xué)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jīng)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shù)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lè)創(chuàng)作領(lǐng)域中,我們應(yīng)該在一系列的實(shí)踐和理論問(wèn)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guī)律性的東西,為未來(lái)器樂(lè)創(chuàng)作的繁榮創(chuàng)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duì)整個(gè)音樂(lè)創(chuàng)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xué)評(píng)論產(chǎn)生有益的、深遠(yuǎn)的影響。②經(jīng)過(guò)了十年動(dòng)亂后的中國(guó),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jìn)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術(shù)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guó)的人文科學(xué)研究以及人文社會(huì)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duì)我國(guó)人文學(xué)術(shù)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xué)術(shù)名著”以及其中關(guān)于哲學(xué)、美學(xué)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xué)》《/西方美學(xué)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shù)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xiàn)的科學(xué)和一般語(yǔ)言學(xué)的美學(xué)的歷史》、鮑桑葵《美學(xué)史》、科林伍德《藝術(shù)原理》、蘇珊•朗格《藝術(shù)問(wèn)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xiàn)象學(xué)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xué)知識(shí)的增長(zhǎng)》、李普曼《當(dāng)代美學(xué)》),以及我國(guó)哲學(xué)界、美學(xué)界一批著作的陸續(xù)問(wèn)世,我國(guó)的音樂(lè)美學(xué)著作出版與學(xué)術(shù)研究也開始復(fù)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lè)學(xué)家愛(ài)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lè)美學(xué)名著《論音樂(lè)的美———音樂(lè)美學(xué)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guó)音樂(lè)學(xué)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lè)語(yǔ)言》中譯本問(wèn)世。之后,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和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率先在音樂(lè)學(xué)系里成立了音樂(lè)美學(xué)小組,并著手對(duì)一些外文音樂(lè)美學(xué)文論與著作進(jìn)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guó)音樂(lè)學(xué)院的音樂(lè)美學(xué)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shí)期開始,作為音樂(lè)學(xué)的學(xué)科任務(wù)———“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就再也沒(méi)有離開過(guò)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shuō)于先生強(qiáng)調(diào)“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的學(xué)術(shù)思想與我國(guó)當(dāng)時(shí)的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人文社會(huì)思潮,以及音樂(lè)學(xué)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wú)關(guān)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yīng)看到這一學(xué)術(shù)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jiān)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lè)學(xué)家特有的理論自覺(jué)———問(wèn)題意識(shí)與批判意識(shí)直接相關(guān)。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jiàn)的理論學(xué)說(shuō),且博采眾家之長(zhǎng);他關(guān)注世界、關(guān)注時(shí)代、關(guān)注當(dāng)下,但絕不是關(guān)注時(shí)髦,而是關(guān)注在時(shí)髦的當(dāng)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xué)術(shù)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lè)的美———音樂(lè)美學(xué)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duì)一種自律論音樂(lè)美學(xué)的剖析———評(píng)漢斯立克的〈論音樂(lè)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duì)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xiàn)不是音樂(lè)的內(nèi)容”④、“音樂(lè)美是一種獨(dú)特的只為音樂(lè)所特有的美”⑤、“音樂(lè)的內(nèi)容就是樂(lè)音的運(yùn)動(dòng)形式”⑥等學(xué)說(shuō)率先進(jìn)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guò)大量的史學(xué)舉證和美學(xué)剖析后才得出結(jié)論:漢斯立克的學(xué)說(shuō)是唯心主義的錯(cuò)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根本對(duì)立的立場(chǎng)。⑦并對(duì)這些表面看起來(lái)似乎僅只是音樂(lè)美學(xué)領(lǐng)域中關(guān)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xué)術(shù)之爭(zhēng),但實(shí)際上卻是直接挑戰(zhàn)甚至動(dòng)搖我們長(zhǎng)期以來(lái)堅(jiān)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xué)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wèn)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fā)表的《符號(hào)、語(yǔ)義理論與現(xiàn)代音樂(lè)美學(xué)》(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xiàn)象學(xué)音樂(lè)美學(xué)評(píng)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jiān)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并重的學(xué)術(shù)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duì)蘇珊•朗格的“藝術(shù)符號(hào)理論”、阿達(dá)姆•沙夫的“語(yǔ)義學(xué)理論”,以及對(duì)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duì)象”以及胡塞爾現(xiàn)象學(xué)等理論學(xué)說(shuō)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xué)評(píng)價(jià)和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p#分頁(yè)標(biāo)題#e#
如果說(shuō),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gè)時(shí)期對(duì)西方各種理論學(xué)說(shuō)進(jìn)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fā)表的《關(guān)于音樂(lè)基礎(chǔ)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lái),則是于先生經(jīng)過(guò)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xué)理論層面上對(duì)音樂(lè)與音樂(lè)藝術(shù)的本質(zhì)、屬性、形式、內(nèi)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史學(xué)、美學(xué)、技術(shù)理論等學(xué)科的一次深刻的學(xué)術(shù)總結(jié)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gòu)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xué)術(shù)思想,同時(shí)也為他在未來(lái)的兩個(gè)時(shí)期中取得更多的學(xué)術(shù)成就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二者在音樂(lè)學(xué)研究中的相互關(guān)系時(shí),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guó)的西方音樂(lè)史學(xué)研究為例,除了史學(xué)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wèn)題之外,音樂(lè)美學(xué)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lè)美學(xué)觀念充斥史學(xué)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lè)史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原因。當(dāng)我們的音樂(lè)哲學(xué)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duì)音樂(lè)美學(xué)的一系列重要問(wèn)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cuò)誤的觀念所占據(jù)時(shí),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shù)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在音樂(lè)技術(shù)理論領(lǐng)域中,關(guān)系相對(duì)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wú)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chǔ)理論素質(zhì)的提高,否則這門學(xué)科就只能永遠(yuǎn)停留在經(jīng)驗(yàn)論的、工藝學(xué)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jiàn),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lái)的“音樂(lè)學(xué)分析”理論學(xué)說(shuō)(1993)以及《現(xiàn)代西方音樂(lè)哲學(xué)導(dǎo)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lè)中的悲情內(nèi)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chǔ),同時(shí)也構(gòu)成了他所有學(xué)術(shù)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jì)念導(dǎo)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shuō)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lè)學(xué)外)“麗薩在音樂(lè)學(xué)上做出貢獻(xiàn)的另一個(gè)領(lǐng)域是歷史音樂(lè)學(xué)。她在體系音樂(lè)學(xué)領(lǐng)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lè)學(xué)方面的淵博知識(shí)分不開的。對(duì)于她來(lái)說(shuō),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yán)格的界限。她的音樂(lè)美學(xué)論著總是給人以強(qiáng)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lè)史學(xué)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nèi)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shí)代的進(jìn)步與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xué)生,于先生強(qiáng)調(diào)和堅(jiān)持“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并重的音樂(lè)學(xué)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dǎo)的“歷史研究”與“美學(xué)評(píng)價(jià)”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guó)當(dāng)下的西方音樂(lè)研究領(lǐng)域中產(chǎn)生了意義深遠(yuǎn)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xué)基礎(chǔ)之上的、具有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特色的音樂(lè)學(xué)研究。
汽車歷史研究新方式
作者:Simon Gunn 丁雄飛 張衛(wèi)良 單位:萊斯特大學(xué) 華東師范大學(xué) 杭州師范大學(xué)
1960年4月,在英國(guó)國(guó)會(huì)的一場(chǎng)關(guān)于道路交通的辯論中,工黨議員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GordonWalker)發(fā)表了一番演說(shuō),他的主題是“預(yù)想未來(lái)”。沃克說(shuō):汽車是能夠促進(jìn)我們國(guó)家當(dāng)下社會(huì)變革最有活力的因素。它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改變我們城市、道路和鄉(xiāng)村的面貌……我認(rèn)為擁有一輛汽車正開始取代擁有一所住房,這體現(xiàn)了人的獨(dú)立感和自尊感。汽車已然日漸成為人的社會(huì)必需品,于是,我們道路上的汽車數(shù)量會(huì)急劇增長(zhǎng)。我們必須以更大的精力,根據(jù)汽車這一維度來(lái)重新建構(gòu)我們整個(gè)工作和生活的環(huán)境。①其他的一些專家并沒(méi)有那么樂(lè)觀,他們更擔(dān)心的是大眾汽車化可能導(dǎo)致的種種后果。1961年,英國(guó)重要的交通規(guī)劃師柯林•布坎南(ColinBuchanan)警告?zhèn)惗爻鞘幸?guī)劃研究院:“作為機(jī)動(dòng)車影響的一個(gè)結(jié)果,許多可怕的事情將會(huì)發(fā)生。”
現(xiàn)在,汽車“正威脅著城市地區(qū)的文明化運(yùn)作”;根據(jù)布坎南的說(shuō)法,汽車正在“產(chǎn)生讓那些地方呈現(xiàn)出一派冷漠的面貌的惡劣影響”[1]。然而,在20世紀(jì)60年代初,英國(guó)所有評(píng)論家一致認(rèn)為,隨著大眾擁有汽車時(shí)代的到來(lái),這個(gè)國(guó)家的景觀及其社會(huì)生活正在發(fā)生改變。在這方面,英國(guó)遠(yuǎn)不是獨(dú)一無(wú)二的。遍及大部分的西方國(guó)家———包括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國(guó)家———正是在20世紀(jì)50年代到70年代的這些年里,社會(huì)學(xué)家們所謂的“汽車體制”的東西才嵌入進(jìn)來(lái)。當(dāng)然,就汽車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它們?cè)?0世紀(jì)初的時(shí)候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但是,只有到了20世紀(jì)50年代和60年代,隨著大眾擁有汽車的規(guī)模擴(kuò)展,全球大部分地區(qū)的基礎(chǔ)設(shè)施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才開始發(fā)生變化。在這些年里,英國(guó)的汽車數(shù)量增長(zhǎng)了五倍。[2]1958-1968年間,法國(guó)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消費(fèi)革命,文化評(píng)論家視其重要性堪比19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工業(yè)革命。盡管洗衣機(jī)、電視機(jī)和電冰箱都是這場(chǎng)消費(fèi)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其最具標(biāo)志性的符號(hào)就是像雪鐵龍德尚(CitroenDS)這樣的汽車。[3]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單單在1960-1970年間,日本的汽車和卡車數(shù)量就增長(zhǎng)了16倍,從而在10年之內(nèi)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大眾汽車社會(huì)。即便是美國(guó),這個(gè)世界上最先進(jìn)的汽車國(guó)家也是在20世紀(jì)50年代建造了全國(guó)高速公路系統(tǒng)和州際高速公路系統(tǒng)。②[4]
在20世紀(jì)下半葉,汽車體制吞噬了西方社會(huì)。沒(méi)有一個(gè)發(fā)達(dá)國(guó)家可以阻擋這種趨勢(shì)。但是,汽車大眾化在不同國(guó)家產(chǎn)生了相當(dāng)不同的影響———新建了道路系統(tǒng),產(chǎn)生了物質(zhì)方面的影響;政府獲得了一個(gè)大眾汽車社會(huì),并給予回應(yīng),產(chǎn)生了政治方面的影響;汽車被作為消費(fèi)者的駕駛?cè)怂鶎S茫a(chǎn)生了文化方面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們并沒(méi)有一部全球范圍的關(guān)于汽車體制的歷史。我們有的僅僅是一些零碎的關(guān)于汽車使用的編史。例如,以英國(guó)和日本為例,主要的撰稿者是一些企業(yè)史家和經(jīng)濟(jì)史家,因此,有一種著名的汽車制造和汽車企業(yè)史,例如像尼桑和福特這樣的歷史;但是,在北美之外關(guān)于汽車對(duì)城市形態(tài)或者社會(huì)生活方式影響的歷史研究卻非常罕見(jiàn)。③盡管如此,由于各國(guó)政府開始認(rèn)識(shí)到汽車對(duì)于碳排放和全球變暖的影響,也因?yàn)槲覀兗磳⒉饺雭喼奁嚫锩@一新階段,所以,許多歷史學(xué)家開始思考1945年之后那幾十年間發(fā)生的所謂大眾汽車化的“第一次浪潮”。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樣,對(duì)于這個(gè)問(wèn)題,我們已經(jīng)開始逐漸拋棄那些相對(duì)淺顯的思考方式,比如僅僅涉及汽車制造和汽車擁有規(guī)模的擴(kuò)張。在這篇短文中,我試圖就大眾汽車化這一歷史現(xiàn)象,查考一些更為重要的研究新路徑。這些路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diǎn):“汽車體制”的概念、大眾汽車化對(duì)于城市形態(tài)的影響、大眾汽車擁有權(quán)的政治學(xué)及其對(duì)于改變?nèi)粘I钇鹆硕啻蟮淖饔谩?/p>
一“汽車體制”
首先,最近有關(guān)汽車化的歷史研究已經(jīng)受到了社會(huì)學(xué)家們所謂“汽車體制”這一術(shù)語(yǔ)的影響。[5-6]這意味著,研究汽車化不能將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基礎(chǔ)設(shè)施割裂開來(lái),正是汽車化導(dǎo)致了這些基礎(chǔ)設(shè)施的出現(xiàn)。當(dāng)大眾汽車制造業(y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開始騰飛的時(shí)候,一系列新的現(xiàn)象隨之應(yīng)運(yùn)而生:各種新的道路系統(tǒng)以應(yīng)對(duì)一個(gè)飛速機(jī)動(dòng)化的社會(huì);一個(gè)為汽車業(yè)供給燃料的石化工業(yè),像殼牌和美孚這樣的跨國(guó)石油公司便是這一現(xiàn)象的縮影;汽車銷售的經(jīng)銷商網(wǎng)絡(luò)以及維修汽車的修理站;大量小型產(chǎn)業(yè)提供一切從汽車配件到道路標(biāo)志的相關(guān)產(chǎn)品。其他的產(chǎn)業(yè),比如廣告業(yè),開始大規(guī)模地重新定位,以便使汽車品牌化和偶像化。這種全新工業(yè)上層建筑的增長(zhǎng)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汽車業(yè)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越來(lái)越占有主導(dǎo)地位,最明顯的是,大規(guī)模的汽車產(chǎn)業(yè)在美國(guó)、英國(guó)、法國(guó)、德國(guó)和意大利已經(jīng)確立起來(lái)。不同形式的汽車運(yùn)輸業(yè)成為一個(gè)主要的就業(yè)雇主,汽車制造業(yè)亦成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主要引擎———尤其在像煤炭、紡織、造船這樣的傳統(tǒng)工業(yè)走向衰弱的時(shí)期。各國(guó)政府設(shè)法通過(guò)調(diào)整消費(fèi)者的借款利率來(lái)管控消費(fèi)行為,因?yàn)榇蠖鄶?shù)的普通人是依靠貸款來(lái)購(gòu)買汽車的。同時(shí),汽車產(chǎn)業(yè)本身也開始將自身確立為一個(gè)能夠施加政治壓力的集團(tuán),這個(gè)集團(tuán)包括制造商、石化利益團(tuán)體、公路貨運(yùn)公司、汽車銷售商團(tuán)體,等等———這個(gè)集團(tuán)以“公路游說(shuō)團(tuán)”(‘roadlobby’)著名。到20世紀(jì)60年代,這個(gè)“公路游說(shuō)團(tuán)”被認(rèn)為是英國(guó)議會(huì)中最強(qiáng)大的政治壓力集團(tuán),它們?cè)噲D對(duì)從稅費(fèi)到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務(wù)施加影響。[7]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汽車在歷史上不僅僅是一種消費(fèi)商品,或者一種交通工具,毋寧說(shuō)是一種體制———汽車體制———的一部分。這種體制同時(shí)還是一種經(jīng)濟(jì)、政治、技術(shù)和社會(huì)的集合。
城市史學(xué)家的一個(gè)任務(wù)就是去理解,這種集合在不同國(guó)家、不同歷史時(shí)期是如何被建構(gòu)起來(lái)的。很多國(guó)家是在20世紀(jì)50-70年代之間確立起來(lái),但美國(guó)要更早一些,在20世紀(jì)的30-50年代之間就已經(jīng)建立。只有意識(shí)到汽車深度嵌入社會(huì)這一本質(zhì),我們才能理解以下事實(shí):汽車本身具有非凡的適應(yīng)能力;政客們屢次試圖限制汽車使用的努力,皆毫無(wú)效果;汽車有能力在油價(jià)連番上漲之后依然生存下來(lái)。和其他的基礎(chǔ)設(shè)施形態(tài)一樣,如電力、自來(lái)水、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等,汽車化已經(jīng)深深地植根于我們的建筑形式、日常經(jīng)濟(jì)乃至現(xiàn)代都市社會(huì)的消費(fèi)想象之中。[8]#p#分頁(yè)標(biāo)題#e#
關(guān)于第一手史料對(duì)歷史研究的幾點(diǎn)辨析
思想史研究亦如此,如法國(guó)歷史哲學(xué)家雷蒙•阿隆寫過(guò)一部《想象的馬克思主義》,論說(shuō)薩特的馬克思研究,認(rèn)為薩特是用存在主義解讀馬克思,這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想象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我們今天研究薩特的思想(如薩特的馬克思觀),不讀薩特本人的著作,而只讀雷蒙•阿隆的《想象的馬克思主義》,那么這就是使用二手史料。但如果我們是研究雷蒙•阿隆的思想,那么他的這部著作,就是我們研究的第一手史料。當(dāng)然,如果要進(jìn)一步推敲,也只有雷蒙•阿隆的法文原著才能算一手史料,因?yàn)檎Z(yǔ)文的轉(zhuǎn)譯,也會(huì)產(chǎn)生一定的誤解錯(cuò)譯。總之,史料的一手、二手,都針對(duì)我們特定的研究對(duì)象而言,也隨著我們研究對(duì)象的轉(zhuǎn)變而轉(zhuǎn)變。離開了研究對(duì)象而指稱某史料是一手或二手,是沒(méi)有意義的。
回到上文提到的“特洛伊題”。A 選項(xiàng)的格羅特是一位嚴(yán)謹(jǐn)?shù)氖穼W(xué)家,也是“一個(gè)很有威望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證人”(恩格斯語(yǔ)),他的《希臘史》以材料豐富、考證精審而受到學(xué)界贊譽(yù)。《荷馬史詩(shī)》中保存了特拉伊戰(zhàn)爭(zhēng)的一手史料(見(jiàn)下文),如果格羅特的《希臘史》采用《荷馬史詩(shī)》來(lái)寫特拉伊戰(zhàn)爭(zhēng),而我們不是從《荷馬史詩(shī)》而是從格羅特的著作去錄用有關(guān)的史料,那么,這只是使用了二手史料。格羅特和他的《希臘史》在當(dāng)年就有很好聲譽(yù),許多學(xué)術(shù)著述都會(huì)引用其中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guó)家的起源》,就引用了這部書的一些資料和結(jié)論。但是,這樣的引用,仍只能說(shuō)是利用了二手資料。當(dāng)然,如果我們要研究 19 世紀(jì)的英國(guó)史學(xué)(格羅特是 19 世紀(jì)英國(guó)史學(xué)家),研究格羅特本人的史學(xué)思想、史學(xué)方法,那么這部《希臘史》就是一手史料了。
第一手史料當(dāng)依據(jù)史料的留存狀況來(lái)判定
按照上文的邏輯,如果我們研究司馬遷的史學(xué)思想,《史記》自然是第一手史料;如果我們借助《史記》來(lái)研究西漢歷史,那么,它只是第二手史料。但是,為什么習(xí)慣上我們常說(shuō)《史記》是研究西漢的第一手史料呢?這與上文的邏輯是否相悖呢?其實(shí)這里有一個(gè)語(yǔ)境的問(wèn)題,而語(yǔ)境的背后,乃是史料的留存問(wèn)題。
《史記》是司馬遷的名著,作為一部史學(xué)著作,它運(yùn)用了大量當(dāng)時(shí)所能看到的原始史料。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擔(dān)任太史令一職,自然可以閱讀、利用宮廷保存的這許多原始史料。呂思勉先生有一篇考證性的文章,題為《本紀(jì)世家皆史記前已有》,認(rèn)為在《史記》之前,已經(jīng)有本紀(jì)、世家這種體裁的歷史資料,《史記》的編撰,大量錄用了這些原有的史料。后人評(píng)說(shuō)《史記》,會(huì)說(shuō)它有很多重復(fù),說(shuō)司馬遷的敘事常常詳略不均;同樣記事,有時(shí)是以人為主,有時(shí)以事為主。其實(shí),這主要因?yàn)榍按舸娴氖妨媳臼侨绱耍?ldquo;如其說(shuō)是好的,史公不應(yīng)盡冒其功;如其說(shuō)是壞的,史公不能盡尸其咎”。我們?cè)谥T如《史籍舉要》(柴德賡著)、《中國(guó)古代史籍舉要》(張舜徽著)一類書中,都能看到對(duì)《史記》史料來(lái)源的詳盡分析。可見(jiàn)司馬遷《史記》所用的材料,原先都有原始的一手史料。但是到后來(lái),《史記》所本的一手史料全都亡佚而不可見(jiàn)了,于是便說(shuō)《史記》是我們研究漢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其實(shí),非但《史記》有這種情況,“二十四史”的大部分,都是這種情況。如成書于后晉的《舊唐書》,治唐史者,無(wú)不稱其為第一手史料。但是,據(jù)史學(xué)家趙翼考證,《舊唐書》的史料,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大都取自當(dāng)年的《實(shí)錄》和《國(guó)史》。唐朝的《國(guó)史》是以《實(shí)錄》為原始資料加以編撰的,而《實(shí)錄》則是朝廷史官(起居令史)實(shí)錄的帝王言行。所以,如果我們研究唐代歷史,與其說(shuō)《舊唐書》《國(guó)史》是第一手史料,倒不如說(shuō)這些《實(shí)錄》是第一手史料。無(wú)奈唐朝的《實(shí)錄》,除了韓愈所撰《順治實(shí)錄》還在,其他早都亡佚了;《國(guó)史》僅韋述所撰的部分,撰《舊唐書》的劉 還能看到,其他的也都散失了。唐之《實(shí)錄》《國(guó)史》已亡佚而不可見(jiàn),而保存了《實(shí)錄》《國(guó)史》之原始史料的《舊唐書》,則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唐代歷史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以同樣的邏輯來(lái)推論《清史稿》卻不一定恰當(dāng)。《清史稿》的史料自然也極豐富,有清一代國(guó)史館的國(guó)史底本、各朝實(shí)錄、圣訓(xùn)、方略、會(huì)典、方志,以及《清史列傳》《耆獻(xiàn)類征》《碑傳集》等各種文集,都是撰史者的原始史料。由于年代較近,《清史稿》的原始史料大多數(shù)至今還保存完好,這就使得今日的文獻(xiàn)整理研究者可以依據(jù)上述材料與《清史稿》做互相校勘。明白了《清史稿》與其原始史料的關(guān)系,以及這些原始史料的保存情況,我們自然就不會(huì)徑直地稱它為第一手史料。所以,史學(xué)家柴德賡在《史籍舉要》中論說(shuō)《清史稿》的史料來(lái)源時(shí)說(shuō):“《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簡(jiǎn)略,是轉(zhuǎn)手多次以后的資料。”這也就說(shuō)明,史料的一手、二手,還當(dāng)依據(jù)史料的留存狀況來(lái)區(qū)分。
第一手史料與史著中引錄一手史料不能視為等同
以三部曲淺談歷史研究著作的創(chuàng)新
《三部曲》作者治史著書的價(jià)值追求是“讓學(xué)術(shù)研究的成果為大眾所共享”,“力求義理、考據(jù)、辭章兼?zhèn)洌枷胄浴⒖茖W(xué)性、可讀性三者統(tǒng)一,寫出有新材料、新觀點(diǎn),有吸引力、感染力的歷史著作”。就是要編寫出普及與提高相結(jié)合的歷史著作,以便于對(duì)干部、群眾和青年進(jìn)行國(guó)史 教育,提高國(guó)民素質(zhì)。這樣的價(jià)值追求,不僅是研究國(guó)史應(yīng)有的,也是研究其他歷史所應(yīng)有的。思想性、科學(xué)性、可讀性統(tǒng)一,理論價(jià)值、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社會(huì)普及價(jià)值兼?zhèn)洌@樣的著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史的研究中并不多見(jiàn)。有的著作,思想水平高,而學(xué)術(shù)性、可讀性略遜;有的著作,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高,而可讀性略遜(也有思想性略遜的);有的著作,可讀性強(qiáng),但思想性、學(xué)術(shù)性略遜(如有些戲說(shuō)類、紀(jì)實(shí)文學(xué)類的書,史實(shí)錯(cuò)誤不少)。而《三部曲》在思想性、科學(xué)性、可讀性統(tǒng)一,理論價(jià)值、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社會(huì)普及價(jià)值兼?zhèn)浞矫嫒〉昧丝上驳某煽?jī),值得彰顯。《三部曲》的理論價(jià)值、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可另文探討,以下只說(shuō)其可讀性、社會(huì)普及價(jià)值的成績(jī),以窺學(xué)術(shù)著作普及路徑。
圖文并茂
書中大量采用了百姓大眾喜聞樂(lè)見(jiàn)的資料照片,題材、內(nèi)容豐富,一覽即可從中獲得一定的感性認(rèn)識(shí)。如,同鄧小平親切握手的照片,鄧小平、汪東興在主席客廳里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中,可以領(lǐng)略鄧小平復(fù)出初期以及其他幾位領(lǐng)導(dǎo)人的精神風(fēng)貌,乃至從中體味這些歷史人物在當(dāng)時(shí)的關(guān)系。
與《三部曲》差不多時(shí)間出版的圖文并刊的書還有幾種,比較起來(lái),《三部曲》無(wú)論內(nèi)容和圖片都豐富多了。如《三部曲》的第一部《前奏》篇幅300余頁(yè),采用照片50余張,文字22萬(wàn),這自然有助于把“”時(shí)期鄧小平領(lǐng)導(dǎo)全面整頓這段歷史反映得更全面、更深入、更詳盡。而且《前奏》中有些照片是很多書中所沒(méi)有的,如“起草的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關(guān)于鄧小平任職決定的通知”(第14頁(yè))、“姚雪垠1977年寫給胡喬木的信”(第199頁(yè))等。《三部曲》其他卷中也有一些照片,如《決戰(zhàn)》第30頁(yè)“1976年3月10日,對(duì)關(guān)于是否•31•印發(fā)講話的請(qǐng)示報(bào)告的批語(yǔ)”,第195頁(yè)“給鄧崗的手令(1976年10月6日)”等照片,《新路》第78頁(yè)“鄧小平為陶鑄平反的批示”,第81頁(yè)“1978年5月7日,對(duì)溫濟(jì)澤要求平反報(bào)告的批示”,第247頁(yè)“胡喬木起草的《歷史決議》手稿”等照片,也是已經(jīng)出版的一些書中沒(méi)有的。以上這些照片不僅史料價(jià)值很高,從中還可以看到、、、鄧小平、、胡喬木、姚雪垠等人的書寫真跡,起到見(jiàn)字如見(jiàn)人的效用,還可以作書法的欣賞。
注重寫史事的細(xì)節(jié)、情節(jié)、場(chǎng)景
讀者有身臨其事之感,引人入勝。如《前奏》寫鄧小平“”時(shí)期復(fù)出,第一次在宴會(huì)上露面:這是他自1967年銷聲匿跡以后,第一次在公開場(chǎng)合同中外人士會(huì)見(jiàn)。雖然他坐的位置并不顯眼,卻吸引了全場(chǎng)的目光。他沒(méi)有說(shuō)一句話,甚至還顯得有點(diǎn)孤單,但無(wú)論是中國(guó)人還是外國(guó)人,都感覺(jué)到他重新登上中國(guó)政治舞臺(tái)的分量。
對(duì)鄧小平及場(chǎng)景寥寥數(shù)語(yǔ)的細(xì)節(jié)刻畫,一讀就使人油然產(chǎn)生一種興奮和驚喜,不斷回味。又如對(duì)追悼大會(huì)的記述,《決戰(zhàn)》寫道:鄧小平致悼詞時(shí)表情凝重,聲音低沉悲痛。當(dāng)讀到“全黨、全軍、全國(guó)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這句時(shí),他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稍事停頓,極力抑制著自己的巨大悲傷。這時(shí)會(huì)場(chǎng)上一片哭泣、嗚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