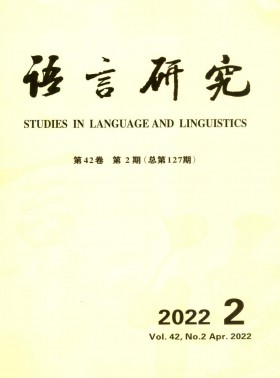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編精選了8篇語言學(xué)范例,供您參考,期待您的閱讀。

英語教學(xué)語言學(xué)探究
摘要:
英語教學(xué)與英語語言學(xué)關(guān)系密切。英語語言學(xué)對(duì)英語教學(xué)的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當(dāng)前的經(jīng)濟(jì)全球化背景下,英語教學(xué)顯得更為重要,如何營造有效的教學(xué)氛圍,幫助學(xué)生理解和掌握英語知識(shí),是當(dāng)前英語教師應(yīng)當(dāng)深入思考的問題。而英語語言學(xué)不僅能夠營造合理語境,還可以提升課堂趣味性。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英語語言學(xué)和英語教學(xué)的特點(diǎn)。又在此基礎(chǔ)上從詞形學(xué)構(gòu)詞法、語音學(xué)、認(rèn)知語言學(xué)等方面分析了英語語言學(xué)在英語教學(xué)中的具體運(yùn)用。
關(guān)鍵詞:
英語語言學(xué);英語教學(xué);運(yùn)用
隨著經(jīng)濟(jì)全球化趨勢(shì)的不斷加強(qiáng),英語教學(xué)日益受到社會(huì)各層人士的關(guān)注。在這種社會(huì)背景下,我國英語教育者及學(xué)者經(jīng)過不斷探索和總結(jié),也歸納出一套有效的英語語言學(xué)教學(xué)法。由于我國高校英語教學(xué)的教材大綱要求學(xué)生必須熟練的掌握聽、說、讀、寫等語言運(yùn)用技能,因此,英語學(xué)習(xí)和教學(xué)就必須從英語語言學(xué)的應(yīng)用本質(zhì)出發(fā)。英語語言學(xué)全面、系統(tǒng)的揭示了英語的發(fā)展規(guī)律與功能。可見,英語語言學(xué)與英語教學(xué)聯(lián)系極為緊密,若要提升英語教學(xué)效率,就必須重視英語語言學(xué)在教學(xué)過程中的運(yùn)用。
1英語語言學(xué)和英語教學(xué)的特點(diǎn)
1.1英語語言學(xué)的特點(diǎn)
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關(guān)鍵性要素
1商務(wù)語言與商務(wù)語言學(xué)研究的興起
1.1商務(wù)語言的研究范疇
進(jìn)入新世紀(jì)后經(jīng)濟(jì)全球化加速了人才流動(dòng)與交往,擴(kuò)大了商務(wù)活動(dòng)領(lǐng)域與范圍,而作為媒介的語言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們開始對(duì)普遍運(yùn)用的商務(wù)語言這個(gè)語言變體給予極大關(guān)注。針對(duì)語言的這種變體和運(yùn)用領(lǐng)域范圍,國內(nèi)的語言學(xué)家對(duì)商務(wù)語言的發(fā)展及其特殊性開始展開研究,2005年黎運(yùn)漢出版了《商務(wù)語言教程》,全面系統(tǒng)地探討了商務(wù)語言的功用和特點(diǎn),涉及內(nèi)容有:商務(wù)語言表達(dá)與領(lǐng)會(huì)的原則,商務(wù)語言使用的規(guī)律,營銷語用策略,商務(wù)談判用語策略等,并將商務(wù)語言作為一個(gè)專門功能分語體加以整體研究。他對(duì)商務(wù)語言的定義如下:“商務(wù)語言不是一種獨(dú)立的語言,而是全民語言在商業(yè)領(lǐng)域交際中形成的一種言語變異,具有自己特點(diǎn)和風(fēng)格的一種言語體式”(黎運(yùn)漢2005:29)。其實(shí),商務(wù)語言是一種動(dòng)態(tài)的言語表現(xiàn),它包括一切語言的商務(wù)性功能與特征。就目前我們所能接觸到最常見的語言取向而言,有商務(wù)漢語、商務(wù)英語、商務(wù)日語、商務(wù)俄語、商務(wù)法語、商務(wù)德語、商務(wù)韓(朝)語、商務(wù)西班牙語等等,在現(xiàn)實(shí)中,這些語種的商務(wù)語言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即除了操本族語人員使用外更多地是為那些非本族語人而言的,都把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譬如:商務(wù)漢語主要針對(duì)漢語為非母語的人群,商務(wù)英語是針對(duì)那些英語為非母語的人群,希望通過這種商務(wù)語言的學(xué)習(xí)使得那些非母語的使用者或從業(yè)者能夠在商務(wù)領(lǐng)域中掌握專業(yè)詞匯與表達(dá),消除語言障礙,完成交際任務(wù)及目的。因此,很多學(xué)者從語言的詞匯入手,對(duì)其構(gòu)成方式、特征、類別屬性等進(jìn)行分析或?qū)Ρ妊芯浚接懫渲械奶卣髋c規(guī)律。就商務(wù)漢語而言,由于漢語是我們的母語,我們對(duì)漢語詞匯構(gòu)成的偏正、動(dòng)賓、聯(lián)合等形式并不陌生,它們是主要的構(gòu)成類別,但如果進(jìn)一步研究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一些其他方面的商務(wù)詞語特征,諸如復(fù)合詞比重較高、大量縮略詞語、外來詞主要來自日本等。
1.2商務(wù)語言對(duì)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建構(gòu)的啟示
在此之后,國內(nèi)的學(xué)者為了構(gòu)建商務(wù)英語學(xué)科的學(xué)理從不同的視角進(jìn)行了探索,尤其對(duì)商務(wù)英語學(xué)科理論的上游學(xué)科學(xué)理,即商務(wù)語言學(xué)理論進(jìn)行了探討。張佐成(2008)認(rèn)為建立商務(wù)語言學(xué)將是商務(wù)英語發(fā)展的最終目標(biāo),他是從分析商務(wù)話語的角度對(duì)商務(wù)英語發(fā)展的最終歸宿畫上了商務(wù)語言學(xué)的句號(hào)。林添湖2012年在“第二屆全國商務(wù)英語學(xué)科理論研討會(huì)”上提出,商務(wù)英語學(xué)科的理論體系建設(shè)可以朝著構(gòu)建商務(wù)語言學(xué)的方向推進(jìn),并把商務(wù)語言學(xué)構(gòu)建成應(yīng)用語言學(xué)范疇內(nèi)一門完整獨(dú)立的交叉型應(yīng)用學(xué)科。在借鑒國外學(xué)者對(duì)商務(wù)語言學(xué)所下定義(Daniushina2010)并全面分析與闡述商務(wù)語言學(xué)可行性的學(xué)理基礎(chǔ)上,林添湖(2014)呼吁學(xué)界同仁關(guān)注并努力建立商務(wù)語言學(xué)本體理論體系。毋庸置疑,在商務(wù)語言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商務(wù)語言學(xué)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與垂直隸屬關(guān)系,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從這層關(guān)系和角度,商務(wù)英語學(xué)者開始尋找并構(gòu)建商務(wù)英語的核心理論支撐。國內(nèi)學(xué)者對(duì)商務(wù)語言學(xué)的建立構(gòu)思體現(xiàn)了新世紀(jì)人們對(duì)商務(wù)環(huán)境跌宕起伏所帶來的語言變化的重視,有利于開拓語言學(xué)發(fā)展的新領(lǐng)域,對(duì)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的構(gòu)建提供了新思維、新路徑。但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在目前中國環(huán)境下商務(wù)語言學(xué)的構(gòu)建包括兩大語言方向,一個(gè)是漢語方面的,一個(gè)是外語方面的,在外語多語種方向里包含英語,也就是說,商務(wù)語言學(xué)涵蓋的面非常廣,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的構(gòu)建只占商務(wù)語言學(xué)的一部分,對(duì)于我們商務(wù)英語學(xué)科的理論構(gòu)建來講,商務(wù)語言學(xué)研究的面過大過多,而作為獨(dú)立的商務(wù)英語學(xué)科,構(gòu)建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核心理論是我們面臨的主要研究課題。不過,商務(wù)語言學(xué)的發(fā)展成果又會(huì)毫無疑問地促進(jìn)與豐富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的發(fā)展,兩者關(guān)系密切,有合而不同之特點(diǎn)。
1.3目前面臨的問題
遺憾的是,目前在中國知網(wǎng)上搜索商務(wù)語言學(xué)詞條,除上面提到林添湖這方面的論文外幾乎查不到有關(guān)該詞條的相關(guān)論文,顯示該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況,而從我們商務(wù)英語目前的研究狀態(tài)、研究成果、研究進(jìn)展、研究目標(biāo)和研究人員構(gòu)成看,以我們的長項(xiàng)去開拓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理論比較適宜,可以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直接走上一條時(shí)間短任務(wù)完成快的路徑。商務(wù)語言學(xué)的構(gòu)建需要大量研究人員從事相關(guān)項(xiàng)目的研究,需要語言學(xué)界同仁的共識(shí),需要不同語種的研究者從各自的語言研究領(lǐng)域共同的參與,需要一個(gè)漫長的研究過程,更需要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作為支撐,所有這一切非英語及商務(wù)英語研究者在可見的時(shí)間內(nèi)所能完成及達(dá)到。當(dāng)然,我們希望有此能力、有此興趣、有此研究方向的英語老師積極進(jìn)行這方面的探索與研究,不過,我們歡迎并期待著有更多的漢語語言學(xué)家的參與,對(duì)商務(wù)語言進(jìn)行更深入的研究,構(gòu)建起堅(jiān)實(shí)的商務(wù)語言學(xué)理論體系,從而豐富商務(wù)英語語言學(xué)的本體理論內(nèi)核,完善學(xué)理體系。
英語口語認(rèn)知語言學(xué)啟示
從認(rèn)知心理學(xué)的角度深入探討第二語言的習(xí)得過程,從中得出對(duì)英語口語教學(xué)的一些啟示。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工具,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架起溝通的橋梁,讓不同文化的人們可以實(shí)現(xiàn)無障礙交流。因此,培養(yǎng)學(xué)生使用英語進(jìn)行交際的能力是英語教學(xué)的重中之重。但事實(shí)上,很多學(xué)生經(jīng)過十幾年的學(xué)習(xí),雖然掌握了很多的語言知識(shí)點(diǎn),但實(shí)際的語言運(yùn)用能力卻較為薄弱。認(rèn)知語言學(xué)是認(rèn)知學(xué)與語言學(xué)結(jié)合而成的新興學(xué)科。本文根據(jù)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理論來探討如何提高英語口語教學(xué)。
一、認(rèn)知心理學(xué)理論
認(rèn)知心理學(xué)理論認(rèn)為人們運(yùn)用一項(xiàng)技能時(shí),要同時(shí)處理各種信息。但由于人腦在一具體時(shí)刻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如果對(duì)一些信息的處理不夠熟悉,就會(huì)導(dǎo)致整項(xiàng)技能的運(yùn)行受挫。因此,學(xué)習(xí)一項(xiàng)技能就要通過大量的實(shí)踐,增加各個(gè)環(huán)節(jié)的熟練程度,從而使各環(huán)節(jié)協(xié)調(diào)運(yùn)行。語言與其他知識(shí)技能一樣,同屬于人類知識(shí)的范疇,因此二語習(xí)得過程同樣也可由認(rèn)知心理學(xué)理論來解釋。語言學(xué)習(xí)者如何掌握新的語言信息,理論界有兩種描述:一是控制處理與自動(dòng)處理;二是陳述性知識(shí)與程序性知識(shí)。
(一)控制處理與自動(dòng)處理
信息處理模式認(rèn)為人在處理信息時(shí),受兩種因素影響:一是人給予一項(xiàng)任務(wù)的注意力;二是處理信息的熟練程度。McLaughlin區(qū)分了兩種信息處理方式:(1)自動(dòng)處理,通過大量的實(shí)踐形成,信息的處理幾乎不需要注意力;(2)控制處理,信息的處理需要使用較大的注意力資源,而且相對(duì)較慢,但可以向自動(dòng)處理轉(zhuǎn)化。控制處理只能短暫激活記憶中選擇出來的信息節(jié)點(diǎn),通過不斷練習(xí),控制處理轉(zhuǎn)變成自動(dòng)處理,這時(shí)自動(dòng)化的技能程序才能被儲(chǔ)存在長期記憶中。當(dāng)環(huán)境需要提取他們時(shí),人們無需注意力的參與很容易就能把它們提取出來。McLaughlin認(rèn)為,一旦習(xí)得這種自動(dòng)化的技能,它就很難消失或被改變。第二語言的學(xué)習(xí)就是不斷地練習(xí),由控制過程向自動(dòng)化過程轉(zhuǎn)變。Brown試圖把McLaughlin控制處理、自動(dòng)處理和注意力這一模式應(yīng)用于解釋二語習(xí)得的諸多方面.Brown將這些最小的基本單位描述為人們對(duì)語言形式(語法、語音、語言規(guī)則等)的處理和注意,并認(rèn)為兒童二語習(xí)得完全是由集中于語言形式上的外圍,即無意識(shí)的注意(基本單位C和D)構(gòu)成。而多數(shù)成年二語習(xí)得者在課堂內(nèi)的語言形式學(xué)習(xí)需要經(jīng)過基本單位A與B和C的組合后,再過渡到D。因此,語言學(xué)習(xí)的過程就是使大量的控制處理向自動(dòng)處理轉(zhuǎn)化的過程。
(二)陳述性知識(shí)與程序性知識(shí)
Anderson指出陳述性知識(shí)是“知道是什么”,具體形式如單詞、事實(shí)、規(guī)則、一系列時(shí)間的記憶等,可以陳述出來。程序性知識(shí)是“知道怎么樣”,屬于潛意識(shí)范疇,能積極地促進(jìn)以陳述的方式儲(chǔ)存的數(shù)據(jù)與事實(shí)進(jìn)行重組。根據(jù)Anderson的理論,可以將語言學(xué)習(xí)過程分為三個(gè)階段。(1)認(rèn)知階段:語言學(xué)習(xí)者參與有意識(shí)的活動(dòng),獲得的知識(shí)在本質(zhì)上是典型的陳述性知識(shí)。(2)聯(lián)結(jié)階段:人腦努力編輯加工陳述性知識(shí),使之逐漸程序化。(3)自動(dòng)階段:語言學(xué)習(xí)者的表現(xiàn)依賴于潛意識(shí),完全或更加自動(dòng)化。Anderson認(rèn)為一語習(xí)得與二語習(xí)得的差別之一就是語言學(xué)習(xí)者所達(dá)到的學(xué)習(xí)階段不同。一語習(xí)得者達(dá)到的是自動(dòng)化階段,而二語習(xí)得者一般只達(dá)到聯(lián)結(jié)階段。雖然一些二語習(xí)得者經(jīng)過練習(xí)習(xí)得了很高程度的程序性知識(shí),但他們并沒有完全達(dá)到自動(dòng)化階段。如果第二語言教學(xué)中只是把有關(guān)的語言規(guī)則,即陳述性知識(shí),告訴學(xué)生,并不算是完成了教學(xué)任務(wù)。因?yàn)榈诙Z言習(xí)得的關(guān)鍵往往還在于如何訓(xùn)練和培養(yǎng)程序性知識(shí)。口頭表達(dá)的過程就是說話者運(yùn)用背景知識(shí)和語言知識(shí)向聽話者提供有意義的信息的過程。通常情況下,說話者說話時(shí)幾乎沒有準(zhǔn)備的時(shí)間,說話者必須在有限的時(shí)間里決定說什么、怎么說,這一切是在潛意識(shí)里進(jìn)行的。如果說話者不能迅速做出反應(yīng),即使已掌握了大量陳述性知識(shí),整個(gè)交流也無法順利進(jìn)行。因此,培養(yǎng)口語能力不能只停留在陳述性知識(shí)的層面,而應(yīng)更多地使陳述性知識(shí)逐漸程序化。因?yàn)槌绦蛐灾R(shí)可以直接操作執(zhí)行,不需要解釋和思考,即不再需要從記憶中提取有關(guān)陳述性知識(shí),記憶的負(fù)擔(dān)減輕了,操作也就熟練了。
語言學(xué)與語言教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論述
作者:陳筱靜 單位:四川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
元音、韻母與對(duì)外漢語語音教學(xué)在普通話中的韻母教學(xué)中,同樣也離不開音位學(xué)理論。如ao、a、ai、ian中的a是四個(gè)音位變體,它們的發(fā)音是有差別的,留學(xué)生的音位系統(tǒng)與漢語不同,聽覺的敏感度也不一樣,這就要求教學(xué)中重視如何既精簡又明白的對(duì)音位a及其各項(xiàng)變體進(jìn)行描述分析。發(fā)音動(dòng)作也會(huì)致使發(fā)音的失誤:在發(fā)卷舌央元音er時(shí),應(yīng)是邊卷舌邊發(fā)音,學(xué)生常常先完成卷舌再發(fā)音。復(fù)合韻母的教學(xué),常常采用兩種方法:析音法和不析音法。析音法是分音素教學(xué):ai由a和i構(gòu)成,先拼a后拼i,然后聯(lián)系起來拼合。析音法的優(yōu)點(diǎn)是分析可以形成分析音素的習(xí)慣,缺點(diǎn)是機(jī)械、割裂的學(xué)習(xí)復(fù)韻母發(fā)音。不析音的方法,如同樣是復(fù)韻母ai,直接交予學(xué)生“愛”的發(fā)音,這樣是發(fā)音整體性、協(xié)調(diào)性好,但是相當(dāng)于一個(gè)新的發(fā)音,增加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負(fù)擔(dān)。我們?cè)诮虒W(xué)中多采用不析音的方法,原因是漢語的復(fù)韻母各個(gè)音素結(jié)合十分緊密,韻頭、韻腹、韻尾不是割裂的獨(dú)立發(fā)音的,而是舌位的逐漸滑動(dòng)和口型的漸變。采用整體的發(fā)音教學(xué)幫助學(xué)生形成整體的發(fā)音概念,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比較復(fù)雜難以一步到位的描述清楚的韻母再進(jìn)一步進(jìn)行析音講解。
聲調(diào)與對(duì)外漢語語音教學(xué)漢語聲調(diào)的差別就是由嗓音高低變化而定的。如:第一聲為高平調(diào),第二聲為中升調(diào),第三聲為降升調(diào),第四聲為全降調(diào)。對(duì)外漢語語音教學(xué)中的聲調(diào)教學(xué)對(duì)于學(xué)生來說尤為困難,因?yàn)閷?duì)他們來說,聲調(diào)是一個(gè)全新的概念。以母語為英語的留學(xué)生為例,英語是以會(huì)話中的語調(diào)為基礎(chǔ)(大部分表現(xiàn)為句調(diào))而沒有聲調(diào),所以聲調(diào)學(xué)習(xí)對(duì)他們來說很是困難;同時(shí),漢語的普通話有四個(gè)聲調(diào)且都起區(qū)別意義的作用,聲調(diào)的掌握甚至比聲韻拼合的掌握更重要,因?yàn)樗苯佑绊懙浇浑H的可理解性和準(zhǔn)確性。基于這種現(xiàn)象,漢語本體論中有許多關(guān)于漢語聲調(diào)的詳實(shí)的研究分析———往年有很多的非材料性分析(理論及應(yīng)用,基于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觀點(diǎn)),近年來出現(xiàn)了較多的材料性分析(包括量化、質(zhì)化等基于材料的研究)。正是這些從具體的漢語語言學(xué)的理論角度對(duì)漢語普通話聲調(diào)不同側(cè)面的描述(包括對(duì)漢語聲調(diào)中的變調(diào)問題的研究)推動(dòng)了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實(shí)踐的進(jìn)步。
在實(shí)踐中,通常四個(gè)聲調(diào)的教學(xué)中第二聲和第三聲最難,第二聲單獨(dú)念時(shí)問題并不明顯,在詞語中卻常常升不上去被誤念為第一聲或降調(diào)。第三聲的在語流中的發(fā)音問題又多于第二聲。此問題在下文語流中的語音研究與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中有詳述。四聲的問題是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發(fā)去聲時(shí),受其母語強(qiáng)調(diào)重音的負(fù)遷移影響,愛用蠻力發(fā)去聲,用力過度,顯得很夸張。留學(xué)生側(cè)重從嗓音的強(qiáng)弱來掌握去聲,而漢語聲調(diào)中的去聲是相對(duì)音高的改變。所以留學(xué)生盡管發(fā)去聲時(shí)音高的變化基本正確,但由于按其母語習(xí)慣加重了音強(qiáng),有了突出強(qiáng)調(diào)的感覺。也就是說,學(xué)生在掌握第四聲的發(fā)音時(shí)方法不完全正確。針對(duì)聲調(diào)對(duì)留學(xué)生難學(xué)易錯(cuò)的現(xiàn)象,區(qū)別特征理論對(duì)聲調(diào)教學(xué)也有啟發(fā)作用。區(qū)別特征理論拋棄了以往把聲調(diào)進(jìn)行精確的調(diào)值描寫的方法,把普通話的陰平的特征定為高,陽平定為升,上聲定為低,去聲定為降。用這四個(gè)特征區(qū)分四個(gè)調(diào)類。由于漢語的聲調(diào)在實(shí)際的語詞中存在變調(diào)現(xiàn)象,以往的過于追求四個(gè)聲調(diào)的精準(zhǔn)調(diào)值的教學(xué)法常常使學(xué)生在實(shí)際的語流中感到運(yùn)用聲調(diào)棘手,新出現(xiàn)的區(qū)別特征理論對(duì)教學(xué)有了新的啟示。
在對(duì)外漢語語音教學(xué)實(shí)踐中,留學(xué)生對(duì)輕聲的掌握一直是一個(gè)難題。輕聲,是一種又短又輕的模糊調(diào)子,是四聲的變調(diào)。當(dāng)一種輕聲音節(jié)處在不同的聲調(diào)音節(jié)的后面,輕聲的讀音是模糊的。留學(xué)生單單從發(fā)音輕重的角度練習(xí)輕聲,總感覺無法完全正確的掌握輕聲。關(guān)于輕聲的相關(guān)研究顯示輕聲音節(jié)在不同的音節(jié)后面也有音高的差別:在上聲后面的略高于其他三聲,在去聲后面最低,在陰平陽平后面則處于中等。不僅如此,音節(jié)讀輕聲后不僅影響到聲調(diào)的調(diào)值,還會(huì)影響到聲母和韻母的音色,使之發(fā)生一定的改變。教學(xué)中側(cè)重講輕聲音強(qiáng)的改變而對(duì)不同音節(jié)后的調(diào)值的差別認(rèn)識(shí)不足,這樣常常造成學(xué)生發(fā)輕聲時(shí)會(huì)出現(xiàn)的偏誤。最近的漢語語言界也開始關(guān)注“輕聲”與“輕音”的區(qū)別。許多留學(xué)生在明確的含有輕聲的詞組中可以比較不錯(cuò)的發(fā)音。但是專家研究發(fā)現(xiàn),漢語中還有一類詞或短語,在詞典中并沒有標(biāo)注出應(yīng)予以輕讀,但在交際中卻不可以按照原來的聲調(diào)去讀,如:“妻子”“快樂”(“子”和“樂”都有輕音化的傾向,卻不如“旗子”和“快了”中的“子”和“了”輕)。同樣的拼音標(biāo)注為“jishu”的兩個(gè)詞“技術(shù)”和“計(jì)數(shù)”的“術(shù)”和“數(shù)”從聲學(xué)上的表現(xiàn)有明顯的差異。有人將這種詞典中沒有標(biāo)注出輕讀而實(shí)際讀音輕化的讀音稱為“次輕”,真正的輕聲稱為“最輕”。此類細(xì)致而詳盡的漢語本體語音研究會(huì)直接指導(dǎo)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的實(shí)踐,對(duì)于發(fā)現(xiàn)和理清留學(xué)生發(fā)音錯(cuò)誤的原因更是有直接作用。
就對(duì)外漢語而言,語言學(xué)的漢語本體論方面的深入研究為漢語教學(xué)提供的理論指導(dǎo)和研究方向。語言學(xué)理論貫穿在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和整個(gè)過程中。相關(guān)的教學(xué)人員只有在了解掌握本體論知識(shí)并通過吸收化解為通俗的課堂知識(shí)或教學(xué)技巧,才能更加有效的進(jìn)行對(duì)外漢語的教學(xué)工作。同時(shí),在具體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我們還發(fā)現(xiàn)對(duì)外漢語在教學(xué)中發(fā)現(xiàn)的許多問題也可以反過來促進(jìn)漢語及漢語語言學(xué)理論的深化發(fā)展,本文限于篇幅并未做具體的探討,但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對(duì)語言學(xué)的反作用亦不可小視。
語言學(xué)角度下語言藝術(shù)論文
一、語言運(yùn)用的特點(diǎn)
巴金先生《家》的英譯本中的語言色彩極為濃重,包含很多的語言藝術(shù),展示出了不同國家的語言在進(jìn)行轉(zhuǎn)換和翻譯的時(shí)候需要注意的一些東西,要注重語言的簡潔化、易懂化、個(gè)性化、形象化,讓翻譯的英語更通俗易懂。
1.簡潔化的語言。
與其他文體相比,小說的語言更要求簡潔化,讓讀者能夠讀懂,所以在進(jìn)行具體的闡述詞語及句子意思和語言表達(dá)的時(shí)候,簡潔化的語言可以強(qiáng)化語言的藝術(shù)效果。而且《家》這部作品是一部話劇,更要求語言的簡潔、簡短化,這樣不僅能夠節(jié)省時(shí)間,還能夠去除很多的細(xì)節(jié)性的陳詞濫調(diào)及“零碎”的詞語,讓語言的組織更為精致、簡練,通俗易懂。比如覺新和瑞鈺在新婚之夜發(fā)現(xiàn)床底下的孩子時(shí)的對(duì)話,在進(jìn)行翻譯時(shí)巧妙的運(yùn)用“sorry”這個(gè)單詞簡潔的表達(dá)出人物話語的言外之意。
2.易懂化的語言。
《家》作為一部話劇,講求的是人物的對(duì)話要呈現(xiàn)出藝術(shù)的最佳效果,因此,必須在文學(xué)表達(dá)上需要讓人物的對(duì)話讓觀眾能夠聽懂、理解的了,實(shí)現(xiàn)讀起來朗朗上口、便于記憶的語言特點(diǎn),因此需要將英語口語的易懂口語化的直觀表達(dá)效果體現(xiàn)出來,這是英譯本小說的一個(gè)尤為突出的特點(diǎn),對(duì)于話劇劇本在翻譯時(shí)要把漢語中特有的短句、諺語用易懂的語言表達(dá)出來。
3.個(gè)性化的語言。
教育語言學(xué)的超學(xué)科性
教育語言學(xué)作為一個(gè)學(xué)科領(lǐng)域肇始于上個(gè)世紀(jì)70年代,教育語言學(xué)(EducationalLinguistics)這一術(shù)語是美國語言學(xué)教授B.Spolsky在1972年哥本哈根第二屆應(yīng)用語言學(xué)年會(huì)上宣讀的一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來的,用以指語言與教育的交叉研究。Spolsky認(rèn)為教育語言學(xué)是一個(gè)以教育心理學(xué)和教育社會(huì)學(xué)為模型的術(shù)語,它描述的是語言學(xué)這一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與教育學(xué)這一實(shí)際學(xué)術(shù)職業(yè)的交叉學(xué)科。[1]P1教育語言學(xué)的研究范圍是有關(guān)教育與語言關(guān)系的所有問題,研究核心是語言在語言學(xué)習(xí)與教學(xu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是一門以問題為導(dǎo)向的學(xué)科,從語言教育實(shí)踐的實(shí)際需要出發(fā),利用相關(guān)理論與實(shí)踐學(xué)科的知識(shí)來解決語言教育者與語言規(guī)劃者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因此,教育語言學(xué)往往被看作是利用諸多相關(guān)學(xué)科如語言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教育學(xué)以及其它學(xué)科的理論和方法對(duì)教育中的語言所進(jìn)行的跨學(xué)科性研究。近年來,它更是被看作是采用生態(tài)的、超學(xué)科的研究方法對(duì)正規(guī)、非正規(guī)教育中出現(xiàn)的與語言有關(guān)的問題所作的研究。教育語言學(xué)的超學(xué)科屬性使這門學(xué)科呈現(xiàn)出更多的特點(diǎn),也為本學(xué)科今后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 一、超學(xué)科性的涵義 處于一個(gè)各種智力活動(dòng)活力發(fā)展、充滿生機(jī)的時(shí)代,教育語言學(xué)獲得了充分發(fā)展并逐漸成熟,尤其是在語言研究領(lǐng)域見證了Fisherman對(duì)語言所作的社會(huì)學(xué)研究和Hymes的交際民族志學(xué)研究,在主張消除學(xué)科之間的界限,采用整體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具體問題的學(xué)術(shù)氛圍及社會(huì)背景下,教育語言學(xué)發(fā)展成為一門以問題為導(dǎo)向,具有超學(xué)科性質(zhì)的學(xué)科領(lǐng)域。[2]P2 Spolsky認(rèn)為教育語言學(xué)雖然研究的中心是與語言有關(guān)的問題,但是必須綜合利用其它學(xué)科的研究方法才能獲得對(duì)具體問題的全面理解,也正是在這里第一次播下了教育語言學(xué)超學(xué)科性的種子。 Halliday在論述廣義的應(yīng)用語言學(xué)時(shí)也指出,要使用“超學(xué)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不是“跨學(xué)科的(interdisciplinary)”或是“多學(xué)科的(multidisciplinary)”字眼,因?yàn)楹髢蓚€(gè)術(shù)語表明研究者仍然把各學(xué)科作為進(jìn)行智力活動(dòng)的場(chǎng)所,正確的做法卻是要?jiǎng)?chuàng)造一種新的形式去取代它們,這種新的智力活動(dòng)形式,是以主題而不是以學(xué)科為導(dǎo)向的。拿外語教學(xué)來說,外語教學(xué)涉及到不止一門學(xué)科的內(nèi)容知識(shí):至少要有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和語言學(xué)。Halliday主張對(duì)外語教學(xué)進(jìn)行超學(xué)科的研究,并且指出:研究的目的不是僅僅創(chuàng)造一個(gè)具有各學(xué)科特征的智力活動(dòng)的混合體,而是要更進(jìn)一步,把各個(gè)學(xué)科有益于解決問題的因素都綜合起來,這樣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就是以主題為基礎(chǔ)的(theme-based)。他解釋說,所要解決的主題不是由內(nèi)容來決定,而是由考察問題的角度來決定。因此,在教育語言學(xué)領(lǐng)域所進(jìn)行的智力活動(dòng)的中心任務(wù)不是要去在各學(xué)科的內(nèi)容知識(shí)領(lǐng)域之間架設(shè)橋梁,而是綜合各種具體的研究工具(當(dāng)然這些研究工具往往是以各學(xué)科為基礎(chǔ)的)來共同解決一個(gè)具體的問題。 跨學(xué)科、多學(xué)科與超學(xué)科的核心的區(qū)別就是它們的出發(fā)點(diǎn)不同:在跨學(xué)科、多學(xué)科的研究中,出發(fā)點(diǎn)往往是本學(xué)科的已知知識(shí),通過在各學(xué)科之間架設(shè)橋梁來獲得對(duì)某個(gè)問題比較清楚的認(rèn)識(shí),從這個(gè)意義上講,這種方法是優(yōu)于以往從單一學(xué)科的角度去研究問題的方法的。但是,在教育語言學(xué)的超學(xué)科性的研究中,研究是從一個(gè)特定的、具體的語言與教育的主題開始的,然后利用研究者所占有的語言學(xué)及其分支學(xué)科、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教育學(xué)以及其它學(xué)科的知識(shí)資源來分析、解決它。用Halliday的話說就是,智力活動(dòng)所進(jìn)行的場(chǎng)所不是在各學(xué)科領(lǐng)地內(nèi),而是取而代之,圍繞要解決的具體語言教育問題來展開。因此,超學(xué)科研究者就像一個(gè)畫家,利用他調(diào)色盤上研究工具的不同光譜勾勒出一幅多維度的生動(dòng)畫面。 二、教育語言學(xué)超學(xué)科性所呈現(xiàn)的特點(diǎn) (一)教育語言學(xué):研究廣度與深度兼?zhèn)? 正如Hornberger所論述的那樣,從根本上說,教育語言學(xué)的特點(diǎn)就是它與很多學(xué)科關(guān)系活躍,以問題為導(dǎo)向(problem-oriented),專注教育中或與教育有關(guān)的以語言為中心的所有問題,這門學(xué)科的研究既有分析問題的廣度,又有研究的深度。[3]P17 教育語言學(xué)的核心特征就是它是語言學(xué)與其它學(xué)科的接口。正如Spolsky所講,教育語言學(xué)是從具體的問題出發(fā),然后向其它學(xué)科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它的學(xué)科范圍就是語言學(xué)以及相關(guān)語言學(xué)科與正規(guī)與非正規(guī)教育的交叉。[4]P2這門學(xué)科所探討的問題廣泛,所采用的研究工具也很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教育語言學(xué)是漫無目的地在“研究的海洋中隨意漂流”,而是它是多元中心的、多方法的和多層次的。也就是說,教育語言學(xué)研究的中心問題很多,解決它們,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教育語言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有很多涉及面廣泛的工作要做,因此這門學(xué)科的研究范圍廣泛;同時(shí),解決問題需要有專門知識(shí)的個(gè)人進(jìn)行縝密的研究,因而這門學(xué)科具有很強(qiáng)的專業(yè)性和深度。教育語言學(xué)者們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途徑進(jìn)行研究,有的關(guān)注微觀層面,有的關(guān)注宏觀,還有的介于其間,從而獲得對(duì)于個(gè)人、語言、社會(huì)和教育的一個(gè)整體的、超學(xué)科式的認(rèn)識(shí)。 實(shí)際上,Spolsky的教育語言學(xué)“以問題為導(dǎo)向(problem-oriented)”與Halliday的超學(xué)科性的“以主題為基礎(chǔ)(theme-based)”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在任一情形下,研究者都不能簡單地把各學(xué)科的知識(shí)直接應(yīng)用到具體問題中去:在教育語言學(xué)研究中,研究者從具體的一個(gè)與語言與教育有關(guān)的問題出發(fā),然后綜合利用他所擁有的知識(shí)儲(chǔ)備中的研究工具來探討問題的解決。因此,教育語言學(xué)的研究工作要在或跨越多個(gè)學(xué)科門類中去進(jìn)行,如人類學(xué)、區(qū)域研究、教育、外語、語言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等。這也正是人類語言學(xué)的先行者EdwardSpair所主張的語言學(xué)研究應(yīng)當(dāng)采取的方式,因此,從這層意義上講,教育語言學(xué)繼承了廣義語言學(xué)的研究傳統(tǒng)。例如,教育語言學(xué)世界三大流派之一的澳大利亞教育語言學(xué)流派,就牢牢抓住這門學(xué)科超學(xué)科性的特點(diǎn),采用了上述研究方法。 #p#分頁標(biāo)題#e# 總之,在教育語言學(xué)的旗幟下,普通語言學(xué)與其它社會(huì)科學(xué)如人類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教育學(xué)相結(jié)合,共同解決在正規(guī)和非正規(guī)教育中與語言習(xí)得、語言使用、社會(huì)語言環(huán)境有關(guān)的所有問題。 (二)教育語言學(xué):研究與實(shí)踐的自反性 教育語言學(xué)以主題為基礎(chǔ)的學(xué)科特征也彰顯了它的另外一個(gè)重要的特點(diǎn)——研究與實(shí)踐的自反性(research-practicereflexivity)。在教育語言學(xué)領(lǐng)域所進(jìn)行的研究不單單是為了獲取一定的知識(shí),而是要去解釋和解決在正規(guī)、非正規(guī)教育實(shí)踐中的具體問題,研究的目的是指導(dǎo)實(shí)踐,對(duì)實(shí)踐產(chǎn)生影響;然而這也是個(gè)雙行車道,正規(guī)、非正規(guī)教育的實(shí)踐活動(dòng)恰恰為研究提供了源動(dòng)力,教育語言學(xué)研究的課題并不是僅僅出自研究者的大腦,而是來自他們與語言教育實(shí)踐的緊密接觸和聯(lián)系。在教育語言學(xué)中,研究與實(shí)踐相互依靠,互通有無,共同發(fā)展。 從一開始,教育語言學(xué)就關(guān)注教育中影響語言使用因素的研究,目標(biāo)就是構(gòu)建一個(gè)有關(guān)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關(guān)系的一個(gè)完整的、系統(tǒng)的知識(shí)體系,以推動(dòng)從語言習(xí)得到語言計(jì)劃等各方面的發(fā)展。很顯然,孤立一門學(xué)科的努力是無法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的,因此,教育語言學(xué)將繼續(xù)沿著超學(xué)科的研究路子走下去,不受制于學(xué)科門類的界限,全心全意致力于它所要解決的問題。 三、超學(xué)科性對(duì)教育語言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的指導(dǎo)—生態(tài)研究的美好前景 作為一個(gè)具有超學(xué)科性質(zhì)的學(xué)科領(lǐng)域,教育語言學(xué)應(yīng)該把語言學(xué)各方面與其它社會(huì)科學(xué)相結(jié)合,然而遺憾的是,正如Gee所提醒我們的那樣,目前來看,語言學(xué)對(duì)教育施加的影響遠(yuǎn)遠(yuǎn)不夠,教師們對(duì)語言及語言學(xué)知識(shí)的了解程度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現(xiàn)今教育中語言研究的發(fā)展水平。 Gee在論述了功能語言學(xué)和生成語言學(xué)理論各自在主要教育領(lǐng)域所起到的作用后,舉例說明了一些我們對(duì)教育中的語言的確已達(dá)到的認(rèn)識(shí),包括:要關(guān)注語言在幫助孩子獲得一種學(xué)術(shù)語言新形式中所起的作用,教師需要理解學(xué)生帶到課堂上的不同的語言與文化資料,以及了解語言的形式與意義在課堂交往中的相互作用。正如他的教育語言學(xué)前輩一樣,Gee主張我們要在已知語言學(xué)知識(shí)應(yīng)用到實(shí)踐中做出更大的努力。人類語言學(xué)家DellHymes也支持這一觀點(diǎn),他之所以擔(dān)任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教育研究院的院長,是因?yàn)樗羁痰卣J(rèn)識(shí)到:需要改變我們對(duì)語言的看法,以及探討我們應(yīng)該如何對(duì)待學(xué)校中的語言。 世界人口的日益多語化,使世界教育體系承受了更大的壓力;在多語主義、多元文化日益顯示出其社會(huì)與經(jīng)濟(jì)優(yōu)越性的今天,研究語言與教育的關(guān)系變得異常重要;語言與教育的關(guān)系越復(fù)雜,所要進(jìn)行的研究也就越復(fù)雜,超學(xué)科的研究也就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重要。雖然,教育語言學(xué)在建立之初就是沿著這樣的一個(gè)路子在走,但是要建立一個(gè)真正統(tǒng)一、一致的知識(shí)體系,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教育語言學(xué)家們也都一致認(rèn)為:教育肩負(fù)著“培養(yǎng)語言恰當(dāng)性”的一份社會(huì)責(zé)任,但是,如何在大規(guī)模的水平上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目標(biāo),現(xiàn)在還缺乏戰(zhàn)略性的對(duì)話,教育語言學(xué)似乎還缺乏一個(gè)清晰的發(fā)展路線。教育語言學(xué)要成為一門系統(tǒng)的專注語言與教育所有問題的學(xué)科,就應(yīng)該去認(rèn)真探討個(gè)人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無論從微觀、從中間、還是從宏觀的層面。如此一來,生態(tài)研究的方法在這個(gè)領(lǐng)域?qū)?huì)有很好的前景。 雖然,生態(tài)研究在社會(huì)科學(xué)中已不新鮮,但只是近來才在教育語言學(xué)領(lǐng)域顯現(xiàn)其重要性。生態(tài)研究的方法已越來越多地應(yīng)用于語言學(xué)各方面的研究,從個(gè)人層次的語言習(xí)得到課堂教學(xué)法再到語言政策的制定,比如,Leather和VanDam的EcologyofLanguageAcquisition也是Kluwer教育語言學(xué)系列的首部集合了語言習(xí)得語境因素研究的作品,另外,Hornberger的“ContinuaofBiliteracy:AnEcologicalFrameworkforEducationalPolicy,Research,andPracticeinMultilingualSettings”一文,強(qiáng)調(diào)了多層次的分析方法在建構(gòu)、實(shí)施和評(píng)估雙語、多語教育計(jì)劃中所起到的作用。這些成果反映了生態(tài)研究的不同側(cè)面,但有一點(diǎn)是一致的:對(duì)于語言與教育的任何方面,孤立的研究都不會(huì)達(dá)到有效的結(jié)果。從這個(gè)意義上講,生態(tài)研究在超學(xué)科的教育語言學(xué)研究中將會(huì)占據(jù)中心位置。 與早先談到的教育語言學(xué)的核心特點(diǎn)相一致,教育語言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所進(jìn)行的生態(tài)研究也是以問題為導(dǎo)向和超學(xué)科性的,以主題為中心的整體觀將推動(dòng)這門學(xué)科扎實(shí)向前邁進(jìn),同時(shí)也堅(jiān)定了它借鑒多學(xué)科來全面探討語言在教學(xué)與學(xué)習(xí)中作用的決心。總之,教育語言學(xué)在其不長的發(fā)展歷史中,一定會(huì)堅(jiān)持其核心原則,同時(shí)又會(huì)不斷滿足持續(xù)變化世界中研究與實(shí)踐的實(shí)際需要。
語言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論文
一、語言應(yīng)用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實(shí)踐
祝克懿《互文性理論的的多元思維特征》首次將互文性理論中“多元”思維特征作為與“互動(dòng)”并列的思維特征提取出來,對(duì)其進(jìn)行論證分析,從語篇語言學(xué)的系統(tǒng)、關(guān)系、層級(jí)觀等角度切入,深入討論了互文性理論的多元思維特征。聶仁發(fā)《有關(guān)語篇結(jié)構(gòu)的幾個(gè)概念》將語篇的宏觀結(jié)構(gòu)分為基于內(nèi)容的事理結(jié)構(gòu)、主題結(jié)構(gòu)、文體結(jié)構(gòu)和基于形式的普遍結(jié)構(gòu),并簡略探討了這幾種結(jié)構(gòu)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施麟麒《孟子的話語理解觀———“以意逆志”新解》對(duì)孟子關(guān)于話語理解的名言“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作了較詳盡的考辨分析。楊亦鳴《言語障礙的神經(jīng)機(jī)制研究》介紹了神經(jīng)語言學(xué)與言語障礙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歷史,并從中英文閱讀障礙跨文化對(duì)比、漢語成年口吃者詞匯加工的ERP研究、語音與聾人詞匯閱讀三個(gè)方面展示了語言學(xué)與科技結(jié)合的良好前景。李怡《跨文化語用研究語料收集方法———觀察記錄vs角色扮演》以漢英“請(qǐng)求”言語行為跨文化對(duì)比研究為例,探討了觀察記錄和角色扮演作為語料收集的兩種方法收集的語料差異、各自的優(yōu)劣及適用領(lǐng)域。周毅《社會(huì)符號(hào)學(xué)視野下文人畫語篇結(jié)構(gòu)及成因》從語言符號(hào)、視覺符號(hào)與社會(huì)文化情景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來探究文人畫。周明強(qiáng)《埋怨性話語標(biāo)記語語用功能探析》討論了埋怨性話語標(biāo)記(如“真是的”“、何必呢”等)的語用功能。
二、漢語國際教育的學(xué)科建設(shè)、漢語研究和教學(xué)法
崔希亮《漢語國際教育的理論與實(shí)踐》圍繞著漢語本體、教師、學(xué)生、技術(shù)保障、基礎(chǔ)研究與應(yīng)用研究五個(gè)方面,結(jié)合豐富生動(dòng)的案例闡述了這個(gè)學(xué)科目前面臨的理論和實(shí)踐問題。周小兵《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yè)學(xué)位與應(yīng)用語言學(xué)》分析了漢語國際教育人才培養(yǎng)現(xiàn)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研究生培養(yǎng)與學(xué)科發(fā)展等重要問題,介紹了中山大學(xué)國際漢語學(xué)院近年在該領(lǐng)域的拓展。王建華《語言經(jīng)濟(jì)學(xué)視野下的漢語國際教育》認(rèn)為漢語不僅是一種人力資源,也是一種經(jīng)濟(jì)資源;漢語國際教育不僅是一項(xiàng)語言文化事業(yè),也具有相當(dāng)重要的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價(jià)值。陸儉明《要加強(qiáng)語言信息結(jié)構(gòu)的研究———重新認(rèn)識(shí)“把”字句》以語言信息結(jié)構(gòu)理論為依據(jù),針對(duì)以往“把”字句教學(xué)中的釋義局限,重新定義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及對(duì)漢語國際教育句法教學(xué)的功用。馬真《要加強(qiáng)詞語的用法研究》以副詞“按說”、狀態(tài)詞“好端端(的)”、“反而”、“一概”等為例,指出外國留學(xué)生詞語偏誤出現(xiàn)的部分原因,是詞語用法研究的缺位和辭書注釋的缺陷(缺乏語義背景),強(qiáng)調(diào)了加強(qiáng)詞語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稅昌錫《面向第二語言教學(xué)的漢語體標(biāo)記事態(tài)分布研究》梳理了“了”、“著”、“過”等體標(biāo)記教學(xué)的歷史,借用過程哲學(xué)將事件看作隨時(shí)間展開的動(dòng)態(tài)過程,建立了一個(gè)事件過程的事態(tài)結(jié)構(gòu)模型。吳應(yīng)輝《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xué)的現(xiàn)狀、特點(diǎn)與思考》全面介紹了沉浸式語言教學(xué)的概念和歷史、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xué)發(fā)展現(xiàn)狀、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xué)的主要特點(diǎn)。嚴(yán)慧仙《文化認(rèn)同的多模態(tài)話語分析及其對(duì)跨文化能力培養(yǎng)的啟示———以〈舌尖上的中國〉為例》以多模態(tài)話語分析為理論框架,從文字、畫面、聲音三個(gè)方面對(duì)《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及加長版宣傳片的多模態(tài)文本進(jìn)行解碼,解讀該片所表達(dá)的文化認(rèn)同特征。沈陽《關(guān)于漢語規(guī)范化的若干問題》闡述了漢語規(guī)范化的理論問題,也對(duì)當(dāng)下語言生活實(shí)踐出現(xiàn)的不規(guī)范亂象進(jìn)行了批評(píng)。胡云晚《政府門戶網(wǎng)站背景下的語言規(guī)范觀》通過對(duì)浙江省101個(gè)地級(jí)市、市轄區(qū)、縣級(jí)市、縣、自治縣政府門戶網(wǎng)站的語言監(jiān)測(cè)表明,政府門戶網(wǎng)站語言失范率奇高,遠(yuǎn)大于傳統(tǒng)紙質(zhì)媒介。并提出要實(shí)現(xiàn)政府語言的規(guī)范表達(dá)的相關(guān)策略。趙翠陽《異形詞社會(huì)使用調(diào)查與〈現(xiàn)代漢語詞典〉兩版整理規(guī)范研究》通過對(duì)北大的CCL語料庫(現(xiàn)代漢語)、人民網(wǎng)語料以及國家語委的現(xiàn)代漢語語料庫的語料考察,整理分析了四類異形詞。楊同用《詞的功能與語文詞典的詞性標(biāo)注和釋義》著重對(duì)詞的功能與詞性的關(guān)系、功能變化與詞義的關(guān)系、詞的功能變化對(duì)語文辭書詞性標(biāo)注和釋義的影響等進(jìn)行了討論。
三、結(jié)語
綜觀論文的研究議題,可以梳理出應(yīng)用語言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的一些重要特點(diǎn):一是“言(研)以致用”。應(yīng)用語言學(xué)的研究滲透了服務(wù)國家、服務(wù)社會(huì)、關(guān)注語言生活的意識(shí)。二是“學(xué)術(shù)無疆”。應(yīng)用語言學(xué)學(xué)科的研究具有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視野;學(xué)術(shù)研究需要多學(xué)科的交流互動(dòng)。三是“學(xué)科有界”。應(yīng)用語言學(xué)雖然多以實(shí)際的語言問題的研究為出發(fā)點(diǎn),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缺乏理論。本次論壇的議題似乎是學(xué)者們約定俗成的一個(gè)自然疆界,其背后的學(xué)理依據(jù),為進(jìn)一步規(guī)整學(xué)科的研究任務(wù)和范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作者:施麟麒 單位:浙江科技學(xué)院應(yīng)用語言學(xué)研究中心
模糊性語言學(xué)的文學(xué)鑒賞
一、兩點(diǎn)理論性的說明 (一)、關(guān)于模糊性和模糊理論的重要性。 模糊理論和模糊語言學(xué)中的“模糊”決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邏輯意義上的“含混”、“不明確”、“含混不清”等等,它是新興學(xué)科的科學(xué)術(shù)語。語言模糊性的研究催生了模糊集合論,正如美國模糊數(shù)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L•A•札德所說:“模糊集合論這個(gè)分支的起源是從語言學(xué)方法的引入開始的,它轉(zhuǎn)而又推動(dòng)了模糊邏輯的發(fā)展”。我國著名數(shù)學(xué)家汪培莊教授指出:“許多卓越的語言學(xué)家紛紛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語言模糊性的研究……它的意義遠(yuǎn)遠(yuǎn)超出一個(gè)學(xué)科的范圍。電子計(jì)算機(jī)在計(jì)算速度和存儲(chǔ)功能方面遠(yuǎn)遠(yuǎn)超過人腦,但其智能水平對(duì)于人腦而言卻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現(xiàn)有的計(jì)算機(jī)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如人的大腦?最重要的一個(gè)區(qū)別便是:人腦能夠理解和執(zhí)行模糊的語言,而計(jì)算機(jī)則不能。 深入研究和剖析人類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及人腦的運(yùn)用功能,使之移植于電子計(jì)算機(jī)及其人工語言中去,是提高計(jì)算機(jī)智能的關(guān)鍵。這是與信息革命直接相關(guān)的重大歷史課題。”我國著名學(xué)者北京大學(xué)季羨林教授早在1993年就指出:“現(xiàn)在大家公認(rèn),21世紀(jì)將是語言學(xué)和生物學(xué)的世紀(jì)。語言學(xué)的研究關(guān)系到我們國家的建設(shè),關(guān)系到人類發(fā)展的前途……當(dāng)務(wù)之急就是要投資開展語言學(xué)的研究。對(duì)當(dāng)前國際上一些流行的語言學(xué)學(xué)派,比如模糊語言學(xué)等等,都要認(rèn)真加以研究。”[1] (二)、我國著名語言學(xué)家、北師大伍鐵平教授 在上世紀(jì)80年代率先把模糊語言學(xué)引進(jìn)我國,并作了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卓著,[2]他在專著《模糊語言學(xué)》中這樣說道:“日本人素以引進(jìn)外國理論并迅速將其運(yùn)用于生產(chǎn)著稱,從80年代初,日本多家大公司積極地投身于模糊理論的研究。1985年日本首先生產(chǎn)出技術(shù)上最著名的樣品:仙臺(tái)市用模糊計(jì)算機(jī)控制的地鐵;接著日本將模糊邏輯運(yùn)用于100多項(xiàng)新領(lǐng)域,包括模糊自動(dòng)調(diào)檔和防滑的煞車系統(tǒng),模糊自動(dòng)調(diào)焦的照相機(jī),……美國也正在迎頭趕上,正在設(shè)計(jì)一種模糊控制器以幫助宇航員在太空駕駛航天飛機(jī);設(shè)計(jì)一種模糊計(jì)算機(jī)芯片,每秒鐘能完成28600次模糊邏輯推導(dǎo)。”[3]由此可見,模糊性和模糊理論在推動(dòng)世界科學(xué)技術(shù)蓬勃發(fā)展和提高社會(huì)生產(chǎn)力方面所發(fā)揮的巨大作用。 本文旨在探討詞義模糊性及模糊理論對(duì)社會(huì)交際所起的積極作用以及在語言教學(xué)、修辭活動(dòng),特別是在文學(xué)鑒賞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關(guān)于詞義的模糊性 詞義對(duì)客觀事物和現(xiàn)象的反映是概括的反映。 所謂概括,是指人腦的思維活動(dòng)對(duì)某一類事物,某一類現(xiàn)象抽象出它們之間共同的、區(qū)別于另一類事物或現(xiàn)象的本質(zhì)特征。換言之,詞義對(duì)客觀事物、現(xiàn)象的概括是經(jīng)過從具體到抽象,從復(fù)雜到簡單,832005年第1期學(xué)術(shù)問題研究AcademicResearch從特殊到一般的認(rèn)識(shí)提煉的全過程。而這種抽象的、簡單的、一般的東西,本身往往缺少明確的界限,只有一個(gè)大致的范圍,這就必然使詞義產(chǎn)生了模糊性。 詞義的模糊性實(shí)質(zhì)上也就是詞義所概括的客觀事物、現(xiàn)象、性狀等本身界限不清在語言詞匯系統(tǒng)中的反映。例如論及人的容貌“美”與“丑”就很難定出一個(gè)公認(rèn)的精確的量化標(biāo)準(zhǔn)。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描繪女子的美,大都只能借助于映襯、比喻等來渲染美人的姿色,例如唐人崔護(hù)的詩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白居易《長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芙蓉如面柳如眉,對(duì)此怎能不淚垂”,以及成語的“傾國傾城”、“天姿國色”、“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花容玉貌”、“冰肌玉骨”、“明眸皓齒”、“雪膚花貌”等等,這些詩句和成語雖然都比較形象,生動(dòng)地體現(xiàn)了“美”這個(gè)概念,但是如果離開具體的文學(xué)表現(xiàn)手法作為“美”這個(gè)詞的意義,依舊是沒有精確的邊緣的,其中也包含著人的主觀性,同樣一個(gè)人,一種事物,有可能張三覺得美,李四并不覺得美,否則俗話里就不會(huì)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這一說法了。關(guān)于詞義模糊性的例子,只要你留心觀察,在日常生活中是俯拾即是的。 我國第一位引進(jìn)模糊語言(含模糊詞義)理論的伍鐵平教授在他的專著《模糊語言學(xué)》(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指出,在人類語言中,許多詞語所表達(dá)的概念都具有模糊性。“夜間”、“白天”、“早晨”、“上午”、“中午”、“下午”等都是具有模糊性的。“早晨”同“上午”、“下午”同“傍晚”、“傍晚”同“夜晚”之間都很難找到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就是這樣一條模糊界限,在不同語言之間差別還很大。說現(xiàn)代漢語普通話的人所理解的‘早晨’的下限一般到8—9點(diǎn)鐘,歐洲許多語言中從黎明一直到上午11點(diǎn)或12點(diǎn)以前都可以稱作morning(英)”[4]難怪乎英美人士到了接近午餐時(shí)間還用goodmorning互相打招呼。漢語的“傍晚”,是指“臨近晚上的時(shí)候”,也是個(gè)相當(dāng)?shù)湫偷哪:拍?首先要確定“晚上”是從什么時(shí)候開始計(jì)算,是下午五點(diǎn)、六點(diǎn),還是七點(diǎn)開始?這個(gè)切線是很模糊的;其次,假設(shè)這個(gè)切線是下午六點(diǎn)鐘,那么“臨近”也是個(gè)模糊概念,是從下午四點(diǎn)鐘算起,還是五點(diǎn)鐘算起等等,這第二條切線的起點(diǎn)也是相當(dāng)模糊的。有人認(rèn)為“中國人所說的‘傍晚’只能到天黑以前”[5]這種說法和《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對(duì)“傍晚”的釋義“臨近晚上的時(shí)候”本質(zhì)上說是一樣的,是精確的,具有概括性,正因?yàn)橛懈爬ㄐ?所以必定具有有模糊性,非模糊不能成其概括,因?yàn)?ldquo;傍晚”這個(gè)時(shí)間概念本來就沒有十分明確的界限,再加上中國疆域遼闊,全國各地“天黑”早晚的時(shí)間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地方不同季節(jié)天黑的時(shí)間也會(huì)有所變化。#p#分頁標(biāo)題#e# 三、詞義的模糊性和言語交際 詞義的模糊性是否會(huì)影響社會(huì)交際的正常進(jìn)行呢?不。詞義的模糊性并不會(huì)成為言語交際中的消極因素,它不但不會(huì)影響語言的社會(huì)功能,相反,在人們的社會(huì)交際活動(dòng)中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協(xié)調(diào)作用。 因?yàn)樵~義的模糊性就好像學(xué)校里給學(xué)生評(píng)定的學(xué)習(xí)成績,有“優(yōu)”、“良”、“及格”、“不及格”,一般說來,很難確定這幾個(gè)等級(jí)之間的確切界限。一個(gè)詞的意義所概括的事物或現(xiàn)象大致有個(gè)范圍,其核心部分是明確的,憑著這一點(diǎn),人們就可以把甲事物(或現(xiàn)象)同乙事物(或現(xiàn)象)區(qū)別開來。譬如“上午—下午—晚上”,雖然邊緣部分缺少明確的界限,但是詞義所要概括的核心部分,即大體范圍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人們注意的重心,是便于給現(xiàn)實(shí)現(xiàn)象分類的,從而能夠適應(yīng)社會(huì)交際的需要。同時(shí),詞義的模糊性使詞義所概括的事物、現(xiàn)象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這一點(diǎn)對(duì)交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每個(gè)詞的意義都有確切的界限,丁是丁,卯是卯,那樣社會(huì)交際必將寸步難行。例如,如果確定一個(gè)人身高要達(dá)到1.75米才算“高”,豈不是要讓說話人帶一把卷尺,把人的身高量出一個(gè)精確的數(shù)字之后,才能說某人是“高”,還是“不高”,或是“矮”的?又如“老”一詞,《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言研究所編,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版)釋義是“年歲大(跟‘少’或‘幼’相對(duì))”,這里年歲大的“大”也是個(gè)模糊概念,多少歲才算“年歲大”,詞典不作明確規(guī)定是有道理的。有人認(rèn)為六十歲算年老(男性退休年齡),那么差兩個(gè)月六十歲,乃至差三天六十歲就不算“老”,非得等到滿六十歲才算老,那樣,交際的進(jìn)行就相當(dāng)困難了。我們?cè)趫?bào)刊雜志上不是常常看到這樣的詞語———(某某人)“五十開外的老人”嗎?有些地方舊俗以男人五十歲、女人四十五歲為“上壽”(達(dá)到壽數(shù)),意謂人若在這樣的歲數(shù)死去就不算夭折了。俗語還有“年滿半百,半截入土”的說法,也說明在舊風(fēng)俗、舊觀念中五十歲就算“老”了。“老”(衰老)是一種生理現(xiàn)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的客觀規(guī)律。但應(yīng)該說這種現(xiàn)象本身也是沒有明確的界限的,它隨著各人所處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社會(huì)制度、生活條件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換言之,是因時(shí)、因地、因人而異的。可見對(duì)“老”不可能人為地定一個(gè)絕對(duì)精確的界線,至于退休年齡的規(guī)定,那是國家為了行政法規(guī)的實(shí)施而制定的。就是這種規(guī)定,不同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職業(yè)、不同工種也會(huì)有所差異。詞典對(duì)“老”的釋義體現(xiàn)了客觀現(xiàn)實(shí)現(xiàn)象的這種模糊性,所以說它是精確的,能夠適應(yīng)千變?nèi)f化的社會(huì)事物和現(xiàn)象的稱謂與表達(dá)的需要。 詞義的模糊性不僅使詞———語言符號(hào)能產(chǎn)生較強(qiáng)的概括性和靈活性,使之靈巧而便捷地服務(wù)于人們的社會(huì)交際,而且便于語言教學(xué)、詞典釋義,以及造成修辭上的表達(dá)手段,增強(qiáng)文學(xué)作品的藝術(shù)感染力和語言表現(xiàn)力。譬如,在語文教學(xué)中我們常常遇到“半”字的釋義問題,詞典釋義是“二分之一;一半”,看起來似乎是比較精確的,其實(shí)也是個(gè)模糊概念,特別是在語用的場(chǎng)合(包括構(gòu)成成語和作家創(chuàng)作等),例如“下半旗”中的“半”,并非“二分之一”、“一半”所能解釋的,而是“先將國旗升至桿頂,再降至離桿頂占全桿三分之一的地方”(《現(xiàn)代漢語詞典》)。詩句“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杜甫《贈(zèng)衛(wèi)八處士》)、“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前者“半為鬼”是說“故舊親友大半死亡”[6],這和后者“半遮面”的“遮面部分”都不可用“二分之一”,或“一半”這樣明確的界限去衡量,去界定,其中都存在著詞義的模糊性。同樣,“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半”也存在這種模糊性。又如四字語式中的“半信半疑”、“半推半就”等等都是如此。類似這樣的語言現(xiàn)象都只能用詞義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論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7]四、詞義模糊性的修辭功能及文學(xué)鑒賞價(jià)值詞義的模糊性還可以幫助人們理解模糊詞語的模糊性質(zhì)及其在修辭活動(dòng)中的意義和文學(xué)作品鑒賞的價(jià)值。“由于日常生活用語中模糊詞語很多,以致精確的數(shù)字語言一旦進(jìn)入日常生活用語之后,不少都變成了模糊語言。例如‘三寸不爛之舌’中的‘三寸’就是從精確詞變?yōu)槟:~,因?yàn)樯囝^不能準(zhǔn)確到恰好是三寸長。漢語的‘一’、‘三’、‘百’、‘千’、‘萬’等數(shù)詞在詩歌和成語中用得很多,經(jīng)常用來表示模糊概念。”[8]在古代漢語里“三”和“九”往往不是具體的、精確的數(shù)字,而是泛指數(shù)量之多。例如,“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rdquo;(《論語》),“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此外,精確詞的模糊概念還可以解釋日常生活和文學(xué)作品中看來似乎不合邏輯的詞語運(yùn)用問題,例如,開會(huì)時(shí)有人說:“我也來說兩句……”,其實(shí)他一說起來就滔滔不絕,海闊天空,一說就是近一個(gè)小時(shí)。 這里“兩句”就是從精確詞轉(zhuǎn)變?yōu)槟:~,其特點(diǎn)是以少代多;也有以多喻少的,例如《千家詩》是舊時(shí)“家傳戶誦”的一種幼童啟蒙讀物,取名“千家”,琢磨起來有些嚇人,因?yàn)槿珪赵妰H二百多首,入選詩人也不過數(shù)十人,何來“千家”?這應(yīng)該說也是數(shù)詞的模糊性在起作用。又如“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fēng)不度玉門關(guān)”(王之渙《出塞》詩),有人認(rèn)為“事實(shí)上玉門關(guān)外還是有春天的”[9],何以說“春風(fēng)不度玉門關(guān)”呢?通常說法是修辭和邏輯發(fā)生矛盾時(shí),后者服從前者。從模糊語言學(xué)看,特定語境使動(dòng)詞“度”在肯定和否定之間產(chǎn)生模糊性,由邏輯意義上的“度”向修辭意義上的“不度”過渡,從而造成修辭上的“夸張”辭格,在人們想象中古代玉門關(guān)以外,一片荒涼地帶,人跡罕至,荒無人煙,簡直是連“春風(fēng)”也“不度”“玉門關(guān)”了。此外,數(shù)詞運(yùn)用中的“權(quán)變”現(xiàn)象,例如以約數(shù)代實(shí)數(shù),以及數(shù)詞的虛指用法等也都是詞語的模糊性質(zhì)在起作用。膾炙人口的唐詩選本《唐詩三百首》,實(shí)際上收詩三百十首,司馬遷《報(bào)任安書》:“《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中說(《詩經(jīng)》)“三百篇”,實(shí)際上是三百零五篇。[10]曾經(jīng)有一位中學(xué)老師拿《木蘭辭》中說到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時(shí)間前后不一致的句子來問筆者:該如何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語言現(xiàn)象———“將軍百戰(zhàn)死,壯士十年歸。”“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一處說是“十年”,另一處卻說的是“十二年”,該如何解釋呢?其實(shí),作為文學(xué)作品,這里并沒有矛盾,傳統(tǒng)說法是以定數(shù)代不定數(shù),是一種借代的修辭方式。從模糊語言學(xué)看來,是精確詞表示模糊概念,從而構(gòu)成修辭上的借代用法,極言木蘭代父從軍、效命疆場(chǎng)時(shí)間之漫長。#p#分頁標(biāo)題#e# 模糊詞語還可以構(gòu)成修辭上的婉曲辭格,表達(dá)委婉的思想感情,因?yàn)槲裢墙⒃谠~義的模糊性基礎(chǔ)上的。例如白居易《長恨歌》中的詩句“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明明說的是唐玄宗的故事,卻要托詞“漢皇”,明明是唐玄宗納自己的兒媳婦、壽王之妻為貴妃,白居易在《長恨歌》里卻說“楊家有女初長成,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shí)”,把楊貴妃美化成純潔的少女,這就是修辭上的婉曲手法,有意不直接說明某事物,用婉轉(zhuǎn)的語言曲折地表達(dá)自己的思想,古人對(duì)于君父尊長的所作所為不敢直說,只能委婉曲折地來表達(dá),所謂“為尊者諱”。白居易在創(chuàng)作《長恨歌》的時(shí)候,雖然安史之亂早已過去,但他畢竟是唐朝人,所以創(chuàng)作的時(shí)候還是委婉一些的好,他的委婉說法也是建立在模糊語言的基礎(chǔ)上,“漢皇”、“人未識(shí)”等精確詞語變?yōu)槟:~語。以上所述都說明了詞義的模糊性可為文學(xué)作品中修辭婉曲手法的運(yùn)用奠定基礎(chǔ),并開拓廣闊的語義領(lǐng)域。總之,模糊語言和詞義的模糊性在幫助人們正確理解與鑒賞文學(xué)作品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除了以上所述,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進(jìn)行探討。 (一)詞義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論可以幫助人們領(lǐng)悟詩人、文學(xué)家在創(chuàng)作時(shí)錘煉詞語的“得體性”。 呂叔湘先生在王希杰著《漢語修辭學(xué)》(北京出版社,1983)《序》中,在充分肯定該專著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后指出:“我覺得稍微有點(diǎn)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說明有一個(gè)原則貫穿于一切風(fēng)格之中……,這個(gè)原則可以叫做‘適度’,又可以叫做‘恰當(dāng)’。”呂叔湘先生所說的“適度”、“恰當(dāng)”,主要就是指文學(xué)作品中詞語運(yùn)用的“得體性”,“得體性”是當(dāng)代修辭學(xué)的最高原則。[11]詞語的運(yùn)用貴在“得體”、適度”、“恰當(dāng)”,而不在于堆砌詞藻;搜索枯腸,標(biāo)新立異的結(jié)果,只能是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古人對(duì)詞語的錘煉(即“煉字”),目的在于尋求恰當(dāng)?shù)脑~語,以便生動(dòng)、貼切、形象而新鮮地創(chuàng)造意境和表達(dá)思想感情。所謂“一字未安,繞室終日”,就是這個(gè)道理。模糊語言和詞義的模糊性為詞語錘煉的“得體性”提供了選擇與恰當(dāng)運(yùn)用的可能性。例如“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jìng)自由。”(《沁園春•長沙》)其中“翔”字本指“飛”、“盤翔地飛”(《現(xiàn)代漢語詞典》),由于詞義的模糊性,在語用的特定場(chǎng)合作者完全可以根據(jù)表達(dá)的需要作詞語搭配上的靈活處置,打破空間局限,將天空和水里兩相貫通起來,“魚翔淺底”顯得新鮮活脫,形象而逼真地描繪出水底游魚自由自在的令人羨欣的游姿,別有韻味,并配合“鷹擊長空”句,使景物描寫從上到下,從空中到水里,渾然一體,自然而貼切地融入“萬類霜天競(jìng)自由”的畫面中,讓讀者如臨其境,收到了感人至深的藝術(shù)效果。又如“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yuǎn)近高低各不同。不識(shí)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詩)這里“橫”、“側(cè)”、“遠(yuǎn)近高低”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詞語,這些模糊詞語由于運(yùn)用恰當(dāng)、“適度”、“得體”,就像“出水芙蓉去雕琢”,別具一格地描繪了廬山的形象,表達(dá)了作者身處廬山中的感受,從而在深層次上揭示了一個(gè)哲理:只有不被各種表面現(xiàn)象所迷惑,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這是一首傳誦千古的說理詩,[12]給讀者以藝術(shù)上的享受,又可獲得哲理上的啟迪。 (二)詞義的模糊性使詞語在語用中的意義,即語境義(或曰言語義)往往比詞語的詞典義(即語言義)要豐富得多,因而便于作家利用模糊詞語或精確詞語的模糊概念來創(chuàng)造意境,表達(dá)情感,從而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感人至深的藝術(shù)魅力。例如①“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shí)照我還?”(王安石《瓜州夜泊》詩),②“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fù)舊池臺(tái);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陸游《沈園》詩)。這里例①和例②的“綠”字作為顏色詞,也是模糊詞,[13]然而這兩個(gè)“綠”字所透露出的色彩和思想感情卻是截然不同的,例①的“綠”是暖色的,鮮明地表現(xiàn)了春到江南大地?fù)Q上新裝時(shí)一派郁郁蔥蔥、生機(jī)勃勃的喜人景象。例②的“綠”,則是冷色的,人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到沈園舊地重游時(shí),思念前妻,緬懷往事,心中無限凄傷的思想感情。模糊詞“綠”,雖然所描寫的也是春天的景物(“春波”),然而所透露出的色彩卻是暗淡的,落寞傷感的,從而抒發(fā)了作者心中無限沉痛和悵惘的思想感情。 (三)詞義的模糊性如前所述由于其所概括的客觀事物、現(xiàn)象的核心部分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便于給現(xiàn)實(shí)現(xiàn)象分類的,而邊緣部分則不是很清晰的,往往沒有一個(gè)精確的界限,這樣,在文學(xué)作品中,模糊詞語的恰當(dāng)運(yùn)用,可以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往往言有盡而意無窮,讓讀者獲得藝術(shù)上的享受。 例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dú)愴然而淚下。”(陳子昂《登幽州臺(tái)歌》),其中“前”、“后”兩個(gè)反義的模糊詞對(duì)舉使用[14],由于語言對(duì)稱機(jī)制的作用[15],“前”、“后”這兩個(gè)模糊詞發(fā)揮了更好的作用,給讀者留下無限想象的空間和回味的余地,在歷史事件的時(shí)間跨度上產(chǎn)生了很強(qiáng)的靈活性,“前不見古人”中的“古人”既可以理解為戰(zhàn)國時(shí)代的燕昭王,也可以是既指燕昭王,同時(shí)也前推及“古代的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我們不必十分拘泥”,[16]所謂“我們不必十分拘泥”正是由于詞義的模糊性使之然。《三國演義》中寫諸葛亮祭拜周瑜時(shí)“祭文”中有這樣兩句“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始”、“終”這兩個(gè)反義的模糊詞對(duì)舉使用,囊括了周瑜短暫而不平凡的一生,讓讀者仿佛看到青年儒將周瑜一生奮斗不息的身影(雄姿英發(fā))。又如“雕欄玉砌應(yīng)猶在,只是朱顏改”(李煜《虞美人》)這里的“朱顏”,精確詞語的模糊概念,增強(qiáng)了表意的靈活性,豐富了語境義,它既指“紅潤的臉色”(意謂如今變得憔悴了),也指故國宮殿的面貌(意謂不幸江山易主)。#p#分頁標(biāo)題#e# 正如清•王運(yùn)所指出的“朱顏本是山河,因歸宋不敢言耳”[17]。“朱顏改”和末尾兩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幾多愁”,其中“愁”(愁緒)這個(gè)抽象無形的模糊概念相互映襯,相互配合,形象而逼真地抒寫了詞人胸中憂愁的無涯無際,讀之令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