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探析國外醫療衛生改革與民主化困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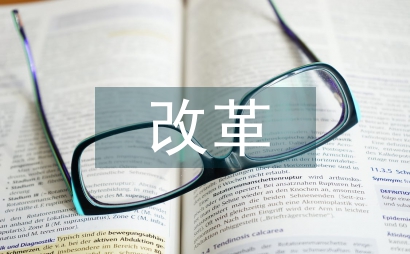
1990年代末,相當數量的外援和相對穩定的政局,為埃及的醫療衛生改革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之窗。1997年,一項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世界銀行、歐盟、非洲發展銀行和奧地利政府聯合資助的衛生部門改革計劃(theHealthSectorReformProgram,HSRP)得以規劃和啟動,其根本目標是解決埃及衛生服務體系的低效,徹底改變其衛生服務籌資、組織和提供方式。該改革計劃旨在全面提高埃及人口的健康水平,減少嬰兒和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提高人均期望壽命,并通過加強初級衛生保健降低傳染病負擔。這一改革計劃基于社會保險模式,以試圖整合埃及分散化的籌資結構,形成單一的國家健康保險基金(NationalHealthInsuranceFund,NHIF),其省級分支機構稱為“家庭健康基金”(FamilyHealthFunds,FHFs),其建立旨在將籌資與提供相分離。家庭健康基金與政府和公、私及NGO提供者建立合約,以給注冊的受益者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1999年,HSRP在 埃 及 的3個 省 (Alexandria、Menoufia和Sohag)啟動了試點項目。試點地區基層衛生機構設施得以改善,新的管理體系得以實施,家庭醫學人員得到培訓。其家庭醫學模式是整體醫學模式,旨在為家庭所有成員提供初級衛生保健。因此,家庭醫學組織(FamilyHealthUnits,FHU)得以建立,其員工由家庭醫生、護士、醫學輔助人員和行政人員組成,為區域居民提供初級衛生保健和全科門診服務。到2003年11月,試點項目已擁有66個家庭醫學組織,2008年達643個,2010年底的目標是達到2500個。HSRP是在穆巴拉克政府領導下規劃啟動的。然而,到了2011年1月,由于民眾的抗議,穆巴拉克30年統治宣告結束,埃及的支柱產業———旅游業也遭到重創,許多銀行、商店和工廠關閉,給公共衛生和醫療體系帶來持久的損害,對已經啟動、且有所成效的衛生部門改革計劃(HSRP)的實施更是雪上加霜,原定到2015年完成的醫療衛生改革計劃的設想將大受影響。
埃及私立衛生機構的發展,對其政府衛生服務體系產生很大影響。私立機構在服務質量、臨床效果和顧客滿意度方面比政府衛生機構要高得多,而政府衛生機構、特別是農村地區的政府衛生機構缺乏衛生資源和衛生人力培訓。更有甚者,政府衛生機構人員工資比私立衛生機構人員的要低得多,致使政府衛生機構的醫生大多私人行醫,以彌補其工資收入的不足。這種公私交叉分立的衛生體系已經顯示了其對衛生服務提供的負面影響,因為它實際上鼓勵醫務人員在公立衛生機構敷衍了事,而將病人引致其私人辦的醫療機構。而且,這一體系有可能導致政府衛生機構中的曠工和腐敗行為,使其服務質量每況愈下。埃及的 衛 生 費 用 偏 低,僅 為 其GDP的3.7%(WorldBank,2010)。這樣低的衛生經費投入,2004年卻有57%的份額流入私人醫療服務提供者,只有43%的衛生經費投入到公共衛生體系。更有甚者,接近一半的公立衛生機構缺少醫療設備和醫務人員。這或許是埃及人均壽命僅為59歲、血吸蟲病等傳染病高發的主要原因。另外,沒有針對弱勢群體或無正式職業者的醫療保險計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可見,埃及多年的醫療衛生改革進程遲緩、效果不佳。2011年2月,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影響下,僅僅18天的群眾大規模游行抗議,就把執政長達30年的中東強人穆巴拉克趕下了臺。在隨后的政治轉型期內,軍方與以穆兄會為代表的埃及伊斯蘭勢力間的矛盾和對抗日益激化,其醫療衛生改革進程與其民主化前景一樣,勢所難料。轉型期,新一輪的醫療衛生改革需謹慎推進,且要確立務實目標。為此,必須在人民群眾多元價值中達成改革共識。其中,有兩個重要問題值得人民群眾和醫療衛生人員高度重視:一是治理結構和反腐敗問題,另一個是衛生人力資源問題。但要解決這兩個重要問題,需要對其進一步具體化并確保其成功實施,衛生部門官員要對其實施成效負責,確保其提供的衛生服務為人民群眾所歡迎。
美國駐埃及大使SamehShoukry指出:醫改是埃及社會發展議程的一個優先領域。今天,埃及的政治形勢使其在許多方面都面臨著挑戰,但其最嚴峻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動員更多的經濟資源,以開發其寶貴的人力資本。在應對各種挑戰過程中,促進人口健康的愿景更具有吸引力,是指導未來衛生改革的主要價值觀。當前,埃及衛生改革除了發展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外,最關鍵的內容包括通過財政可持續的健康保險計劃提供高質量的醫療衛生服務、擴大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覆蓋面、提高計劃生育服務水平、建立并強化消費者保護機制。他認為,革命后的新埃及特別需要在衛生部門這一關鍵領域進行持續、全面的改革,使人民獲得更多看得見的利益,提高埃及人民的福利水平。
總之,埃及新政府亟待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做出戰略規劃和投資,特別要制定公共政策以克服其公私分立的衛生服務體系帶來的巨大挑戰,防止有限的資源從公立衛生服務體系流入私人部門為富裕群體服務,實現衛生資源的公平分配。在轉型期,衛生改革是社會改革的一個關鍵領域,謹慎、務實的改革尤為必要。
埃及醫療衛生改革與其動蕩局勢的復雜關聯
如何解讀埃及動蕩局勢與醫療衛生改革之間的復雜關聯?阿拉伯語專家鄒蘭芳指出:當埃及等西亞北非國家變局以多米諾骨牌的效應令國際中東事務專家、政界、史學界、媒體人士“失語”時,我們卻在阿拉伯文學家那里找到些許答案,至少能從較長的歷史語境來看當下變局的內在邏輯和文化征候。早在2002年,埃及小說家阿拉•斯托旺尼(AlaaAlAswany)的小說《雅古卜彥大廈》(TheYacoubianBuilding)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阿拉伯社會強烈的反響。據此小說改編的電影2006年躍居票房榜首,一舉榮獲28屆埃及電影奧斯卡7項大獎,并包攬了同年在巴黎舉辦的第8屆阿拉伯電影節全部獎項,以及國內外其他幾十個獎項。小說中那座經歷了四分之三世紀的風風雨雨、朝代更迭、而今行將傾覆的大廈便是當今埃及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一個縮影。正如一位法國評論家所言:“如果埃及是一座大廈,那么這座大廈的名字必定是雅古卜彥大廈。”2008年4月,阿斯旺尼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憤懣地表示:“專制統治者誅殺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我們生活在埃及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個時期。階級差別從未像今天這么懸殊,統治者在衛生、教育、民主等一切領域都告失敗……有這么暴虐不公的政權,有這么逆來順受的人民,連夢想都變得無比艱難……埃及的生活如此不堪,無法再沉默下去。一切都該改變,也必定會改變。我覺得前方有巨大的意外在等待我們。”#p#分頁標題#e#
然而,這一警世預言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如今,埃及憲法草案雖獲通過,但參加投票的人只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顯示埃及人厭倦了動蕩,更擔心不斷加深的經濟危機。對此,人們仍應從阿斯旺尼的警世預言中獲得啟示,新的統治者和人民要在衛生、教育等領域進行全面、公正的改革,以重建社會政治基礎,提高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衛生、教育等民生領域的改革,也只有從重建社會政治基礎的高度,才能真正取得實效。因此,擺正民生與民主的關系,對于民生工程實施和民主政治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認為,好的社會改革路徑———無論是歐洲、北美還是亞洲的成功國家,都遵循先經濟、后社會、再政府的過程。中國從孫中山到現在,比較好的道路應當就是以民生促民主,如果倒過來,以民主促民生,肯定是不成功的。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經驗表明,沒有民生的民主,是“空民主”,是“空中樓閣”的民主;但沒有民主的民生,是“假民生”,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民生。民生與民主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民主發展必須與民生建設相結合。對此,復旦大學林尚立教授明確指出:在任何國家,民生都必然是民主的基礎。但是,民生不能代表民主,沒有民主的民生,一定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因為,民生建設不僅需要國家的力量,而且需要社會的參與。社會參與的制度基礎一定是民主。民主發展要具有現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就必須與民生建設相結合,并對民生建設產生積極的效應。從人民民主與民生建設的內在邏輯來看,民主建設與民生建設的互動,首先體現為相互擁有,其次體現為相互促進。相互促進是在相互擁有的基礎上展開的。所謂相互擁有,就是民主建設中包含民生建設,民生建設中包含民主建設。民主建設與民生建設的相互促進正是人民民主得以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
實際上,無論是像埃及等發展中國家,還是西方發達國家,都需要注重民生與民主的攜手并進。當西方國家因福利政策影響其在全球化中的國家競爭力而試圖改革其福利保障體系時,德國著名學者哈貝馬斯曾發出這樣的警告:“如何解決把經濟效率同自由和社會保障,即把資本主義同民主結合起來的問題,關鍵在于實行某種致力于在高就業水平下比較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政策。”因而,“放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導致社會福利國家曾經抑制住的危機趨勢重新抬頭,由此產生的社會代價使自由社會的一體化能力不堪重負”。
可見,西方國家民主的發展與鞏固,也離不開對民生問題的妥善解決,一旦民生出現危機,歷史上的民主危機也必將卷土重來。對于像埃及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衛生等民生問題的解決更離不開民主。民主是政治手段,民生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民主是方法、途徑;民生是結果、表象。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沒有民主,就無以保障民生;沒有民主的民生,靠統治者和富翁恩賜的民生,是靠不住的民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民生困境的。吳敬璉認為,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當機立斷,痛下決心,真實地而非只是口頭上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和過渡。這也是埃及醫療衛生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給我們的啟示。
本文作者:楊善發 單位:安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