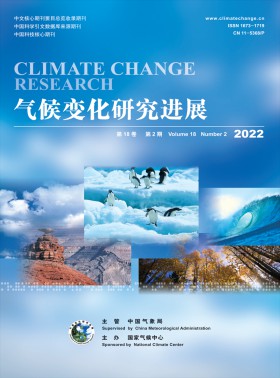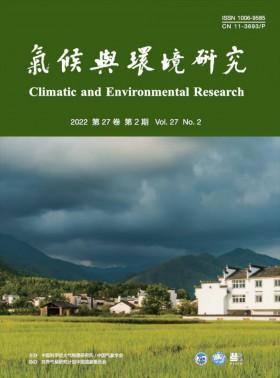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氣候改變對(duì)草原植被的作用,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0引言 氣候變化已成為當(dāng)前全球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問題。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顯示,在全球范圍氣候變化呈現(xiàn)出溫度升高(1906—2005年溫度升高0.74℃)、降水時(shí)空異質(zhì)性增強(qiáng)和氣候?yàn)?zāi)害事件頻繁發(fā)生的特征[1-2],且有研究[3]預(yù)估,2010—2060年,平均氣溫可能升高1.3℃(1.1~1.4℃)。中國氣候變化與全球氣候變化保持基本一致的特征,主要指標(biāo)的變化幅度較全球平均水平略強(qiáng)[4]。陸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主體,以“氣候變暖”為標(biāo)志的全球氣候變化對(duì)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影響[5],森林、農(nóng)田、草原作為3大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沖擊。目前,國內(nèi)外有關(guān)氣候變化對(duì)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影響與系統(tǒng)響應(yīng)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森林和農(nóng)田生態(tài)系統(tǒng)[6-15]。對(duì)于中國而言,草原是面積最大的綠色生態(tài)屏障,堅(jiān)守著森林、農(nóng)田等其他植被難以延伸的干旱、高寒等自然環(huán)境最為嚴(yán)酷、生態(tài)環(huán)境最為脆弱的廣闊地域,中國草原占國土面積的比重和其特殊的地理分布,彰顯了其極其重要的國家生態(tài)安全戰(zhàn)略地位[16],同時(shí)也賦予草原在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作用方面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是,關(guān)于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對(duì)氣候變化響應(yīng)的研究還較少,近年來才開始受到研究者們的重視,雖然相繼有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17-26],但與農(nóng)田、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相比,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略顯遜色,亟待進(jìn)行階段性總結(jié),以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1溫帶草原區(qū)氣候變化趨勢(shì)、特征及預(yù)測(cè)研究 1.1溫帶草原區(qū)氣候核心要素變化趨勢(shì)的研究 1.1.1溫度升高明顯 溫度升高是氣候變化的主要表征之一,無論在全球還是國家尺度,都有大量的數(shù)據(jù)可以證明。內(nèi)蒙古草原區(qū)地處北半球,是溫度變化最為明顯的地帶之一,近年來大量的以點(diǎn)代區(qū)的研究結(jié)果不斷支持氣溫升高的結(jié)論。從內(nèi)蒙古大尺度空間區(qū)域來看,吳學(xué)宏等[27]選用內(nèi)蒙古各盟市2~3個(gè)記錄年代較長(zhǎng)的代表性站點(diǎn),用多年平均氣溫反映氣候冷暖變化的情況,其研究結(jié)果顯示,20世紀(jì)70年代中期以前,氣溫為負(fù)距平較多;70年代后期,氣溫為正距平偏多,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全部為正距平。這表明20世紀(jì)70年代以后,內(nèi)蒙古地區(qū)出現(xiàn)了持續(xù)性增暖,80年代以后,增暖趨勢(shì)明顯增強(qiáng),到90年代,氣溫呈現(xiàn)加速上升趨勢(shì)。從局地區(qū)域來看,不同生態(tài)類型草原區(qū)溫度也朝著增加趨勢(shì)發(fā)生變化。劉及東等[28]利用呼倫貝爾鄂溫克自治旗中心氣象站數(shù)據(jù)代表草甸草原區(qū)分析了1959—2006年間的氣候變化,結(jié)果表明,期間該地區(qū)的平均氣溫總體變化趨勢(shì)先降后升,1959—1970年平均氣溫-2.15℃,1971—1980年10年平均溫度為-2.28℃,1981—1990年升高到-1.55℃,1991—2000年為-0.74℃,2001—2006年升至0.47℃。可見,從20世紀(jì)70年代初開始,該區(qū)域的升溫趨勢(shì)非常明顯。云文麗等[29]以錫林浩特站為典型草原區(qū)代表性氣象站,分析了1953—2003年區(qū)域平均氣溫的變化,研究結(jié)果表明,期間平均溫度在波動(dòng)中逐漸升高,上升趨勢(shì)和全球變暖的趨勢(shì)相一致,50年來氣溫累計(jì)上升大約3.4℃,特別是近20年平均氣溫累計(jì)上升4℃,另對(duì)季節(jié)變化的分析顯示,4個(gè)季度的氣溫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但是冬季和春季氣溫增加趨勢(shì)較夏秋季明顯。韓芳等[30]利用11個(gè)氣象站點(diǎn)1961—2007年的氣象資料分析了中溫性荒漠草原溫度的變化情況,研究結(jié)果顯示,50年來區(qū)域年平均氣溫呈極顯著上升趨勢(shì),每10年上升0.49℃(50年累積達(dá)2.45℃),特別是近20年,是升溫最為明顯的時(shí)段。 1.1.2降水量變化區(qū)域差異顯著 從大區(qū)域尺度有研究表明,在北半球溫暖時(shí)期,中國東南沿海降水量偏多,西北降水量將減少。溫帶草原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北、中北和西北地區(qū),東西和南北跨度較大,降水時(shí)空不均勻性明顯。從海拉爾氣象站數(shù)據(jù)資料分析來看,草甸草原區(qū)降水主要在250~400mm之間波動(dòng),降水年際變率很大,多雨年份可以達(dá)到少雨年份的2~3倍,其中各年份間春季的變率要明顯大于其他季節(jié),從1959—2006年的年降水量變化趨勢(shì)來看,20世紀(jì)60—80年代降水量呈增加趨勢(shì),90年代后期呈下降[31]。閆偉兄等[32]對(duì)內(nèi)蒙古典型草原1960—2004年降水量變化的分析結(jié)果表明,20世紀(jì)70年代末以前,處于正常偏少階段,80—90年代降水偏多,1998年降水量異常偏多,之后降水明顯偏少。但是,從1960—2004年間,典型草原區(qū)的年降水量線性變化趨勢(shì)并不明顯。李曉兵等[33]利用荒漠草原區(qū)二連浩特、朱日和和蘇尼特左旗1961—2000年氣象數(shù)據(jù)分析獲知,40年間,年降水量均表現(xiàn)出波動(dòng)性變化,1961—1982年多數(shù)年份的降水量大于多年平均值,而1983—2000年小于和大于多年平均降水量的年份基本持平,總體分析研究的40年中,后20年較前20年相比降水量略有下降,但是總體趨勢(shì)不明顯。 1.2溫帶草原區(qū)主要?dú)庀蠛禐?zāi)發(fā)生與變化的研究 多年來,干旱一直是制約中國北方地區(qū)農(nóng)牧業(yè)發(fā)展的主要?dú)庀鬄?zāi)害。有研究[34]證實(shí),近50年來中國北方一些地區(qū)降水量明顯減少,這將預(yù)示著干旱的加重,這一趨勢(shì)和結(jié)果必將對(duì)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造成日益嚴(yán)重的影響[35]。當(dāng)前,干旱已經(jīng)成為危及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嚴(yán)重問題,人類可利用水資源的嚴(yán)重匱乏及荒漠化、沙漠化的加劇都是干旱發(fā)展的具體表現(xiàn)[36]。關(guān)于氣象干旱災(zāi)害的評(píng)估研究方法已有不少報(bào)道,如美國廣泛應(yīng)用的Palmer干旱指數(shù)[37]、加拿大常用的標(biāo)準(zhǔn)化降水指數(shù)(SPI)[38]、中國國家氣象中心在旱澇監(jiān)測(cè)中使用的Z指數(shù)[39]以及各種模型或集成模型[40]等。需要注意的是,在2006年中國了《氣象干旱等級(jí)》國家標(biāo)準(zhǔn),列舉并推薦了一系列干旱監(jiān)測(cè)評(píng)價(jià)的單項(xiàng)指標(biāo)和綜合指標(biāo),為中國各地區(qū)的干旱等級(jí)評(píng)價(jià)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和方法。雖然評(píng)估氣象干旱的指標(biāo)很多,但是,每種評(píng)估方法在應(yīng)用的過程中都會(huì)有區(qū)域局限性,對(duì)于不同時(shí)空尺度的評(píng)價(jià),往往需要研究修正模型參數(shù)。 旱災(zāi)是溫帶草原地區(qū)次數(shù)最多、分布范圍最廣、影響程度最烈的一種氣象災(zāi)害[38],對(duì)草原牧區(qū)的生產(chǎn)和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了嚴(yán)重影響。馬宗普等[41]從第4紀(jì)氣候變化和發(fā)展規(guī)律出發(fā),據(jù)此認(rèn)為21世紀(jì)初雖然可能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是該時(shí)期仍屬于干旱期,特別是中國北方將受到干旱災(zāi)害的嚴(yán)重威脅,并將誘發(fā)或伴生一系列其他自然災(zāi)害。另據(jù)劉志剛等[42]對(duì)錫林郭勒草原氣候變化與干旱特征的分析結(jié)果表明,1953—2005年的53年中,荒漠草原區(qū)氣候干旱發(fā)生頻率占62%,典型草原氣候區(qū)干旱發(fā)生頻率達(dá)60%,草甸草原氣候區(qū)干旱發(fā)生頻率也達(dá)51%。大旱年景典型草原氣候區(qū)發(fā)生率最高,53年中出現(xiàn)了13次,占比25%,荒漠草原和草甸草原也都達(dá)到11次,占比達(dá)21%;與此同時(shí),研究還分析了錫林郭勒草原氣候干旱發(fā)生的時(shí)間分布特征,結(jié)果顯示,50年代干旱發(fā)生較少,各氣候區(qū)發(fā)生頻率在30%左右,20世紀(jì)60—70年生頻率都較高,荒漠草原發(fā)生頻率最高達(dá)80%,90年生頻率明顯減少,但是,進(jìn)入2000年以后,干旱又明顯增多,達(dá)80%。目前,錫林郭勒地區(qū)正處在連續(xù)干旱時(shí)期,自1999—2007年已經(jīng)連續(xù)7年發(fā)生不同程度的干旱,其中6年為嚴(yán)重干旱。#p#分頁標(biāo)題#e# 1.3溫帶草原區(qū)氣候變化趨勢(shì)預(yù)測(cè)的研究 在正確分析和認(rèn)識(shí)氣候變化歷史的條件下,合理預(yù)測(cè)評(píng)估未來時(shí)段氣候變化發(fā)展趨勢(shì),對(duì)于尋找全球、國家和區(qū)域氣候變化適應(yīng)對(duì)策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近年來,中國利用自行研制的全球海氣耦合模型,綜合IPCC幾個(gè)模式結(jié)果,對(duì)全球、東亞以及中國未來100年的氣候變化情景進(jìn)行了預(yù)估,分析結(jié)果顯示,未來50—100年全球地表氣溫將逐漸增加,而降水在南北極地增加、低緯度地區(qū)減少;對(duì)東亞和中國地區(qū),未來將表現(xiàn)出一致增暖,亦具有明顯的南北差異和季節(jié)差異,中高緯度地區(qū)增暖大于中低緯度地區(qū),冬春季增暖更為明顯。降水變化與全球相比,時(shí)空變率較大,預(yù)估2070年CO2增倍情況下,中國地區(qū)的降水將普遍增多,降水百分率增多的區(qū)域中,最大在中國西部,范圍從華北西部延伸到新疆,增加幅度預(yù)估在20%以上;華南的廣東東部和福建西部以及廣西東北部也有增加較多的地方;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的降水量變化不大,大部分地區(qū)略有增加,少數(shù)地方略有減少;東北北部是降水增加較多的區(qū)域之一,局地增加量也在20%以上;但是,東北南部至華北北部地區(qū)的降水將有一定的減少,減少多的地方數(shù)值在-10%以下[43]。盛文萍等[44]利用PRECIS區(qū)域氣候模式構(gòu)建并分析了中國區(qū)域高分辨率SRES氣候變化情境下內(nèi)蒙古年均溫和降水量的變化趨勢(shì),研究結(jié)果表明,在A2、B22種情景下,內(nèi)蒙古年平均溫度都有明顯升高,A2情景增幅大于B2情景,雖然年均溫度在21世紀(jì)與基礎(chǔ)年時(shí)期相比有明顯升高,但是年均溫的全區(qū)分布格局在不同時(shí)期沒有太大變化;同時(shí)研究結(jié)果還顯示,內(nèi)蒙古年降水量的變化趨勢(shì)不像年均溫在全區(qū)的變化那樣一致,與基準(zhǔn)年時(shí)期相比,21世紀(jì)初期全區(qū)年均降水量有明顯降低,A2、B22種情景分別下降27.4%、29.7%,但21世紀(jì)中期開始,全區(qū)平均降水量又有所回升,到21世紀(jì)末,A2、B2兩種情景下全區(qū)年均降水量分別比基準(zhǔn)年下降11.3%、23.6%;未來時(shí)段內(nèi)蒙古的年降水量空間分布極不均衡,高值區(qū)分布在大興安嶺—陰山山脈一線的東南緣迎風(fēng)坡以及嫩江西岸平原,低值區(qū)分布在最西部的大陸內(nèi)部,各降水量帶平行于大興安嶺山脈呈東北-西南帶狀分布;到21世紀(jì)末,氣候變化將使內(nèi)蒙古西部地區(qū)降水量上升,而東北部和中部偏東南地區(qū)下降。 2氣候變化對(duì)溫帶草原植被影響與響應(yīng)的研究 2.1主要?dú)夂蛞刈兓瘜?duì)溫帶草原植被影響的研究 草原地區(qū)氣候變化以CO2濃度增加,溫度升高,降水減少或變化不明顯為基本特征,這些變化對(duì)溫帶草原植被產(chǎn)生多方面的影響。 2.1.1CO2濃度CO2濃度升高被認(rèn)為是氣候變暖的主要?jiǎng)右颉2菰菍?duì)CO2增加反應(yīng)較敏感的生態(tài)系統(tǒng)[17]。CO2對(duì)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產(chǎn)生的影響并非單一因素的線性關(guān)系,其作用往往受到其他因子的制約。Parton等[18]研究認(rèn)為,氣候變化和CO2的增多,將提高熱帶和溫帶草原的NPP(netprimaryproductivity,NPP),但是,早在10多年前Melillo等[45]對(duì)氣候變化下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chǎn)力的模型預(yù)測(cè)研究卻認(rèn)為,溫度和CO2濃度增加將使北半球和溫帶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chǎn)力增加,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系統(tǒng)的生產(chǎn)能力將受到土壤N缺乏的限制。最近Berge[46]發(fā)表的有關(guān)溫帶草原的研究結(jié)果認(rèn)為,N不會(huì)因?yàn)槿狈Χ蔀橄拗撇菰脖簧a(chǎn)力增加的因素,因?yàn)槲磥須夂蜃兓闆r下N利用效率將極大降低。Shaw等[47]在加州開展的模擬全球變化的單因素及包括氣候變化、降水增加和N沉積在內(nèi)的多因素試驗(yàn),試圖來回答草原對(duì)全球環(huán)境變化的響應(yīng)時(shí),得出了與Berge分析類似的結(jié)論,即大氣CO2濃度升高抑制植物根的分配,從而降低溫度增加、降水增多和N沉積對(duì)NPP的積極作用。 2.1.2溫度溫度變化是氣候變化最為明顯的因素之一,對(duì)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有顯著的影響。全球變化極大地改變了全球溫度與季節(jié)氣候條件的相應(yīng)時(shí)間[19]。溫度升高、氣候變暖將加快春天(返青期),并延遲秋天(枯黃期)的到來[20],這將延長(zhǎng)生物的生長(zhǎng)期,此過程有助于CO2吸收,從而降低大氣中CO2濃度,但是,生物與大氣的相互作用又將影響氣候[48],隨著生物活性的增強(qiáng)與綠色植被覆蓋時(shí)間的增長(zhǎng),在干旱地區(qū)極易吸收更多的光照,但又沒有足夠的水分蒸發(fā)散熱,這將進(jìn)一步導(dǎo)致溫度升高[21],此過程將是正反饋過程。溫度對(duì)植物生長(zhǎng)期干物質(zhì)分配的影響取決于不同的物種及其環(huán)境,Morgan等指出,在未來溫度升高2.6℃,且水分并沒有成為限制因子的前提下,美國矮草草原的生產(chǎn)力將呈增加趨勢(shì)。與此同時(shí),Bachelet等[49]采用平衡模型和動(dòng)態(tài)模型研究的結(jié)果表明,溫度對(duì)草原生產(chǎn)力的積極作用是有極限的,這一極限值為溫度升高4.5℃。國內(nèi)在氣候變化對(duì)草原影響方面也開展了大量研究,方精云[50]認(rèn)為草原地區(qū)絕大多數(shù)植物為C3植物,溫度升高對(duì)其生長(zhǎng)將產(chǎn)生不利的影響;高瓊等[51]則指出,不同群落對(duì)溫度變化有不同的響應(yīng)機(jī)制。 2.1.3降水氣候變化當(dāng)中,降水變化作為影響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非生物因素,通過影響植物的生長(zhǎng),改變物種間的關(guān)系,隨即影響植物群落的組成和結(jié)構(gòu),最后影響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功能及對(duì)氣候變化的潛在反饋?zhàn)饔肹25,52-54]。草地NPP受降水量及生物溫度的影響較大,但是受降水影響更為直接、明顯。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半干旱區(qū)溫度顯著增加、降水減少或沒有顯著變化,相對(duì)濕度表現(xiàn)為下降,這意味著大氣在向干旱化方向轉(zhuǎn)變,連鎖反應(yīng)的結(jié)果是導(dǎo)致土壤朝著干旱化方向轉(zhuǎn)變,自然水分虧缺成為限制草原生產(chǎn)力的重要因素[55-56]。草原生產(chǎn)力不論是在自然狀態(tài),還是在人為強(qiáng)烈干擾的情景下,都將會(huì)受到降水梯度變化的極大影響[57]。大量研究表明,在中國溫帶草原區(qū)氣候變化呈現(xiàn)出“暖旱化”特征,即使在降雨有所增加情況下,都會(huì)對(duì)草原生產(chǎn)帶來不利影響,牛建明[58]基于年均氣溫增加2℃或4℃,降水均增加20%的2種方案下對(duì)內(nèi)蒙古草原生產(chǎn)力進(jìn)行了預(yù)測(cè)研究,結(jié)果表明,氣候變化使草地生產(chǎn)力明顯下降,如果不考慮草地類型的空間遷移,在2種方案下,分別減產(chǎn)約一成和三成,若計(jì)入各類型空間分布的變化,減產(chǎn)則高達(dá)三成和1/2以上,且荒漠草原的減產(chǎn)最突出。 2.2草原植被對(duì)氣候變化響應(yīng)的研究 #p#分頁標(biāo)題#e# 氣候變化正在改變植物生長(zhǎng)的有效資源和關(guān)鍵條件[59]。氣候變化的發(fā)生及持續(xù),將打破原有氣候格局,一些氣候有可能消失,而新的氣候可能占據(jù)更為廣闊的空間,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維持,必須依賴于系統(tǒng)組分的不斷自我調(diào)節(jié)以適應(yīng)氣候變化的步伐[60]。 物候變化是物種響應(yīng)氣候變化的重要表現(xiàn),近年來已有很多研究報(bào)道。氣候變化中的溫度升高、CO2濃度增加、N沉降以及降水的變化等將通過影響植物的生理過程進(jìn)而改變物候,變暖加速萌發(fā)和開花,但是植物物候響應(yīng)其他環(huán)境變化卻是多樣的[61]。有研究認(rèn)為,中國生長(zhǎng)季在過去20年間增長(zhǎng)了1.16天/年,春天早到0.79天,秋天晚來0.37天,這將增加夏天的溫度,但降水變化又影響了植被類型和物候,從分布來看,在中國的東北、北部等都出現(xiàn)了物候期提前的跡象[11]。但也有報(bào)道認(rèn)為,春季物候期推遲而秋季物候期提前,導(dǎo)致生長(zhǎng)季縮短。楊曉華等[62]對(duì)內(nèi)蒙古典型草原植物物候變化的研究表明,草本植物春季物候期延遲,結(jié)束期(枯黃期)提前,其原因系降水對(duì)干旱的內(nèi)蒙古草原非常重要,是制約植物生長(zhǎng)發(fā)育的關(guān)鍵因子,氣候變暖導(dǎo)致蒸發(fā)加劇,在降水減少的條件下,加速了土壤干旱化程度,導(dǎo)致春季物候推后。 氣候變化下,不同物種具有不同的生理可塑性,而這種可塑性是植物響應(yīng)環(huán)境變化的重要機(jī)制。Goldman等[63]對(duì)典型草原的3個(gè)物種(Festucalenensis,Potentillaacaulis,P.sericea)開展了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在干旱脅迫的平均水平上P.sericea表現(xiàn)出較高的水分利用效率,這預(yù)示著未來土壤水分減少的狀況下,其豐富度將增加,此結(jié)果也進(jìn)一步說明,物種的豐富度和植被的蓋度將對(duì)氣候變化產(chǎn)生差異性響應(yīng)[64]。物種對(duì)氣候變化的響應(yīng)也將引起群落的變化,而這些過程往往與土壤系統(tǒng)緊密相關(guān)[25],F(xiàn)ridley等[24]研究指出,植被和氣候的相互作用實(shí)際上是對(duì)環(huán)境(如土壤結(jié)構(gòu))和生命過程(競(jìng)爭(zhēng)和適應(yīng))的調(diào)諧,他們?cè)谟卤认柌菰祥_展了冬季控溫、夏季控雨試驗(yàn),試圖解釋生態(tài)系統(tǒng)通過物種組成的變化來響應(yīng)氣候變化,結(jié)果顯示,在響應(yīng)氣候溫暖、干旱的過程中,通過深根系物種豐富度的增多來彌補(bǔ)淺根系物種豐富度的減少,物種變化主要發(fā)生在土壤根系最深和最淺者之間。黃培?等[65]針對(duì)準(zhǔn)格爾盆地南緣梭梭群落對(duì)氣候變化的響應(yīng)開展了研究,認(rèn)為氣候變化導(dǎo)致干旱區(qū)早春期氣溫波動(dòng)更加劇烈,當(dāng)春雨較少且雨日間隔較長(zhǎng)時(shí),將引起天氣急速升溫、表土層水分迅速下降,造成春萌型植物幼苗隨之大量夭折,梭梭幼苗補(bǔ)充亦因而受阻,導(dǎo)致準(zhǔn)格爾盆地南緣的梭梭種群年齡結(jié)構(gòu)普遍呈衰退趨勢(shì),梭梭群落出現(xiàn)逆行演替。到目前為止,大多數(shù)研究都集中在氣候變化對(duì)物種的物候、生理變化及分布范圍的影響,然而,物種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其相同或相鄰營養(yǎng)水平上其他個(gè)體通過互動(dòng)來共同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26],這方面的研究將成為未來的重要研究方向。 生產(chǎn)力或覆蓋度(NDVI)往往是多種變化的綜合表征,是系統(tǒng)對(duì)氣候變化響應(yīng)的綜合表現(xiàn)。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chǎn)力或NDVI對(duì)氣候變化的響應(yīng)目前已經(jīng)有不少報(bào)道,中國學(xué)者在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生態(tài)系統(tǒng)對(duì)氣候變化響應(yīng)的一個(gè)重要策略就是通過不同層次水平組分的消長(zhǎng)補(bǔ)償來維持系統(tǒng)穩(wěn)定性,白永飛等[66]研究認(rèn)為,內(nèi)蒙古草原生產(chǎn)力的波動(dòng)主要取決于6—7月降水的變化,沿著組織水平的提高,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不斷增強(qiáng),這種穩(wěn)定性主要取決于系統(tǒng)組分或官能團(tuán)的補(bǔ)償。氣候的強(qiáng)烈變化,會(huì)導(dǎo)致生產(chǎn)力或NDVI的明顯變化,而且不同的類型對(duì)不同氣候因子的變化會(huì)表現(xiàn)出不同的響應(yīng)特征。馬文紅、方精云等[22]指出,在干旱區(qū)草原(荒漠草原或典型草原),生物量對(duì)氣候變化的響應(yīng)主要取決于降水,而在相對(duì)濕潤(rùn)的地區(qū),群落生物量對(duì)氣候變化的響應(yīng)主要取決于1—5月的溫度。同時(shí),他們還深入研究了內(nèi)蒙古典型草原地上生物量年際(1982—2003年)變化規(guī)律,結(jié)果顯示,群落生產(chǎn)力對(duì)氣候變化的響應(yīng)主要體現(xiàn)在生長(zhǎng)季,生長(zhǎng)季前期群落生物量的上升趨勢(shì)是對(duì)春季氣候趨于溫暖濕潤(rùn)的響應(yīng),而生長(zhǎng)季末期生物量趨于減少是對(duì)秋季干旱增強(qiáng)趨勢(shì)的響應(yīng)[23]。近日,據(jù)樸世龍等[67]的研究報(bào)道,北美西北大部分地區(qū)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植被生產(chǎn)力下降的現(xiàn)象不能由干旱脅迫解釋,而是與該地區(qū)春季溫度下降密切相關(guān)。 3結(jié)論與討論 全球氣候變化已被普遍接受。目前,氣候要素和氣候系統(tǒng)的變化幅度、原因及區(qū)域分布迥異,且對(duì)未來氣候變化預(yù)測(cè)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68]。氣候變化已經(jīng)對(duì)中國溫帶草原區(qū)產(chǎn)生較大影響,上文簡(jiǎn)略綜述了溫帶草原區(qū)氣候變化特征、趨勢(shì)及其對(duì)植被的影響,從未來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基礎(chǔ)研究方向來看,亟需從植被、土壤、人類活動(dòng)等自然-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多維角深入研究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系統(tǒng)各要素的響應(yīng),尤其重視增強(qiáng)系統(tǒng)氣候變化適應(yīng)能力。縱觀前人在草原地區(qū)關(guān)于氣候變化的研究,雖已獲得大量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領(lǐng)域和角度需要開展深入地研究。 (1)加強(qiáng)氣候變化點(diǎn)數(shù)據(jù)分析,重視點(diǎn)與面相結(jié)合的研究。目前,國內(nèi)關(guān)于氣候變化的研究大多利用氣象站的點(diǎn)數(shù)據(jù),對(duì)認(rèn)識(shí)氣候變化特征和規(guī)律提供了一定的重要信息,但由于中國溫帶草原區(qū)面積廣大,氣候變化具有強(qiáng)烈的局地異質(zhì)性,單靠點(diǎn)數(shù)據(jù)不足以準(zhǔn)確、全面地了解氣候各要素在區(qū)域上的變化趨勢(shì)。因此,在未來研究中,亟需選取更多的氣象站點(diǎn),開展大尺度氣候變化的時(shí)空格局研究和微地形下氣候變化的時(shí)空一致與異質(zhì)性研究。 (2)提高氣候變化預(yù)測(cè)精準(zhǔn)度,科學(xué)評(píng)估生態(tài)系統(tǒng)脆弱性。氣候變化特征的年代和百年尺度分析,有助于認(rèn)識(shí)氣候變化規(guī)律及其對(duì)自然-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系統(tǒng)的影響。但是,作為核心目標(biāo),增強(qiáng)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氣候變化適應(yīng)能力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指導(dǎo)意義。因此,引進(jìn)、借鑒并開發(fā)適合中國利用的氣候變化預(yù)測(cè)模型,提高氣候變化預(yù)測(cè)精準(zhǔn)度,同時(shí),在科學(xué)認(rèn)識(shí)不同生態(tài)系統(tǒng)本質(zhì)屬性特征的基礎(chǔ)上,做出合理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氣候變化脆弱性評(píng)估與生態(tài)分險(xiǎn)分析,也是當(dāng)前和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3)研究草原植被受影響過程,明晰系統(tǒng)氣候變化響應(yīng)機(jī)理。從不同的尺度層次挖掘和闡釋氣候變化對(duì)生態(tài)系統(tǒng)影響的機(jī)理及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尤其是植被系統(tǒng)響應(yīng)氣候變化的規(guī)律,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應(yīng)用價(jià)值。目前,很多定點(diǎn)控制試驗(yàn)多以研究和揭示了氣候變化單因子或多因子對(duì)植物個(gè)體、官能團(tuán)及群落的影響,在大時(shí)空尺度上的研究還相對(duì)薄弱,而在氣候變化背景下,準(zhǔn)確地把握大尺度時(shí)空下草原植被變化的特征、規(guī)律及對(duì)氣候變化的響應(yīng),將對(duì)國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氣候變化對(duì)策、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對(duì)策以及宏觀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政策等都有重要的意義。#p#分頁標(biāo)題#e# (4)綜合氣候和人類活動(dòng)影響,解析草原退化過程與機(jī)制。近年來,由于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放牧等人類活動(dòng)的影響,溫帶草原已經(jīng)開始面臨諸多困境,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沙化嚴(yán)重,表現(xiàn)為植物小型化、生產(chǎn)力持續(xù)衰減等,加之極端氣候?yàn)?zāi)害事件頻發(fā),氣候變化-放牧利用-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與演化變得更為復(fù)雜。因此,研究氣候變化和放牧利用等人類活動(dòng)對(duì)溫帶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影響機(jī)理與恢復(fù)機(jī)制,辨析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在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演變中的貢獻(xiàn)率,是認(rèn)識(shí)與保護(hù)建設(shè)退化草原的研究和實(shí)踐中亟待解決的熱點(diǎn)和難點(diǎn)問題。 (5)開展氣象災(zāi)害的科學(xué)評(píng)價(jià),構(gòu)建災(zāi)害預(yù)警與應(yīng)急系統(tǒng)。應(yīng)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開展適合草原區(qū)及各草原植被亞類的氣象災(zāi)害等級(jí)評(píng)價(jià)與預(yù)測(cè)研究,對(duì)于草原地區(qū)來講,主要是氣象干旱和雪災(zāi)等的分析評(píng)價(jià),目前,雖然在國際和國內(nèi)有很多指數(shù)供試,但是,局地性比較強(qiáng),對(duì)面積廣大、氣候-植被-土壤類型復(fù)雜的溫帶草原來講,還有待進(jìn)一步商榷與完善。同時(shí),應(yīng)加強(qiáng)氣候?yàn)?zāi)害預(yù)警的研究,結(jié)合草原自然、氣候等監(jiān)測(cè)系統(tǒng),建立科學(xué)的災(zāi)害預(yù)警與評(píng)估模型,并結(jié)合區(qū)域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等狀況,開發(fā)草原氣候?yàn)?zāi)害應(yīng)急救助決策系統(tǒng),為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引發(fā)的災(zāi)害頻發(fā),有效增強(qiáng)氣候變化適應(yīng)能力提供決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