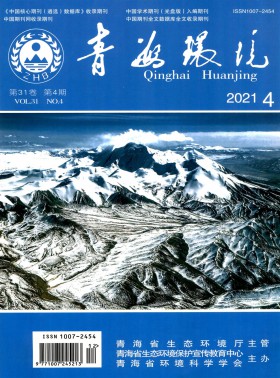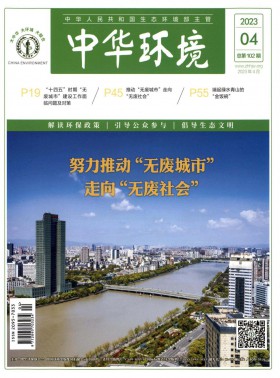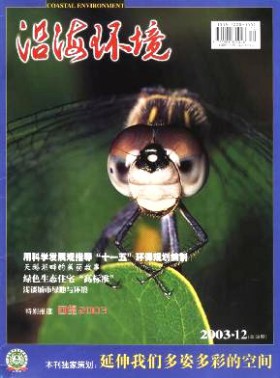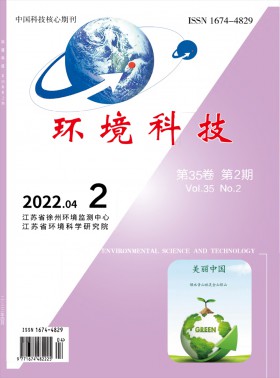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環境整治主體差別思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劉小青 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一、問題的提出
面對環境問題,人類需要的是系統的視角與多維的合作,其中公眾參與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環境治理機制。而建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從而促進公眾在環境治理中主體作用的發揮。與西方國家自下而上的環境治理模式不同,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由是一種由政府積極制定、推行政策,組織教育群眾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從經濟起飛的一開始,中國政府就提出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基本國策。1992年中國政府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其后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首次對公眾參與做出規劃。在獲得這個政治保障后[1],社會實踐領域的環境公眾參與才逐步發展起來。可以說,中國的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政府主導的特殊性。本文提出的問題是: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在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方面成效如何?具體而言:(1)在多年的政府引導下,中國公眾是否已經具備了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2)中國環境領域的社會化過程有什么特殊性?(3)這種特殊性又對公眾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為了探討以上問題,本文將利用跨度十年的兩次全國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并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運用量化分析和比較分析的方法,以“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為切入點進行分析。之所以選擇這個切入點,是因為“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體現了公眾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政府主導公眾參與制度的績效。通過考察這一偏好的影響因素,一方面可以獲得對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普遍意義上的認知,另一方面也為評價制度績效及其轉變方向提供依據。
二、研究設計及變量描述
(一)研究假設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政治系統傳播政治文化、公民個體學習政治文化的互動過程。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誕生于政府主導的模式并歷經20多年發展,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政治系統傳播其理念,公民個體學習并接受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從政治社會化的外部條件來看,家庭、學校、同齡群體、工作單位以及大眾媒介是政治社會化的介質[2](P506-601)。在中國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中,宣傳教育是實現社會動員的最主要方式。時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的曲格平曾于1988年指出:“我們重視環境宣傳工作,這是由我們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歷史短,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對這項事業還缺乏認識;我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又比較落后,使各行各業和廣大群眾自發地增長環境意識、提高環境道德還有困難”[3]。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國的環境教育開始進入高校專業教育和廣大中小學普及教育領域,并迅速具有了廣泛的群眾性。這就意味著,學校教育是中國公民環境政治社會化最主要的介質。
從政治社會化的生命歷程理論考察,青少年時期的社會化過程是公民習得政治文化、形成特定政治態度和傾向的最關鍵時期[4](P16)。這就意味著,集中接受了政府環境教育的公民,尤其是當青少年時期正好處在中國政府開始實施環境教育政策的特殊階段的公民,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會明顯高于其他年代的公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設: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將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為驗證這一核心假設,估計出生年代對這一選擇偏好的凈影響,還要納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從環境意識理論考察,作為一種環境意識,“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會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環境感知和環境污染經歷的影響。而從治理理論考察,公眾參與基層環境事務的邏輯起點是對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缺陷的彌補,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高低影響著公眾是否參與基層環境事務,即是否愿意從管理對象變成治理主體。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就包括:社會經濟基礎變量、環境污染感知變量、環境污染經歷變量以及政府績效評價變量。
(二)變量描述
1.因變量: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首先來描述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狀況。數據顯示,有61.30%的受訪者選擇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環境治理主體。可以看到,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仍然具有很強的“政府依賴性”特征。認為公眾應該承擔治理責任的公民比例為17.09%。接下來依次為內資企業、中央政府、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僅有1.70%的公眾認為社會團體應該負主要的治理本地環境污染的責任。這一比例說明絕大部分中國公眾對ENGOS還很陌生,對其在環境治理中所應發揮的作用不甚了解。本文認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基層環境系統中,地方政府、企業和公眾是最主要的三個參與主體,公眾對這三方主體的偏好將是本文所要解釋的因變量。之所以忽略中央政府和社會團體,主要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從研究的問題和中國的環境管理體制來看,中央政府是基層環境治理的制度提供者,而不是具體環境治理的參與主體;二是從統計分析的有效性考慮,選擇社會團體的受訪者比例太低,將其納入回歸分析模型將導致分析結果偏差。另外,研究合并了兩類企業,并且直接刪除了因變量上無回答的個案。最終本研究的樣本是2 161個明確表示了選擇態度的受訪者。
2.自變量:出生年代。按照社會化理論,影響社會化變遷的因素一般包括“變化的成年經歷,如失業、婚變;重大的特殊事件,如經濟大蕭條;長期的社會變遷,如社會轉型;領導層的變革;社會化介體的瓦解或變遷”[5](P174)。本研究認為,人們在環境參與意識上的代際差異實際上體現了社會化的變遷。因此我們在劃分出生年代時,考慮了社會轉型、社會結構以及特殊事件的影響,將人群分為四個出生年代:1949年及以前出生(建國前出生)、1950—1965年出生、1966—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自變量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轉化為虛擬變量。
3.控制變量。(1)社會經濟基礎變量描述。控制變量中納入的社會經濟基礎變量包括了性別、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行業類型。這四個變量均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分別轉化為虛擬變量。(2)環境污染感知變量描述。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公眾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有三種,污染驅動型、世界觀模式和后物質主義模式[6](P57-59)。假定公眾是否選擇自身直接參與環境治理是與其實際感受到的污染嚴重程度相關的,于是本研究選取了公眾對對本地環境問題嚴重程度的感知作為控制變量之一。這是一個0~10分的連續變量,分數越高代表認為環境問題越嚴重。數據結果顯示,公眾打分的平均分為5.77分②,總體來看還是傾向于認為本地的環境問題比較嚴重③。3.環境污染經歷變量描述。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人們在認識和評價事物時存在著“近因效應”,因此本文將公眾最近一年是否經歷過環境污染作為控制變量納入研究。數據結果顯示,有32.35%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經歷過環境污染事件④。#p#分頁標題#e#
4.政府績效評價變量描述。由于基層環境治理既具有區域分隔性,又具有系統相依性,因此社區層面和縣/市層面都被考慮在內。本研究選取公眾對本市/縣政府工作的評價和對本村/居委會/社區工作的評價兩個變量,共同反應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的評價狀況。這兩組變量的可靠性檢驗以及因子分析顯示,其信度系數α=0.62,因子負載率是0.707 1,證明這兩個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并處于同一個維度。所以對上述兩個變量進行加總,建立當前公眾對于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綜合指標。加總后該變量是一個取值范圍為0-20的連續變量,樣本均值為14.14⑤。
(三)數據來源
本文有兩個主要數據來源,一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2008年組織實施的“公民文化與和諧社會調查”的環境問題部分。該調查在全國范圍的25個省、市、自治區的73個縣級單位進行,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中國公民,共完成有效樣本3 989個。為了滿足覆蓋流動人口的需要,該調查采用“GIS/GPS輔助的區域抽樣”方法,按照分層、多階段、概率與規模成比例(PPS)的方式抽取概率樣本。為比較中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分析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的績效,本文還使用了由國家環保總局和教育部立項,委托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于1998—1999年設計實施的“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有關數據。該調查在全國共抽出139個縣級樣本單位,成功完成9 202戶訪問。值得一提的是,這項調查設計了針對青少年的問卷。最后合格的成人樣本數是9 919,合格的少年樣本數是2 682。
(四)分析方法和模型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基于大樣本社會調查的定量研究仍然不多見。本文選取了定量研究方法,不僅克服了規范分析和定性研究在代表性和客觀性上的兩難處境,還可以通過統計控制,有效地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凈效應。同時,本文還采用了同期群研究的方法,縱向比較跨度十年的兩個全國規模的調查數據,從方法論來看更具有因果分析的科學性和規范性。
三、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描述
在構建上述模型的基礎上,本文采用Stata10.0軟件對公眾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了社會經濟基礎、環境污染感知、環境污染經歷和政府績效評價四類變量的基礎上,出生年代對公眾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存在著顯著的影響。標準化的回歸系數⑦可以用來說明各解釋變量對于因變量的相對作用大小。通過對其考察進一步發現:代際差異是影響公眾對區域環境治理主體偏好的相對作用最大的因素。換言之,在諸多影響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因素中,出生年代是影響作用最大的因素。縱向觀察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如表4所示:不同年代出生的公民在選擇“政府”還是“公眾”時,呈現出逐級遞增的顯著性差異。研究發現,隨著年齡的增加,公眾選擇“本地政府”的發生比遠高于選擇“公眾”的發生比,而其標準化回歸系數也在逐步增加。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選擇“公眾”的發生比則是選擇“本地政府”的2.505倍,并在P<0.00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標準化回歸系數最高,為0.187。再結合描述分析的結果來看,越是年輕的一代人,就越偏好“公眾”這一治理主體;越是年老一代,對于“地方政府”的偏好就越多;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一代人,其偏好具有典型性和顯著差異。
四、解釋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
(一)基于政策背景的宏觀解釋
1.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歷程回顧。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始于1972年。當時中國政府提出了環境保護的“三十二字方針”,強調了環境保護領域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7](P140)。1973—1979年是政府環保工作的單純治理階段。此階段環境教育以促進環境污染防治為主要目標,面向全社會的環境教育和環保動員未見起色。1979—1992年,中國政府的環保工作進入到環境管理階段,同時環境教育初步發展。在這個階段,促進環境管理成為重要的環境教育目標。1993年以來,中國當代環境教育快速發展。在這個階段,環境教育開始重新定向,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高等環境教育持續快速發展,基礎環境教育不斷增強,各中小學都開設了環境教育專題課;宣傳部門廣泛開展以“中華環保世紀行”為主題的環境宣傳教育;“自然之友”為代表的民間環保組織成為環境教育的新生力量;以環境倫理學為代表的環境人文學科開始融入教學內容。
2.不同年代出生公民的環境意識社會化。按照早期經典社會化理論,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主要發生在青少年時期,即成人之前的這段時間,也就是通常界定的10~15歲。按照生命歷程視角的政治社會化理論,這段時期是個人形成對國家和對政府抽象效忠感和公民意識的啟蒙階段[8](P17)。通過對中國政府主導的環境保護制度的簡要回顧,可以看到,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沒有接受過任何環保動員和環境教育。而1950年到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即主要集中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一階段只是在政府層面提出了環保目標,但實質的環境教育和公眾參與處于零水平狀態。1966年到197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其青少年時期大致是在1978—1993年間,這段時期正是環境教育的初步發展階段,不過其主要對象還是高校學生,并未普及到中小學校。也就是說,這一人群中的環境意識差異較大,這一時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會更多地接受到環境教育,而且其所受環境教育多為專業性教育而非參與式的環境意識教育。那么到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這一代人,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大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之后,這段時期正是公眾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環保教育開始進入中小學課堂,也開始有ENGOs積極介入,并與政府一起共同推動公眾環境教育。將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中國政府環境教育的不同階段繪制在一個時間坐標軸上,可以直觀地展示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環境教育各階段近似重合的情況。作為環境意識社會化結果的偏好選擇的變化與環境教育的發展階段呈現一致的變化規律。例如,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尚未開展環境教育的階段,而其在2008年調查時,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低,為12.10%;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階段,在2008年調查時其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高,為24.22%。這一比較結果說明,青少年時期的環境教育,實際上是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實現途徑。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即對“公眾”作為環境治理主體的偏好。#p#分頁標題#e#
(二)基于兩年度數據比較的微觀解釋
1.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正如前文討論過的那樣,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之一即是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本文認為,相較于“企業”和“本地政府”,具有“公眾”治理主體偏好的人群,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也相對較高。而這類人群將成為中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模式變遷的推動力量。研究發現,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具有這樣特征的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80后”人群偏好“公眾”這一環境治理主體,高于全體人群近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他們具有最強的參與傾向。為考察這個特殊人群的環境意識特征,需要借助政治社會化理論。“個人的行為舉止通常都被分析為歷史的與同時代的影響共同起作用的結果。研究政治社會化的意圖是探討歷史對成年人政治態度和行為舉止的影響。”[9](P2-3)這就給了一個考察視角,即追溯到這代人的少年時代,即社會化的關鍵時期。為此,本研究用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數據做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解釋環境意識社會化的過程及其對制度模式變遷的影響。
2.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少年部分數據描述。1998年的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少年(10~15歲)的環保意識水平明顯高于成人。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少年的環保意識在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自然觀、環保行為等各方面高于成人近10個百分點。(2)少年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高于成人近20個百分點。(3)少年環保知識主要來源于學校課堂,學校課堂是少年環保知識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來源途徑,說明中小學教育對提高少年環保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少年的環境意識社會化與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對比2008年和1998年兩項調查的相關數據發現,1998年調查中的少年(當時為10~15歲)恰是2008年調查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可以看到,少年時代高水平的環境意識對成年后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具有塑造作用。少年作為接受環境宣傳教育最為集中和系統的群體,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的高低集中體現了政府主導的環境參與制度的成效。這是因為學校教育作為少年社會化的主要機制之一,對于少年環境意識的養成,以及這種個體層面的環境意識群體化并成為一代人所共有的價值理念具有關鍵的作用。
兩年數據比較為研究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論據支持,對前文的兩個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印證和解釋:(1)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形成集中的環境參與傾向。同時又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啟示:雖然是政府主導了自上而下的環境參與模式,可卻通過環境意識的社會化過程,使得這個制度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那里被內化為一種特定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而這種偏好正體現了一種積極參與的傾向。于是,在基層民眾中產生了自下而上的社區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因此可以說,環境意識借由“80后”這個新生代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從個體意識匯集成為一種群體意識,進而影響了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狀態向著自下而上方向的轉變。而這個轉變過程本身,即是制度目標———培育參與主體意識、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現,從而體現出正向的制度績效。
五、討 論
通過比較相隔十年的數據,本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十年前的少年群體具有顯著高于成人群體的環境意識;十年后的這些少年已經成長為本研究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群體,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高于其他年代出生人群。其原因可以通過環境意識的社會化來進行解釋,即環境意識借由“80后”這個新生代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從個體意識匯集成為一種群體意識,進而內化為一種偏好,影響著他們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從狹義角度審視青少年環境意識的社會化,可以發現,社會變遷以及特殊事件成為社會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中國的環境保護問題,是隨著現代化和市場化進程逐漸凸顯出來的,體現了社會轉型問題的特征。而社會變遷對于社會化的影響是顯著的,它會中斷已有的社會化進程,其具體的表現就是顯著的代際差異。而特殊事件的影響機制也類似。可以看到,在政府主導的環境參與制度下,環境教育在中小學校的普及成為1980年以后出生的這代人所共同經歷的特殊事件。這一代人所共同經歷的特殊事件對于環境意識從個人意識凝聚為群體意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個人與系統互動的角度考察,在政府主導的環境公眾參與模式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經過政府的環境教育,在其自身的社會過程中,也將環境參與理念逐漸內化為一種在群體間更具一致性的特征。在這個過程中,既可以看到社會化所具有的文化傳送功能,又可以看到其社會引導和變革功能。再從代際互動的角度考察環境意識的社會化,可以發現青少年在扮演社會化主體角色的同時,也扮演著社會化介體的角色。當依據制度績效的視角考察這種參與主體意識時,發現這個社會化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制度目標:培育公眾環境參與主體意識,促進環境治理主體多元化變遷。在體現了正向度的制度績效的同時,也影響著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狀態向著自下而上方向的轉變。正是基于以上結論,可以預期,環境公眾參與領域將生長出一股穩健增長的力量,推動著區域環境治理單極模式的變遷和自上而下參與制度的逆向發展。而這股力量將成為一種社會內在的制約經濟盲目發展的因素,推動中國環保事業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