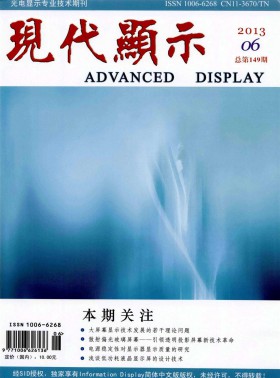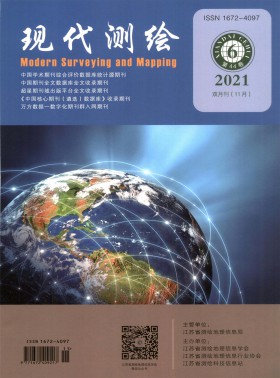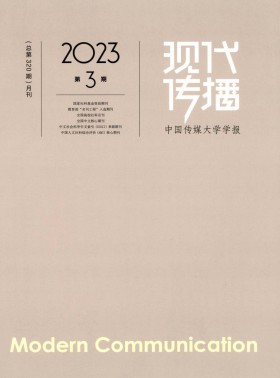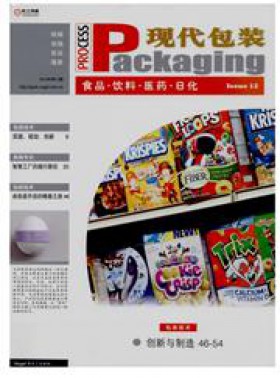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小說的虛構性論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趙攀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
一、小說對虛構的演變———從對虛構的回避到對虛構的全面認定
曹文軒在《小說門》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小說史是以虛構開始的。“小說的起源被推至神話,是一種被普遍認同的說法。如果這一說法果真成立的話,那么,小說史的第一步就是踏在虛構的蒼茫大道上”[1]86。毋庸置疑,神話在后來的漫長歲月中被慢慢演化為小說,作為一種虛構能力預示著小說這種文學形式是完全可以被創造出來的。然而,在小說發展的歷史中,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小說家都對虛構躲躲閃閃,努力營造一個小說等同于歷史的逼真感。華萊士•馬丁曾在《當代敘事學》中寫道:“在最好的現實主義敘事作品中,我們為其真實感所震驚:我們也許根本想象不到我們翻開書頁時會出現什么,但當它出現后,我們感到這是必然的———它抓住了我們歷來所了解的,盡管也許是極其朦朧地了解的,經驗的真實。”[2]67然而,到了20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家們終于對真實感到了疲憊,面對哲學上“真實觀”的崩潰,小說家們也終于摒棄了真實,開始了對虛無、背離、荒誕、陌生化甚至是零度寫作的追求。作者不再扮演“在場者”和“目擊者”這種全知全能的敘述者形象,而是承認“上帝之死”的事實,小說家不再是上帝,小說家必須直面“說謊者”的身份。戴•赫•勞倫斯反復說:“藝術家是個說謊的該死家伙,但是他的藝術,如果確是藝術,會把他那個時代的真相告訴你。這才是要緊的事。”[3]224米蘭•昆德拉也說過:“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假設的。我是小說家,而小說家不喜歡太肯定的態度。”[4]66普魯斯特居然聲稱,在整本書中,“沒有一件事不是虛構的”[5]345。在世界文壇上享有盛名的英國作家約翰•福爾斯則更勝一籌,在小說中直接討論小說寫作的虛構性。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人把他看成是英語世界里最偉大的現代作家和第一個后現代小說家。他的代表作《法國中尉的女人》(下文簡稱《法》)一經問世,立即引起轟動。有評論家說,福爾斯的聲名大振,不僅僅因為他像托馬斯•哈代那樣是一個講故事、描摹景物的高手。他的出色之處還在于:他的小說從不重復同一個內容,文體也因書而異,給人以不斷推陳出新的新鮮感。有關《法》的評論從存在主義到后現代敘事策略,從自由主題到女性主義以及和某些現實主義作家作品的互文性解讀數不勝數,足見其在評論界受重視的程度。筆者在此只對福爾斯在《法》中對小說創作的虛構性進行解讀,以凸顯虛構性在小說中起到的強大功效。
二、虛構的功效
虛構的功效之一:彌補現實或逃避。虛構就是為了彌補現實。“現實是遠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甚至是千瘡百孔的,造物主的設計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對于那么多的缺憾,我們一直未能找到補救的辦法。而小說的出現,卻使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與哲學和詩不一樣,小說擅長的就是描繪實狀。這個實狀完全可能是虛擬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小說當初出現,就是帶了這種彌補現實的天任的。這也成了它存在的理由”[1]96-97。福爾斯在《法》中對莎拉的虛構是為了彌補現實中不盡如人意的莎拉。小說以哈代的詩歌《謎》開篇,女主人公莎拉是一名在眺望大海的神秘的黑衣女子,進入讀者眼簾的是一個與維多利亞時代淑女形象格格不入的另類形象。而萊姆鎮上的人又把她描述成“悲劇”、“法國中尉的婊子”、“墮落的女人”和“被社會遺棄的女人”各種名詞的混合體。而站在她的對立面的歐內斯蒂娜卻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淑女。用一個充滿爭議而且并不漂亮的另類女性莎拉來彌補美麗聰慧看似完美的傳統女性歐內斯蒂娜似乎有些荒誕,而這恰恰是福爾斯創作的精妙所在,他在告訴讀者一個哲理:世界無真實,缺憾即完美。而具備這么多“缺憾”的莎拉讓我們看到了什么希望呢?作者這樣來描述莎拉的外貌:“在他們那個時代,最受推崇的女人面容是文靜、柔順、靦腆。那張臉不像歐內斯蒂娜的那么漂亮。不論什么時代,也不管用什么樣的審美標準衡量,那確實不是一張漂亮的臉蛋兒。
但那卻是一張令人難忘的臉,一張悲涼凄切的臉。那張臉上所流露出的悲哀,正像樹林中所流出的泉水一樣,純凈、自然、難以遮攔。那張臉上沒有矯揉造作,沒有虛情假意,沒有歇斯底里,沒有騙人的面具,最重要的是,沒有神經錯亂的痕跡。”[6]35作者宣揚的是莎拉的一種自然美,悲劇美。而她對男主人公查爾斯的吸引又遠非如此,莎拉具有和男人一樣的思想和情懷,查爾斯對莎拉不僅有同情還有敬佩和某種相近的感覺。而莎拉本人對萊姆鎮上的人對她的誤解和詆毀卻抱一種漠然的態度,她心里想,“侮辱也好,指桑罵槐也好,都不能動我一根毫毛,因為我已把侮辱和指責置之度外了,我一錢不值,我幾乎不再是人了,我只是法國中尉的娼婦”[6]177。莎拉具有在逆境中生存的決心和勇氣,她在“法國中尉的娼婦”的惡名下獲得了一種自由,她的離經叛道、不合時宜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她的惡名成了她的避難所。也恰恰是這一點讓她不僅對男主人公查爾斯而且對讀者都具有一種像謎一樣強大的吸引力。
如果說福爾斯虛構的莎拉是對現實中不能掌控自己命運的眾多莎拉的彌補,那么男主人公查爾斯身上卻有很多“逃避”的痕跡。當然我們首先要重新理解“逃避”。曹文軒的觀點是“小說帶領我們背棄現實,而逃避到它所構造的世界之中。小說成了焦灼心靈的港灣和荒漠面前的綠洲”[1]97。在《法》的前十二章,福爾斯對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寫作方式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模仿,其中在第四章他全知全能地告訴讀者查爾斯個什么樣的人,“讀者們將會看到,查爾斯有好高騖遠的毛病。聰明的懶漢為了證明自己懶得有理,總是要好高鶩遠的。總而言之,查爾斯有著拜倫式的游手好閑,卻沒有拜倫那些發泄情感的途徑:作詩和尋花問柳”[6]56。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里的查爾斯無法逃避作者對他的安排和評價,這是傳統小說的慣用手法。然而到了第十三章,福爾斯完全換了一種口吻,承認作者的無能為力,他不僅不知道莎拉是誰,她從哪里來,而且對查爾斯也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在文中寫道,“一個計劃的世界是一個僵死的世界。只有在我們筆下的人物和事件開始不受我們的約束時,它們才開始變得活生生的。#p#分頁標題#e#
當查爾斯離開站在懸崖邊緣的莎拉時,我命令他直接回萊姆鎮去,可是他并沒有那樣做,而是轉身走下坡,無緣無故地到牛奶房去了”[6]128。當代小說里的查爾斯逃避了作者固有的安排,小說人物從作者筆下逃脫出來,有了自己的主見,獲得了人物該有的選擇和自由。然而查爾斯對莎拉的態度卻是一直有所回避的,盡管莎拉的叛逆和孤獨、不明的身世和復雜的經歷對他有一種強大的吸引,可他總在提醒自己不能和這個女人太過接近。在第十九章的末尾作者道出了他的心聲:“而經過自然選擇的查爾斯卻非常聰明,頭腦清醒,自由自在,像永遠閃爍的明星,對一切都能理解。唯獨莎拉,他不能理解……”[6]163對于查爾斯最初對莎拉的逃避讀者無可厚非,那個時代的查爾斯就應該是那樣的,墨守成規,循規蹈矩,安度一生。然而作者筆下的查爾斯卻要橫跨兩個時代,現代的查爾斯不允許他總是躲著,查爾斯重新開始了思考,面對莎拉對自己境遇的漠然態度,他驚住了,“查爾斯在那兒呆呆地站了半晌。那女人好比是大門,男人卻沒有鑰匙”[6]205。后來莎拉主動聯系查爾斯,說是引誘也好,她在幫助查爾斯打開桎梏,找到那把“鑰匙”。從《法》中的第十八章中讀者可以了解到查爾斯的多種性情,“對于這一現象,從生物學上解釋,就用得著達爾文的一個術語,叫做‘保護色變’,即學會與環境協調一致,以便求得生存。年齡變了,社會地位變了,相應的變化也就勢在必行。在維多利亞時代,這種保護色變已成公理,極少有人提出疑義。然而,莎拉的目光卻充滿了疑義。它直射查爾斯,但也有著膽怯的成分。這種目光的后面隱藏著一個現代術語,叫坦白交代,‘查爾斯,坦白交代!’它要求他去掉自己的保護色變,迫使他的內心失去了平衡”6]155。查爾斯最終在莎拉的目光下妥協,放下防衛,具備了新的勇氣。他最終解除了和歐內斯蒂娜名存實亡的婚約,放棄了一成不變的生活。然而莎拉并非只為了拯救查爾斯而存在,莎拉注定要離去。莎拉的離去卻讓新時代的查爾斯毅然決定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小說至此,莎拉拯救查爾斯的任務已經完成。查爾斯的“逃避”有了新的意義,他不僅從一成不變被安排好的婚姻中逃避出來,從貴族的身份中逃避出來,也從作者的筆下逃避出來,在新女性莎拉的幫助下成為一個追求夢想、敢于直面一無所有的人生的人。
虛構的功效之二:保持人類的想象力。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說過:“想象力的自由除了受制于感性外,從有機結構的另一極看,它還受制于人的理性。嶄新世界或嶄新的生活方式的最大膽的想象,仍然是由概念指導的,仍然遵循著代代相傳的、精織于思維發展中的邏輯歷史。”[7]111這一論斷無可厚非,然而與此同時也恰恰是因為概念太多反而束縛了人的想象力。關于這一點曹文軒說過,“知識史,實際上是好知識與壞知識對抗甚至是惡斗的歷史”[1]99。他認為“壞知識最可詛咒的地方,是它破壞了人的想象力。它讓無數的僵死的、違背人性的甚至是充滿惡毒的概念,成為數不勝數的可怕的藤蔓,對人的想象力進行千纏萬繞,甚至使想象力枯萎。我以為人的最大悲劇,既不在于愛情的毀滅,也不在于事業上的一事無成,而在于想象力的損傷與衰竭”[1]99。而這正是小說存在的意義,“因為小說是對想象力的操練,并激發起人對想象力的留戀。它是為數不多的可將人的想象力保持住的辦法之一”[1]99。《法》中最具想象力的虛構當推它的三個迥然不同的結尾。第一個結尾在第四十四章,查爾斯選擇離開莎拉,仍與歐內斯蒂娜結為連理,回到了原來的生活軌跡。第二個結尾在第六十章,查爾斯歷經磨難后終于找到莎拉,找回了夢寐以求的愛情,有情人終成眷屬。第三個結尾在第六十一章,查爾斯雖然找到了莎拉,莎拉卻拒絕了他。莎拉選擇在一個叫羅賽蒂的拉菲派畫家家里從事藝術工作,作者此時還設計了一個叫“拉拉治”的小孩出場,查爾斯在懊惱和疑惑中離開,真正開始了在生活洪流中的自由選擇。對于“拉拉治”的出場,作者給予了這樣的解釋:“時間已經證明,小說家是不在自己作品的結尾引進新的人物的,除非這個人物無足輕重。我想,拉拉治的出場還是可以說得過去的。”[6]521拉拉治的出場雖說無足輕重,但是也增加了莎拉的獨立精神。
無論是莎拉還是查爾斯都沒有什么最終的結果,福爾斯給了他筆下的主人公以充分的自由,也給了讀者自由想象的空間,他不再去操縱小說里任何人物的命運,虛構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作者只想說明世上并無“決策者”這樣一個道理:“我繞了一個大圈子,實際上還是回到了我本來的原則:像本章的第一條引語所說的那樣,世間萬物的背后,并沒有支配一切的神仙。”[6]545其實早在第十三章里,作者就承認了他的虛構:“我講的故事純屬想象中的虛構。我塑造的這些人物只存在于我的心目中。如果迄今為止,我仍然假裝我對我創造的人物內心深處的種種思想深有了解,那是因為我寫作的手法是我寫的這個故事的時代所普遍接受的。在那個時代,小說家僅次于上帝。他不見得什么都懂。可是,他總是想方設法裝出一副樣子,似乎他什么都懂。但是,我卻生活在產生了阿蘭•羅布—格里耶和羅蘭•巴特的時代。如果這是一部小說,它不可能是一部現代意義的小說。”[6]101這也就是后來被命名的“元小說”創作,也就是說這是一部“關于小說的小說,是關注小說的虛構身份及其創作過程的小說”[8]238。李丹在其論文中也說道:“福爾斯在1973年出版的《詩集》中論述了小說的虛構性和游戲性:‘小說與謊言是最親密的表親。’”[9]90然而這種虛構和謊言卻意義重大,曹文軒曾闡述過,“小說家是騎士,是堂吉訶德式的騎士。他們騎在虛構的馬背上,不僅走遍了現實,還走進了現實疆域之外一個無邊無際的虛空”[1]101。福爾斯在《法》的結尾處其實也彰顯了這種虛空,既像是在勸說查爾斯,又像是自言自語,更像是告訴讀者要用新的眼光來欣賞小說:“雖然莎拉在某些方面似乎完全適合扮演獅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的角色,但生活并不是一個象征,并不是一個謎,不是一個猜不透的謎,生活并不是執著追求某一個人,不能看作一著失算便滿盤皆輸,更不能立即輕生;生活應當是忍受———盡管在這無情的城市中忍受是何等的無益,何等的無效,何等的無望。再說一遍,生活的洪流滾滾向前,奔向那深不可測的、苦澀的、奧妙無窮的大海———”[6]556福爾斯在小說創作形式上的創新已經毋庸置疑,更可貴的是他的創作帶給讀者以無盡想象的空間并激發了讀者和其他作者或許早已缺失的想象力。#p#分頁標題#e#
三、對虛構的現代性理解
關于對虛構的現代性理解,筆者想再次引用曹文軒的觀點:“對虛構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的最徹底的理論支持是:存在即虛構———存在便是不真實的。”[1]107被稱為“哲學小說家”的福爾斯自然受到過法國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存在主義不是一種僵死的哲學,而是一種實用的個人主義哲學,它幫助人們在特定的處境中得以生存。莎拉的生存環境是特定的,即她可以在一系列虛構的名分下生存。她虛構了自己和法國中尉有一段不堪的戀情,虛構了不為眾人所接受的一些虛假事實,當查爾斯真正走近莎拉時發現她原來還是一個處女,這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她卻從不去辯解。也就是說莎拉可以活在虛構中,卻不能活在真實中。正如陳靜所言,“莎拉似乎只有在假面之下才能真實地安置自身。她似乎是同性戀者,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查爾斯的拯救者,又似乎是他的陷害者;她似乎是貞女,又似乎是蕩婦。福爾斯不斷地建構她的形象,又不斷地消解她的形象”[10]99。莎拉實存的表面真實與實存的底部真實完全不一致,甚至是互相拆臺、互相消解的。福爾斯在《法》中對莎拉的創造徹底揭露了存在的虛構性。現代小說的虛構也體現在它的反邏輯傾向上。
“二十世紀的小說家被保守勢力視為反理性主義,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二十世紀的小說家對邏輯的回避與輕視。由反邏輯而生發了其它許多現象:反說教,反解釋,反清晰……”[1]111《法》這部小說無論是人物的創造、情節的安排,還是極具特色的結尾都具有很強的反邏輯性,它的每一步發展都似乎不按常規,都似乎超出了讀者的預料。對小說本身加以懷疑是現代小說推出的重磅炸彈,“它把世界的虛構性推向了極致”[1]113。在《法》中福爾斯不僅揭露了小說本身的虛構性,而且還混淆了作者與人物、人物與人物。書里書外分不清楚。“一切變得不可確定,如霧中之人,夢中之事”[1]114。作者與人物的混淆主要體現在作者時而是敘述者或者是講故事的人,時而又跳進書中扮演一個角色。《法》中的第五十五章,作者就以一個大胡子的形象出現在小說里,作者福爾斯和男主人公查爾斯在同一列火車的車廂內不期而遇,雙方都抱以冷漠的目光。查爾斯對作者福爾斯的印象是:“這家伙肯定是個讓人討厭的男人,一個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因此,如果他想同我談話,我一定會斷然拒絕。”[6]316福爾斯原本打算“就在此時此地結束查爾斯的生涯,讓他永遠地停留在去倫敦的旅途中,以此了結這個人物的存在”[6]316。然而他并沒有這樣做,他對人物進行了放手,把自由交給人物,讓他自己決定自己的方向和命運。人物和人物的混淆主要體現在一個人物的多重身份上。小說的第三十八章中這一特點最為明顯,三個時代的查爾斯同時出現:“一二六七年,查爾斯帶著法國人的新觀念在尋求圣杯;六百年后,即一八六七年,查爾斯對經商頗為反感;今天的查爾斯可能是一位計算機科學家,他對那些善良的人道主義者的大聲疾呼充耳不聞,那些人自身已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人們可能覺得這三個查爾斯之間毫無聯系。事實遠非如此。他們都反對‘占有’是生活的目標這一見解。”[6]248當然這里的查爾斯并不指某一個人,而是指當時的任何一個英國人。
主人公查爾斯與三個時代泛指的查爾斯完全混淆,小說的虛構也達到了極致。福爾斯在《法》中對小說虛構性的探討無疑是現代小說寫作的典范。推而廣之就可以說虛構大搖大擺地走進了現代小說,那么現代小說作為一種虛構之物有何存在的意義?再次引用曹文軒的一句話,小說帶給我們的“僅僅是精神上的快感、智慧上的磨礪、美感上的熏染,而并不能幫助我們去解決任何一個實際問題。小說不能成為研究所、勘察隊與移民事務局”[1]110。彰顯虛構的小說也是一種文學欣賞,而“文學欣賞,本就是一種非功利、非物質性的精神遨游,它們到底是實在還是非實在,一切都無所謂”[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