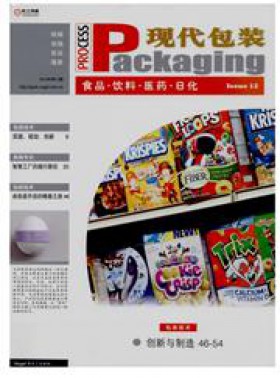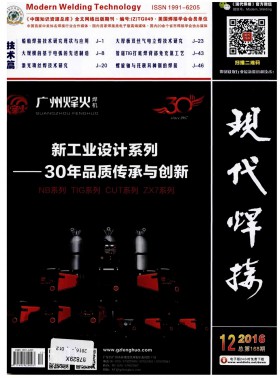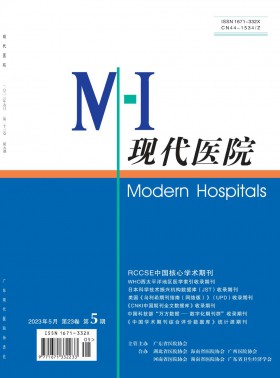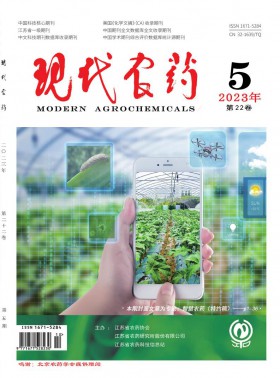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文學批評史寫作方法嬗變,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為文學史寫作類型之一的文學批評/理論史寫作,既受制于寫作者身處時代中主導的學術思潮與風尚,也受制于本身的史識、視野與趣味,以及編纂者在凝思歷史時被激發的情懷。現代文學批評史的寫作,始于“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重寫文學史”的思潮。至今已有若干有影響的著述,如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教程》(再版時改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劉鋒杰《中國現代六大批評家》、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及《新編》,還有曠新年《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二部之下卷)、余虹《革命•審美•解構》等。本文不是要對所有此類著述一一評點,而是想考察:在后“”時代,已經名聲不再的正統文學史觀蘊涵的總體性敘述是否還可能?如若可能,它作出了怎樣的變通以適應“新時期”的知識—精神氛圍?在“新時期”之后,那種帶有總體性的歷史敘述意識是否還在?如果還存在,它又以什么形式存在于編纂者的編撰活動之中?它隱含的歷史意涵是什么?
一、正統文學史觀的尾聲
王永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三卷本)(以下簡稱《理論批評史》)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版,這是現代文學批評史寫作的開始。[1]然而,這部得到王瑤、李何林等前輩學者肯定的著作,可以說是正統的新民主主義敘事框架的延續。和唐?本的現代文學史一樣,作者首先肯定現代文學批評史的新民主主義性質,而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則是“我國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的終結,社會主義文藝運動的開始。”[2]作者將現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看成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實現的過程,而作者自述編寫此書的目的在于建設“有本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3]這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表述,因為作者在一開始就把現代文學批評史定性為馬列主義在中國從萌芽到和中國革命結合,最后完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文藝思想。然而,到了作者所在的時空,又要重新建設有本國特色的馬克思文學理論體系。一個已經實現的體系和一個有待完成的體系之間究竟是怎么樣的關系?如果一個體系已經建成,為何又還要重新建設?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試圖堅持正統的文學史觀與敘述模式的寫作者在“新時期”面臨的尷尬。
和20世紀50年代末“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由革命學生編寫的各種現代文學史相比,《理論批評史》的編纂者們已經從嚴厲的階級斗爭思維后退。作者將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論爭區別對待:左翼文學與沈從文、施蟄存等的論爭看成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而左翼文學內部的論爭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路線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之間的斗爭,而是“我們”內部的意見沖突。但是,胡適、陳源、梁實秋還是被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比如梁實秋,就被當作是配合國民黨對革命文化圍剿的需要,因此,作者認為左翼陣營對梁實秋的批判是“當時‘圍剿’與‘反圍剿’的重要戰役之一”。[4]在作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區分之后,作者便在學科性質的名義之下,才對批評家在文學本體層次上加以肯定。但是,這種有條件的客觀性敘述,總是要被歷史總體性判斷所侵擾。黃修己對《理論批評史》中局部的學科客觀性表示贊賞,認為它“畢竟是80年代的作品,總會有其新意”。例如,黃修己認為編纂者“給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各立一節,細述他們的文學觀”。“恢復了‘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文藝思想家的面目”。[5]但是黃修己沒說的是,作者在介紹了他們的觀點后,馬上就要對他們的觀點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例如,將胡適的功績僅僅定位于提倡白話文學,“五四”之后“背叛反封建統一戰線,倒向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勢力的發動營壘”。“墮落成新文學運動的敵人。”這種評價,并不是作者作為保護色的一種寫作策略,而是作者所依傍的構建歷史敘事的總體性模式所致,既然現代文學批評史的本質是馬列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實現過程,在這種歷史一元論敘事中,胡適、梁實秋等必然要被樹立到對立面,并且成為被必然性淘汰、消滅的力量之代表。
這些細節的處理,可以看作是正統的文學史書寫模式在新時期面臨的尷尬,而作為專門史的文學批評史寫作來看,王氏又打開了現代文學史寫作的另一個領域。在這個意義上,王氏的批評史寫作既是一種開端,也是一種終結。該書上冊初版于1986年,即使站在1986年來看,該書也是撥“亂”有余,返“正”則不足。許志英等在1980年代初為了返還歷史原貌而撰文試圖恢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性質。新一代的學人也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主題是“改造民族的靈魂”。[6]王氏為了堅持新文化運動是馬克思主義領導的,不惜從《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找出片言只語來證明提出了“新文學”建設的重大問題,只為證明五四新文學理論的馬列主義性質,這只能說是為了維護正統史學觀而騰挪跌宕了。在新民主主義的這樣的歷史主義敘事框架中,無論怎么騰挪,終究無法返本(返回文學史)開新(建設有本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論體系)。
二、總體判斷的懸置與重述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教程》(以下稱《教程》)出版于1993年,劉鋒杰的《中國現代六大批評家》出版于1995年。這兩部以個案體例編撰的現代文學批評史,是“重寫文學史”的構成和結果。王永生等編著的《理論批評史》某種意義上是溫著的對話文本。溫儒敏拋棄了王氏所采用的新民主主義這一總體性敘事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溫著才是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開山之作。它也是最早把“現代性”這一范疇引入現代文學批評史敘述的著述。溫儒敏并不放棄呈現歷史總體面貌的追求但懸置了對文學批評史的總體性判斷。總體性判斷的懸置給溫儒敏的批評史寫作帶來極大的便利。因為,帶有總體性的歷史敘事,為求得敘述的統一性而必對批評家進行列隊、編排、裁剪,進而勾畫出一條可見的有某種指向的運動虛線,最終以此來印證總體性中蘊含的歷史理性與目的論,這樣的歷史是“必然性之眼”所見的風景。而溫儒敏懸置總體性問題,就以寫作者的“個體之眼”代替“必然性之眼”,他就可以采用個案式的體例來安排他的評述對象,可以采用隨物(對象)賦形(批評特征)的方式靈活處理批評家。而批評家最有個性的文學主張和鑒賞活動可以不因尋求標準的統一而被遮蔽或被過分地凸顯。例如,對王國維,作者著重闡釋王國維文學批評所蘊含的“現代性”;而對周作人,則側重他的“人的文學”觀念及隨后的變動,等等。這樣,作者就勾勒了在他看來批評家最有特征的部分。對周揚,作者觀照他一生的文學批評,而成仿吾,作者只討論他前期創造社時期的批評活動。同樣是左翼批評家,周揚的批評可以討論到1980年代,而茅盾在1949年后的批評則被忽略。這種對對象看似自由的處理,可以極大幫助作者凸顯對象的批評特色與成就,彰顯敘述對象最閃耀的思想晶片。#p#分頁標題#e#
陳平原認為:“所謂‘著述體例’,不僅僅是章節安排等技術性問題,還牽涉到史家的眼光、趣味、學養和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場等等,不能等閑視之。”[7]《教程》之所以冒著體例不統一的風險,除了說明著者文學觀的寬容與多元外,其實和作者對文學史總體性判斷的懸置有關。以李健吾為例,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確代表了京派批評家那種審美主義批評的典范,但是在1940年代,逼仄的歷史就開始改變作為批評家的李健吾的審美感覺,社會歷史批評的批評范式開始入侵1930年代形成的印象式批評。[8]這種感知模式的變異其實是歷史發生異動的苗頭與暗示。在新民主主義的敘述框架內,李健吾的變化恰恰可以印證他拋棄了資產階級的審美向無產階級的趣味轉變,從而印證“人民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終將成為文學史的終極這一歷史必然性。溫儒敏將李健吾定格在審美主義批評家上,恰恰以一種微妙的方式瓦解了正統史觀帶來的書寫壓力。溫著認為周揚的“異化”論是一個老革命試圖返“(馬克思之)本”開“新(時期)”的最后掙扎,認為他在人道主義問題上將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啟蒙人道思想接續起來的努力為新時期打開了文學回歸“五四”人學的通道。同時也認為周揚的是有歷史合理性的革命批評家。兩個周揚都有存在的歷史合理性。如果不是摒棄正統的總體性敘事(新民主主義),如果不是懸置新的總體性敘事(啟蒙敘事),著者恐怕很難在邏輯上自我說服。
如果說溫儒敏采用了“去總體性”的方式敘述現代批評史,那么劉鋒杰則在19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基礎上重置了另一種總體性。劉鋒杰的《中國現代批評六大家》(以下稱《六大家》)雖然沒有以“批評史”命名,但是作者對批評史有明確的總體性判斷。作者在“余論”指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一場沒有完成的建構。”[9]而之所以未完成,乃是因為從錢杏?到胡風這些批評家堅持“人和文學對政治的服從,故而他們代表之文學思想的勝利”,使得“中國現代批評不是走向宏大與精深,而是走向極端與片面”,最終“埋下了眾多現代批評在當代的畸變,乃至癌變”。[10]劉鋒杰對現代文學批評史總體判斷帶上濃重的1980年代的色彩,但是他和1980年代構成了既承接又對話的關系。19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元話語”是“救亡壓倒啟蒙”敘事模式。[11]而他小心翼翼地析出“救亡壓倒啟蒙”這一敘事模式遮蔽的復雜性。作者認為,周作人自身對自己的“人的文學”的退卻,李健吾對自己的“純美文學”的偏離,乃是一種“啟蒙的自我瓦解”。而周揚等則是從外部瓦解“人與純美的文學”,這是“革命壓倒啟蒙”。因此,現代文學批評成了未竟之事業。這樣的敘述構架為現代文學批評的發展留下需要填補的“空白”,只有填補這一“空白”,才有現代文學批評的實現。而這一“空白”并非任何一種思想都可填上,這是一個意向性的“空白”,只有“新啟蒙”的現代才是合適的填充之物。這就必然導出1980年代“新啟蒙”的歷史合理性。
劉鋒杰認為,“人的軸心”與“文學的軸心”是近代批評向現代批評轉化得圍繞的兩大軸心。而現代批評之所以不同于近代批評的標志就在于它的批評家提出了這兩個標準并付之于實踐,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在這一理路衡量下,劉鋒杰提出了不同于溫儒敏的起點判斷,周作人成了有“起點”意味的批評家。他的主題不斷地被后來者或片面式地分享或結構性地顛覆并重新表述。劉鋒杰在勾勒各個批評家的批評思想的輪廓時,都能圍繞著這兩個話題來展開:文學該表述怎樣的人,或文學該遵循怎樣的藝術規則。作者評述對象時能夠持比較、聯系的視野與歷史的觀念。例如茅盾,作者在討論他的“人”學思想時,將周作人、鄭振鐸并置,這的確可以比較清晰地呈現論述對象的主張。更重要的是,作者認為茅盾是在接過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觀念時,將它化為更具體“為人生”的文學,并為此論題帶來新的階級意涵。作者在比較了鄭振鐸、周作人和茅盾的“為人生”的文學觀后,認為只有茅盾的“為人生”的文學觀內在存在使他“成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同道者,做好了必要的準備”的意向性結構。[12]作者在敘述批評家自身內在的觀念與時代選擇之間的契合時,其實已經暗示了“五四”人學思想的消解命運。劉鋒杰通過對對象的核心觀念/表層觀念之間的變動與消長的考察,看到歷史發展的輪廓。而這個輪廓恰恰映出的作者在“余論”中做出的總體性判斷:現代批評的未完成性,也就是“五四”所提出的關于人的方案的未完成性,更是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
三、“復數現代性”的闡釋路徑與潛伏的歷史幽靈
一般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現代性”討論的后果就是“復數現代性”的發現,以及瓦解了由“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所建構的文學史觀,[13]全面地改變了“新啟蒙”視野下的現代文學觀念。啟蒙與革命、傳統與現代、民族國家與全球化、思想創造與知識生產等諸多命題被重新討論。由思想向學術的變化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在1980年代末受挫的心理表征,他們在“新啟蒙”被中斷后試圖查探并理解歷史的復雜性;另一方面,1990年代的學術明顯地被納入了全球化的知識生產場域。影響1990年代的學術風氣很明顯有一批側身西方學院卻活躍于大陸學界的華人學者。“復數現代性”擴大了現代文學史敘述空間。“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在1990年代受指責的原因是它仍然是一種線性文學史觀;這使它成為一種新壓抑機制,排斥了左翼文學實踐,確立“西方中心論”,神話化“五四”等等。正如80年代的文學反思影響到1990年代的批評史寫作一樣。上世紀90年代的討論影響的是新世紀的批評史著述。新世紀初,兩本文學理論史性質的著作出版:一是曠新年著《二十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二部之下卷;以下簡稱《學術史》),另一是余虹所著《革命•審美•解構》。這兩部批評史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現代性反思的產物。曠新年的《學術史》,無論是體例安排還是所討論的話題,都可以發現作者集中討論的是左翼文學的話題,作者也沒有要掩飾自己的價值立場與敘述傾向。20世紀末,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浮出歷史地表”,知識界的分裂自此開始。各方不再掩飾自己的主張和立場。曠新年在自己的學術寫作中,亦深深地滲入自己對歷史的價值判斷。《學術史》設定的話題有:“現代文學觀念的演化”、“文學的定義”、“文學的重新定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本質和功能”、“大眾化與民族化”、“新詩理路建設”、“文藝思想”、“胡風的文藝思想”。這些問題都是基本都是左翼文學的話題。大陸當下社會的急劇分化,帶給知識分子新的“階級”體驗,這種體驗又喚起他們的左翼文學記憶;全球化的知識生產,給他們帶來重鑄左翼文學的知識合法性。曠新年認為,左翼文學一方面是“解構”的文學,它通過重新定義文學,重釋文學的功能,它在反抗資產階級文學神話;同時他也是“建構”的文學,它建立自己的霸權,并在民族國家建立中融入現代官僚體制。而左翼文學的這種悖論也是中國的復數現代性之表現。在曠新年的闡釋框架中,胡風和都是對現代性的悖論有深深體察的思想者,所以“胡風的悲劇命運并不像通常人所說的那樣是反封建的英雄,而是從一種特定的角度出發對現代性的悲劇思考和抗爭”。[14]由于建國后的無論中國文學體制還是國家政權都迅速地官僚化,同質化,韋伯用“鐵籠”來形容這種建立在現代治理技術上的官僚體制,這種官僚體制對文學中人的觀念的影響,就是把人也看成是抽象的階級人。而由于對“現代性矛盾的復雜思考”,“對黨八股、教條主義的批判”,因而成了胡風的一同反抗現代性的“理論同調”,[15]而周揚、林默涵等則成為現代性負面的象征,所以被“官僚主義的天然敵人”“在‘中’打倒”。#p#分頁標題#e#
曠新年認為,胡風的悲劇乃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悲劇,因為,新文學的本質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民族國家又是20世紀中國人從梁啟超開始就追求的現代國家形式。而作為“民族國家文學”的“現代文學”必然帶上悲劇性的撕裂品質,因為,作為民族國家文學,它要為民族國家提供關于人的意識形態來構建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它又要以“文學的感性”去反抗民族國家“同是一種既建構現代性又反抗現代性的悖論結構。而胡風和都是這樣和現代性矛盾抗爭的悲劇英雄。這也是為何曠新年要死死地抓住現代文學的“民族國家文學”的本質,并將和胡風的文藝思想單列作為最后兩章。曠新年對“左翼傳統”的闡釋,其意旨應該不是要為教條化的左翼文學正名,而是要從教條化的左翼文學中拯救“左翼文學”。因為左翼文學已經被“馴化”,[16]因此需要恢復左翼文學的反抗與批判功能,為當下的知識與文學批判尋求“傳統”,建構歷史的合理性。曠新年一方面用“歷史化”來消解“五四”資產階級文學觀的的永恒性,一方面又以“非歷史化”的方式來闡釋“左翼傳統”,恐怕這是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矛盾。曠新年不僅利用“復數現代性”拯救了1980年代聲名狼藉的“左翼文學”,而且,通過“復數現代性”重新敘述了現代文學的知識系譜,這一敘事模式本身就是對1990年代以來“中產階級文學敘事”的反抗。已故的余虹教授所著《革命•審美•解構》也描述了20世紀文學理論演變史,他把左翼文學和審美人道主義文學視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的兩面。著者將20世紀的文學理論的演變勾勒了兩條線索,一是開啟于梁啟超的文學工具主義線索,一是起端于王國維的審美自主論傳統。
兩者的沖突都是現代性文論之間沖突,而不是先進/落后、革命/反動、現代/古代之爭。文學工具主義在“五四”后融進中國現代的政黨政治實踐而演成“革命文學”,并隨著政黨政治的發展而先后表現為“主義”話語、“政策”話語、“領袖話語”三個階段與形態。它的強勢與衰敗和政黨政治的生態緊密相關。審美自主論的內在理路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它不可能有集團式的抗爭。在余虹看來,審美自主論之所以無法抗衡革命文學話語,除了言論制度等原因,還有就是“有效地質疑現代性必須有一種后現代性思想,而審美自主論的思想資源仍是現代性的(亦即一種意識形態反抗另一種意識形態)”。[17]最后一點才是作者所著重論述的。審美自主論在80年代的復興而成為中國現代性沖突的主導方面,也是和政黨政治疏離文學工具主義有關,而非源自自身的邏輯力量。因此,這是一種“顛倒”,而非“終結”。“‘終結’有賴于從根本上抽取其基礎”,而要抽取其基礎只有“跳出現代性話語的形而上信念才有可能。”[18]以余虹之見,現代性話語的標志就是它們都是一套建立于科學的意識形態話語,而80年末對文學現代性的瓦解在兩個路徑上展開:一個“解構‘自我’”,使得作為審美自主論的“元話語”人道主義成為虛幻,另一條路徑是“解構‘現實’”,從而瓦解了文學工具論的真理性。兩種質疑都指向現代性的形而上學基礎:即歷史理性和語言理性。歷史理性認為通過目的論來構建現實主義敘事中的“現實”,而語言理性則相信語言可以再現自我與世界。瓦解了歷史理性與語言理性,由現代性話語構筑的文學與世界的確定性鏈條出現了松動甚至斷裂。文學理論由“大理論”變成了“小批評”,“其理論的啟示性源泉不再是作為科學意識形態的元話語,而是不確定性的偶發性文學經驗和自身不斷受到質疑的‘小批評’”。[19]但是,這種“小批評”形式存在的文學理論話語,在風行一時后也被質疑。因為它使文學走向了審美形式主義和神秘主義。“文學”和“歷史”之間的關聯斷裂后,但是“歷史”依然還在顯示它的意欲和走向。這樣,“小批評”式的文學理論受到當初他們自己的倡導者如王家新的質疑。一種“奧斯維辛之后的詩學”作為重構“文學”與“歷史”的關聯的方案提出來。它的提出,是“為避免‘一元決定論’或‘虛無主義’的兩極搖擺”。[20]無論是曠新年的左翼文學路徑,還是余虹在后現代語境中對“奧斯維辛之后的詩學”的暗贊,都是在“現代性”遭到質疑之后的理論話語重建實踐。曠新年將目光投向文學史上反抗的文學,而余虹在敘述文學理論的范式變遷:現代性內部矛盾的演變到現代性終結,到文學理論的后現代性的出現。這樣的敘述模式最后帶出了“奧斯維辛之后的詩學”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兩者都是對百年之前的啟蒙之未竟事業的回應。那未完成的現代依然以幽靈的形式潛伏于知識人的言說沖動之中。
結語
新民主主義敘事不是純粹的歷史知識范式,它是一種總體性。因為,總體性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方法論。在人類社會的幾個階段的辯證替代過程中,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成了可以把握這中歷史總體性的力量。史前時代的所有階級都只能片面地理解歷史與自身的命運。他們是必然性的表象,碎片,是歷史朝向終極目的運動最終實現自身的必要的階段。而新民主主義就是這樣的有本土特色的歷史主義話語。然而,這套終極話語在1949年后的實踐中走向衰憊倒是很符合辨證法哲學。王永生主編的批評史內部結構的分裂感,舊模式與新的歷史內容之間的不協調,以及試圖維持作為“元話語”的新民主主義敘事的勉強,都說明這一總體性的衰落。畢竟作者所處的是1980年代。在這樣的總體性敘事衰落之后,建立在新的總體性敘事基礎上的批評史是否還可能?溫儒敏摒棄了這樣的敘述結構和判斷。劉鋒杰和他相反,在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的基礎上,他在自己的批評史中重申了自己的啟蒙主義的文學觀。
從短歷史的角度看,啟蒙主義框架中的歷史敘事也是一種帶有總體性品質的敘述模式。因為它也是有濃厚價值判斷色彩的歷史主義之一種。因此,它也遭到新的知識范式的攻擊。曠新年和余虹都是在“復數現代性”的視野中探討現代文學理論的問題,曠新年借用了西方左派(從老左派葛蘭西到新左派馬爾庫塞)觀念激活已經聲譽不再的左翼文學,激活現代文學的反抗氣質,他要攻擊的恰恰是1980年代建立的啟蒙話語和純文學觀。而余虹則視從晚清到“新時期”的文學理論沖突為現代性內部的話語爭斗,它們無法終結彼此,只有后現代觀念瓦解它們的形而上學基礎之后,才談得上現代性的終結。文學現代性的終結也為文學與世界的關聯帶來脫節的風險,余虹因而提出“奧斯維辛之后的詩學”,以重建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這兩種努力都表明:現代性固然可以終結,而現代所追求的事業于我們仍是未竟之業。這一陳述還可以這樣說:作為時間的20世紀已經過去,但作為問題的20世紀尚未終結。#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