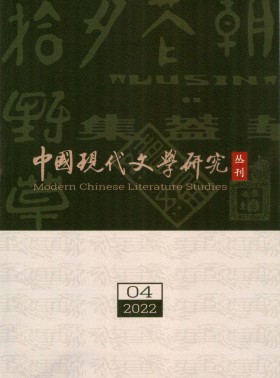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xiàn)代文學女性敘事操作對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從20世紀初葉始,知識精英出于思想啟蒙的客觀需求,采取了一種批判“孔教”詆毀“傳統(tǒng)”的運作策略,進而開啟了文化虛無主義的歷史先河。到了五四時期,詆毀“傳統(tǒng)”之勢,更是被冠以“反封建”的時髦口號,愈演愈烈變得更加一發(fā)不可收拾。魯迅一篇《狂人日記》振聾發(fā)聵,揭示了中國幾千年來傳統(tǒng)文化“吃人”之惡習,故他“對于‘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是強調應“掃除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吳虞更是撰寫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jù)論》、《吃人與禮教》、《說孝》、《禮論》等重頭文章,全面批判和否定了孔子思想對中國人的負面影響。批判“孔教”與詆毀“傳統(tǒng)”,婦女問題自然也就成為了一個社會焦點。他們痛斥“三綱之說,是屠殺民族之利刃也”①。他們甚至還強調說:“自有那三從七出的怪說,便把東方的女子束縛得如同牛馬一般。”②如果不“打破舊禮教信條的束縛,掃除盲從的舊貞操觀念”,一切關于婦女解放的社會討論,都只能是蒼白無力的一紙空談③。故家長專制作為封建婚姻的歷史弊端,也便成了啟蒙精英詆毀“傳統(tǒng)”的極好借口。
一、五四時期兩個偶發(fā)事件的歷史契機
五四反封建“拿女人來說事”,既是一種時尚也是一種策略,啟蒙者在此期間所做的輿論宣傳,顯然都帶有詆毀“傳統(tǒng)”的主觀目的性。這其中“趙五貞事件”與“李超事件”的突然出現(xiàn),無疑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1919年11月15日,長沙《大公報》以《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為標題,率先報道了青年女子趙五貞在出嫁途中刎頸自殺。趙五貞曾受過新學教育且擅長女工,她遵循父母之命許配給吳姓商人,于1919年11月14日舉行婚禮,當吳家人前來迎娶之時,她用剃刀在轎中自殺身亡。關于趙五貞的自殺原因,《大公報》給出了三種不同說法:其一是誤信謠言,以為其夫吳某被抓,所以便由此而萌生了死意;其二是趙五貞曾許配某氏,還未成親其夫就已病故,所以她是在以死去殉情;其三是趙五貞嫌棄郎君年紀偏大,而其父母又收下了對方的財禮,所以她是在以死去抗命。其實無論是哪一種說法,都是因人而異各執(zhí)一詞:“謠言說”是出自于老百姓之口,“殉情說”是出自于保守派之口,“抗命說”則是出自于激進派之口,這真是各取所需莫衷一是。但《大公報》的編輯和記者,卻敏感地覺察到了這件事情的新聞價值,因此他們采取了連續(xù)性的強勢報導,不僅將其視為“為女界爭解放的急先鋒”,并且還將其當作婦女解放運動的鮮活教材,進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大討論。實際上,趙五貞自殺究竟與“傳統(tǒng)”觀念有何關系,這根本就不是思想啟蒙精英們的關注重心,說白了他們只關心怎樣去利用這一事件,以引起社會讀者的強烈反響與充分注意。如果沒有新聞界的連續(xù)報道和思想界的積極跟進,一個出嫁女人途中自殺只不過就是一種街頭巷議,市民們也至多只會刨根問底談論幾天便熱情散盡,更談不上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突破口。比如同一時期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同樣也披露過一則揚州船娘銀貞子抗婚投河自盡的慘劇“新聞”,然而由于報社編輯與記者并沒有采取強勢性宣傳,故而社會讀者與啟蒙精英對此也就反映冷淡不那么關心了。“趙五貞自殺事件”走進了公眾視野,它既授予了激進派以詆毀“傳統(tǒng)”的確切口實,同時又使守舊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其對推動新文化運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
就在長沙發(fā)生“趙五貞事件”之后不久,北京也發(fā)生了一個“李超事件”,而啟蒙精英對于這一事件的社會運作,恐怕更是聲勢浩大有過之而無不及。1919年11月30日下午,北京各界名流齊聚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為一個他們素昧平生的女學生去送葬。李超是北京“女高師”的廣西籍學生,父母雙亡只身來到北京求學,后被檢查出患有肺癌并已晚期,1919年8月病逝于法國醫(yī)院。一個女學生患病身亡原本波瀾不驚,但最終卻演變成了轟動全國的公共事件,在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關鍵人物,當然是那些思想界的啟蒙精英。李超死后其同學便將她生前的往來信件,直接寄給了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希望他能為這位不幸的女學生寫點什么,以便能夠在追悼會上宣讀。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形象代表,不僅欣然接受而且還費時幾天,寫出了一篇洋洋數(shù)千字的《李超傳》,發(fā)表于當時影響極大的《晨報》正刊上。胡適說他之所以要替李超立“傳”,是因為“覺得這一個無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跡很有做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fā)生憐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所以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督軍做墓志銘重要得多咧”。胡適認為李超之死,使“舊家庭的黑暗,歷歷都可想見”:李超本人渴望求學上進,其兄嫂則希望她早日嫁人,故李超桀驁不馴我行我素,成了其兄嫂霸占家產的最后障礙。在胡適看來李超之病乃由心生,而致其抑郁染病的根本原因,無外乎就是女子獨立的經濟問題。故胡適一再申明說:“我為什么要用這么多的功夫做他的傳呢?因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shù)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胡適在《李超傳》的結尾之處,還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四大要義———“家長族長的專制”、“女子教育問題”、“女子承襲財產的權利”、“有女不為有后的問題”———并期望“諸位讀了這篇傳,對于這種制度”,能夠產生深刻的思想反省。京城各界為李超所召開的追悼會,真可謂是規(guī)模空前場面壯觀:蔡元培、蔣夢麟、陳獨秀、、胡適、梁漱溟、吳弱男等社會精英,以及羅家倫、康白情、、黃日葵、鄧中夏等青年英俊,率領千余來賓一起聚首北京“女高師”禮堂。李超遺像上方是蔡元培親自書寫的“不可奪志”四個大字!追悼會上社會名流紛紛演講,他們無不感嘆舊家庭之殘暴,無不表示對女青年之同情。追悼大會從下午2點一直開到了5點,實際上變成了婦女問題的演講大會。#p#分頁標題#e#
無論是“趙五貞事件”還是“李超事件”,無疑都是一種新文化運動的運作策略,只要我們稍加留意一下這兩件事情的發(fā)生時間,就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其實都是當時思想啟蒙最需要的絕好材料。自從1917年1月胡適以《新青年》雜志為陣地,拉開了中國文化現(xiàn)代轉型的悲壯序幕,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反響卻并不那么熱烈,盡管也有林紓之流跳出來撰文攻擊公然反對,但是整個思想界與學術界仍是靜如死水無動于衷。即使是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專號”,新文化的宣傳攻勢同樣是備受冷落無人喝彩,故魯迅才會不無調侃地諷刺說,那時“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也許是感到寂寞了”!“寂寞”的新文化陣營,當然需要人為地制造社會熱點,以便維系剛剛開始發(fā)動的思想啟蒙運動,而“趙五貞事件”與“李超事件”則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歷史契機———這兩起事件不僅使“娜拉”出走具有了民族意義,同時也使《終身大事》具有了現(xiàn)實意義,它極大地激活了反傳統(tǒng)與反封建的社會情緒,使“新思想”找到了它能夠迅速扎根的生存土壤!兩個女性以其悲壯之死,成就了男性社會的啟蒙大業(yè),她們雖死猶榮揚名一時,自然很快便會被人們所忘記,她們唯一能夠留存記憶的,只是男性話語的啟蒙宣傳。陳獨秀在李超追悼會上的慷慨演說,就非常地煽情并且耐人尋味:“李超女士之死,乃社會制度迫之而死耳。社會制度,長者恒壓迫幼者,男子恒壓迫女子,強者恒壓迫弱者。李女士遭逢不幸,遂為此犧牲!”他認為:“蓋皆中國數(shù)千年社會相治之惡習,不以為殺一女人,乃以為死一俘虜耳。……今日亟待解決之問題,非男女對抗問題,乃男女共同協(xié)力問題,共同協(xié)力鏟除此等惡根性,打破此等惡習慣。如李女士、趙女士之悲劇,庶幾不至再見。”④在陳獨秀的意識當中,“李超事件”不是個人的悲劇事件,而是中國女性群體的悲劇事件,而造成這種悲劇的歷史原因,自然又是家長專制的傳統(tǒng)惡習,故女性解放應伴隨著社會解放而進行,而社會解放又應以家庭解放為前提條件。這無疑是男性思想啟蒙者所發(fā)出的共同心聲!
二、中國古代社會“節(jié)烈”現(xiàn)象的真實狀態(tài)
毋庸置疑,從五四新文學開始,封建禮教與家長專制,就是啟蒙精英的批判重點———無論是魯迅的《祝福》、許欽文的《瘋婦》,還是巴金的《家》、蕭紅的《呼蘭河傳》,都帶有明顯反傳統(tǒng)的強烈愿望。問題在于真正意義上的傳統(tǒng)文化,是否如現(xiàn)代作家筆下所描寫的那樣黑暗?即使是國人極度關注的婚戀大事,是否也如現(xiàn)代作家筆下所描寫的那樣糟糕?這種令人困惑的歷史疑問,我們必須從歷史原場去尋找答案。
我們先來說一說五四時期攻擊最猛烈的“節(jié)烈”與“貞節(jié)”問題。目前已有學者依據(jù)《古今圖書集成》一書,對于中國古代社會歷朝歷代的“節(jié)婦”和“烈女”,做過一個縝密詳細貫穿始終的數(shù)字統(tǒng)計,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這些極有價值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節(jié)婦”———周代記載有6人,秦代記載有1人,漢代記載有22人,魏晉南北朝時期記載有29人,隋唐記載有32人,五代記載有2人,宋代記載有152人,元代記載有359人,明代記載有27141人,清代記載有9482人;“烈女”———周代記載有7人,漢代記載有19人,魏晉南北朝時期記載有35人,隋唐記載有29人,遼代記載有5人,宋代記載有122人,金代記載有28人,元代記載有383人,明代記載有8688人,清代記載有2841人⑤。我們僅從以上數(shù)字來分析,宋代以后“節(jié)烈”人數(shù)明顯上升,而尤其是以明代為盛,這似乎恰恰印證了程朱理學的制約作用。但如果我們僅以宋代以后為計算單位,并以“節(jié)婦”、“烈女”人數(shù)去除以朝代年限和人口均值,那么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統(tǒng)計結果:宋(包括金)代人口均值為近7000萬左右,朝代延續(xù)時間為319年,“節(jié)婦”、“烈女”之總和為302人,若按女性占人口比例一半、成年女性又占女性人口三分之二來計算,她們每年出現(xiàn)的實際次數(shù),也只占成年女性人口的千萬分之六;元代人口均值為8000萬左右,朝代延續(xù)時間為97年,“節(jié)婦”、“烈女”之總和為742人,若按女性占人口比例一半、成年女性又占女性人口三分之二來計算,她們每年出現(xiàn)的實際次數(shù),也只占成年女性人口的百萬分之二點七;明代人口均值為1億人左右,朝代延續(xù)時間為276年,“節(jié)婦”、“烈女”之總和為35829人,若按女性占人口比例一半、成年女性又占女性人口三分之二來計算,她們每年出現(xiàn)的實際次數(shù),也只占成年女性人口的十萬分之三;清代人口均值為2.3億人左右,“節(jié)婦”、“烈女”之總和為12323人,朝代延續(xù)時間為295年,若按女性占人口比例一半、成年女性又占女性人口三分之二來計算,她們每年出現(xiàn)的實際次數(shù),也只占成年女性人口的百萬分之五點二(以上人口均值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主要依據(jù)葛劍雄先生主編的《中國人口史》)。提供這樣一組統(tǒng)計數(shù)字的真實目的,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去認真總結女性“節(jié)烈”的發(fā)展變遷,另一方面更使我們明白了即便是在理學昌盛的明代,“節(jié)婦”、“烈女”在成年女性當中的出現(xiàn)頻率,每年也就不過十萬分之三左右。故“節(jié)烈”也絕非我們今天主觀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普遍存在于中國社會的道德現(xiàn)象,相反它還伴隨著時間的逐漸后移,從清代開始呈現(xiàn)出急劇下降的運行軌跡!由此可見,五四時期啟蒙精英拿“節(jié)烈”去說事,顯然是具有以偏概全詆毀傳統(tǒng)的造勢意圖。
關于封建禮教與家長專制迫害女性之說,從中國古典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分析,《孔雀東南飛》和《梁山伯與祝英臺》無疑都是經典范例,它們對宗法制度壓迫婦女決斷婚姻的強烈控訴,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這就是漢樂府《焦仲卿妻》一詩的開卷之句,它以凄涼婉轉的哀怨情緒,奠定了這首樂府詩的悲劇格調。仲卿妻“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頌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從該詩的卷首描寫中我們可以得知,仲卿妻應該是一個知書達理能織善裁的賢惠女子,盡管她辛勤操勞但卻不受婆婆的好臉待見,最終只能求自己的夫君將其“及時相遣歸”。焦仲卿當然是對妻子鐘愛有加,但是其母親則蠻橫地認為“此婦無禮節(jié),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當焦仲卿乞求母親時,其母卻勃然大怒道:“小子無所謂,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焦仲卿與母親之間的這段對話,最典型地反映出了中國家長的十足霸氣,以及封建社會不可撼動的專制意識!劉蘭芝被“休”以后,其父兄逼其再嫁,結果焦、劉二人殉情自殺,成就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大杰作!胡適說《孔雀東南飛》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故事詩”,“它譬喻的是男子不能庇護他心愛的婦人,欲言而口噤不能開,欲負他同逃而無力,只能哀鳴瞻顧而已”,言下之意其主題當然就是反封建。#p#分頁標題#e#
《梁山伯與祝英臺》則是中國“四大傳說”之一,最早載于初唐梁載言的《十道四蕃志》,晚唐張讀的《宣室志》則取名為《義婦冢》,元代又曾被人改寫成雜劇《祝英臺》,明代馮夢龍編輯的短篇平話《古今小說》亦有收錄,而比較詳細地去講述這一故事情節(jié)的,當屬清人俞樾在《茶香室四鈔》中所援引的《祝英臺小傳》。《梁山伯與祝英臺》這一傳奇故事,之所以會世代流傳經久不衰,就因為它熱情謳歌了男女青年之間的真摯愛情,同時也抨擊了男尊女卑嫌貧愛富的社會陋習,其所飽含著的民間反封建的人文理想,最終也使其成為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反封建與反傳統(tǒng)的客觀需要,學術界精英們還出版了一個《祝英臺故事專號》,女作家馮沅君也專門創(chuàng)作有《祝英臺的歌》,這一切顯然都是為了配合當時社會的思想啟蒙,故而使這一美麗傳奇也肩負起了文化變革的神圣使命。然而,中國古典文學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保守,至少在對待兒女婚姻大事問題上,沒有那么絕對霸道或武斷專制,應與現(xiàn)代社會無太大的本質區(qū)別。如宋人皇都風月主人編《綠窗新話》里的“郭華買脂慕粉郎”:郭華家富好學,求名不達,遂負販為商。
游京城,入市,見市肆中一女子美麗,賣胭脂粉。華私慕之,朝夕就買。經半年,脂粉堆積房內,財本空竭。此女疑之而問曰:“君買此脂粉,將欲何用?”答曰:“意相愛慕,恨無緣會合,故假此覿姿容耳。然每一歸,必形諸夢寐。”女悵然有感曰:“郎君果有意相憐,妾豈木偶人耶?明日父母偶住親戚處會宴,妾托疾守家,君可從東街多景樓側小門直入,即我屋后花園也,有小亭寂靜,可敘綢繆。”及期,華因遇親友話,至已二鼓矣。女久候不來,乃留一鞋而入。華視門扃,扉左得鞋,哽愴歸去,以口吞之,氣噎而絕。翌晨,主人見華尚有余息,于喉中得鞋,又見胭脂粉多,遂挑鞋于粉肆詢之。其父問女,女不敢隱,父乃同主人歸店視之,華已蘇矣。遂命主人為媒,因嫁為夫婦。⑥郭華借買胭脂粉主動去追求某女,這已經是一種觸犯倫理道德的忤逆行為;而某女竟然還敢約他私會于后花園,這同樣也是挑戰(zhàn)禮教秩序的反叛之舉。令我們倍感詫異之處是某女之父,他不僅沒有嚴厲斥責二人的大逆不道,相反還主動去成全兩人的美滿婚事,足以見得古代家長也并非全都專制。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加以闡釋:中國古代女性絕不是被禁閉在“高墻深院”里,過著一種“無言獨上西樓”或“凄凄慘慘戚戚”般的囚獄生活,她們同樣也具有拋頭露面外出游走的行動自由,這恐怕也是會出乎我們現(xiàn)代人的意料之外。比如唐末詞人韋莊在其《思帝鄉(xiāng)》中,便曾這樣描寫道:“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在韋莊的筆下,古代女子不僅可以外出,而且還可以野外踏青賞花,男男女女自然也不大避諱,完全是一幅自由徜徉的悠然神態(tài)。
三、中國現(xiàn)代文學貶斥“禮教”的偏執(zhí)認識
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產物,以封建禮教和家長專制為主要的批判對象,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給予了顛覆性的徹底否定,婦女解放問題自然也是他們所刻意去關注的創(chuàng)作母題。但是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發(fā)現(xiàn),啟蒙精英完全是以無視歷史的虛無態(tài)度,為了追求“現(xiàn)代”而一味地去詆毀“傳統(tǒng)”,甚至還把民族文化描寫成漆黑一團,并將女性悲劇全都歸結為“禮教”之罪,這種偏執(zhí)至今仍在束縛著當前學界的理性思維。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判禮教同情女性,首先體現(xiàn)為對宗法制度的猛烈攻擊。宗法制度是一種由“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所構成的文化體系,它在現(xiàn)代作家眼中無疑就是壓迫婦女制造悲劇的萬惡之源。從魯迅的《祝福》到蕭紅的《呼蘭河傳》,中國現(xiàn)代作家無疑是把封建社會的宗法制度,看作是一種貫通古今普遍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甚至無一例外地都將其視為壓迫婦女的精神枷鎖,這顯然是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所采取的棄其“精華”取其“糟粕”的實用功利主義態(tài)度。
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判禮教同情女性,其次體現(xiàn)為對家長專制的無情批判。家長專制是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因素,同時也是束縛女性人身自由與精神解放的最大障礙。田漢的話劇《獲虎之夜》,就講述了一個現(xiàn)代家長專制扼殺純潔愛情的悲劇故事:富裕獵戶魏連生之女魏蓮姑同其表兄黃大傻,兩小無猜青梅竹馬早已在暗中眉目傳情私定了終身,但由于黃大傻家中父母雙亡又遭受火災債務纏身,因此嫌貧愛富的魏連生才堅決不同意將蓮姑嫁給他;當黃大傻得知魏家已為蓮姑另外擇婿時痛苦萬分,他半夜三更來到魏家希望再見上蓮姑一面,可未曾想卻被魏家當作是老虎打了一槍身負重傷;黃大傻訴說衷腸乞求魏家能夠理解自己,然而魏連生卻暴跳如雷大罵他是“畜生”,黃大傻絕望之際用刀自盡以死殉情,而蓮姑也悲慟欲絕泣淚灑血欲隨之而去。相比《獲虎之夜》的藝術表達,謝冰瑩在《一個女兵的日記》中,對于自己逃離家庭去追求自由,則描寫得更為真實也更為生動:父母為其定下了一門婚事,她表示堅決反對絕不同意,“‘笑話!禮教也敢反對嗎?’母親越來越威風了,‘它是數(shù)千年來圣人立下的’”規(guī)矩,“誰敢反對,難道你這丫頭,也敢反對禮教嗎?”我對這段記實敘事所感興趣的地方,不是謝冰瑩本人反抗封建婚姻的莫大勇氣,而是家長專制體系古今一致的表現(xiàn)特征:“這東西簡直不是人,父母大于天,豈敢和我們作對!送你讀書,原望你懂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誰知你變成了畜生,連父母也不要了!婚約是父母在你吃奶的時候替你訂下來的,你反對婚約,就等于反對父母!”《獲虎之夜》與《一個女兵的日記》對家長專制的藝術描述,我們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西廂記》的現(xiàn)代翻版。除了父母干涉兒女的婚姻大事,現(xiàn)實生活中“婆媳關系”的矛盾沖突,也被納入到了家長專制的基本范疇,成為了現(xiàn)代作家密切關注的表現(xiàn)題材。曹禺的話劇《原野》,寫婆婆焦瞎子恨媳婦花金子,不僅成天罵她是個“狐貍精”,而且還從廟里求來個木人天天扎“她”,最終使花金子站在了仇虎一邊,直接導致焦家發(fā)生了一場滅門慘劇。巴金的小說《寒夜》,其對“婆媳關系”的深度揭秘,恐怕是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汪母曾是云南一個大戶人家里的千金小姐,傳統(tǒng)文化教育使她知書達禮溫文爾雅恪守婦道,而她一旦當上了“婆婆”并掌握了家庭權利,又以同樣方式去要求媳婦遵守祖制。巴金毫不掩飾“《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小說”⑦,因為他已經感到了傳統(tǒng)文化的不可撼動性,而自己筆下“汪母”虐待媳婦曾樹生的種種行為,又與《孔雀東南飛》中那個“焦母”有何不同呢?“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這既是作品結尾的感嘆之語,也是《寒夜》主題的自我生成!但無論是曹禺還是巴金,他們描寫“母系家長”的獨裁專制,都只是從文化層面上去看問題,這顯然會落入非理性的認識盲區(qū)。弗洛伊德在談及女性心理學時便曾指出:女性在其青少年時代的性格特征,恰恰是要表現(xiàn)出與母親相對立的一種態(tài)勢;而一旦“為人妻”、“為人母”之后,她會“變得越來越像她格格不入的母親了”。原因其實非常的簡單,她不是“母親”時拒絕“母親”,她成了“母親”時又認同“母親”,這完全是生理與經驗的雙重結果。“婆媳”地位的交替演變,也完全是同樣的道理。“經驗”自然是一種不可否認的文化因素,但卻并非是女性變化的唯一因素;如果僅把“婆媳關系”理解為專制文化,我們必然會陷入主觀主義的教條陷阱。#p#分頁標題#e#
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判禮教同情女性,還體現(xiàn)為對男性摧殘女性的血淚控訴。男性壓迫女性并使其喪失人格與自由,這是“女性解放”文學敘事的一大特征,它在具體實踐方面又表現(xiàn)為這樣三種基本模式:其一,是對女性淪落為“玩偶”現(xiàn)象的深切悲哀。彭家煌的小說《節(jié)婦》,講述阿銀十歲便以八元錢為身價,賣給了“候補道夫人做小婢”,“候補道夫人”去世以后,十八歲的阿銀又成了七十歲“候補道大人”的續(xù)弦填房;可僅僅過了兩年“候補道大人”也駕鶴歸西,阿銀在家人眼里既沒有地位也沒有尊嚴,由于“改嫁在官方人家是不太成話”的,所以阿銀只好被逼無奈地去為丈夫“守節(jié)”。然而,道貌岸然的長子柏年卻對后母發(fā)生了興趣,“那個四十多歲的胡子臉”把她“逼到床里邊”,“以后的一切誰知道,只有室內一點微薄的洋燈光照見那個瘋狂了的胡子在……”;不久,其新派長孫振黃也對年輕的“祖母”產生了好感,他將“阿銀接到自己的寓所里住了半個月”,但“多情繾綣”時間不長就被父親柏年發(fā)現(xiàn),他要振黃送“祖母”返鄉(xiāng)“守節(jié)”以避免在社會上生出流言蜚語。這一故事荒誕就荒誕在阿銀作為一個不幸的“守節(jié)”女人,她幾乎成了“候補道大人”一家三代男性的共同“玩物”,逆來順受地成為柏年父子的“亂倫”對象,佯裝“守節(jié)”卻又出賣肉體并以此了卻殘生!作者顯然是想通過關于阿銀的悲劇敘事,去諷刺與揶揄封建禮教的虛偽本質;不過“亂倫”本身卻是一種違背“禮教”的忤逆行為,以此去抨擊“禮教”制度也只能是適得其反難以自圓其說。其二,是對女性淪落為“商品”現(xiàn)象的強烈關注。柔石的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述一個有關“典妻”的野蠻故事:春寶娘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撇下五歲的兒子,被丈夫典給鄰村的一個地主,去充當傳宗接代的生育工具。三年期滿她必須離開地主家,只能與兒子秋寶生離死別,可當她回到原來的家中,大兒子春寶已經不認識她了!柔石借“典妻”之事去反“禮教”之制,同樣是一種不得要領的徒勞之舉,因為“典妻”現(xiàn)象雖然古已有之,但惟清末民初江南地區(qū)為盛。《元史•刑法志》中就對“典妻”現(xiàn)象明文禁止,《明律》也對此現(xiàn)象禁令在冊,而《大清律例•戶婚》更是明確寫到:“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方坐此律。”這充分說明“典妻”現(xiàn)象只是一種社會陋俗,它不僅與“禮教”無關,還被“禮教”所禁!其三,是對女性淪落為“工具”現(xiàn)象的無情批判。蕭紅的小說《生死場》,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月英是打漁村最美麗的女人”,可自從她婚后生病不能下床,失去了傳宗接代的生育能力之后,其夫家認為她活著已無意義,所以用磚頭把她身體圍了起來,任其肉體生蛆腐爛也不去理睬———一個“無用”女人的生命消亡,并不能引起男性社會的絲毫憐憫:“死人死了!活人計算著怎樣活下去。”死了女人的男人,可以去再找別的女人,只要能延續(xù)種姓文化,他們不在乎有多少女人為之犧牲!《生死場》對女性悲劇的絕望敘事,應該說是多方面與多層次的,但是作者所舉之例多屬民間的愚昧思想,而與封建“禮教”本身并沒有太大的必然聯(lián)系。因此把男性摧殘女性當作是反傳統(tǒng)的時代口號,總是讓人感覺有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
實際上,早在五四新文學時期,從西洋歸來的“學衡派”諸君子,就對胡適等人全面否定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極端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們認為新文化陣營之弊,“曰淺,曰隘。淺隘則是非顛倒,真理埋沒。淺則論不探源,隘則敷陳多誤”。僅以中國古代的婚制為例,“士不介不相見,男女不相知名”,此乃“屬于風俗者也”,完全是與“禮教”無關的;故“今之盛倡解放女子、男女社交公開、女子貞節(jié)諸問題,不過為破除風俗之一端”,與中國古代圣賢又有何相干呢?⑧他們甚至還警告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說:“以駭俗為高尚,以激烈為勇敢,此非國家社會之福,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⑨“學衡派”諸君子以其沉穩(wěn)自持的理性精神,客觀評價孔儒學說對中國人的積極影響,強調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立足百世千年,“此皆古昔圣哲立教垂訓所賜”,“禮教豈易言哉”⑩。我無意替已經發(fā)生過了的歷史翻案,只是注重一個不容辯解的客觀事實:如果傳統(tǒng)文化真是那樣陳腐不堪難以救藥,那么它為什么還能夠成就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如果封建“禮教”真是那樣不近人情扼殺人性,那么它又為什么還能夠鑄就炎黃子孫的聰明智慧?說穿了,從五四開始,啟蒙精英誠如“學衡派”所說的那樣,是在以“禮教”文化的思想精華,去反對“民俗”文化的思想糟粕;而這種以傳統(tǒng)去反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意識”,恰恰正是他們“詆毀”傳統(tǒng)的運作策略,雖然它已被人為地打上了“西化”標簽,但卻終究遮掩不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厚重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