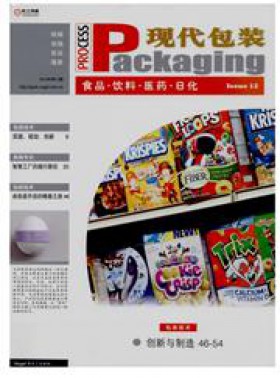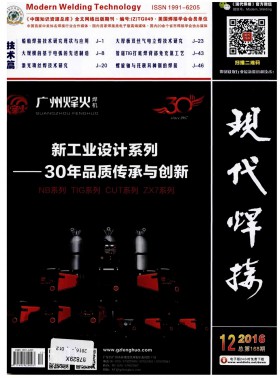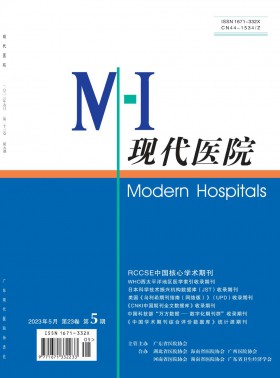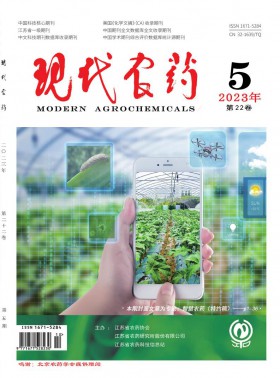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古現代文學語言的研究方向,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二十世紀的西方文論,在文學語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從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開始,直到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學、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等,幾乎所有的文論流派,無不給文學語言問題以優先的地位和特別的關注,并且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觀點和意見,所取得的成果也最突出、最引人注目。可以說,西方二十世紀文論是以文學語言的研究為重要標志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時期文論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反映論到主體論,從主體論到本體論,都曾領一時風騷。現在又有些學者大談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所謂的“后”學已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本體論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倡興,文學語言研究也迅速開展起來。一時間,一些有影響的理論家和批評家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了文學語言問題的研究,以至于到九十年代中期,有些論者認為我國的文藝學、美學出現了“語言論轉向”,甚而認為這種轉向標志著我國文藝學總體范式的必然轉換[1]。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文體和語言的研究熱潮中,人們對文學與語言的關系以及文學語言的特性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這種新的理解和認識必然影響到總體的文學觀念的改變,從而彌補了原有理論的缺失和不足,并為我國新時期文論的發展確立起一個新的“增長點”,其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不能低估。但是,我國當前的文學語言研究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問題應該引起特別注意:一是過分的西方化傾向。我國當代文學語言研究是從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有關理論起步的,這原本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后來的發展卻更多地表現為不顧中國具體語境的機械照搬和盲目“緊跟”,這就有些不太正常了。從目前情況看,為數不少的研究者,眼睛只是盯著西方,不是“跟著說”,就是“順著說”、“重復說”。這樣的研究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缺乏自己的創造性。二是與過分西方化傾向同時并生的對本土傳統文論的忽略和遺忘。盡管已有論者再三呼吁要重視古代文論的研究,并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總的趨勢依然未得到根本的扭轉。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仍盤踞在某些研究者的腦子里,以為現代的、新的東西就一定是先進的、有價值的,而傳統的、舊的東西就一定是保守的、落后的。其實,這種觀點、態度本身就是一種非現代的、偏狹的、獨斷的思想方式的表現。要知道,我國當代文論如果最終不能在辯證思維的基礎上打通與古代文論的一脈相承的聯系,就不能建成有中國特色的文論。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認為,目前的文學語言研究除了繼續深入地學習和借鑒西方現代的有關成果之外,還應該盡力拓寬理論視野,把目光伸展到中國古代文論這個極為廣大而豐饒的領域中去。 中國古代文學中,詩歌最為發達,而詩歌創作又最講究語言形式的創新和語音的抑揚頓挫,因而中國古代文論一方面強調“言志”、“宗經”、“載道”,另一方面又始終對詩歌語言問題相當重視,產生了大量的有關詩歌語言的論述,其成果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西方傳統文論。 從亞理斯多德到別林斯基,西方傳統文論都是以模仿論為基礎的。這種理論最重視的是作家的創作、作品的內容和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語言不過是傳達作者創作意圖和作品內容的手段,是為內容服務的,居于次要的、從屬的地位。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分析悲劇的構成時提到了六個要素,“語言”雖也列入其中,但排在“情節”、“性格”、“思想”等內容要素之后[2](P20-24)。可見,在亞氏的心目中,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并不高。俄國的文豪高爾基倒是說過“文學的第一要素是語言”,但在這句話之前他又附加了一段說明:“文學就是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語言來反映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維過程。”[3](P294)這就是說,他是在認定了語言是內容的表達工具的前提下談語言的重要性的。他所說的語言的“第一”的位置,其實還是排在“第二”,排在內容之后。這與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并無實質上的差別。比較而言,在二十世紀以前的文論中,給予文學語言以較多重視的是十九世紀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們。雪萊甚至說過:“較為狹義的詩則表現為語言,特別是具有韻律的語言的種種安排。”[4](P52)這種觀點盡管已具有了現代文學理論的某些特征,但依然沒有完全脫開傳統的文學語言工具論,因為浪漫主義者的總體文學觀是把詩歌看作是詩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們最看重的是詩歌的情感內容,而不是語言。西方傳統文論既然深受以再現論和表現論為基礎的內容主義的影響,總體上把語言界定為內容的從屬要素,就不會給予它太多的重視,對它的研究也就不會太深入。可以說,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期內,西方傳統文論在文學語言研究方面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以至于成為它的一個越來越突出的薄弱環節,越來越嚴重地阻礙著它的進一步發展。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的出現才徹底改觀了這種局面,促使文學語言的研究迅速興盛起來。 中國古代文論并不像西方傳統文論那樣走極端內容主義的路子,它在強調文學內容的同時,也特別重視文學的語言形式和語言技巧。先秦時代的思想家們就曾從哲學、倫理學、美學等不同的角度論及到文學語言的問題。孔子《論語•雍也》有“文質彬彬”的主張;老子《道德經》有“大言希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說法;《莊子》中的《天道》篇提出了“言不盡意”、《外物》篇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觀點;《墨子•非命》反對“以文害用”,強調“先質而后文”;《韓非子•五蠹》認為“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孟子•公孫丑上》主張“知言養氣”;《荀子•非相》則斷言“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先秦諸子們的這些言論,雖然有的并不專指文學語言,但對后世的文學語言研究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概而言之,中國古代的文學語言研究可歸納為五條路向:一條是由孔子開端的“文質論”。《論語•雍也》載:“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認為:文采不足,文章就粗野;文采過于華麗,文章就膚淺。只有文質并茂,內容與形式統一,才是君子作文的準則。孔子的這一理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最大,引發的論述也最多,幾乎古代的每個有影響的文論家都談到過這個問題。#p#分頁標題#e# 如:王充的“言事增實”說,陸機的“辭達理舉”和“尚巧貴妍”說,劉勰的“情采”說,韓愈的“陳言務去”和“氣盛言宜”說,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說,白居易的“尚質抑淫”說,歐陽修的“道盛文至”說,程頤的“作文害道”說,黃庭堅的“理得辭順”說,等等。“文質論”探討的是文學的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總的來看,重內容但又講求文采的觀點占上風。 第二條路向是以莊子的“得意忘言”和《周易》中的有關論述為發端的“言、象、意”理論。《易傳•系辭》中談到“卦象”的產生時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魏代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對《易傳》的這一理論作過系統的闡發。他認為“言、象、意”三者的關系,從發生順序上看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從表達順序上看是“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5](P609)這一原本是闡釋《易經》的哲學理論,被后世的文論家所吸取,用來解說詩歌中“言與象”、“象與意”的關系,從而產生了一系列有關詩歌語言特點的論述。例如陸機所說的“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文賦》),皎然所說的“假象見意”(《詩式》),司空圖所說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十四詩品》),葉夢得所說的“意與言會,言隨意遣”(《石林詩話》),嚴羽所說的“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話》),袁宗道所說的“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論文》),陳廷焯所說的“意在筆先,神余言外”(《白雨齋詩話》),都是這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文論家的上述觀點與西方“新批評”的“合混”、“復義”等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與現象學派英加登的文本結構層次論有不謀而合之處,但至少要比“新批評”和英加登早出現千年以上。 中國古代文論有關文學語言研究的第三條路向肇始于《詩大序》中的“賦、比、興”理論。《詩大序》把“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為《詩經》的“六義”,是對《詩經》的一種解釋。從唐代的孔穎達開始,“賦、比、興”被理解為詩歌的三種表達方式,“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詩大序正義》)。以這個論點為基礎,古代文論家重視詩語的“精巧”與創造性,由此形成了古代文學語言研究中的修辭學向度。例如司馬遷從語言表達的角度盛贊屈原的《離騷》,認為它“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揚雄對漢賦過度地鋪陳事物、雕繪辭藻提出批評,認為漢賦“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法言•吾子》);陸機比較重視文學表達的技巧和獨創性,提出詩歌創作“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選文按部,考辭就班”,“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主張(《文賦》);劉勰在《文心雕龍》的《熔裁》、《夸飾》、《比興》、《事類》、《附會》等諸多篇章中,系統地論述了詩歌所運用的各種修辭手法。特別是對“夸飾”的論述(“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對“比興”的論述(“比者,附也”,“寫物以附意”,“興者,起也”,“依微以擬議”),對后代的影響更大。其他如何景明提出的“辭斷意屬,聯類比物”(《與司空圖論詩書》),王驥德主張的“意常則造語貴新”(《曲律•論句法》),袁宏道贊揚的“本色獨造語”(《敘小修詩》),劉大櫆強調的“論文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論文偶記》),劉熙載推崇的“詞眼”和“極煉如不煉”(《藝概•詞曲概》),也都屬于詩歌修辭學方面的論述。 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體學理論構成了文學語言研究的第四條路向。中國古代的文體學主要是研究文體的分類及其語言風格的。這種研究最早發源于曹丕的《典論•論文》,即“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隨后陸機在《文賦》中把文體分為十類,并分別指出其各自的風格特點。劉勰也在《文心雕龍•體性》中用大量篇幅專門論述了各類文章的形式和寫作特點,還從語言形式的差別著眼,把所有的文體概括為八種風格,即“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其他如李嶠的《評詩格》、王昌齡的《詩格》、皎然的《詩式》、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陳的《文則》等,都是專論文體風格的著作。在中國古代文體研究史上,南朝的蕭繹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人物,他第一次以自覺的文學意識辨析了自古以來的“文筆”之爭,明確指出,“善為奏章”、“善輯疏略”的論事說理實用之文,叫做“筆”,而“至如文者,惟須綺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性情搖蕩”,即具有華美的辭藻,協調的聲律,精粹的語言,有強烈感染力的文章,才能稱為“文”(《金樓子•立言》)。這種對文學文體和文學語言特性的自覺而深入的認識,在古代文論史上是一個重大進步。 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研究的第五條路向是以“聲律論”為主體的詩歌音韻學。聲律理論的開創者是南齊的沈約等人。早在沈約之前,陸機在《文賦》中已對詩歌的音樂美有所描述,他說過:“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沈約第一次對詩歌聲律進行了專門系統的理論探討,提出了所謂“四聲八病”說,即用“平、上、去、入”四字標四聲,并把詩歌創作中出現的使四聲不和諧的病犯總結為“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他強調指出:“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沈約聲律論的提出,直接促成了五言古詩向律詩的演變,同時也開啟了詩歌語言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即詩歌音韻學。在沈約之后,宋代的李清照強調詞“別是一家”,必須“協音律”,反對“句讀不葺之詩”(《詞論》);明代的李夢陽提倡作詩要“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園,思沖,情以發之”(《潛虬山人記》);清代的沈德潛標榜格調說,提出“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詩中韻腳,如大廈之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說詩1語》)。這幾位詩論家都對中國古代詩韻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難能可貴的是,明代的王世貞在論述曲詞的音韻時還談到了聲律的情感意味,提出了“聲情”這一概念,并與“辭情”加以區別。他說:“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曲藻》)這種“聲情”論與克來夫•貝爾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論顯然有相通之處,可以相互參照。#p#分頁標題#e# 以上的簡略敘述,難免掛一漏萬,但也足以見出,中國古代文論中有關文學語言的論述是相當豐富多彩的,所論的問題也非常廣泛和深入,有些論點也極富啟迪性,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寶庫,應該盡量納入當今的文學語言研究的視野之中。當然,無庸諱言,這些論述和理論,也像中國古代文論中的其他理論一樣,帶有評點式、感受式的弱點,也受歷史的局限,其中許多內容已經不能適應或不能完全適應現時代的要求,這就需要對之進行現代性的轉換和提升。所謂現代性的轉換和提升其實就是綜合的工作,就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溝通和整合。 所以,綜合的觀點是與徹底反傳統的觀點截然相反的,它不僅不排斥傳統,不與傳統決裂,而且還認為現代是從傳統發展而來的,現代與傳統之間有著一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可以站在現代的高度上對傳統做出新的闡釋和評價,從而實現現代與傳統間的綜合。只有經過這種綜合,現代的文學語言研究才能在原有的水平上獲得深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