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李東陽文學思想闡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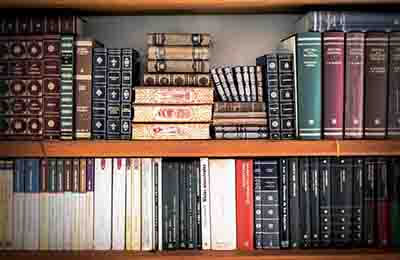
作者:林冬梅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李東陽一生歷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明史•李東陽傳》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后,東陽而已。”“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李東陽弘治時期的文學思想上承臺閣文學,下啟七子派之格調(diào)說,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后作用。王世貞說:“長沙之啟何、李,猶陳涉之啟漢高。”[1](p.245)胡應麟在《詩藪》中也說李東陽“興起何李”,七子派重視詩體的詩學觀念,他們對詩的審美性的重視,便是發(fā)端于李東陽。
一、典雅脫俗之風格追求與“兼綜互出”的師法理論
李東陽詩學思想的第一個方面是對典雅脫俗之創(chuàng)作風格的追求,與之相關,李東陽在師法理論上主張博學廣納,“兼綜而互出之”,這是由其閣臣身份和人生經(jīng)歷決定的。李東陽等臺閣文臣在政治、文化上處于優(yōu)越地位,他們的詩文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富貴福澤之氣,這種富貴氣象不是通過腰金枕玉、鏤彩錯金的描寫體現(xiàn)出來,相反,常常是通過蕭散閑淡的情懷體現(xiàn)出來。北宋的晏殊就是一位善寫富貴者,他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清淡至極,描寫的卻正是富貴福澤之氣象。
張《仕學規(guī)范》記載:“……公(晏殊)每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氣象,若曰‘樓臺側(cè)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2](p.190)富貴中人在面對人生時有一種安閑、平穩(wěn)的氣度,臺閣詩人在表現(xiàn)私人情懷時,往往側(cè)重于表現(xiàn)這樣的氣度:在選擇題材的時候,他們偏向于閑適、隱逸的方面;在詩歌風格方面,他們追求典雅脫俗。李東陽《麓堂詩話》說: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酸餡氣。詠閨閣過于華艷,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于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卻不可少。[3](p.489)幽寂雅澹、瀟灑超脫、擺落塵滓,都是一種脫俗的情調(diào),如果不能做到“脫俗”,則詩會有“頭巾氣”、“酸餡氣”、“脂粉氣”,都不是好詩。那么什么樣的詩歌是情調(diào)脫俗的好詩呢?情調(diào)脫俗是李東陽詩歌創(chuàng)作的審美理想,是一種超越于現(xiàn)實生活之上的文人士大夫情調(diào),是幾千年來中國文人集體無意識的積淀。李氏從題材和風格的角度,列舉出兩種:一種是有“臺閣氣”的,一種是有“山林氣”的,他認為,兩者必居其一才能稱得上是好詩。所謂“臺閣氣”,指的是臺閣詩歌典則雅麗、高昂盛大的風格,是詩歌表現(xiàn)國家之盛時體現(xiàn)出的一種繁榮富貴氣象;而“山林氣”,指的是清麗脫俗、安閑大氣的風格,是詩歌表現(xiàn)私人情懷時體現(xiàn)出的一種閑適愉悅的氣氛。臺閣體之代表作家,楊士奇、楊榮、楊溥,均為善寫閑適、隱逸題材的高手。通過閑適詩和隱逸詩,他們寫出對山居生活的向往,寫出公退之余在自己或友人的園林、別業(yè)中能夠享受到的情趣。所謂繁華之極歸于平淡,李東陽所謂“山林氣”正是富貴中人語,并非真心歸隱之意,其與陶淵明輩“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的情懷迥然相異。從整體風格上來說,李東陽的隱逸詩常常寫得清艷絕倫,作者的閑適情懷和心靈愉悅呼之欲出,很好地體現(xiàn)了他有關“山林氣”的理論。李東陽說:“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作閑靜詩易,作繁擾詩難。貧詩易,富詩難。賤詩易,貴詩難。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為難也。”[3](p.497)更進一步說明了李東陽詩中之“山林氣”本質(zhì)上是一種富貴情調(diào)。李東陽一生清貴,“立朝五十年”[4](p.4825),“歷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1](p.245),他的經(jīng)歷簡單平淡,既沒有大的身世之險,也沒有在官場顛沛流離,人生經(jīng)歷所限,也決定了他的詩只能表現(xiàn)臺閣詩人的雅致情趣,缺乏更豐富的風格,典雅脫俗的風格追求正是由其館閣身份和士大夫情趣決定的。也就是說,李東陽雖然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突破了臺閣文學思想的限制,但實際上并未擺脫臺閣文人身份在創(chuàng)作題材和創(chuàng)作風格方面對他的影響。
典雅脫俗的風格追求,使李東陽在師古方面強調(diào)取法對象之寬博與風格辨析之精細。具體地說,館閣身份決定了李東陽在創(chuàng)作上追求典雅脫俗的風格,對典雅脫俗風格之追求是士大夫階層集體無意識的積淀,要與這種集體無意識溝通,就必須飽覽典籍,決定了他必然采取博學廣納的師法理論。李東陽論詩特別強調(diào)“學”與“識”的作用,“漢唐以來,作者特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后世”[5]。他從古代典籍中尋找作詩的題材與靈感,他的《擬古樂府》就是模擬漢魏古樂府的歌辭進行創(chuàng)作的。《擬古樂府序》云:“兼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意,托諸韻語,各為篇什。”[6]他強調(diào)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授受方式,如他論楊守陳的詩說:“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乎才”[7],說這樣才能作出好詩;他評價劉定之說:“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岳為鎮(zhèn)”,“污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為河為江為海”。[8]在學古對象方面,他提倡學習唐詩,也主張宋元詩亦有佳者,他在《麓堂詩話》中對宋代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等都頗為稱道,對元代劉因、虞集的詩也甚為許可,他還常常引用宋元詩人的詩論;在他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集句詩中,除了唐人作品之外,也大量采用宋代和元代詩人的詩句;從這些例子都可以見出他是采取了兼收并取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與取法對象之寬博相對應的,是對前人創(chuàng)作的精細化辨析。例如,他雖然認為唐、宋、元詩各有佳者,但仍然強調(diào)指出唐詩因其“天真興趣”而更勝一籌。其《麓堂詩話》說:“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他稱盛唐詩歌如內(nèi)法手造酒,能夠點俗為雅,化腐朽為神奇,有難言不測之妙。他強調(diào)選集對后學者的重要性,其《麓堂詩話》云:“文章如精金美玉,經(jīng)百煉歷萬選而后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皇芝草,人人皆以為瑞,閱數(shù)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強調(diào)選集的作用,實際上是一種精品意識。總的來說,取法對象之寬博與辨析之精細是一體兩面,都是為了達到李東陽追求“詩之工者”、“無一字一句不佳”者的境界。#p#分頁標題#e#
二、追求詩歌體貌之盛大,強調(diào)詩歌表現(xiàn)個人情感
在李東陽與茶陵派主盟文壇以前,臺閣體盛行于世,在臺閣體階段,創(chuàng)作上表現(xiàn)出的一個鮮明的特征即文盛于詩,文盛詩衰;作詩也如同作文一樣,一味追求典雅平正的風格。沈德潛在《明詩別裁》中說:“永樂以還,尚臺閣體。諸大老(指三楊)倡之,眾人靡然和之,相習成風,而真詩漸亡矣。”這種局面的形成是由明前期以來的文化氛圍和文化政策決定的,一方面科舉考試的壓力使士人無心于詩的創(chuàng)作,所謂“舉業(yè)興而詩道大廢”;另一方面,“文以載道”理論的宰制,使得詩歌抒情言志的功能被遮蔽。當時詩道之不振還有另外一個深刻的原因:臺閣體作家的“清慎”心態(tài)。出于謹小慎微的心態(tài),仁宣士人很少在詩歌中表現(xiàn)個體情感和志向,此即臺閣體缺乏真正的情感深度與深刻內(nèi)涵的原因[9](pp.19-23)。弘治時期,君王勤政,士風高昂,士人的主體意識增強,為了表達個體情感,抒發(fā)個人情懷,他們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擺脫原有價值觀念的制約,給詩更大的發(fā)展空間成為時代的需要。這首先要求詩人和評論家在意識上將詩與文區(qū)別開來處理,進而彰顯其固有的價值與意義。弘治時期,在詩文辨體方面走出重要的第一步的是李東陽。李東陽提出了詩文各體的觀點。其《麓堂詩話》曰:“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為文,韓退之以文為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自命者,至其為詩,則毫厘千里,終其身而不悟。”其《滄州詩集序》云:“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于記述,短于諷吟,終其身而不能變者,其難如此。”他的辨體理論主要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
1.李東陽強調(diào)詩歌的音樂性、抒情性和形容性,反對實用主義的文學觀。李東陽認為,詩必須講究聲律節(jié)奏,它是借助于韻律之美來區(qū)別于文的,這是詩與文最明顯最主要的區(qū)別: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詩又其成聲者也。章之為用,貴乎記述、鋪敘、發(fā)揮,而藻飾、操縱、開闔,惟所欲為,而必有一定之準。或歌吟詠嘆,流通動蕩之用,則存乎聲,而高下長短之節(jié),亦截乎不可亂。[10](p.58)言之成章者為文,文之成聲者則為詩。[11](58)詩與諸經(jīng)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xié)音律,言志勵俗,乃其所尚。后之文皆出諸經(jīng),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12](p.69)李東陽對詩歌音樂性的強調(diào),始終緊緊圍繞詩與文在文體方面的區(qū)別,在比較中突出詩體的獨特性。首先,他認為文是語言按照某種條理和結(jié)構組合而成的文學樣式,而詩則是在文的基礎上,又依照一定的聲律所構成的、富有音樂韻律美的文體。其《麓堂詩話》說:“詩在六經(jīng)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于詩,終于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fā)志意,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后世詩與樂判而為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為哉。”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調(diào)聲律實際上是對詩的感性形式的強調(diào),是對詩的體貌的強調(diào)。強調(diào)詩歌體貌,就是強調(diào)詩歌作為審美對象的屬性,是李東陽自覺使詩疏離于傳道致用文學觀的表現(xiàn)。其次,李東陽通過聲律這樣一個紐帶,突出了詩的抒情性,界定了詩與文在社會功能方面的區(qū)別。文的功用雖有一定要求,但它相對詩歌而言仍較為自由,即是通過記述、鋪述等手段來考察社會得失,勸誡統(tǒng)治者,詩歌則比較嚴格,有截乎不可亂的音節(jié)約束,必須依賴聲韻來發(fā)揮作用,相對而言,詩歌更多地訴諸情感,其社會功能也是通過感發(fā)作用來實現(xiàn)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他的一則序言里了解得更為透徹:“詩之體與文異,……蓋其所謂有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諷詠,能使人反復諷吟,以暢達情思,感發(fā)志氣,取類于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于明教政事之大。”詩歌的社會功能是“暢達情思,感發(fā)志氣”,是通過訴諸審美體驗來實現(xiàn)的,這就是詩不同于文的特殊之處。由于文體不同,決定了二者對于社會所起的作用有異,“用于天下,則各有所宜而不可偏廢”。李東陽重視詩體,強調(diào)詩歌體貌的獨特性,還表現(xiàn)為他對詩歌形容性和抒情性的強調(diào)。李東陽《麓堂詩話》說:“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fā)。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重視詩體,強調(diào)詩在體貌和功能上的獨特性,實際上是將文學觀念轉(zhuǎn)向?qū)Ω行孕问胶蛯徝烙鋹偟淖⒁?這是弘治時期社會審美需求膨脹的表現(xiàn)。黃卓越說,茶陵同人在文學新變之際首先涉手的就是詩,“這不僅僅是因為起衰要比超強容易,也在于詩歌于特性上更能滿足正在積極尋求依附的社會審美需求。”[14](p.170)洪武、永樂時期,明王朝處于篳路藍縷、艱苦奮斗的開創(chuàng)階段,王朝的思想控制嚴密,從文學思想上看,文學被要求保持與意識形態(tài)目標的充分一致性,“載道說”和“世用說”盛行,實用主義的聲音遮蓋一切;成化時期,文官集團飽受宦官等黑暗勢力的摧殘,或被貶官或主動歸隱,曾與皇權產(chǎn)生了一定的距離感,在這樣的心態(tài)之下,他們當然無心于審美的追逐;而弘治時期是明王朝少有的“中興”時期,孝宗與士人關系融洽,并且在穩(wěn)定朝政、整治腐敗方面進行了一定的努力,社會生產(chǎn)得到了恢復,士人生活雍容優(yōu)裕,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復了對朝廷的信任以及應有的政治熱情。從這個角度來看,士人群體的注意力由文向詩的遷移,正是國家發(fā)展、政治變換的一個縮影,古文受到體式、功能的限制,顯然無法像詩一樣承載迅速膨脹的、大量的、強烈的審美需求,而詩歌作為“緣情綺靡”的文藝形式可以承載這樣的需求,但必須從觀念上將其與傳統(tǒng)的、實用主義的傳道致用的文學觀劃分清楚,這是文學思想發(fā)展的要求。
2.李東陽強調(diào)詩歌風格的個體差異性,以詩表現(xiàn)私人感情。既然詩的振興承載著士人的審美需求,那么作為新的政治時代的詩壇引領者,將詩與實用主義的、傳道致用的文學觀劃分開來還不夠,還需要把對詩美的追求與單純的技術性講求區(qū)分開來。李東陽《麓堂詩話》說:今之歌詩者,其聲調(diào)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同,而知其為吳為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shù)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diào)之為唐、為宋、為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邪?大匠能與人以規(guī)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guī)矩之謂,而其為調(diào)則有巧存焉。茍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3](p.485)他把“聲”(聲調(diào))與“律”(格律)劃分開來,認為格律是對于平仄、字數(shù)的技術性講求,是為了追求音律美而在語言文字方面不斷探索和積累,并最終固定下來的一種規(guī)定,而聲調(diào)則是在此基礎上靈活運用語言文字傳達特定情感內(nèi)容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審美形式。格律是固定的,不能輕易改變;而聲調(diào)則是個別的,特殊的,不可復制的,不同時代、不同詩人,詩歌聲調(diào)千差萬別。他特別強調(diào)文藝隨感而發(fā),因人而異。關于文藝的個體性和特殊性,前人多有論述,曹丕《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jié)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劉勰《文心雕龍•體性》說:“各師成心,其異如面。”[14](p.229)法國布封說:“風格就是人本身。”李東陽認為,不同詩人、不同作品可以帶來不同的審美感受,反對用單一標準評價詩歌。李東陽的這種詩歌審美觀,是與其詩歌功能觀相一致的。李東陽的心態(tài)中有自我適意的人生追求,這種人生追求貫徹在文學思想中,使得李東陽的文學觀向重視表現(xiàn)私人感情的方向轉(zhuǎn)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xiàn)就是他在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個體自我的真實感受,表現(xiàn)士大夫的閑情逸致和私人的感情。#p#分頁標題#e#
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15](p.279)這首詩是李東陽寄給友人彭民望的。彭氏以舉人官應天通判,落魄歸家,生計艱難,此詩并未以朝廷大員的身份對彭氏施以鼓勵勸誡,而是對其窮困孤寂的生活作了感同身受的描寫,感慨人情淡薄,并抒發(fā)無力援手的無奈。傳說彭氏讀此詩時潸然淚下,悲歌數(shù)十遍不休,《麓堂詩話》說:“彭民望始見予詩,雖時有賞嘆,似未然當其意。及失志歸湘,得予所寄詩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黯然不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乃潸然淚下,為之悲歌數(shù)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論文耳。’蓋自是不閱歲而卒,傷哉!”這首詩沒有盛大的格調(diào),只是表現(xiàn)了對于一個不幸文人的同情,但那種朋友之間的相互慰藉自然真摯,感人至深,是李東陽集中頗有代表性的佳作。這一類詩還有《贈彭民望三首》、《再贈三首,用前韻》、《寄彭民望》、《封江野泊,偶步江上無主竹園,呼酒召戴侍御、謝寶慶、彭民望同飲》八首,以及《哭張行人暉吉》、《楊武選挽詩》等,都是描寫私交的,都寫得真情流露,自然天成。
三、和諧盛大的審美理想
李東陽認為,不同地域、不同時代詩歌在聲調(diào)上存在差異,這實際上是一種風格論,他區(qū)分唐調(diào)、宋調(diào)、元調(diào),意在說明一代有一代之聲調(diào)(風格),那么在李東陽心中,是否有一個理想格調(diào)存在呢?這個理想的聲調(diào)(風格)是什么樣的呢?首先,從時代聲調(diào)來看,李東陽主張回歸高古宛亮、聲韻和諧的古典審美理想。在李東陽的時代,學古還未專于學唐及其以前的詩歌,宋詩也在學習的對象之列。
從聲調(diào)的角度講,宋詩在唐詩之后,為了不步唐人后塵,宋人在詩歌中常常使用拗體和險韻,以求造成奇崛生新的效果,力圖打破唐詩已經(jīng)凝固化了的聲律規(guī)范。宋詩可備一體,但對宋詩的刻意模仿使詩成了生澀難讀的泥胎木塑,李東陽說:“宋人于詩無所得”,他反對學宋所造成的“其詞艱澀,如入神廟,坐土木骸”的生澀僵硬之弊,想要糾正宋人的險拗,回歸聲韻和諧、平仄合律的古典審美理想。李東陽《麓堂詩話》說:古雅樂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因憶詩家聲韻,縱不能彷佛《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長篇中須有節(jié)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wěn)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diào),未可遽為杜學也。[3](p.481)他認為,弘治時期詩的聲調(diào)應該是“一派中和”,是像堯舜時期的《賡歌》那樣雍容和美的音樂,他還特別區(qū)分了唐調(diào)和杜調(diào),認為杜甫才高氣雄,盡管使用拗體和險韻,但是能夠運用自如,達到“音響與格律正相稱”的境界,而初學者學力不足,不宜從杜詩入手,應該先學“委屈可喜”的“唐調(diào)”。
其次,從詩人個體聲調(diào)來看,李東陽對杜甫“集大成”式的創(chuàng)作成就非常仰慕,提出在創(chuàng)作方面兼綜并善的追求。《麓堂詩話》說: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xiāng)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yōu)。蓋可以兼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于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于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3](p.481)他從“聲調(diào)”論的角度提出最好的詩是“宮聲”,認為李白、杜甫的詩就是“宮聲”,他自己的詩也是宮聲;“宮聲”是盛世之音,能夠體現(xiàn)盛世氣象。那么什么樣的聲調(diào)才能算作“宮聲”呢?李東陽論詩喜歡從聲調(diào)入手,但他同時也承認,“后世詩與樂判而為二”,“古詩歌之聲調(diào)節(jié)奏不傳久矣”,故而李氏之以“宮聲”論詩,與其說是對聲調(diào)的議論,毋寧說是對風格的概括。李東陽《麓堂詩話》評杜詩說:杜詩清絕如“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富貴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高古如“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華麗如“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斬絕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云擁樹失山村”執(zhí)此以論,杜真可謂集詩家之大成者矣。[3](p.500)杜甫是唐代集大成的詩作者,一方面,他的詩歌在創(chuàng)作風格方面兼容并包,有清絕、富貴、高古、華麗、斬絕等多種風格,體貌各異而俱臻精妙,這正是李東陽心向往之的境界;另一方面,杜詩集大成的成就來自他對前代詩歌兼收并蓄的學習,這也是李東陽身體力行的。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說:“西涯之詩,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其詩有少陵,有隨州、香山,有眉山、道園,而其為西涯者自在”[1](p.246),完全概括了李東陽在師古方面“兼綜而互出之”的特點。可見,李東陽心目中能夠代表盛世氣象的理想的詩歌形式是“兼綜而互出之”的詩歌,是詩歌風格的兼容并包,是詩歌體貌的全面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