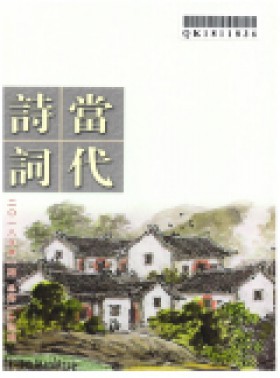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當代文學史作品分析模式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趙雷 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作家作品是文學的歷史敘述的基礎,對作品的闡釋更是文學史書寫的重點。面對一部文學作品,切入的角度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這其中既有對前人成果的繼承借鑒,也需要獨出機杼的新觀點、新發現。縱觀1949年以來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品分析模式可以基本分為兩種類型:分析式和感悟式。前者類似于“二分法”,即把對象劃分為思想內容(包含故事梗概、時代背景、思想認識、社會意義等)和藝術形式(囊括結構手法、人物塑造、語言特色、情節設置等)兩個基本組成部分。后者更多地將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分析時注重對作品的藝術感悟和閱讀體驗。二者間的區別不僅在于治學路數,也體現在思維方式上:前者則更接近自然科學的方法,有一套可資遵循的既成的思路和操作規程,只要將作品套入其中就可得到結果,近似于一種模式化的知識生產;后者更多地是一種類似中國傳統文論“整體感悟”的藝術體驗,要求寫作者有較強的藝術敏感和概括能力,有時甚至需要一點“靈感”。這兩種作品分析方法原本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實卻是,分析式的作品分析方法逐漸成為主流以至文學史書寫的固定模式,而感悟式的作品分析方法卻幾成絕響。本文試圖通過回顧建國以來的學科發展歷程,分析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并對兩種作品分析模式進行初步評價。
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中,王瑤是把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和分析的,并未將其條塊分割。例如他對《阿Q正傳》的評述:這是以辛亥革命為背景,漫畫式的集中了一切民族的弱點而寫成的農村無產者的浮浪的性格。在這里,對于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和那時革命形勢的實際的表現達到了可驚的成功,(但這并不是主題,只是側面的背景的描寫。)而且說明了革命的動力是要向背負著封建歷史重擔的農民身上去追求的。魯迅先生說:“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這就說明了他底現實主義眼光的敏銳。他說:“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確已有了好幾年,”就因為他老早感覺到,要雕塑我們民族的典型,農民氣質是不可分離的因素;“辛苦而麻木”的農民生活,也和整個他所感到的中國灰色的人生調子很調洽,這樣,就自然集中地成了他所要諷刺的影子。實際上,阿Q雖然是被壓迫在社會最底層而缺乏反抗意識的浮浪性貧農的典型,但他卻多少是漫畫化了的,就是說阿Q那些特征并不是農民所獨有的,而是集中了各種社會階層的,特別是新舊士大夫型的缺點和毛病的。魯迅的人間愛深深地藏在那些嘲諷的背后,他要我們正視我們身上的缺點,勇于洗滌我們自己的靈魂。事實上,自從阿Q被創造出來以后,我們民族是有許許多多的先驅者,在做著不斷地洗滌自己的工作的。周揚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者魯迅曾經痛切地鞭撻了我們民族的所謂國民性,這種國民性正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長期統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種落后精神狀態。他批判地描寫了中國人民性格的這個消極的,陰暗的,悲慘的方面,期望一種新的國民性的誕生。”這話主要是指《阿Q正傳》說的。〔1〕
此外,書中比較重視作品創作背景的描述和介紹,并且往往將其放在首要的位置。比如論述《彷徨》,第一段如下:《彷徨》中的十一篇是一九二四年開始寫的,魯迅說:“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哪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新青年》初期,魯迅就說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但他既“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又“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終于“吶喊”起來了。而且這聲音是如此的宏亮,立刻搖撼了青年人的心。到《新青年》分化以后,魯迅是游勇作戰了,正是“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時候,但他并沒有停止了戰斗,他是“荷戟”的;而且這韌性的持久戰是一步步更深入了。當然,看見很多戰友的中途變節,心境是凄涼的,《彷徨》中就不免帶點感傷的色彩,熱情也較《吶喊》減退了些。他自己說“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這是實在的。但魯迅是并不會孤獨下去的,當他默感到革命的潛力和接觸到青年的熱情的時候,他的戰斗是極其尖銳的,這在雜文的成績里就更可找到了說明。〔2〕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史稿》最突出之處無疑是在作品分析中所表現出來的敏銳的藝術感知和卓越的概括能力。作者用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一個作家或一篇作品的獨特風格和整體面貌,語言優美而精煉。如把廬隱小說的主人公概括為“負荷著幾千年因襲的重擔,熱情而又空想的追求人生意義,苦悶彷徨而又狂叫著自我發展;是那么脆弱,那么焦灼的青年”〔3〕;將朱湘的詩歌特色描述為“作風恬淡平靜,也以文字韻律的完美著稱。詩中還保持著一些五四時期的高亢的情緒;歌唱著對世界的溫暖的愛,而又找不到思想的歸宿,這就是率直而到處碰壁的詩人的寫照”〔4〕;俞平伯的散文則被貫以“文字不重視細致的素描,喜歡‘夾敘夾議’的抒寫感觸,很像舊日筆記的風格。文言文的詞藻很多,因為他要那點澀味;絮絮道來,有的是知識分子的灑脫與趣味”的評價等等〔5〕,均妙語連珠而簡練貼切。尤其王瑤先生對《野草》的經典闡釋:“這是詩的結晶,在悲涼之感中仍透露著堅韌的戰斗性。文字用了象征,用了重疊,來凝結和強調著悲憤的聲音”〔6〕,寥寥四十余字勝過成篇累牘的條分縷析而抓住了作品的神采與韻味,堪稱神來之筆。此外,他還注意對藝術上具有相似性的作家進行比較,明確各自的獨創性,找到“同中之異”。例如分析王統照的小說“和初期葉紹鈞的作品相似,都追求著人生的真意義,但他卻更憧憬于美和愛;后期的熱情雖然少了一些,也并不像葉紹鈞那么‘客觀’”〔7〕。#p#分頁標題#e#
《史稿》因其“個人化”的寫作特點,較少帶有后來文學史著述的“體制化”痕跡而更多帶有史家個人色彩。注重藝術分析和史著語言的錘煉,而在運用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上則較為機械,更多帶有嘗試的意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政治理論與文學感受二者間的某種“分裂”。對于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定的“落后”作家及其作品過于肯定(雖然是在藝術層面)缺乏批判,便成為《史稿》受到嚴厲批判的一個重要原因。王瑤的《史稿》作為學科開山之作,一方面許多問題需要自己去面對和處理,可資借鑒的前人經驗和知識積累不多;另一方面,這也給了作者極大的自由,可以不拘一格,少有畫地為牢的思維定勢和種種既成的框架。這二者結合起來的最明顯的體現,也是書中最精彩、最為后人稱道之處,是他對作品的闡釋和解讀。作者采取了一種嶄新的卻也是傳統的論述模式。說它新,是因為此前從未有人在文學史中運用過這一方法;稱其傳統,則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古代傳統的文學評論樣式。也就是上文所說的“感悟式”的作品分析范式。它更多繼承了中國傳統文論注重從整體看待對象的思路,善于對作品進行全局性的把握。對研究者來說,這并不是忽視作品的多層次性,但在思維和論述中常常不把它分割開來,而是努力將其融和在一起。尤其藝術性方面,不是條分縷析的“拆零”,而是整體的“體驗”,即借助研究者的藝術感知去體味作品的藝術風格和整體風貌。這種處理不是借助把作品拆分為語言、敘述、人物等零散的諸多方面來進行,相反,它是依賴于在閱讀中產生的直接的心理活動和審美體驗,其中也許不乏理智的認知,但更多的卻是個體的藝術感悟。在將主體所把握到的作品之“味”完整地傳達出來的過程中,行文也是高度簡練和藝術化的。寥寥幾句詩一樣的語言,就把對象之“魂”勾勒出來,頗有傳統寫意畫的趣味。大概也只有這種藝術化的語言方能較為完整地表達閱讀者的審美感受并使其在由思維到語言的轉化過程中盡量不走“神”、不變“味”。讀《史稿》猶如欣賞中國畫的大寫意,所專注傳達的是對象之“神”而非對象之“形”,在生氣淋漓間盡得各中真味與意趣。需要指出的是,《史稿》走的是“個人著述”的路子,以一人之力寫成,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全書在這一方面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下冊在此方面似乎稍遜一籌)。而此后流行的集體合作、分工撰寫的組織方式似乎并不適合運用這種更體現個人能力、依賴主體感受的研究路數。但此一方法也非完美無缺。首先,它對研究者從藝術敏感到文字表達的諸多方面的才力都提出了較為嚴格的要求:感知力不強,就難以體會和把握作品的藝術魅力;文字功夫欠缺,則無法準確傳達已有的審美體驗。其次,如果將之作為個人學術路數,研究者還可以有所選擇:勝任者自可侍才逞能,任意揮灑而左右逢源;不濟者也可知難而推另尋它途。但作為教材的話,恐怕未必那么適合。
在現代學科體系和教學體制中,作為教材,既需要向學生傳授知識,又必須通過示范和學習讓學生掌握獨立思考和研究的方法。這樣一來,學習內容就必須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重復性,傳授者也不能不考慮受眾的接受能力和認知水平。而且,教學還必須有能夠量化的檢驗標準,需要通過考試來測試學生的掌握情況。且不說學生的知識能力千差萬別,并非人人皆有此藝術敏感,即使了解其間門徑,在具體運用中也是人異言殊,有時還得靠點“靈光一現”式的鋒機與靈感,很難通過“教”與“學”的過程予以傳授和掌握,也難于進行正誤評判。這都和學校教學的要求有所差異。換言之,它更適合作為一部優秀的專家之作,供研究者借鑒參考,也可讓專業以外的讀者興趣盎然,卻不適合作為教科書讓學生學習模仿。《史稿》的上冊于1951年出版,被不少高校用作教材,但批評之聲也不絕于耳。批評者所針對的是其政治思想方面的“嚴重錯誤”,主要是收錄作家作品的標準在政治上把關不嚴,讓一些“落后”以至“反動”的作家也進入文學史;此外對作品的分析也被認為忽視思想內容和時代意義,具有“唯藝術論”的傾向。批評者所依據的顯然是一種與時代合拍的、具有方向意義同時也更為激進的歷史觀念和藝術標準。作者也立即進行了自我批評和反省,在1953年出版的下冊中不難發現這一思路調整的痕跡,但似乎仍無法為主流意識形態所接受。其后著述及其作者的命運便都經歷了一番曲折坎坷。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即使言辭尖銳者,參與討論的人們都是熱情而不乏真誠的。但論者似乎較少注意到這部專著所表現的另一層面的、也許是更具有啟發意義和學術價值的問題,那就是傳統文學批評方式如何通過現代轉換而被運用于現代學科體系里的文學研究之中,揚其長而避其短。中國文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曾被歸納為民族化和現代化兩條基本道路。那么,中國的文學研究(包括文學史研究)是否也需要在將外來的理論、觀念、方法民族化的同時,也將傳統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進行現代轉換呢?王瑤先生為現代文學學科奠基的同時也為文學史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能。可惜的是,此后的時代風云變幻,基于主客觀多方面的種種因素,別的研究者沒有繼續沿著這條初現端倪的路子走下去,《史稿》遂成絕響。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分析式的作品分析方法得到眾多文學史的廣泛運用。一方面說明“二分法”自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研究者已經將這一模式駕輕就熟以至于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分析文學作品,必定是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大板塊。共同的思路、重復的模式、相似的語言不能不說是導致眾多現代文學史著似曾相識、面目雷同的重要原因。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以下簡稱《史略》)出版較之《史稿》晚了四年,自然力求更加符合主流意識形態。一個突出表現是《史略》將作品的思想內容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予以關注,藝術成就則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說,作品“寫什么”比“如何寫”更加重要。如分析葉圣陶的代表作之一《倪煥之》,首先是思想內含的分析:“首先,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的,這是第一部。其次,有意地表現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受了時代的潮流激蕩,從埋頭教育到群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這也不能不說是第一部”;其后又用兩段的篇幅論證小說主人公“可以說是當時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8〕;緊接著又是如下的一段分析:“這就說明了當時作者對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認識還不夠深入,只是看到了革命遭受挫折的暫時現象,而沒有看到革命在工農大眾中的深厚力量。作者在本書中對革命者王樂山的描寫,便可以證明這點。王樂山是比倪煥之更了解革命的意義的,但作者卻沒有表現出他做了怎樣推進革命的工作,讀者只能隱約推求他的活動,而不能得到正面的更深切的印象。另外,二十二章中的倪煥之,似乎已經加入了一個政治集團,但以后倪煥之的行動都不曾明顯地反映出集團的背景,仍是個人活動。而倪煥之參加革命后就寫得有些概念平面,沒有凸出。這些都是由于作者對當時中國共產黨怎樣領導革命知道得不大清楚的緣故”。小說的藝術成就則被拆解為三個方面:“就人物形象方面說,它塑造了革命陣營中一些軟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就結構方面說,可以稱得上謹嚴完整;就語言方面說,字斟句酌,十分精煉”。《倪煥之》被稱為“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確能部分的反映了時代的真實”〔9〕,從而使得《史略》的作品分析帶有某種“題材決定論”的意味。#p#分頁標題#e#
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以下簡稱《史綱》)在《史略》基礎上更進一步,以政治意義、階級分析作為作品分析的核心。例如書中對魯迅前期小說的分析,分為思想意義、人物階級、形式獨創三個部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作品的思想意義“、“《風波》《明天》《故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的階級性”、“魯迅初期作品在形式上的獨創性”。不過,書中對于如何在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中運用政治理論仍舊處在探索和嘗試之中,二者的結合較為生硬,有時過多的思想定性和階級劃分反而掩蓋了作品自身,使其成為政治理論的材料和論據。如分析郭沫若的《卓文君》,先通過引用卓文君與卓王孫的對白來說明女主人公“是以資產階級的個性解放來反對封建倫常的束縛”,“仍未超出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的水平”;再以卓文君和程鄭的對話表現后者“荒淫無恥而又滿口孔孟道德文章的封建文人”〔10〕形象,最后總結“《卓文君》所提出的問題,是表現在婚姻問題上的人性解放問題。卓文君的解決辦法,是小資產階級式的個人主義的奮斗”〔11〕。這一分析模式在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以下簡稱《初稿》)中得以進一步完善。以《狂人日記》為例,《初稿》首先論述的是其“標志著魯迅創作事業的偉大開端,也標志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偉大開端”的文學史地位〔12〕,其次是介紹作品“借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自白,來暴露封建社會的‘人吃人’的悲慘事實,來反對封建社會的腐朽的傳統和因襲的罪惡”的內容,并著重指出其“超過舊的批判現實主義的范疇,并且開始包含著極其顯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因素”的意義〔13〕,最后則是藝術分析:“《狂人日記》只是十三則不記月日的日記,但人物、情節和主題思想表現得十分鮮明、十分完整。這一方面說明了魯迅的創作正是承繼了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嚴謹、洗煉的特色,而且給了它以創造性的發展;同時,《狂人日記》這個標題是采自俄國作家果戈里在一八三四年所寫的一篇小說的篇名,這也說明了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而把這種重要影響首先帶到中國文學上來的,正是我們最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魯迅。”〔14〕
這一模式的集大成之作,是1979年開始陸續出版的唐弢主編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唐弢本”)。以書中對《女神》的分析為例,先概述了詩集的文學史地位和開創意義;接下來簡介其寫作背景;其后分析了作為代表性篇章的《鳳凰涅搫》和《女神之再生》;隨之按照題材分類論述詩集中的四類作品;最后綜論詩集的藝術特色。不僅面面俱到,而且條理清楚,重點突出。有時還將多方面的分析結合起來,如《子夜》一節中,在分析吳蓀甫時融會了人物形象的定位和塑造手法的分析:舉出其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又以“個人利害的籌慮”為中心的事例,一方面證明了作者“從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征”的藝術手法,另一方面也借此闡釋了主人公作為精明強悍與軟弱并存的“鮮明的矛盾的統一體”的性格特征〔15〕。尤其唐弢撰寫的魯迅專章,縱向上歷時地再現了作家數十年的創作歷程,囊括了其各種文體的全部創作,橫向上對作品的藝術特色、思想內容、時代背景、歷史意義等均進行了分析和描述,代表性的經典作品也設置了專節(如《阿Q正傳》)。原本內容龐雜而頭緒繁多,卻安排得不蔓不枝,結構勻稱而舒緩有致。為文學史該如何寫法提供了一個優秀(但不是唯一的)的范例。從《史綱》到“唐弢本”,對作品的分析思路和方法一脈相承,逐漸形成了較為固定和規范的分析范式,從而在現代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中占有絕對地位,成為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寫作的既定模式。分析式的方法的突出特點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將文學作品進行逐步的剝繭式的分解,第一層是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前者又劃分為分為背景、主題、社會意義等,后者則解析為語言、形象、結構手法等,由此層層深入,步步為營,達到對作品的“解構”。如果說前述感悟式分析注重的是整體的話,分析式的思路就是逐步細化,猶如由江河到水滴再經分子而原子、電子的科學觀察過程。
面對豐富多彩的作品卻采用千篇一律的方法,雖有重復呆板之嫌,卻也頗有自身的特點和長處:其一,有一套成型的分析思路,也提供了具有可重復性的操作規程,以及一套與之相配套的名詞術語,不管什么樣的作品,只要按此方法處理,就好比把原材料放進機器,可以得到同樣質量、一個模子的產品,學術研究在這里幾乎成為一種模式化的知識生產;其二,由于上述特點,這一方式更適合教育教學的需要:對學生來說,只要掌握了這個方法就能大體不差地對付任何一部作品(當然也有不那么適用的,比如某些現代派的作品),對教師而言,因其方法、思路的整齊劃一,也便于對教學成果作量化的檢測和考評。由此,它受到文學史撰寫者的青睞就不是偶然的了,因為絕大多數現代文學史著都是高校教材,所擔負的首先是知識傳授和思維訓練的任務,就適應建國后“一體化”的現代學術體系尤其是教學體制而言,“分析式”的作品論述模式無疑是成功的;其三,這一模式也適應了常用的集體合作、分工負責的教材編撰組織方式。編寫者之間知識結構、學術取向乃至識見高下的差異本屬人之常情,這一模式化的方式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個體間的種種差異而代之以統一的思路和語言,把彼此間不一致的流露的可能與范圍限制到了最小。而其相應的結果便是著述個性的消弭,眾多文學史無論篇章布局還是分析論述,都大同小異,行文風格也趨于一致。對研究者個人來說,這種模式也許太過呆板,不免畫地為牢,限制了研究的突破和思路的拓展。但天才和大家終歸是少數,開一代風氣者也要有天時地利之便。更多情況下,多數人只要按著既成范式按部就班兢兢業業,也會有所斬獲。這也是推動學術研究穩步前行的動力所在。
分析式與感悟式相比較,前一種方式的廣泛運用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它更符合學校教學的需要,適應多數學生的水平,可以作為“傳授”與“學習”的對象。雖然條分縷析的分析與整體感悟的體驗相比各有優劣,也有不同的適用對象,不能說哪一方就具有絕對的優勢。但任何一種方法,無論其自身如何科學和有效,一旦成為了無新意不斷重復的模式,后果不僅是眾多文學史著述的低層次的重復性,還導致研究思路、學術視野的僵化,這才是需要研究者注意和警惕的。自《初稿》之后,文學史個人寫作的傳統中斷近三十年,直到1984年才有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予以再續。關于這一“斷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評價也需要將其放在具體的歷史情景中予以觀照。畢竟,沒有哪一種史著體例稱得上完美無缺,也不會有“萬金油”式的寫作方式、分析路數。除去學術發展的階段性和個人才力、學識等因素外,時代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過多的限制固然可能“屈才”,但百無禁忌(實際上這也是不可能的)也會令人無所適從。在這方面,文學史寫作者和研究者是應該有更多的歷史眼光和開放思維的。#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