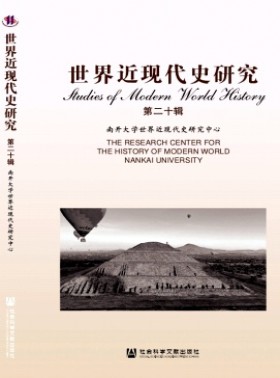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近現代與現代的史識融合,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長期有感于因通俗文學一支的闕如而導致的殘缺不全的文學史現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范伯群教授就把研究的視域轉向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帶領自己的科研團隊在完成了資料匯編、作家傳記、重要論文等先期成果后,終于在2000年4月出版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范伯群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提升了近現代通俗文學研究的高度,填補了這方面的研究空白。但范伯群并沒有滿足于此,為彌補《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粗放性、筆調格調的不一致等不足,他退休之后依然筆耕不輟,對自己鐘愛的通俗文學園地進一步精耕細作,于2007年1月出版了《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達到新的研究高度,賈植芳教授評價為:“這是設計精巧、施工精心的優質二期工程。”[1][p.3]對比這所謂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我們發現后者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一作為一種“史”的整合,文學史同樣需要文學史家的史識觀照和勾勒,需要文學史家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有充分的理性把握,需要“突出文學演進的趨勢,而不是大作家的生平逸事;注重結構的分析,而不是事件的敘述”[2][p.3]。否則,如果把重寫文學史看作是單純時間的延伸和敘述量的激增,那文學史就變成了散漫的“資料長編”,而真正失卻了“史”的含金量。對比范伯群主編、著寫的兩部通俗文學史,我們發現后者相對于前者而言,文學“史”的意識明顯加強了。 首先,在書寫體例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改變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板塊式的結構形式,不再把全書主要分為社會言情編、武俠會黨編、偵探推理編、歷史演義編、滑稽幽默編、通俗戲劇編、通俗期刊編、大事記編等八個部分,不再遵循“大按題材小按時間”等形式的編寫體例(如社會言情編分述倡門小說、社會小說、言情小說、地域小說,倡門小說,個案分析按照時間先后順序從1848年的《風月夢》論到1938年的《亭子間嫂嫂》),而是大體上按照時間順序分時代地把各種題材的文學作品潮與報刊雜志的興辦結合起來論述,把通俗文學的發展與興盛放置于現代傳媒的文化語境中,突出了其世俗現代性的文學特質,進一步彰顯了與精英文學互動相生的發展脈絡:“19世紀90年代到‘五四’前,現代通俗文學曾得到大發展與大興旺,它不僅有《海上花列傳》那樣的藝術成就極高的小說,而且有譴責小說這樣的得到老百姓擁戴的通俗小說;而在‘五四’后,情況有了變化,它得在知識精英文學的相克中求得相生。這是一個通俗文學在被貶中不斷改進自己,以求得自強,以及在自強中不斷開拓新墾地,不斷探索新的生長點的時期,無論是民國武俠小說的奠基,狹邪小說的人情、人道化,偵探小說的移植與本土化,都市鄉土小說的崛起,電影、畫報熱的潮起,都說明通俗作家在相克中的求得相生,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途徑;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張恨水、劉云若與還珠摟主等人的作品更是形成了新的沖擊波,通俗文學的成就已開始與知識精英文學‘雙翼齊飛’的格局;到20世紀40年代,有的作家則已經進入‘超越雅俗’、‘融會中西’的境界,其實這是很好的發展勢頭。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股勢頭不得不移到臺、港去作通俗文學的血脈承傳。”[1][p.588-589]可以說,變更體例后的通俗文學史較好地體現了上述的史識脈絡,更容易從宏觀角度把握現代通俗文學史的性質和發展歷程,更加嚴謹凝練,通透性和體系性更加鮮明。 其次,在某些文學史觀點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闡釋,力求更加嚴謹可信。《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毅然把講“史”的范圍從原來的近現代壓縮到現代,隱去了近代工商業日趨發展背景下的上海文學趨于現代的萌發歷程,刪去了關于《風月夢》、《品花寶鑒》、《花月痕》、《青樓夢》等作品的現代通俗文學“前史”或者說近代史的論述,而把論述的起點放到了《海上花列傳》上,把它界定為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并論述其六個“率先”的開創意義,賦予其成熟的現代性特征,把現代文學的起點前移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這種界定是需要勇氣和膽識的,它改變了“注重作家作品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功能,突出外在價值和文學歷史價值的文學史觀念”[3],體現了“注重文學作品的藝術創造力、審美價值等內部本質特征,以此闡釋評論作家作品本身的價值,突出作家作品對藝術本身的貢獻”[3]的文學史觀,不失為一種富有新意的獨到見解。另外,《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又在第十九章論述新市民小說時重點論述了張愛玲、徐讠于和無名氏,稱其為文學領域中的“一國兩制”[2][p.573]者,體現了20世紀40年代通俗文學“融會中西”、“超越雅俗”的發展勢頭。以三位在新文學史上叫響的作家為其通俗文學史收尾,這也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一個新創,既能“承上”———是現代通俗文學發展的結果,又能“啟下”———為將來《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史》甚至《中國二十世紀通俗文學史》的研究提供某種契機,因此它的命名與確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還有,《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對“都市鄉土小說”的命名、對“黑幕”與“黑幕小說”的概念辨析、大眾化和通俗文學的生命潛力等諸多文學史命題的分析,或是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思考,或是范伯群新近的思考所得,都顯示了其通俗文學史研究的繼續深入。 最后,在文學現象的成因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更加注重“史”的勾連,努力把通俗文學現象放到與外國文學、古代文學或者知識精英文學的關聯中去做動態的分析,而不是把它們看作“孤立的存在”。既然“凝聚與變異相交而成的坐標,是文學研究整體所依據的主要框架”[4][p.34],那么古今融會、中西交流融會背景下的通俗文學同樣也呈現著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的復雜印痕,表現出傳播與接受之間的同步態與錯位態,而這些方面的分析對文學史的勾連與敘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其實,作為“一期工程”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也非常注重這方面的論述,比如在分析通俗文學中的社會小說時,指出明之人情小說的“世情書”和清之“諷刺小說”都是近現代通俗社會小說的“淵源”[5][p.3];在論述社會問題小說時,專門對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問題小說進行了比較[5][p.155-164];在分析民國武俠小說興起原因時,首先指出了它與晚清公案小說并非同一譜系,屬于“新派”而不屬于“舊派”,而是與“尚武”“、愛國主義”的時代精神和外國有關思想特別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5][p.451]。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史”的勾連,如《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在論述“黑幕小說”時,僅僅對“黑幕”與“黑幕小說”進行了概念辨析,為“黑幕小說”正名[5][p.105-112];而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則進一步把它與同時期的美國“揭黑運動”進行比較分析,找到了一個同時代的參照系,使得這時期中國“黑幕小說”的面目更為清晰。又如在論述包天笑創辦的《小說大觀》和《小說畫報》時,《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僅僅對這兩個期刊進行了較長的資料常識介紹[6][p.576-602],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則承接上一階段報刊文言的興盛,進一步對其白話的運用原因進行了論析———民間倡導和官方的合圍,從而對報紙傳媒形式變革的論述更為周全深入。如此不一的深入剖析使得《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更顯通觀理性。#p#分頁標題#e# 當然,為了進一步強化文學史識的整合作用,突出文學史的整體色彩和理性意識,《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基礎上還做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改,比如刪去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一些主觀情感色彩過強的小節標題———“啊!46年塵夢,秋海棠!”“、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上海小說’”等;一些過于招搖的小節題目———“從鮮血洗過的焦土中傳來的鬼哭人聲”、“那張抹不掉的血紙片”“、一只半夜伸出來的手”等;一些過于深奧難辨的標題———“既無‘屈子湘江’,不如‘信陵醇酒’”、“以羅兩峰畫鬼之筆涂抹小說”、“秋笳復作漢槎再生”等;一些冗長的標題———“孫玉聲的《黑幕之黑幕》是一部佳作”、“戀愛全建筑在‘賣方自由’的金錢關系上”等,把主標題和副標題相結合的形式變成了較為簡潔明了的單一標題,進一步深化了文學史“史論”的表現力度,這些都是新著的可取之處。 二治史(包括文學史)離不開史識和史料,并且二者關系非常密切“,重史識者不能沒有史料,要不然只能空口說白話;重史料者也不會沒有一點史識,要不怎樣知道那個是應該搜集的史料”[2][p.250-251]。雖然由于閱讀對象的不同,文學史可以分為研究型文學史、教科書文學史和普及型文學史,在史識深度和材料展現上各有側重,但是治文學史者不應以所謂的“質的規定性”從史料中抽出中意的部分來分析其線索、趨勢、規律,用“性質”論來遮蔽或抹刷史料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遮蓋了文學史的基本面貌和豐富內容,這樣的文學史只能是某種觀念的產物。由于諸多方面的原因,此類文學史已經產生了不少,我們的文學史家秉承著各式的意識形態觀念,不斷地讓一部分作家作品“筆下超生”,對另一部分作家作品“草菅人命”,所以長期以來我們接觸到的往往是殘缺不全的隱去真實面目的文學史,因此對它的去蔽、還原是非常迫切重要的,而要擺脫某種“性質”論的束縛和制約,文學史家必須從史料出發,在史料考證的基礎上發言。為復現真實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版圖,《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把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部分人“診斷”為“死亡”的通俗作家作為主體來展現,在史料的挖掘、打撈和整合上具有彌補文學史“空白”的開創意義,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做得更好一些。 首先,《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從最原始的文學史料出發,更加注重作品的體驗與分析,把作品細讀與文學體驗緊密結合,注重文學經驗的傳達。在大的編寫體系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更加嚴密了,但它并沒有以大而皇之的史論代替史料細節的展示與分析,非常注重感性文學史畫面的呈示,并在此基礎上得出自己獨立的理性判斷。以點帶面依然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梳理通俗文學的重要方法,它把對通俗文學演進發展的論述化入典型作家與作品的論述之中,諸多文學個案的分析顯示了它頑強回到文學經驗本身、回到審美體驗本身的努力。其實《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也比較注重作家作品的個案分析,但是在專章介紹作家的時候采用史料比較龐雜,無形當中遮蔽或淹沒了文學作品的審美意義和作家獨特的文學經驗,如第二編第十章分析悲劇俠情小說家王度廬時,分四節分別介紹他的人生經歷、社會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的心靈悲劇色彩和“平民化”追求傾向,過多地方的平均使墨使得論述有泛泛之論的嫌疑;而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則把有關王度廬的部分壓縮為一節,簡單交代他的生平資料后,重點分析了他的“鶴—鐵系列”里兩部作品《寶劍金釵》和《臥虎藏龍》,在對其情節、人物、主題等方面的細讀比較后,得出俠情悲劇的共同點,又看到它們的重大差異:《寶劍金釵》以情節為中心,而《臥虎藏龍》以性格為中心,由主要作品的特色突顯了作家的創作特征。這種抓典型作家的典型作品的描述方法與魯迅用“藥、酒、女、神”勾勒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用“廟堂與山林”勾勒唐朝文學史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樣,在分析“超越雅俗與融會中西”的張愛玲小說時,重點分析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從小說的文化環境、情節發展、人物心理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它雅俗共賞的特征,說出了它是“將古老的‘梁祝’故事,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形式表現出來”[1][p.554],實質上描繪了“香港的大墳山‘活埋’了一個‘拎得清’的上海少女”[2][p.552]。這種從作品細讀中得出結論的方式成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一個表述方式,從某種意義上還原、豐富了文學史的細節,使得文學史結論更加真實可信。陳曉明論述當代文學史時認為:“對文學經驗本身的關注依然是基本評判標準,在這個學科已有的歷史傳統序列中來思考不斷變更的文學經驗,顯然也是一項重要的原則。”[7][p.2]其實從文學經驗出發,對任何階段的文學史都非常重要,顯然《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這一點上做得比較好。 其次,《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還更加注重征引前人的觀點資料,或對之進行批駁,或用它們證明自己的文學史觀點,從而豐富、深化了對文學史的認識。“文學史研究是一種‘對話’,與凝聚為文本的作家心靈的對話,也與落實為論者的各式詮釋者對話。”[2][p.42]前者的“對話”需要研究者從文學體驗、作品細讀出發,而后者的“對話”需要治史者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來突現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在論述《海上花列傳》時,《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多處征引魯迅、胡適、劉半農、張愛玲、孫玉聲等人的觀點來闡釋它的思想藝術價值,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則在這些人論述的基礎上把它定位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開山之作,深化它六個“率先”的前衛性。另外,兩部書在為通俗文學“正名”時,都批判了茅盾等人在特定歷史時期對通俗文學的責難和不實之論,引用了朱自清的通俗文學為文學史之“正宗”的觀點,在為“黑幕小說”、前期《小說月報》、《禮拜六》等“正名”時均采用了這種批駁—立論的方式,顯得論據充足、真實可信。對于獨創的說法,《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也比較謹慎,力求追溯它能成立的淵源,比如為了命名“都市鄉土小說”,范伯群拿來了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觀點,一步步引向自己的概念,從而彰顯自己概念提出的“合法性”。總之,兩部書不僅大量引用了與作家作品同時代人的原始資料,還大量引用了后來者的諸多資料;不僅援用了國內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對海外學者的重要論證也不放過;不僅引用自己前輩學者的科研成果,而且重視后來學人的研究資料。這種“拿來主義”式的開放眼光既展示了文學史的厚重性,又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比如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多處援引海外學者夏濟安對通俗文學的贊賞言論,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論述張愛玲的小說時,用王德威與夏志清的相關論述來論證張愛玲作品與“鴛鴦蝴蝶派”和“舊小說”的親緣關系;在論述徐讠于時,引用自己學生吳義勤的論述,這種原援引材料的實證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也是該書的一大特色。#p#分頁標題#e# 最后,相對于《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而言,《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增加了近三百幅的圖片資料,以圖文并茂的形式來復原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原貌”。這些來之不易的圖片資料更容易把讀者帶向早已逝去的歷史場域,在相對感性的歷史語境中體味通俗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歷程,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①重要作家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像;②作家的原稿或手跡;③代表作品封面或有一定藝術水準的插圖;④編發的報刊雜志的創刊號;⑤與通俗文學有關的社會背景資料[1][p.587-588]。這些圖片的篇幅相對于整部書而言,比例還是比較小的,只是起到了一個輔助認識的作用,并不像真正的“讀圖時代”那樣圖像淹沒了文字,造就和培養了“識字一代的文盲”,使人們的思考在“視覺文化”的觀賞中無所適從,委頓消弭。圖片在書中起到一個介紹說明的作用,輔助于文字論述,讓讀者深入體會通俗文學發生的所謂的場域和契機,從而對這一被長期打入“冷宮”的文學“逆流”的生存歷程表示同情和理解。相對于當前高科技的數碼照相技術,這些大部分產生于舊時代的圖片資料是比較粗糙原始的,有些作家小像甚至已經模糊不清了,更談不上制作的精美與華貴。但正是由于它的原始,才顯得難得,因為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相當一部分資料早已經“灰飛煙滅”了,這種原始資料的打撈是相當艱難的,它們不像知識精英文學的資料那樣長期被人們重視而保存的相當完好(關于魯迅、丁玲、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資料在博物館、紀念館里相當完備),因此需要搜集者通過向圖書館、向作家的家屬和后代、向收藏愛好者等多種途徑堅持不懈地摸索,范伯群在該書的《覓照記(代后記)》里詳細記載了自己打撈這些圖片偶遇階段—主動“搜集”階段—攻堅階段“三部曲”的艱難而漫長的歷程。所以,文學史敘述中插入大量的圖片資料不僅僅更新了文學史的表述方式,而且也是文學史家科學實證精神的重要顯現形式,它既是一種新鮮的敘史嘗試,又是現代通俗文學治史者艱辛付出的最好見證。 三同時,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還僅僅是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一期工程”基礎上的“二期工程”,屬于范伯群及其同事所進行的“文學史拓荒性工程”的重要成果,這一工程有“一期”、“二期”,也可能有“三期”“、四期”等等,《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確實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賈植芳評價為:“資料更充實了,論點更深化了,歷史脈絡梳理得更加清晰,發展周期得升降起伏得勾勒也顯得全局在胸,了如指掌;還為現代文學史的一個不可或缺得組成部分留下一份豐富的圖像資料。”[1][p.2]但是,我們在驚嘆于《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巨大進步的同時,還應看到一些地方也值得商榷。比如,它在體例結構上更加嚴謹理性了,但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漏掉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的某些內容板塊呢?它對“通俗戲劇”和“幽默滑稽”文學的論述明顯減少;它在論述“黑幕小說”時與美國的“揭黑運動”進行比較固然加深了論述的深度,但這一節是不是與全書結構顯得游離呢?它在論述武俠小說家宮白羽作品的“現代”色彩時,用相當長的篇幅資料來證實魯迅兄弟對他的大力提攜,這種論證是不是到位呢?另外,該書在處理作家資料與作品細讀、史的脈絡與作品的賞鑒、文人群落與小說類型的關系等方面都值得我們商榷。 但不管怎樣,作為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留給我們的開放性啟示依然是非常珍貴的,比如期刊等印刷媒介的入史,電影等圖像媒介的入史,文人—刊物經營者—編輯—讀者等“文化生物鏈條”的入史,文學史發生點的確立,文學史的分期等等。另外,這兩部文學史還僅僅處于將通俗文學從“逆流”的地位挽救出來為自己“平反”的研究階段,對之進行策略性的“彰顯”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它們的內容是非常龐大的(一部130多萬字,另一部近80萬字),為普及實用,它們還需要繼續精簡濃縮,還需要在與新文學的互補交流敘述中“比翼齊飛”,因為“是現代人文主義文化孕育了新文學,是世俗的市民文化滋生了通俗文學,只有兩者的并存并行發展方能適應人們不同層次的審美期待和工商社會保持平衡的需要”[8][p.13-14],范伯群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后記里有著清醒的認識:“‘現代通俗文學史’只是一部斷代的專業文學史,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