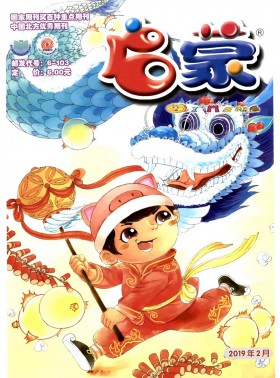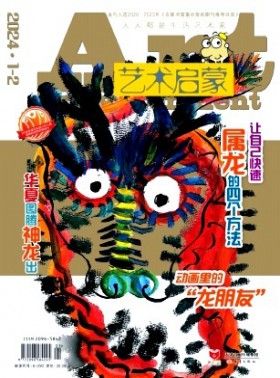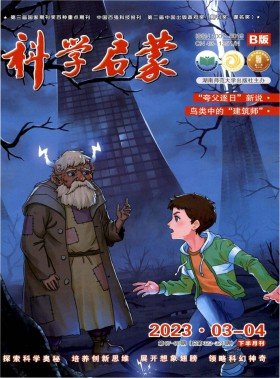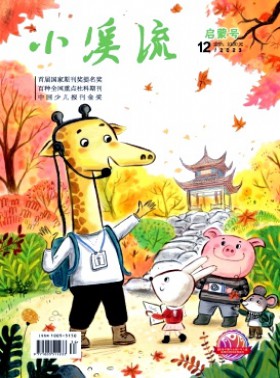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啟蒙與文學(xué)的契合關(guān)系,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lái)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廣大中國(guó)人民的焦慮和探索中,啟蒙并非以完全本色的面貌且多少有些匆忙的出場(chǎng),在缺乏長(zhǎng)久的鋪墊和積蓄力量的境遇中,在中國(guó)的大地上留下一段并不長(zhǎng)遠(yuǎn)的坎坷曲折的印跡。在中國(guó)特定歷史和文化語(yǔ)境下,啟蒙的遭遇啟示我們需要深刻的思想力度與堅(jiān)定的“生命回歸”的守望,以澄清啟蒙的源頭及其指向。當(dāng)真正廓清了啟蒙的內(nèi)涵與指向,諸如有關(guān)啟蒙闡釋過(guò)程中概念的偷換、固有思維模式的禁錮等等問(wèn)題都會(huì)得到清晰的揭示,對(duì)于啟蒙自然會(huì)得到更透徹和準(zhǔn)確的審視與把握。 如果說(shuō)啟蒙存在一個(gè)終極的精神指向,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而魯迅是真正領(lǐng)悟了啟蒙實(shí)質(zhì)精神的一位思想者,他從實(shí)現(xiàn)“自我啟蒙”看見自身開始,義無(wú)反顧地走向生命的回歸。魯迅以他的文學(xué)印證了文學(xué)與啟蒙精神的深度契合。但是魯迅的文學(xué)也以它的豐富和特別,超出了僅僅“啟蒙主義”這樣粗略的概括和界定。在他文字的下面深深鐫刻的是他不無(wú)悲痛的守望與憤然前行的背影。 在我們民族已經(jīng)走過(guò)了一個(gè)多世紀(jì)的漫漫啟蒙之路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在經(jīng)濟(jì)占主導(dǎo)地位的社會(huì)運(yùn)行模式中,對(duì)啟蒙的正本清源,及其與文學(xué)關(guān)系的深入把握,仍然十分有必要和有價(jià)值。具有深刻生命有限性體驗(yàn)的魯迅和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魯迅的文字,無(wú)疑是更可信的。 一 根據(jù)康德的闡釋,啟蒙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1](P1),即喚醒自我對(duì)自身蒙昧的自覺(jué),從而走向“成熟狀態(tài)”。換句話說(shuō),啟蒙是源于自身并指向自身的。相對(duì)照之下,啟蒙在中國(guó)的被解釋被傳達(dá)都與此有很大的差別。在慣性的思維邏輯下,啟蒙一般被理解為一部分人對(duì)另一部分人的教化式的知識(shí)傳輸和指導(dǎo)啟發(fā),這仍是落于封建統(tǒng)治思維模式的窠臼。 啟蒙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作為不斷重新審視世界、審視自己的生命自覺(jué)狀態(tài),是始終保持對(duì)固有思維模式的反思,從而維護(hù)生命本源性的自由狀態(tài)。在這個(gè)意義上,可以說(shuō)啟蒙是一種回歸:重新獲得祛文化化的生命狀態(tài)和思維視野,跳出一切桎梏的牢籠,還生命以澄明,反思自身被建構(gòu)的歷史。所以說(shuō)啟蒙不是一部分人針對(duì)另一部分人,不是從上到下,不是主流意識(shí)對(duì)民間意識(shí),不是精英意識(shí)對(duì)大眾意識(shí);也不是針對(duì)某個(gè)歷史階段,或是某個(gè)特殊的群體……正如康德所說(shuō):“啟蒙運(yùn)動(dòng)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1](P3) 啟蒙不是要傳輸某種知識(shí)、某種主義,傳播某種理論,而是回到生命的本初,自己把自己照亮。所謂知識(shí)分子先覺(jué)者的啟蒙主體、人民大眾作為啟蒙對(duì)象等等這樣的認(rèn)識(shí),本身就是對(duì)啟蒙精神的庸俗化理解和把握,意識(shí)深層仍是對(duì)人類整體做出區(qū)別對(duì)待的固守。眾多的限定性術(shù)語(yǔ),如審美啟蒙、革命啟蒙、階級(jí)啟蒙、政治啟蒙、民族啟蒙、個(gè)人啟蒙等等,如此繁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啟蒙本身變得模糊,逐漸偏離了啟蒙的根本性內(nèi)涵,拆解了對(duì)啟蒙的整體性把握、在特定領(lǐng)域的取舍,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種誤解或是遮蔽,始終不能脫離庸俗化的實(shí)用主義的思維邏輯,很有可能導(dǎo)致新的蒙昧,反而走向了啟蒙的對(duì)立面。啟蒙需要個(gè)體生命,突破內(nèi)化為無(wú)意識(shí)的思維結(jié)構(gòu)和范疇界定,以避免啟蒙在種種有形或無(wú)形的障礙面前擱淺。真正的啟蒙只有一個(gè),而且是對(duì)每一個(gè)人、每一個(gè)歷史階段、每一個(gè)民族乃至整個(gè)人類。 二 在中國(guó)的思想史及文學(xué)史上,啟蒙已經(jīng)成為魯迅及其文學(xué)的重要標(biāo)簽。然而對(duì)魯迅及其文學(xué)與“啟蒙主義”之間做一個(gè)直接的概括和界定,無(wú)疑會(huì)忽略或遮蔽其中許多豐富曲折的意蘊(yùn),這其中仍有許多情感、思想與矛盾需要去做細(xì)致的挖掘和思索。 雖有“無(wú)可措手”的寂寞與悲哀,“卻也并不憤懣,因?yàn)檫@經(jīng)驗(yàn)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2](P417),從這里我們看到了魯迅的重大思想轉(zhuǎn)折,對(duì)于“啟蒙他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透視,他從這一刻起開始了“啟蒙自我”、照亮自我的歷程。魯迅深入到了啟蒙精神的內(nèi)核,堅(jiān)守了與康德相通的啟蒙視野。“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科學(xué)與民主作為中國(guó)啟蒙樹起的旗幟,它們的歷史有限性和現(xiàn)實(shí)局限性,對(duì)生命及文化都有異常清醒透視的魯迅,于此都保持了警惕性的深深質(zhì)疑與反思。對(duì)于知識(shí)分子也沒(méi)有因?yàn)橥槎鴾p弱對(duì)他們的批判,同時(shí)對(duì)自身堅(jiān)持了慘烈的自剖與反省。 “最要緊的是改造國(guó)民性,否則,無(wú)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3](P31)不難看出,在否定了外在性“招牌”的國(guó)民性改造,在魯迅的思維里是內(nèi)向性的追問(wèn)與指向。魯迅所謂的改造國(guó)民性,在根本上就是要恢復(fù)人的本源性的生命狀態(tài),是在“自我啟蒙”完成之后的生命回歸之旅。“我們覺(jué)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就是誠(chéng)與愛(ài)。”[4](P7)這即是魯迅為啟蒙吶喊、提倡改造國(guó)民性的源發(fā)點(diǎn)。也正是從這樣的起點(diǎn)出發(fā),魯迅發(fā)出這樣的祈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wú)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qiáng)暴。我們還要發(fā)愿:要人類都受正當(dāng)?shù)男腋?rdquo;[5](P125)。從個(gè)體生命到整體的人類群體,魯迅始終給予現(xiàn)世最本真的觀照。 著名的“鐵屋子”的比喻,在出現(xiàn)于《吶喊•自序》之前,魯迅已經(jīng)沉默了十年。在“看見了自己之后”,沉潛于自己內(nèi)心的悲觀和虛無(wú)之中。面對(duì)啟蒙理想的窘境,“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shuō)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yàn)橄M窃谟趯?lái),決不能以我之必?zé)o的證明,來(lái)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2](P419)。“在年青時(shí)候也曾經(jīng)做過(guò)許多夢(mèng),……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忘卻的一部分,到現(xiàn)在變成了《吶喊》的來(lái)由。”[2](P415)縱然魯迅內(nèi)心有怎樣凄惶的生命感觸,有怎樣曲折的矛盾與掙扎,有怎樣苦痛的懷疑與反思,啟蒙的夢(mèng)是他始終不能忘卻的,是他生命中不可磨滅的期望與憧憬,所以魯迅始終堅(jiān)持“立人”的主張,“有時(shí)候仍不免吶喊幾聲”[2](P419)。魯迅以他的文字及自身的行為和遭遇,自始至終捍衛(wèi)了啟蒙的精神實(shí)質(zhì)和個(gè)體生命自由的尊嚴(yán)。#p#分頁(yè)標(biāo)題#e# 從“啟蒙他者”失敗后的熱情中走出來(lái),到看到自己后的“自我啟蒙”,魯迅對(duì)啟蒙始終有他“自己的確信”。在對(duì)科學(xué)與民主的熱烈呼喊中,魯迅保持了靜觀,并對(duì)其進(jìn)行了批判性的深思。然而令人可嘆的是“人們巧妙地將魯迅對(duì)現(xiàn)代民主之存在本身所提出的尖銳問(wèn)題,弱化為他為民主政治之具體實(shí)施過(guò)程中可能出現(xiàn)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的具體的不利狀況的思想警覺(jué)。這樣,人們就成功地為魯迅保留了一種先知般的深刻性外觀,但構(gòu)成魯迅之深刻的問(wèn)題本身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掉了”[6](P68~78)。 作為民主最根本的理論建構(gòu)基礎(chǔ)———個(gè)體生命的自我實(shí)存,在民主的環(huán)境中常常不知不覺(jué)地被抽離、被遮蔽,甚至被遺忘,從而民主往往失之于技術(shù)性、工具性的社會(huì)運(yùn)作方式。所以在充分肯定民主和科學(xué)思想的歷史進(jìn)步與成就的同時(shí),應(yīng)當(dāng)始終保持對(duì)它們清醒的關(guān)注與審視。社會(huì)的完善與建設(shè)不可能一勞永逸,民主與科學(xué)也不會(huì)是所有社會(huì)問(wèn)題的“終結(jié)者”。“出于人的有限性本質(zhì),民主政體作為人的一種歷史性選擇的結(jié)果,其歷史性本質(zhì)決定了它并非某種至善,相反,它的合理性必定是有限度的。”[6](P68~78)民主與科學(xué)自身仍需要不斷完善甚至被超越。魯迅所作出的質(zhì)疑與反思,其起點(diǎn)即是在存在論意義上的個(gè)體生命,是旨在實(shí)現(xiàn)心靈的“生命回歸”至本源狀態(tài)所生發(fā)出的辯證思考。不難看出,魯迅的思考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有限視野,他的超前與清醒也使得他少有與之同行的人。 似乎自然會(huì)成為啟蒙承擔(dān)者的知識(shí)分子,魯迅同樣給予批判,并揭示其悲劇的命運(yùn)。孔乙己一樣的舊知識(shí)分子仍未獲得新生,需要拯救,“自我啟蒙”根本就沒(méi)有完成,如何可能走向“啟蒙自我”,去求索生命的自由,他們?cè)缫淹鼌s了生命“來(lái)時(shí)的路”。而新知識(shí)分子如涓生、呂緯甫、魏連殳等,對(duì)于他們的理想、激情、信仰,在殘酷的現(xiàn)實(shí)面前不得不選擇拋棄,選擇退守,在孤獨(dú)與痛苦中承受靈魂的煎熬、凄涼的沉寂或死滅;他們身心的遭遇讓我們看到生命個(gè)體啟蒙的艱辛及慘痛的過(guò)程,以及蒙昧慣常的歷史力量的強(qiáng)大與頑固,幾個(gè)人的燭火終還是被黑暗吞噬。另一方面,知識(shí)分子自身存在的問(wèn)題,如不敢正視現(xiàn)實(shí)、無(wú)奈的逃避、容易陷入內(nèi)心傷痛的沼澤難以自拔等等,都警示我們知識(shí)并不直接帶來(lái)覺(jué)醒、抗?fàn)幣c堅(jiān)持,知識(shí)分子同樣是有限的,所謂知識(shí)分子的啟蒙主體地位依然被質(zhì)疑與懸置。所謂由知識(shí)分子構(gòu)成的精英階層在何種意義上存在,他們是否擁有經(jīng)得起時(shí)間檢驗(yàn)的真理,他們是否可以擁有更大的話語(yǔ)權(quán),都是需要重新審視的。 在魯迅所有的小說(shuō)中,我們發(fā)現(xiàn)根本就沒(méi)有啟蒙成功的范例和方案,而只有啟蒙與蒙昧之間的曲折復(fù)雜的愛(ài)憎和沖突的人生感悟。作為魯迅吶喊第一聲的《狂人日記》的主人公狂人,當(dāng)他意識(shí)到“我未必?zé)o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7](P432),就已宣告了覺(jué)醒者自身的悲劇與尷尬的境遇。《祝福》中祥林嫂的出場(chǎng)滿含深意。作為見過(guò)世面的“我”對(duì)祥林嫂的描述與“我”自身形成了多重的反諷映照。“我這回在魯鎮(zhèn)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shuō)無(wú)過(guò)于她的了。”“她分明已經(jīng)純乎一個(gè)乞丐了。”“我就站住,豫備她來(lái)討錢。”[8](P6)祥林嫂關(guān)于靈魂有無(wú)的拷問(wèn),見證了“我”的虛弱無(wú)力、彷徨失措;“我”卻見證了祥林嫂的“改變”與造成她“改變”的幾番積極努力背后的掙扎、苦痛、自責(zé)、悔恨、無(wú)奈,以致最終麻木的徹骨的凄涼。“我”通過(guò)祥林嫂看到了啟蒙的沉重,也看到了自己的逃避和無(wú)能為力,而祥林嫂從“我”這里徹底走進(jìn)了希望的覆滅。 自我既是啟蒙的終點(diǎn),也是啟蒙的起點(diǎn),自我就是啟蒙自始至終的主線。啟蒙也可以說(shuō)是從發(fā)現(xiàn)自我的“自我啟蒙”到完成“啟蒙自我”的過(guò)程。而“他者啟蒙”,本質(zhì)上是教化式的主體對(duì)受體的對(duì)立思維的結(jié)果,是對(duì)啟蒙基本要義的悖反,是無(wú)法真正實(shí)現(xiàn)啟蒙的。“啟蒙他者”是具有精英意識(shí)的人的文化想象,每個(gè)人都是有限的存在,但是真正的“生命回歸”仍需要靠每個(gè)人自己去實(shí)現(xiàn)。 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寫道:“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shuō),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gè)人的無(wú)治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zhǎng)起伏罷。我忽而愛(ài)人,忽而憎人;做事情的時(shí)候,有時(shí)確為別人,有時(shí)確為自己玩玩,有時(shí)候則竟因?yàn)橄M鼜乃傧?hellip;…”[3](P79)“總而言之,我為自己和為他人的設(shè)想,是兩樣的。所以者何,就因?yàn)槲业乃枷胩诎担烤故欠裾娲_,又不得而知。”[3](P80)這就是魯迅,勇于坦露自己內(nèi)心異常苦痛的矛盾,承認(rèn)自己對(duì)世界的不確知,而這樣對(duì)自身的無(wú)情解剖,是讓人難以想象和承受的。作為“歷史的中間物”[9](P285~286),無(wú)法完全割斷因襲。“覺(jué)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wú)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后來(lái)的青年。”[9](P286)所以告誡自己,也告誡那些“偏愛(ài)他未熟的果實(shí)”的人,“但我并無(wú)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méi)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fā)起什么運(yùn)動(dòng)。不過(guò)我曾經(jīng)嘗得,失望無(wú)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lái),有人希望我動(dòng)動(dòng)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lái)者一些微末的歡喜”[9](P282)。因?yàn)橛兄@樣深重的“自知之明”和“毫無(wú)把握”,他這里沒(méi)有答案,“自我啟蒙”的覺(jué)醒沒(méi)有實(shí)現(xiàn),啟蒙是難以想象的。關(guān)于未來(lái)的路“連我還不明白應(yīng)當(dāng)怎么走。中國(guó)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dǎo)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gè)終點(diǎn),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wú)須誰(shuí)來(lái)指引。問(wèn)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9](P284)。前行中魯迅始終保持對(duì)自己思想的審視態(tài)度,也時(shí)刻提醒他人應(yīng)有所質(zhì)疑的對(duì)待。 #p#分頁(yè)標(biāo)題#e# 三 啟蒙,最重要最關(guān)鍵的一步是自我懷疑與自我發(fā)現(xiàn),從而走向“自我啟蒙”。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的“魔咒”。“自我中心是生命的必要條件,但是也是地球上包括人在內(nèi)的所有生物與生俱來(lái)的一種內(nèi)在限制和缺陷,因此每一種生物實(shí)際上都處于終身的困境中。”[10](P12~13)的確,個(gè)體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相信的與生俱來(lái)性,使得自我懷疑異常困難,無(wú)異于宣告自我存在合理性的破產(chǎn),從而導(dǎo)致生存失去根基。筆者認(rèn)為可以從兩個(gè)層次來(lái)認(rèn)識(shí),第一個(gè)層次,從生命本體的意義來(lái)理解,生命的存在是需要肯定和認(rèn)可的,需要珍惜和熱愛(ài)的;第二個(gè)層次,生命在歷史的進(jìn)程中,經(jīng)過(guò)漫長(zhǎng)文化的洗禮,形成具有相對(duì)穩(wěn)定的思想意識(shí)、情感結(jié)構(gòu)、人格特征的歷史性存在,這個(gè)層次是需要懷疑的,需要不斷審視和檢驗(yàn)的。 而人們通常的理解是把這兩個(gè)層次混為一體,以致模糊不明;或是看不到第一個(gè)層次的生命的本初狀態(tài),直接把第二個(gè)層次理所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是自身的根本性存在,從而陷入“歷史的牢籠”,成為特定意識(shí)模式的囚徒,以致陷入終身困境中。這可以說(shuō)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啟蒙異常的艱辛與坎坷。在20世紀(jì)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中,魯迅就是一位少有的穿透了歷史的迷霧與“自我中心”困境的深刻自省的思想者。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魯迅一生所嘔心瀝血的就是旨在打破“自我神話”的迷夢(mèng),展現(xiàn)了自身完成“啟蒙自我”的苦痛歷程與悲壯的“生命回歸”。 中國(guó)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倡導(dǎo)的家國(guó)意識(shí),使得民族國(guó)家這些巨大的文化構(gòu)成元素根深蒂固,占據(jù)著人們觀念的主導(dǎo)地位。個(gè)人的一切都與家與國(guó)深深地、不容質(zhì)疑地連在一起,以致在思想和精神的領(lǐng)域,個(gè)體生命本位總是處于被遮蔽或被壓抑的缺失狀態(tài)。一個(gè)人若只是生活在自我獨(dú)立的精神世界中,便會(huì)遭到普遍的排斥與隔離。這種生命個(gè)體對(duì)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守護(hù)與人類的群體性生存的歷史文化凝聚和認(rèn)同之間的沖突,是人類面對(duì)的一個(gè)時(shí)刻潛在的深遠(yuǎn)矛盾。在《彷徨》和《野草》的字里行間,同樣透露出這個(gè)矛盾也是魯迅所深深體驗(yàn)并難以釋懷的生命情結(jié)。中國(guó)馬克思主義先驅(qū)先生“愛(ài)人比愛(ài)國(guó)更重要”的聲音已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中,但需要申明的是啟蒙并不是否定集體性的解放的。這其中的思辨關(guān)系,“五四”一代的先輩們已給出了極富啟示性的思考。魯迅有言:“國(guó)人之自覺(jué)至,個(gè)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guó)。人國(guó)既建,乃始雄厲無(wú)前,屹然獨(dú)見于天下。”[11](P56)胡適有言:“爭(zhēng)你們個(gè)人的自由,便是為國(guó)家爭(zhēng)自由!爭(zhēng)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guó)家爭(zhēng)人格!自由平等的國(guó)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lái)的!”[12](P663)每個(gè)個(gè)體都是集體中的一員,都受集體的制約,但每個(gè)人都有自我獨(dú)立思考與質(zhì)疑的權(quán)力。當(dāng)啟蒙的個(gè)體生命本位遭到否定和遺棄,那啟蒙也就失去了路徑和根本的指向。在并不遙遠(yuǎn)的我國(guó)中,整個(gè)國(guó)家的民眾對(duì)“革命”和個(gè)人崇拜的盲目迷信與狂熱,其中的教訓(xùn)不能不令我們深思和反省。 由此可見,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形式,有其自身存在的本源性的悖論和矛盾,加之各個(gè)人類群體不同的歷史文化的原因,啟蒙自有艱難曲折的深刻根源,在特定的時(shí)代和歷史情境中與特定的民族背景下,啟蒙也許會(huì)面臨更加復(fù)雜多變的環(huán)境,祛蔽的過(guò)程中常常會(huì)形成新的遮蔽,以致造成或長(zhǎng)時(shí)期或短時(shí)期的新的蒙昧。所以客觀地講,對(duì)于啟蒙的現(xiàn)在與未來(lái),我們?cè)谑冀K堅(jiān)持永不放棄的基礎(chǔ)上,不能急于看到一個(gè)啟蒙的結(jié)果,也不能急于給出或悲觀或樂(lè)觀的判斷和結(jié)論。“自我中心”的“魔咒”和歷史文化的凝聚與認(rèn)同的積淀力量的難以抗拒,牢牢地規(guī)約著每一個(gè)人,以致人被困為無(wú)意識(shí)的囚徒。暫不論由此衍生出的種種迷霧與阻礙,時(shí)間與生命自身的制約使得啟蒙幾乎無(wú)法避免的艱難與漫長(zhǎng),然而像魯迅一樣穿透并超越這些無(wú)形障礙的思想者本身,就是實(shí)現(xiàn)“生命回歸”的啟蒙指向的最好詮釋。 四 啟蒙作為一種生命精神的指向,是重要的思想資源。啟蒙元素的融入對(duì)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是極大的推動(dòng)和豐富。在啟蒙精神和視野的拓展與提升下,文學(xué)展現(xiàn)出新的面貌。剝離種種主義、種種理論,以生命為根本指向,文學(xué)真正成為審視與表達(dá)生命情感和思考的園地,也真正出離于形形色色的意識(shí)形態(tài)或顯在或潛在的影響和束縛,在原有的審美情趣及結(jié)構(gòu)之外,不斷開拓出新的審美天地。從接受美學(xué)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啟蒙對(duì)生命個(gè)體的審美心理與情感都產(chǎn)生影響與革新,從而產(chǎn)生新的審美期待,形成新的審美情趣與視野,進(jìn)而促進(jìn)文學(xué)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 關(guān)于啟蒙與文學(xué),魯迅的文字對(duì)于加深我們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探索的價(jià)值。魯迅的文學(xué),尤其是小說(shuō),所表現(xiàn)與傳達(dá)的復(fù)雜幽深的人生體驗(yàn)與生命況味,是難以用僅僅“啟蒙主義”這樣理論性的術(shù)語(yǔ)來(lái)概括和容納的。作品人物的遭遇,心理的變化起伏,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微妙,情感的波瀾,日常生活中人情的冷暖薄厚,季節(jié)的生息交替,人生五味的細(xì)微描寫與呈現(xiàn),個(gè)體與群體、與社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繁復(fù)糾纏的情與理……魯迅給我們展現(xiàn)了作為一個(gè)生命個(gè)體的人的生存———由微觀生活而直透宏觀存在的本相。另外,魯迅言明的在創(chuàng)作中運(yùn)用的“曲筆”以及未曾都說(shuō)出來(lái)的話,這些隱去的思索話語(yǔ)與體驗(yàn),同樣在向我們昭示著生命的生存更為難言的創(chuàng)痛、孤獨(dú)與絕望。魯迅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多重審視視角、多重注視的目光,是他一層層反思質(zhì)疑的體現(xiàn),是深厚思維力量透視與洞穿的體現(xiàn)。這樣的藝術(shù)手法更適合于、也更深刻地展現(xiàn)出他思想的脈絡(luò)和經(jīng)緯。 魯迅的文字簡(jiǎn)練、樸實(shí)、真摯,同時(shí)飽含感情,而這背后正是廣博深刻的沉思與體驗(yàn),在語(yǔ)言上凝練的結(jié)果。這樣富含情感與思想的句子在魯迅的作品中隨處可見。《明天》里“單四嫂子終于朦朦朧朧的走入睡鄉(xiāng),全屋子都很靜”[13](P456);在吶喊之前“我因此也時(shí)時(shí)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14](459~460);回鄉(xiāng)的路上眺望“蒼黃的天底下,遠(yuǎn)近橫著幾個(gè)蕭索的荒村,沒(méi)有一些活氣”[15](P476);離鄉(xiāng)時(shí)“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15](P485);對(duì)于生命“假使造物也可以責(zé)備,那么,我以為他實(shí)在將生命造的太濫,毀得太濫了”[16](P553);《祝福》的夜里“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8](P10);童年的回憶里“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fā)散出來(lái)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lái);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里”[17](P564)。#p#分頁(yè)標(biāo)題#e# 對(duì)于逝去的歲月“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jué)得大半年來(lái),只為了愛(ài),———盲目的愛(ài),———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18](P121)。痛心“死于無(wú)愛(ài)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18](P128)。感傷于“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的板床,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shí)使我希望,歡欣,愛(ài),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gè)虛空,我用真實(shí)去換來(lái)的虛空存在”[18](P129)。當(dāng)收回追憶的思緒,“我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jìn)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shí)深深地藏在心的創(chuàng)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shuō)謊做我的前導(dǎo)……”[18](P130)這些文字隱去了紛繁復(fù)雜的思索和沖突,只是體驗(yàn)與思考深深融合在文字里留下的質(zhì)感和重量,讓我們所感觸到的是一顆偉大的心靈無(wú)限的悲思與哀愁。 如若沒(méi)能深刻體驗(yàn)啟蒙精神的內(nèi)核,無(wú)法內(nèi)化于生命,以致真正的啟蒙對(duì)某些創(chuàng)作者來(lái)說(shuō)始終是外在性的。因此在自身未完成“自我啟蒙”的情況下,創(chuàng)作者對(duì)啟蒙的狹義理解和處理束縛于固有的思維框架內(nèi),從而在作品的呈現(xiàn)上不但會(huì)削弱了形象的深度和表現(xiàn)力,而且不能藝術(shù)化傳達(dá)啟蒙的真正內(nèi)涵。藝術(shù)上的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啟蒙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出了問(wèn)題,而是創(chuàng)作上的欠缺,對(duì)思想和藝術(shù)造成兩方面的損傷。 文學(xué)的審美意識(shí)追求的是生命的真與善,是生命的豐富與心靈的自由,而啟蒙所要實(shí)現(xiàn)的正是生命回歸到本真,同樣是指向生命的自由。“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的啟蒙,與文學(xué)的天然契合,使得文學(xué)不會(huì)淪為庸俗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工具。啟蒙對(duì)人生命自由的不斷拓展和澄明,為文學(xué)打開了更加廣闊和自由的精神時(shí)空與生命情懷;文學(xué)會(huì)更好地展現(xiàn)透徹的啟蒙理想與方向。啟蒙有了文學(xué)的審美的承載,使得旨在“生命回歸”的精神自由追求不至于顯得虛無(wú)縹緲。也正是文學(xué)的審美化的傳達(dá),使得真正的啟蒙不至于滑入新的蒙昧。雖然文學(xué)并不必然負(fù)載著啟蒙的使命,文學(xué)也不是實(shí)現(xiàn)啟蒙的絕對(duì)力量,但是啟蒙與文學(xué)的契合是高度統(tǒng)一的。在藝術(shù)上把握這種統(tǒng)一,就需要廣闊深厚的思維視野與富有生命力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