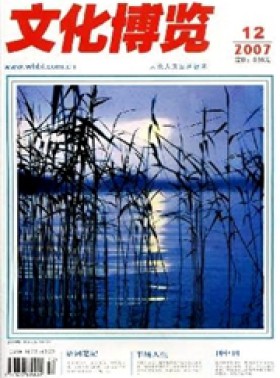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化視角闡述地域文學現象,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地域是相對于整體區域概念而言的,地域的存在,單純從自然因素考慮,更多側重的是其地理方面的內涵,然而把地域一詞放至空間和時間的維度來看,其最主要的特點是文化內涵。“從外延來說,它主要指自然地理地貌,再深一層有民俗習慣、禮儀制度、宗教信仰、方言俚語等,處于核心層面的則是人的心理意識、性情秉賦、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1]那么,依托“地域”而發源的文學,也就會因為此地域與彼地域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或者說多元化的發展,這種依托獨特的地域特色而發展起來的文學,我們可以粗略的稱之為地域文學。地域文學是中國文學整體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地域文學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創作個性、地方性、民族性得到了很好的統一,使得地域文學在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而且極其重要的作用。從外在的表現形式來看,由同一地域成長起來的作家雖然作品各具特色,但是卻有一個共同相似點就是對本土精神的堅持和對本土文化的傳承,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學現象或者形式上松散的作家群系列。 在對地域文學的研究上,如果把對地域文學的作品所作的審美分析,諸如作品的思想意蘊解讀、語言特色賞析等看做是內部研究的話,那么從文化的方面,諸如歷史、政治、經濟、風俗、宗教或者自然環境等方面對地域文學所作的研究應該屬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是一個更寬泛的環境,這個環境可以稱之為是文化語境,從這個出發點出發所作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地域文學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點,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視野,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內涵。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反映出地域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缺失,甚至可以說是偏頗,這就是將地域文學與地域文化對應起來,過于強調“一方水土與一方文學”的固有關系。而事實上,文學與文化的關系是異常復雜的,這種關系不僅有相對程度的穩定性,而且還有相當程度的流變性。文化不僅僅構成了文學的一些背景和特點,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文化是文學的深層底蘊與資源,文化的流變與文學的流變還有著深刻的互動性。[2] 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文化和文學的關系,給予地域文學研究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把對文化的理解不是放在地域文學研究的背后,或者說是轉變文化作為地域文學研究語境資源的固定套路,讓文化放在一個與地域文學對話的位置,那么在文化參與地域文學研究的過程中,就會產生不同的研究視角,從而拓展地域文學研究的新思路,并且還能多側面、多角度地關注地域文學,反思地域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地域文學的可持續發展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本文以云南昭通作家群為例,探討文化視角對地域文學研究的拓展。 一、文化與作家 地域文學中的作家,在文化的傳承上是屬于地域文化的,可以說地域文化是本質要素,而作家及其作品則是地域文化的一個表現形式,在地域文化的母體中,孕育出了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學作品。地域文化“是在人類的聚落中產生和發展的,它以世代積淀的集體意識為內核,形成一種網絡狀的文化形態、風俗、民情、宗教、神話、方言,包括自然生態和種族沿革等等,組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的系統。”[3]任何一個有獨特風格,尤其具有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濃厚而深遠的文化傳承淵源,他的創作必然帶有地域文化的鮮明印記。[4]根據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原理,一個人少兒時期積淀的認識基礎,會形成一種心理定勢,這種定勢對他終生的經驗都起著不可擺脫的“同化”或“順化”作用。那些曾為我們深切體驗的東西并未在我們腦海中消失,相反,它們儲存和潛藏于個人無意識,而這個個人無意識包括一切在個人經驗中曾被意識但又被壓抑或遺忘,或在一開始就沒有形成意識印象的屬于視覺閾下的東西。處于無意識表層的個體無意識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可將一組心理內容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情結。[5]對于地域文學中的作家來講,自己植身其中的就是文化土壤,這種文化土壤為其創作提供了一種潛在的基因模式。在這里,文化視角的介入,可以全方位的解讀作家的創作心理、作品的文本氣質和思想意蘊,并能對地域文學的興起和作家群體的出現做宏觀的概覽和深入內部的透視。 近年來在文壇興起的昭通作家群,主要指的是現在在昆明和昭通兩地的一群昭通籍的中青年文學寫作者,這是一個以地域來命名的文學作者群體。它不是一個很準確很嚴密的概括,但它又反映出了人們憑印象、直感感覺到的云南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現象:九十年代以來,來自昭通的一群作者,文學創作出現了可喜的勢頭,在云南顯得較為突出;他們文學創作的相對豐收與他們文學發生地經濟的相對落后,構成了一個奇特的反差,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昭通文學現象”。[6]這個特殊的地域文學創作群體,始于上世紀80年代,并且到目前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勢頭,這個中青年創作群體,從事著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評論等方面的創作,著名作家夏天敏和著名詩人雷平陽先后獲得魯迅文學獎,代表了這個地域文學群體創作的最高水準。 昭通文學現象的興起和昭通作家群的出現,從本質上看,不可忽略他們所共同擁有的“昭通文化搖籃”。在這個文化搖籃中,他們作為一個受動體在不知不覺中承受了這塊古老土地的文化浸潤和氣質熏陶,并且積淀成為作家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這種文化心理結構影響著作家對文學價值觀的選取,影響著作品的文本氣質,以及作品思想意蘊的表達。故鄉是佇立在他們心靈深處的一處永不褪色的風景,是他們心靈深處永遠珍藏的一壺老酒,更是他們心靈深處濃得化不開的“情結”。因此,昭通作家群的文本中更多透出的是一種對家鄉的迷戀、熱愛、思考、對弱勢生命的關注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著名詩人雷平陽在《雷平陽詩選》封底中寫到“我希望能看見一種以鄉愁為核心的詩歌,它具有秋風與月亮的品質。為了能自由地靠近這種指向盡可能簡單的‘藝術’,我很樂意成為一個繭人,縮身于鄉愁。”他寫云南、昭通,寫昭通的土城鄉,鄉愁、鄉思和鄉戀是他詩歌有力而堅實的依托;夏天敏《好大一對羊》,以凝重的筆觸,描寫了地處烏蒙山腹部農村的現狀和窘迫的生活境遇,對農村農民的生命處境表現了深重的憂慮;陳衍強的詩《農村現狀》、《母親的遠方》,泣血的文字書寫的是背后的烏蒙淚;黃玲《四季流云》以自己的家鄉“牛場壩”為題材,盡顯凄美神韻;劉廣雄《星光木棉》和《父親的疆土》雖為軍事題材,卻不失昭通式的文化本色……。在昭通作家群的創作中,他們從自己生活過的那一片土地汲取營養,他們關注著自己的家鄉,展示著自己家鄉的風土人情,描繪著家鄉的發展變化,同時也對家鄉發展過程中的缺陷和不足給予揭示和理性思考。豐富的童年經驗,深沉的童年記憶,對家鄉生活的熟稔,與家鄉文化的血緣關系,使得這些作家創作的價值取向與文本氣質的呈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p#分頁標題#e# 相比之下,身處昆明的昭通籍作家面臨的卻是離開原生地帶來的困惑,以及由此必然導致的在創作上各自不同的發展趨向。一方面,他們與昭通這片故土的精神聯系永遠也不會割斷,他們與昆明這個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精神上的距離,不能完全地融入這個城市。這個城市不是他們的家,一個人真正的家是伴隨自己成長的那個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的家永遠在他生長的故土。這一群人進入昆明時都已經成年了,也就失去了在昆明這個城市里擁有精神上的家的感覺。同時,這些年來,城市變化太快,不是他們拒絕了昆明這個城市,而是變化太快的城市拒絕了他們。另一方面,他們離生長的故土時間越久,對這片土地當下的生活就會越來越陌生,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極為不利的,特別是當他在寫作時又不能忘懷這片土地時。這就是所謂的被“懸置”的狀態。因為這幾位作家都還很年輕,創作以當下生活、現場生活為主,還沒到以回憶往事為主的時期,若到那時,寫作的客體與主體精神也就統一了。目前,他們必然地要在一定程度上經歷客體與主體的分離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漸漸與所生活的城市產生更大的交融,他們的創作與“昭通籍”這一指稱漸行漸遠,也就是說從作品中看不出多少關系,與故土漸行漸遠,直到回首往事的年齡;另一些人由于“常回家看看”,而保持了與故土更長久的精神聯系,在創作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上尋求統一。[6] 從以上昭通作家群的文學創作狀況可以看出,地域文學依據地域文化而存在,文化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影響著地域文學的發生和發展,那么從文化視角入手,通過文化與作家關系的紐帶,可以帶來對地域文學整體性的關照,以及對作家創作心理、創作個性、創作風格和文本的深入解讀。 二、文化與讀者 如果說從文化與作者的關系中,探討的主要是文化對地域文學產生的影響,以及對作家作品的關注和解讀的話,那么,在文化與讀者的關系建構中,強調的是地域文學的接受方面。對地域文學的研究,如果僅僅探討其興起原因及地域特色,或者把其創作者以及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的話,就割裂了文學與讀者的接受環節,文學如果失去了讀者,就沒有了生命力,也失去了成為經典的可能。姚斯在《文學史作為文學理論的挑戰》中指出,文學作品并非是與讀者無涉的客觀存在,相反,作品渴求讀者閱讀,希求與接受者的對話。 文學接受具有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兩種形式,所謂垂直接受即從歷史沿革的角度考察作品的接受、評價和影響情況,而水平接受,指的是同時代人對作品的接受具有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情況。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包蘊了接受的全部深度和廣度。讀者的接受和評價,反過來能影響作家的創作。因此,“文學接受并非是對作品的單一的復制和還原,而是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反作用。”正是由于讀者的接受是對作品中蘊含的作家創作意象的檢驗,正是由于讀者的期待視野和判斷標準會反饋到作家的創作活動中,所以作家就不可能再走司空見慣的舊路,他只能不斷的創新以拉開與讀者期待視野的距離。[5]在20世紀興起的眾多文學研究浪潮中,無論是以姚斯為代表的接受美學還是以伊塞爾為代表的讀者反應批評論,都強調不要把文學活動中“作家———作品———讀者”這一動態持續過程分割成靜態封閉、互不關聯的領域。同樣,地域文學的存在相對于文學整體而言,如果單純從地理系統上來看,似乎是一個封閉自足的系統,雖然客觀的地理環境因為人為區位的劃分,不能得到無限的延伸,但是文化是一個動態的交流過程,無論在共時性還是歷時性上,文化都是沒有邊界限定的,我們稱之為某某地域文化,只是就這一地域獨特的文化內涵而言,也是為了區分這一地域與另一地域的主導特色,在文化的本質上,并不能做出嚴格的區分,這也顯示出了文化的發展變化性及相互交流性。正是由于文化的無邊界和相互交流性,也給地域文學的傳播帶來了有利的支撐,當然也擴大了地域文學的讀者市場。 昭通位于云南東北部,自古歷史悠久,是云南的一座文化城市。其地處滇川黔三省結合處,成為“鎖月南滇、咽喉西蜀”的重要通道,境內烏蒙磅礴,金沙拍浪,山川俊秀,是我國“南絲綢之路”的要沖,為西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起過重要作用。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在這里繁衍生息,自秦開五尺道之后,它就成為了中原文化傳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到西漢時更是創造了燦爛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介于巴蜀文化與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匯點,又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及區域特色,這使其成了早期云南文化三大發源地之一。后來由于交通閉塞和地理條件限制,昭通成為全國相對貧困的地區,但也使昭通成為云南特色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區,崇尚讀書,崇尚文化的傳統在這里一脈相承。此外,杜宇傳播先進的農耕文明演繹出“望帝春心托杜鵑”的千古絕唱;滇中瑰寶漢孟孝琚碑素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內第一石”之美譽;融儒道釋三教為一體的威信觀斗山石雕群被稱為“天下絕”。豐富的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紅色文化形成了昭通獨特的地域文化,昭通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特征,形成了其兼容并包的容納精神。昭通作家的作品通過對大量的民俗、方言等的藝術表現充實著當代鄉土文學創作。他們對地緣環境的描寫和對地域文化的展現既大大增強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特征,也加強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歷史縱深感和真實感。烏蒙大地對廣大讀者來說,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宋封烏蒙,元置烏蒙路,明代置烏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歸流后,改烏蒙為昭通,“烏蒙磅礴走泥丸”的詩句,無人不知。承載昭通獨特文化氣質的昭通文學,據不完全統計,昭通作家近年來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當代》、《十月》、《鐘山》、《詩刊》、《星星》、《大家》、《解放軍文藝》、《散文》、《啄木鳥》、《文學評論》等數十種全國性報刊雜志上發表作品數百萬字,并有多篇作品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小小說選刊》、《詩選刊》、《名作欣賞》、《作品與爭鳴》、等全國著名選刊多次轉載。[7]昭通文學走出昭通,走向全國,甚至有些文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這其中就有一個讀者接受的問題,文學傳播的實質是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這里涉及兩種接受情況:一是讀者與作者屬于同一地域文化,二是讀者與作者屬于兩種地域文化。#p#分頁標題#e# 地域文化作為一定范圍的社會文化,包圍著、浸染著、熏陶著生活在這一范疇內的每一個人,它作為一種文化視野和水準,影響著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選擇、感受和理解,在文學閱讀活動中,進入閱讀過程的讀者的心靈并不是一張白紙,也不是空無一物的單純容器,他們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質和地域文化知識積累,[8]這些參與進讀者的“前見”和“期待視野”建構,影響著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和闡釋。以昭通文學為例,在讀者接受作品的過程中,如果作品所承載的地域文化與讀者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質接近,或者存在某種重要的相通的東西,就越能喚起讀者的情感記憶,讀者對作品也會投入極大的關注和熱情。由于地域文化對讀者期待視野的建構,往往會使得讀者在接觸作品的時候,期待與自己地域文化相近和相通的作品,期待作品中熔注進作家濃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并希望通過對作品的閱讀拓展自己的文化視野,[8]昭通地處云貴川三省結合部,又是上千年來云南邊地聯系中原的咽喉要道,這種唯一重要的位置被改變不到半個世紀,中原文化對云南邊地的影響,最早影響的是昭通,它是云南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長期以來形成了豐厚的文化積淀。[6] 這種文化積淀有別于其他地域文學傳承的文化因素,烏蒙大地古老神奇的文化,通過作家的作品表征出來,能讓其他地域的文學愛好者,通過閱讀作品加以了解和推廣。讀者對拓展文化視野的渴望,能帶動作為文化主要表征的文學作品的消費,從而帶動文學的發展。在這里,讀者與作者之間,所聯系的表面現象是作品,是文本,其深度的紐帶其實是文化的交流。讀者閱讀后的反饋,能對作者的創作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能讓作者通過文學作品與讀者對話交流,這種對話交流必然能拓展作者的創作視界,不是僅僅把眼光限定在一個小的文學圈子內,自娛自樂,忽視文學在傳播過程中的接受問題。作家在展現自己獨有地域文化的同時,也關注其他地域的文化,讓文學創作更加適合不同讀者閱讀的需要,不斷地進行創新,給自己所屬的地域文學增添魅力,也能使自己在創作領域視界更開闊,作品更成熟。九十年代后,隨著中國文學多元化狀態的形成,中原文化對云南文學的關注目光也開始發生變化,不僅僅只關注云南邊地與民族生活的作品,一些報刊雜志、出版社開始注意寫更豐富的云南生活的作家作品,昭通這一群作品沒有多少邊地與民族特色的寫作者獲得了一次機會,他們的作品開始在全國的大刊物上出現。[6]其實這中間體現的就是一個文化視界的開放,讀者對多元文化的接受,所帶給昭通地域文學的一次發展機會。 三、文學與文化品牌的互動 文化是人們通過生產勞動把精神生產中的思維方式、審美觀念、價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凝聚于建筑、工藝品等各種物質形式或音樂、文學等非物質形式對象當中的一種創造性活動。精神創造是文化的本質,沒有創造,文化就會缺乏內在生命力而衰竭。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文化觀念的更新和變革,是文化本質的內在要求。隨著當今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物質需求達到一定程度后,開始把關注點更多的投向精神需求,對文化消費的渴望將越來越大。[9] 文化品牌的推廣,對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當今大到世界范圍的競爭,小到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的發展,文化競爭力可以說是競爭核心,它直接影響著地區經濟的發展。文化的表征多種多樣,不僅包括物質生產,同時也包含非物質生產,而地域文學就是地域文化一個極其突出的表征,地域文學是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實踐,地域文學的充分發展,并且在全國能嶄露頭角,就可以成為當地文化的一張亮麗名片。對本地域起到宣傳帶動作用,對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促進。興起于滇東北的昭通作家群,文學創作的良性發展,與當地經濟的相對落后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反觀此文學群體走過的發展歷程,更能看到其可貴之處。昭通作家群興起于上世紀80年代,這個時期活躍在文壇上的主流是“精英文化”,作家通過文學創作構造著關于國家、民族、理想、信念與自我的文化想象,當時港臺傳入內地的流行音樂、電視劇和通俗讀物雖然受到部分讀者的歡迎,但并沒有對“精英文化”構成嚴重沖擊,也沒有引起知識分子強烈的關注。但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確立,使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文學的生存局面被納入到市場選擇的境地,新興的大眾文化迅速發展,精英文化的社會影響力和關注度都受到了挑戰,于是就有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直至今日,大眾文化從生產、傳播、流通到消費都受到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調控,文學適應新的時代轉型,也被納入了生產消費機制。生產消費文學,實則是生產消費一種文化,誕生于滇東北偏僻地區的昭通作家群,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這個文學群體,并沒有受到太多經濟浪潮的沖擊,仍然保持著對文學本真精神的堅持,并不斷涌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他們的創作讓此地區之外的人了解到這個獨特的群體,了解到他們生活的環境,同時也更關注此地域獨特的背景文化。 當今傳媒技術的發展,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對地域文化有所沖擊和消解,但是很好的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并融入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并不會使自己原有的文化失聲,多種地域文化的并存與良性發展,讓整個文化局面“多聲調”,不同地域文化之間展開對話和交流,有利于達到可持續發展的局面。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給地域文化既帶來了挑戰又帶來了機遇,關鍵看如何創造屬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品牌,并利用此達到經濟與文化的良好互動。作為昭通本地具有影響力的昭通作家群,肩負著塑造本地域文化品牌形象的重任,各級領導和同行們這兩年多以來對昭通作家群給予了更多的關心和支持,可以看出,昭通作家群的創作與過去相比也取得了更為突出的成績,這是令人欣慰的事。但是,當我們把這些成績放回全國背景上去衡量的時候,我們仍然感到實現文學夢想還很遙遠,這個群體還沒有成為在全國有影響的群體,云南文學界期待著這個群體出現更多的有厚度有沖擊力的作品,這個群體在目前取得的成績面前,必須更上一層樓。[6] 因為昭通作家群的努力,使昭通文學創作走出云南,走向全國,這其實代表著一個欠發達地區不斷在增強著自己的發言權,文學上的成功,向外輸出的是一種文化資源,這種文化資源的擴張,能吸引更多的眼光關注這塊古老的土地,也必然帶來經濟上的發展與繁榮,經濟的發展也能給文學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讓在這塊貧困土地上誕生的作家群,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能夠越走越遠。#p#分頁標題#e# 四、小結 地域文學是中國文學整體的一部分,地域文學的繁榮能促進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尤其在當今大眾文化蓬勃發展的時代,文字式微,圖像興起,人們對于“讀圖”的渴望勝于對文字的閱讀,文學作為發揚傳統、表達人文精神、承擔社會責任感的一種特殊文化形式,其發展繁榮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加強對地域文學的研究,從文化角度探討地域文學發展的規律,多側面、多角度地整合地域文學研究的資源,可以有效地引導地域文學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