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詩歌敘事學(xué)的構(gòu)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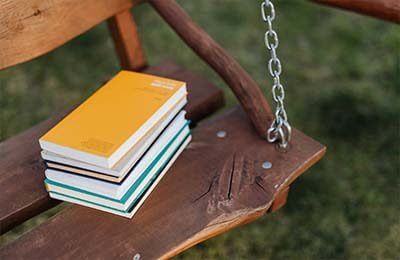
在接受筆者的訪談時,《故事世界:敘事研究學(xué)刊》雜志主編、美國著名敘事學(xué)家戴維•赫爾曼指出,要在后經(jīng)典語境下進一步推動敘事學(xué)的發(fā)展,主要有兩條路徑可走:第一,重新思考敘事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第二,開辟新的不斷出現(xiàn)的研究領(lǐng)域。①實際上,赫爾曼所提到兩條路徑也正是敘事學(xué)在后經(jīng)典階段的主要趨勢與特征。就前者而言,西方敘事學(xué)家近年來對“隱含作者”、“不可靠敘述”、“全知敘述”、“敘述者”、“副文本”、“敘事時間”、“敘事性”等基本概念進行了重新審視甚至展開了激烈的論戰(zhàn);就后者而言,敘事學(xué)研究領(lǐng)域被不斷拓展,不僅涌現(xiàn)了認知敘事學(xué)、女性主義敘事學(xué)、修辭敘事學(xué)、非自然敘事學(xué)、跨媒介敘事學(xué)(包括電影敘事學(xué)、音樂敘事學(xué)、法律敘事學(xué)等)而且也使本文所討論的“詩歌敘事學(xué)”浮出地表。筆者認為,在“超越文學(xué)敘事”的“跨媒介”敘事研究背景下,②有必要把“超越小說敘事”的“跨文類”敘事研究提上日程。詩歌敘事學(xué)既是敘事研究的“后經(jīng)典轉(zhuǎn)向”與“敘事范疇的擴展”或“泛敘事性”的雙重結(jié)果,同時也是“超越小說敘事”的“跨文類”敘事研究的一個新領(lǐng)域。本文以建構(gòu)詩歌敘事學(xué)為中心旨趣,主要闡述如下幾個論題:第一,詩歌敘事學(xué)興起的語境;第二,詩歌敘事學(xué)的建構(gòu)路徑;第三,詩歌敘事學(xué)的批評實踐。 詩歌敘事學(xué)興起的語境 在敘事學(xué)誕生之初,羅蘭•巴特就已經(jīng)提出了敘事無處不在的思想,在《敘事作品結(jié)構(gòu)分析導(dǎo)論》一文中,巴特指出:世界上敘事作品之多,不可勝數(shù)。種類繁多,題材各異。對人來說,似乎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來進行敘事:敘事可以口頭或書面的有聲語言,用固定的或活動的畫面,用手勢,以及有條不紊地交替使用所有這些手段。敘事存在于神話、寓言、童話、小說、史詩、歷史、悲劇、正劇、喜劇、啞劇、繪畫(例如,卡帕奇奧的《圣于絮爾》)、玻璃彩繪窗、電影、連環(huán)畫、新聞、對話之中。③但遺憾的是,在經(jīng)典敘事學(xué)階段,巴特的這一思想沒有得到較好的繼承和發(fā)揚。首先,敘事學(xué)過多地集中在文學(xué)敘事領(lǐng)域。例如,總部位于美國的“國際敘事學(xué)研究協(xié)會”(InternationalSocietyfortheStudyofNarrative)的前身曾直接冠名為“敘事文學(xué)研究協(xié)會”(SocietyfortheStudyofNarrativeLiterature),以凸顯文學(xué)敘事的地位。其次,單就文學(xué)敘事而言,敘事學(xué)一般集中在“小說敘事”(narrativefiction)這一類型。例如,以色列敘事學(xué)家施勞米什•里蒙-凱南將其敘事學(xué)論著的主標(biāo)題取名為“小說敘事”。④把敘事主要限定在文學(xué)敘事尤其是小說敘事的范疇內(nèi),其原因主要與西方敘事文學(xué)的傳統(tǒng)有關(guān)。在《敘事的本質(zhì)》一書中,羅伯特•斯科爾斯等人解釋說:“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小說是西方敘事文學(xué)的主導(dǎo)形式。”⑤可喜的是,這一狀況在敘事學(xué)研究的后經(jīng)典階段得到了根本轉(zhuǎn)變。在后經(jīng)典語境下,敘事范疇不斷擴張,研究方法日漸多元。從大的方面來說,伴隨著“超越文學(xué)敘事”的呼聲,敘事學(xué)開辟了諸多新的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社會敘事學(xué)、身體敘事學(xué)、教育敘事學(xué)、圖像敘事學(xué)等多種派別;就小的方面而言,文學(xué)敘事研究內(nèi)部也逐漸出現(xiàn)了“跨文類”的趨勢,即從單一的小說敘事研究中脫離出文學(xué)敘事研究的多重分支,如傳記敘事學(xué)、戲劇敘事學(xué)等。在這種背景下,詩歌敘事學(xué)的發(fā)生和興起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說,敘事研究的后經(jīng)典轉(zhuǎn)向和敘事范疇的擴張不僅使得詩歌敘事成為可能,而且也間接地催生了詩歌敘事學(xué)。在《后現(xiàn)代敘事理論》一書中,英國敘事學(xué)家馬克•柯里宣稱:“如果說當(dāng)今敘事學(xué)還有什么陳詞濫調(diào)的話,那就是敘事無處不在這一說法。”⑥對此,赫爾曼持有相似論點,他說:“‘敘事’概念涵蓋了一個很大的范疇,包括符號現(xiàn)象、行為現(xiàn)象以及廣義的文化現(xiàn)象;例如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性別敘事、歷史敘事、民族敘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甚至出現(xiàn)了地球引力敘事。”⑦從發(fā)生學(xué)的角度來說,后經(jīng)典語境下的“泛敘事”觀也是詩歌敘事學(xué)得以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比利時敘事學(xué)家呂克•赫爾曼和巴特•凡瓦克認為:“如果說敘事學(xué)是關(guān)于敘事文本的理論,那么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敘事的定義。”⑧同理,如果詩歌敘事學(xué)是關(guān)于詩歌敘事的理論,那么首先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詩歌敘事”或“什么是詩歌的敘事性”這個問題。 在《敘事性的理論化》一書中,約翰•彼爾和加西爾•蘭德說:敘事為什么成為敘事?什么可以使敘事更像敘事?符號再現(xiàn)的哪些成分可以被看作敘事?哪些形式手段和交際手段可以被視作具體的敘事方法?敘事話語的什么特征使得敘事被看作敘事,而不是被看作描述和議論?不同媒介會對敘事的實現(xiàn)有何影響?這些問題至少部分地將敘事的具體性或敘事性納入考察的范疇。⑨從彼爾和加西爾•蘭德的以上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敘事性”(narrativity)大致指涉兩個含義。第一,敘事的基本屬性,即回答“敘事為什么成為敘事”的問題。也即是說,“敘事性”是敘事的“特有屬性”或“區(qū)別性特征”,凡具有“敘事性”的就是敘事,否則就是非敘事。第二,敘事的程度,即回答“什么可以使得敘事更像敘事”的問題。由此出發(fā),則不難回答“什么是詩歌敘事”或詩歌的“敘事性”問題。 首先,“敘事性”是詩歌成為敘事的前提條件。彼得•許恩等人以為,敘事性由“序列性”和“媒介性”構(gòu)成。序列性指的是通過時間把單個事件組織起來形成一個連貫的序列;媒介性指的是從具體的視角對這一序列事件的選擇、再現(xiàn)和富有意義的闡釋。⑩按照這兩個標(biāo)準,毫無疑問,詩歌具有成為敘事的條件。無論是年代久遠的十四行詩還是現(xiàn)代主義新詩等不同歷史時期的詩歌,無論是史詩、戲劇詩還是抒情詩等不同文類的詩歌,都有其特定的序列。根據(jù)《文學(xué)手冊》的解釋:“大部分詩歌都在某種統(tǒng)一性的原則下對其各個部分按照一定的次序編排,它們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給人一種審美愉悅或情感愉悅。”瑏瑡?這個序列就是詩歌的“情節(jié)”,這個情節(jié)既可以是事件、感知、情感的開端、發(fā)展和變化,也可以是想象和焦慮等的開端、發(fā)展和變化。對此,許恩持有相似論點,他說:“詩歌在話語層面上的總體組織(像任何敘事文本一樣)可以被稱作是情節(jié)”。“在詩歌中,情節(jié)典型地使用心理現(xiàn)象如思想、記憶、欲望、感情和態(tài)度等,人物把自己獨白式的自我反思和認知過程作為媒介,通過這些心理現(xiàn)象,人物能界定或穩(wěn)定其自我概念或身份。”瑏瑢?此外,同其他文學(xué)敘事一樣,詩歌也需要通過特定的媒介來實現(xiàn)。許恩認為,詩歌敘事媒介包括兩個基本成分:媒介的使用者(傳記作者、文本的組織結(jié)構(gòu)、說話者或敘述者、主要人物)和視角。瑏?瑣可見,許恩所談?wù)摰拿浇閷崉t是再現(xiàn)詩歌敘事的“媒介化”(mediation),或“敘述”與“聚焦”,即“誰說”(whospeaks?)和“誰看”(whosees?)的問題。筆者認為,除此之外,詩歌敘事媒介還具有其他文學(xué)敘事媒介所共享的載體,詩歌既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既可以是表演的也可以是文字的。#p#分頁標(biāo)題#e# 其次,敘事性使得不同文類的詩歌甚至同一個文類下的不同詩歌既有可能“更像敘事”,也有可能“不像敘事”。如果按照許恩所列出的敘事性的兩個維度(序列性和媒介性)來判斷,序列性比較明顯或比較強的詩歌,具有較高程度的敘事性,反之則具有較低程度的敘事性。同理,若媒介性比較明顯的或比較強的詩歌,就會具有較高程度的敘事性,否則就具有較低程度的敘事性。例如,英國古代史詩《貝奧武夫》按照時間順序,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視角,講述了勇士貝奧武夫先后同怪物格倫德爾及其母親展開殊死搏斗,被擁戴為王,在年老時勇戰(zhàn)火龍,傷重而死的故事,表現(xiàn)出較高程度的敘事性。與此形成對照,一些先鋒實驗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詩歌,如林•賀金年(LynHejinian)的長詩《奧克索塔:一部簡短的俄羅斯小說》(Oxota:AShortRussianNovel,1991)充滿了戲仿和拼貼的技法,缺乏清晰可辨的敘事序列,“蹩腳地”講述一個蒙籠不清的故事,表現(xiàn)了先鋒敘事詩歌的“弱敘事性”。 總之,敘事學(xué)研究的后經(jīng)典轉(zhuǎn)向與敘事范疇的擴張推動了詩歌敘事學(xué)的興起,也基本回答了“為什么詩歌是敘事的”以及“什么是詩歌敘事”的問題。那么接下來需要回答的是“如何研究詩歌敘事”或“如何建構(gòu)詩歌敘事學(xué)”這個問題。 詩歌敘事學(xué)的建構(gòu)路徑 經(jīng)過半個世紀的發(fā)展,敘事學(xué)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不僅“占據(jù)了文學(xué)研究的中心”,瑏瑥?而且還大有“超越文學(xué)批評”的趨勢。瑏瑦?作為展現(xiàn)人類文明的重要領(lǐng)地之一,詩歌卻長期遭到敘事理論界的忽視和冷遇。在布萊恩•麥克黑爾看來,這種忽視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為“若沒有荷馬詩歌作為敘事理論的試金石,至少西方就不會產(chǎn)生從柏拉圖至熱奈特與斯滕伯格等人以降,系統(tǒng)地研究敘事的傳統(tǒng)。敘事理論的許多重大發(fā)展都與詩歌敘事分析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麥克黑爾認為,導(dǎo)致詩歌敘事學(xué)長期沒有得到發(fā)展的原因可以歸咎于專業(yè)研究的分工:“有學(xué)者專門從事敘事研究,也有學(xué)者專門從事詩歌研究,但很少有學(xué)者既研究敘事又研究詩歌。”瑏瑨?為了將詩歌敘事學(xué)研究提上日程,麥克黑爾建議參照迪普•萊斯的“段位性”(segmentivity)和約翰•肖普托的“反分段性”(countermeasurement)理論來思考和建構(gòu)詩歌敘事學(xué)。迪普萊西認為,詩歌“涉及通過空白的協(xié)調(diào)(跨行、跨節(jié)、頁碼空白)來生產(chǎn)意義序列”;與此相反,段位性則是“一種能夠通過選擇、使用和結(jié)合段位說出或生產(chǎn)意義的能力”,是“詩歌作為文類的基本特征”。瑏瑩?詩歌不僅可以分段,同時也可以是“反分段的”。肖普托認為,在很多詩歌中,一種層面和范圍的韻律與另一種層面和范圍的韻律是對立的。例如,艾米麗•狄更森的詩歌一般是以短語來分段,但是其短語層面上的段位劃分又是與詩行和詩節(jié)層面上的段位劃分相對立。在段位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之間,肖普托提出一種段位對立于另一種段位的“音樂結(jié)構(gòu)”(musicofconstruction)。 麥克黑爾指出:在某種意義上,“段位性”和“反分段性”就構(gòu)成了詩歌敘事學(xué)的主要特征,因為“詩歌的段位性、詩歌的空白就是詩歌意義生產(chǎn)的主引擎”。瑐?瑡由此,麥克黑爾得出結(jié)論:如果詩歌既是可以分段的又可以是反分段的,那么敘事也同樣如此。瑐瑢?盡管從定義上看來,段位性不是敘事的主要特征,但敘事學(xué)似乎可以在不同的范圍和層次被分成不同的段位。比如,在故事層面上,事件流可以被分成不同范圍的序列:動作、次要情節(jié)、場景、事件等。在話語層面上,敘述被切分成多重變化的聲音:引用的聲音、闡釋的聲音、在同一層面上相互并置或相互嵌入的聲音,“視角”也可以被切分成多個不斷變化的聚焦。敘事中的時間、空間以及意識都被切分成多個段位。由此產(chǎn)生了不同種類、不同層面的空白。在詩歌敘事中,敘事自身的段位與詩歌的段位形成互動,由此奏響了不同種類、不同范圍的段位之間的“音符”。? 為了驗證“段位性”和“反分段性”之于詩歌敘事研究的效度,麥克黑爾以荷馬《伊利亞特》第十六章的四種英譯為分析個案,重點探討了敘事序列與詩歌文本的相互關(guān)系,以及敘事性與段位性之間相互強化、相互對位、相互抵消的方式。不可否認,麥克黑爾關(guān)于從詩歌的形式尤其是從“段位性”和“反分段性”角度來建構(gòu)詩歌學(xué)的設(shè)想以及他為此所付諸的批評實踐,頗有新意,為詩歌敘事學(xué)的建構(gòu)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換一個視角來看,麥克黑爾的長處也暗示了其研究的短處,因為他僅僅依賴詩歌形式的兩個方面來試圖建構(gòu)詩歌敘事學(xué)的宏偉大廈,這種想法未免過于理想化和簡單化。正如《敘事》雜志主編詹姆斯•費倫所指出的那樣,麥克黑爾的文章大致存有兩點不足:(1)把段位性作為詩歌的區(qū)別性特征是不盡人意的,因為段位性不涉及詩歌的內(nèi)容和目的;(2)詩歌的段位性和敘事段位性的類比似乎有失偏頗,因為詩歌的段位性主要是通過聲音和排版的形式為標(biāo)志,而敘事的段位性則不盡如此。 ?同后經(jīng)典敘事學(xué)的其他分支如女性主義敘事學(xué)、修辭敘事學(xué)、認知敘事學(xué)、非自然敘事學(xué)等相比較,詩歌敘事學(xué)起步較晚,目前依然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為了建立較為完備的詩歌敘事學(xué)體系,加速詩歌敘事學(xué)的發(fā)展進程,筆者嘗試性提出如下五個建構(gòu)路徑或研究方向: 第一,詩歌敘事特有的“話語屬性”。按照敘事學(xué)的慣常說法,敘事分為“故事”和“話語”兩個層面。前者涉及敘事所要表達的內(nèi)容,后者涉及表達敘事的手段或形式。盡管詩歌和其他文本類型都屬于“敘事”這個大的范疇,共享一定的“敘事性”即“敘事之所以成為敘事”的基本特征,但是詩歌除了具有一般敘事作品所共有的敘述形式(如聚焦和聲音等)之外,也有自己獨特的“話語屬性”。考辨這些“話語屬性”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中的比例以及它們所產(chǎn)生的敘事效果,是研究詩歌敘事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在許恩看來,詩歌具有五種獨特屬性:(1)詩歌具有很多與小說敘事不同的情節(jié)形式或敘述形式。例如,詩歌不是從故事的終點講述故事而是從正在發(fā)生的故事內(nèi)部開始講述;詩歌以預(yù)敘述的方式講述故事,并且通過講述事件的故事來塑造事件的序列;(2)詩歌中的人物不是通過他們的名字和通過對他們的描述被辨別出來,而是通過人物的視角、內(nèi)心以及他們個人的敘事被辨別出來;(3)詩歌中的敘述行為更多地使用“非常規(guī)的”時態(tài)和語態(tài),如第二人稱敘述、祈使語氣、否定式敘述等;(4)詩歌中的敘事序列經(jīng)常缺少明確的對其所處情景的解釋;(5)詩歌文本的物質(zhì)性和形式結(jié)構(gòu)也可以被用來作為敘事序列的附加模式,進而強化、修正或反作用于情節(jié)的發(fā)展。#p#分頁標(biāo)題#e# ?可見,許恩主要是從敘述策略或敘事學(xué)術(shù)語的角度,辨析了詩歌不同于其他敘事文類的特征,即詩歌在情節(jié)、人物、聲音等敘述策略上同小說敘事之間的區(qū)別。許恩的上述總結(jié)不乏洞見,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涉及詩歌自身的文體樣式和構(gòu)成要素;麥克黑爾雖然討論了詩歌形式的“段位性”和“反分段性”,但也略顯不夠全面。筆者認為,作為一種文學(xué)體裁,無論是古體詩還是現(xiàn)代詩,無論外國詩歌還是中國詩歌,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形式。例如,就英語詩歌而言,聶珍釗認為,“英語詩歌的形式主要通過重音、韻律、節(jié)奏、押韻等表現(xiàn)出來。”瑐?瑦實際上,詩歌除了韻律上的特殊形式之外,還存有標(biāo)點符號、意象、詩行、排版等不同形式。考察這些形式對于表達或傳遞詩歌的內(nèi)容(故事、情感、思想等)等的作用與效果,無疑是詩歌敘事學(xué)研究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 第二,詩歌敘事研究的多元方法。敘事學(xué)在后經(jīng)典階段,引入了各種新方法,如女性主義批評方法、認知方法、修辭方法等。作為文學(xué)敘事的一個亞類型,這些新方法對于詩歌敘事應(yīng)該可以同樣適用。事實也是如此。例如,就抒情詩敘事而言,帕特里克•科姆•霍根使用了認知方法來研究抒情詩的情感;費倫從修辭方法的角度研究了抒情詩的目的和手段。瑐瑨?隨著敘事學(xué)的不斷進展,詩歌敘事研究呼喚更多的新方法,也勢必會產(chǎn)出更為豐厚的研究成果。 第三,現(xiàn)有的敘事學(xué)理論與詩歌理論之間的相互借鑒與交流。當(dāng)下,無論是詩歌理論還是現(xiàn)有的敘事理論都非常發(fā)達,這是不爭的事實。敘事學(xué)研究與詩歌研究之間互不往來,部分地導(dǎo)致了詩歌敘事學(xué)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正如莫妮卡•摩根所言:雖然詩歌理論與敘事學(xué)理論“很少接觸,但是它們可以相互強化、相互補充,也可以相互批判”。?如何充分吸收詩歌理論的優(yōu)秀成果,為建構(gòu)詩歌敘事學(xué)所用,這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第四,不同文類的詩歌敘事學(xué)研究。毋庸置疑,詩歌本身也是一個范疇很廣的文類。如前所述,詩歌敘事學(xué)的出現(xiàn),主要原因在于后經(jīng)典語境下文學(xué)敘事研究的“跨文類”傾向。要使得詩歌敘事學(xué)能得到更為深入、更為全面的發(fā)展,詩歌敘事學(xué)也需要走“跨文類”研究的路徑。換言之,可以在詩歌敘事學(xué)研究的總體框架下對具體詩歌類型的敘事展開研究,如抒情詩敘事研究、史詩敘事研究、戲劇詩敘事研究等。 第五、詩歌敘事學(xué)的理論建構(gòu)與批評實踐并舉。在建構(gòu)與發(fā)展詩歌敘事學(xué)這門學(xué)科時,需要把敘事理論建構(gòu)與敘事批評實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廢任何一方。一方面,詩歌的敘事學(xué)分析既需要借用詩歌敘事理論框架,同時也能夠修正詩歌敘事理論,使之更為完善。另一方面,詩歌敘事理論不僅需要經(jīng)過詩歌敘事批評實踐的驗證,同時也能不斷地給詩歌敘事批評實踐提供框架支撐和新的研究視角。為了驗證上述五種路徑之于建構(gòu)詩歌敘事學(xué)的可行性和效度,筆者在論述抒情詩敘事性的基礎(chǔ)上,以中世紀的一首匿名抒情詩《西風(fēng)》(WestWind)為例,從認知方法的角度分析該詩的敘事性和敘述話語。 詩歌敘事學(xué)的批評實踐舉隅:《西風(fēng)》的敘事性與世界建構(gòu) 在文學(xué)史上,抒情詩長期被放置于敘事的對立面。例如,受到歌德的影響,傳統(tǒng)的德國文學(xué)批評把文學(xué)作品劃分出三大類型:“史詩”(epic)、“抒情詩”(lyrics)和“戲劇”(drama),而在這三者之中,只有史詩被看作是敘事的原型,因為史詩包含一個吟游詩人,即講述故事的敘述者。根據(jù)這一論點,即便存有一定故事的文學(xué)類型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敘事。戲劇便是如此,因為盡管戲劇講述了一個故事,但是戲劇中沒有敘述者的存在。有鑒于此,德國敘事學(xué)家莫妮卡•弗魯?shù)履峥苏f:敘事就是“故事+敘述者”。? 顧名思義,抒情詩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抒發(fā)情感。朱光潛認為,“人生來就有情感,情感天然需要表現(xiàn),而表象情感最適當(dāng)?shù)姆绞绞窃姼瑁驗檎Z言節(jié)奏與內(nèi)在的節(jié)奏相契合,是自然的,‘不能已’的。”根據(jù)《文學(xué)術(shù)語匯編》的解釋,所謂的抒情詩指的是“任何短詩,由單個的說話者所說的話語所構(gòu)成,表達說話者的心理狀態(tài),或感知、思維和情感的過程。”?那么抒情詩究竟是否存有敘事性,或抒情詩是否是敘事的一種類型呢?麥克黑爾認為,“長期以來,抒情詩的敘事性是有問題的和爭議性的。”與麥克黑爾的質(zhì)疑態(tài)度相反,德國學(xué)者許恩和舍納特對抒情詩的敘事性持有肯定態(tài)度:在術(shù)語的嚴格意義上,抒情文本(即,不是明顯的敘事詩歌如民謠、羅曼司以及詩歌故事)同散文敘事如小說等具有三個相同的敘事學(xué)基本層面(序列性、媒介性以及表達)。它們涉及事件的時間序列(通常是大腦的或心理的,但也可以是外在的,如社會本質(zhì))。通過從一個具體的視角來講述這些事件,它們創(chuàng)造出連貫性和相關(guān)性。最后,它們需要一種表達行為,憑借這種行為,媒介在具體的語言文本中發(fā)現(xiàn)自己的形式。 ?可見,許恩等人還是在參照敘事性標(biāo)準的基礎(chǔ)上,把抒情詩判定為敘事的一種類型,即抒情詩既有一定的序列,又有講述事件的視角,而且還依賴于某種特定的媒介方式表達出來。筆者認為,從敘述交際的角度來,抒情詩也無疑具有敘事性。譬如,按照費倫的話來說,敘事如果是某人為了某個目的在某個場合下向某人講述某事,那么抒情詩則是某人在某個場合為了某個目的向某人講述某事是什么。敘事中所包含的三個重要因子如“人物”、“事件”、“變化”在抒情詩中也以不同的面貌得到呈現(xiàn),如“人物”變成了“說話者”,“事件”則變成了“思想”、“態(tài)度”、“信仰”和“情感”等,而狀態(tài)的變化也是可有可無的。瑑瑥?在英語文學(xué)界有如下一首名為《西風(fēng)》的抒情詩。該詩創(chuàng)作于中世紀,流傳甚廣,但作者不詳:WestWindOWestwind,whenwiltthoublowThesmallraindowncanrain?Christ,thatmylovewereinmyarms,AndIinmybedagain!這首短詩是典型的抒情詩,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個詩行,卻不乏敘事性的特征。無論是按照許恩等人關(guān)于敘事性的標(biāo)準還是按照費倫的說法,該詩都具有一定的敘事性。倘若參照許恩等人的論點,該詩存在一定的序列(西風(fēng)吹起———小雨降落———擁情人入懷———自己躺在床上);具有一定的視角(說話者的視角),也具有一定的媒介(通過文字表達出來)。假如按照費倫的說法,該詩再現(xiàn)了說話者在自己孤單的場合下講述自己的內(nèi)心渴望,詩歌中的人物就是敘述者(或說話者),所要講述的事件就是詩人自己內(nèi)心的渴望和情感,狀態(tài)的改變也是說話者所苦苦祈求的(雖然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種狀態(tài)并沒有發(fā)生)。就“話語”層面而言,《西風(fēng)》除了存有小說敘事中常用的敘述手段如“敘述聲音”(說話者“我”的聲音)、“聚焦”(“我”的視角)、“人物刻畫”(孤單的懷念情人的“我”)之外,還有詩歌特有的話語表達手段。#p#分頁標(biāo)題#e# 在韻律上,該詩的第2行與第4行押尾韻,如“rain”,“again”;詩歌的第1行押頭韻和押尾韻,如“west”,“wind”,“when”,“wilt”,“thou”,“blow”。在單詞選擇上,該詩利用了詞匯重復(fù)的手段,如“rain”(兩次),“my”(三次)等。在音節(jié)上,該詩傾向于使用開口元音節(jié)[ou]和[ai],如“O”,“thou”,“blow”,“I”,“my”等,這些元音節(jié)大大地增強了感情的抒發(fā)力和表達力。此外,詩歌還通過運用意象“西風(fēng)”和“小雨”,塑造出傷感和悲涼的氛圍。總之,通過使用這些特殊的話語手段,《西風(fēng)》有效地講述了其要表達的“故事”內(nèi)容:“我”的強烈情感。弗魯?shù)履峥苏f,“敘事是通過語言和(或)視覺媒介對一個可能世界的再現(xiàn),其核心是一個或幾個具有人類本質(zhì)的人物,這些人物處于一定的時空,實施帶有一定目的的行動(行動或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瑑瑦?就認知方法而言,再現(xiàn)世界或者建構(gòu)世界既是構(gòu)成敘事的一個基本要件也是敘事的一個重要功能。赫爾曼認為,“建構(gòu)世界”是敘事的四個基本要件之一。瑑瑧?“建構(gòu)世界”的核心理念是“故事世界”。所謂的故事世界是“由敘事或明或暗地激起的世界”或是“被重新講述的事件和情景的心理模型,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時間、地點,出于什么原因,同什么人或?qū)κ裁慈俗隽耸裁词?rdquo;。瑑瑨?也即是說,在這個世界中有一定的人物、事件、因果關(guān)系、時間與空間。埃娃•穆勒-澤泰曼(EvaMüller-Zetelmann)指出:詩歌研究的敘事學(xué)方法“凸顯了詩歌建構(gòu)世界的潛勢”。 不難發(fā)現(xiàn),《西風(fēng)》也同樣存在某種可以激活讀者認知機制的“腳本”和“藍圖”。在閱讀詩歌的過程中,讀者依據(jù)自己對真實世界的知識掌控情況,在大腦中建構(gòu)起一個“故事世界”,從而實現(xiàn)對詩歌的“自然化”與“敘事化”。這個世界的存在物主要由說話者“我”及其“情人”構(gòu)成。該詩又從“我”的視角出發(fā),再現(xiàn)了發(fā)生在該“敘事世界”中的一序列事件:主要人物兼說話者“我”呼吁西風(fēng)的吹起;“我”企盼雨水的降落;“我”渴望情人和自己的團聚;“我”渴望再次躺在床上。讀者還可以根據(jù)先前存在的世界知識,自發(fā)地在這些事件之間建構(gòu)一定的因果關(guān)系。主要人物“我”呼吁象征力量的西方再度吹起,希望西風(fēng)能導(dǎo)致降雨,而西風(fēng)和降雨這兩個事件又增加了“我”的哀愁和對情人的思念,渴望和離別的情人再度相聚,擁情人入懷。讀者由此建構(gòu)了一個完整的敘事鏈條和一個可能的“故事世界”。上述簡短分析表明,《西風(fēng)》既是抒情的也是敘事的。該詩在話語層面上除具有小說敘事的常用手法如敘述聲音、聚焦、人物刻畫等之外,還有其特定的話語特征,如韻律、節(jié)拍、詩行、意象等。這些特定的話語特征無疑是對小說敘事之外的文學(xué)敘事研究的補充和拓展,為跨文類的敘事學(xué)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進路。 結(jié)語 在《心靈與心靈的故事:敘事普遍性和人類情感》一書中,霍根說:“敘事文學(xué)是廣袤的,沒有理由要期待把對敘事的明晰解釋擴展到另一個文學(xué)領(lǐng)域。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擴展會增加最初的解釋力,也會以諸多有價值的方式推進敘事文學(xué)的研究課題。”瑒瑠?當(dāng)下敘事學(xué)研究不斷涌現(xiàn)出“超越文學(xué)敘事”的論調(diào)。相比之下,在文學(xué)敘事內(nèi)部“超越小說敘事”的呼聲反倒被湮沒了,這無疑是文學(xué)敘事研究的一大缺失,容易產(chǎn)生“文學(xué)敘事研究=小說敘事研究”的誤解。這種誤解必須盡快得到澄清,文學(xué)敘事僅限于小說敘事研究的現(xiàn)狀也必須得到改變。筆者認為,詩歌敘事學(xué)無論對于詩歌研究還是敘事學(xué)研究,都開辟了新的研究視角,打開了新的進路。當(dāng)下,詩歌敘事學(xué)依然是處在初創(chuàng)階段,筆者歡迎學(xué)界同仁共同探討這一話題,引起共鳴或者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