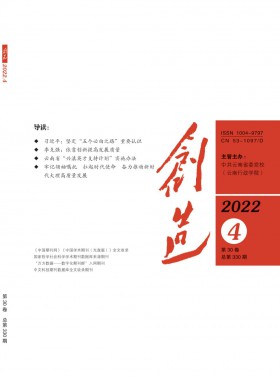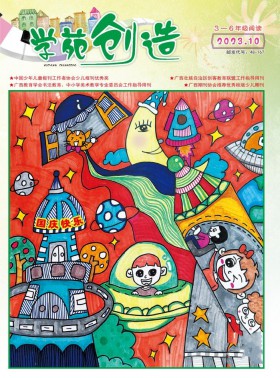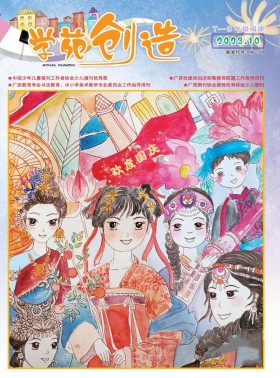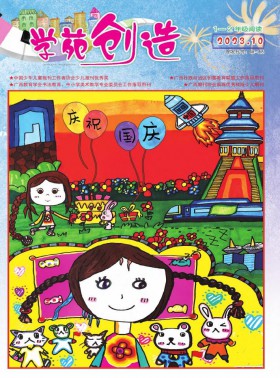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創造社革命文學觀,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討論創造社倡導的“革命文學”,不應以創造社的“前”、“后”分期,而應以“元老”和“新銳”劃界。其理由主要有二:一、創造社“元老”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在創造社“前期”就已經發表涉及“革命文學”問題的文章。比如郭沫若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郁達夫的《文學上的階級斗爭》都發表于1923年5月,都被文學史家看作是“革命文學”的先聲。李何林認為郭沫若的這篇文章“簡直是‘革命文學’的呼聲了”[1]110。劉綬松把這兩篇文章都判定為“已經是后來‘革命文學’運動倡導的前奏了”[2]131。二、雖然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在“五卅”以后有比較大的變化,但總體看來仍保持著前后的一致性,且后來的變化也與創造社“新銳”們的觀點明顯不同。按郭沫若在《文學革命之回顧》[3]84中的說法,創造社“元老”們在“五卅工潮”前后的劇變,“也是自然發生性的,并沒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識”。在他看來,“這個目的意識是規定一個人能否成為無產階級真正的戰士之決定的標準”。持有這種“清晰的目的意識”的,正是創造社“新銳”李初梨、馮乃超、彭康等人。 創造社“元老”們在創造社前期主要以張揚浪漫主義文學聞名,并沒有過像文學研究會、早期共產黨人那樣,在較為固定的報刊上展開相對集中的關于“文學與革命”問題的討論,其“革命文學”的觀點都零星地發表于刊物之上,一般文學史著作往往只把它們作為創造社“后期”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萌芽,并認定其中“包含了許多不正確的觀念”[2]131;對于“五卅”以后“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言論,一般文學史著作多從同一團體的角度強調其與創造社“新銳”們的一致性,卻忽略了他們之間的重大差別,從而使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的真實面目長期處于遮蔽狀態。 筆者認為,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是與文學研究會、早期共產黨人的“革命文學”觀并列的重要文學觀念,可以也應該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進行考察。那么,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到底有哪些特點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簡單地了解一下創造社的“變”與“不變”。 創造社以善變聞名。最明顯的或者說是“翻著筋斗”的變,是從崇尚“天才”、注重“靈感”、標榜藝術的“無目的”、追求文學的“全”與“美”,到遵從“時代”、主張“寫實”、強調藝術的“功利性”、贊美文學的“同情于無產階級”的轉變。這種“善變”有兩種情況:一是因掌握話語權的成員的變化而顯現出“團體性”的變,二是它的一些重要成員因主客觀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的文學觀點的變。 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元老”們的“革命文學”理論,在創造社的前、后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不僅表現在其前期只是零散的萌芽,而直到后期才有比較系統的論述,更表現在一些重要理論觀念的改變。 1925年底郭沫若在《〈文藝論集〉序》[4]146里就曾開誠布公地說過,他的思想、生活和作風“在最近一兩年間,可以說是完全變了”。這話說得有些過頭,但變化是確實存在的。比如,郭沫若在《我們的文學新運動》[3]3中是把“無產階級的精神”與“精赤裸裸的人性”并列的,他既要“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也要“反抗不以個性為根底的既成道德”;而他在三年后發表的《革命與文學》[3]32中,則明確表示“對于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要根本鏟除”。郁達夫在《文學上的階級斗爭》[5]46中“大聲疾呼”的,是基于“反抗”意義上的“斗爭”而不是“階級”;而在三年多以后發表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5]287中,他則“斷定”:“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學,必須由無產階級者自己來創造。”成仿吾在《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6]205一文中還強調“如果要是永遠的革命文學,它的作者還須徹底透入而追蹤到永遠的真摯的人性”;但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6]241一文中,他就呼吁“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但是,這就是創造社嗎?筆者以為不能這么說。 善變只是創造社的一個方面,甚至極端一點地說,還只是創造社理論觀念層面的一種表現。創造社其實還有許多不變或只是變形而沒有變質的東西。這在個性鮮明成就非凡的“元老”們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關于創造社的理論觀念與意識本質相分裂的狀況,王富仁、楊占升在《馮雪峰與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一文中曾有一段分析:“在他們那里,先進理論只是一種‘知識’、一種‘主張’,只要有了這種‘知識’和‘主張’,他們便以為完成了自己的‘奧伏赫變’,因而先進理論對于他們只是一種身外物、異化物,而自己的意識本質、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還是舊的一套。”[7]12雖然王富仁、楊占升所指稱的主要是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中的創造社與太陽社,但把這段話移用到創造社“元老”們身上,也是非常適用的。從某種意義上看,“元老”們倡導“革命文學”的文章中,或隱或顯地存在著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變”的因素,或許更能體現其“革命文學”的真實內涵。#p#分頁標題#e# 二這些“真實內涵”,概括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始終強調文學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他們的“革命文學”論文本身就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這表明在他們的潛意識中非常注重文學形式的感染力。郭沫若文藝論文的這種特點特別突出。他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自然與藝術》、《桌子的跳舞》等一系列論文,都不講究嚴密的論證邏輯,而是洋溢著一種澎湃的詩情。不少學者曾尖銳地指出過郭沫若談論文藝的文章,存在概念含混和誤用甚至自相矛盾的說法,其實,這正體現出郭沫若那種容易沖動、多變的詩人特性。郁達夫的文藝論文同樣富有文學感染力。他的《文學上的階級斗爭》從“風光明媚,空氣澄清的奧靈泊斯(Olympus)山”說起,又以詩性語言結束。文中不斷出現的充溢著作者個人感情色彩的形容詞、帶有鮮明的音樂節奏感的句子、以及流貫在整篇文章中的那種無法抑制的激情,都能給人一種巨大的情感沖擊力。相比而言,成仿吾的文藝論文顯得樸實些,邏輯思維嚴密些,但其在語意回環中突出重心的技巧,如《新文學之使命》,在嬉笑怒罵中點破疑團的功夫,如《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以及對后浪推前浪式的表達思想的氣勢的強調,如《祝詞》,也都頗具文學特色。 另一方面,他們的“革命文學”觀念也始終注重文學。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中再三強調:“真正的文學永遠是革命的前驅。”兩年多以后,在特別強調文學的時代性和階級性的時候,他在《英雄樹》[3]44中仍然說:“文藝是應該領導著時代走的。”在《桌子的跳舞》[3]51中又重申:“文藝是階級的勇猛斗士之一員,而且是先鋒。”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6]89中說:“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士。在我們這種良心病了的社會,文學家尤其是任重而道遠。”五年后他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6]248中還是說:“文藝決不能與社會的關系分離,也決不應止于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應該積極地成為變革社會的手段。”郁達夫的“革命文學”觀念與郭沫若等人有著很大的分歧,但在強調“革命文學”運動中文學的重要作用方面,他們還是一致的。郁達夫在《文學上的階級斗爭》中認為:“法國的大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德國的反拿破侖同盟,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都是些青年的文學家演出來的活劇。”后來在《創造月刊•卷頭語》[5]183中仍然表示:“我們的志不在大,消極的就想以我們無力的同情,來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慘敗的人生的戰士,積極的就想以我們的微弱的呼聲,來促進改革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會的組成。”創造社“元老”們注重文學,源自他們對“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等基本概念的理解。雖然他們的理解同中有異,但導向的都是對文學的看重。 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是“進化論”意義上的“革命”,他只是在社會進化的寬泛意義中加進了“階級斗爭”的“進化”模式。他說:“革命本來不是固定的東西,每個時代的革命各有每個時代的精神,不過革命的形式總是固定了的。每個時代的革命一定是每個時代的被壓迫階級對于壓迫階級的徹底的反抗。”郭沫若理解的文學,是基于人的“氣質”和“感情”意義上的文學。他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始于感情終于感情的”,“神經質的人感受性很銳敏,而他的情緒的動搖是很強烈而且能持久的。這樣的人多半傾向于文藝”,所以,“文學家并不是能夠轉移社會的天生的異材,文學家只是神經過敏的一種特殊的人物罷了。”郭沫若所理解的“革命文學”具有動態的特征。 他認為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每個時代都是不斷地革命著前進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時代精神一變,革命文學的內容便因之而一變”。“所以革命文學的這個名詞雖然固定,而革命文學的內涵是永不固定的”。既然把革命看成是一種進化,把文學看作是神經敏銳的人所進行的一種感情活動,文學家能夠最早感受到階級的壓迫,能夠最早喊出反抗的呼聲,那么,文學就不但是“和革命是一致的”,而且還是“能為革命的前驅”[3]37-39。他注重文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郁達夫對革命的理解也是基于社會進化的角度,不同的是,郁達夫的階級意識并不夠強。他特別強調,謀取“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是革命的一個階段,“革命的最后的目的,是在謀絕對全體的絕對幸福,不能說少數人就可以犧牲不顧的”[5]287。這種人類意識,使得郁達夫對于一些人可能“利用民眾”來壓迫人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郁達夫對文學的理解是眾所周知的自敘傳思想。這與郭沫若基于“氣質”和“感情”的文學觀也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郁達夫更強調直接經驗在文學創作中的意義,主張“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他堅信:“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5]341他把文學的作用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類。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所謂“消極的”文學的看法。他在《文學上的階級斗爭》一文中認為,“表面上似與人生直接最沒有關系的新舊浪漫派的藝術家,實際上對人世社會的疾憤,反而最深。不過他們的戰斗力不足,不能戰勝這萬惡貫盈的社會”,“只好逃到藝術的共和國里……以表明他們對當時的社會懷抱著的悲憤”。郁達夫對文學的看重由此可見一斑。 成仿吾的觀點也很有特色。他在《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一文中把革命理解為“一種有意識的躍進”。他認為,人類的進化存在“被移動著”和“有意識的能動的躍進”兩種。至于文學,成仿吾也是把它看作與革命相一致的,他說:“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多少總可以說是革命的。”但不同的是,成仿吾基于人性的立場更具體地論證了“一般文學”和“革命文學”的不同。他認為“一般文學”如果同時具備了“真摯的人性”和“審美的形式”,也就具有了它的“永遠性”。而“因為革命文學究不過在一般文學之外多有一種特別有感動力的熱情”,所以,永遠的革命文學=真摯的人性+審美的形式+熱情。尤其是,成仿吾理解的“革命文學”更多地具有歷史的延續性,而不特別強調其“時代效力”。他說:“一個作品自成一個世界,它是不受時代效力的影響的。”在他看來,拜倫的《哀希臘》“在希臘已經獨立自由了的現今”,我們今天仍然能“感到他原來的熱力”。#p#分頁標題#e# 創造社“元老”們是以強調文學藝術要忠實地表現自己“內心的要求”而走上文壇的。文學藝術既是他們安身立命的處所,也是他們開展社會活動的重要媒介。深厚的文學修養、過人的藝術才華、以及對文學藝術事業的深深熱愛,使得他們無論接受什么新奇的理論,都無法割斷與文學絲絲相連的血脈姻緣。他們在倡導“革命文學”時不忘文學的重要作用,完全合乎他們的“個性意識”,也可以說,這正是他們借以表明“自我存在”的一種方式。 (二)始終強調“叛逆與反抗”的精神 創造社“元老”們的“階級對立”意識有一個從獲得到逐漸清晰和成形的過程,而“叛逆與反抗”的精神,則貫穿了他們文學活動的始終。 郭沫若《我們的文學新運動》的核心思想就是“叛逆與反抗”。他之所以要掀起“黃河揚子江一樣”的“文學新運動”,根本原因就在于“黃河揚子江”能夠做到“有崖石的抵抗則破壞,有不合理的堤防則破壞,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和平海洋滔滔前進!”由此,郭沫若進而得出結論:“我們的事業,在目下渾沌之中,要先從破壞做起。我們的精神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郭沫若的這種“叛逆與反抗”的精神,在他的思想發生“劇變”之后同樣存在。他在《革命與文學》一文中,把革命理解為“被壓迫階級對于壓迫階級的徹底的反抗”,把文學的進化看作是線性的一種思潮取代一種思潮的“反抗斗爭”。在《英雄樹》一文中,郭沫若更是直言“文藝界中應該產生出些暴徒出來才行”,應該“一齒還十齒,一目還十目!”郁達夫與郭沫若有些不太一樣,但他的文學思想也有著鮮明的“叛逆與反抗”精神。當然,在郁達夫看來,所謂“灰色和感傷的情調”也是一種反抗,是“藝術家對現實社會絕了望”[5]46以后的反抗。他的《文學上的階級斗爭》一文,把古往今來的藝術創作,歸結為藝術家的“滿腔郁憤,無處發泄;只好把對現實懷著的不滿的心思,和對社會感得的熱烈的反抗,都描寫在紙上”。直至1926年,在《創造月刊•卷頭語》中,郁達夫還是言詞懇切地希望《創造月刊》“能堅持到底”,“為天下的無能力者被壓迫者吐一口氣”。 成仿吾更加特別。郭沫若、郁達夫畢竟都屬于“神經質”一類的創作家,他們的文章雖充滿了濃烈的叛逆情緒,卻具有情感的親和力。成仿吾的理性制約情感的能力相對較強,他的文章原本就顯得比較生硬,再加上經常出現真理在握的教訓式口吻,因而往往具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粗暴”的特點。他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甚至使用“十萬兩煙火藥”那樣的文字,來表達他對“北京的烏煙瘴氣”的不滿。他此后不久發表的《打發他們去!》[8]152一文,又把軍事名詞“工事”應用于文藝斗爭中,主張必要時需用“武力”“把一切封建思想,布爾喬亞的根性與它們的代言者”“踢他們出去”。其實,就成仿吾整個的“反抗斗爭”思想而言,他是很注重理論的“分析與批判”的。他在《新文學之使命》一文中主張:“現代的生活,它的樣式,它的內容,我們要取嚴肅的態度,加以精密的觀察與公正的批評”。四年多以后,他在《〈洪水〉終刊感言》[9]501中還誠懇地反思自己“只是反抗,也教人反抗”,卻“不曾有觀察與推考的余暇”,“忘記了這種種舊的惡勢力的批判”,他為此感到遺憾。他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更是全面地分析了“批判”的涵義及目標。他把批判理解為“文藝理論方面的努力”。所謂的“全部的批判”,并不是一般所指的“橫掃一切”,而是指“意識形態”以及它的各種形成要素(包括他所理解的“純經濟過程”、“生活過程”、“意識過程”等)的“全面的批判”和“表現方法的批判”。他認為經過批判,既“把舊的意識形態奧伏赫變”,也“把舊的表現樣式奧伏赫變”,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轉換方向”。 (三)或隱或顯地張揚自己的個性意識 從顯在的觀念層面看,創造社“元老”們的個性意識隨著他們接受并倡導“革命文學”而呈現出逐漸消減的趨勢;但從他們說話寫文章的字里行間所表現出來的感情傾向和氣質特點來看,骨子里仍然保有濃厚的個性意識。王富仁、楊占升說的創造社理論觀念與意識本質相分離的情況,在個性意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郭沫若前后“劇變”的具體表現非常典型。他公開對自己的個性意識展開批判性分析是在1925年底。那時他在《〈文藝論集〉序》里說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話:“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間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未免出于僭妄。”所以他主張:“在大眾未得發展個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倒應該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為大眾人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先不論他的這種邏輯是否合適,僅就他對個性意識的態度而言,也是既有批判,也有肯定的。他所批判的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實現的“自我的個性與自由”,仍然肯定“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一般意義上的“個性與自由”。而且,他的那種“拯救大眾”的豪情,犧牲自我的悲壯,也正是其個性意識的一種無言的展示。 郭沫若的這種思想在他1926年發表的《文藝家的覺悟》、《革命與文學》等文章中,還在不斷地重復著。直至1928年發表《英雄樹》一文,號召文藝青年們“當一個留聲機器”,要做到“無我”,才可以說他對個性意識真正進行了“清算”。但是,郭沫若的這種“清算”仍然主要是觀念層面的。不必說他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對無產階級的想象,仍然帶有濃厚的個性意識,他把無產階級想象為“他們是日日站在生死關頭與死神搏斗;他們的生產力、爆發力,是以全生命、全靈魂為保障的”,僅就他在《英雄樹》中鼓吹的“睚眥必報”的精神和“有筆的時候提筆,有槍的時候提槍”的率性生活,在《桌子的跳舞》中強調的“作家也要費無限的心血然后才能”“把捉著時代精神”的艱難過程,和“不怕他昨天還是資產階級,如果他今天受了無產者精神的洗禮,那他所做的作品也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文藝”的自信而言,都散發出了濃濃的個性意識。#p#分頁標題#e# 郁達夫的情況與郭沫若有些相似。他在《文學上的階級斗爭》中大談文學“對現世社會的厭棄與反抗”,但并不否定個性。一方面,他明確指出“目下的政府法律和道德”都是“箝制個性發展的”,應該成為“攻擊最烈的目標”,自然主義文學“沒有進取的態度,不能令人痛快的發揚個性”,應該成為反抗的對象;另一方面,他對“有權有產階級”激烈的反抗態度,以及“即使失敗了,死了”也“非要一直的走往前去不可”的決心和意志,也鮮明地表達出了他的個性意識。直至1926年,郁達夫的這種矛盾依然存在。 他在《創造月刊•卷頭語》中還是一方面哀嘆“社會的混亂錯雜!人世的不平!”一方面又堅持宣稱:“我們所持的,是忠實的真率的態度!”與郭沫若不同的是,郁達夫沒有那么自信,沒有像郭沫若那樣發生天馬行空式的劇變。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中認為,人的感情和個性不是在短時間內通過學習和改造可以根本改變的,始終堅持文學創作要忠于自己的感情和個性,堅持“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學,必須由無產階級者自己來創造”。他批評那些“抄襲外國的思想,大喊無產階級的文學”的人“是不忠于己的行為”。他把文學的階級意識、社會責任與作家的個性意識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如果兩者不能夠做到統一的話,則把前者作為一種目標和理想來推崇,而在具體創作中則依然強調的自己的個性。 個性意識與使命意識的矛盾,在成仿吾身上也是長久地存在著。他發表《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時,一方面極其堅定地認為“文學的內容必然地是人性”,一方面又熱情地鼓吹“文學的感化的功勞實在不小”;一方面強調“維持自我意識”與“個人感情”,一方面又主張“維持團體意識”和“團體感情”。既然文學的根柢在人性,人性又是可以有意識地加以改造的,那么,把文學應用于革命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因為人性具有永遠性,那么“革命文學”也具有永遠性。在1927年發表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文藝戰的認識》、《文學革命與趣味》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依然堅持這種矛盾著的思想。只有在1928年發表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中,他強調“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要“努力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要“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要走向“農工大眾”,才可說他不再從理論上論說文學的人性,不再強調作品的個性精神,而專注于文學的社會使命了。這種思想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中更明確地表述為:“我們的文藝現在已經到了應該實行方向轉換的階段”。轉換的內容,一是“由自然生長的成為目的意識的”,二是“由文藝的武器成為武器的文藝”。 但成仿吾的這種變化,更多地也還是在觀念層面進行。不必說他文章中那種真理在握、唯我獨尊的氣勢,即就他文章中時時流露出來的一些與他的早期個性思想極為相似的詞句,也可以感受到其中所隱伏著的個性意識。比如,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他告誡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要“自覺地參加這社會變革”,“莫只追隨,更不要再落在后面”,要“以明了的意識努力你的工作”,“以真摯的熱誠描寫”;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他反復強調“有意識”:“我們有意識地革命”,“有意識地促進文藝的進展”。諸如此類的詞句,在他前期主張自我表現的文章中是屢見不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