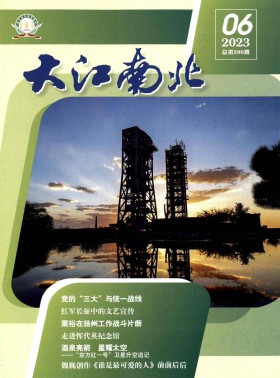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江南文學和嶺南文學的聯系及區別,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嶺南自古偏居一隅,文化相對落后。但從明初開始,以孫蕡為代表的“南園五先生”(另四人為王佐、趙介、黃哲、李德,又稱“南園五子”)在廣州南園結社唱和,開創嶺南詩派,一躍而成為當時國中五大地域流派之一①[1],對嶺南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建立起了嶺南文學發展的自信。歐大任在《潘光祿集序》里甚至說“嶺南五子”“軼視吳中四杰遠甚”。其次是確立了嶺南文學的傳統①[2]。 嶺南后世稍有影響的文學團體,多集于南園,如明中葉歐大任等5人重修南園詩社,明末陳子壯、黎遂球等12人復集南園詩社,清末梁鼎芬、黃節等8人重開南園后社,上述諸家皆為一代翹楚;且每以“南園后五先生”(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梁有譽還是明代復古派的“后七子”之一)、“南園十二子”(陳子壯等12人)、“南園今五子”(李洸、熊潤桐、曾希穎、余心一、佟紹弼)等相稱,以示文脈相承。嶺南文學,自此漸由附庸蔚為大國,如康熙時主盟詩壇的王士禎說:“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3]當代文史大家謝國禎也說:“廣東地方雖然僻遠,但文化極為昌明。在崇禎間,陳子壯、黎遂球、陳邦彥、歐必元等人,以文章聲氣與江南復社相應和。”[4]探溯這一光輝的文學傳統,我們發現與宋濂甚有淵源,并可以由此進一步探討嶺南文學與江南文學的淵源。 一、何真及部將高彬與宋濂 先從四庫全書《廣東通志》卷六十《藝文》中的一篇宋濂的佚文《何氏義田遺訓記》②[5]1639說起。 文說:何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初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榮之盛,由于先世,既于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捐入以祭其禰祖。公猶未愜于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并有所私之田百余頃為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族人不能立也,有粟帛以賑給之,嫁娶葬祭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養之;懼其久而或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記于余。……何真是廣東人,從出生到成長及至后來割據一方,均在廣東。洪武元年(1368年),嶺南“和平解放”,何真率部歸順明朝。這無論于朱元璋擬或嶺南地區,都是一件具有豐碑意義的大事。揆諸當時的形勢,朱元璋雖然征服了長江流域的陳友諒、張士誠和方國珍,但元王朝實力尚存,如其軍師劉基所言:“王保保未可輕也。”整個西南邊陲當時也尚在元室手里,所以黃佐說:“方是時,操斛揚舲之夫,甫統烏合之眾,即稱帝稱王,蓋不特張、陳而已。使其為尉佗之業,夫誰能禁之?”[6]《明史•何真傳》也說:“時中原大亂,嶺表隔絕,有勸真效尉佗故事者。”這一點,朱元璋在何真歸順之后的褒贈之詞中也說:“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之屬,擁兵據險,角立群雄間,非真主不屈。 此漢、唐名臣,于今未見。爾真連數郡之眾,乃不煩一兵,保境來歸,雖竇、李奚讓焉。”(《明史•何真傳》,四庫全書本)這等于是間接地予以承認了。所以,朱元璋雖派廖永忠大兵壓境,但何真是以逸待勞,無論勝負如何,至少是雙方都會付出慘重代價。 這樣一來,朱元璋統一全國的時間將被大大延滯。 更令人不愿看到的是,整個江南與嶺南的老百姓,將為這場戰事付出沉重的代價,后果難以估量。 何真的可貴和不俗之處在于,他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赳赳武將。《明史•何真傳》說他“尤喜儒術,讀書綴文”。他稍有勢力時,即開府辟士,與文人儒士交往,明初嶺南詩派的五大家孫蕡、王佐、趙介、李德、黃哲皆受禮遇。而這些文人儒士,從文學發展以及儒家的民本立場出發,是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 何真審時度勢歸順朱元璋,就頗受這些士人的影響。 據《明史•孫蕡傳》,其歸順朱元璋的降表,“曲盡誠款”,即孫蕡所擬。前此明人黃佐在《廣州人物傳》中對此大加贊揚:“(廖)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帖然者,蕡之力也。”[7] 何真所帶來的和平,對于嶺南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南園五子的交往及嶺南詩派的形成與其有相當關系;其次,避免了戰亂,為廣東文學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如黃佐所言“元末大亂,豪杰云起,鋒鏑連海嶠,血肉渥草莽,獨我南海,賴何真保障,得以奠枕無虞,其功偉矣”;第三,客觀上促成了嶺南地區長期由地方豪強向士紳治理的歷史轉折,為嶺南文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8] 還要指出的是,何真歸順以后,并未居功自傲,而是“始終一心”。正如他在詩中所言:“鼎沸圖存僅十年,平生忠義在安邊。英雄不學萬人敵,方寸長懸五尺天。宣布曾分南國政,賢勞敢詠北山篇。真心獨有松堪比,臣節惟應老更堅。”[9]他的這種堅定的心志,與孫蕡等昔日同鄉幕僚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他任山東行省參政時,孫蕡就投詩勸勉:“皇風來播南陲日,開府兼持將相權。千里分封鸞誥下,三珠耀日虎符懸。長憐野日違清顧,且喜恩光照暮年。勛業已成頭半白,蔣陵佳氣麗中天。//君侯昔在東藩時,英風遠略人共知。帳前鐵騎金鎖甲,腰下寶玦珊瑚枝。將相兼權未足貴,身名兩存今始奇。便可臨風搔白首,對酒且賦歸來詞。”(《西庵集》卷五,四庫全書本)因此,朱元璋對他是放心的、滿意的,“未聞微譴加焉”,一直讓其擔任山東、山西、浙江、湖廣等處參知政事或布政使等鎮守方面的重要職務,致仕后還封其為東莞伯,并“予世券”。正如時人所說,在明初朱元璋雄猜好殺、大肆屠戮功臣的背景下,“其生榮死哀,誠非一時諸臣所可幾而及也”[6]。由于他的善終,使得與其過從甚密乃至依附其下的嶺南五子,未曾牽連受禍,這客觀上有助于嶺南文學的發展。#p#分頁標題#e# 應當說,正是何真的這種政治姿態及其現實的踐履,使作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樂于與其交往,并在其致仕之后,接受其請求,為作《何氏義田遺訓序》。但是,這篇序的意義還不止于此。事實上,何真捐作義祠的私第及供養義祠的義田,后來由其子辟為豐湖書室及書室的義田,后人再將豐湖書室發展成豐湖書院。這豐湖書院,乃在惠州城區最佳名勝西湖之上,曾為今日惠州學院所在之地。惠州文脈佳話,因之演為傳奇。在這傳奇歷程中,宋濂又再度影入其間。這一次,是通過其得意門生方孝孺,后敘。 何真親近宋濂,其部下之士如高彬也努力與宋濂交往,其中介應該是通過孫蕡。孫蕡與高彬同屬何真麾下,交往相當密切。據黃佐《廣州人物傳》(《嶺南遺書》本)卷十一《簡祖英傳》的附傳說: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 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為巨賈。征為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為詩,有奇語。孫蕡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 孫蕡《西庵集》中,有多首與高彬往還之作①,在其他詩文中也不止一處提到高彬。在其中一首《寄高彬》的七言律詩中,還有“與君夙有通家好,堂上嚴親未白頭”句,足見其與高彬關系非同一般。在孫蕡的影響下,高彬與宋濂交往,并請為其父撰寫了《南海高君墓銘》[5]1697。 二、何真父子與宋濂門生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師從明開國第一文臣宋濂,被譽為天下讀書種子,是宋濂最得意的門生。洪武間曾任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世子師;外放經歷,乃朱元璋對其刻意安排的歷練,以便輔佐未來的建文皇帝。朱元璋死后,建文皇帝繼位,方孝孺入朝任侍講學士,為建文皇帝設計了一套復古的治國方略。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攻入南京,方孝孺因拒絕為其起草詔書,被誅連十族,成為明代文化的重大損失。 方孝孺與何真父子的交往,俱見于其因何真之子何奉先之請所作的《豐湖書室序》: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于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舉南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賜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人莫敢犯,而所為皆本于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孝孺獲侍幾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因已知公之有后,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公命相與論辨往昔治亂之理……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為學之功,必有過人者。 已而奉先來言:“居惠嘗即惠州之濱為豐湖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為詩稱其善。詩已聯為巨卷,子為我序之。”某于是又知奉先之過人者在是也。生乎富貴而好禮,圣人以為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違圣人二千載。惠距圣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沉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郁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于家,善格于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十三,四庫全書本)方孝孺初識何真于山東。當時,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任山東濟寧知府,而何真適由江西調任山東行省參政,是方克勤的頂頭上司。方克勤是明朝著名的循吏,事跡載于《明史•循吏傳》。方孝孺與何真,輩份不同,地位也相去懸殊,但從序文看二人相得甚歡。方孝孺甚至“獲侍幾杖者數月”,愿為方氏幕僚或曰私人秘書。這一不淺的情誼,一直維持著:何真致仕京居,方孝孺父親遭冤殺,居喪期滿回京,即往拜訪,與其相論歷代治亂之道,情志十分契合。 與何真父子的交往,影響到方孝孺對嶺南文學的態度。他在另一篇為廣東人而作的文章《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十四,四庫全書本)中,極力駁斥人分南北之說,大力為嶺南文學張本。 三、孫蕡與宋濂父子及劉基 宋濂與何真的關系先于孫蕡,而與孫蕡的關系也與何真有關。孫蕡是何真所辟之士,宋、何的關系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宋、孫關系,而宋濂與孫蕡的關系最為重要,對嶺南文學的影響也最為深遠。至于孫蕡之結緣宋濂,在其最初贄見宋濂的詩中已有表白:“惠州枉禮遇,揣己愧明恩。際會幸有時,感激復何言。”(孫蕡《贄翰林宋先生諸老》,《西庵集》卷一,四庫全書本)這里“惠州”,當指何真,他們初次見面應該就是在何真府上。 孫蕡,字仲衍,號西庵,廣東順德人,生于元惠宗元統二年(1334年),早年與好友王佐、趙介、黃哲、李德相聚于廣州南園抗風軒,共組詩社,人稱“南園五先生”,負節概,不妄交游;何真據嶺南,禮遇之。 洪武三年(1370年)舉于鄉,旋登進士,授工部染織局使,繼調安徽鳳陽府虹縣主簿,其后入京任翰林典籍官,跟隨宋濂等參與編修大型韻書《洪武正韻》,后出任平原縣主簿,不久受胡惟庸案牽連下獄,罷官還鄉。洪武十五年(1382年)孫蕡復出,任蘇州府經歷,八年后又遭貶謫,遠戍遼東;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因曾為涼國公藍玉題畫,坐藍黨案致死。 《明史•文苑》有傳,有《西庵集》傳世。 前面已經述及以孫蕡為首開創的嶺南詩派在嶺南文學史上的極其重要的地位與極為深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與宋濂甚有淵源。明以前,嶺南與內地文化的聯系,基本上單向的,主要是為官或貶謫嶺南者對嶺南士民施加影響,鮮少有嶺南士子主動北上游學、返教于鄉者。在此背景下,孫蕡景仰并師事或私淑宋濂,自有其一種特別的意義。其時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海外都競相求閱其文章,孫蕡可以像其他士子那樣,雖景仰之,但不一定師事之,之所以師事之,其內在的原因在于雙方的文學主張相近。在文化上,宋濂為理學正宗婺學傳人,孫蕡也傾心理學。據四庫全書總目《西庵集》提要:“蕡著述甚富,自茲集外,尚有《通鑒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可見其理學修為與成就。“其《孝經集善》則宋濂為之序”,也可見出他們在理學上的授受淵源。在文學上,宋濂乃至整個浙東派都傾向于征經、宗唐、得古,以孫蕡為代表的嶺南詩派,明顯的特色也是標舉唐音,詩風雄直,這已成學界的不刊之論。#p#分頁標題#e# 淵源既明,下面我們就考察其間的具體情形。 今檢《宋濂全集》,孫蕡乃是向宋濂獻詩最多的一位,有31首之多。而且從一開始,就表達了對宋濂的崇敬之情。第一首獻詩,如前所述,當是在何真府上。如詩中所示,當是宋濂對他這位荒僻之地來的小伙子,不以其位卑名微,而青眼有加,故其感激不已,獻詩以為贄,并表達師從之意:依依野田雀,本在桑榆間。深林蔭棲息,卑枝覆羽翰。春風照九垓,陽和德澤寬。翱翔宵漢上,乃得隨鴛鴦。群公珪璧才,盛世仕明君。出入金門里,百辟同繽紛。顯宦極崇高,下顧念斯文。惠州枉禮遇,揣己愧明恩。際會幸有時,感激復何言。斐文謝嘉誨,久敬道彌敦。(孫蕡《贄翰林宋先生諸老》,《西庵集》卷一,四庫全書本)在稍后所獻的《陪翰林宋承旨游鐘山》中,師從意更為明顯:天上禪關敞薜蘿,每緣休沐得經過。云籠梵宇青蓮濕,地接皇居紫氣多。甘露結花凝木末,醴泉和雨落巖阿。欲陪謝傅金屏約獉獉獉獉獉獉獉,未解朝獉獉獉簪奈爾何獉獉獉獉。 而當宋濂致仕返鄉之際,更再三表明這一層意思:承恩初入詞林日,亦得叨陪侍從班。云彩九重開鳳閣,天光咫尺近龍顏。彤闈侍讀青春暖,彩筆題詩白日閑。此去定酬優老愿,軟輪游遍越東山。 一自先生離禁闥,玉堂清致更無人。金蓮飏彩初寒夕,燕瘦凝香散暮春。著作有官惟故事,論思此道竟誰陳。青云志氣慚悲梗,不覺臨歧淚滿巾。(孫蕡《餞宋承旨潛溪先生致仕歸金華》,《西庵集》卷五,四庫全書本)而最集中最直白的表達,見于《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二十五首》[5]2612。這一組詩,既全面反映了宋濂的志趣與功業,也直白而急切地表白了彼此之間的關系或者孫蕡所想象的關系。其三說:“二十余年侍禁闈,趨朝常早晚歸遲。春坊一掬臨分淚,記得垂髫受業時。”很直白地將宋濂說成是自己的受業之師。而在受業門生中,孫蕡還認為宋濂對他是青眼有加的:“門生日日侍談經,獨向孫蕡眼尚青。幾度背人焚諫草,風飛蝴蝶滿中庭。”(其四)因為這種感覺,所以孫蕡對宋濂的致仕十分不舍,不僅說“后學無師誤少年”,將宋濂抬到天下師表的高度,更說“在于蕡也更堪憐”,表明一意師宋的堅貞情懷:“聯班欲上陳情表,留取先生住講筵。”(其十九)組詩的余下部分,在全面反映了宋濂的志趣、功業與聲名的同時,也表達了一些不同于流俗的意見。 如其五(千載班揚亞六經,先生高步續芳聲。高麗日本朝王使,長向仙班問姓名)和其六(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東夷買得潛溪集,已向扶桑石上鐫)反映宋濂文傳四夷的成就與聲名,但其七則說:“頭百勛庸列上卿,君王豈是重文名。朝廷禮樂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字面上說朱元璋看重的不是宋濂的文名,而是其禮樂制度的建設。這多少與事實上相違的,這只不過反映了孫蕡和乃師的不得其志的理想,故其十二就說宋濂:“蓋世文章未是雄,真純卓有古人風。”其八說:“幾逆龍鱗進治安,朝回只說圣恩寬。小儒日侍絲綸閣,不得寰中奏稿看。”宋濂在朱元璋的雄猜之下,溫樹自警,自是不會輕逆龍鱗,這也只能看做孫蕡的想望。其十六(山僧野客莫相過,碑板人間刻已多。從此黃庭不須讀,自開池水養群鵝),十七(榮歸詔許老山垌,火棘交梨養性靈。秘府圖書翻閱盡,卻從方士借丹經),十八(近欲長參不語禪,水云飛盡月輪圓),均是說宋濂歸去,會禮佛崇道,不問世事。不過在其二十又說:“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止青牛乞著書”,則表示并不希望宋濂就此隱廢了文章大道。而有意味的是其十八所說:“惟余一冊龍門子,留與西江學者傳”,十分看重宋濂的《龍門子凝道記》。這是宋濂46昆明學院學報2012年4月在元時未得志之時著以期將來之用,就像劉基在元末以為其志不得用于今世,而著《郁離子》以傳世一樣。已入大明,而孫蕡仍戮力表彰,其用意何在呢?應當是為乃師打抱不平也,這在當時十分難得。孫蕡日后竟坐藍玉黨禍而死,草蛇灰線,或許于此已埋。因此,希望當今研究宋濂與孫蕡的方家,對此一關節切不可輕輕放過。這也是筆者撰作本文的用意之一。 宋濂也確曾對孫蕡施以青眼,從其為孫所作《〈孝經集善〉序》可以見出:“東廣孫君讀(吳文正《孝經注》)而善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蕡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于篇端。蕡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5]622 序的口吻,乃前輩為晚輩作,并有明顯的揄揚之意:宋濂在序中還得點明孫蕡的來歷,表示其尚是藉藉無名之輩;但所作“當可傳誦”,而事實上也沒有那么好,不然不至于不傳于世。 孫蕡景仰宋濂,與其子宋璲也甚相得。其《西庵集》卷六有一首《懷朱太史芾宋舍人璲》:“誰憐飄泊向江關,獨倚長風憶妙顏。老我黃塵三楚外,羨君華藻五云間。清時步武蜚聲蚤,晚歲逶迤奏牘閑。鍾阜冶城蒼翠里,何由更得共躋攀。”孫蕡明初與宋濂齊名、同為浙東詩派首領的劉基的交往,文獻乏載。不過《西庵集》卷五有一首《奉太史令護軍公》:“虞淵捧日帝羽儀,文事武備天人師。筆端詞翰河漢決,胸次韜略風云隨。邦基肇造古伊呂,謨猷篤棐今皋夔。畫圖麒麟盟帶礪,仙游更與赤松期。”詩雖未明言獻給誰,但詳詩意,明初做過太史令,而又有開國勛業者,只有劉基。此詩可以見出孫蕡對于劉基的無限推崇之情。 四、李質與宋濂及劉基門生徐一夔 道光《廣東通志》和《肇慶府志》都載有一篇標為宋濂所撰的《靖江右相李公墓志銘》,其實即洪武年間曾任桂林府學教授的東莞人陳璉所撰的《故資政大夫靖江相府右相李公墓志銘》,載在其別集《琴軒集》卷九,《國朝獻征錄》卷一百五、《皇明文衡》卷八十九也均有載。我們感興趣的是,李質的后人,包括后來方志修纂者,為什么這么容易甚至有意地要去張冠李戴?宋濂與李質的淵源,也將由此談起。 #p#分頁標題#e# 這一方面當是因為李質和宋濂關系原本不淺,二則作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以及以其為代表的浙東學術或更寬泛地說江南文學,在嶺南士民中留下了較深的影響。 據《明史》卷一三八《李質傳》:“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材略。元末居何真麾下,嘗募兵平德慶亂民,旁郡多賴其保障。名士客嶺南者,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蕡、建安張智等,皆禮之。洪武元年,從真降,授中書斷事。明年改都督府斷事,強力執法。五年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治獄平恕。 遣振饑山東,御制詩餞之。尋出為浙江行省參政。居三年,惠績著聞。帝念質老,召還。嘗入見便殿,訪時政。質直言無隱。拜靖江王右相。王罪廢,質竟坐死。”這一篇傳記,傳遞出幾個重要信息。首先是,李質既為軍閥,亦為文士,這一點是引入本文論述的重要前提。需要說明的是,《明史》本傳以及前述黃佐的傳記,都說李質是從何真附降朱明王朝,其實李質雖曾為何真僚屬,但至元末明初,在嶺南的地位亦是一獨立的割據軍閥。其起身緣由如下:“德慶民何國賓、張宗達倡眾為亂,真以兵遣質歸,募鄉兵二萬余,立堡柵于龍岡之上,與陳文仲設策防御。 時官舍民廬俱焚毀殆盡,守令將帥悉付印綬於于質,質亦挺身為經畫,朝夕練兵。遣其從子伯豫同總管文仲督募兵討諸賊,悉平之。上連蒼梧、象郡,下接三山、九江,皆蒙其保障。”至此割據嶺西。對此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五七《李質傳》的說法是:“一時三山、龍潭諸賊,莫能與爭。朝廷嘉之,授廣東樞密同僉。”以至于連“何真恐質圖之,遣其幕士孫蕡說與連和。”而黃佐祖父黃瑜《雙槐歲抄》卷一“何左丞賞罰”條引東莞謝用賓京錄何左丞真遺事言:“李質據有嶺西,真欲并之,以從簡諫而止。”黃從簡即黃佐的高祖。[10] 正因為李質作為割據一方的鄉豪與軍閥,他雖然名義上附從何真降明,而所獲得的待遇則近似何真,最后官至刑部尚書的高位。反是,真正的何真的部屬,往往只得授較低級官員,例如巡檢、百戶等。 即使何真本人的子弟,開始也只任低級軍職,如其子何貴,只是因為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回粵收集舊部有功才得任指揮僉事。洪武五年(1372年)九月,在賑濟山東回京后,李質由刑部尚書出任浙江行省行政。浙江行省在當時是朱明王朝最重要的省份之一,而何真也只做到山東參政,由此可見李質的地位與影響。李質赴任,朝官多人以詩文相送者,由于李質的《樵云集》未能傳世,具體情形已經不明,而宋濂所撰的《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倒在《宋學士文集》《巒坡后集》中保存了下來:大丈夫生于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卮無當其質,雖美弗適于用也。問學既充,不遘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茍處之閑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岳之巍峨,亦未易叫閶闔而呈瑯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后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與!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之者,浮沈府掾中,日以澤物為己任。會海內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為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巖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欿然,每以為未足。 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上,署為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升秋官。又未幾,上御外朝,親擢為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艷之。 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翱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畫省長棘,儼乎其雄肆,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余計,而東廣為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為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于民,兇奸之未屏也,我則鋤刬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修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圣天子寵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勛業,焜耀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朂哉。[5]710 對比為何真所作之序,宋濂顯然對李質的評價要高一些,盡管何真的地位相對更高。而尤須注意的是,盡管二人的功業地位與官品均高出宋濂不少,但作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在為二人寫的序中,均表現出一種文化上的自信與優越:為何真寫的序中,僅就何真為祠堂義田之事“來請記于余”而敷陳成篇,毫無恭維之意;為李質寫的序,則徑從有志于學,逢時而用,勉勵李質在新的崗位上有所作為,仿佛言之于后生晚輩;再從文中宋濂說嶺南仕宦,自古以來,惟張九齡與余靖可以名世,希望李質他日能躋肩于三,其認為嶺南自古人文不興的心態溢于言表。 李質還曾請宋濂最好的朋友劉基的門生徐一夔寫過一篇《德慶府端溪縣新建廟學記》(《始豐稿》卷五,四庫全書本):……邑人李公質,今為浙江行省參知政事,以其邑建學始末授余請記,余既序其事,且告之曰:“人莫切于務學,而有民社者,亦莫先于興學。古之人在畎畝則學于畎畝,在山林則學于山林,在漁鹽版筑則學于漁鹽版筑,固不皆待于上之人也。然而天之生人不能家稷契而人游夏,為之上者,必立學校以教之。故自三代而降,未有舍學校而為治者此也。夫學校興則民不惑于他道,詩書禮樂之教可講而明,道德性命之蘊可求而知,而人皆可至于成德達材之地,而后政可成也。皇上龍興,慨然欲以儒術為治,重念儒效不振,干戈甫戢,亟下興學之詔,其慮深且遠矣。廣雖夐在嶺海之表,唐宋以來,若張文獻公九齡、余文襄公靖,實生其地,聲名文物,遂與中國等。圣明之見,視四海猶一家,為守令者,何可以遐陬裔壤而鄙之哉。此端溪之學所以煥然一新于今日也,且異時端溪之士,非有振起之者,而養材積學以待用于明時,如今李公者,且不乏人,矧今縣大夫奉宣德意而為此振起人心之具,則夫人材之盛,豈不十倍前日哉。筆以俟之,識余言之不佞也。#p#分頁標題#e# 相較李質,徐一夔輩份低了一級,官階幾乎沒有(也不愿有),其姿態仍然是平視的。應當正是基于這種文化上的仰視,李質的后人才愿意張冠李戴將陳璉之文改篡成宋濂之文,同時也見出宋濂對于嶺南文學與文化的深遠影響之一斑。 五、由宋濂與嶺南仕宦的交往看嶺南文學與江南文學的淵源 從現存文獻來看,明初嶺南仕宦與江南文人的交往,多限于浙東之士。這是時勢所然,也是嶺南仕宦的選擇使然。浙東在元末明初是理學正宗嫡傳之地,群星璀璨,人才輩出,史有定論。就詩歌創作而言,后世雖有五派之論,然就經史之學,實各區域均難與相抗。再則,即便就五大詩派而言,吳中派既乏老成之士,又早經朱元璋的彈壓,聲勢不浮。其他各派,與浙東相較,直可謂晚輩后生。從何真、李質、孫蕡與宋濂、方孝孺、徐一夔等浙東士人交往中所取的姿態,即可充分說明。孫蕡的姿態,更有象征性意義。因為孫蕡并不僅僅是何真幕下之士,而是代表嶺南士人的一股力量。故前述何真當心李質相圖時,出面調停的乃是孫蕡。明兵下嶺南,主張歸附,并親草降表的,是孫蕡。孫蕡雖是何真門下之士①,同時也不諱言為李質門下之士②[11]。嶺南詩風,向以雄直、古雅著稱,并將其歸之于中原文學的傳統。從上述嶺南仕宦與江南文人的交往中,筆者認為,這是有問題的。因為嶺南文學的真正崛起,就始自南園五子。此前零敲碎打,不成氣候,也不成傳統;此后是局面大異于前,文章開篇已有所述。那么,嶺南文學淵源考索,重點應從元末明初開始,重中之重是嶺南五子及其周圍人士———固然也要顧及此前。循此,從上述以孫蕡為代表的明初嶺南仕宦與以宋濂為代表的浙東文人的交游考述中,我們可以說,嶺南文學的主要淵源,當是江南,而在江南之中,又集矢于有深厚經史傳統,主張宗經致用的浙東。相較之下,嶺南詩風的雄直、古雅,如孫蕡“五古遠師漢魏,近體亦不失唐音”(朱彝尊《明詩綜》卷十一,四庫全書本),在當時五派之中,與吳中的相對軟媚、江右的偏于館閣之氣、閩中的偏于擬古,更接近以劉基為代表的奇崛雄肆,跨宋元而上的浙東詩風。再則,當時江南作為人為淵藪,文化后起的嶺南,尋找一個學習的對象,一個努力的標桿,也是舍江南而其誰。試想明初之所以興起科場大案,乃因為所取多為江南之士;揆諸當時情形,并無偏袒之處,倒是后來推倒重來,純出政治的需要。而在文化重心南移江南的歷史背景下,真正與中原士人游,不僅無助于詩風的雄直、古雅,相反還增其軟媚。這一點,洪亮吉論清初嶺南三大家詩已有揭示:“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12]鄧之誠進一步闡述道:“大均與江南畸人逸士游,未改故步,佩蘭與中原士大夫游,俊逸勝而雄直減矣。”[13] 但是,以學生的心態以江南為師,并不妨礙嶺南文學堅守自己的特質。在明初嶺南五子的作品中,大量反映嶺南風物的詩篇,就是一個象征。對此,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總結道:“百川東注,粵海獨南其波;萬木秋飛,嶺南不凋其葉。生其土俗,發于歌詠,粵之詩所以自抒聲情,不與時為俯仰也。”[14]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從此之后,嶺南文士的對外交往取向,也多為江南文人,而且常以受江南文人的教誨、品題等為榮尚。陳永正先生的《嶺南詩歌研究》,提供了大量此類材料。比如說:惠士奇,江蘇吳縣人,雍正年間提督廣東學政六年,嶺南詩人何夢瑤、勞孝輿、羅天尺、蘇珥入署從學,人稱“惠門四子”,又與吳世忠、陳世和、陳海六、吳秋合稱“惠門八子”,具一時人文之盛;杭州人杭世駿乾隆十九年(1754年)任教粵秀書院,與何夢瑤等往還,遍游嶺南名勝,作詩500余首,編成《嶺南集》;阮元任兩廣總督,創辦學海堂并親任山長,網羅張維屏、譚瑩、陳澧、朱次琦等,嶺南文風極一時之盛[15];尤其是屈大均,在其成長的關鍵時期,先后得到兩位文壇盟主錢謙益與朱彝尊的獎掖,屈大均本人對此也感念不已:“名因錫鬯起詞場,未出梅關人已香。” 江南文學固可為嶺南文學的重要淵源,嶺南文學也在自我的堅守中,不斷成長,并反過來影響到江南文學,頗有教學相長,青出于藍的味道和方面。比如屈大均,先是其以僻處嶺南的一介布衣而獲得文化中心領袖的獎掖乃至推崇所帶來的最重要正面影響,而后卻是“三吳竟學翁山派,領袖風浪得兩公”[16],反過來竟影響到江南文學的發展,與江南互為師表了。再如后起的黎簡,錢仲聯就說:“清中期廣東詩人黎簡,受浙派的影響,反過來他又影響浙派。有兩方面:一方面影響浙西秀水派,但畢竟不同;另一方面影響浙東大詩人姚燮。”[17]因此,在中國文化趨勢南移的大背景下,嶺南文學以江南文學為師,但又有自己的堅守,并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反過來又影響到江南文學,從而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的區域間文學生態。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