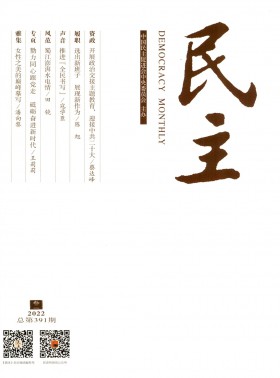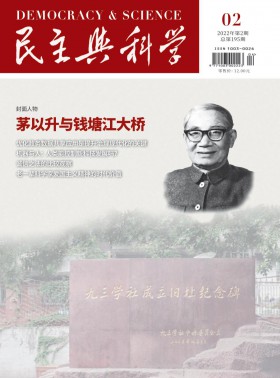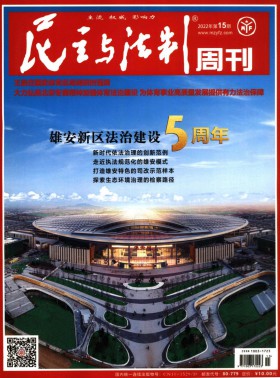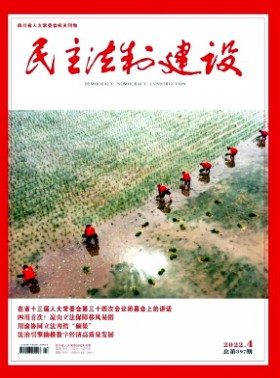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民主時期的左翼文學,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工作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進行的,是與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同步發展的。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文學仿佛是時代的晴雨表,社會歷史的每一次動蕩都會從不同角度折射到文學上來,都對文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文化運動從五四時代對外國思潮流派的兼收并蓄轉到格外關注“普羅”(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是我國的革命文學對風行全球的左翼思潮的一個響應,是紅色的30年代的一個健康產兒,更是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對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的一次示威。因此,本文想從左翼文學這個特殊角度,探討一下新民主主義時期,我們黨是如何以文學藝術為武器,歷盡千難萬險,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的。 概括來說,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文化運動的特點,是反封建、反專制,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在這漫長的30年(1919一1949)的發展過程中,文化運動的發展也不是筆直向前的,這之中也有反復,也有潛流,但它的基本脈絡是革命的,是進步的。特別是經過反帝反封建的的洗禮,他們由單一的追求個性解放這一自身利益出發到關照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工人農民的生活群體,就是他們思想的一大進步。如果說第一個十年是啟蒙主義,個性解放思想壓倒多數,那么第二個十年就是個性解放主題淡化,讓位于階級斗爭。從“二七”大罷工到五州運動,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已日漸被一些激進的青年所接受。1923年,一些從事實際工作的共產黨人鄧中夏、揮代英、蕭楚女開始寫文章,明確提出革命文學的主張,號召作家深人革命實際,培養革命感情,由于他們本人不是文學家,考慮問題的角度多.從社會政治著眼,對當時的文學現象多有批評,但也在文壇上引發一r一場不小的討論。 1924年,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國民黨召J下了“一大”,孫中山宣布并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國共兩黨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結成革命統一戰線,這不僅促進了‘!,國革命的發展,也給革命文學的發展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出版了一批宣傳革命思想的進步刊物。這個時期,在我國廣大的農村,特別是南方一帶,農民運動正方興未艾,在廣州主力、了農民運動講習所。隨著農民運動的深人,各種矛盾也十分突出。為了對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有一個真實而全面的分析,澄清當時各種強加到農民運動上的罪名,在1925年至1927年相繼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重要文章,陸續發表在《中國農民》、《戰士周報》等刊物上。這是共產黨人關注進步文化運動,并在思想宣傳上進行積極引導的一個例證。 正當革命文學運動出現勃勃生機、迅猛發展的時候,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他們查禁進步書刊,捕殺進步文化工作者,共產黨人、蕭楚女慘遭殺害;但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并沒有被敵人的囂張和殘酷所嚇倒,郭沫若寫出了《請看今日之》的討蔣檄文,為躲避迫害,此后遠走天涯、亡命日本。北伐戰爭中投筆從戎的部分作家重新回到久違的文壇,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專制和暴行,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創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即左翼文學。當時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在歐洲各國都有程度不同的發展,在日本、德國、美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均形成了一定的規模。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而蘇聯正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發展很快,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策源地,蘇聯的理論對于各國想變革社會的文學藝術家都有著不同凡響的吸引力和不容質疑的正確性,這些主客觀上的原因都在這一時期推波助瀾,從而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主流一左翼寒學的一個高峰。 在1928年至1929年,同是進步文化工作者,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等又圍繞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問題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論爭。這場論爭雖然對革命處于低潮形勢下的廣大群眾起到鼓舞和激勵作用,但不利于革命文化戰線上的團結對敵,而且容易被敵人分化和利用。黨中央注意到這場論爭,為加強對文化戰線的領導,根據黨的指示,共產黨人馮雪峰、潘漢年在論爭雙方之間做了大量工作,消除誤解,達成共識,并具體籌劃了左聯的成立工作。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左聯的成立,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對文藝戰線領導的一個偉大勝利,也是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我黨領導廣大左翼文藝戰士進行反圍剿斗爭的一個勝利。 左聯時期的文學活動,有其鮮明的革命色彩,在這十年間,中國的左翼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它不僅要正面反擊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還要對付打著“中立”、“文藝自由論”,“無黨派文學”等形形色色的文藝派別的圍攻,壓力之大在我國進步文化運動史上是空前的。繼左聯成立后.潘漢年代表黨又先后領導了“劇聯”、(左翼劇團聯盟),“社聯”(社會科學家聯盟)等的籌備工作,并擔任了此后成立的“中國左翼文藝總同盟(文總)”并擔任其第一任黨組書記,另一位共產黨人瞿秋白到上海后,也積極參加了左聯的工作,并與魯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談中國的左翼文學,不能不涉及蘇聯文學對它的巨大影響,當時的國民黨御用文人就叫嚷“革命作家是被盧布所收買”,文藝理論是“向俄國批發的”。這從反面也說明了蘇聯文學對中國左翼文學的發展有著多么至關重一要的影響。在這里談蘇聯文學的影響,不能低估日本的媒介作用,在中國的左冀文學發展過程中,日本是兼有模式和媒介和雙重身份的,一方面,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較之中國開展得要早;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壇大多是由日本留學生筑成的,”•(郭沫若語),因此說,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是通過日本間接受到蘇聯文學的影響的。一方面中國的左翼作家接受了蘇聯文藝思想中階級斗爭白爾學說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個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廣大的勞動人民群體,視野和創作題材也都拓寬,使左翼文學無論是表現思想還是藝術手法都日臻成熟。另一方面,中國也接受了蘇聯排斥“同路人”思想,中國的左翼作家認為當時“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廣大工農群眾”。甚至提出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直接的斗爭對象”。.這樣做的結果,使自己很孤立,而且授敵人以攻擊的口實,他們還接受了蘇聯倡導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創作方法”,.機械地在現實主義與唯物主義、浪漫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劃了等號,這些影響都是消極的。、在這十年間,由于左聯的工作和世界性左傾思潮的推波助瀾,特別是蘇聯文學的巨大影響。使中國的左翼文學成為國際范圍內“紅色的30年代”的一個組成部分。左翼文學在30年代,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幾乎滲透到各個領域,粉碎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使國民黨在文化領域一直處于防范的地位,終于一敗涂地。#p#分頁標題#e# 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積極宣傳與介紹,是左聯當時開展的一項主要活動,被譽為“文藝的重工業運動”。先后出版了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普列漢諾夫歷史唯物主義的《藝術論》,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魯迅譯的心車勒丙綏夫斯基的文學論》(車爾尼雪夫斯基著),盧那察爾斯基的《作家與藝術家》。這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介紹,對尚在迷惘中徘徊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無疑是久旱遇甘霖,他們采取拿來主義的辦法,對蘇聯的文學藝術采取教條主義的照搬,以致在左聯前期產生了二些標語口號文學,多是圖解革命的急就章,大多數比較粗糙、簡單,曾授論敵以攻擊的口實。隨著左聯各項活動的開展和馮雪峰、魯迅的積極倡導,一些左聯成員在倉啡實踐中逐步克服了革命文學倡導時期的幼稚現象,•作品日趨成熟。同是寫勞動人民的遭際,五四時代單純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對筆下的人物充滿了同情,.憐憫。到了30年代,’由于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文藝的領導,‘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階級斗爭思想的深人人心,左聯作家筆下的工農群眾不再逆來順受,而是有了反抗意識,如工人罷工,農民暴動等。由子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這一時期寫工人題材的作品較之五四時期大量描寫農民生活的困苦和知識分子苦悶的作品,在數量上增加了。這也與左聯成員身體力行從事實際革命工作(包括培養工人通訊員),發動工人罷工的實踐有關。 國民黨當局是不會聽憑左翼文化的蓬勃發展的,他們加強了法西斯文化專制統治,查禁進步書刊,搗毀進步書店,捕殺左翼文化工作者。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等五位左聯作家被害,被收人中學語文課本的魯迅寫的《為了忘卻的記念》就是激憤于此而寫成的。丁玲被監禁,應修人被國民黨軍警所逼墜樓犧牲。墨寫的謊言是永遠也掩蓋不了血寫的歷史的。 中國左翼文學在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尊重厲史_并不等于美化失誤。在充分肯定左翼文學在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史_上的主流地位的同時,也要一分為二地總結它的不足和局限。 首先,左聯時期的作品題材比較單一,社會涵蓋面有限。因為左聯作家聲稱要當一個政治的“留聲機”,因此他們沒有時間在斟酌作品的布局謀篇,加之客觀條件也不允許,一個作品往往不是深思熟慮,經過時間積淀的產物;而是革命熱情加創作沖動的產物,題材也多集中在左聯倡導的幾類之間,如寫兵變等,這無形中限制了作家配創作視野,作品的單一、粗糙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二,宗派思想作怪。宗派意識是封建幫會意識的產物,是一種極其狹隘的觀念形態,是產生無原則糾紛和個人主義、滋生文藝市儈習氣的土壤。可以這樣說,宗派主義在左聯時期一直存在,只是或輕或重的區別。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要置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的社會現實不顧而故意危言聳聽,由宗派情緒引起的幾次論爭,影響了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也使大多數中立作家長期處于仿徨狀態,不利于他們向左翼作家靠攏。 其三,教條主義。左聯時期,對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的學習有生吞活剝的現象。蘇聯文學對我國左冀文學的積極影響是無可辯駁的,但我們也應看到它的消極一面,即教條主義地照搬蘇聯的一套,甚至左聯在當時提出了一個“左”的不易被人接受的理論,視蘇聯為自己的祖國,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這顯然是教條主義的思想。它不利于中國共產黨爭取大多數的民眾來擁護自己的主張。 縱觀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的文學一直是它的主流。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反抗黑暗統治的斗志的決心,在中國革命史上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