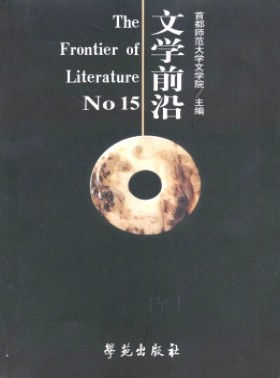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學教學中的素養提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當前,文學素質培養不僅在大學教育中普遍缺失或弱化,而且在漢語言文學專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也日趨凸顯。固然,這其中主要有社會轉型與文化環境改變的原因,也有當代大學教育改革探索過程中失敗因素的影響。但是,需要我們迫切反思的應該是文學專業課程教學本身存在的疏漏與不足,我們應當回到最基本的教育與教學立場來探討最基本的文學素質培養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文學素質培養為何弱化 以培養適應新的社會需求人才為目標,當前大學的文科教育普遍進行了定位的調整,即由原來的培養專業化、理論型人才的目標向培養綜合型、應用型人才方向傾斜。適當淡化專業教育,增強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成為當前文科課程改革的普遍趨勢。 然而,在改革的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及時關注和探討。其中比較突出的矛盾是:淡化專業意識,勢必削弱專業素質的培養。 從專業教育層面看,就業導向和應用型人才培養思路,落實于課程設置改革,就不得不增加大量公共課和通識課,專業課課時被迫大大壓縮。此外,在當今大學教育體制規范下,已經出現一種普遍現象,就是從事某種專業的教學與研究者,往往受制于專業領域的額定任務———比如具體的教學任務和科研任務,在全力完成這些任務時卻往往忽視這個專業本身的性質、特色、發展等。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性質與特色固然包含了很多內容,但最基本的文學性和文學特色卻在所謂的知識體系建構中日趨模糊和淡化;文學教育也在所謂的學術化、標準化、量化的教學要求、教學評估、教學管理等制度下喪失了個性。 多年前,就有一些教授、學者對大學文學教育和文學本身的實際狀況表示擔憂:“文學教育在文學之上,建立了一套頑固、強大的闡釋體系。它刻板、教條、貧乏、單一,它把我們與文學的聯系隔開了,它取代了文學,在我們這個精神已經極度匱乏的社會里發揮著使其更為匱乏的作用。”[1](P14)“在學術的合唱中,文學被日益顯得有學識的知識分子再一次拋棄、再一次出賣了;對學術的歡呼鞏固了對文學的遺忘、鞏固了對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隔膜。”[2](P5)這些批評的聲音應當引起大學文科教育與改革的關注。 從專業學習層面看,近二十年的社會現實與文化環境發生了劇變,在經濟大潮的全面沖擊和影響下,在就業壓力和應試教育機制的制約下,普遍的社會心理與價值觀中,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厚。一方面,優秀的高考生幾乎全部擠向那些就業前景好的金融、電子、管理等熱門專業,許多進入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往往不是出于對此專業的熱愛而是出于無奈,在專業素質上嚴重的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化的趨利風氣,使當下文學藝術過度追求娛樂化、快餐化,經典文學的影響力卻在日趨弱化。這些環境影響必然使文學專業學習很難達到理想目標。同時,畢業后的出路問題也迫使學生在本科四年內要付出主要精力去考外語、計算機、普通話等各類等級證書,而專業課學習反而變得無足輕重,似乎沒有什么實用意義。 固然,在當前大學文科教育重新定位、全面進行課程改革的大趨勢下,我們既不能因循守舊,也不能對社會的發展變化與需要漠不關心,而應積極探索培養新型人才的教育策略和實踐途徑,努力使教學改革獲得顯著成效。大學文科教育始終不能輕視更不能放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質的培養,而漢語言文學專業教育就是要通過文學類專業課程的教學實現這一目的。文學教育對于當代大學生的思想生成、人格培養、心靈滋潤、素質提升等能夠產生深刻且深遠的作用與影響,也直接關系著我們未來民族精神的建構與傳承。 因此,當下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的專業教育有沒有遠離文學教育?我們當今培養的學生,其文學專業素質究竟如何?雖然他們可能學到了許多前沿性的知識或可操作性技能,甚至也實現了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的求學目的,但他們是否擁有對文學本真的熱愛或興趣?他們是否能夠對文學產生來自個性經驗和審美主體的感動與感悟?難說。如果說文學專業的學生不具備文學的寫作能力尚可歸因于社會閱歷及生活體驗的欠缺,但是文學閱讀能力與文學審美能力的匱乏就是文學專業教育的失誤了。 二、領悟“文學閱讀境界”,培養學生獨立的審美主體 長期以來,某些帶有偏見的論斷———比如文學創作靠天賦、勤奮和生活積累,大學培養不出作家等,不僅在文學界有著似乎很充分的證實,而且在文科大學教育中也形成毋需明說的暗示。不錯,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出來的不可能都是文學家,許多優秀的詩人、作家的確不是大學培養出來的。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而言,文學的感悟能力、審美能力,特別是文學的創作能力也不是直接迅速地教之即會的。文學教育不可能像教數學定理和公式那樣,立竿見影地使學生可以用定理公式去解決實際問題。但是,如果按照以上邏輯推斷,否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育功能與教育意義,則是極為錯誤極為無知的。無論是否上過大學,任何一個文學家或具備較高文學修養的人,在其成長的歷程中,都必有對他產生深遠影響的文學啟蒙或文學教育。我們應該讓所有選擇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都能夠真正懂得:文學給予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是受益終身的。 作為文學教育者,首先應該自覺匡正文學教育偏見,抵制消極的隱性邏輯影響,以熱愛文學的真誠感染學生,引領他們走進文學閱讀和文學感悟的精神境界,培養學生獨立自由的審美主體。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借名家詞章意蘊比況人生(求學、成事)的三種境界,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3](P41) 我們可以通過文學教育幫助學生實現文學素質的養成,也應該是逐漸抵達三境界的過程。#p#分頁標題#e# 讓文學閱讀和文學感悟進入較高的境界,必須要有“獨上高樓”的獨立自由的審美主體人格。但不幸的是,我們的學生都是應試教育的產品,應試教育已經十分嚴重地限定、規范了文學閱讀的目的與方法,名著在這樣的閱讀過程中支離破碎。空洞、教條、模式化的闡釋話語在中小學階段就已經養成。 在大學文學專業課學習中,學生普遍是被動閱讀作品,之后又在作業或考試中被動地評價作品。不少學生在評析作品時,習慣性地總要聯系實際發議論、表態度;對于藝術形象的評析則像是給人做思想鑒定,或者照搬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權威化定論,或者生吞活剝地引用西方一些理論批評術語。當前文學批評與研究中的某些浮躁之氣已經滲透到大學教育中。多數學生對文學缺乏純真的喜愛與興趣,他們對原創作品中鮮活獨特的生命意識、感悟、體驗、智慧,豐富深邃的社會觀照、人性洞察,以及文學創作中迸發出的靈感、浪漫情懷和想象等自然也缺乏審美的感受力。 針對目前文科學生文學素養的先天不足,筆者認為不宜完全從教學要求出發,按照教學大綱既定的內容逐章逐節地灌輸文學史或文學理論知識,而是應該首先引領學生走進真正的文學世界———由那些個性、氣質、風格卓然不群的作家們所創造出的包羅萬象、廣闊迷人的文學宇宙,感受領悟文學深邃豐富的蘊涵。那么,在文學史或文學理論的教學過程中,雖然要注重學術與理論層面的深入,但不能因此脫離我們個人的審美主體感悟和經驗,文學史是由個體的作家作品構成的,而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是鮮活的生命,我們閱讀他們,首先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呼喚,怎能先以無生命的標尺去度量、評斷呢?中國當代文學史課程在講授1950—1970年代教學內容時存在較大困境,學生對這一時期的文學不感興趣,不愿意讀作品;而學術界也已有諸多的否定聲音,認為那時期的文學都是極度政治化的宣傳品,毫無文學價值可言。作為學術爭鳴,有其探討的理由和意義。但是,我們不能以不夠客觀,甚至帶有偏見的判斷和評斷建構我們的當代文學史。筆者在講授這段文學史時,就特別注意通過一些史料文獻的介紹,使學生充分了解那個時期文學的歷史語境和生態條件。 頻發的政治批判運動對文學藝術橫加干擾甚至肆意摧殘都是鐵的事實,高度組織化、行政化的文藝機構也行使著管束、限制文藝創作自由的種種權力。 雖然,那個時期作家們主體思想被政治所鉗制,他們很多時候只能充當政治傳聲筒而不能發出個人的聲音;文學藝術在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規范下,很大程度上概念化、公式化了。但是,需要特別提醒學生,不要因此簡單化地全盤否定、拒絕那一時期的優秀文學,那些堪稱“紅色經典”的優秀作家與作品,正如批評家張炯先生所言:“它們確有很高的文學性和審美性,相當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歷史風貌和民族精神,開拓了前人沒有寫過的題材、主題,塑造了前人不曾刻畫過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創造了不少新的文學形式和風格”,“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是不可重復的”[4](P1)。因此,“望斷天涯路”———尋找每個時代那“不可重復”的文學風景和文學生命,正是文學史必有的使命感,也是文學精神傳承的根本目的與意義。我們在當代文學教學過程中,應該讓學生真正走進每一特定時代去認識那些優秀作家———那些對文學理想有著真摯深厚的鐘情和熱愛,對美的境界忘情沉醉并執著追尋的作家們,他們對自身所處時代的敏感感應,對歷史、現實、未來的洞察或幻想,對個人所經歷的或豐富或坎坷的人生況味,以及由生活體驗與人生況味中凝聚、升華的思想和情愫……當這一切付諸飽含心血的創作,便是他們物質生命向精神生命的轉化。因此,文學史中的“作家作品”不應是教學強加給學生的“名詞解釋”,而應是“為伊消得人憔悴”的靈魂呼喚和美的執著探尋。 比如,柳青的《創業史》所反映的是合作化運動歷程,雖然作者立場鮮明地表現了社會主義偉大革命的時代政治主題,但我們不能簡單斷定它就是時代政治的傳聲筒。作品以宏大敘事展現了歷史的縱深質貌和現實的廣闊生活畫卷,因而獲得厚重的史詩品格。而梁三老漢這一成功的藝術典型,更是柳青十幾年扎根農村,從真實、深厚的體驗與情感中孕育鑄造的血肉豐滿的生命,這一生命也就是作者“眾里尋他千百度”的靈魂遇合,由此賦予《創業史》不朽的藝術生命。 再比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如果按照文學史教科書的引導,視其為干預生活的反官僚小說進行評說,我們何以能體味時年22歲的青年王蒙“獨上高樓”的人生憧憬以及激情和迷惘交織浸染的青春成長體驗?主人公林震是懷抱理想、單純熱忱的青年人,對“知音”趙慧文產生了朦朧的情感,而趙慧文是被生活壓抑的已婚女性,小說中有一段敘述林震在趙慧文家里做客的情景———趙慧文進屋后先去吻藍色小床上熟睡的孩子,林震則小心地問:“他父親不會來嗎?”而不是說“你丈夫不會來嗎?”或者“孩子的爸爸不會來嗎?”這里微妙地暗示了林震對趙慧文已經有丈夫這一事實的抵抗心理,而且那個熟睡的小孩也成為有潛在敵意的第三者“他”。林震敏感地注意到臥室“墻壁因為空無一物而顯得過分潔白”,“窗臺上的花瓶傻氣地張著口”……他細微地體察到女主人公不幸福的婚姻。而趙慧文因為林震的到來,往日的疲倦與悒郁不見了,變得十分活潑可愛,她煮了一鍋荸薺,“端著一個長柄的小鍋,跳著進來,像一個梳著三只辮子的小姑娘。”當林震告別時,“夜已經深了,純凈的天空上布滿了畏怯的小星星……林震站在門外,趙慧文站在門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她說:‘下次來的時候,墻上就有畫了。’……林震用力呼吸著春夜的清香之氣,一股溫暖的泉水在心頭涌了上來。”[5](P104-107)這些細膩又生動的描述,散發著獨特迷人的青春文學芬芳,非常動人地傳達出年輕的生命在早春季節對理想和愛情產生的心靈悸動。而新時期之后更為成熟深刻的王蒙再也寫不出這么清純靈動的情境了,只有在他二十歲出頭時,在20世紀50年代激情燃燒的歲月才寫得如此真切傳神。可見,我們一旦避免囿于成見,就能夠引領學生進入文學閱讀與文學審美的較高境界,幫助他們逐漸確立獨立自由的審美主體人格。#p#分頁標題#e# 三、探微“文學創作境界”,豐富學生審美經驗 在“文學閱讀境界”里逐漸確立獨立自由的審美主體人格,只是為培養學生的文學素養奠定了必要的基礎,若要進一步豐富并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還需要帶動學生在文學專業課教學所營造的濃厚的文學情結中,去探微“文學創作境界”———那獨特的精神創造活動怎樣由萌生到豐富再到升華的奇妙過程。這個過程同樣經歷了王國維所描述的三境界。 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三境界里感同身受,就必然可以獲得更高一層的文學領悟力和審美經驗。 當然,激勵學生積極嘗試文學創作,從自身的創作實踐中去探尋文學的“山重水復”與“柳暗花明”也是文學教育的重任之一。但是事實上,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文學創作實踐活動是缺失的或者是非常有限的,僅僅依靠寫作課教學來培養學生的文學創作熱情與文學寫作能力也存在著諸多困難和局限。因此,筆者認為,所有文學類專業課雖然沒有“教授、指導學生文學寫作”這一規定性教學目的與教學內容,但都應該責無旁貸地以另一種途徑實現帶動學生進入“文學創作境界”、豐富并提升學生的審美經驗及文學素養的終極目的。通過文學專業課教學,開闊學生的視野,鼓勵他們拓展閱讀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獻或史料,比如優秀的作家傳記、日記、書信、隨筆、回憶錄、訪談錄、創作談等,不僅可以幫助學生走進現代文學真實的歷史語境,更好地理解特定時期的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亦可使學生間接體驗、感受他人(尤其是經典作家)的“文學創作境界”。像《新文學史料》這樣的刊物中就可以找到非常豐富珍貴的史料,那些鮮為人知卻又極富傳奇色彩的文人往事、文壇佳話、創作軼聞等在許多知名老作家的日記、書信、回憶錄中得到鮮活生動的再現,還有那些泛黃的老照片、歷經滄桑的作家手跡、遺稿等等,似乎復活了被歷史塵封的文學史,既使人產生身臨其境的親切感又喚醒了一種幽深久遠的文學想象。 為了幫助學生更深入地感知作家創作境界的變化,從而對當代文學的藝術探索或審美形態嬗變內因有充分的理解和認識,也可以引導學生去追蹤當代作家的創作及心路歷程。近幾年有多位當代作家自覺反思、解構甚至否定他們新時期之初的代表作———那些寫進文學史已成為標志性的作品。比如北島之于《回答》,梁小斌之于《中國,我的鑰匙丟了》,劉心武之于《班主任》等,都有了自我批評的聲音。此外像張賢亮《我的菩提樹》之于《綠化樹》,張潔的《無字》之于《愛,是不能忘記的》等,也可視為顛覆性的自我重寫。 這些現象和信息折射出他們對“新啟蒙時代”的整體性反思,揭示了文學發展中豐富的內在變化。同時,作家們文學意識與審美傾向的變化,也是經過漫長的“眾里尋他千百度”之后,創作境界抵達到一個新的“燈火闌珊處”的發現與歸屬。 當代先鋒小說家余華的創作轉變是非常具有啟示性的個案。余華早期創作很明顯有為先鋒而先鋒的姿態,他著迷于形式主義的死亡與暴力描寫,如代表作《現實一種》,從幼兒之間出于游戲快感而引發的死亡傷害,到成人們因復仇而連環演繹的虐殺游戲,所有游戲狂歡式的死亡過程覆蓋了人性的殘忍、恐懼和悲痛。但是20世紀90年代的第一部長篇《在細雨中呼喊》,他對死亡的敘事發生了變化,作者不再是一個冷漠地操縱死亡游戲的機器,而是以敏感且沉重的生命意識“回憶”了弟弟、養父、朋友、母親等人的死,其中“蘇宇之死”尤為觸動人心,作者從主人公孫光林的敘事視角,在回憶與想象中仿佛親歷了“我的朋友蘇宇”那天早上因為腦血管破裂陷入生死邊緣時的掙扎———他“以極其軟弱的目光向這個世界發出最后的求救”……但是起床后的母親、父親卻因為蘇宇沒有像往常那樣去茶館打來開水而訓斥他、嘲笑他,他們“吃完早餐以后,先后從蘇宇床前走過,他們去上班時都沒有回過頭去看一眼自己的兒子。他們打開屋門時,我的朋友又被光芒幸福地提了起來,可他們立刻關上了。蘇宇在灰暗之中長久地躺著,感受著自己的身體緩慢地下沉,那是生命疲憊不堪地接近終點。”當他的弟弟蘇杭也像父母那樣向屋門走去,“那是最后一片光明的涌入,使蘇宇的生命出現回光返照,他向弟弟發出內心的呼喊,回答他的是門的關上。蘇宇的身體終于進入了不可阻擋的下沉,……在經歷了冗長的窒息以后,突然獲得了消失般的寧靜,仿佛一股微風極其舒暢地吹散了他的身體,他感到自己化作了無數水滴,清脆悅耳地消失在空氣之中。”[6](P114-115)敘事人沉浸在蘇宇的生命意識中,那彌留間的感受那么珍貴、美好卻又那么虛渺,一向羞澀敏感的少年蘇宇,懷著對生的無限留戀在一次次無聲地呼救,可是他身為醫生的父母和粗心的弟弟卻是那樣的冷漠、自私、麻木,一次次決絕地把生之門關上了。看似重復的敘事形成死亡情境的渲染,但不是血淋淋的渲染,而是無限惋惜、惆悵、悲憫的渲染。悲憫情懷的回歸,意味著余華創作境界和文學胸懷的改變。 本文僅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課教學的微觀視角,對提升學生文學素養提出個人疏淺之見。針對當前文學素質培養在大學教育中的弱化現象,還需要我們更加全面深入地進行觀察、調查、思考和研究。毫無疑問,直面現實困境且積極探索改革出路,乃是我們當前大學文學教育研究的迫切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