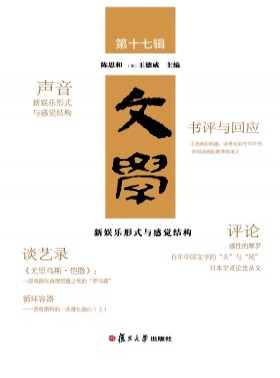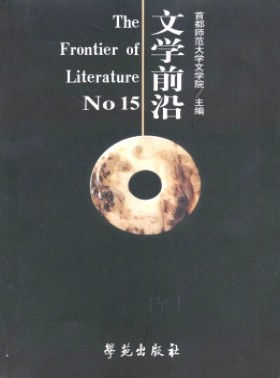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學理論建設模式,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民族性原本是政治學、人類學的概念。當民族的“自我獨特性”和“民族身份”處于需要強化的歷史階段,民族性話語往往會成為一支強大的話語力量。近代以來,國勢低弱、中西文化的不平等狀況強化了中國學人自卑與自強的雙重心理,面對“中西、古今、體用”等兩難選擇,民族性話語成為中國文學理論在處理中西古今關系、解決資源配置及方法選擇上的一種元理論話語模式。 然而,民族性話語畢竟是一個充滿多義性、矛盾性的話語系統,具有濃郁的時代性、情感性、地域性,而這些自身問題往往又被帶入文學理論的研究中來。比如,歷史地看,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在不同時期均表現出不同的對外關系傾向:或保守的激進,過于強調傳統的力量;或開放的激進,過于依賴西學資源的引入。這種歷史的情緒化表現顯然應該得到進一步的清理的矯正。而諸如“民族性話語概念元素的邏輯關系”、“民族性話語的歷史表現及其最終形態”等問題,則仍需要從根源上予以剖解分析。惟如此,才能處理好傳統與現代、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實現中西、古今的融會貫通,完成中國文學理論的時代性創生。 一、模糊與糾結:民族性話語的內涵及命運 (一)民族性話語的內涵 民族性話語往往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民族話語權等概念糾結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復雜的概念群,其間的界限與關系含糊不清。從學術考古學和理論譜系學上看,這個概念群仍然是西方舶來品。 總體上講,在西方學術界,學者對這些概念的區分也是五花八門、各說各話,并未形成一個固定的、為大部分人所普遍接受和認同的結論。這自然很符合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的一般規律。在中國學術界,古今問題和中西問題是每個歷史時期的顯著問題和矛盾的集中地,是選擇中國文學理論發展所必須回答和必須解決的前提,所以,這兩組相聯結的問題必須用一個概念或范疇加以表征才能進一步形成理論話語系統。這個范疇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的概念和定義同樣相當模糊。“對特定群體和類別的人們來說,民族性概念可能是主觀的或者客觀的、含蓄的或者鮮明的,明顯的或者隱蔽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它們把這些標識聯系到關于文化—社會—階層—種族或國家的思想上。”[1](P225) 若從辭義上考察,在英文中,“民族性”可以是ethnicity,也可以是nationality,前者指族群意識,后者強調國家意識。當從人類學的角度把中國視作一個多民族國家時,民族性即ethnicity;若把中國當作一個各民族的共同體即“中華民族”時,民族性即nationality。近代中國是以整體的“中華民族”這一主體與西方世界發生關系的,所以更側重于國家意識方面,民族性等同于國家性。但是,無論是ethnicity、還是nationali-ty,都強調在與他者的比較中自我作為主體的基本屬性,即我之區別于他者的自我性、獨特性、差異性、完整性。這就是民族性話語的核心。因此,“民族性”是基于本民族的獨特屬性而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比較概念,它試圖清晰地標識出不同民族主體之間的差異與界限。或者說,民族性即對自我共同體的標志和屬性的一種主觀認同和追求。 文學理論的民族性概念則稟有中國文化的心理、情感特征,二者呈現出同質同構的存在樣態。 “在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領域,‘民族性’這一概念的產生以及關于這一概念的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論爭,從根本上說,是最充分地體現了上述中國文化的發展特征的。”[2](P239) 中國文學理論近代化、現代化的轉型過程,歷史地表現出古代傳統文論被否定、西方文學理論處于強勢地位,從而自然而然地在文學理論自西向東的流動態勢中呈現出中與西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一般而言,越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存在,越是需要強調其存在的自我性、合法性。近代以來,雖然古代文論暴露出更多的自身缺陷,然而中國文學理論的新形態卻遠未生成,中西對立、強弱對比的語境所造成的中國學人文化心理上的陷凹,愈發導致文化心態上的焦慮、急躁、以及明確的功利目的。由此,建設“當代的”、“中國民族性的”文學理論,便成為中國文學理論的歷史任務和主題。 “中國的文學理論”邏輯上就等同于“民族性的中國文學理論”,民族性話語由此層面折射出民族文化與文學理論的弱勢地位和復雜心理。 (二)民族性話語的歷史糾結 民族性話語是民族主義思想的衍生品。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首先是近代的,其次是較為復雜的。 雖然這一思想成為中國學術發展的最深層的意識力量,然而,歷史地看,無論是民族主義思想還是民族性話語,都存在著內在的深刻悖論:從情感上需要強化,在理性上卻予以反抗;從政治上需要認同,在文化上卻必須反對;從國際關系上必須重視,在國內關系上卻必然淡化。即表現為在此種場合的反抗和在彼種場合的尊崇。 但是,不管承認與否,民族主義文化心理永遠是中國學者的指導意識,居于壓倒性地位。然而,隨著歷史的演變發展,有三個原因也導致學者們的理性意識不能完全屈從于純粹的情感形式。其一,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矛盾是明顯的,而全球化與地方化卻在矛盾的張力中同時得到強化。于是,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悖論成為中國學人的理性泥淖之一。其二,西方現代哲學與近代哲學不同,近性主義哲學、歐洲中心主義圖景、政治上的專制主義與封建主義、人類學的男性中心主義等等,表達的是同一個結構主義主題,即一個具有一個中心、一個完整而明確的意義的結構。這里,中心永遠居于權力地位,權力與信息影響從中心向四周擴散并控制邊緣。而到了現代,西方現代哲學最為集中的改變和表現形式,是取消了中心、否定了意義、修改了信息流動與權力控制的單向性,并強調對話、平等及意義的生成性。這種變革為中國學者歡呼,因為它與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形成遙相呼應、殊途同歸的態勢,由此,視界融合、對話商討、以及對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成為中國學者的理性追索形式。并且,由于這些思想均來自于西方,所以中國理論的他依性、缺乏原創性也在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三,民族主義有政治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之分。中國學者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意識,強調對外關系的對立與自我的獨立,這可謂政治民族主義;同時,中國學者還具有天下意識、開放意識、以及理論探索上與日益強大的國勢相對稱的學術訴求,而這種種的思考又不斷強化著他們的文化認知與使命。因此,政治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交錯對立往往同時出現在理智和情感中,撕扯著他們的靈魂,令他們表現出在民族主義取舍去從上的選擇之難。#p#分頁標題#e# 除此之外,客觀上講,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的本質屬性,這種屬性必然能夠從當下的文化現實中分析結晶出來,民族性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屬性。從古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來看,中國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非常明顯的,但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處于外來壓抑、中西混雜、未有主導、無所適從的境地,無法使之生成一個基本固定的、可供分析的民族存在屬性。 那么,在邏輯和現實必要性兩個方面,民族性必然尋求“傳統”這一力量的支持。盡管傳統是變化的,但是傳統基本是有據可查、可資立足的,所以,民族性與傳統達成了話語權的同謀,民族性通過傳統的內容與形式加以表達和再現。這樣,民族性話語的深層結構無不具有傳統性、后視性、復古性、保守性,而且,這種保守性有時還呈現為極端激進的保守。這類封閉保守的民族性話語或隱或顯地存在于近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各個歷史階段,以中國本位為旨向,試圖在不可規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捍衛傳統文論的民族地位。如果說,這種內含多重動因的言語表達顯示了政治的策略和必要性的話;那么,當歷史跨入了21世紀,在歷史文化語境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若仍抱守這種帶有封閉色彩的自我獨特性顯然已不合時宜,也已成為拖拽中國文學理論健康發展的后滯力量。因此,這種單向立足于自我傳統資源的民族性話語勢必歷史地走向終結。 (三)民族性話語走向終結的現實邏輯 首先,中國文學理論的民族性話語母體是一種“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民族主義,民族性的認同和民族屬性的確立,產生于與西方世界的不對等交往。 中國古代較少民族主義概念,只有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主義,這種民族觀在晚清以來由于國家地位的改變而發生了逆轉。在被動開放、中外文化不平等交流的背景下,中國人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屈辱心理與奮發自強的救亡圖存意識相互交織,中國文化書寫了漫長的爭論與探索的文化變遷史。屈辱心理和情感焦慮支配著從改良主義到洋務運動、從辛亥革命到、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等不同階段的抗爭與探索,期間,中國學人一直在尋找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恰適關系,尋找中國文學理論在世界上的位置、以至中華民族區別于他者的特殊屬性,從而形成了挑戰與應戰、批判與調和、接受與排斥的中西文化關系的搖擺機制。由此,中西、古今之爭也成為中國文化現代化變遷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然,中西和古今可分為兩個大的問題,但古今問題是由中西問題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導地位。也就是說,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于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民族交往,既要反抗西方、又要學習西方的時代困境中,建基于國家民族之間不平等的發展形態和文化心理的對峙中,所以,每當中外各層面的沖突產生并加劇,民族性問題就會集中出現,成為一種對外防御和自我保護的工具。因此,我們發現,民族性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它更多適合于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歸屬于特殊的歷史范疇。而當中國國家實力上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處于平等對話的良性態勢時,整個社會文化心態便會發生不同以往的變化,以“對立”和“保守”為特征的中國民族性話語自然會隨著歷史的演進而失去根基,走向消弭和終結。 其次,民族性具有情感性,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對文化“自我身份”的焦慮。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越強烈、越明確,民族自豪感就越強,越能煥發出民族精神;而在遭遇外來文化壓力而被迫作出文化調整時,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的確認問題也會暴露出來,形成在文化選擇過程中的認同危機和情感壓迫。 這一點與具有主動引進外國文明傳統的日本不同,在充滿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中國,外來文明滲入的每一步幾乎都是被動的、曲折的,幾乎都與民族生存和社會危機休戚相關。故而,中西文化之爭具有十分明顯的政治性質,文化領域中出現的混亂、沖突和喪失自信,被視作整個民族動蕩、危急和喪失獨立性的精神表征。于是,中華民族形成了較強的消除中西文化的不平衡、重建民族文化體系、重新找到民族自信的歷史緊迫感。這就是“民族性話語”的情感“焦慮”。這種情感焦慮與義理性、邏輯性不能劃等號,民族性具有合情感性,卻未必具有合理性;封閉與保守的文化追求與開放、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相違背,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所以,一旦我們用義理性來考察反省這個問題,民族性就會成為一個過時了的歷史問題,就會在理性的審視中變味。因此,理性的平和、視界的高遠,以及中和的理念、融通的操作模式,必然取代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話語。 再次,自我與他者的復雜關系所產生的民族性話語的內在悖論和張力,也使之充滿了解體的必然性。民族性話語一方面強調處于封閉形態的自我性、區別于他者的獨特性;另一方面,這種自我性和特殊屬性又必須依賴于他者的燭照才能得以顯示。 這種必須拒斥和不得不接受的內在悖論,瓦解了民族性話語本身。民族性通過對比與否定的機制來實現,民族性這個概念的主要功能,是用來在某一群體與另一群體之間作或明確或含蓄的對比,這樣,任何時候使用民族性概念,肯定都有“我們”與“他們”之分。然而,標識和對比本身又是動態的,是隨著環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的,同時,這些由不同的層次、標識和對比所建立起來的界線并不排除人們在各個群體或類屬之間的往來,也不因他們的往來而阻止了民族的認同或被認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學理論的民族性話語又內含著辯證理路,在特定的社會或民族國家中,“我們”和“他們”的對比是通過否定的范疇來確定的:對比是中與西、古與今的對比;否定是對傳統的否定,也是對西方的否定,更是對自我的當下狀態的否定。這就是民族性概念的辯證法。這樣,對于他者的依賴、對于“對比”關系的強調,必然要求民族性走向一種交流形態的共存———民族主體在對立格局中與他者悖論共生,在與異族的交往中借助異族去指認、想象并生成自己。 #p#分頁標題#e# 所以,以封閉為特色的民族性與開放性旨向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文化的發展必須以開放性為前提。 從現實的情景來看,雖然這種內在的邏輯在中國似乎很難展開,近代以來,民族性話語在多個歷史階段之所以成為引人注目的話語表達,總是隱含著對立排他的多重緣由、以及民族情感的訴求,甚至任何以推拒姿態置自我于世界之外的誘因,都會成為保持“自我存在”、保持純潔性的心理先導。但是,經過了漫長曲折的社會現代化的轉型,在當下中國,如果我們真正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個性、又要不斷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因子,如果我們真正要在對話、交流、融合中熔鑄出具有現代性新質的中國文化;那么,遵循事物發展的規律,秉持開放的旨向、博大的胸懷就是必不可少的,狹隘、封閉的民族性話語也就必然走向終結。 二、“虛在”與“實存”:民族性話語的歷史存在及消解過程 (一)民族性話語歷史存在的三種形態 中國文學理論的民族性話語,有一個從顯到隱、自身演變消失的歷史過程。從文化發展的歷史形態看,民族性話語的歷史存在可以分析為: 1.作為純粹的民族情緒和心理表征的、強勢的民族性話語。作為民族情緒的一種表達,民族性以偏激的保守為特征,拒斥外來文化。這種民族性作為心理上的強勢話語,得到中國人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認可。但是,盡管其勢力強大,卻未必在實踐中得到實在的回應與應用,處于“虛在”的狀態。 2.與開放性并生共在的民族性話語。中國文學理論被動變革、不得不走中西融合會通之路,以及由中西文化論辯體式所呈現出來的文化震蕩,具有被動的開放性。這里,民族文化對西方文化或拒或迎,民族性的保守性與實際上的開放性并行不悖。只是,這里的保守性作為純粹話語形式被架空,開放性卻是這種民族性的歷史實在樣態。 3.正在消失的民族性話語。在國家日益繁榮、社會心態日趨理性的今天,極端保守的民族性話語已經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義,中國文學理論正表現出中和的胸懷與姿態。如果說,在2中,1作為制衡全盤西化的力量、同時也能夠多少反映當時學界的聲音包括文化的焦慮心態,有其存在的歷史必要性的話;那么,在3中,“虛在”的情感上的民族性及其心態已經基本消失,如果繼續延用“民族性”這一概念,那么其內涵和外延均需重新界定。與其如此拖著一個不合時宜的概念的沉重尾巴,還不如直接以3的形式終結了它更好。 我們再來具體分析。民族性話語作為第1形態主要集中于之前,在改革開放后的文化論爭中也時有體現。南社成員馮平面對西方文化東來之洶洶氣勢就大聲疾呼:“慨自歐風東漸以來,文人學子咸從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倫之詩,莎士比之歌,福祿特爾之詞曲,以謂吾祖國莫有比倫者。嗚呼!陋矣!……彼白倫、莎士比、福祿特爾輩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軒、白石諸先哲遠甚也,奈何盡棄國學而學于人?”[3]開了中國近代以來文學理論復古的先聲。一戰后,梁啟超歐洲游歷歸來,發表《歐游心影錄》,痛斥歐洲文明之弊病。梁漱溟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堅信人類文化要發生“由西洋態度變為中國態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陳嘉異在長篇論文《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中,認定東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擬的巨大優越性,“故將來之世界文化,必為吾東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締造而成”[4](P311)。1949年之后的30年,我們總體上閉關鎖國,可謂一元獨尊,然20世紀90年代舉“失語癥”旗幟的人依然認為,“當代文學批評的有效話語是自‘五四’以來不斷引入的西方文論話語,而國學精粹———中國古代文論卻束之高閣正被人淡忘,他們把這種‘胡音噪鬧,母語希聲’現象稱為‘失語癥’”[5](P819)。由此可以看出,在一個多世紀洶涌激蕩、你來我往的中西文化交戰中,民族性話語時不時會躍上風口浪尖,成為時論核心。但是,保守的民族性話語盡管強勢一時,又會歷史性地快速跌入谷底,遭到各方面的批評和拋棄。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現象:民族性確乎是中國近代以來民族文化心理最恰切的表達,但是,保守的民族性卻總是在各個時代都受到質疑批判。從歷史的實在狀態觀察,這種極端狹隘的民族性話語盡管真切地表達出國人的民族性心態,但是,中國人對待外來文化又從來不是封閉拒斥的,這就使得此種狹隘的民族性話語事實上成為不受歡迎的話語形式,淪為一種潛在的情感式“虛在”,停留在空洞的概念意義上;而真正在歷史現實中占有更多話語權力、發揮實際效力的,是在跌跌撞撞地對外開放中的互動與融合。開放性,才是中國文學理論對外關系史的“實存”態度和狀態。 在2中,民族性話語的封閉性與開放性處在并在態勢,開放性對封閉性從民族性話語內部展開了重新闡釋與消解,從而造成民族性話語的歧義和由保守形態的“虛在”向開放形態的“實存”的潛在變化。這里,民族性話語沒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拋棄,但是卻被從內部闡釋為兩個內涵:A,保留第1形態的純粹民族性話語的情感特征,它僅僅作為精神符號和概念而存在;B,釋民族性為開放性,認開放性為民族性之必有內容。表面上看,前者仍然處于話語的顯赫地位,但在實踐上卻被架空、忽視,后者才是實踐中的實存狀態,并且,后者對前者的再闡釋,也表現出一種偽裝成民族話語的新話語。盡管A也還能在一定語境中得到共鳴,但它因為不能適應當今世界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現實境遇,不能為中國文化提出切合實際的突破性良方,必然淪為純粹的情感符號和概念。這樣說并不意味著中國人放棄了民族性話語A,那種偽裝了的、被重新闡釋的“民族性”話語B也并非對民族性話語A的實質視而不見,只是沒有否定民族性話語A的心理背景和需要,并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中,從依然頑固的民族性話語的內部開始革命性的顛覆,在實質上開始拋棄A這個作為情感和純粹概念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的空殼。#p#分頁標題#e# 事實上,這種剝離民族性話語的孤立性、封閉性,從B的角度闡釋民族性、倡導民族文化的融合或綜合,隨著歷史的發展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遠遠超越了A,甚至讓人有種錯覺,以為民族性就是B這種融合會通的實際操作方式。可見這種消解的力度之大。雖然A與實際操作層面的、重視中外文化交流和對話匯通的B同時存在,但是我們要做的,仍然是通過變通的方式對民族性話語進行內部改造和重新闡釋,并歷史地表現為在實踐領域里對民族性狹隘心理的摒棄,以推進A這種民族性話語的徹底“虛在”化。這樣做,既不傷害中國處于低凹地帶的文化自尊,又能確保中外文化交流與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路徑的暢通。 (二)民族性話語在膠著中突破 無論中國人的情緒如何焦慮,或如何試圖強化自我特性,中國文化包括文學理論的發展事實上卻無視這種民族性情結;無論“民族性”的要求多么強烈,“中國文學理論”卻不可能僅僅是“只有中國有,其他人沒有”的東西。更多中國文化內核的發掘,以及民族文化關系在本質上所具有的社會性、交往性等等,都導致民族主義理論及其話語不能再作為強勢話語統攝于學術殿堂。然而,它又不能被放下,于是,作為解決這一尷尬局面的手段,民族性話語就只能從內部改造、重新闡釋,促進和壯大以“開放性、對話性、平等性、融合性”為基本特征的內涵表達。 在中外古今多維的復雜關系中,傳統和西方文化發生了長久的爭執與摩擦、批判與融合。比如,我們經歷了近代以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爭;五四時期,有著“全盤西化”式的“批判”,調和論者折中公允的理性態度,學衡派“情感中立”的文化融鑄論,十教授的“中國本位文化論”,戰國策派的“文化綜合時代論”;以及之后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形成為標志的“融合”等各種典型形態。在以上種種形態中,開放性永遠都是實存的文化主旋律。尤其是20世紀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文學理論也走向了新的改革開放:改革是文學理論范式的革新,開放是與世界文學理論的對話、交流與融合,八九十年代文學理論的盛大景觀就是在“西化”與“傳統”的并行與糾葛雙重力量的作用下鑄就的。人們對西方文學理論有熱衷、有抵制、有平靜的思索,同樣,對自身文化傳統也有懷念、有反思、有重建。這種文化多邊力量的交互影響與作用,正是新時期文化和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鮮明特色。我們看到,新時期的文化和文學理論建設表現出兩種相反的路子,即以“現代化”與“方法論”為主題詞的西化之路,和以“國學”為主題詞的傳統之路,并歷史地呈現為一中一西、一左一右的兩種力量、兩種道路的對立與互補。正是在這種雙重力量的綜合作用下,新時期文學理論在中與西的斗爭對立中融合會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向綜合與創新,其胸懷之博大、志向之高遠、精神之剛健、德性之寬厚,前所未有。 歷史自然地拋棄了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民族性話語,走向第3形態。21世紀以來,文學理論研究愈發在心態上趨于平和,在路徑上趨于明確,在方法上趨于多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文化傳統研究多年來積淀了許多豐富成果,尤其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整體性“和合”思維,在新的歷史時期得到重新挖掘和重視;另一方面,西方現代思想界亦開始呈現出新的動蕩和創造,以闡釋學哲學、存在主義、現象學、新歷史主義、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哈貝馬斯的商討理論,以及后現代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及其固化的結構、單一的意義的顛覆消解等,都使得多元思維、無中心結構、對話與共同體的存在形式、意義生成的歷史性等理念成為一種時代主導,這些思想漸次被中國學人所接受。這樣,中國古典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哲學思潮在更多的層面產生呼應,促使中國學術界醞釀形成新的天下主義:它既消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自卑,又削弱了對西方文化的崇拜;既矯正了夜郎自大、天下獨尊,又不必惟西方文化思想馬首是瞻,從而達成“古今轉換、中西會通”的共識。如此一來,在信守中外融通、古今轉換的必然路徑前提下,中國文學理論那種含有偏激保守情緒的“民族性”話語,事實上正在走向終結。這是歷史發展的邏輯必然。 三、會通與轉換: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圖景前瞻 如果說,保守、焦慮的民族性文化心態和情感在對話與交流的語境中消失,中國文學理論拋棄了對立,拋棄了對“自我性”消失的擔憂,走向視野的融合,走向文學理論深層次的結構性革命;那么,也就宣告了與此相關的民族性話語的徹底消解。當虛構的理念不再發揮作用,當中國文化的發展不再困守于民族主義的緊箍咒,這便預示著中國文學理論研究開始卸下沉重的心理負擔,輕裝上陣;同時,便也只剩下了“中外會通、古今轉換”這一實踐操作方式,讓我們能夠走向實際,進入實踐環節。“在涉及到當代中國文論發展的文化選擇方面,主張重視傳統文論資源,融會古今,貫通中西,走綜合創新之路,這種見解毫無疑問占據著主導地位。”[6]在獨立以保持自我性、對話以成就關系性的文化場域,如何致力于找到自我與他者對話的渠道,惟有真正“通”開。會通、轉換、對話、融合,其最終目的是“通”,只有通了,才能架起二者自由往來、資源共享的橋梁。“通”,是中西文學理論交流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通”,必須在深層次的心理結構圖式上完成“格式塔轉換”,即心理結構的整體轉換。 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要義在于“同”和“通”。是以“通”求“同”,以“通”達“同”。“同”是一種宇宙存在的整體狀態,包納萬物萬事;而“通”則是克服萬事萬物之間的差別和隔閡,通過事物與事物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流和溝通,達到物物相通、人物同在的一種途徑和狀態。“通”的精義所在,并非是否認事物的差異性并消滅它,并非是強求一致和同化異己,恰恰相反,而是強調同一性和差異性的互通共在。“‘通’是中外古今文藝理論交流融合的橋梁,中西傳統在這里進行碰撞和交流,傳統與現代在這里進行對話和應答。”[7](P14)#p#分頁標題#e# 當然,相通不等于相同和劃一。當我們發現和理解這種應合現象時,并不僅僅是去說明和描述某一理論事實,而且要去理解和闡釋這種現象存在的可能性和潛在意義,進入一種善出善入、東西交融的境界。由此,我們應該把對傳統的理解和對現代的描述結合起來,在尋求理解中理解自我,追尋東西方美學的原始魅力,確立整體性的東西方相通的理論淵源。 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同于一個人的身外之物,是不那么容易與所有者分離的,它深深根植于相關主體的心理圖式中,成為主體存在的一個有機部分,最終演化成深層的文化心理圖式。文化的融合,意味著文化本身的某種變異。移植的過程是一個雙向同化的過程:一方面,外來文化同化了引進者的主體心理圖式;另一方面,引進者本身的主體心理圖式也同化了外來文化本身。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傳統創造性轉化,在我們看來實質上就是一種轉型,即心理結構上的“格式塔轉換”。由于中西文化是兩種相對異質的文化體系,在整體上不存在一方融解另一方的實力,因而作為中西文化融和的產物,新文化本應是一種既不同于傳統、又有異于西學,同時卻又兼有二者成份在內的文化新圖式。它的必要歷史前提之一,就是傳統的深層結構被打破,從而為與東西方文化的重新組合創造條件。 總之,作為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歷史實存,民族性話語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在某個歷史時期具有出現與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另一個歷史時期卻具有消失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的問題。當我們有意無意地、作為口號或作為潛在的努力方向,把“中國文學理論”當作一個問題、當作一個努力的目標時,“民族性”的內涵實際上就一定存在于我們的邏輯和情感世界里,并影響著我們的各種努力。只是,在今天,“民族性”話語本身已經不能精確地描述我們的學術本質特征,作為一個口號型概念,它的消失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邏輯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