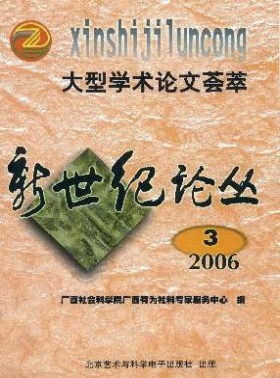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新世紀文學理論發(fā)展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中國,作為文學研究的學術話語體系,用了“文藝學”和“文學理論”這兩個名稱進行二而一又一而二的言說,呈現(xiàn)了學科的用語混亂。這兩個名稱,前者擁有權威學科目錄支持(為共和國前期權威部門和改革開放后學位委員會學科目錄用名),后者占有權威教材名稱的優(yōu)勢(為童慶炳、陳傳才、王一川、南帆、陶東風的著名教材用名),讓言說者選詞時或多或少地產(chǎn)生困惑;往往是互換著運用,引起讀者理解上的困惑。與此同時,這一話語體系,究竟應集中在文學理論的本位,還是要把自身擴展到文化研究上,自21世紀以來,又形成了巨大的爭論。宏觀地看,文藝學與文學理論的名分之爭和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方向之爭,后面都有同一邏輯在左右。鑒于此,且從這一學科名稱的產(chǎn)生與演進來切入這一邏輯,并希望以這一邏輯來引導這兩種爭論向有益的方向演化。 一、文藝學:詞源與演進 以學術方式和學科的形式言說文學,在西方至少有兩個傳統(tǒng),英語里的literarytheory(文學理論)和德語里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學科學)。當東亞受西方文化沖擊的時候,這兩種西方類型都經(jīng)日本的二傳而進入中國,前者以“文學概論”一詞進入中國(體現(xiàn)為后來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一書),成為民國時期的主流話語;后者以“文藝學”(日本學人用的漢字是“文蕓學”,蕓即藝)一詞進入中國(體現(xiàn)在當時岡崎義惠的用文藝學為名的論著),在民國時期影響不大。然而,德國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學科學)進入蘇俄,以俄文(文學科學)為旗幟而蔚為大國,當蘇俄的文學科學在中國革命的高漲中進入中國,中國則用日本人早年傳入的文藝學一詞對接而成為中國的文藝學,共和國前期蘇俄理論一統(tǒng)天下,文藝學也成為學科的正式名稱。 (1)英語文學理論和德語的文學科學的主要區(qū)別,在美學的理解上,英人更加突出美學是由知情意而來的情感之美,從而文學是情感之美在各文學體裁(詩、小說、劇本)上的體現(xiàn),這在從20世紀前期譯成中文的論著(如C.T.Winchester的SomePrinciplesofLiteraryCriticism)中有鮮明的體現(xiàn)。德人更強調(diào)美學是藝術哲學,藝術追求美,文學是一種藝術,文學科學對作為一種藝術的文學之研究,包括三個組成部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然而,英語的文學理論和德語的文學科學又有共同點,即這一學科是藝術之學,追求美。日本人引進文學科學,是為反對當時文學理論界把文學作為文獻來研究的“國文學”,突出和強調(diào)文學是一種藝術,要從藝術(即美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因此,把德國的文學科學譯為文藝學,這個“藝”是為了讓文學不是成為文獻之學而是成為藝術之學。蘇俄承接德國的文學科學,同樣認為文學是藝術的一種,但認為整個藝術都須為政治服務,因此,文藝學成了服務于政治的政治之學,只是這一服務要通過文學中的藝術形象來實現(xiàn)。 這一蘇聯(lián)的影響,極大地影響了中國20世紀中期的文藝學面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重開與西方的對話,英語世界的文學理論進入中國,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1984年譯成中文,有兩點甚為重要,一是認為德國學統(tǒng)的literaturwissenschaf(t與此詞對應的英文詞為lit-eraryscholarship)不恰當,認為“文學理論”一詞,除了是文學的原理、范疇、判斷標準之外,還足以包括必要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文學史的理論”;(2)二是把文學研究分為內(nèi)部研究(研究文學自身)和外部研究(研究文學與社會、思想、心理等其文學的關系),強調(diào)內(nèi)部研究才具文學本性。前一個方面讓英語的文學理論與德語——俄語的文藝學對接,并影響了文藝學語匯向文學理論語匯的轉(zhuǎn)變;后一個方面應合了文學研究從政治的緊密關聯(lián)中走出,而轉(zhuǎn)向文學性的學術研究。由于文學以及相關的文學理論在文化中一直都有的先鋒作用,這一轉(zhuǎn)向?qū)嵸|(zhì)是更好地擺脫了舊的文學與政治的關聯(lián),而以文學本性作為主體性,充當了時代的先鋒。可以說,文藝學成了強調(diào)自身特性的主體之學。 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是西方現(xiàn)代思想在20世紀前期的尾聲,20世紀后期后現(xiàn)代的出現(xiàn),引起了西方文學理論的新變,其對中國的影響,一是1987年伊格爾頓的《當代文學理論引論》譯成中文,文學理論呈現(xiàn)為一個流派史,而其中的流派,現(xiàn)象學、解釋學、符號學、精神分析等,不僅是文學本身,而還關聯(lián)到社會、心理、政治等諸多領域;二是1998年卡勒《文學理論》譯成中文,一方面把對內(nèi)部研究進行了文學性的推進,另一方面把外部研究擴大到文化研究,并認為文化研究是既把文學作為文化實踐加以研究,又把文學分析的技巧運用到文化的其他領域,還把文學作品與其他論述聯(lián)系起來(3)。這兩種傾向的合力,使文藝學成為流派之學和文化研究之學。 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新潮出現(xiàn)在西方并迅速并傳入中國,于是,中國文藝學界出現(xiàn)了關于文藝學應展方向的爭論:是文學理論的本位研究,還是進入社會的文化研究? 二、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在分裂、關聯(lián)、張力中演進文藝學中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不同走向,第一,前者應合了現(xiàn)代化進程中教育體系和學術體系中學科建設和學術規(guī)范的要求,后者應合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互動中的文化轉(zhuǎn)型的要求。第二,文藝學在中國一直都有兩個功能,一是完善自身的學科體系,二是作為文化先鋒。自中國進入現(xiàn)代性進程以來,文學一直扮演了文化先鋒的角色,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對文化變革有重要推動;從魯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都因文學上的成功而在文化上有巨大影響;從《暴風驟雨》《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業(yè)史》到《艷陽天》《金光大道》,顯示了共和國前期的文化功用;從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有巨大的社會影響文學在文化中的高位決定了文藝學的科學建設和文化先鋒這兩個功能可能而且確實在合一的狀態(tài)下進行。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藝術體系和文化體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視覺文化中的電影和電視占了藝術體系的王位,而文學走向邊緣。文藝學僅在文學之內(nèi),圍繞著文學進行言說就難以取得文化先鋒的作用,而要保持文化先鋒的作用,就必須逸出文化之外,進入電影、電視、互聯(lián)網(wǎng)、手機、廣告等各種對社會有巨大影響的文化領域。這一變化,從現(xiàn)象上看,引起了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之間的論爭,從實際上看,文學理論的本位守界與文化研究的跨界活動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共同推動了文藝學在新世紀以來的豐富演化,使文藝學呈現(xiàn)出一種多層級的深入和界內(nèi)外的互動。#p#分頁標題#e# 在文學理論的界域里,有關于文學性質(zhì)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大討論(童慶炳、錢中文、朱立元、董學文等),有文學如何形成中國經(jīng)驗的言說(哈金、南帆、張清華等),有關于文學形式的多方面研究(趙憲章、南帆、劉曉麗等),有關于文學敘事學的持續(xù)討論(譚君強、張萬敏、車文麗、陳德志等)在文化研究的論域,有視覺文化的言說(周憲等),有圖像時代的談論(金惠敏等),有文學與傳媒文化以及與媒介公共事件的關系的研究(陶東風、周憲等),有文學與公共性、公共領域的言說(陶東風等),有關于文化產(chǎn)業(yè)、奧運會、世博會與中國形象塑造的研究(金元浦等)在由文藝學的自然延伸且又關聯(lián)上其他學科并彼此關聯(lián)而自成領域的,還有生態(tài)美學(曾繁仁等)、網(wǎng)絡文學(歐陽友權等)陸揚新近的文章用斯圖亞特•霍爾的核心概念“連接”(articufation)來命名文化研究的新范式(4)。這一后現(xiàn)代意義上的“連接”正可以借來描述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之間豐富而動蕩的關系。然而,從學科的角度講,怎樣才能把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從理論上“統(tǒng)一”起來呢?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文化活動,不一定需要統(tǒng)一起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即可,但作為學科建設、理論把握、學術演進,卻需探討這種理論統(tǒng)一的可能。而從“文藝學”的中文名稱產(chǎn)生以來時而含混時而明晰時而變形的演進,從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都把自己看成是文藝學的發(fā)展方向來看,追求理論的統(tǒng)一,正好形成一種前瞻性的“規(guī)劃”。 三、文藝學的重釋:西方之Literature與中國之“文”文藝學作為一個科學,來自于世界現(xiàn)代性進程中教育體制中的科學體系和知識體制中的學術體系的建立,現(xiàn)代學術是以區(qū)別和獨立來達到整體的統(tǒng)一,正是在這一區(qū)分性和獨立性中,藝術與廣大的技術區(qū)分開來,成為美的藝術,文學與其他藝術區(qū)分開來,其研究成為文學科學或文學理論。正是在這一區(qū)分性中,literature一詞才從廣義性的文化,蛻變而成狹義性的文學。同樣,中國之文,最初指一切形式的美(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動植)。先秦以后,主要指語言之美,因此,一切對語言進行美的呈再現(xiàn)的都是文,無論是哲學之文,如《莊子》、《孟子》),歷史之文,如《史記》、《漢書》,政論之文,如章、表、奏、啟還是駢文、古文、小品文,都是文。當中國走向現(xiàn)代進程,引進西學之后,與一般的文區(qū)別開來的,由詩歌、小說、劇本、散文構成的,作為藝術之一的“文學”,才產(chǎn)生出來。在西方現(xiàn)代性之前,作為大文化literature是有統(tǒng)一的法則的;在中國古代,作為一切語言之美的文,也是有統(tǒng)一的法則的。金圣嘆在《水滸傳》評點的幾篇序和在《西廂記》評點里,把《莊子》這樣的哲學之文,《法華經(jīng)》這樣的宗教之文,《左傳》這樣的史學之文,《公羊傳》這樣的理論之文,與杜甫詩這樣的抒情之文,《水滸傳》《西廂記》這樣的虛構性的敘事之文,放在一起,認為其有共同的“文法”。 而世界現(xiàn)代性的演化,進入20世紀,特別是進入到后現(xiàn)代/全球化時代之后,在學科和學術的獨立和區(qū)分繼續(xù)演進的同時,各學科和交匯與互滲所勃然興起而蔚然成風,正是在這一跨學科的氛圍中,西方的文學理論變成了流派理論,面對的已經(jīng)不是狹義的文學,而是廣義的文化。精神分析文論把文學與夢、藝術、現(xiàn)實現(xiàn)象相關聯(lián),敘事學把文學與語言法則、圖像敘事、電影敘事、新聞敘事、廣告敘事相關聯(lián),后殖民主義把文學與游記、報道、講演、歷史等統(tǒng)一把握可以說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文論的每一流派,都對文學作了這樣或那樣、此向和彼向的延伸,從而,以流派史的形式出現(xiàn)的西方當代文學理論,已經(jīng)事實上擴大了文學研究,可以說已經(jīng)成為了文化研究。因此,中國的文藝學應考慮如何從狹隘的只以詩歌、小說、劇本、散文為文學的研究范圍里超逸出來,形成可以把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綜合起來的更為廣闊的學科胸懷,在理論上必要起來,在實踐上需要起來。 怎樣進行這樣的綜合呢? 正如文學一詞需要重釋一樣,文藝學一詞相應地需要重釋,文學可回到西方古代的文化之廣(lit-erature)和中國古代的語言之美(文),語言在文化的一切領域中流動,作為語言之美的文學也在文化的一切領域中流動。而作為研究文學的文藝學之“藝”就是對“文”之美的追求。正如在西方,藝術是追求美,在中國,文就是由內(nèi)在蘊籍而外顯出來的美。文有各種各樣的形態(tài),文藝學之“藝”(審美特性)隨之有多樣的風彩和各自的規(guī)律。當對文學之“文”和文藝學之“藝”作為新的解釋之后,德語的文藝學與英語的文學理論就統(tǒng)一了起來,同時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邏輯齟齬也渙然冰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