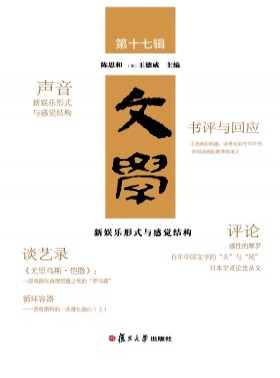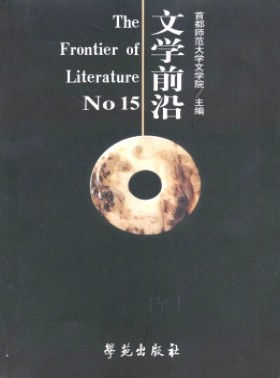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貝婁文學的對話藝術,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索爾•貝婁因其作品中能夠體現出“對人性的透徹的理解”而榮獲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海明威和福克納之后的第三個獲此殊榮的美國人。他的小說通常以黑色、荒誕和運用經典的形式體現個人和社會之間存在的分裂。心碎一詞巧妙地代表了現代人的靈魂所處的狀態。在現實世界中,死于戰爭、饑荒的人大有人在,但比起肉體活著而內心卻時刻經受著折磨、隨時處于奔潰邊緣的現代人而言,心中的憂傷卻比上面提的傷害危害更大。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那些不追求物質享受,更關注自己的內心、反抗心碎的人的行為和思想就顯得有些荒誕和充滿了黑色幽默。 本文試通過對《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里主人公的對話藝術的分析,來闡釋文章背后真正的意思。 一巧用文學典故,借力諷刺現代生活 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索爾•貝婁巧借文學典故對現代生活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小說中多次被提到的《致海倫》(作者是愛倫•坡)成為小說中貫穿始終的諷刺線索,同時對歷史宗教的廣泛涉獵的目的也是顛覆傳統的信仰,對被顛倒的生活目標進行嘲諷。 小說中巧用文學典故最顯著的地方就是在瑪蒂爾達和貝恩的男女關系變遷上,相見之初,貝恩對瑪蒂爾達的感覺好極了,可以說是如癡如醉,貝恩把她譽為如詩中所描寫的那種最可愛的人兒,并盛贊她的秀發和容顏,但在小說里面,貝婁通過第一次的運用典故就為故事后來的發展在做鋪墊。因為后來通過肯尼斯的話我們能夠了解到貝恩是個生物學家并對紫藍色十分的青睞,因此聯系文中的對瑪蒂爾達頭發的形容“紫藍色的頭發”,就會讓讀者自然而然聯系到其植物學家的職業身份。另外,在詩中充滿了作者對海倫的愛慕之情,但現實世界則剛剛相反,在這個物質世界里面,對著極度物質的并且自戀過度的瑪蒂爾達,讓人們能夠想到的就只能是物質的輝煌和心靈的空虛。但隨著貝恩和瑪蒂爾達關系的慢慢接近,貝恩慢慢對瑪蒂爾達顯示出不滿意的地方,如其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慢慢地顯示出不融合和不協調。因此,作者改變了對《致海倫》使用的典故而改用布萊克的詩,這個時候,變成了“婚姻的靈柩載滿了瘟疫”。而這時作者用了一個詞———Blight,這個詞是枯萎的意思,對于植物學家而言,枯萎對植物是滅頂之災;對于人物而言,這個詞則很容易就讓我們聯想到貝恩和瑪蒂爾達的關系走到了盡頭,以此來形容植物學家和富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典故的運用給我們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除此之外,《致海倫》還被作者用來諷刺另外一個主人公肯尼斯,其對深愛的姑娘特麗基是這樣形容的:“這個女人猶如孩子般嬌小,正如坡所娶得的姑娘一般,但我卻沒有這種福分。”通過這段話,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肯尼斯既通過運用典故對坡和克拉蒙的婚姻進行了嘲諷,同時又對特麗思徒勞無益的追求之后的自嘲形成對比。在故事的發展中,作者又再次用到坡去暗示特麗基和肯尼斯還有蒂塔之間的三角戀關系,作者最后通過對坡的典故說明肯尼斯對羅曼蒂克的理解,肯尼斯曾經說過:“對于愛倫•坡類似的嗜好,其實我本沒有權利去說什么,我根本就沒有權利的,但我確實那么做的,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舅舅對我引用‘海倫,你的美是為我’這話時戲弄他一下。”通過使用典故,作者有機地把坡、維吉尼亞和海倫與肯尼斯、瑪蒂爾達和特麗基形成了一種對照,并且成功地把難懂的文學語言轉換成通俗的俚語和行話,這對于引發讀者的思考和共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又產生了幽默輕松的效果。 二巧用第二人稱,拉近和讀者之間的距離 就寫作本質而言,第二人稱很容易拉近和讀者之間的距離,具有溝通交流的屬性,能和讀者之間引起共鳴。因此在小說中,作者在使用第二人稱的時候,是渴望和讀者產生交流,把讀者拉到故事里面,參與故事,參與小說中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感受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經歷,同時由于自由直接引語在小說中被廣泛使用,通過這種方式可以自由直接地表現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生活,甚至能夠感受到主人公說話的語氣和神態,這是一種敘述方式最輕松的表達方式,如:“人就是這般的,都是這樣的,你的成就越大,成績越突出,那么你的家庭生活和你的感情就越不滿意,因為你的主要精力都被成就帶走了。”通過這種表達方法,我們很容易就能感覺到,作者其實在通過主人公和我們進行生活理念的交流,能夠很輕松地就引起讀者和作者在生活經歷方面的共鳴。 再如“,當人們都用這種目光看你的時候,你發生了什么?你可能會感覺到你整個人都在這被看穿了,但是當一個女人為你把燈熄滅了,難道你就要向全世界的夫妻揭示什么是責任嗎?那你就自討苦吃了。”很明顯,在小說中,肯尼斯正在和本諾說話,但正是通過肯尼斯的口,作者在和讀者之間進行著溝通,讓讀者在讀這段話的時候反思自己,一個女人為我滅燈的時候,我在干什么?通過這種直接與讀者的對話,讓讀者感覺到好像自身也活在小說中,如果這件事情換做是我,我會怎么辦?這樣讀者就涌出一種強烈需要和作者交流的情緒和愿望。 三使用黑色幽默,刻畫爾虞我詐的社會 在貝婁的早期小說中,善意調侃、諷刺和幽默被廣泛使用,但在完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過程中,貝婁使用最多的還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最大的表現效果就是將真實人物和荒誕人物并列安排,因此嚴肅場景和喜劇場面也就成了交錯出現。另外,貝婁還會經常轉換語調,故意誤導讀者。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創作過程中,為了刻意描繪空虛無聊的生活、爾虞我詐的世人和腐化墮落的社會,貝婁大量運用黑色幽默,他能把歷史事件和第三世界狀況巧妙地和黑色幽默融合,通過哲理性思考與平淡的談話并置的方式,很輕巧地將駭人聽聞的場景與輕描淡寫的詼諧結合,同時再輔以適時適當的諷刺性評論,相當出色的黑色幽默效果就造出來了。 例如,小說中談到科雷馬集中營的看守讓囚犯去墳墓里扒下逝世官員的襪子和內褲,以此來交換面包或多活幾天命。這種荒誕的聯系讓讀者難忘,也讓他們在大笑的同時給予受難者同情。再如,肯尼斯將斯特茨維爾監獄的研究和他舅舅目前從事的科學研究相比,居然得出兩個犯人會比科學家帶給人更多的刺激的結論,但接下來他說在美國當一名學者有多榮耀和了不起,這種把哲學思考與恐怖場景并置的手法,在閱讀中很容易激起讀者矛盾的反應,而作者就在這些稀奇古怪的情境中給作品抹上了黑色幽默的氛圍,讓讀者驚奇的同時也在為這個社會感到悲哀。#p#分頁標題#e# 全文中使用黑色最高潮的的地方是作者對第三世界悲慘狀況的描述,肯尼斯去拜訪他的母親,此刻正在東非做傳教士的母親憂慮滿懷地向肯尼斯傾訴親眼所見的兇案和索馬里難民的悲慘、難民營的擁擠不堪、埃塞俄比亞民兵的強奸與暴行。而肯尼斯的評論卻不著邊際,甚至拿來開玩笑。母子對話的內容是饑寒交迫、處于生死邊緣的難民,而他們倆卻在大嚼著高檔食品。貝婁的巧妙安排,將痛苦的現實與可笑的哲學評論交錯,反映了肯尼斯的無奈。黑色幽默產生于把高貴的理想與卑微的現實混淆并置。將不同的思想與不同程度的諷刺嫻熟聯系,在恐怖與鬧劇的轉換中使讀者發出笑聲,從歷史的角度看,小說反映更多的是現代社會精神世界轉換過程中遭遇的困惑,或者說是這段時間經歷的精神荒原,通過各種諷刺技巧的嫻熟運用,作者讓讀者在這些繪聲繪色的敘述中,不經意地使人看到人間殘酷的爾虞我詐,善良與同情在此刻顯得是那么蒼白無力,那么無濟于事。 四借用夸張的諷刺,刺痛骯臟的政治小說中另一個后現代主義的表現就是使用夸張的諷刺,作品中的諷刺界定于后現代主義風格的原因在于:諷刺傳統上往往會以某個情景、事件或人物為中心,并且傳統的諷刺到最后總會給這個社會留下一些希望。但在貝婁的作品中,諷刺是沒有中心的。他在作品中通盤諷刺著中西部和那里人們的一切,而且因為這種諷刺是隨心所欲的,也是包羅萬象的,所以就很難給這些諷刺界定一個清晰的中心。作品中對西部生活和城市政治的諷刺顯得是那么輕車熟路,并且對于不同的主題貝婁會采用不同的語調和氛圍加以諷刺。對于中西部的生活,貝婁的語氣是親切輕松的,并且經常伴以調侃和善意的玩笑;但一旦說到四處泛濫的政治腐敗時,他的語調立刻變得尖酸刻薄,并且不留情面。肯尼斯出生在巴黎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但當他一旦真正移居美國后,卻發現身邊圍繞的都是些來自亞洲、非洲、中東、中美和南美的人,因此肯尼斯的內心中升起一些失落,通過這種感覺的描寫,作者其實是想透露出異化感和邊緣感,是對在美國的歐洲人的無根感的詼諧諷刺。在作者把中西部人嘲笑完以后,又開始對城市政治生活里的腐敗進行更為深刻的挖苦,他把腐敗的政府組織還有無能的官員挖苦得體無完膚“,政府不再是將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充斥著欺詐之徒的骯臟場所,此刻社會習俗不僅認可了貪污和不知廉恥的撒謊,而且對其還贊賞有加”。他在小說中細致入微地描述了犯罪和政客之間編織成的犯罪網絡。如肯尼斯的舅公僅僅在一次房地產交易中,就輕松地從其母親那里騙取上百萬元,而且哈羅德還不斷地吹噓他那些狐朋狗友,那些為他服務的銀行家、法官和政府官員是如何骯臟無恥地和他沆瀣一氣。 另外,作者的另外一個后現代主義諷刺對象就是所謂的權威人物,整篇小說中自始至終沒有出現正面人物,多諾萬•斯圖爾特作為州長考慮的不是民眾利益,而是一心只為自己謀取利益,雖然他負責聯邦地區所有的大陪審團,但他卻很少去主動履行職責,因此受到社會和公眾的廣泛批評,為了恢復他的聲望,斯圖爾特決定主持一個關于強奸犯的假釋聽證會,從而向大眾證明自己也在執行公務,可是整場聽證會他卻完全是在作秀,伴隨其華麗言辭的背后的是他對事實的無知和毫不關心,他把大把的時間花費在追問強奸細節上,甚至糾纏于受害人丹娜當年遭強奸時穿過的內褲的顏色和款式,卻對兇手強奸的動機毫不知情,甚至是有意掩飾。市政府大廈出出進進的全是些十惡不赦的家伙,大陪審團可以從中任意選擇目標。作者在描寫中加入了幽默元素,使這些辛辣的諷刺變得滑稽可笑,他創造幽默場景并不是為了提供解決問題的出路,而僅僅是讓讀者身臨其境,饒有興趣地看清楚20世紀城市中的政治腐敗。 結語 貝婁通過他筆下的主人公尋找生活的快樂和意義,但不幸的是,卻無法和現實世界達成妥協。在這部小說中,作者通過對黑色幽默以及夸張諷刺的巧妙運用表達出了對人類的墮落和世界無奈的憤怒。因此,薩拉科恩是這樣評價貝婁的“:他的作品雖然沒有揭示出生活的奧秘,但作品中的喜劇手法和對話藝術運用,使得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感覺更加敏感,增強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