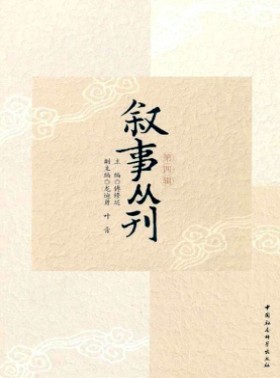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項狄傳的敘事學(xué),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對于英國十八世紀著名的感傷主義作家勞倫斯•斯特恩(1713—1768)及其風(fēng)格獨特的小說作品《項狄傳》,我國出版的英國文學(xué)史教材一般都會做一些介紹,然后便嘎然而止。誠如劉意青所言:“斯特恩在過去五十年我國的文學(xué)教學(xué)中基本上被除了名,但作為一個敘事技巧上別具一格又先于時代的小說家,他理應(yīng)獲得一席地位。”[1]劉意青的專著初版于2000年,不僅總結(jié)了斯特恩在我國文學(xué)教學(xué)中的地位,也總結(jié)了他在我國外國文學(xué)研究中所處的狀況。這種狀況直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才開始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在其專著《英美意識流小說》中,李維屏追溯了英美意識流小說的淵源,指出斯特恩的《項狄傳》“將有關(guān)主人公社會經(jīng)歷的描寫降到了最低程度,而是以極大的篇幅來展示其豐富多彩、變化多端的感性生活”,[2]認為“這種標新立異的表現(xiàn)手法以及他強調(diào)感性的創(chuàng)作原則使現(xiàn)代意識流作家受到了深刻的啟迪”。[3] 二十一世紀雖然才走過了十一個年頭,卻已經(jīng)目睹了我國《項狄傳》研究史上的第一次繁榮,值得總結(jié)一番。一方面,有關(guān)十八世紀英國小說研究的專著不斷問世,其中不少都涉及了斯特恩及其《項狄傳》。另一方面,專門研究《項狄傳》的期刊文章和碩士、博士學(xué)位論文也不斷涌現(xiàn),不僅數(shù)量可觀,深度和廣度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期刊文章中,李維屏、楊理達(2002)的《英國第一部實驗小說〈項狄傳〉評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不僅全面介紹了這部小說,而且“深入探討這部小說中標新立異的結(jié)構(gòu)形式、別具一格的敘述手法以及作者對時間問題的巧妙處理”。[4]更令人振奮的是,2006年4月,《項狄傳》的第一個漢譯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譯者是蘭州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的退休教授李登科,筆名蒲隆。該譯本的出版發(fā)行,至少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國內(nèi)敘述學(xué)研究方興未艾,《項狄傳》在這種氣候下得以出版,真有點‘應(yīng)運而生’的味道”[5];二是因為《項狄傳》確實結(jié)構(gòu)混亂復(fù)雜,語言晦澀難懂,該譯本實際上是填補了一個空白。雖然閱讀譯本不能代替閱讀原著,但誠如譯者引用孟加拉諺語所言:“有個瞎叔叔總比沒有強。”[6] 就研究的視角而言,不一而足,有宗教的、哲學(xué)的、歷史文化的、女性主義的,也有敘事學(xué)的。另外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和體裁理論也被用來解讀《項狄傳》。近來,有兩篇新作探討《項狄傳》中的游戲精神。就專題研究而言,李維屏教授的《英國小說人物史》專節(jié)討論了斯特恩的小說人物,指出他們“無不執(zhí)著和認真,是理性與感傷的忠實踐行者”(李維屏,2008:131)。相比較而言,對《項狄傳》的敘事學(xué)研究最為興盛,正應(yīng)了蒲隆在《譯后記》里的預(yù)測。[7] 一、宗教與哲學(xué)研究 斯特恩家族不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而是和宗教有著很深的聯(lián)系。1733年,勞倫斯•斯特恩作為一名減費生到劍橋大學(xué)的基督學(xué)院就讀。1737年,他從這里畢業(yè)并獲得學(xué)士學(xué)位,1740年又獲得碩士學(xué)位。而在他之前,家族里已有三個成員在這里上過學(xué):堂兄理查德、叔叔雅克和曾祖父理查德•斯特恩。其中以他的曾祖父最為著名,曾任約克大主教和基督學(xué)院的院長。他的叔叔雅克當(dāng)時正擔(dān)任克里夫蘭副主教和約克教堂贊美詩領(lǐng)唱,他便借助叔叔的影響進了教會,于1738年成為一名牧師。他在牧師的職位上干了21年后,才動手寫他的不朽著作《項狄傳》。所有這一切都為探索《項狄傳》的宗教主題奠定了基礎(chǔ)。杜維平(2004)認為,《項狄傳》“不僅僅是玩笑”,而是有兩個明確的宗教主題:忍耐和愛。[8]杜文指出,項狄一家承受的是約伯式的痛苦,而痛苦的典型代表就是特里斯舛•項狄本人:他的不幸始于十月懷胎之前,出生時被產(chǎn)鉗夾斷了鼻梁,被起了他父親認為最為不幸的名字,五歲時被掉下來的窗框砸傷了小男孩的命根。那么,面對這么多的痛苦,人應(yīng)該怎么辦呢?答案便是忍耐,而忍耐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者則是沃爾特•項狄。小說家對于發(fā)生在特里斯舛身上的那些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的過程敘述得比較簡略,但對于他父親的痛苦程度和承受痛苦的方式的渲染則濃墨重染,有的甚至長達幾個章節(jié)四十多頁。更可甚者,沃爾特•項狄不僅要承受次子特里斯舛的一連串不幸所帶來的痛苦,還要承受長子博比的死亡所帶來的痛苦,從而使他“經(jīng)歷了從起初被動地忍受到最后笑對痛苦這一忍耐方式的轉(zhuǎn)變,他學(xué)會了忍耐。”[9] 所以,“嚴格地說,《項狄傳》的玩笑和游戲是為斯特恩宣揚基督教教義服務(wù)的,而他在這部作品中所宣揚的教義則是學(xué)會忍耐。”[10]杜文還指出,《項狄傳》的另一個宗教主題是“溫情:對人類的愛。”[11]小說不僅洋溢著人間的溫情,而且通過強調(diào)這種溫情來對抗當(dāng)時流行的唯我論,反對理性,“通過對人類溫柔情感的強調(diào)來確立他所信奉的宗教—英國圣公會—在宗教中的地位。”[12]從哲學(xué)的角度研究《項狄傳》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斯特恩在《項狄傳》中七次提到英國著名的經(jīng)驗主義哲學(xué)家約翰•洛克的名字,并涉及他的著作《人類理解論》及其核心概念觀念聯(lián)想、時間的延續(xù)等。杜維平、金萬峰(2003)認為意義是《項狄傳》的一個哲學(xué)主題,即《項狄傳》是“關(guān)于意義的哲學(xué)思考。”[13]具體來講,斯特恩通過這部小說完成了兩項哲學(xué)任務(wù):第一,質(zhì)疑理性和語言在人們獲得意義的過程中的作用,強調(diào)意義的源泉是“構(gòu)成感性內(nèi)容的東西,如情感、想象、動作等。”[14]第二,試圖把故事作為講解、闡釋哲學(xué)思想的一種形式,并對洛克的《人類理解論》所包含的哲學(xué)思想進行了“藝術(shù)性的闡釋”。 二、歷史文化及女性主義研究 以推崇理性著稱的啟蒙運動是十八世紀的主流思想,更有科學(xué)和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其助陣,矛頭直接指向?qū)M狹隘的宗教勢力。[15]就英國而言,十八世紀也是一個思想家輩出的時代,前期有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洛克、牛頓、莎夫茨伯里和曼德維爾,中后期則有休謨、亞當(dāng)•斯密、伯克等。受這種激流和巨變的影響,十八世紀英國文學(xué)具有“多樣化和過渡性質(zhì)”[16],小說的文體形式和功用也處于探索階段。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有些學(xué)者便從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項狄傳》,探索該小說形式在社會變化中的適應(yīng)與變遷。黃梅、顏靜蘭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qū)者,后有劉戈、曹波等學(xué)者繼續(xù)探討。#p#分頁標題#e# 黃梅(2002;2003)詳細地介紹了《項狄傳》的敘述特點和文體風(fēng)格,并結(jié)合歷史文化語境、作者生平以及十八世紀的文學(xué)傳統(tǒng)來分析其敘事實驗和文本游戲,指出“如果我們更多地把斯特恩的作品放到當(dāng)時的文化情境中閱讀,便可以意識到,盡管斯特恩的敘事實驗和文體游戲包含思想及藝術(shù)上的探索,但是并不構(gòu)成根本的‘挑戰(zhàn)’,它們在本質(zhì)上只是時代主流的一種變調(diào),是特權(quán)者的炫示和自娛”[17],“反映了小說在十八世紀里作為尚未定型的文類所擁有的巨大的可塑性和相對寬闊的空間……體現(xiàn)了在當(dāng)時調(diào)整階級關(guān)系的社會格局中,仍處在成長與融合時期的統(tǒng)治階級思想文化的豐厚、駁雜和柔韌。”[18]顏靜蘭(2003)以情節(jié)處理、人物塑造、敘述模式、寫作手法為切入點進行探討,“分析了作者試圖通過凌亂無序的情節(jié)敘述反映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紛亂無序,并渴望讓讀者擺脫故事情節(jié)來獲取閱讀樂趣的創(chuàng)作嘗試”[19],指出“《項狄傳》對小說藝術(shù)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并對小說的觀念進行了拓展與更新,豐富和補充了十八世紀剛剛興起的小說文學(xué)式樣”[20]。顏靜蘭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別指出了以下幾點。第一,“斯特恩的創(chuàng)作和費爾丁一樣是遵循了一定的小說創(chuàng)作的系統(tǒng)理論”;[21]第二,斯特恩本人認為,自己的小說和費爾丁等人的傳統(tǒng)小說不一樣是體現(xiàn)了小說的進步,是對以費爾丁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挑戰(zhàn);第三,“斯特恩自己則認為他的作品首尾一致,具有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22]對于顏靜蘭這里所說的第三點,斯特恩在《項狄傳》第一卷第二十二章里的原話如下:“Inaword,myworkisdigressive,anditisprogressivetoo,—andatthesametime.”[23]翻譯過來便是:“簡而言之,我的作品是東拉西扯的,它也是循序漸進的,———而且是在同時進行的。”[24] 劉戈(2005)順著前面兩位學(xué)者的思路繼續(xù)挖掘,著重探討了《項狄傳》與十八世紀英國的小說傳統(tǒng),指出斯特恩在《項狄傳》中所使用的敘事策略并不是與當(dāng)時的主流敘事模式徹底地分道揚鑣,《項狄傳》也沒有違背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現(xiàn)實主義基調(diào),也不像其表面上顯示的那樣與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格格不入;相反,斯特恩突出對人物及心理意識的刻畫,“同以心理描寫著稱的理查遜走得更近”[25];斯特恩“尊奉的依然是笛福、理查遜和菲爾丁等人確立的寫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只是他做得更徹底,以致表面看來變成了一種悖逆”[26];斯特恩“真正嘲弄的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道德家們?yōu)榱送怀龅赖轮黝},不惜犧牲作品真實性的假道學(xué)做法。”[27]劉文認為,就上述三個方面而言,《項狄傳》“都表現(xiàn)出其與傳統(tǒng)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28]曹波(2009)的專著探求的是人性,是“對18世紀英國小說人物性格與形象的全面盤點,也是他對當(dāng)時英國的道德風(fēng)尚和價值體系的人文思考”。[29] 曹波認為,沃爾特•項狄是古怪的思想者,托比是古怪的善感者,特里斯舛是古怪的敘事者。他們背離普通大眾的思維方式,“在項狄廳里演繹出了一曲十八世紀反理性、重感情的絕唱,而敘事中的主角特里斯舛則以小說藝術(shù)的形式將父輩們的絕唱推向高潮,展現(xiàn)出種種情感主義的德行。”[30]相比較而言,國內(nèi)對《項狄傳》的女性主義研究甚少,截至目前只發(fā)表了一篇論文,而且還不算是徹底的女性主義研究。王曉培(2010)的論文雖然以小說中男女角色的刻畫和性別特點之間的對立為切入點,但其結(jié)論卻認為這種對立折射出了作者對當(dāng)時“英國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抗衡的看法,展現(xiàn)了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大眾的情感與思想,同時也暗示了作者的意識傾向和道德判斷。”[31]究其本質(zhì),這仍然是歷史文化研究而已。 三、敘事學(xué)研究 相比較而言,國內(nèi)學(xué)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從敘事學(xué)的角度來分析《項狄傳》的結(jié)構(gòu)特點,并試圖予以解釋。陳浩東(2000)、李維屏(2002)、黃梅(2002)、顏靜蘭(2003)、韓加明(2003)、申丹(2005)、徐俊芳(2006)、朱妮婭(2006)、李春燕(2007)、李紅(2007;2008)、李艷芳(2007)、呂娟霞(2007)、易志華(2009)、賴騫宇(2009a;2009b)、張揚(2009)等學(xué)者都不同程度地探討了《項狄傳》敘事結(jié)構(gòu)上的實驗性和現(xiàn)代主義特點及其對二十世紀意識流小說家的深遠影響。在追溯斯特恩對于敘事結(jié)構(gòu)的獨特認識的根源時,雖然有少數(shù)學(xué)者沿用傳統(tǒng)的敘事學(xué)或者烏托邦視角,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把目光投向了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及其核心思想觀念聯(lián)想理論。那么,洛克的觀念聯(lián)想理論究竟是如何影響斯特恩及其小說《項狄傳》的呢?綜合起來看,學(xué)者們給出三種不同的解釋:直接使用、批判性繼承、直接影響。 韓加明(2003)指出,“真正構(gòu)成《項狄傳》特殊的整一性是什么呢?是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提出的‘觀念聯(lián)想’……換言之,斯特恩提出并在《項狄傳》實踐的小說敘事原則就是非理性的‘觀念聯(lián)想’。”[32]徐俊芳(2006)的碩士學(xué)位論文專章論述斯特恩對洛克思想的批判性繼承,認定“對洛克思想的批判性繼承是斯特恩作品創(chuàng)作哲學(xué)的內(nèi)在根源”,[33]指出“斯特恩把洛克的聯(lián)想主義思想用于小說創(chuàng)作技巧”,[34]而且“這種聯(lián)想已經(jīng)滲透到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小說中一個關(guān)鍵的銜接點。”[35]陳浩東(2000)確信,“洛克對斯泰恩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36]而“洛克對斯泰恩的直接影響與斯泰恩小說的成功使洛克的理論獲得廣泛的接受,這種作用與反作用使得對文學(xué)的研究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和更高的視界。”[37]李春燕(2007)和呂娟霞(2007)在其碩士學(xué)位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和陳浩東的基本相似,這里不再贅述。 四、巴赫金狂歡理論和體裁理論的應(yīng)用 截至目前,只有兩位學(xué)者將巴赫金的理論運用于對《項狄傳》的解釋和分析。宋建福(2005)探討了《項狄傳》的狂歡化藝術(shù)。他首先指出,所謂小說藝術(shù)的狂歡,是“有意識地顛覆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各種清規(guī)戒律,把小說的藝術(shù)形式推向了極致,使得小說表現(xiàn)出一種雜蕪混亂、難以卒讀的假象……并不完全否定藝術(shù)傳統(tǒng),而是在保留小說基本要素的前提下以新的異樣形式與之對話,展示小說藝術(shù)的多樣性和內(nèi)在活力,揭示了固化的小說藝術(shù)并不等同于藝術(shù)的全部的樸素道理。”[38]在此理論基礎(chǔ)上,他認為“《項狄傳》在小說技巧的主要方面,如情節(jié)、主題展示、邏輯(旁述)、時間和小說語言方面獨樹一幟,自成體系,明顯具有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本質(zhì)特征;”[39]而且,《項狄傳》的這種狂歡化藝術(shù)形式,“不僅解構(gòu)了以線性邏輯為代表的情節(jié)、主題結(jié)構(gòu)、邏輯(旁述)和時間等內(nèi)在于小說的重要概念,而且也顛覆了外在要素小說語言的理念。”[40]蔡熙(2008)是從巴赫金的體裁詩學(xué)理論出發(fā)來探討斯特恩《項狄傳》文本特征的。他從體裁面具、諷刺性模擬、雜語性和小說性等四個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項狄傳》在文本結(jié)構(gòu)和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指出該小說“顛覆了西方傳統(tǒng)的理性思維模式以及強調(diào)規(guī)范和等級、條理和秩序的詩學(xué)體系,把小說從嚴肅的政治的、道德的、社會的說教模式中解脫出來,注入了輕松、幽默的成份,從而革新了審美趣味。”[41]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蔡熙在行文中特別強調(diào):“在巴赫金那里,狂歡化主要是作為文學(xué)體裁的傳統(tǒng)產(chǎn)生影響的。狂歡化小說最能體現(xiàn)小說體裁的本質(zhì)特征和發(fā)展趨勢。小說是具有顛覆性的體裁,它能利用其修辭和體裁上的異質(zhì)性顛覆居統(tǒng)治地位的體裁觀念。”[42]在論述到諷刺性模擬、雜語性和小說性時,蔡熙繼續(xù)強調(diào)巴赫金對于體裁和狂歡的密切關(guān)系的認識,諸如“在巴赫金看來,狂歡化小說本能地蘊含著諷刺性模擬”[43]、“在巴赫金那里,史詩話語只是單一的作者話語,史詩人物缺乏語言創(chuàng)造性,而小說卻是多風(fēng)格的、雜語的、多聲部的。狂歡化程度較高的小說,即最具小說性的小說是雜語小說。”[44]#p#分頁標題#e# 五、游戲精神 對于斯特恩的游戲態(tài)度,黃梅(2002)早已有所涉及,并指出這種文體游戲并不構(gòu)成根本的“挑戰(zhàn)”,“只是時代主流的一種變調(diào)”而已。[45]崔洋、呂滿金于2010年9月共同發(fā)表兩篇新作,著力探討《項狄傳》中的游戲精神。她們認為,“斯特恩在十八世紀創(chuàng)作出如此奇特的、‘先鋒’的小說,都得益于他的游戲精神。《項狄傳》就是一部游戲之作,為愉悅自己而作,為調(diào)笑他人并游戲他人而作,為消解現(xiàn)實生活的悲苦而作。”[46]至于這種游戲精神的根源,她們認為是“源于他追求快樂的心境”,[47]認為“從創(chuàng)作的動機到創(chuàng)作心態(tài),從創(chuàng)作過程到創(chuàng)作結(jié)果,從創(chuàng)作內(nèi)容到創(chuàng)作形式,斯特恩都像游戲一般自由揮灑,所以才能不落窠臼。”[48] 六、結(jié)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二十一世紀的頭十一年,的確目睹了我國《項狄傳》研究的空前繁盛,不僅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視角和方法不斷拓寬,而且研究成果也更加豐碩,研究深度不斷推進,局面大開,令人欣慰。同時,我們也應(yīng)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項狄傳》研究起步比較晚,整體水平還相對滯后。就研究視角而言,國外學(xué)者對《項狄傳》的闡釋早已涉及互文性、懷疑論、色情傾向、倫理學(xué)、諷刺藝術(shù)、敘事學(xué)、社會文化、政治、視覺藝術(shù)、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等領(lǐng)域,[49]而我國學(xué)者的注意力卻極不平衡,尤其是大多數(shù)學(xué)者糾結(jié)于小說的敘事結(jié)構(gòu),而對其他視角的關(guān)注則相對薄弱,研究成果相對也較少,這一局面亟待克服。就具體的研究視角而言,深度也急需推進。例如,就《項狄傳》的敘事結(jié)構(gòu)和洛克的觀念聯(lián)想理論之間的關(guān)系而言,我國學(xué)者所持的三種觀點都以承認洛克的觀念聯(lián)想理論為前提,實際上沿襲的是詹姆斯•A•沃克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提出的觀點。[50]而在國外,學(xué)者們很早就圍繞沃克的觀點展開了爭論,并且已經(jīng)有學(xué)者指出,觀念聯(lián)想理論(associationofideas)不是洛克所支持的觀點,洛克的心理學(xué)思想中關(guān)于人類認識的真正觀點是觀念串連理論(trainofideas);而且,這一理論對《項狄傳》敘事結(jié)構(gòu)的解釋力更強一些。[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