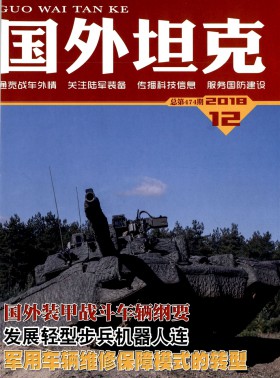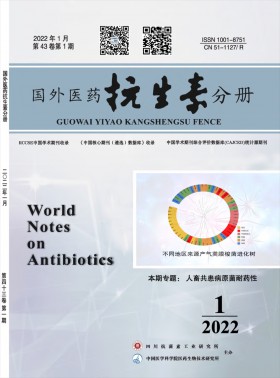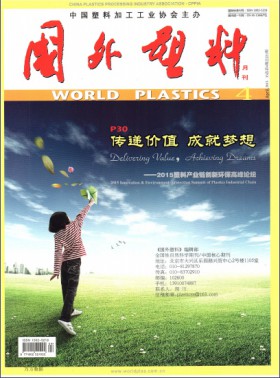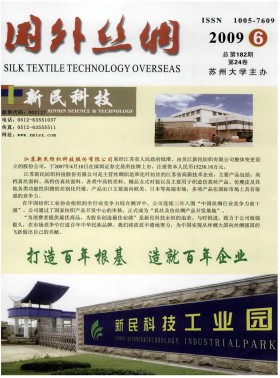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國外詩歌的自然寫作,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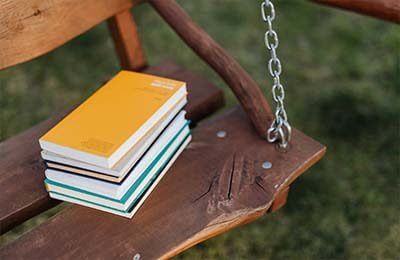
巴特勒說過,英國其他時期產生過一些同樣偉大甚至更偉大的作家,但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像浪漫主義時期這樣涌現這么多確實舉足輕重而又各具特性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和評論家。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歷時并不算長,縱然是從布萊克的《天真之歌》(1789)算起,到1830年即已趨于結束。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們幾乎同時生活在英倫三島,但彼此卻很少唱和追隨,從政治信仰到文學理念,他們往往大相徑庭,彼此悖駁。 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浪漫主義作家們身處這一影響深遠的文學運動之中,反倒對這場運動的性質和意義并無透徹的自覺,這便使得浪漫主義文學并未形成高度一致或基本統一的風格和理念,反而呈現出一派復雜多樣的文學氣象,使后來的文學史家很難對“浪漫主義”做出令人滿意的理論概括。人們意識到,浪漫主義不同于以往的藝術運動或文學流派,如巴洛克風格和洛可可風格,這些流派容易辨別且相對統一;而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則是變動不居、各具特色的,有激越有含蓄,有精致有粗獷,有細膩有豪放,有寫生有寫意……,但是,歷史愈沉淀,我們愈能清晰地感受到這些經歷同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作家們畢竟存在著諸多共性。例如,他們都反抗某種社會羈絆,顛覆某種社會規范,執著地追尋個人的自由和理想。從布萊克到濟慈,這種“熱情奔放而叛逆”的精神匯聚成一道浩大的洪流。 就英國來說,同樣的,盡管浪漫主義詩人彼此間很少相似之處,但只要將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與法國或德國的浪漫主義作家們做一比較,就會使人立刻感受到他們身上共同的英國氣質。追本溯源,這種英國氣質可以歸結到一個明顯的本源上,即生機勃勃的自然主義。勃蘭兌斯在《19世紀文學主流》中指出:“自然主義在英國是如此強大,以致不論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義、華茲華斯的英國國教的正統主義、雪萊的無神論的精神、拜倫的革命的自由主義,還是司各特對以往時代的緬懷,無一不為它所滲透。它影響了每一個作家的個人信用和文學傾向。”[1]的確,似乎惟有自然主義,才構成了英國詩人氣質中普遍的、核心的藝術因素,他們對鄉村、大海、花草和一切動物的熱愛使得他們成為大自然的觀察者、愛好者、崇拜者和謳歌者。 一、田園風光之上的冥想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有大量的田園生活描寫。在詩人們筆下,無論是清新恬淡的自然,還是絢爛綺麗的自然,無不透露出靈與慧、現實與虛幻相交織的境象。詩人的自然寫作并非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觀物、以景抒情、以物觀我、以象寓理,在自然中尋求智慧與美感、力量與慰藉,甚至世間的真理。至于借自然之物言情述志,更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自然觀的真實流露。“寫平凡而表達不平凡,寫社會和自然環境而表達人物內心世界,寫客觀同時表達主觀的情況,這是華茲華斯在藝術上的造詣”[2],也是整個浪漫主義詩人的寫照。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并不滿足于翔實地描繪自然、展現自然,而是將大自然當作實現夢想的天堂,凈化靈魂的樂土。他們是真正的大自然的愛好者,愛好到狂熱的程度。由于這一特點,他們的創作盡管旨趣不同,如布萊克和拜倫作有許多“托自然而說理”的詩篇,而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和濟慈則有更多“托自然而思理”的華美篇章,但他們在作品的審美意境上無不在自然上下工夫,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縱然描述最簡樸的鄉間日常生活,也能詩意盎然;縱然描寫最虛幻的夢境天堂,也能真實得歷歷在目,躍然紙上。 若說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是在用詩歌描繪自然,莫如說他們是生活在詩意的自然中。柯勒律治說過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我們得的只能是我們給的,大自然只存在我們自己的生活里。”華茲華斯這位描寫日常田園生活的大師便以自己的詩歌語言證實了這一道理,也演繹出美的神話。在《早春即興》中,詩人似乎把自己的神經觸角伸展到整個自然中去了,“當我倚坐在灌木叢中,我聽見一千種柔和的音響;愉快的遐想,甜美的心境竟把縷縷哀思送到我的心上。”可見,在自然的懷抱中,詩人是在用心靈感悟自然,用熱情探尋美的存在,用生命記錄自由之歌。 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賦予生命和情感,有著豐富的象征意義。如布萊克的《向日葵》,“啊,向日葵!懷著對時間的厭倦,整天數著太陽的腳步,它尋求甜蜜而金色的天邊———倦旅的旅途在那兒結束”。向日葵,暗喻了人類的欲望,看似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實則令人疲倦。那是多么無奈而又無盡的俗望啊。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詩人還常常將自己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如華茲華斯的《詠水仙》,“我好似一朵孤獨的流云,高高地飄游在山谷之上。”或借自然之物闡述其人生體悟,如布萊克《天真的預示》,“一顆沙里看出一個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無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剎那間收藏。”這些詩歌或贊譽大自然的神秘與美麗,或將自然視作心靈的慰藉。在寫自然的幽美和雄偉時,也寫自己內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似乎只有在親近自然時,詩人才能感受到心靈的平靜和精神的愉悅,才能靈感泉涌直至神靈附體之境。由此可見,詩歌中的自然,乃是詩人心中的自然;詩人在自然中汲取心靈的慰藉,在對自然的崇尚中追尋夢想的天堂。 自然、生活、美和自由,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始終是渾然一體、相互滲透的。我們甚至無法分辨是自然賦予了詩人以靈魂,還是詩人賦予了自然以生命。在這些詩篇中,既有瑰麗奇異的想象世界,也閃現著真實生動的現實生活圖景,不論是平鋪直敘或跌宕起伏地講述故事,還是激情澎湃或黯然神傷地抒發情感,自然的形象始終都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自然語境下的人性思考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另一個特點是詩人們對人性的思考,對人的自然性的關注。他們并不是消極遁世地描摹大自然,而是回歸自然,探索隱匿在近代工業文明陰影背后的大自然的價值。詩人們從未放棄過在自然的語境下對人、社會和自然關系的思考。雖然從創作機制來說,自然是激發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進行思考的動因,詩歌是由感悟自然之物而起,但實則詩人們關注的往往是人類的核心經驗與生存本質。#p#分頁標題#e#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期望的是通過重返自然來解決工業社會中的種種問題,平息商品社會中人類的騷動,甚至凈化人類的心靈。當詩人們在紛繁的社會領域找不到出路時,英國豐富的自然世界和美麗的田園風光便成了他們最樂于憑借,并寄予無限希望的解決現世問題的法寶。正是這種對人的自然性的關注和期冀,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自然描寫生活化;這些詩歌通常語言簡樸,結構簡單,內容平實但卻充滿摯情而且清新自然。也正是這種試圖重返自然、關注自然的理念,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社會現狀描寫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敘事視角。這些故事往往娓娓道來,既沒有聲嘶力竭的抨擊,也沒有深邃精辟的評論,卻能發人深思,痛人肺腑,使人們不得不思考工業文明帶給人類的種種危機和隱患,以及所造成的人性缺失。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從自然之美出發,探索和思考人的社會性和自然性的本質和關系,這是英國浪漫主義詩篇歷久而彌新的魅力所在。他們將生態的自然、物質的自然擴展到人性的自然,極大地拓展了藝術表現空間。浪漫主義詩人在處理自然性和社會性的關系時,他們更愿意把社會性納入自然性中,透過自然的視角觀察評述人類社會的本質。如布萊克的《掃煙囪孩子》,華茲華斯筆下的《孤獨的割麥女》,彭斯《兩只狗》中的莊稼人,一次次地叩響人們心靈的良知之門,引發出無數人的憤懣與哀傷。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歌頌的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自然性,也包括人性中存在的自然性,這使得浪漫主義詩歌的自然描寫不僅充滿了人格魅力,而且觸及到人性的深邃內涵,揭發出社會生活的嚴酷真相。這類詩歌往往體現著詩人們用詩歌重塑自然的努力,傳達出詩人們揮斥生活的全部熱情與信念。如彭斯在《不管那一套》中大聲唱出:“有沒有人,為了正大光明的貧窮,而垂頭喪氣,挺不起腰———,這種怯懦的奴才,我們不齒他!”當許許多多的人完全接受了普遍存在的社會價值中的財富尺度概念時,人們似乎已經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這種財富尺度的能力。的確,當人們過多地關注自身的社會性時,似乎已經忘記了人類的自然性。人類將生存需求和金錢扭曲地連接在一起,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遺忘了幸福的本質,而困頓于金錢的枷鎖之中。彭斯大聲疾呼,他所要喚醒的正是漸漸被人們所遺忘的人之自然性。 正是這種對人的自然性的認同與關注,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自然寫作更深邃、更宏大、更質樸。人不僅經濟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會性的存在,人同時也是物質性的存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從心出發,他們是真正的自然主義者,觀察大自然,思考社會問題。他們不局限于現實社會的影響和羈絆,在詩歌中追求真理,謳歌人性的坦蕩、豁達和真實。 三、浪漫主義詩歌之生態批評 回到當下的社會,不難看出,正是由于處在生態危機愈演愈烈的時代,“生態文明”前所未有地受到了人類的關注,才出現了“生態學”視角下的文學批評理論。文學生態學為浪漫主義詩歌的自然寫作的解讀,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文學和生態學的聯系何在?文學研究能為世界生態系統的發展做些什么?生態批評家喬納森•萊文指出:“我們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獨一無二的方式。不研究這些,我們便無法深刻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而只能表達一些膚淺的憂慮。”生態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3]3生態思想家唐納德•沃斯特也明確指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的機能,而在于我們的倫理系統的作用。要渡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對自然的影響。……研究生態與文化關系的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雖然不能直接推動文化變革,但卻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文化變革的前提。”[3]4 文學生態學的發生緣起于生態危機的客觀要求,它“大致涵蓋了3個方向:文化與自然的關系;以生態視角對小說、戲劇進行研究;環境文學的研究。”[4]27文學生態學的發展必將召喚出新的文學內部研究,包括對文學作品中的自然環境描寫和文學作品中承載的自然觀進行深入細致的闡釋,簡單說就是要研究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寫作。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寫作,既包括自然描寫,也包括人的情感、天性等自然性的描寫,這種內在于人的自然主要指人相對獨立于社會經濟、政治利益等因素影響的自然屬性。事實表明,以此為對象的自然寫作正是以某種自覺程度的自然觀為基礎,對自然予以描寫、說明并表達人的自然感受與價值意識的寫作活動,包括文學創作和其他自然寫生。 英國,作為工業文明的策源地,既是人類和自然之間依附關系被徹底割裂的起始處,也是現代生態危機的體現者。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正處在這一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的前沿,自然也是最先目睹人類生態危機的見證者。雖然受時代條件的限制,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生態意識”,但他們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人類社會生活中自然的缺失,并不乏余力地歌頌自然,重申自然對于人類的價值。 自然是人類生存的依托和靈魂的歸宿,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從未遺忘這一點。其詩歌中的自然主題既是大自然的描摹,也是作者心靈的流露;既是在自然景觀之上的冥思,也是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結晶,因而得以流傳至今,沉淀為現代的生態意識。人類對自然的強烈的依附感原本來自早期記憶,那時人類從自然中獲得最可憐但卻最珍貴的生存資源,維持了自身的存在和自我評價。而工業革命帶給人類社會翻天覆地的巨變,也猛烈而徹底地動搖了這個社會的自然根基。時至今日,各種非人道勢力裹挾著科技力量,在使人類獲得對自然的實際支配權的同時,進而發展到了桎梏人類自由和人類良知的程度。人類在狂歡中甚至呈現出遺忘和自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勢頭。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重溫英國浪漫主義創作的自然主題,不禁得出這樣的結論:生態意識固然是時代的產物,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雖未具備明確的生態意識和人類存在的憂患意識,但不可否認,他們熱愛自然,敬畏自然,在思索人類命運和人類社會、歷史問題時,格外注重人類和自然的聯系,將其置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自然帶給人類怎樣的命運,人類注定要和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一致的認知。#p#分頁標題#e# 時至今日,現實逼迫人們關注環境,生態意識迫使人們重新審視文學作品中的自然描寫。人類業已開始關注這些自然寫作的現實生態價值(因而才導致英國浪漫主義創作受到世界各國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同時在努力建設基于生態意識的新的文學評價標準。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以敏銳的視角,關注工業革命和商品經濟的弊端,轉而回歸大自然,汲取自然的力量,重新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構成了我們今天能夠倚重的思想和藝術資源的一部分。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自然寫作傳統既體現出歷史性和繼承性,又彰顯出前瞻性和超越性,為現代生態批評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從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思潮,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再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甚至包括19世紀的科學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潮,英國社會的每一重大思想運動和實踐活動,都閃現著自然主義創作的影子。”[5]英國社會的這一濃厚的自然主義傳統無疑在現代文學藝術以及一般社會文化的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英國浪漫主義的興起是種種歷史境況使然;回歸自然,是詩人們在時代境遇下必然做出的抉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不是生態文學的開創者,但他們至少可以被看作是生態文學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