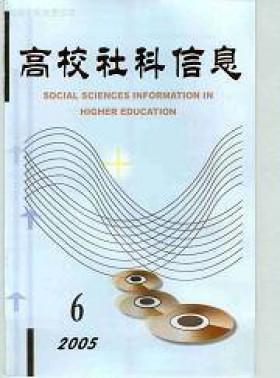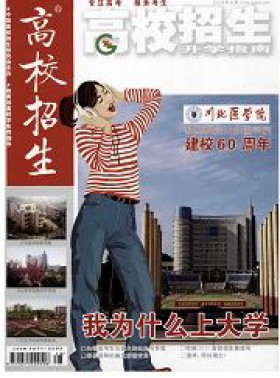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高校外國(guó)文學(xué)教育的難點(diǎn)與對(duì)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lái)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我國(guó)改革開(kāi)放和世界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國(guó)文學(xué)作為高校中文專業(yè)讓學(xué)生了解國(guó)外文學(xué)與文化的一門重要課程,彰顯著時(shí)代意義。 1998年我國(guó)教育部將中文師范專業(yè)的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合并為一個(gè)學(xué)科,取代了以往的外國(guó)文學(xué),這給我國(guó)高校中文專業(yè)的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帶來(lái)了諸多挑戰(zhàn)。但是面對(duì)這種挑戰(zhàn),一些高校本科的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理念沒(méi)有與之相適應(yīng)地發(fā)生轉(zhuǎn)變,這勢(shì)必影響高校中文專業(yè)的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效果,也不利于高校高素質(zhì)人才的培養(yǎng)。這些問(wèn)題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一、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的“比較文學(xué)”意識(shí)欠缺 現(xiàn)在高校的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工作者都能意識(shí)到外國(guó)文學(xué)已經(jīng)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國(guó)外文學(xué)或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而是一個(gè)具有“比較文學(xué)”性質(zhì)的新型課程,這要求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不能局限于民族文學(xué)的范圍來(lái)思考文學(xué)發(fā)展問(wèn)題,要面對(duì)學(xué)科“開(kāi)放性和國(guó)際性”的新要求,改變傳統(tǒng)教學(xué)以時(shí)代背景、作家介紹、作品分析的教學(xué)思路,在“比較”中初步確立學(xué)生對(duì)世界文學(xué)的總體認(rèn)識(shí)。但是在傳統(tǒng)教學(xué)的慣性思維作用下,教師往往不能認(rèn)清外國(guó)文學(xué)的學(xué)科屬性,在無(wú)意中漠視“比較文學(xué)”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的存在,造成了教學(xué)中缺乏“比較文學(xué)”意識(shí)。其主要表現(xiàn)為: (一)漠視一種文藝思潮下國(guó)別文學(xué)和作家個(gè)性的差異。目前,國(guó)內(nèi)外國(guó)文學(xué)史教材的編寫多從一種文藝思潮出發(fā),再選擇不同國(guó)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這些作家、作品往往會(huì)因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個(gè)人經(jīng)歷等因素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但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卻總以文藝思想的普遍性代替文學(xué)個(gè)性的差異性,抹殺了在一種文藝思潮中不同作家、作品的文學(xué)表現(xiàn)形式和作品內(nèi)涵的豐富性。在外國(guó)文學(xué)史上,每一種文藝/文學(xué)思潮的總結(jié)都是對(duì)同一時(shí)期的共性說(shuō)明,但是共性在每個(gè)國(guó)家、每個(gè)作家身上卻并不等于千人一面,正是他們各自的文學(xué)特色才使每一種文藝思潮的表現(xiàn)形態(tài)豐富多彩。在目前外國(guó)文學(xué)的教學(xué)過(guò)程中,教師要么搞一刀切,以統(tǒng)一性代替差異性;要么根據(jù)教材以各自為政的方法來(lái)講解每一個(gè)作家,缺乏作家與作家、國(guó)與國(guó)之間文學(xué)的比較,造成學(xué)生對(duì)作家或作品之間差異性認(rèn)識(shí)不足。 比如19世紀(jì)歐洲的浪漫主義文學(xué),這一文藝思潮的特征就是主張個(gè)人的感情抒發(fā)和主觀化描寫,文學(xué)史一般會(huì)選擇華茲華斯、拜倫、雨果、惠特曼等作家或詩(shī)人,他們的共同特征就是對(duì)人的感情非常重視,但在此基礎(chǔ)上,每個(gè)作家的文學(xué)表現(xiàn)方式卻存在著差異。華茲華斯追尋伊甸園式自然里存在的完美人性,歌頌和大自然一致的人類質(zhì)樸感情;而拜倫對(duì)“自我”的描繪卻具有強(qiáng)烈的超越精神和生命意志,他蔑視一切法則,追求自由與解放,帶有極端人個(gè)主義的傾向,這使他成為了歐洲浪漫主義的高峰。 [1]雨果則激情與平和并舉,在博愛(ài)中顯示著深沉;而遠(yuǎn)在大洋彼岸的惠特曼,為了建立美國(guó)的文學(xué)話語(yǔ),徹底擺脫殖民地的文學(xué)統(tǒng)治,熱情地謳歌了美利堅(jiān)民族的自然和人民,在物質(zhì)和精神上均給予了人無(wú)限的贊美,以“靈與肉”的統(tǒng)一作為完美人性,把宗教的束縛置于一旁,以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力為最終旨?xì)w。[2] 以上只是對(duì)19世紀(jì)浪漫主義文學(xué)粗淺的分析,旨在說(shuō)明要用比較文學(xué)的視野來(lái)分析一種文藝思潮下國(guó)別文學(xué)以及作家之間的個(gè)性差異,這不僅在跨文明的語(yǔ)境中幫助學(xué)生加深對(duì)浪漫主義的認(rèn)識(shí),也有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對(duì)文學(xué)的分析能力。而這一切,在當(dāng)下中文專業(y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的課堂上卻并不多見(jiàn),更多地是對(duì)作家的單一性介紹,其結(jié)果不過(guò)是讓學(xué)生機(jī)械地記住了作家和作品的名字。 (二)缺乏與中國(guó)文學(xué)的對(duì)話、碰撞與交感意識(shí)。從當(dāng)今世界的格局來(lái)看,西方國(guó)家在經(jīng)濟(jì)和文化領(lǐng)域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文化滲透和文化侵略成為了國(guó)與國(guó)之間的暗戰(zhàn)。高校中文專業(yè)的外國(guó)文學(xué)教師也是西方文化的宣傳者,這就容易犯文學(xué)視閾過(guò)于單一的毛病。教師在課堂上對(duì)外國(guó)作家和作品口若懸河,而忽視了中國(guó)文學(xué)也是世界文學(xué)的一部分。缺乏中國(guó)一極的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不是完整的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3] 所以在外國(guó)文學(xué)課堂中引入比較意識(shí),增強(qiáng)與中國(guó)文學(xué)的碰撞,體會(huì)審美的多元性,對(duì)于探索文學(xué)的實(shí)質(zhì),提高人文素養(yǎng)是非常重要的。中國(guó)學(xué)者方漢文就認(rèn)為:在全球化的時(shí)代,無(wú)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的研究主體,都必須改換自己的思維方式,采用一種比較性思維方式,即承認(rèn)主體間性,理解他人……從理性與感性的辯證合一,從西方思維與東方思維的互相契合來(lái)研究文學(xué)。[4] 如何通過(guò)中西文學(xué)比較建立正確的文學(xué)觀念,是一個(gè)不能忽視的問(wèn)題。 中國(guó)文學(xué)源遠(yuǎn)流長(zhǎng),有著與西方文學(xué)不同的文化特質(zhì),但在審美之維上也不乏相似之處;另外,我國(guó)“五四”以來(lái)的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頗深,也不乏顯現(xiàn)出“世界性”因素(陳思和)。而外國(guó)文學(xué)課程一般安排在中文專業(yè)二、三年級(jí)開(kāi)設(shè),學(xué)生已有一定的中國(guó)文學(xué)基礎(chǔ)知識(shí),在外國(guó)文學(xué)史課堂教學(xué)的基礎(chǔ)上,完全可以將兩者置于世界文學(xué)(文化)的背景下進(jìn)行新的闡釋,這樣更能顯示出各自的特色,也能在超越時(shí)空的文學(xué)交流中增強(qiáng)學(xué)生對(duì)中西文學(xué)異質(zhì)性和同一性的認(rèn)識(shí)。比如在講到自然詩(shī)人華茲華斯時(shí),可以與陶淵明作一個(gè)對(duì)比。華茲華斯將人與自然割裂開(kāi)來(lái),認(rèn)為人回歸自然才能實(shí)現(xiàn)人性的完美,體現(xiàn)著西方思維的二元對(duì)立;而我國(guó)的晉代詩(shī)人陶淵明對(duì)待人與自然的態(tài)度,則體現(xiàn)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將自然規(guī)律和人的性情聯(lián)系在一起。這樣就可以從他們對(duì)自然的態(tài)度上區(qū)分兩位詩(shī)人的文化信仰。再比如,五四時(shí)期的我國(guó)很多作家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惠特曼和郭沫若、華茲華斯和徐志摩、尼采與魯迅、契訶夫與凌叔華……他們不僅存在事實(shí)材料上的關(guān)系,在文學(xué)風(fēng)格和精神氣質(zhì)也有相似性,這就為探討中西文學(xué)在審美情趣上的一致性提供了便利。但是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卻往往將外國(guó)文學(xué)與中國(guó)文學(xué)割裂開(kāi)來(lái),把外國(guó)文學(xué)史教學(xué)幾乎等同于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鑒賞(研究),這一方面不利于順應(yīng)世界文學(xué)與比較文學(xué)的學(xué)科發(fā)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學(xué)生文學(xué)素養(yǎng)的綜合提升。#p#分頁(yè)標(biāo)題#e# 不僅是中外作品間的審美交感意識(shí)需要加以導(dǎo)引,中西文類也是一個(gè)不能回避的問(wèn)題。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引入比較法,通過(guò)歷時(shí)的和共時(shí)的方法,了解中外文類發(fā)展的歷史和基本特征。這樣可以使學(xué)生在宏觀上把握中西文類發(fā)展的不同軌跡,并由此進(jìn)一步探討中外民族不同的審美心理模式。比如西方的悲劇在文學(xué)殿堂中有著崇高的地位,早在古希臘時(shí)期就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xué)類別,出現(xiàn)了悲劇性的史詩(shī)和戲劇,亞里斯多德也對(duì)悲劇做出了定義,別林斯基認(rèn)為悲劇是戲劇類的詩(shī)的最高階段和冠冕。[5] 而在中國(guó),“悲劇”一詞在辛亥革命前后從西方文化中引入,一些學(xué)者根據(jù)中國(guó)戲劇普遍存在著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認(rèn)為中國(guó)沒(méi)有悲劇;而有些學(xué)者就持相反的意見(jiàn),認(rèn)為中國(guó)雖然沒(méi)有將悲劇作為一種文學(xué)類型確定下來(lái),但是中國(guó)文學(xué)中卻較早地存在著悲劇意識(shí)。在此,問(wèn)題不在于討論悲劇在西方作為一種文學(xué)類型是如何產(chǎn)生的,而是要在課堂上有一種中西文類的比較視閾,引導(dǎo)學(xué)生對(duì)中西文學(xué)類型不可通約性的認(rèn)識(shí)。 二、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過(guò)程中的英文原著引入量嚴(yán)重不足 譯介學(xué)是比較文學(xué)的重要分支,其研究對(duì)象是翻譯和翻譯文學(xué),而對(duì)“翻譯”起直接作用的就是外語(yǔ)水平。雖然在大學(xué)階段,教師不能全面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譯介學(xué)的教學(xué),但是利用學(xué)生公修英文的優(yōu)勢(shì)引入適當(dāng)?shù)挠⒄Z(yǔ)文學(xué)原著,不僅可以增強(qiáng)對(duì)外國(guó)語(yǔ)言文學(xué)和文化性質(zhì)的認(rèn)識(shí),而且可使學(xué)生認(rèn)識(shí)到譯介在外國(guó)文學(xué)學(xué)科中的重要性,也可以為學(xué)生的繼續(xù)深造奠定基礎(chǔ)。但這一優(yōu)勢(shì)卻并沒(méi)被教師所利用,教師們大多拿漢語(yǔ)版的翻譯文學(xué)為范本,以分析作品的思想意義來(lái)覆蓋文本所有的藝術(shù)價(jià)值,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的本體論認(rèn)識(shí)不清。如有些學(xué)生知道簡(jiǎn)•愛(ài),卻不知道Jane Eyre;知道《呼嘯山莊》,卻不知道Wuthering Heights;另外,傳統(tǒng)英文詩(shī)歌中十四行詩(shī)的形式和抑揚(yáng)格音步,在翻譯成漢語(yǔ)之后形式和韻律會(huì)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wú)存。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語(yǔ)言的差異所形成的矛盾是該課程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盡管外國(guó)文學(xué)所涉及的作家作品都與異國(guó)語(yǔ)言相關(guān),但中文系的外國(guó)文學(xué)課程不僅使用中文教材,而且講讀的所有作品為中文譯本。這樣,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實(shí)際上脫離了外文原著,中文系講授的外國(guó)文學(xué)并非真正的外國(guó)文學(xué),而是“翻譯文學(xué)”。 雖然,在“創(chuàng)造性叛逆”中,通過(guò)翻譯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我們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的審美接受,但是這樣一來(lái),我們所教授的外國(guó)文學(xu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翻譯者。 正是由于教學(xué)只能通過(guò)母語(yǔ)講授外國(guó)文學(xué),學(xué)生同樣只能借助母語(yǔ)閱讀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致使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改革遭遇困難。若要從根本上解決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長(zhǎng)期存在的難題,真正走出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的尷尬,在課堂上引入原著作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從文學(xué)史的角度看,英語(yǔ)文學(xué)在世界文學(xué)史上所占的地位也是顯著的。對(duì)以英語(yǔ)為主要外語(yǔ)語(yǔ)種的中文系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都可以比較方便地接觸到英文原版著作。同時(shí),中文專業(yè)的外國(guó)文學(xué)一般都在大二下學(xué)期或大三開(kāi)設(shè),此時(shí)學(xué)生已經(jīng)基本學(xué)完了大學(xué)英語(yǔ)四級(jí)詞匯,一般都具備接受英文原著基本的外語(yǔ)能力。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引進(jìn)英文原著,不僅有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能力,而且至少可以解決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存在的以下兩個(gè)問(wèn)題:第一,更加準(zhǔn)確地解讀作家作品的問(wèn)題。涉及作家作品分析時(shí),若僅憑中文譯本則不利于學(xué)生對(duì)作家作品的解讀,雖然教師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的講解都力求準(zhǔn)確,但因憑借的文本皆為中文譯本,這些譯本因?yàn)樽g者外語(yǔ)水平的差異、文學(xué)修養(yǎng)的優(yōu)劣以及“歸化”手法的運(yùn)用不當(dāng)?shù)戎T多因素,都會(huì)導(dǎo)致文學(xué)作品翻譯的良莠不齊。倘若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引入原著,則能讓學(xué)生在閱讀原著過(guò)程中感知作品,使學(xué)生更加準(zhǔn)確地把握作家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理解作品的藝術(shù)特點(diǎn),也可以提高學(xué)生對(duì)譯本的鑒別能力。第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詩(shī)歌教學(xué)問(wèn)題。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詩(shī)歌教學(xué)歷來(lái)屬于薄弱環(huán)節(jié),其主要原因在于詩(shī)歌的翻譯,詩(shī)人雪萊就認(rèn)為“譯詩(shī)是徒勞無(wú)功的”。詩(shī)歌翻譯之難,導(dǎo)致外文詩(shī)作譯成漢語(yǔ)后節(jié)奏、韻律、聲音之美的改變或喪失。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中講授詩(shī)歌時(shí),盡管選擇的都是名家名作,如果不是詩(shī)歌富有倫理或哲理意義,學(xué)生普遍對(duì)它們沒(méi)有興趣。要改變這種狀況,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通過(guò)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引入原詩(shī)賞析,讓學(xué)生領(lǐng)略外文詩(shī)歌的節(jié)奏、音韻、意象之美,培養(yǎng)學(xué)生對(duì)外國(guó)詩(shī)歌的興趣,提高他們欣賞外國(guó)詩(shī)歌的能力。比如華茲華斯的一首詩(shī)叫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詩(shī)的第一節(jié)是這樣的:She dwelt among theuntrodden ways/Beside the spring of Dove,/A Maid whomthere none to praise/and very few to love……翻譯之后就是:她住在沒(méi)有人到的幽徑,/鴿泉旁邊,/一個(gè)沒(méi)人贊美,少有人/鐘愛(ài)的姑娘。[6] 這樣一來(lái),詩(shī)原先的韻腳完全被打破,音步的重音已經(jīng)完全喪失,而且翻譯之后的文字如同說(shuō)了一段大白話,如果引入原詩(shī),讓學(xué)生在朗讀原詩(shī)的基礎(chǔ)上,然后再對(duì)照翻譯,這樣既可以領(lǐng)略到英文詩(shī)的節(jié)奏和韻律,也可以加深對(duì)英文詩(shī)歌形式和結(jié)構(gòu)的認(rèn)識(shí)。 三、缺乏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的多元性闡釋20世紀(jì)西方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豐富多彩,精神分析、存在主義、原型批評(píng)、新批評(píng)、解構(gòu)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這些理論豐富了西方文學(xué)和文化的內(nèi)涵,外國(guó)文學(xué)也在這些理論的參照下顯示出持久魅力。文學(xué)的流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靠理論來(lái)支撐的,有些作品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環(huán)境中并未受到重視,但是在后來(lái)新的理論解讀下卻能呈現(xiàn)出新的意義。《呼嘯山莊》在當(dāng)時(shí)情況下并沒(méi)產(chǎn)生什么影響,但是后來(lái)在敘事學(xué)和心理學(xué)分析的基礎(chǔ)上,人們才發(fā)現(xiàn)這部作品的價(jià)值。我們的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對(duì)作品的分析,普通采用的是社會(huì)歷史批評(píng)的方法,從創(chuàng)作主體出發(fā)來(lái)推究作品體現(xiàn)的時(shí)代特征和歷史意義。如在古希臘文學(xué)中,把以地母該亞和烏拉諾斯為中心的神話說(shuō)成“表現(xiàn)的是原始社會(huì)雜婚時(shí)期和母權(quán)制時(shí)期的社會(huì)生活”,把以宙斯為中心的神話說(shuō)成是“反映了母權(quán)社會(huì)向父權(quán)制社會(huì)發(fā)展的歷史”。[7]#p#分頁(yè)標(biāo)題#e# 社會(huì)歷史批評(píng)經(jīng)過(guò)馬克思的發(fā)展,形成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意識(shí)形態(tài)向度。當(dāng)前,我國(guó)高校的外國(guó)文學(xué)教材就普遍采用了這種基于階級(jí)分析的社會(huì)歷史批評(píng)模式。 應(yīng)該說(shuō),社會(huì)歷史批評(píng)在對(duì)大量文學(xué)作品的解讀方面取得的成績(jī)是明顯的,而且,這種方法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普適性,能夠通論文學(xué)史。因?yàn)槿魏挝膶W(xué)作品、文學(xué)現(xiàn)象都是特定歷史形態(tài)下的產(chǎn)物,文學(xué)作品都會(huì)帶有一定的階級(jí)性,這樣用社會(huì)歷史批評(píng)方法自然就可以一以貫之地進(jìn)行。但是,文學(xué)作品的價(jià)值取向是多樣的,如果全部采用這種單一模式進(jìn)行分析,就會(huì)流于機(jī)械和蒼白,我們應(yīng)該注重批評(píng)模式的多元化。美國(guó)學(xué)者彼得•威德森認(rèn)為:理論的位能導(dǎo)致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的作家、批評(píng)家以及文學(xué)史家”,通過(guò)界定以及他們對(duì)構(gòu)成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進(jìn)行客觀性研究這兩種有效處理的景觀。[8] 文學(xué)其實(shí)就是在作者、文本、讀者這三者沒(méi)有窮盡的、不穩(wěn)定的辯證關(guān)系中不斷構(gòu)建的,這也就是說(shuō),我們沒(méi)必要用一種眼光去看待文學(xué),要用多元的視角和理論去理解文學(xué)。 比如《哈姆雷特》,不僅可以結(jié)合歷史背景,闡釋人文精神的內(nèi)涵,對(duì)其中的悲劇性進(jìn)行解讀,也可以用精神分析理論或原型批評(píng)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再比如,《等待戈多》不僅可以從現(xiàn)代主義文化的角度解讀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人的精神危機(jī),也可以從存在主義角度分析“戈多”這一文化意象所代表的最終旨?xì)w。 四、結(jié)語(yǔ) 外國(guó)文學(xué)的課程目的應(yīng)該讓學(xué)生掌握世界文學(xué)的發(fā)展規(guī)律,掌握一些重要的文學(xué)思潮,了解各民族文學(xué)的大體特點(diǎn),這樣才無(wú)悖于外國(guó)文學(xué)中的“比較文學(xué)”性質(zhì)。但是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的學(xué)科屬性認(rèn)識(shí)不清或是漠視,無(wú)法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比較文學(xué)觀念,學(xué)生不能針對(duì)文學(xué)問(wèn)題進(jìn)行比較文學(xué)層面的思考,這更不符合學(xué)科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正視當(dāng)下高校中文專業(yè)外國(guó)文學(xué)教學(xué)問(wèn)題,最終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推進(jìn)課堂教學(xué)改革,提高教學(xué)和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這需要外國(guó)文學(xué)教育工作者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時(shí)刻保持問(wèn)題意識(shí),不能為了完成課時(shí)量而忽略這些問(wèn)題,或者只顧伏案鉆研,讓新事物、新思想成為了教師個(gè)人享受的科研成果,這不僅影響對(duì)學(xué)生文學(xué)思維的拓展,也會(huì)使外國(guó)文學(xué)課程逐漸失去特色。